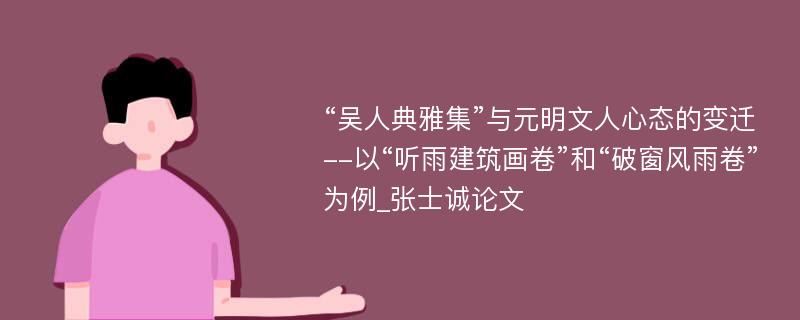
元明之际吴中文人雅集方式与文人心态的变迁——以《听雨楼图卷》、《破窗风雨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吴中论文,文人论文,为例论文,听雨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0)01-0078-06
《听雨楼图》是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香光居士、黄鹤山樵,吴兴人,“元四家”之一)为江南名士卢士恒所建“听雨楼”所作的一幅画,此画作于至正二十五年。《破窗风雨图》是王立中(字彦强,生卒年不详,江苏苏州人,元代画家)为刘易(字性初,杨维桢弟子)所作的一幅画,此画作于至正二十六年。这两幅画在当时的吴中文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呼应,相继有十八位文人为《听雨楼图》题诗,如张雨、倪瓒、王蒙、苏大年、饶介、周伯温、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张羽、道衍、高启、王谦、王宥、陶振、韩奕等[1],形成了《听雨楼图卷》。《破窗风雨图》的题诗者更多,有陆居仁、杨维桢、钱鼐、王国器、张翨、李绎、钱惟善、张庸、易履、张端、张昱、金絅、徐一夔、牛谅、朱武、杭琪、钟虞、韩元璧、钱岳、徐汝霖、张羽、董存、杨基、李江汉、高子仪、冯恕、赵俶、龙云从、沈庭珪、李讷、丘思齐、岳偷、雅安、何恒、孔思齐等三十七人,形成了《破窗风雨卷》。这两幅诗卷最大的特点是,非同时同地的同题唱和。如《听雨楼图卷》,张雨是“樵人张雨为庐山甫题,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1],倪瓒是“至正廿三年,岁在乙巳,卢士恒携至绮绿轩示,趣走笔次贞居外史诗韵以寄意,云陶蓬寄亭中人暨诸名胜当不黯然也,后十又八年四月九日瓒记”[1],鲍恂是“至正廿五年四月一日樵李鲍恂书”[1]。再如《破窗风雨卷》中诗人的落款,“至正甲辰嘉平初,吉东维叟会稽杨维桢记”[1],“至正二十有三年龙集癸卯冬十二月朔旦记”[1],“至正乙巳秋八月十五日,会兰雪聘君于铁崖先生小蓬莱,见示此卷,遂为之赋,金盖山人钱岳”[1],“洪武癸丑三月晦日钱塘陈彦博书于南湖寓所”[1]等。
关于这两幅图的题咏,不惟人数众多,规模较大,其方式也迥异前人,以一种“异地同调”的方式进行唱和。这种特殊方式的形成绝非偶然。它们的形成,既标志着元明鼎革之际,文人题咏方式的新变,也表征着新的历史环境下文人心态的变化,以及在此一心态影响下的文学思想的变迁。
一、雅集结社的变相延续
雅集结社是贯穿元代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从时间上看,这种现象越到元代后期越普遍,从空间上看,这种现象主要产生于吴中地区。至于其产生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元代的建立,不实行“文官制度”,导致唐宋文明突然中断,其各种统治政策不利于汉族知识分子,汉族知识分子和中央政权始终处于一种“隔膜”状态),也有经济上的(吴中地区的富庶,士商的普遍合作)。但是,这种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现象,是文人心态演变的结果。雅集结社以赋诗唱和为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结社分韵赋诗和同题赋诗。从元代诗坛整体上看,最具代表性的雅集结社都出现在元末的吴中地区:以顾瑛、杨维桢为代表的“玉山雅集”和以高启为代表的“北郭诗社”。
“玉山雅集”是元末吴中地区规模最盛、历时最长、对后世影响最强的文人盛会。以玉山草堂主人顾瑛为组织者,以文坛盟主杨维桢为精神领袖,以“玉山佳处”为根据地,“玉山雅集”基本囊括了当时吴中地区所有的知名文人,如张雨、倪瓒、张翥、李孝光、黄公望、陈基、袁华等①。其主要活动时间始于至正八年(1348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入吴开始衰落,在这近十年的时间中,见诸记载的大小集会不少于几十次。他们或饮酒赋诗、觞咏酬唱;或挥羽清谈,探究玄理;或赏鉴古玩,濡墨作画;或携酒远游、纵情山水,同时伴之以轻歌曼舞、美酒佳肴。至正八年一次草堂聚会的盛况,杨维桢有《雅集志》记载:
右《玉山雅集图》一卷,淮海张渥用李龙眠白描体之所作也。玉山主者为昆山顾瑛氏,其人青年好学,通文史,好音律,钟鼎古器、法书名画,品格之辨。性尤轻财喜客,海内文士未尝不造玉山所。其风流文采,出乎流辈者,尤为倾倒,故至正戊子二月十有九日之会,为诸集之最盛。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杨维祯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者,为天香秀;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旁侍而指画,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琼英也。一时人品疏通隽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童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扬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有发,是宜斯图一出,为一时名流所慕艳也。[2](P46)
类似的聚会还有很多,且都有记载。玉山文人还编撰了《草堂雅集》、《玉山名胜集》、《玉山纪游》、《玉山倡和》、《玉山遗什》等诗文总集存世。
稍晚于“玉山雅集”的“北郭诗社”,是以高启为中心的另一个吴中文人集团,其存在时间主要集中于张士诚统治平江时期②。据高启《送唐处敬序》载:
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交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余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辨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湮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岁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窃尝以为一郡一邑,有抱材之士,而出于凡民者,皆其地之秀也。[3](《凫藻集》卷二)
上述七人,加上宋克、吕敏、陈则,就是后世所谓的“北郭十友”(或“北郭十子”)。
“玉山雅集”和“北郭诗社”从时间上看,并非历时性的继承关系,“北郭诗社”活动频繁之日,“玉山雅集”仍在继续,只是其规模大不如以前③。同为吴中文人集团,这两个文人群体的成员还有联系,如“北郭”中的杨基、周砥、高逊志、宋克等人,就与顾瑛、杨维桢关系密切。其中周砥、高逊志是“玉山雅集”成员,杨基尝跟杨维桢在松江受学。杨维桢说:“吾在吴,又得一铁矣。若曹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4](P7329)这个“又得一铁”就是指杨基。
以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吴为分水岭,“北郭诗社”渐渐成为吴中地区最重要的文人集会。和“玉山雅集”相比,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活动方式呈现了一种从“世俗化”向“文艺化”④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北郭诗人多为张士诚集团幕僚⑤,参与主体或以官僚为主导,或是纯粹的文人雅士。从客观上讲,他们委身于张士诚幕下,行为必然有所收敛;从主观上讲,高启等人性情和顾、杨等人也截然不同。所以,其活动方式更类似于传统的文人雅集聚会,无非诗酒风流、更迭唱和、山川游览。如王行在《跋东皋唱和卷》中记载:“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茗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5](《半轩集》卷八)这里没有“玉山主人”刻意修建以供文人耍玩的“玉山佳处”,也没有玉山文人肆无忌惮的纵情狂欢,北郭诗人的活动更加精雅,呈现出一种“文艺化”的倾向。
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开始攻打张士诚所据郡县。从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到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围攻苏州达十个月,高启等一批吴中文人均困于城中,前后十个月不得出⑥。苏州城破,张士诚政权覆亡,士诚自缢而死。同年,朱元璋开始实行了打压吴中文人的政策。朱明王朝建立后,吴中文人相继被流放、征召,开始了飘摇而惶恐的命运,“玉山雅集”和“北郭诗社”基本消歇。熟悉此一背景,我们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听雨楼图卷》和《破窗风雨卷》的形成及其所孕育的诗学意义。
前文已述,《听雨楼图卷》和《破窗风雨卷》是由众多吴中诗人在同一幅画上的题诗,但与玉山文人和北郭诗人题诗方式的不同在于:以一种“异地同调”的方式进行题咏。在前两个时期,诗人们身处的环境还相对稳定,于是得以在同一时空下进行唱和题咏,观诸玉山文人和北郭诗人的记载,他们留下了大量同时、同地、同题的诗词唱和。玉山文人甚至以“争才斗艳”的方式进行作诗大比拼,以罚酒的形式比拼高低,以此为乐。北郭诗人也有过这种方式,如时为淮南行省参政的饶介,曾以《醉樵歌》为题,向吴中文人征诗,张简第一,高启次之,饶介赠张简黄金十两,高启白金三斤,传为一时佳话。而到了张士诚政权覆亡之际,随着朱元璋对吴地吴人实行高压政策,吴中文人从此命运多舛,相继被杀戮、贬谪、流放、徙濠、征召,天涯一方,各自飘零,再也没有此前得以共聚的环境,只能借助于这种异地、异时、同题题咏的隐晦方式来“神交”彼此,于是才有了《听雨楼图卷》、《破窗风雨卷》的出现。可以说,这两幅诗卷的形成过程,是“玉山雅集”和“北郭诗社”的变相延续,是吴中文人在失去固定场所聚会的条件下又想回到过去而被迫采取的一种隐晦策略,既体现了吴中文人对雅集聚会的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在新环境下身各一方的悲哀。
二、雅集文人心态的变迁
玉山文人、北郭诗人、《听雨楼图卷》和《破窗风雨卷》中诸诗人,在人员结构上,并非一个群体。但这三个群体中的人员多有重叠,如杨维桢,既是玉山文人,也是《破窗风雨卷》的作者之一;再如高启、张羽等人,既是“北郭十子”,也是两图的题诗者,有的甚至贯穿了这三次活动,如僧人释道衍。从整体上看,这三个文人群体,既有历时性的新老更替,也有共时性的相互来往,同时还有人员上的交叉重叠现象。
关于元明之际吴中文人的心态研究,左东岭提出了“旁观者心态”⑦一说,从整体上把握了吴中文人在元明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细而论之,由于元明之际的吴中文人相继经历了三个统治时代:元末、张士诚入吴、明朝建立。在不同的阶段,“旁观者心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有不同,于是其内涵又有相当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玉山雅集”阶段——庆幸与颓废。“玉山雅集”基本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为享乐,后一时期为避祸,但两个时期都不乏饮酒作乐、歌儿舞女的纵情狂欢。“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局,加上各地农民起义带来的烽火四起,玉山文人既为能在“玉山佳处”的诗酒风流而备感庆幸,同时随着局势的紧张,也有着对未来不可知的恐惧和对当下享乐一去不返的担忧。在乐而忘忧的背后,恰恰深藏着一种颓废与恐惧。如李瓒说:“夫人生百年,忧患之秋多,宴集之日少,而况友朋南北东西迄无定居,则今日之簪盍乎其偶然哉?”[2](P76)顾瑛说:“缅思烽火隔江,近在百里,今夕之会,诚不易得,况期后无会乎?吴宫花草,娄江风月,今皆走麋鹿于瓦砾场矣。独吾草堂,宛在溪上。予虽祝发,尚能与诸公觞咏其下,共忘此身于干戈之世,岂非梦游于已公之茅屋乎?”[2](P144)他们用大量的诗歌表达了这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
袁华《郑丈招隐》:人生几何胡不乐,兰亭梓泽俱寂寞。虚名煊赫鼠在橐,慎勿苦被微官缚。[6](P1107)
李瓒《鬓丝行》:人生百年宁有待,富贵功名岂长在。何如日饮金樽酒,醉学山公归倒载。[6](P831)
僧宝月《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分韵赋诗得阑字》:惊风起山河,断鸿行路难。嘉会岂云易,长歌为辛酸。[2](P78)
“北郭诗社”阶段——闲适与放达。玉山文人们出于对未来命运的不可知,在“及时行乐”中难免颓废与恐惧。而到了北郭文人时期,由于张士诚政权的保护,一时间,吴中地区显得“歌舞升平”。张士诚对文人十分礼遇,其手下的蔡彦文、饶介也都是文人之士,尤其是饶介,更是以书生的姿态和吴中文人相酬唱,吴中文人多纷纷入幕。吴中文人在张士诚的保护下,其生存状态相对稳定与安宁,如高启作于至正二十二年的《游天平山记》所云:“今天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3](《凫藻集》卷一)“在上者”就是张士诚。他们纷纷用诗歌表达了在张士诚政权下的闲适与放达:如杨基《梁园饮酒歌》:
东藩诸侯遂见徵,白璧玄纁贲林薮。屡辞不获始强起,野服长揖坐谈久。青闺漏箭传午滴,紫幕炉薰散春牖。时翻玉检题鸾凤,复赐银笺篆科蚪。[7](P109)
再如徐贲《题南窗》:
南窗对高树,中夏绿以枝。偶然倚窗坐,值此凉风时。我非傲世者,寄身聊在兹。有酒但尽醉,余事无所知。[8](《北郭集》卷二)
又如张羽《于书簏中得高吹台所寄诗遗稿》:
忆昔吴苑游,文采众所推。名谈析妙理,华襟吐芳词。予时侨城北,高斋临清池。焚兰延佳月,对酒弹清丝。[9](《静居集》卷一)
需要说明的,至正二十六年以后,张士诚政权被朱元璋彻底包围,北郭诗人的心里也多少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表现出深深的惶恐与无奈。张羽在《续怀友诗序》中说:“予在吴城围中,作怀友诗二十三首,其后题识四人,乃嘉陵杨孟载、介休王止仲、渤海高季迪、郯郡徐幼文也。时予与诸君及永嘉余唐卿者游,皆落魄不任事,故得流连诗酒间,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9](《静居集》卷一)
题《听雨楼图》、《破窗风雨图》阶段——愁苦与压抑。《听雨楼图卷》和《破窗风雨卷》中的诗作,具体的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但是可以断定的是,这些诗作最早也作于至正二十五年⑧(《破窗风雨卷》都作于至正二十六年以后,还有的是入明之后的作品)。这个时期,道路阻隔,烽火连天,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人”困守苏州,基本无法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诗歌表达了对朋友的怀念,对自由的渴望,心情蒙上了愁苦与压抑的色彩,如张羽所作的《怀友诗》组诗,情思凄婉,哀怨悱恻。这一情况,到了入明之后更为严重,由于朱元璋实行的高压政策,他们更是天各一方,四处飘零,只能靠“异地题咏”的方式交流感情,相互慰藉。
三、雅集文人文学思想的变迁
在三个政权的更迭中,在烽火连天、干戈四起的环境下,吴中文人的心态经历了多重演变,其“旁观者心态”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环境中和不同心态的支配下,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不同,表现在文学上的情感基调、审美情态、艺术风格也有诸多不同。
“玉山雅集”时期,玉山文人表达了对生存的庆幸、生命的张扬、及时行乐的讴歌与礼赞,但在对酒当歌、把盏交欢的背后,却又透露着深深的悲哀,在自娱、自慰,把作诗逞才当做一种生命存在方式的同时,又表现出颓废的情绪。既然作诗是一种生命的寄托,那么“以诗存名”以图不朽才是他们内心真正企及的,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作诗,极尽所能地渲染才艺。他们在庆幸中有悲哀,在放纵中有颓废,《玉山名胜集》、《玉山纪游》、《草堂雅集》、《玉山倡和》、《玉山遗什》中的大量诗歌,在情感基调上,都呈现出一种感伤、悲哀、压抑、幻灭的色彩。同时,玉山文人经常以群体性“作诗比赛”的方式雅集聚会,其诗歌难免受到此种“剧场效应”的影响。诗人们在攀比作诗的环境中,不遗余力地展现才气和技艺,大量用典,对仗谨严,使用生字、僻字,诗歌风格纤浓而绮艳,多选用结构谨严的七言律诗力图拔高诗歌的艺术性和表现力。这种以牺牲诗歌思想性为代价的结果是:诗歌单调而重复,思想孱弱空洞,流于形式与技巧,既缺乏“刚健有力”的社会写实,也缺乏“真挚动人”的情感抒怀。兹以《玉山草堂题诗》中的两首为例:
袁华:玉山之中草堂深,石床萝磴秋阴阴。华林月白鹤在野,水馆风情鱼听琴。底须封侯醴泉郡,自好躬耕梁父吟。碧桐翠竹吾所爱,他日杖履重幽寻。[2](P21)
张天英:结构郊居胜杜陵,草堂幽性喜重乘。白泉出洞浮金粟,碧树当帘挂玉绳。坐看中天行古月,炯如万壑浸清冰。浣花风致今犹在,日日轩窗一醉凭。[2](P19)
两诗无论从诗性、诗情,还是审美效应上都大体一致。至于其他人同题的诗作,其内容也是千篇一律,无鲜明的个性。当然,这些诗歌的价值不在诗歌本身,更多在于其彰显了一种生命内涵和生活方式。在玉山文人眼中,这种性灵的、艺术的作诗方式比作诗内容更有魅力。
身处张士诚统治下相对稳定的平江,北郭诗人得以在闲适放达的心境下进行创作。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感怀抒情、歌咏自然的诗,其最著名的《青丘子歌》就作于这个时期。再如杨基的《结客少年场行》:“情如飞絮任悠扬,心与游丝共短长。花底若教连日醉,座中犹可少年狂。新调锦瑟争传谱,巧制罗囊别贮香。衣以凤翎分缝织,带将蛇角遍鞓装。豪名独擅秋千社,侠气平欺蹴踘场。白璧一双酬剑客,明珠百斛买胡娼。金丸挟弹章台左,宝骑闻筝太液旁。梅子短墙羞掷果,桃花深坞笑分浆。每嘲春比人先老,不信愁如海叵量。犹有旧时桃李梦,尚随蝴蝶到辽阳。”[6](P106)此一时期,吴中文人的诗歌表达了狂傲的人格、真实的性情、丰富的趣味。在题材上,他们写了大量的抒怀诗、写景诗、纪游诗、状物诗,语言清新,意象清丽,充满情趣。在诗体上,他们众体皆备,乐府、律诗、绝句,五言、七言、杂言,形式多样。
至正二十五年开始,平江局势突然紧张,以高启为首的北郭诗人困守其中,通过对《听雨楼图》、《破窗风雨图》的题咏,表达感情,慰藉心灵。这两幅诗卷仿佛成了一场吴中文人的题咏盛会,在压抑与愁苦的心理状态下,这些题诗充满着悲哀、惨淡、愁苦之意。如《听雨楼图》题诗:
高启:春雨霭江郭,鸠鸣朝梦余。楼中风飒至,烦抱淡云除。历历树头乱,萧萧窗影虚。如何门外水,泥淖没行车。[1]
王谦:山风满楼来雨脚,耳底萧萧生远情。还丹化鹤去句曲,破屋无人住洛城。酒停深夜苍灯在,帘近余寒湿叶鸣。板上漆书空爪迹,绕簷依旧落春声。[1]
马玉麟:江雨飞来夜气澄,小楼高处冷于水。声留蕉叶频倚枕,影乱簷花独对灯。远客异乡生白发,故人今夕拥青绫。致君尧舜愧无术,思入湖天睡未能。[1]
“树头乱”、“窗影虚”、“破屋”、“空爪”、“影乱”、“白发”等意象的使用,凝聚了诗人们愁苦、悲哀、压抑的感情。再如题《破窗风雨图》诗:
杨基:十载江湖梦,满空风雨宵。窗虚声易入,灯暗手慵挑。竹洗千竿翠,林喧万古潮。东北枯渴甚,藉而倒天瓢。[1]
赵俶:客窗读书过夜半,江上长风将雨来。茅屋声和木叶落,竹床笑对灯花开。何人鸡鸣解起舞,此际蜨梦付衔杯。我欲哦诗慰寂寥,衰笠敲门步绿苔。[1]
何恒:一室萧然四壁空,客怀况复风兼雨。湿沾衣服愁仍重,清到肌肤句转工。知名肯随时变化,甘贫岂为道污隆。夜深尚对义皇易,应怪寒灯不耐红。[1]
韩元璧:刘郎读书如学仙,朝不出户夜不眠。时闻破窗风雨急,政自凝心对圣贤。尚书汪公下帷处,敬亭山色青连天。执经念子最清苦,层层跻道心相传。鸡鸣喈喈天欲暮,疏椿潇飒寒声度。庭前飘麦总不知,屋上卷茅宁复顾。人生穷达那可知,玉堂金马自有期。青藜还忆夜相访,却忆破窗风雨时。[1]
这些题诗,在情感基调上,愁苦哀怨;在艺术风格上,沉郁压抑;在表现手法上,曲折婉转。通过对《听雨楼图》、《破窗风雨图》的题咏,靠着这种“异地同调”的方式,他们得以在不同时空下“神交”彼此,引发共鸣。在烽火连天、战火纷争的时代,吴中文人以这种耐人寻味的隐晦方式抒发了对过往的怀念,对自由的向往,也表达了“却忆破窗风雨时”的无奈与悲哀。到了洪武年间,当道衍看到《听雨楼图》时,不禁发出感叹,“胜国之际,兵变之余,前辈翰墨存者无几,间或获一见如遇醀彝兕敦,不由不使人惊艳也,听雨楼诗,句曲外史及一时名流所作,词翰兼美,亦稀世之宝也。吴中卢士恒父一日出示于予,卷中作者多予故友,兹觇其翰墨,俨若现其风度,士恒宜珍藏之,勿轻示于人焉。洪武二年正月二日”[1]。足见曾经的“故友”在题诗时心情的复杂与悲哀。
四、结语
从“玉山雅集”时的颓废放纵,到“北郭诗社”时的闲适放达,再到题《听雨楼图》和《破窗风雨图》时的愁苦压抑,吴中文人的“旁观者心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在不同心态的支配下,吴中文人雅集结社的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他们对文学的理解以及使用的表现手法也不同。随着朱明王朝的建立,吴中文人面临的外部环境渐趋冷酷紧张,其生存状态更加严峻逼仄,其心态更加隐晦复杂,文学思想也更加丰富。了解此一状况,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把握元明之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施力于“文人心态”,从而引起雅集方式与文学思想的变迁,进而解释吴中文学由盛转衰的关键之所在。
注释:
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列举有“玉山草堂饯别寄赠诸诗人”,共三十七位。而实际上的参与者,远不止于这个数。据杨镰先生统计,玉山草堂文人约有百人,作诗总数达5100首左右,参见其《顾瑛与玉山雅集》一文(《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9期)。
②据欧阳光先生考证,“北郭诗社”结社时间应为至正二十年(1360),其依据是高启《荆南唱和诗后序》中有关于此年高启与周砥相识,且有“相论诗甚契”的记载,见其《北郭诗社考论》一文(《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③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攻破平江,玉山草堂各景点遭到破坏,顾瑛奉母携家到了吴兴,“玉山雅集”开始衰落。
④这里使用“文艺化”一词,并非文论中的术语,只是借喻“北郭诗社”更像一个纯粹的文人诗团,其活动更多以诗词唱和为主。而“玉山雅集”最大的特点在于“雅俗共赏”,雅集过程中有大量的声妓参加,同时还有诸如听戏、度曲等活动。
⑤陈基任学士院学士,张宪为枢密院都事,陈秀民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陈汝言任藩府参谋,钱用壬任太尉府参军,鲁渊任博士,苏大年为参谋,杨基为丞相府记室,唐肃为嘉兴路儒学正,郑元祐任平江路儒学教授,戴良任起居郎,张经任松江府判官,等等。高启、余尧臣、张羽、徐贲、王行、王蒙、宋克、邵亨贞,也都可能接受过张士诚所授的官职。
⑥如高启《兵后逢张孝廉醇》描述:“问我胡为亦憔悴,十月孤城陷围内。”(《高青丘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⑦左先生在《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中把“旁观者心态”分为三种表现形态: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责任感的淡漠;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生活态度的闲散和个性的放任。
⑧需要说明的是,在《听雨楼图卷》中,张雨的《听雨楼》作于至正八年,倪瓒的和诗作于至正二十三年。其余的和诗都是《听雨楼图》成形后所作,这些和诗才是分析《听雨楼图卷》的主体,上述的说法只是为了突出后面和诗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