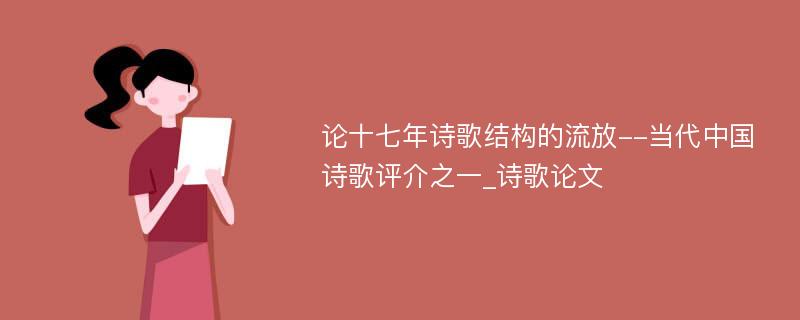
论十七年诗对结构的放逐——中国当代诗歌检讨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诗歌论文,结构论文,论十七年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评论界早已注意到了十七年的许多诗在艺术上的失败。而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是缺乏“诗”的结构,亦即缺乏与诗的体式相吻合的能够承载“诗”的内容的艺术结构。
诗的成败主要不在于表现了什么和不表现什么(十七年诗的失败主要是在于它太计较表现什么,多数时候是只看重表现什么),而在于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去表现,在于是否以成功的组织方式释放并框定了诗人对生活的认知,并通过这种组织方式去激活后人的接受灵感,以达到对上代人留在诗中的情感与思想的认读。这就是结构的功能。
十七年的主流诗歌恰恰是丧失了这种功能。我们今天在读到的大量的当时的诗歌中,很难遇到因出色的结构运作而引发出的阅读快感。我们通常能够看到的是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与在小说、散文或戏剧中见到的并无二致。这就是说,当时的诗人在对结构的认识与运用上与小说家们没有差异,这便是诗人遗失了“诗”的根本原因。古人将文学创作分为诗、文两大类,这两大类在构思上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文”(含散文、小说等)因更注重外在描述而倾向于大众化的话,那么“诗”则因更注重内情展示而带有精英化色彩。表现在结构上,它更需要有化博为精、化散为聚、引浅入深的功能。一个小说家可以引导他的人物作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一个散文家也可以作一次长距离的放足,但一个诗人只能将“距离”截断,在戛然而止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因为“人们要求的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突然领悟那更高、更富哲学意味、更普遍的某个真理。”(郑敏语)这“某个真理”是诗人经过长时间的人生体验所获得的灵动一闪。它往往带有稍纵即逝的特点。而它要想以诗的方式得到永恒。最可靠的途径是获得一个有生命的依附体。这个依附体就是“结构”。如果说通过对某种生活的流程或情节的叙述即能完成一篇(部)“文”的结构的话,那么对于“诗”的处理就没法来得这么干脆。它的结构的背后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而其本身则又是对于生活与诗人情愫的一种意义的安排。结构不构成诗的内容,但“内容”必须有效地弥散在结构的逻辑组织里才有意义。一个诗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与丰富的人生体验,但要把它们变为“诗”的内容还必须经过一次诗艺的催化。这需要一个或短暂或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受到难以名状的煎熬。当那些无序的素材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呈现于某种逻辑的安排里而变得有序时,结构就诞生了,素材便活了,诗人也便解脱了。因此,结构不是一个外在于内容的皮囊,而是化入内容之中的诗的灵魂。结构既不属于内容,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形式的范畴。它是超乎“内容”和“形式”之外,又使得“内容”与“形式”弥散于其中并显示其各自价值与意义的特殊存在。
结构的诞生是创作的关键。
二
结构的诞生是一个惨淡经营的过程。诗人积累的良好素材如果找不到一个好的结构形式,就不会写出一首好诗。十七年诗的观念恰恰相反。它看重的只是题材本身(表现什么),以为只要正确地表现了什么,一首诗就完事儿了,结构自然地就存在于诗中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因了这种误解而使当时的诗坛造就了轰轰烈烈的创作局面与成千上万的“诗人”。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个局面与那些“诗人”其实极大程度上与诗无关。因为其多数“诗”作放逐了诗的结构,而放逐了结构也就放逐了诗。
十七年诗歌风范是在吸收以北方民族为主的中国民间文艺营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风范表现在结构上,就是以逐渐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治道德体系为指针,按规定的政治思路和人们熟知的政治道德风范或客观事物发展与事态演进的外在逻辑为线索,安置素材,构架作品。这是一种最讨巧的“结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具备这种素质。因此,建国后十七年(还有文革开始后的10余年),最便宜的是诗人,最好作的是诗歌。“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大爆炸和诗人大出笼几将这个命题敲定为真理。十七年诗的这种结构思维实质上是一种机械的构思模板,任何题材、任何内容的“诗歌”都可以塞进模板中“克隆”出来。因此,战争回忆诗、抗美援朝诗、农业合作化运动诗、工业建设诗……,出笼后都是一个色调。它无须创造,也无能创造。
真理是大众的,而对于创作某首诗的某个诗人来说,它又必须是“某个”的。因此,诗人必须表现“某个真理”。要恰到好处地表现这“某个真理”,就必须寻找“某个结构”,因而这个结构对表现某个“真理”具有惟一性。十年诗歌的结构是万能的,诗人所表现的“真理”也货真价实的是大众的。它抽掉了诗的结构的惟一性与所表现真理的“某个性”(特殊性),而使诗成为一种不折不扣地流行色。每一个政治运动的出场,必将引出大量以此为主题的诗章。这些诗章不是经过诗人的情感的过滤和诗艺的发酵,而只是一味地跟着时代的感觉走。对于某个群体或群体中的个体的描写,也无需进行独特的思考与艺术的把握,只需取政治集团的定义或公众的普遍认知即可。如汗牛充栋的工业诗和农业诗对工人和农民的抒写,依据的就只是“工农联盟为主体”的政治内涵。诗人们以此为构思的模本,填进去工人和农民的工作流程及衣着打扮,喊几句他们伟大“我”渺小的话语,一首诗就制作完毕。而事实上,工人或农民可以有无数种写法。作为物象或典型,其含纳的意义可能有多种指向性,靠着诗人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寻找到的独具的艺术结构,完全可以写出多个各具韵味的“这一个”。“森林诗人”傅仇写了许多赞美伐木工人的诗篇。伐木工人是劳动人民,应当歌颂。但并不是他们的每一次劳动都能带来正面价值。如果站在1998年“三江抗洪”的视角上看,他们的不少劳作却可能成了“恶”的象征。那种由生活表象出发进入到对哲理和理想的阐释的能力是诗人应该具备的素质。坦率地说,十七年的许多诗歌作者不具备这些素质。他们的思维是惰性的,而通过这种惰性又在诗歌中复制出众多的有惰性思维的读者。
三
如上所述,十七年诗歌在结构上有两大特征:一是利用流行的政治思维为构思模板去进行“克隆”;一是依据事物发展或事态演进的外在逻辑去安排构思。这实际上是新诗结构的两大顽症。这两大顽症其实是二而一的毛病。其产生的根源是惰性思维和非诗理念。惰性思维使其无需去创造性地思考,只拿“现成的”(“理”或“事”)来套即可。非诗理念,使其不把作诗当作诗,只当作文谈天或写思想汇报,或者干脆就不知诗为何物。一般诗人姑且不论,即使声名赫赫如郭沫若、冯至、艾青(国际题材诗除外)、田汉、何其芳、阮章竞、王辛笛等等,也莫不曾害此顽症。为了增加我的判断的可信度,请允许我在这里摘引一段诗句:
此事发生在,今年一月末,
江南春草生,河北坚冰弱,
某日已深夜,远生来访我,
寒暄才几句,忽然双泪落。
问他“妻可好,何以心情恶?”
他说“林娴好,自己也还可,
只是整风时,狠狠受批驳。
……
能否对组织,替我说一说?”
我说“不用说,党是很正确,
狠狠批评你,待你却不薄,
没有当‘右派’,把你相斗搏,
你该自省察,苦口是良药。
快快应号召,离开办公桌,
走向工农中,与他人共苦乐。”
这是田汉1958年2月8日作的诗《歌一九五八年之春》首节的摘录部分。写的是诗人与深夜来访者的夜谈。在写作体式上,它是典型的十七年(或建国后三十年)的写法:排行整齐(也可以不整齐),有节奏,有韵脚,读起来流利上口。总之,在外形上打扮得十分像“诗”。结构也是当时主流诗歌常用的顺口溜式的叙事体:零距离的叙述方式、叙述时间和叙述长度与现实生活中诗人与“远生”的夜话同构。但它不是诗的结构,至少不是一个成功的诗的结构。诗的结构必须掐断流程,在“乍迸”“突变”或“山重水复”中求得。那种平铺直叙、一目了然的结构方式只能交给小说、散文或其他什么文体。虽然各种文体都要传达信息,都要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或情感的震动,但诗歌所给予的更为强烈、更为集中,其突出特点是带给读者的“领悟”是突然的。这种效果的获得不是靠叙述的平稳或叙述的长度,而是靠叙述的陡峭或结构的张力。正如“九叶”诗人郑敏所言:“诗的内在结构是实现诗的这种特殊功能所必须的有机组成部分。一首诗可以不押韵,却不能没有这种诗的内在结构,修辞的美妙,细微的观察,音调的铿锵都还不足以成为构成好诗的充分条件,正像美丽的窗格,屋脊上的挂铃都还不能构成富丽的宫殿。只有结构才能够保证一首诗站起来,存在下去。”[2](P23)像《歌一九五八年之春》所代表的大量诗歌的那种写法,实际上是放弃了诗的结构,而取了“谈天”、“标语”、“报告”等叙述方式。意思虽然明白晓畅,线索虽然十分清晰,所要传达的信息也都传递了出去,但就是没有让读者产生心灵的震荡、智慧的启迪或审美的愉悦。一句话,读者就是没有同诗同诗人产生心灵的共振。他们惟一的反应是“知道了”诗人所说的那事儿,别的感觉全无。
四
由于惰性思维和非诗理念的影响,许多诗人已经丧失了进行诗的艺术构思的能力。咀嚼着他们的诗长大的读者们也丧失了将诗当诗欣赏的能力。大伙儿径直将诗当作与散文、小说、工作报告等一样的东西来看待。只求目无遮障,一览无余,深忌隐秀衔彩,曲径通幽。20世纪80年代那场堪称新诗史上争鸣之最的“朦胧诗”之争正是缘于这种文化心理而产生的。“朦胧诗人”觉得作诗不可直挺挺如作文,而应采用诗的结构。他们普遍采用了“距离化”的方式进行构思,即不约而同地与生活表象拉开距离(而非其前辈和同代诗人之“零距离”叙述的办法)。由于“距离化”而引起了当时读者的误会。事实上,“距离化”不应该遭到我们的唾充。它应该是一切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和审美属性。宗白华先生曾在《美学散步》中说;“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距离化,间隔化。”“朦胧诗”人们大量运用象征、意象、隐喻、错觉、梦幻等方式进行艺术构思,有意地与生活表象拉开距离,创造“距离美”。这是他们的成功之处,是他们对多年来新诗粘于生活表象,因而使诗过实过直过于平面化的倾向的反拨。
“距离化”其实就是“陌生化”。“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俄国形式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然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3](P45)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论不仅在俄国文艺学界,而且在世界文学论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文艺创作不能够照搬所描写的对象,而是要对这一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陌生化原则是艺术加工和处理的必不可少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要将本来熟悉的对象陌生,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与政论等其他文体作品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有无审美感受。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让人们通过阅读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在这一感觉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感。陌生化手段的实质就是要设法增加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
十七年诗人多数不懂得陌生化原则,(或懂得却不能遵守),因而其诗作绝大多数时间都徘徊在审美的跑道之外。它是那样的“忠实”于生活,以至于亦步亦趋,失去自我。这种对于生活的表象的愚忠,其实就是对艺术的背叛。艺术不需要将生活的原貌搬入它的殿堂,它需要的是变形的一族。歌颂新中国,表现土地改革,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表现工业建设的腾飞,反映抗美援朝,表现部队生活,表现基层人物,表现集体化道路,描写祖国山水……这些曾经燃烧着激情,披露着肝胆的诗篇,今日已覆盖着沉甸甸的历史尘埃。由于没有结构的保证,这些诗也就没有能够“站起来,存在下去”。它背叛了艺术,就只能换来艺术的背叛。
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刻薄尖酸不留情面的印象,我这里举新民歌中无名作者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其实新民歌是50年代诗歌创作观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的所有长处和短处其实与十七年绝大多数诗人的绝大多数诗歌并无二致。新民歌崛起于一个浪漫主义时代。它的作者和其他有名有姓的作者一样,胸中回荡着豪迈的激情。诗人们把自己的位置定在浪漫主义的坐标上,而且创作了大量豪迈“诗句”,如“将它扔进太平洋,地球又多一个洲”(写南瓜),“粮食堆到白云天,凑着太阳吸袋烟”(写丰收),“白菜长成一搂粗/扛回一棵进食堂/九十九人吃一顿/还剩十斤零八两”(写白菜)。这些“浪漫主义”诗章颇有浪漫主义豪情,但缺乏浪漫主义精神,更与浪漫主义创作原则背道而驰。因为浪漫主义同样反映真实情感和生活本质,而不是靠吹牛撒谎来吓唬民众。新民歌作者不懂其中奥妙,以为依样喊几句大话就可成事儿。事实上,浪漫主义作为一个创作方法,它要求运用丰富的想象和贴切的夸张,对生活进行高度的陌生化,以此来完成作品的构思。而许多新民歌(以及许多诗人作的非新民歌)恰恰忽视了这些。充斥于诗中的形象恰恰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原貌。虽然作者在构思时尽量把话说大些、空些、玄些,而这些“大”、“空”、“玄”本质上是生活化而非艺术化的,是诗作者为将生活拔高而故意简单地将生活原形放大。因此,这些新民歌是“放大镜”式的思维,而非浪漫主义的构思。再如:
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
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
这首名为《铺天盖地不透风》的诗篇,被郭沫若、周扬从多如牛毛的新民歌中扒出来,收在他们编选的《红旗歌谣》中。这首诗不好轻率地认定其为浪漫主义,尽管它颇有浪漫主义激情。但作为那个时代的诗,它在写法上却有很强的代表性。首先,没有“诗”的结构,诗人不懂得运用陌生化或距离化的手段进行艺术构思,而只是凭着直感,近距离地组织材料,表现生活。全诗靠一个浮夸了的丰收主旨作为贯穿线进行构思,而这个主旨本身恰恰又是分裂和自相矛盾的:第一句和第三、四句是说庄稼产量高,而第二句恰恰是在表示庄稼不可能丰收。这种构思上的分裂症尽管是因违反客观规律而顾此失彼的思想认识所造成的,但它恰恰说明了排斥诗的结构,仅从政治理念或生活表象出发,近距离原生态进行创作是注定要失败的。其次,由于不懂得陌生化原则,尽管诗歌饱含着激情,但整首诗却因充斥着异常实在的材料而又缺乏想象性和形象性。因为没有运用陌生化手段对生活材料进行诗化处理,所以全诗除了“卫星”一句尚有些许空灵外,其他材料均无形象性和想象性可言。而事实上,“卫星”是流行于当时民众口头上的一个很平常的名词(郭沫若当年的诗作《跨上火箭篇》就有“文艺也有试验田,卫星何时可上天”之句),因此也是一个很实的概念。作者非常实在地把这些材料排列在一起,从而在整个诗中几乎完全排斥了空灵和想象。这正是诗之大忌。因为没有想象就没有诗。“陌生化”在这里与想象是一致的。这首诗在艺术上还有一个弊病,就是语言的日常化和平直化。这也是十七年诗的一个通病。实际上,一切文学的语言都需要陌生化。而诗的语言陌生化程度最高,处于文学语言的最高层。什克洛夫斯基在谈诗歌创作时强调:“在艺术中,引人注意的是创作者的目的,因而它‘人为地’创作成这样,使得接受过程受到阻碍,达到尽可能紧张的程度和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作品不是在某一空间中一下子被接受,而是不断地被接受。‘诗歌语言’正好符合了这些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诗歌确定为受阻碍的、扭曲的语言。”[3](P47)日常语言是诗歌语言的直接来源。但诗歌语言必须是日常语言的变形和升华。十七年诗歌的那种平白寡淡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诗的特殊韵味和阅读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