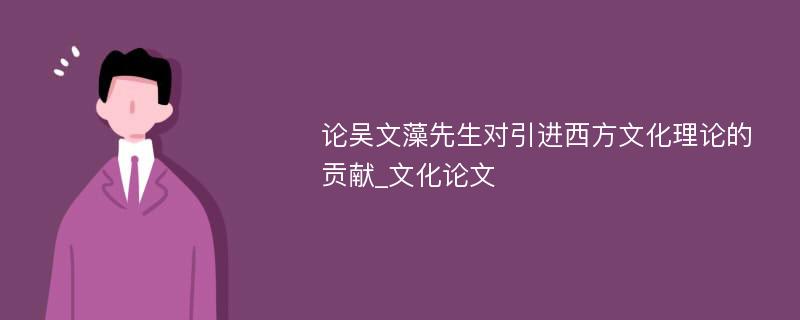
论吴文藻先生引进西方文化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文化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吴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2)04-0037-05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这三个学科在中 国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和民族卷都有吴先生 一席重要之地。如果文化人类学卷问世的话,自然也少不了吴先生的位置。社会学、民 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三个学科都是“舶来品”,在中国落地生根不过一百年,这一历程 ,伴随了吴先生的一生,吴先生为引进、传播、吸收、改造这三个学科,并使之中国化 贡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这三个学科,各自独立门户,但在中国它们之间又沾亲带故,相 互间的紧密联系是割不断的。而吴文藻先生一生对于这三个学科的呵护培育,可以说是 悉心备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时至今日,学界对于这三个学科的关系仍存仁者 见仁、智者见智之歧义,但是,有一点却是共识,这三个学科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以 人的文化为研究核心。正是这三个学科的崛起,给中国文化研究拓宽了全新的视野,使 文化研究真正步入科学的殿堂。在中国,吴文藻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文化研究入门的启蒙 大师。是他最早把西方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论全面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并发扬光大。
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语言中,文化一词的内涵不尽相同。就汉字“文化”一词而 言,中国古已有之。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象征古代文身之人。“化”字本意 为变化、改变,引申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造化之功。“文”与“化”并联使用,在《易 经》中已出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与“化”组成“文化”一词,意为 文治和教化,汉代刘向《说苑·指武》中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 加诛。”可见“以文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义,与“武功”相对。这一层本原 之义,使现代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更富人文色彩。
今日“文化”一词,已注入了西方的“文化”(Culture)。虽然至今人们仍然对文化有 诸多不同解释,但对于专业术语的文化一词源出于文化人类学却是没有什么分歧。而英 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Tylor,E.B.)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 学界所公认的经典性定义。
吴文藻先生早年赴美留学,攻读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于这两个学科的理论方法体 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认识到“文化”是这两个学科中的核心支柱。1926年4月,他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时发表文章,概述了孙中山、张慈慰、梁启超等关于民族之论 述,并介绍了瑞士法学家柏伦知理(今译布伦奇里,Bluntschili,J.K.1808—1881)、法 国哲学家吕南(今译勒南,Renan,J.E.1823—1892)的见解,鲜明地指出:“故民族性不 应视为政治上之概念,必视为文化上之概念。”他说:“中国近五十年来之政治思想史 ,一部民族思想之发达史也。吾国民族思想有二渊源:一为固有者,一为西洋输入者。 吾国固有之思想,多属片麟断爪,不及西洋输入者之完善。且吾国固有之民族思想,十 之八九为种族思想。西方民族学说之影响吾国近代思想至为深刻。”[1]
早在70多年前,吴先生精辟透彻地认识到中国固有的和西方传入的民族观之差异,阐 明民族的文化性,指出“今日科学的人类学家,对于种族之见解,完全与往日盛倡同文 同种说者之见解相左。”应该说,这是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吴先生能有 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化人类学文化理论的深刻理解。正是在这篇论 文中,他首次引用了泰勒著名的文化定义:“文化之范围甚广。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之界 说,为今日学者所公认。其言曰:文化乃‘该复杂之全体,包括知识、信仰、美术、道 德、法律、风俗及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由于人为社会中之一分子而习得者。’一民族 自信其有特殊之知识、信仰、美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等,遂组成一特殊之文 明社会,此其所以足重者三也。言文,历史及文化三者,为人文精神之所寓。故民族者 ,乃一文化之团体也。”[1]
吴文藻先生对于文化概念的介绍和理解,无疑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民族学、社会学、文 化人类学迈开第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启蒙之功,不仅仅造福于这三个学科在中国 之建设,也对于改变中国数千年形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民族观起到了振 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吴文藻先生发表于1932年的《文化人类学》讲义大纲,是全面系统介绍西方人类学理 论与方法的启蒙著作,他指出:“文化人类学上最近的趋势,可分为两方面来叙述,一 是实地调查的注重,一是文化概念的尊崇。”这篇大纲篇幅虽不长,但却一针见血地挑 明了当时西方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前沿方向。他写道:“人类学家本实地考察的经验而创 造的文化概念,乃是20世纪社会科学上最伟大的贡献。文化这一个名词,在最近20年来 无时不在人类学家的脑海中盘旋。人类学的文字中,充满了文化的字样:如文化特质、 文化丛、文化型式、文化中心、文化区域、文化圈、文化模型,文化迁移、文化辏合、 文化分播,文化历程之类。这一切新名词都集中于文化的中心概念之上。文化原是一个 难以捉摸的概念,自批评派的学者努力研究初民文化以来,文化的内容遂变为充实而丰 富。凡关于文化的诞生与发育,迁移与接触,配合与孕胎,终至成熟而凋零,无一不在 他们的热心注意中。因此,他们一反古典进化派的笼统的头脑,而变为文化的解剖学家 及传记作家。他们又以文化分播的辩论为根据,兼用葛莱勃纳派的地理分布观,及黎佛 士派的历史改造观之长,而去其短。于是由方法之讲求,而大胆地主张文化本身为人类 学正当研究的范围。他们创立一种新的思维术,打破历来学者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来衡 量他种文化的态度,而养成克罗伯所说的‘文化的超脱精神’。这一来,人类学的影响 骤然扩大。这种新思维术,不但侵入了他种社会科学的领域,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论,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走上20世纪新思潮的大路,遂开了科学上文化研究的新 纪元。”[2]
吴文藻先生在全面系统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理论过程中,紧紧地抓住“文化 ”这个核心。在诸多西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他特别青睐英国文化人类学 家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B.K.1884—1942)等人创建的功能学派(Functional Scho ol)。他称马凌诺夫斯基“独树一帜”,“至于功用派自己的立场,马氏说得很简明。 他以为此派的目的在于本功用的眼光,来解释一切文化现象。每种文明形式,每种风俗 、实物、观念或信仰,在一地方社会中,各占其本身的相当位置,各须履行某种的生活 机能,代表了工作全体上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吴文藻先生的研究著作中,有关功能学派理论的介绍与阐释所占分量为重。1935—1 936年他先后发表了《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3],《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 其在学术上的贡献》[4]。吴文藻先生重视功能学派,是因为这一学派最大的价值在于 提出全新的文化研究理论。他评价说:功能学派提出的“新法系则就各个文化体系的全 部来比较,因为文化必须视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每一元素在这统一体中,有其特殊的 功能。”吴文藻先生认识到功能学派文化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学科建设的 宝贵价值,在引进功能学派文化理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1935年秋,担任燕京大学社会 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特别邀请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 adcliffe Brown,A.R.1881—1955)来学校讲学,并指派他的弟子林耀华先生担任拉德克 利夫—布朗的助教。这一年《社会学界》第9卷编为布朗教授纪念专号。拉德克利夫— 布朗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界第一位访问中国并在中国大学讲学的西方学者,对于传播 西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功能学派的文化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才的培养, 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1936年,吴文藻先生重访欧洲,与马凌诺夫斯基会面。同年,为了培养中国社会学、 民族学人才,吴文藻先生派他的弟子费孝通先生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马凌诺 夫斯基专攻社会人类学。1937年费孝通先生归国时,马凌诺夫斯基将他尚未发表的《文 化论》(What is Culture)赠送给他携带回来。在吴文藻先生支持和指导下,费孝通先 生将《文化论》译成中文,发表于1938年6月出版的《社会学界》第10卷,后又作为《 社会学从刊》甲集第一种出版。费先生在《译序》中写道:“从生活本身来认识文化之 意义及生活之有其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自必从文化之整体入手。于是,功能派力辟 历史学派对于文化断章取义之惯技,而主张在一具体社区作全盘精密之实地观察。马凌 本人即在新几尼东岸特洛布陇岛(Trobriad Islands,British New Guinea)上实地工作 多年。其名著如《西太平洋上之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 、《初民之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1929)及《珊瑚岛上之田园及其巫 术》(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1935)俱为人类学史上之经典,即与马氏理论见 地不同者,亦无不异口同声地推为划时代之贡献也。”[5]
《文化论》是马凌诺夫斯基功能理论的精华,这部在英国尚未出版的著作首先在中国 发表,表明作者对于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的真诚信任。吴文藻先生对于《文化论》 非常重视,特别写了《论文化表格》,附在《文化论》之后,对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理 论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并“发挥及补充文化论之原意”。吴文藻先生特归纳出《文化 总表》、《主要制度表》、《生殖历程的社会组织表》、《经济表》、《巫术与宗教表 》,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一目了然。《文化论》及《论文化表格》,为中国社会学、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提供了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入门的钥匙,影响了几代人。时至今日 ,仍有参考价值。
从文化的整体性理论出发,吴文藻先生倡导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他在《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特别强调:“布朗教授在学术 上的第一贡献,是继杜尔干、摩斯之后,努力促使人类学与社会学重新联在一起,成为 合一的东西。”在他有关论述西方社会学派的文章中,特别介绍了德国的“文化社会学 ”。吴文藻先生倡导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理论注入社会学研究,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社会 学研究的视野,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学与文化 人类学、民族学紧密相结合的学科发展局面,是吴文藻先生开创的。
借鉴文化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吴文藻先生特别重视“社区研究”。1935年,他在 《社会研究》第66期上发表《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他指出:“文化是社 区研究的核心,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他认为,研究社区文化的基本方法就 是进行实地调查。同年,他还写出《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6]一文,特别介绍了 文化人类学在实地调查方面的动向,指出“在现代人类学派别中,理论方法兼擅且富有 独到的见解者,当推功能学派。”吴文藻先生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引进社会学所阐 发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明确而具体的研究方向,对于中国社会 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起步阶段,吴文藻先生是一位引进、吸收西方文 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启蒙导师,为这三个学科在中国生根,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他 并不照抄照搬,而是倡导让这些学科扎根于中国土壤。他密切注意中国国情,强调实地 调查,重视社区研究,主张关注“现代”。他亲自于1934年到内蒙古地区考察,写下《 蒙古包》一文,他在文章结尾写道:“改变此状况首由改善蒙民现在的生活做起,要渐 渐地把蒙民从游牧生活改成定牧生活,从而调查户口,改良住屋、蒙井、造林,而邮政 、医院、学校、工厂等近代式的机关,亦逐渐设立。使蒙民生活步步地趋于现代化,然 后以现代的人民,来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以抵御现代化的强邻的侵略。”[7]
吴文藻先生热心地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营养,目的全在于应用。1942年,他发表 《边政学发凡》一文,明确地阐述注重应用的观点。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吴 文藻先生提倡‘边政学’,实际上也是他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之主张和努力的一个重 要的组成部分,是他有关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化之进一步具体化的尝试。”[8]吴文藻 先生在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方面是一位启蒙大师,他在倡导社会学、民族学、 文化学研究的中国化方面也是一位杰出的先行者。
收稿日期:2001-12-25
标签:文化论文; 吴文藻论文; 文化人类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