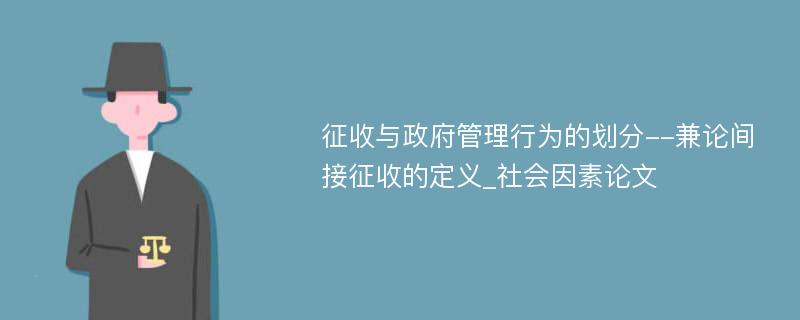
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划分——论间接征收的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征收和国有化问题是国际投资法领域重要的课题之一,①它关系到一国政府能否正当地行使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也关系到对外国投资的保护。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征收的补偿标准以及征收价值的评估方式上存在分歧,但现代国际法已承认国家征收外国投资的权力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近来关于“间接征收”的话题,又成为征收领域研讨的重点。所谓“间接征收”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他们将征收分为直接征收和间接征收,前者指直接剥夺财产所有权的征收,后者指其他对外国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财产的无理干涉”,从而使所有权人在干涉开始后的合理时期内不能使用、占有和处置该财产的行为。②在国际法中,并非所有干涉外国投资者投资权益的行为都被认定为征收,国家采取的反垄断、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国家安全等政府管理行为虽然也可能对投资者的财产使用、收益权造成影响,但只要不是歧视性的,就不能认定为征收并因此支付补偿。③因此,政府的哪些行为属于征收,哪些又属于正当的管理行为,就需要作出区分。区分征收和政府管理行为的意义非常重要,前者使国家承担对被征收者进行补偿的义务,而后者则通常不予补偿。
笔者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创造“间接征收”概念,根源在于国家的征收行为和合法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行为之间,客观地存在一个灰色区域,处在这个灰色区域中的政府行为,很难通过其表面形式来确定性质归属。对灰色区域内行为的定性,直接关系到一国政府管理职能的行使和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因此,关注并讨论“间接征收”问题是有客观原因的。关键是如何将国家正当的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行为与征收行为区分开,从而在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外国投资者个体的合法利益之间保持平衡。本文尝试以实证的方法,从国际法角度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通过考察有关条约和判例,最终得出笔者自己的观点。
一、有关条约的实践
多数双边投资条约都有关于间接征收的规定,但表述过于一般化,并且多是从征收的效果角度予以描述,对政府管理行为很少或不予提及,更不用说对如何界分政府管理行为和征收作出明确的规定。例如,德国投资条约通常约定,财产保护扩及到“其效果相当于征收或国有化的任何其它措施”。法国对外签订的条约一般将政府行为的后果是否直接或间接剥夺投资者的财产权作为判断征收或国有化的标准。美国旧版样本条约也仅提到“等同于征收或国有化的措施”,此外,在美国和个别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对这种征收措施有更详尽的描述,如征税、对全部或部分投资的强制出售要求、对经济价值、管理和控制权的损害与剥夺等行为均有可能被认定为间接征收。④
某些多边条约对间接征收也有提及。例如1994年欧洲能源宪章第13条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在另一缔约方区域内不应被国有化、征收或者被采取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的措施。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第1110条规定,一方不得在其境内对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实行直接或间接的国有化或征收,或者对此项投资采取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此外,1992年世界银行外国投资待遇指南第4(1)节规定,一国在其境内不得征收或没收全部或部分外国私人投资,或者采取具有相同效果的措施,除非按照法定程序,为了公共目的,不存在国籍歧视并给予适当补偿。
也有一些条约或法律文本从征收和政府管理行为两方面共同作出规定,从而为二者的划分定下基调。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在第1款规定了财产权保护的原则后,紧接着在第2款规定不应以任何方式损害一国执行为维护公共利益或保证捐税或罚金的征收而制定的必要的法律的权力。美国第三次对外关系法重述特别关注如何区分征收和政府管理行为,认为当一国通过税收、管制或其他没收措施干扰、阻止或不正当的拖延该外国人对其财产的有效使用或向该国境外转移时,该国应对财产征收行为负责。同时,一国对因公平税收、管理、刑事罚金或其它类似的被公认为在一国公共权力范围内的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经济损失不负责任。⑤侵害外国人的国家责任公约哈佛草案(1961)对不予补偿的征收行为进行了列举,这些行为包括:执行税收的法律、币值变动、有权当局维持公共秩序、健康和道德的行动、交战权的正当行使,法律的正常实施。经合组织 (OECD)关于保护外国财产公约的草案第3条规定,缔约任何一方不得采取直接或间接剥夺另一缔约方国民财产的措施,除非符合国际法规则认可的条件。在随后的注释中,OECD解释了什么是“直接或间接剥夺”,即任何有意的、错误的剥夺相关缔约国国民财产权利并导致损失的措施,例如,以低于公平市场价格强制要求出售的方式禁止该国民出售财产。OECD甚至还通过举例陈述了“蚕食征收”的概念,例如,根本地剥夺外国人对其财权价值的使用或享有,又不表现为任何可以被认定为彻底征收的行动;又如过分或武断的征税、禁止分红并加以强制性贷款、强制指定管理人员、禁止解雇员工、拒绝提供原材料或重要的进出口许可证。与此同时,OECD认为,草案第3条承认了一国为了其政治、社会或经济目的而在其境内根据国际法剥夺任何财产所有者(包括外国人在内)财产的主权。但又随即加上:“这种权力是与国家尊重和保护外国人财产的义务相调和的,这种调和首先体现在对被征收的外国人的补偿”。⑥OECD多边投资协议(MAI)草案将保护外国投资的范围扩展至与征收有相同效果的措施,从而涵盖了所谓“蚕食征收”。MAI谈判小组于1998年5月4日提交了一份主席报告,在该报告附件3中,对政府管理的权力和征收行为进行了阐述。关于政府的管理权力,该报告认为凡一国政府认为适当并且符合MAI要求的、为确保投资行为服从于健康、安全和环保目的而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保留或执行的。关于征收,MAI试图引入“现存国际标准”,将“征收或国有化”与“相当于征收与国有化的措施”相提并论,并认为这反映了国际法对征收予以补偿的要求,而不论一种措施是否以征收的名义进行。OECD部长会议在1998年4月28日的一项声明中提出:“MAI将建立起一套互利的国际法规范,这种规范并不制止一国政府正常的非歧视的行使其管理权力,只要这种管理权力的行使不构成征收。”⑦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智利、中美洲、摩洛哥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美国新版双边投资协定、加拿大目前使用的协定范本。它们对间接征收提供了明确的界定标准。根据这些协定,在特定情况下,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通过个案的事实调查予以确定。除其它因素外,还需要考虑: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政府行为在多大范围内影响了投资者对于投资的直接的、合理的预期;政府行为的性质。除非极个别情况,一国政府为了保护合法的公共利益的非歧视的管理行为,例如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间接征收。
二、有关司法判例
晚近关于间接征收的判例主要有伊朗-美国求偿法庭的判决、NAFTA关于征收的判例、ICSID的有关判决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
(一)伊美求偿法庭的判决
伊美求偿法庭在Tippetts,Abbett,McCarthy,Stratton v.TAMS-AFFA Consulting Engineers of Iran案中认为,⑧如果政府的措施剥夺了外国投资者基本的所有权,并且这种剥夺不是暂时的,就应当认定征收已经发生了。甚至一国对投资财产使用权、受益权的干涉也构成征收,即使该项财产的所有权未受影响。至于政府采取措施的目的和形式,法庭则认为不如该措施的效果和实际影响那么重要。Starrett Housing Corp.v.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案中,⑨法庭认为,一国采取的干涉财产权利的措施如果致使该财产权利毫无用处,即使该国没有征收该财产的目的,并且该财产法律上的权利仍归原先的所有者所有,也应当认定征收已经发生。法庭认为上述观点已被国际法认可。Phelps Dodge Corp v.Iran案中,⑩法庭表示理解伊朗政府为保护自己利益而转移企业的管理权以及政府为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目的而执行有关法律,但是法庭认为这些理由和目的不能减轻伊朗政府赔偿原告损失的义务。
可以看出,伊美求偿案的判决单纯从政府行为的效果出发判断其性质,明确地表明政府行为的合法目的不如政府行为的效果重要,甚至将其排除在判断政府行为性质所需考虑的因素之外。
(二)NAFTA的仲裁裁决
在Pope & Talbot Inc.v.Government of Canada案中,(11)仲裁庭认为,加拿大政府的出口配额限制造成了原告的利益减损,但原告的海外销售并没有被完全禁止,投资者仍能获利。因此,“干扰本身不是征收,要构成征收,还需要证明财产所有权的基本权能受到了严重程度的剥夺”。在Metalclad Corporation v.United Mexican States案中(12),仲裁庭认为,为了确定间接征收的存在,不需要确定或考虑征收的动机,也不需要考虑通过环境法令的目的。NAFTA下的征收不仅包含公开、随意和明知的对财产的剥夺,例如为了东道国利益而采取的五条件的扣押或者正式地、强制性地所有权转移,还包括隐秘地、附带地、与征收效果相同的对全部或大部分财产使用权的干涉或者对可合理期待的财产利益的干涉,即使这种干涉对东道国的重大利益来说是不必要的。在S.D.Myers Inc.v.Government of Canada案中,(13)仲裁庭仍然是以对财产权的干涉程度为基础,由此区分征收和管理行为,认为征收倾向于对所有权的剥夺,而管理行为对所有权的干扰则小的多。关于干涉或影响的程度,仲裁庭认为,即使没收是部分或临时的,但在某些情形和条件下仍可将其认定为等同于征收。仲裁庭认为,NAFTA1110中的“tantamount to expropriation”应被理解为“equivalent to expropriation”,并提出不仅要看到事实发生的形式,更应看到其实质。不应被技术上的或表面上的因素迷惑,因而无法得出征收或等同于征收的行为已经发生的结论,必须看到政府措施所包含的真正利益因素以及这种措施的目的及效果。在Marin Roy Feldman Karpa(CEMSA)v.Unitied Mexican States案中,(14)仲裁庭认为,“管理行为没有剥夺原告对公司的控制,没有直接干涉公司内部的运转或取代原告作为控股股东的地位。原告仍可从事其它商业活动。……当然,实际上,他不能再从事香烟出口,但这不等于原告对公司的控制权被剥夺了。”
在NAFTA体制下的上述判例,继续坚持以政府行为的效果划分政府管理行为与征收行为,在此基础上,关注到征收与管理行为在对外资干扰程度上的不同,并且提出了要考虑政府行为所包含的真正利益因素以及这种行为的目的及效果。
(三)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判例
在Té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 S.A,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案中,(15)仲裁庭在确定墨西哥政府的行为是否构成征收时,引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认为应考虑政府行为的影响在保护公共利益和保护投资者之间是否成比例。仲裁庭试图确定墨西哥政府的措施对于该国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对于投资者财产权利的影响以及投资者的合法预期是否都是合理的。即使确认了征收的存在,仲裁庭仍认为:“国家作为管理者在公共管理权框架内行使国家主权权力,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无需补偿,这一原则无论如何是没有争议的。”而在Compaía 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 v.Costa Rica案中,(16)仲裁庭认为为了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征收财产并不改变征收的法律性质,即使保护环境是一项国际义务也不例外。
(四)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
在James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为缔约国留出了一个评价本国政府行为目的的广阔空间,即由一国政府来初步判断公共利益是否存在,除非缔约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判断明显不合理,否则法院将接受该国的判断。(17)法院还认为,依据以促进社会公正为目的的政策而进行的征收可以被合理的视为“为了公共利益”。尤其是,有关合同和私权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公平也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因此,为了促进这种公平而采取的立法措施也符合公共利益,即使它们包含了私人之间强制性的财产转移。(18)法院还采用了一种一般评估方法,用以判断是否存在征收或对财产使用权的控制。首先,基于稳定原则、透明度原则以及法治原则的要求,在国家层面上,必须存在一个合理的、可预见的有关征收的法律基础。其次,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成比例性的。第三,干涉行为或措施是否在社会公共利益需求方面和自称征收受害者的个体利益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平衡,并且原告是否承担了不公平的负担。最后,为了进行这种评估,法院还坚持在个案基础上考虑各种确定的因素以进行事实分析。在Sporrong and L·nnoroth v.Sweden(1982)案(19)中,法庭认为,尽管原告平静地享有财产的权利受到了一些损失,但该权力并没有消失。法院注意到原告仍能继续使用他的财产,虽然将其出卖变得更加困难,但其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便如此,根据上述评估方法,法庭认为瑞典由于在多年内未能合理地考虑到本案中被告作为个体的利益,使其承担了额外的负担。因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的规定。
三、笔者的观点
(一)关于间接征收的界定,在国际法上尚无法找出明确的规定,新的趋势表明政府行为的目的及其对外资影响的具体程度已经受到重视
多数条约对间接征收的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无法根据这样的规定划分征收行为和政府管理行为的界线。即使有的双边条约作出了进一步的努力,但是由于双边条约只对缔约国双方有约束力,构成有关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它们只能形成缔约国的行为规则,具有明显的特殊性,而一般来说不能对非缔约国有任何约束力,不能形成普遍适用的规则。(20)NAFTA和欧洲能源宪章虽具有多边性,但一方面,其规定与大多数双边条约一样,仅从征收行为的效果这一单一角度进行规定,未能给出明确的界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缔约国数量较为有限,其间接征收条款也不具备普遍效力。世行投资待遇指南、哈佛草案和MAI草案都不具有约束力,尤其是MAI草案,由于使用了蚕食征收的概念,极大地扩张了征收概念的范围,同时对政府管理行为的限定又过于苛刻,很容易将一部分正当的政府管理行为划分到征收行为中去,从而进一步限制了一国政府实施经济社会管理的权力,招致了多方面的批评。因此,界定间接征收的标准,或者说,划分征收行为与政府管理行为之间的界线在国际条约中仍然没有确立,并且限于双边条约的效力和多边条约缔结的难度,短期内通过条约规范征收行为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划分,其可能性不大。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司法判例只是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辅助资料,除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件有拘束力外,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因此,本文所引判例中所阐述的原则和方法是否能构成区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国际法原则,尚有疑问。并且,即使抛开效力问题不谈,上述案例中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伊美求偿法庭的各案,法庭坚持了效果分析的原则,将政府行为的合法目的放在次要的位置,甚至不予考虑。NAFTA各案中,虽然效果分析的方法仍被坚持,但是仲裁庭也注意到了征收行为与政府管理行为对于外资干扰程度的不同。而且,在Myers案中,仲裁庭还指出,必须看到政府措施所包含的真正利益因素以及这种措施的目的及效果,由此将利益因素、目的及效果共同作为划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标准。而在欧洲人权法院和ICSID的判例中,法庭或仲裁庭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和投资保护之间的平衡,并且将判断公共利益是否存在的权利保留给了当事国政府。由此看来,在不同的国际司法实践中,法庭或仲裁庭所偏重考虑的因素差异直接导致了对政府行为性质的判断差异,因此,国际司法实践关于区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标准尚未确立。
上述条约和司法实践同时还表明,坚持“唯效果原则”是行不通的。学理上对征收的判断有两种对立的标准。一种是将区分征收与管理行为的标准集中到政府行为的效果上,尤其是对外资的影响上。这要求政府行为不能对投资者的财产权产生任何实质的限制性影响,否则就构成征收。这种标准的极端是将政府行为影响外资的效果作为唯一的、排他的标准,不考虑政府行为的目的和具体内容,这就是所谓的“唯效果原则”。该原则极大的扩张了征收行为的外延,限制了东道国基于合法的公共目的对本国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正常管理的权力,自从提出之日起,就争议不断。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从政府行为的性质入手,分析其本质,认为只要政府行为或措施是基于合法的公共目的,就足以认定其属于正当的公共权力的行使,而不是征收。从一些国家的最新条约实践,尤其是前述NAFTA、ICSID、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以及各方对MAI草案的批评,可以看出唯效果原则已经没有市场,各国在判断征收时,对于政府行为的目的及其对外资影响的具体程度,已经越来越重视。但尽管如此,仍不能说界定间接征收的国际法标准已经确立。
(二)在缺乏公认标准的情况下,国家主权原则和公平互利原则仍然是界定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国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和公平互利原则不仅是征收与国有化补偿的重要原则,(21)在区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则。依据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并依照其国家目标和有限次序,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任何国家不得被迫对国外投资给予优惠待遇,每个国家有权管理和监督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根据这一重要原则,国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或者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的必要的合法管理行为,即使对外国投资有所影响,也不应被认定为征收,更不能像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的那样以“间接征收”或“蚕食征收”来定性这些政府管理行为。布朗利说:“国家采取的措施,从表面上看是政府权力的合法行使,可能会对外国人利益造成很大影响而不能等同于征收。这样,外国人财产及其使用将会受到税收、包括许可证和配额在内的贸易限制或者贬值措施的影响。具体情况可能不同,但原则上,这些措施不是非法的,不构成征收。”(22)索纳冉加也认为,“与反托拉斯、消费者保护、安全、环境保护、土地规划有关的非歧视措施是不予补偿的征收,因为他们被认为对于国家功能的有效发挥至关重要。”(23)美国第三次外国关系法重述也表明:“一国对因公平税收、管理、刑事罚金或其它类似的被公认为在一国公共权力范围内的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或经济损失不负责任,只要不是歧视性的……”。(24)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基本原则,是改造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25)公平互利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要谋求实质上的公平互利。表现在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划分问题上,就要求政府同时兼顾本国公共利益和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既不能因为保护外国投资而损失公共利益,也不能以公共利益为由,非法干涉外国投资者的权益。结合ICSID裁定的Tecmed案以及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的评估方法,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利益平衡的考虑要重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即不单单考虑社会利益,也不单单考虑个体利益,而是将二者之间的平衡或“比例性”作为更重要的因素,同时,强调不让外国投资者承担不公平的负担。这种“平衡”或“比例性”要求,并非简单的利益平分,而是对单纯形式上公平的扬弃,这种评估方法已经比较接近于公平互利原则在实质上的要求了。
(三)区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应坚持条约解释与个案分析的方法
多数双边或多边投资条约都有专门的征收条款,为了正确地确认一项投资是否包含在该条约征收条款所调整的范围之内,不仅有必要认真审查征收条款本身,而且也有必要认真审查条约中的一般条款,以及议定书或者附加于条约正文之外的附文。(26)例如,在判断是否构成“征收”时,往往需要考察同一个条约中有关“投资”、“国民”、“公司”、“政府”等概念,不同条约中对于上述概念的阐述差异,有可能导致征收行为范围的不同,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的界线也会相应发生变动。因此,应该按照善意解释的原则,通过上下文之间的联系,推出条约用语所通常应具有的含义。
除了条约解释之外,还应注意每个个案所包含的事实因素也都千差万别,不同国家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法律传统不尽相同,忽视这些因素而盲目寻求统一的划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之间的界线的作法是站不住脚的。在上述多个判例中,政府行为的性质、目的、影响及其程度、持续时间、投资者的合理经济期望、利益之间的平衡、国家管理经济行为的需要等等都曾经被仲裁庭或法庭所考虑。并且,多数判决中也都明确的肯定了个案分析的重要作用。因此,考虑个案中的多方面因素是划分征收与政府管理行为之间界线的重要方法。
(四)发展中国家应在改善外资待遇的同时加强在间接征收方面的研究
晚近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减少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27)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纷纷改善外资待遇,接受了发达国家投资条约中有关征收与国有化的条款,而这些条款在征收的认定上往往过于宽泛,严重的影响了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在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往往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忽视社会整体协调进步,而将来一旦为了社会和谐发展,例如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劳动保护水平、减少收入差距,需要加大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力度的时候,苛刻的征收条款或宽泛的间接征收的定义就会成为政府合理实现管理职能的障碍,发展中国家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未雨绸缪,在改善外资待遇的同时,加强“间接征收”方面的研究,关注最新的条约和国际司法实践,尤其政府行为的目的及其对外资影响的具体程度在判断征收时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积极维护本国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主权,在实现政府管理职能方面建立实体上和程序上的合法基础,丰富实践依据。
注释:
①Rudolf Dolzer,"Indirect Expropriation:New Developmem?" 11 N.Y.U.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64(2002),at 66.
②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页。发展中国家学者对“间接征收”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
③M.Sornarajah,"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 (199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at 283.
④ICSID,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Rudolf Dolzer and Margrete Stevens,Chapter.4,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P102。
⑤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Law Institute,Volume 1,1987,Section 712,Comment g.
⑥OECD Indirect Expropriation and the Right to Regulat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2004,9,P8。
⑦同注⑥,P9。
⑧Tippetts,Abbett,McCarthy,Stratton v.TAMS-AFFA Consulting Engineers of Iran,Award No.141-7-2,reprinted in 6 IRAN-U.S.Cl.Trib.219 (1984),at 225.http://tldb.uni-koeln.de/php/pub_show_document.php?page=pub_show_document.php&pubdocid=231000&pubwithtoc=ja&pubwithmeta= ja&pubmarkid=904000。在该案中,原告与一家伊朗工程企业合伙为德黑兰国际机场项目提供工程和建筑服务,该合伙企业通过一个四人委员会实施管理,每方投资者任命两人进入委员会。伊朗革命后,机场项目停工,伊朗政府任命了一个临时经理,在不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作出有关合伙企业的管理决定。法庭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已经剥夺了原告在合伙企业中的基本所有权。
⑨Starrett Housing Corp.v.Govern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Award No.ITL 32-24-1(Dec.19,1983),4 Iran-U.S.Cl.Trib.Rep.122,reprinted in 23 ILM 1090(1984),at 1115.在该案中,原告投资于伊朗德黑兰的一个住房项目,伊朗革命发生后,伊朗政府通过“革命法令”任命了一个临时经理,代表政府管理所有与原告投资有关的活动。法庭认为任命临时经理的行为构成征收,因为原告已经被有效剥夺了管理公司以及有效使用和控制投资的权利。
⑩Phelps Dodge Corp.v.Iran,Award No.217-99-2 (Mar 19,1986),reprinted in 10 Iran-U.S.Cl.Trib.Rep.121 (1986),at 130.转引自George H. Aldrich,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An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s of The Tribunal,Clarendon Press Oxford,1996,at 180.该案中,原告在一家经营电线电缆的伊朗公司中拥有股权,因为伊朗革命的原因,伊朗政府将管理该公司的权利转移给了政府的代理人。法庭认为伊朗政府实际上已经完全剥夺了投资者财产权利的价值。
(11)Pope & Talbot Inc.v.Government of Canada,Interim Award(June 26,2000).http://www.dfait-maeci.gc.ca/tna-nac/documents/pubdoc7.pdf。在该案中,原告通过在加拿大的子公司制造并向美国出口软木,1996年,加拿大根据美加两国的协定,对向美国出口的软木实施数量限制。原告认为加拿大政府的措施根据NAFTA1110等同于征收。仲裁庭最后否定了原告的此项主张。
(12)Metalclad Corporation v.United Mexican Srates,ICSID Case No.ARB(AF)/97/1,Award,(August 30,2000),http://www.worldbank.org/icsid/cases/ mm-award-e.pdf。该案中,原告在墨西哥投资开发和经营一家有害垃圾填埋场,投资前获得了墨西哥政府的许可。建成后,填埋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却以可能破坏环境为由拒绝许可其经营。仲裁庭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等同于征收。
(13)S.D.Myers Inc.v.Government of Canada,Partial Award(November 13,2000).http://www.dfait-maeci.gc.ca/tna-nac/documents/myersvcanadapartialaward_final_13-11-00.pdf。该案中,原告通过在加拿大的子公司向美国出口印刷电路板进行处理,但加拿大随后制定了一项出口禁令,禁止向美国出口印刷电路板废物,对原告子公司的经营造成了影响。
(14)Marin Roy Feldman Karpa(CEMSA)v.Uniti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ARB(AF)/99/1,Award of 16 December 2002.http://www.world bank.org/icsid/cases/feldman_mexico-award-en.PDF。该案中,一家外国贸易公司从墨西哥出口香烟,墨西哥政府拒绝为该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原告认为墨西哥政府违反了NAFTA1110,构成征收。仲裁庭否认了原告的主张。
(15)Té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 S.A,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ARB(AF)/00/2,http://www.worldbank.org/icsid/cases/laudo-051903%20-English.pdf。该案中,一家西班牙公司的子公司在墨西哥经营一家有害垃圾填埋场,墨西哥联邦政府主管生态和环境的部门在垃圾填埋场经营的第3年未再继续发放许可,原告公司认为墨西哥政府违反了西班牙与墨西哥的投资协定,构成征收。仲裁庭支持了原告。
(16)Compa ia 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 v.Costa Rica,ICSID Case No.ARB/96/11,http://www.worldbank.org/icsid/cases/santaelena-award.pdf。该案中,哥斯达黎加政府以承担保护环境的国际义务为理由,针对原告公司的财产发布了一项征收法令。仲裁庭认为,不论是为了保护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只要财产被征收,国家就有义务补偿。
(17)James and others v.the United Kingdom,8793/79 [1986]ECHR 2 (21 February 1986),para.46,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CHR/1986/2.html.。该案中,威斯敏斯特二世公爵的遗嘱受托人,由于英国1968租赁改革法的修改,失去了伦敦城中心上流住宅区内的部分不动产所有权。原告认为英国政府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的规定,以及公约第6、13、14条的规定。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主张。
(18)同上注,para.41。
(19)Sporrong and L·nnoroth v.Sweden,7151/75;7152/75[1982]ECHR5(23 September 1982),http://www.worldlii.org/eu/cases/ECHR/1982/5.html。该案中,瑞典政府给予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一项长期征收许可,准许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23年)征收包括原告在内的多数人的财产,并禁止原告在一定时间内(8年)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整修和建设。原告认为这干涉了其平静地享有财产权的权利。瑞典政府则强调这是出于改善城市交通的公共目的。仲裁庭最后认为,瑞典政府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一议定书第1条的规定。
(20)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21)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22)Ian Brownlie,"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6th Edition,2003,P509.
(23)同注(3)。
(24)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Ameriean Law Institute,Volume 1,1987,Section 712,Comment g.
(25)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6)同注(4)。
(27)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杜2003年版,第2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