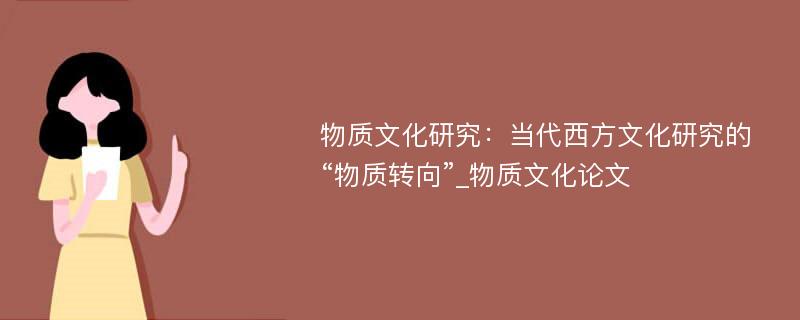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文化论文,西方文化论文,当代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现代社会科学很早就开始研究物,研究各种技术物品和商品对人的影响,作为客体的物也是现代哲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和研究对象,但是,只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物质文化研究’(MCS)才被学界视为是一个研究领域”①,而且呈“快速拓展”②趋势,被西方学者视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③。这个兴起于西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名词“物质文化研究”英文全称是“Material Culture Studies”,简称为“MCS”。在2007年出版的《理解物质文化》中,伊安·伍德沃德对物质文化研究作了详细介绍和归纳,不但厘清了物质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还分析了不同时期学者们关于物和物人关系的论述,试图为物质文化研究建立一个全面的知识坐标系;在2009年出版的《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阿瑟·埃萨·伯格细致梳理了物质文化和其他学科领域中话语的关系和重叠,介绍了物质文化研究中的不同视角,如物质文化的符号学视角、物质文化的社会学视角、物质文化的精神分析视角,并对物质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详细阐释。这些具有导读性质的专著研究成果将物质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凸显了近10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新的走势。 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物质文化读本》,译介了当代西方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成果,表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新热点——“物质文化研究”在我国学界得到了一些初步的关注。在该书的前言中,主编孟悦用了两个模糊的否定句来表达自己对于物质文化的理解:物质文化既“不是一个新学科”,也“不算是新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激发新思考和促进新的对话的场所”④。那么,被西方学者视为新兴研究领域的“物质文化研究”在当代西方是如何起源与发展的?究竟什么是“物质文化”的内涵?西方学者所言的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有哪些研究范式?本论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和讨论。 一、“物质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起源,安·斯玛特·马丁和J·瑞切·加里森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的导论中,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支源头,即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认为这三个学科的理论话语为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研究注入了丰富的理论滋养,为物质文化在今后一二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弗兰兹·伯厄斯、詹姆士·迪兹和亨利·葛莱西等人类学家在各自的研究中将物质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家涂尔干倡导的人种志研究相结合,运用物质文化记载分析了早期殖民时期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强调了人造物品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历史研究领域,受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和年鉴派的影响,从人造物品入手开展研究成为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作为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关于物质文明和资本的思考》中显示了对日常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的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吃饭、穿衣、居住永远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⑤。在艺术史领域,长期主持温特图尔博物馆工作的E.M.弗莱明在1974年的重要论文《人造物品研究:一种建议模式》中提出“弗莱明模式”,亦称“蒙哥马利鉴赏原则”,即从人造物品中提取文化意义;而研究装饰艺术的历史学家们记载了器物的风格和技术的改变,视器物为最牢固稳定的研究证据,拓宽了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马丁和加里森认为,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三个学科的理论话语为物质文化提供了基本研究方法和视角,“共同奠定并确定了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⑥。 马丁和加里森在该书中特别提到1975年在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召开的物质文化研讨会,将这次会议视为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第一次重要转折,是物质文化研究渐渐成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的标志,在物质文化研究史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该会议邀请了11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物质文化专家,重点讨论“物质文化研究与美国生活研究之间的关系”,具体议题是“人工制品的研究是如何影响改变了人们对美国历史的理解”,之后1978年出版的论文集《物质文化和美国生活研究》则是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较早的一次“理论奠基”⑦。 从马丁和加里森的研究来看,西方物质文化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对象是物质器物及其反映的观念和文化,研究主体主要是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三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从马丁和加里森归纳的物质文化研究的三支源头来看,这一时期的物质文化主要还是来自“博物馆的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关注对象”,研究方法也主要局限于历史考古研究,从“物”入手研究物品所处的历史背景,关注物被制作、代理、使用、交换、占有、丢弃的相关语境和文化。 物质文化真正得到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的重视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研究不断升温,不但吸引了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专门从事物质文化研究,还成立了专门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数次以“物质文化研究”为题的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物质文化研究的进程,使之日趋成熟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早期,美国特拉华大学和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分别成立了“物质文化研究中心”。1986年,由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和美国温特图尔博物馆合作举办了物质文化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生活在物质世界:加拿大和美国的物质文化研究视角》;英国剑桥在1986年召开了多次高级研讨会,讨论怎样将不同的理论视角应用到物质文化研究中,这些会议论文后来被收录进《阅读物质文化:结构主义、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考察了列维-斯特劳斯、格尔兹、德里达、福柯等理论家对物质文化研究视野的影响;1989年,史密森纳研究院赞助召开了物质文化会议,意图在于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各种器物,能够打破区别它们的壁垒和界限,使之相互交流,并发现各自研究的共同根基,之后出版了论文集《物的历史:物质文化论文集》;温特图尔博物馆1993年赞助召开了议题是“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的物质文化研讨会,重点探讨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出版了论文集《美国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1992至1995年,史密森纳研究院召开了多次物质文化研讨会,之后出版论文集《物的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了不同专业学科中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⑧。1993年的温特图尔会议被认为是“物质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因为物质文化研究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于某一具体物的描述性研究,而是将物作为各自研究领域的入口,关注“物被制作和使用的相关语境和文化”⑨。 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来看,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慢慢走出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专属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物质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再简单局限于对某一物的考古,而是可以和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的理论相结合,用来研究物所指涉的社会意义和人物身份。从发展脉络来看,物质文化研究呈现两股明显的走势。首先,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这一时期的商品研究、日常生活研究形成交汇。比如,阿尔君·阿帕杜伊1986年出版的《物的社会生命》中以商品为例论述了物有“社会生命”;詹姆士·G·凯瑞厄在1995年的专著《礼物和商品:1700后的交换和西方资本主义》中论述了礼物和商品在消费领域的意义;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物质文化:为何物重要》等专著中展开了对法兰克福学派商品论述的批判,强调了物的“物性(materiality)”⑩。其次,对文化的关注也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苏珊·皮尔斯在《体验西方世界的物质文化》中强调了物质文化中物人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西恩·赫迪斯在论文《物质文化和文化身份的系谱》中示范了如何借助物质文化勾勒文化身份;威廉·皮埃兹的《物恋问题》和罗素·W.贝尔克的《占有和延伸的自我》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了物和自我身份的关系(11)。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自觉参与到物质文化研究中,将物质文化理论话语和自身的学科领域相结合,不但使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话语更加宽泛包容,同时也拓宽了自身学科的研究视野和路径。由于物质文化最早是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共同关注的话题,所以物质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开放性,为后来广泛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但是,正是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和边界的模糊性,物质文化研究在这一时期还没有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具有自身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独立研究领域。 新千年来,物质文化研究呈纵深发展态势,越来越以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流。《理解物质文化》(2007)、《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2009)等导读性专著详细梳理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廓清了物质文化研究和其他理论话语的关联和界限。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更深的哲学层面思考物质文化中的一些核心概念,试图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架构,“物性”、“物人关系”、“物的社会工作”、“物的社会生命”等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重点。2001年《批评探索》秋季专刊推出了《论物》的专辑,是新世纪以来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物质文化研究动向。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比尔·布朗的《物论》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他从后现代哲学对主体的解构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认识“物”的意义和地位,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关键词“物”建立理论谱系。约翰·弗罗和W.J.T.米切尔在各自的论文中把“文学批评与新近对物的兴趣联系起来”(12),从具体的物入手研究其中承载的文化政治内涵。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以《与其他东西一样,死也是一种艺术》为标题分析了西尔维尔·普拉斯的诗歌,从死亡角度分析了物人关系。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也在思考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试图和从具体的物入手来分析特定时期的文化观念的传统做法有所区别。在《物、物性和现代文化》、《物的王国》、《物质文化读者》等论文集中,研究者们尝试用不同研究方法开展物质文化研究,比如为物“作传”,考察物在不同语境中的“运动轨迹”等(13)。此外,研究对象也更为微观具体,技术物品、被不断转手的礼物常常是学者们的重点关注对象。在论文《撞的总是同一辆车》里,格拉维斯-布朗将视野投向现代社会中的重要物品—汽车,分析了汽车的“人化”以及使用汽车的自我的“物化”。在他看来,“汽车既是自我的延展,也是自我的束茧”;汽车也许是“所有人造物品中最体现某种人格的东西”。在作为地位象征和表达自我的物品同时,汽车也渐渐变成凭自己本性行事的主体”(14)。 将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自身的学科领域相结合是近10年来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这既丰富了物质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也拓宽了研究者自身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比如,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将物质文化的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使物质文化批评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视角,文学批评中“对物质文化、客体性和物性的兴趣已经渗透到文学和文化史的各个经典时期”(15)。在一些研究者的眼里,物质文化批评视角弥补了多年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遗憾:在从前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像读书那样去‘读’物,去理解制造、使用、丢弃物品的人和时代”(16)。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和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批评概念,如“物质无意识”等,从不同侧面塑造了本学科的理论话语。 二、何谓“物质文化” 究竟什么是物质文化?阿瑟·埃萨·伯格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指出,“必须承认,物质文化是一种文化,但是这个术语有数百种定义。”(17)的确,几乎每个物质文化研究者都试图给物质文化下定义,但是他们的定义也和各自的研究背景相关。从事历史考古研究的勒兰德·费格森将物质文化定义为“人类留下的所有物体”,“物质文化不仅是人类行为的反映,也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18);人类学家詹姆士·迪兹认为物质文化“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指文化的产物”(19)。费格森和迪兹在定义中将物质文化强调为各种人造物品,这在托马斯·施莱勒斯看来有些局限。在《美国物质文化研究》的前言中,施莱勒斯认为,物质文化不仅应该包括“所有人们从物质世界制造出来的东西”,也应该包括自然物品,如大树、岩石、化石等,因为“这些自然物品有时也体现了人类的行为模式。”(20)来自艺术历史领域的学者朱尔士·大卫·普朗认为物质文化就是“人造器物所体现的文化”,因此,物质文化这个术语“不但包括了物品本身的研究,而且也包括物品研究的目的,即文化的研究”(21)。施莱勒斯在普朗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晰了物品和文化的关系以及物质文化的内涵,将物质文化研究定义为“通过物品研究一个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观念体系。”施莱勒斯认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人所制造的物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制造、委托制造、购买、使用的个体们的思想观念,从而从更大范围来说,反映了个体们所处社会的观念体现”(22)。施莱勒斯从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剖析了物质文化研究的目的,为物质文化研究明确了思路:通过人造物品来研究那些制造、代理、购买或使用这些物品的个体们的观念体系;通过人造物品来研究特定群体和社会的各种观念体系,如价值、思想态度和观念假设。 尽管费格森、迪兹、普朗、施莱勒斯等从不同层面阐释了物质文化的内涵、物品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但是他们在研究中将人造物品和未经改造的自然物品视为是人类思想在特定社会活动的固体存在,通过这些牢固、“不会说谎”的实存证据,研究与这些物品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体系,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局限于物品的考古研究。 随着物质文化研究成为更多学科领域关注的对象,物质文化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的考古意义,而是更多地强调其文化内涵。阿瑟·埃萨·伯格在《物的意义:物质文化导论》中借用亨利·普拉特·费尔查尔德的表述试图为物质文化下定义。费尔查尔德在《社会学和相关科学辞典》中将物质文化定义为所有“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不但包括语言、工具制造、工业、艺术、法律、政府、道德和宗教,也包括各种体现文化成就的物品和器物,这些物品和器物赋予了文化特征以实际的效果,如建筑、工具、机器、通信方式、艺术品等”(23)。阿瑟·埃萨·伯格称赞费尔查尔德关于物质文化的定义,认为它“揭示了文化和物之间的关系”,从两个层面具体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物不但象征了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而且也是各种文化观念和成就的具体体现。”(24) 伍德沃德在《理解物质文化》中也讨论了“物质文化”这个概念。他认为,虽然“物质文化”在传统意义上指涉可以携带、感知、触摸到的实存物品,是人类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类和物品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物质文化”这个术语强调“人类所处环境中的无生命的物如何作用于人,又是如何被人所作用,其目的在于执行社会功能、规范社会关系、赋予人类行为象征意义。”(25)根据这一定义,伍德沃德推导出物质文化研究最主要的理论假设:“物和人一样,有指涉能力,或者说可以构建社会意义,或者说做社会工作”。物的作用在于“指涉意义、行使权力关系、建构自我”。伍德沃德认为物质文化研究应重点关注物人关系,尤其是“人们如何使用物、物能为人们做什么,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等议题,应致力于分析“物人关系如何成为文化依存的意义,而文化又是怎样通过物人关系进行传承,物人关系如何使文化被接受和创造。”(26)总体来看,和阿瑟·埃萨·伯格相比,伍德沃德更为强调物人关系,强调物的语境性和文化关联性,因为物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各种社会、文化、政治的力量在定义物时,总是将物置于和其他物的关系体系中”(27)。 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学者们在论述物质文化定义时特别强调物的“物性”。丹尼尔·米勒在《物质文化:为何物有意义》中梳理了布尔迪厄、阿帕杜伊等关于物的阐释,通过两个疑问句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向当前物质文化研究的转变,将是否强调“物性”概念作为划分物质文化研究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他认为,第一阶段的传统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物很重要”,而第二个阶段,即二十世纪80年代,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为何物有意义”,在承认物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将视野引向“物性”的研究。第二阶段是“物质文化的关键理论发展阶段”,“社会世界和其他方式一样也被一种物性所建构”(28)。在2005年主编的《物性》中,丹尼尔·米勒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物性”从古代到现在的不同表现形式,指出物性对于塑造人性的重要作用。对于“物性”概念阐述得较为深入的是比尔·布朗发表在2001年《批评探索》中的《物论》。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布朗继承了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拉图尔、巴什拉关于物的阐释,消解了有生命的人和无生命的物之间的对立区分,认为“物性”是一种“类似主体结构的东西”(29),和主体相对应,且地位平等,同等重要。物所具有的“物性”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无生命客体如何构造人类主体的新思想,客体如何感动主体或威胁主体,客体如何促进和威胁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等。布朗在后现代语境中论述了物的“物性”,使得物质文化这一概念在当代话语语境中凸显出新的意义,成为当代西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假设和理解“物人关系”的关键。 物质文化研究对于“物性”的强调也丰富了物质文化关键词“物”的内涵。不同内涵的物对应了不同的英文表达,如“things”、“stuff”、“objects”、“artefacts”、“goods”、“commodities”、“actant”(行动元)等。无论是何种内涵的物,其共同点都在于关注人们周围的“各种形式的物”和“人和物之间的相互关系”(30)。其中,“行动元”指涉了各种具有社会功能行为能力的实体或者存在,包括人与非人的物品。这一术语消解了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和没有生命或外在的物品之间的界限,将人与物之间的种种藩篱统统剔除,彻底解决人与非人的种种区分(31)。 三、当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与范式 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物性”、“物有社会生命”等理论假设大大丰富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内涵,也有效拓宽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路径。在传统物质文化研究中,物是人类思想在特定社会活动的固体存在和实存证据,因此可以通过物的考古研究,挖掘与物相关的个体和社会的观念体系。而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不再局限于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传统做法,将研究视野投向物的社会意义以及物人关系的深度考量,在研究方法呈现出两个重要特点: 首先,当代物质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提倡物的“过程”观,强调关注物的运动“轨迹”和“重新语境化”。这种重视物的意义变化过程的研究被弗雷德·R.迈尔厄斯认为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大的革新”(32)。阿帕杜伊和克比托夫在各自的研究中都从物的动态过程入手研究“物的社会生命”,重点指出物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阿帕杜伊在研究商品时,揭示了商品在流通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意义变化,包括购买过程中的商品、作为礼物的商品等;而克比托夫则研究了商品的商品化——去商品化——重新商品化的过程。在《物的王国》的导论中,迈尔厄斯在强调“物的社会生命”时指出,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于,“物在文化上不是固定的,总是处于存在和形成的过程中”;“移动、不稳定、动态”是物的社会生命的非常明显的过程。在具体研究中要考虑物的“动态形式,而不只是关于他们定义的某一个静止的时刻”;要关注物的动态发展过程的谱系研究,善于捕捉物的运动“轨迹”(33)。因此,为某一具体的物“立传”,研究物的“前世今生”是此类研究的常见模式。比如,在《鸦片在中国的社会生命》中,作者另辟蹊径,考察了“鸦片先生”在中国的“运动轨迹”,借此透视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关系(34)。还有一些研究者会特别关注物的“交换”,如礼物交换、婚姻中的交换,拍卖等,通过物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改变透视其中折射的文化框架和文化语境。 其次,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和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话语形成一定程度的交叉。在研究物如何作为社会标记完成“文化工作”,如何成为标记社会地位的符号时,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者或借助布尔迪厄、福塞尔等关于社会“区隔”的研究方法,从不同阶层的品味差异入手揭示阶级分层和阶级冲突,挖掘特定社会空间的权力关系;或借助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等社会学家关于商品研究的思路,通过人们的消费方式用来划分社会群体,研究不同社会地位群体的文化差别。在研究物如何帮助调节自我认同与自尊的形成,如何从心理动力上创造了意义和自我的感觉时,往往会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考察物如何与人形成亲密纠缠,物人关系如何实现“能量的辩证转换”(35)等。比如,《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的性别物质化》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型,作者威尔·费希尔综合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话语,从服饰、交通工具、香烟、手枪等具体物品入手,研究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文化中性“性别化的身体”的“物质化”机制(36)。 从近年来和物质文化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受不同理论视角影响,在具体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主要范式: 首先,从具体的物入手,考查物在虚构社会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常见范式。物能够做“文化工作”、指涉意义、行使权力关系的理论假设引导物质文化研究者关注每一个微小的物质细节的意识形态意义,“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物品,比如手帕、胡须,可以帮助完成严肃的意识形态工作。”(37)部分研究借助布尔迪厄、福塞尔、道格拉斯、伊舍伍德等相关理论,考察物如何作为审美和文化价值的标记,帮助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尤其是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物品的“表达功能”使之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成为社会表达、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再现的方式。社会“区分的物质化”逐渐成为建构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基础,“文化与社会地位的差异重现于物品自身的再次编码”(38)。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受福柯“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影响,在研究物的“文化工作”时,特别关注物如何参与权力的控制和实施。他们认为物和人一样都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元”,不但和人之间有着“交互性和互补性”,而且物存在于关系网络之中,和人一起构建关系网络的意义,反之也是在关系网络中意义才得以构建。“物被一些特殊的权力关系建构,反过来又积极地建构这些关系。”(39)受福柯断头台、圆形监狱、制服、时间表、写字台等物的研究启示,研究者们往往特别关注现代社会的技术物品,研究物如何作为“行动元”来行使或体现权力关系。此外,受福柯对于监狱建筑的形状或者位置的走向更为微观具体研究的影响,研究者们也还会开展物的形状、质地、构造等更为细致的研究,揭示物的外在形式如何“体现某种政治形式”,如何以微妙但又有力的方式“作用于身体和灵魂”(40)。 将物作为身份的标记,研究人物的心理身份和社会身份是另一种重要研究范式。研究者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重点研究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观念、心理、情感和身份,关注物如何参与建构人的性别、种族等文化身份。在研究物和自我身份的关系的时候,研究者从主体拥有的财产、商品等入手,探讨了占有的财产物品与延伸的自我的关系,从心理学层面论证了“物恋”以及物对主体意识的建构。罗素·W.贝尔克在《财产和延伸的自我》中从心理学层面论证了财产和自我感觉的关系。他借用威廉姆斯·詹姆士早年关于现代自我的概念“一个人的自我是他所拥有的全部东西的总和”,作了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财产是自我感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贝尔克继而论述了住房和自我的关系,认为住房是“扩大的自我”,是稳定自我身份的一个重要物品,“这种延伸的自我有助于了解消费者行为如何对更广泛的人类生存产生助益,延伸自我的作用”(41)。研究者往往会特别关注消费社会中商品对人的心理影响。当处于消费社会的商品王国中,个体将希望、梦想和欲望投射在商品中,通过购买、积聚商品来构建起商品化的自我身份,但是,提供并承诺给予意义和满足的物品,最终却不能满足个体的深层需求,使个体陷入物的占有和深层欲望之间的断裂和永恒矛盾中。此外,研究者们也会关注从物入手研究人的社会身份,包括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在研究方法上与女性主义联系越来越密切,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种族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和交叉。 此外,将物作为特定历史语境的文化标记,通过物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形态和文化结构也是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范式。研究者借鉴新史学派“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考察普通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衣食住行,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物品研究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社会空间的物质文明结构。此类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无论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在《物质无意识》中,比尔·布朗呼吁关注物的本体地位,物本身就是“历史文本”:历史不应该只包括马歇里、詹明信所说的关于生产模式和反映阶级冲突的叙事方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应该包括一个时代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外表层面的物质细节。历史的不引人注目的表层表现,或者象布朗自己所说的那些“没有明确叙述的、次历史的片断”,是“生命短暂却获得历史性的浮游生物”,能够揭示出它们所处空间和时间的文化逻辑(42)。比尔·布朗将“物质无意识”概念应用到了文学作品的研究,认为文学文本中那些不引人注意的、不连贯的物质细节和记录,不但可以揭示日用物品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如何重新想象和建构特定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还可以深入理解作品中使用、丢弃、制造和购买那些物的个体的观念体系。 和传统物质文化研究相比,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中很多关于“物”的研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范式并没有取代对物的传统考古研究,但是,对于“物”的内涵的拓展大大丰富了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成果。总体来看,当代物质文化研究无论理论旨趣,还是研究方法,呼应了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众多论题,是文化研究的范式。 当前,各种新的物品层出不穷,在技术进步和大众消费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和文化支持的同时,物质产品也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不是我们占有物品,而是物品占有了我们”(43)。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不但和恒在的物质世界脐带相连,也契合了当代社会以物质丰裕为标志的时代语境,研究意义不言自明。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穿梭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广阔的跨学科领域,日渐汇聚为一个具有独特研究视角的新的学术空间,成为当前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 当下,“快乐的跨学科主义”盛行,各种学科理论话语交叉重叠,任何一个学科的传统疆界都开始变得模糊,而任何一个新的学术话语又想要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疆界,这似乎是当前理论界的一个悖论(44)。当代物质文化研究者在后现代语境中企图突破意义的边缘,重塑与“物”相关的话语,努力廓清自身的研究疆界,但也面临很多理论话语的悖论:一方面是“物”的概念的丰富指涉性,另一方面是概念本身的发散性、暧昧性。但是,这也使得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拓展性和未完成性。总之,将理论视野转向一切物及客体相关研究的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独具特色但极富包容性的研究领域,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其他理论话语交相辉映,互为补充,以其无限的活力和开放性,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①Ian Woodward,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4,5-14,55,57,81,4-14.113. ②Babette Barbel Tischleder,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s—Case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Campus Verlag,2014:17. ③Tony Bennett and Patrick Joyce,eds.,Material Powers:Cultural Studies,History and the Material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5. ④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⑤Fernand Braudel,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tran.Patricia M.Ranu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29. ⑥⑦Ann Smart Martin and J.Ritchie Garrison,eds.,American Material Culture:The Shape of the Field.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7:12,1-2. ⑧具体可以参见以下著作或论文集:St.Johns,Living in a Material World:Canadi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to Material Culture,Newfoundland:Institut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1991; Christopher Tilley,ed.,Reading Material Culture:Structuralism,Hermeneutics,and Post-Structuralism,London:Basil Blackwell,1990; Ann Smart Martin and J.Ritchie Garrison,eds.,American Material Culture:The Shape of the Field,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7; Steven Lu-bar and W.David Kingery,eds.,History From Things: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3; W.Kingery David,ed.,Learning from Thing:Method and Theory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6.引者按。 ⑨Ann Smart Martin and J.Ritchie Garrison,eds.,American Material Culture:The Shape of the Field.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97:3. ⑩具体可以参见以下论著:Arjun Appadurai,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James G.Carrier,Gifts and Cornmoditie:Exchange and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1700,London:Routledge,1995; Daniel Miller,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London:Blackwell Publishing Limited,1987; Daniel Miller,eds.,Material Cultures:Why Some Things Matter,London:UCL Press,1998.引者按。 (11)具体可以参见以下专著或相关论文:Susan M.Pearce,ed.,Experiencing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Sean Hides,"The Genealogy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Cultural Identity",in Susan M.Pearce,Experiencing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Western World,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 William Pietz,"The Problem of the Fetish,I",Res,IV,(Spring 1985); Russell W.Belk,"Possession and the Extended Self",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September 1988:15)PP.139-168.引者按。 (12)John Frow,"A Pebble,a Camera,a Man Who Turns into a Telegraph Pole"; M.J.T.Mitchell "Romanticism and the Life of Things:Fossils,Totems,and Images".In Bill Brown,Critical Inquriry,Vol.28,No.1(Autumn 2001). (13)具体可以参见以下论著:Paul M.Graves-Brown,ed.,Matter,Materiality,and Moder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00; Fred R.Myers,ed.,The Empire of Things:Regimes of Value and Material Culture,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2001; Victor Buchli ed.The material culture reader,Oxford; New York:Berg,2002.引者按。 (14)Paul M.Graves-Brown,"Always Crashing the Same Car",in Paul M.Graves-Brown ed.Matter,Materiality,and Moder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00:32-43. (15)W.J.T.米切尔:《浪漫主义与物的生命:化石、图腾和形象》,《物质文化读本》,孟悦、罗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页。 (16)Janis P.Stout,ed.,Willa Cather and Material Culture,Tuscaloosa: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2005:6. (17)Arthur Asa Berger,What Objects Mean: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9:16. (18)Leland Ferguson,"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terial Things",in Leland Ferguson,ed.,Historical Archaeology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terial Things,East Lansing:Society for Historical Archaeology,1977:6. (19)James Deetz,Small Things Forgotten: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American Life,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1996:24. (20)(22)Thomas Schlereth,"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 America,1876-1976",in Thomas Schlereth,ed.,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in America,Nashville:Nashville,Tenn.: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1982:2,3. (21)Jules David Prown,"The Truth of Material Culture:History and Fiction?" in Steven Lubar and W.David Kingery,eds.,History From Things: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3:2. (23)Henry Pratt Fairchild,Dictionary of Sociology and Related Sciences,Totowa,NJ:Littlefield,Adams & Co.,1966:80. (24)Arthur Asa Berger,What Objects Mean:An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 Culture,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9:17. (25)(26)(27)Ian Woodward,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4,5-14,55,57,81,4-14.113. (28)Daniel Miller,ed.,Material Cultures:Why Some Things Matter,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1998:3. (29)比尔·布朗:《物论》,《物质文化读本》,孟悦、罗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92页。 (30)Ian Woodward,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4. (31)关于“行动元”的论述可以参见:Donald MacKenzie and Wajcman Judy,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Philadelphia:Open University Press,1999; John Law,Aircraft Stories:Decentering the Object Technoscienc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2.引者按。 (32)(33)Fred R.Myers,ed.,The Empire of Things:Regimes of Value and Material Culture,Santa Fe: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2001:3,9-15. (34)Zheng Yangwen,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35)Nancy J.Chodorow,The Power of Feelings:Personal Meaning in Psychoanalysis,Gender,and Culture.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15. (36)Will Fisher,Materializing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24. (37)Margreta de Grazia,"The Ideology of Superfluous Things:King Lear as Period Piece",in Margreta de Grazia,Maureen Quilligan and Peter Stallybrass,eds.,Subject and Object in Early Modern Cul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3. (38)(39)Ian Woodward,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7:4,5-14,55,57,81,4-14.113. (40)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New York:Penguin,1977:139. (41)罗素·W·贝尔克:《财产与延伸的自我》,《物质文化读本》,孟悦、罗钢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113页。 (42)Bill Brown,The Material Unconscious:American Amusement,Stephen Crane,and the Economies of Pla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3-26. (43)Anon,"The Contributor's Club:The Tyranny of Things," Atlantic Monthly 97(May 1906),in Bill Brown,A Sense of Things: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5. (44)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