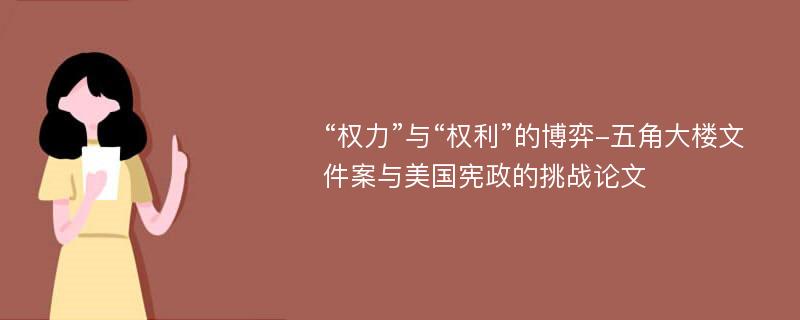
研究生论坛
“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五角大楼文件案与美国宪政的挑战
滕凯炜*
摘 要 五角大楼文件案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事先限制新闻出版的案例。本文从“权力和权利”的视角来检视五角大楼文件案中美国各方力量的角力,展示“权力”(包括国家和政府权力)与“权利”(公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是政府不同分支之间的权力建构和分配;二是公民权利的享有、维护和诉求;三是“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与博弈。借助此案,政府批评者将美国宪政的分权原则和公民权利话语结合起来,在公共领域、国会和最高法院等平台抵制尼克松政府的越权行为。同时,该事件刺激尼克松政府采取了更为激进的“反异议者政策”,为水门事件及“帝王式总统”的谢幕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五角大楼文件案 国家安全国家 权力与权利 美国宪政
“五角大楼文件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首例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事先限制新闻出版的案例。学术界的研究历来集中在从法理的角度阐释“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论争,进而讨论第一修正案所谓“表达自由”的适用性问题。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五角大楼文件案被限定在几个重要的法庭审判上,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审判。[注] 参见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Floyd Abrams, Speaking Freely :Trial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 New York:Viking, 2005; Susan Dudley Gold, The Pentagon Papers :National Security or the Right to Know , New York:Benchmark Books, 2004; John Prados and Margaret Pratt Porter, eds., Inside the Pentagon Papers , Lawrence: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Geoffrey A. Campbell, The Pentagon Papers :National Security versus the Public ’s Right to Know , San Diego:Lucent Books, 2000; Louis Henkin,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Duty to Withhold:The Case of the Pentagon Pape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 Vol.120, No.2 (December 1971), pp.271-280。国内从法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代表著作有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颜廷、任东来:《美国新闻出版自由与国家安全——以 1971 年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研究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 年第 6 期。从宪政史的宏观角度考察五角大楼文件案是受到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一书的启发。该书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宪政最突出的特点是,国内安全的需要与维护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的需要发生尖锐冲突。而“五角大楼文件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最高法院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 同时该案也成为美国“帝王式总统”宪政衰落的前奏。此外,学术界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探究政府与新闻界的关系,阐述事件的结果对尼克松政府和新闻界产生了哪些影响,有些学者还借此分析了媒体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注] 参见David Halberstam, The Powers That Be ,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79; Joseph Spear, Presidents and the Press :The Nixon Legacy , Cambridge:MIT Press, 1984; Louis Liebovich, Richard Nixon ,Watergate ,and the Press , Westport, CT:Praeger. 2003。涉及外交决策与新闻界关系的有Martin M. Shapiro, eds., The Pentagon Papers and the Courts :A Study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 San Francisco:Chandler, 1972; Nicholas O. Berry,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ess :An Analysis of The New York Times ’Coverage of US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Greenwood, 1990。
然而,上述两种研究路径都未能将该事件置于美国宪政发展的宏观历史语境下加以分析。实际上,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国家安全这一极端例外状态所触动、牵扯和呈现的远不止新闻自由一端,而是美国宪政秩序里“权力”(包括国家和政府权力)与“权利”(公民的个人和集体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上政府不同分支之间的权力建构和分配;二是言论自由、知情权和法律正当程序等权利的边界,公民的个人与集体权利的享有、维护和诉求;三是“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与博弈。换言之,该事件关系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面对不断扩张和内化的“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美国宪政实践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前所未有的暴露和凸显。本文即选取“权力与权利”的视角,重新检视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不同力量的角力,包括行政部门、国会、法院、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以及知识分子,观察角力的过程和结果如何改变了“权力”和“权利”体制的设置,从而影响了美国宪政实践的发展。
一
1968年,尼克松以“法律与秩序”的竞选口号赢得总统大选,然而,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分裂与混乱之中。随着美国在越南问题上越陷越深,冷战共识几近瓦解,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相继出现。[注] 参见Michael W. Flamm, Law and Oder :Street Crime ,Civil Unrest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in the 1960s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在这种深刻的转变中,有两种社会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国家安全国家”的内部出现裂缝。在反战思潮影响下,一批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开始反思越战政策,他们认为现行政策是错误的,必须加以调整。但是,他们的观点却不见容于当权者,且自身也逐渐被孤立于核心权力层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选择辞职,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而有的人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选择将政府机密公开,成为“吹哨者”(Whistle-Blower)[注] “吹哨者”指的是那些在组织内部任职,但却挺身而出揭露组织的不轨或不法行为的人。 ;二是“冷战共识”破灭后,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一批社会精英不满于行政部门垄断国家权力,要求获得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参与权。他们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冷战形势下人民是否有权了解政府的运作?这是杰弗逊式自由主义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达,即为了得到明智的公共决策,就必须有事先的广泛的公众讨论。充分的讨论是一个民治政府体系的关键因素,而表达自由的目的是使公民能够在知情的情况下就公共问题做出决定,以此避免出现自利的代表制以及政府权力为私人派系所窃取。[注] 凯斯·森斯坦:《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2期,第144—145页。 在这种思想下,各种非政府组织、新闻界与部分国会议员组成了松散的联盟,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权。然而,上述两种社会动向都遭到了尼克松政府的强烈抵制,行政部门的“秘密”倾向更为严重,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打压不同政见者的活动。这些措施被统称为“反异议者政策”(Anti-dissent Policies)[注] 所谓“反异议者政策”(Anti-dissent Policies)泛指尼克松政府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方案及其活动,包括一些非法的活动,如窃听、监视、擅闯民宅等。对此问题最早的一批研究认为,尼克松个人要为该政策负主要责任。近来,学者倾向于把尼克松的政策置于“国家安全国家”的语境下重新检视。他们认为,尼克松并不是一个特例,冷战时期的总统都有一种利用“国家安全国家”的手段或工具来对付“敌人”的倾向,而敌人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参见Athan Theoharis, Spying on Americans :Political Surveillance from Hoover to Huston Plan ,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Joan Hoff, Nixon Reconsidered , New York:Basic Books, 1994; Keith Olson, Watergate :The Presidential Scandal That Shook America ,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3; Melvin Small, At the Water ’s Edge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Vietnam War , Chicago:Ivan R. Dee, 2005; Katherine Scott, “Nixon and Dissent,” in Melvin Small, eds., A Companion to Richard M .Nixon , Malden:Wiley-Blackwell, 2011, pp.311-327。。充分把握上述社会动向与尼克松政府的反应,是理解五角大楼文件案何以发生和扩大的关键。
编撰五角大楼文件的工作是在麦克纳马拉的指示下进行的。作为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任政府中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亲自制定和执行了美国的越南政策。随着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他意识到美国对越政策无疑是失败的,而且会继续失败。于是麦克纳马拉开始劝说约翰逊总统改变对越政策,在写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他提到自己的想法与以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认为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的失败和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等事态发展表明,亚洲的形势向对我们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样就降低了南越的重要性……因此,我提出了一项存在让步可能的政治军事策略”。[注]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陈丕西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77—278页。 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且自身逐渐遭到核心权力层的排挤。1966年11月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座谈会让麦克纳马拉萌生撰写一部美国的越南政策决策史的想法,他的回忆录里提到,“我初次表达了我的一个想法:由于战争的进程出乎意料,未来的学者们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为这种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了《五角大楼文件汇编》的形成”。[注]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63页。 1967年6月,他委托一个班子开始撰写这一文件,主持该项目的人是莱斯利·盖尔布(Leslie H. Gelb),参加编撰工作的有很多专家学者,包括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理查德·诺伊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还有最后将文件泄露出去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注]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1931—),生于底特律,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美海军陆战队担任两年的上尉连长,服役期满后重回哈佛深造,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哈佛期间他与基辛格从游甚密,深受后者赏识。1959年受聘兰德公司,1964年进入国防部,成为助理国防部长麦克诺顿的助手。曾在越南为国务院工作两年,之后回到兰德公司。 。文件于1969年1月编撰完成,题为《美国的越南政策决策史》,文件装订成47卷,约7000页,整套文件只复印了15份,归类为“绝密”(top secret)。
当时,政府内与麦克纳马拉有相同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埃尔斯伯格就是其中较为激进的一个。1967年,他从越南回到美国时已确信,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美国应该改变政策,从越南脱身。利用一次为基辛格工作的便利,埃尔斯伯格得以阅读已经完成的五角大楼文件,阅后更加坚定了他已有的想法:“以前我一直认为,我们完全有权利采取各种方式竭力‘赢得’这场战争;有权利通过军事手段,将美国的政治取向强加给其他国家。但是从1969年8月和9月起,上述观点已经从我内心深处彻底消失了”。[注]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邢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他同时发现,尼克松政府又采取了让战争升级的行动。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越战的悲剧并不是某届政府的政策失误造成的,而是战后美国宪政秩序紊乱的结果,即传统的三权分立被打破,总统权力过于膨胀。埃尔斯伯格认为:
总统亦是问题所在。现在的问题与总统所扮演的角色有关,与他的个性和身边顾问没有任何干系。我开始认识到,二战之后,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因此所有政策的‘失误’全部归咎于总统一人。与此同时,总统也利用手中的权力,颠倒黑白,隐瞒个人的失误。就像在越南问题上,尽管外界不断施压,总统手中的权力还是让其误入歧途……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由国会和公众从外部对总统施压。[注]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第217页。
聚焦到化学学科,“生活化教学”就是在日常教学环节充分利用学生所熟悉的现象、情境等,在探索这些现象或情境的过程中学习化学知识点,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在探究的过程中完善知识储备,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能让学生形成观察生活、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积极态度.
除了当事双方外,许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方式表达了自身对案件的态度。这些人主要是国会议员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他们大多反对尼克松政府的观点,指责行政部门滥用权力和侵害公民权利。纽约联邦地区法院在6月18日第一次审理该案时,就有一些团体希望介入,如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托马斯·爱默生(Thomas Emerson),他代表27位众议院议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莫顿·斯塔维斯(Morton Stavis)代表一大批组织,包括越战老兵反战组织(VVAW)、反战者联盟(WRL)和美国之友服务委员会(AFSC)等。[注] 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 pp.139-141。在代表ACLU的发言中,诺曼·道森(Norman Dorsen)强调,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公民的知情权,这是民主的基础,“没有什么东西比所谓的秘密更能削弱民主,自治只有建立在享有知情权的公众基础上才会有意义”。[注] Ibid., p.166. 另一位ACLU的代表约尔·格拉(Joel M. Gora)表示,“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他既不能篡夺国会的权力,也不能向司法部门强行施压按他的意图审理有关国家安全的案子”。[注] Joel M. Gora,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and the Path Not Taken:A Personal Memoir on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Cardozo Law Review , No.4(March 1998), p.1316.与《纽约时报》律师毕克尔的观点相比,ACLU更加倾向于绝对的第一修正案观点。对于毕克尔而言,言论自由就是妥协和协调,“除此之外,它不是任何东西”。[注] 毕克尔:《同意的道德性》,第78页。 他批评ACLU的绝对主义立场,“如果你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带着意识形态,像ACLU一样,那么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你将什么都赢不了”。ACLU则警告,如果政府所谓“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被接受,那么几乎不能限制政府使用“事先限制”的权力,“国家安全”是个可能会被未来政府所误用的政治观念。[注]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 pp.289-290.在《华盛顿邮报》的审理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罗伯特·埃克哈特(Robert Eckhardt)也作为法庭之友发表了观点,他指出,由于泄密而对外交事务产生损害是政府维护民主的“代价”。
超高压萃取法又叫超高冷静压法,它是指在常温条件下,将高压作用于料液中,保持一定的压力后再迅速将该压力卸除,从而达到萃取目的的方法。此法因为十分有效地增大了成分的收率,而被广泛应用于植物和食品有效成分的萃取中。贾春晓等通过正交试验优化了超高压提取法从花椒中提取精油的提取条件,最后得出用超高压法提取花椒精油的最优工艺条件:压力为300 MPa,固液比为1∶40,加压时间为3 min,在此条件下得到的提取率为24.16%,配合GC-MS联用法进行分析,确认了花椒精油中包含67种成分。
二
1971年6月13日早晨,尼克松正在翻阅当天的《纽约时报》,该报头版的一则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标题写道:“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追溯30年来美国不断介入越南的过程”。当时,尼克松并未有激烈的反应。据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H.R. Haldeman)回忆,“五角大楼文件公布以后,尼克松的直接反应不像在秘密轰炸柬埔寨被泄露以后那样感到紧张,而是默不作声”。[注] H·R·霍尔德曼:《权力的尽头》,唐笙、李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28页。 但是,这仅仅是最初的反应,一天后,尼克松对泄密事件的态度发生扭转。他意识到,“这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件泄密事件。”[注]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伍任, 裘克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8年,第182页。 也就是在6月14日晚,尼克松授权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事先限制出版的禁令。[注] 白宫电话录音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Richard Nixon and John Mitchell, June 14, 1971, 7:19 P.M., in Thomas S. Blanton, eds., The Pentagon Papers :Secrets ,Lies and Audiotapes :The Nixon Tapes and Supreme Court Tapes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48, Published:June 5, 2001。 这在美国宪政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行为,在此之前,尽管经历了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也从来没有对出版和言论自由进行事前审查,无论以直接的形式还是以司法诉讼的形式。[注] 亚历山大·毕克尔:《同意的道德性》,徐斌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要是把家庭将来的幸福都押在几只兔子身上,怎么行?”郭书凤心里想到了家里七八块零零碎碎的山地,“是不是可以种上果树?”当郭书凤把这个想法和丈夫李贵说了后,李贵却说,“种果树是好事,咱们这些地闲着也是闲着,利用起来可以,但是没有技术,就是种上了果树不也是瞎忙乎?”
“对分课堂”的教学理念最早出现在大学教学中,引入中学阶段是教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高中物理的教学中,大量的实践需要学生同手去做.不管是电学的电路还是力学.人教版在教材的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后续发展,将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都做出了适当的更新,满足了当前物理教学的需求.
尼克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泄密事件。他要求霍尔德曼一方面要从法律上评估《纽约时报》是否构成犯罪,另一方面要彻查泄密者,当时的怀疑对象是莱斯利·盖尔布。在一份标注着“只限霍尔德曼查阅”的总统备忘录中,尼克松命令霍尔德曼断绝同《纽约时报》的一切联系,任何白宫工作人员不经总统批准不得同其记者接触。[注] 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 pp.75-76.随后按照总统的指示,司法部联合国防部、情报部门开始对泄密的危害性进行评估,并探讨政府是否可以采取法律行动。当天晚上,尼克松在总统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和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建议下,授权司法部采取法律行动,向法院申请禁令。尼克松在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时提到两点原因:一是考虑到文件泄露后的国际影响。文件公开后“国际社会感到一阵震惊,因为文件中有些材料涉及他国政府作为外交中介人的作用;有几个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迪安·腊斯克发表书面谈话说,这些文件对北越和苏联将很有价值”;二是考虑到行政部门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尼克松提到“采取行动以防止继续发表材料还有一个甚至更为根本的理由。此事牵涉到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一份绝密文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由《纽约时报》去做判断……莱尔德认为95%可以撤销保密……如果我们不对《纽约时报》采取行动,那无异于告诉政府中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官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泄露任何机密,政府不会过问”。[注]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第183—184页。 基辛格的立场与尼克松基本一致,他认为:“我们当时正处在我秘密访问北京的前夕;正在同河内举行秘密会谈……同时,我们正在探索与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可能性,以及进行从柏林解决办法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一系列敏感谈判。如果其他国家感到我国政府是在疲于应付局面,政府的组织纪律日益涣散,那么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受到挫折。盗窃并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的动机,显然是要发动一场政治战,压我们接受在越南问题上我们认为不体面的条件……我们的政体就要完全失去统一性。”[注]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张志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49—150页。 实际上,五角大楼文件本身并不包含多少直接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它更多的是一份历史文件,指向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注] 五角大楼文件全文迟至2011年才由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公开。关于文件到底包含多少机密的讨论,参见Prados and Porter, eds., Inside the Pentagon Papers , pp.147-153。然而,尼克松政府更多考虑的是泄密事件损害了政府的权威,破坏了行政体制的统一性,如果不加以遏制,行政职权将不可避免将受到削弱。甚至,在尼克松看来,对情报和文件的控制情况关系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注] Stanley I.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0, p.103.
尼克松政府对该事件的反应远不止此,之后其还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如窃听泄密者埃尔斯伯格、组建“管子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办公室;甚至有人提出,为了获得布鲁金斯学会所藏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资料,采取纵火突袭的办法。[注] Stanley I.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 p.111. 一般认为这个想法是白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提出的,尽管最后没有实施,但在白宫这种场合提出这样一种明显违背法律和道德的提议实属罕见。尼克松对埃尔斯伯格的行为十分恼怒,他向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W. Colson)下令,“我要他完全暴露出来……我不管你怎么去做,但是一定要到达目标。”[注] Charles W. Colson, Born Again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the White House Hatchet Man , New Jersey:Chosen Books, 1976, p.56. 6月17日下午,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召开会议,会议中没有讨论任何关于五角大楼文件本身的事项,而是千方百计要攻击自由主义者和异议者。尼克松想要赢得的不仅是法庭上的胜利,还有公共关系上的胜利。[注] Prados and Porter, eds., Inside the Pentagon Papers , p.85。1973年3月,在一次法庭审判上,司法部揭露了联邦调查局(FBI)曾对埃尔斯伯格实施窃听,随后更多的非法窃听行动被曝光。材料显示,自1969年以来,白宫就开始大范围的监听异议者,包括新闻记者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注] Kutler,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 pp.119-121。1970年7月,尼克松还短暂批准一份所谓的“休斯顿计划”(Huston Plan),该计划建议扩大对反对派和各种社会组织的监听,秘密闯入他们的住宅和办公室以获取相关资料。计划起草人汤姆·休斯顿(Tom C. Huston)明确承认秘密闯入是违法的,尽管如此,这份计划得到当时几乎所有情报部门负责人的同意。[注] Samuel Walker, Presidents and Civil Liberties from Wilson to Obama :A Story of Poor Custodians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05. 有关“休斯顿计划”的历史,参见Athan Theoharis, Spying on Americans :Political Surveillance from Hoover to Huston Plan , pp.13-39。
总的来说,在尼克松政府看来,五角大楼文件的公布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泄密事件,而是政府内外的批评者联合起来试图削弱行政部门权力的“阴谋”,这乃关系到美国宪政体制稳定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行政部门在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享有完全和绝对的权力,且行政部门内部应该铁板一块,不容任何挑战总统权威的行为发生。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某些明显违法、侵犯公民权利的举措也是可以容忍的。或者说,自由和秩序的代价有时候就是不自由和非法的手段。一言蔽之,在尼克松等人的宪政观里:行政权力至高无上,“权力”压倒“权利”。
三
随着尼克松政府将事件诉诸法庭,一次反战运动影响下的泄密行为演变为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桩里程碑事件。《纽约时报》对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遭到事先限制后,《华盛顿邮报》于6月18日继续公开从埃尔斯伯格处获得的文件。政府立马向法院申请禁令,同时起诉《华盛顿邮报》。这样,新闻界与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官司几乎同时在纽约和华盛顿展开。两个联邦地区法院都裁决新闻界有继续发表文件的权利,尼克松政府随即上诉。这时,两个上诉法院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裁定:管辖纽约地区的第二联邦上诉法院继续维持临时禁令,命令地区法院举行更多的听证会。而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再一次判定新闻界有权继续发表文件。由于判决不一,《纽约时报》和尼克松政府都请求最高法院立即审议这两个案件。6月25日,最高法院受理该案。以往的研究将法庭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适用性问题,而本文试图从“权力和权利”的角度来检视这几次审判,关注的焦点是参与各方(包括作为法庭之友的第三方)如何界定冷战后的“国家安全”,如何认识美国宪政下的分权原则和公民权利。
两份报纸的法律观点和辩论策略相差不大,都强调新闻界享有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不受事先限制的出版自由。[注]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担任《纽约时报》辩护律师的是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亚历山大·毕克尔(Alexander Bickel)。毕克尔的观点是,为了争取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的支持,宜采用这样的立场,即承认政府在某些特定的情况有权限制新闻出版,但是在本案中,这种情况并不存在。这是一种妥协后的第一修正案观。除此基本立场外,《纽约时报》还补充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即宪法规定的分权原则:国会并没有制定相关可供行政部门依据的法律来实施事先限制,尼克松政府此举侵犯了立法部门的职权,乃是按照自身的意志执行一条没有经过国会通过的法律。任何认为总统有权实施事先限制而无须国会立法的观点,都是违反了宪法的分权原则。《纽约时报》还指出,政府的行为是有意破坏美国传统上的政府与新闻界之间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对于美国人的福祉至为重要。[注] Brief for the New York Times (Public Brief) filed in 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 (Oct. Term, 1970, No.1873), in the Supreme Court. 政府与报社在最高法院的诉状均可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网站下载: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8/supreme.html。
与之相对,尼克松政府首先指出,《纽约时报》泄露国防部绝密文件已经触犯了联邦有关反间谍的立法。其次,行政当局认为文件泄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在向法院提交的秘密附件中,政府部门详细分析了文件的危害性,特别是对当前的军事行动和外交关系构成严重威胁。[注] “Secret Appendix,” in Thomas S. Blanton, eds., The Pentagon Papers :Secrets ,Lies and Audiotapes :The Nixon Tapes and Supreme Court Tapes ,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48, Published:June 5, 2001.最后,尼克松政府也谈到了宪法分权问题。宪法赋予总统以行政首脑和三军总司令的地位,并主管外交事务。不应该片面分析第一修正案,而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宪法框架下,结合其本身的历史和目的来看。法院应该维护宪法赋予的总统权,唯此,总统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保卫美国人民。行政当局的律师也多次在庭审中强调,有关国家安全事务不应该由法官、律师或者新闻界来作判断,而要交给专业人士,如情报人员、军人和外交官来处理。[注] 尼克松政府的观点和立场集中表达在上交最高法院诉状中,参见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filed in New York Times Company v .United States (Oct. Term, 1970, No.1873), in the Supreme Court。 概言之,政府诉求的本质在于维护行政分支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绝对权力。
2018年是中国电商阿里巴巴举办“双11”的第10个年头,“双11”已经成为全球电商购物节。今年“双11”总成交额为2135亿,电商交易再次呈现火爆景象,中国社会井喷的消费潜力,又一次让人们惊叹。
科研项目管理大多情况下实行刚性管理原则,由于刚性管理的不可抗拒性和强制性,科研项目管理者偏向于被动、机械地依据法规条款对科研项目进行管理,忽视与被管理人员的沟通和协调,造成科研项目的控制与调整效果较差。同时,科研项目管理多为定量管理,量化指标的不完善或过度量化容易滋生有关人员的功利化心理,片面追求成果数量,阻碍创新水平的提升。此外,科研管理工作在项目后期往往只是简单地督促,缺乏科学系统的管理,致使部分项目草草结题或者延期,给企业财力物力带来一定的损失。
埃尔斯伯格和《纽约时报》的决定令世人震惊,尤其考虑到他们要泄露的秘密是关于一场美国正在进行的战争。不过,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运动为他们的行动创造了基础条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是较早将对抗的矛头指向美国政府体制的非政府组织,1965年该组织主席保罗·波特(Paul Potter)就曾在一次集会上高呼:“只有当(政府)体制发生改变和可控时,才有希望结束社会不公引起的暴力,并使美国民主得以重生。”[注] Paul Potter’s Speech, April 17, 1965, http://www.sdsrebels.com/potter.htm. 另一个影响更大的非政府组织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这个创建于1920年的组织在60年代末成为行政部门滥权的强烈批评者。该组织的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为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政府内部异议者提供司法援助;二是大量发行出版物宣传公民权利观念。[注] 有关ACLU的活动,参见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 Carbonda: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9; Aryeh Neier, Taking Liberties :Four Decades in the Struggle for Rights , New York:Public Affairs, 2003。另外,在埃尔斯伯格之前也出现了诸多“吹哨者”,他们寻求与新闻界合作,公开政府机密,大多都涉及行政部门滥用权力的内容。1970年1月,前陆军上尉克里斯托弗·派尔(Christopher Pyle)在《华盛顿月刊》上公开了他参与过的军队监视项目,描述了军队三年来监视国内异议者的行动细节。[注] Christopher H. Pyle, “CONUS Intelligence:The Army Watches Civilian Politics,” Washington Monthly , Vol.1, No.12(January 1970), pp.4-16. 后来克里斯托弗·派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写成了一篇探讨军队监视项目的博士论文,参见Christopher H. Pyle, Military Surveillance of Civilian Politics ,1967-1970 , 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6。 1971年2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揭露了国防部利用公共关系资金伪造国内支持越战舆论的丑闻。[注] Beth Bailey, “The Army in the Marketplace:Recruiting an All-Volunteer For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94, No.1 (June 2007), pp.71-72.质疑行政部门权力过大的声音也不断在国会山上出现,参议员塞缪尔·欧文(Samuel Ervin)在1971年2月主持了为期9天的听证会,调查行政部门的非法活动。听证会指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行政部门不愿意与国会分享情报;二是白宫无视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注] 参见Julian Zelizer, On Capitol Hill :The Struggle to Reform Congress and its Consequences ,1948-2000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Karl Campbell, Senator Sam Ervin ,Last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综上可见,五角大楼文件案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它与当时社会的新动向密切相关,是由吹哨者、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和主流新闻界所组成的“一部分美国人”试图遏制行政权力扩张,维护公民权利的又一次有力的尝试。
显然,埃尔斯伯格深刻洞察到战后“国家安全国家”的不断扩张侵蚀了美国宪政基础,从而让美国在外交内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他决定,将文件公之于众,让美国公众了解真相。起初,埃尔斯伯格曾想通过国会议员将文件公开,并先后联系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均遭拒绝。1970年夏天,他还督促基辛格好好阅读一下这些绝密文件,但基辛格亦不以为然。1971年3月,几经权衡,埃尔斯伯格最后把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经过报社内部的激烈争论后,时报发行人阿瑟·索兹尔伯格(Arthur Sulzberger)决定公开发表这些文件。尽管意识到会面临一场潜在的法律冲突,但时报的编辑们坚信自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来公开这些文件,因为这既是“新闻自由”,也是维护公民“知情权”的行为。他们也相信文件的出版会是美国新闻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注] 关于《纽约时报》的抉择过程,参见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 pp.48-65;戴维·哈伯斯塔姆:《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尹尚泽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670—675页。
6月13日的白宫录音显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 Jr.)是第一个向尼克松汇报有大量机密泄露的人。他在给总统的电话中说明了泄密文件的内容,指出泄密者可能是民主党人,而且特别强调文件是被“偷窃”的,而政府应该对此所有回应。[注] Conversation between Richard Nixon and Alexander Haig, June 13, 1971, 12:18 P.M. 霍尔德曼的日记中也提到,黑格给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事件将给南越人带来严重的问题……泄密和发表机密都是严重的叛国犯罪行为”。[注] H.R. Haldeman, The Haldeman Diaries :inside the Nixon White House , New York:G.P. Putnam’s sons, 1994, p.300. 约1个小时后,尼克松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通电话,总统主动提起五角大楼文件,使用了几乎与黑格一样的语言。[注] Conversation between Richard Nixon and William Rogers, June 13, 1971, 1:28 P.M. 有白宫工作人员见到尼克松怒斥国务院,并要求其中每一个工作人员接受测谎,以便查出谁是泄密者。[注] Prados and Porter, eds., Inside the Pentagon Papers , p.77.下午,尼克松与基辛格详细谈论了这起事件。基辛格的看法是,“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一点的话,那是因为它是一座金矿,展现了前任政府是怎样把我们带到那的”。基辛格承认五角大楼文件揭示了政府“严重的治理失误”,但那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事。尼克松不同意这种“事不关己”的判断,他重复了黑格的观点,即“那个泄密的混蛋”做出了背叛政府的举动。随后,基辛格立刻表示赞同总统的观点,“这是背叛,毫无疑问应受到起诉”。[注] Conversation between Richard Nixon and Henry Kissinger, June 13, 1971, 3:09 P.M. 可见,尼克松从黑格报告中意识到泄密行为的“背叛”性质,这种背叛不是针对某个总统,而是整个美国政府。从这时开始,尼克松决定要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
6月30日,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以六比三确认驳回政府维持禁令的要求,新闻界可以继续出版文件,基本理由是:政府未能履行重大举证责任,证明文件的泄密确实对国家安全产生“直接的、立即的和无法弥补的伤害”。显然,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判决,区分危险的性质和程度。一方面,它并没有完全否定政府事先限制出版的权力。也就是说,当国家安全的危险是明显且即刻时,政府有对公民权利进行必要侵犯的空间。另一方面,法院要求行政机构以最为清楚、细致和直接的形式说明其行为的合法性。本质上,法院所苛求的乃是充分的、多样化和开放的政治过程,而不是行政部门中一小撮人的权力垄断。无论如何,从这一系列的法庭审判中可以看到,除了有关第一修正案适用性问题是法庭论辩的焦点外,参与各方都围绕美国宪政更为核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即“权力宪政”与“权利宪政”的纠结互动的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如何界定?“权力”在政府内部如何分配?“权利”如何防止“权力”的侵害并对后者形成制约?这些关系构成了美国宪政秩序的基础,并左右美国政治发展的进程。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法律上为五角大楼文件案画上了句号,但关于宪政秩序中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争论却并未停止。
以上各方的陈述与论辩,均从有关第一修正案的适用性深入到宪政分权原则和公民权利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联邦地区法院到最高法院的各级法官也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默里·格法因(Murray Gurfein)指出:“国家安全不是唯一的屏障,国家安全存在于美国的自由制度中。一个安全的国家需要新闻自由,尽管新闻界吵吵嚷嚷,固执己见,无孔不入。当今是一个纷扰的时代,对政府事务宣泄不满的最大安全阀莫过于各种形式的表达自由。这是美国制度历史上形成的精髓,也是所有美国总统的信条,这是美国制度区别于其他政府制度的主要特点。”[注] United States v. New York Times Co., 328 F. Supp.324(1971), 转引自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第85页。 这段话最清晰地表达了格法因法官的国家安全观,即维护美国的自由制度同样是在捍卫国家安全。哥伦比亚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格哈德·格赛尔(Gerhard A. Gesell)认为美国的民主需要政府和新闻界和谐相处,公众享有知情权。在审理过程中,格赛尔法官两次驳回尼克松政府限制发表的要求,多年后他回忆:“如果有人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些什么的话,他们可以说我是听审‘五角大楼文件案’的所有29名法官中,唯一从未让印刷停止哪怕一分钟的法官。我一直为此感到自豪。”[注] 凯瑟琳·格雷厄姆:《个人历史》,苗萌、李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526页。 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以第一修正案绝对主义观点著称,他表示:“只有自由的、不受限制的新闻报道能够有效揭露政府的欺骗行为。新闻自由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保护人民免受政府的欺骗,这种欺骗行为使得美国人民被送到遥远的大陆,死在异乡的瘟疫与敌人的炮火之下。”[注] 有关最高法院大法官言论的引述,均出自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403 U.S. 713 (1971).No.1873,下文不再注明。资料来源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http://www2.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8/supreme.html)关于大法官对该案意见的摘要,还可以参见斯坦利·I·库特勒编:《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朱曾汶、林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0—455页。 另外,他从宪政分权原则角度来进一步分析,“政府甚至根本没打算依据任何一条国会立法来行事,相反,他们胆大妄为的宣称法院应该遵从它的意志,以公平、总统权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创造’一条违背新闻自由的法律”。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也指出,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在国防和国际关系领域享有过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缺乏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有效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有见识的公民成为对行政权力的唯一制衡因素。另一位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直接反对总统拥有“固有的权力”来寻求事先限制的禁令,他不认为总统在国防和外交上的责任赋予其此种特权。当然,也不乏支持尼克松政府立场的法官。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乔治·麦金侬(George E. Mackinnon)就声称:“法院并不是处理国防和外交政策的地方。”[注] 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 p.248.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与约翰·哈兰(John Harlan)持相同的观点——对国家安全事务拥有决定权的是总统,而不是法院。哈兰指出,司法部门在外交领域的职能极为有限,这正是美国宪法赖以运作的三权分立原则。换言之,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司法部门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来做判断,自然也没有相应的权力。
当{xn}关于度量d收敛到1时,对任意的ε>0,存在N,使得d(xn,1)=1-xn<ε。此时, ρ0(xn,1)=1-(xn→1)∧(1→xn)=1-xn<ε。故{xn}关于度量ρ0收敛,且收敛到1。
四
最高法院关于此案的判决在美国宪政史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社会各界存在多种说法。作为麦克纳马拉的前助手,卡特政府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R. Vance)在他的就职听证会上曾提到,五角大楼文件事件缩短了越南战争。[注] Prados and Porter, eds., Inside the Pentagon Papers , p.183.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尼森(Charles Nesson)认为该案刺激了反战舆论,并赋予其合法性和正确性。[注] Ibid. 还有学者认为:“本案在解释和适用第一修正案过程中,保障了新闻自由,扩大了公众的知情权,从而维护了联邦宪法第四条第四款主张的共和原则。”[注] 邱小平:《表达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研究》,第97页。 但另一方面,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亚历山大·毕克尔、任东来等学者认为,本案可能会危及美国代表制民主政府的合法运作,它的判决非但未能给新闻自由提供充分保护, 反而成为政府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减少了。[注] 参见Louis Henkin, “The Right to Know and the Duty to Withhold:Case of the Pentagon Pape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 Vol.120, No.2(December 1972), pp.271-280;毕克尔:《同意的道德性》,第59页;颜廷、任东来:《美国新闻出版自由与国家安全——以 1971 年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研究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 年第 6 期。
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五角大楼文件案促使美国历史朝向水门事件和尼克松辞职的情节发展。在法庭上失败后,尼克松及其幕僚将矛头对准了泄密者埃尔斯伯格,并且认为政府中隐藏着很多类似的人,存在着巨大的保密漏洞。为此,尼克松政府一方面起诉埃尔斯伯格,罗列了其15条罪名,包括盗窃政府财物和间谍罪;另一方面组建所谓的“管子工”(Plumbers Unit)小组,其目的是堵住政府中存在的保密漏洞,并调查埃尔斯伯格。尼克松一直认为埃尔斯伯格泄密行为背后隐藏一个巨大的“阴谋”,基辛格说,“尼克松深信,有人心怀敌意,在搞阴谋反对他”。[注] 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三册,张志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08页。 这些人是美国东海岸受常春藤教育的政治家、主流新闻媒体(尤其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肯尼迪的追随者、民主党自由派和新孤立主义者。[注] Samuel Walker, Presidents and Civil Liberties from Wilson to Obama :A Story of Poor Custodians , p.285.尼克松命令埃利希曼负责组建“管子工”,他对埃利希曼说:“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糟糕的政府中找到任何人为我们出点力来解决这个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那么,我的上帝啊,我们就得自己干了。我希望你在白宫这里建立一个小组。让参加小组的人避开盯梢的密探,查明情况,想出如何堵塞泄密的办法。”不久,尼克松要求查克·科尔森对埃尔斯伯格施加更为严厉的打击:“我们现在遇到了一股反政府的势力,而我们是非同它斗争不可的。为了堵塞这些泄密漏洞并防止将来再发生未经许可的泄露事件,你怎么去干我都不管,需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注] H·R·霍尔德曼:《权力的尽头》,第131、135页。 这个决定对于尼克松来说是致命的。9月3日,由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与戈登·利迪(Gordon Liddy)指挥的“管子工”小组非法闯入了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菲尔丁的办公室,期望找到能够抹黑埃尔斯伯格的材料。1973年闯入事件曝光后,尼克松政府宣称此行为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埃利希曼还劝说检察官不要进一步调查,因为总统不希望他介入国家安全领域。[注] Stanley I. Kutler, The Wars of Watergate :The Last Crisis of Richard Nixon , p.115.实际上,这件事与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目的仅仅是要找到埃尔斯伯格的“黑材料”。尼克松曾说:“调查埃尔斯伯格事件总的来说,是最高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注]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册,伍任、 裘克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8年,第109页。 管子工小组正是在这种思想下从事非法活动,还自认为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事情说明,尼克松政府在五角大楼文件案发生后反应过度,甚至有点“神经过敏”,在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注] 事后埃利希曼曾评论道:“五角大楼文件问题根本不成为问题,直到亨利捅到总统那里,他总把事情炒得发烫,结果尼克松来来回回地下令干这干那,只是惹得一身骚。”转引自沃尔特·艾萨克森:《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刘汉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第241页。 事实证明,水门事件的制造者与这次闯入事件的实施者是同一批人。结合尼克松政府事后反应,就不难理解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尔(Melvin Small)在评价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影响时所说的话,“五角大楼文件的出版是政府的一大失败,在当时,没有人料想到这件事扮演了摧毁尼克松总统地位的关键角色”。[注] Melvin Small, At the Water ’s Edge ,American Politics and the Vietnam War , Chicago:Ivan R. Dee, 2005, p.179.
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结果代表“新闻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格雷厄姆夫人谈道:“五角大楼文件案把政府和新闻界之间持续不断、日复一日的较量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信……的确刊登‘五角大楼文件’使得将来做出决定变得更容易。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做好准备迎接‘水门事件’。”[注] 格雷厄姆:《个人历史》,第533页。 此时,许多媒体纷纷刊文揭露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欺骗行为,之前美国社会关于越战的主流认识“沼泽论”受到挑战。经过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等人提炼后的“沼泽论”认为,美国是怀着良好的愿景一步一步卷入越南的。[注] 参见David Halberstam, The Making of a Quagmire , New York:Ballantine, 1965; 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Bitter Heritage :Vietnam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941-1966 ,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67。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伪命题,一篇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反驳说,“越南确实是一摊泥沼,但我们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清楚这一点”。[注] Leslie H. Gelb, “Vietnam:Nobody Wrote the Last Act,” Washington Post , June 20, 1971.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并不满意,认为最高法院依然给政府事先限制出版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因此,此事件给ACLU敲响了警钟,组织负责人阿耶·奈尔(Aryeh Neier)把应对“秘密政府”作为1972年ACLU的首要任务。[注] Samuel Walker, In Defense of American Liberties :A History of the ACLU , p.290.不久,奈尔吸纳了另一个组织公共正义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Public Justice),他们一起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1971年10月组织了一场针对联邦调查局的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一次涉及敏感机构的学术公开讨论会,五角大楼文件案后,联邦调查局等部门不再是不可触碰的了。1973年,他们又组织了另一场研讨会,专门讨论“政府秘密”问题,会议质疑了所谓的“行政特权”。[注] 研讨会的成果最后都编辑成书出版,参见Pat Watters and Stephen Gillers, eds., Investigating the FBI , New York:Ballantine, 1973; Norman Dorsen and Stephen Gillers, eds., None of Your Business :Government Secrecy in America , New York:Penguin, 1975。
五角大楼文件案暴露出的问题使美国国会深受震惊,许多议员意识到,行政权力过于膨胀,而国会对此缺少监督。6月22日,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要求政府尽快撤军的决议,而相同的提案在前六个月被否决多次。[注] David Rudenstine, The Day the Presses Stopped :A History of the Pentagon Papers Case , p.329.6月29日晚,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利用自己作为参议院建筑和土地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权力,连夜召开听证会。会上他宣读了五角大楼文件,文件也随之载入了国会听证会记录当中。[注] 参见Prados and Porter, eds., Inside the Pentagon Papers , 2004, pp.72-74;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第324—325页。不久,一部分国会议员联合专家学者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专门讨论五角大楼文件案给国会带来的挑战。诸多议员表示,要采取行动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注] 这次会议的成果也编辑成书出版,参见Anatomy of An Undeclared War :Congress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ntagon Papers ,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2。 9月,参议员欧文(后来成为参议员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其目的是“重新检查与再一次强调第一修正案的诸原则”。[注]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Freedom of the Press , 92nd cong., 1st and 2nd sess., 1971-1972.
对于控制变量,速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的相关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作为一项严重依赖于企业内外部融资约束的经营决策,企业的综合偿债能力越好,相应会促进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与研发支出在1%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主要可能因为按照会计准则,当期研发投入没有达到资本化条件的计入费用处理,一定程度上冲减了当期经营业绩,这也是管理者不愿进行过高研发投入的原因之一。此外,公司的成长性、市场份额与营运能力和研发投入呈负相关,企业年龄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总而言之,五角大楼文件案刺激尼克松政府实行了更为激进的反异议者政策,但也使尼克松的批评者更为坚定地站在“国家安全国家”的对立面。五角大楼文件案不仅让部分美国人反思越战政策,也让他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的本质——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对美国传统宪政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由主流媒体、非政府组织、吹哨者和国会议员组成的松散联盟在各个领域采取行动遏制“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人们大概都清楚“水门事件”是美国“帝王式总统”的谢幕,也知道菲尔丁办公室闯入事件和水门事件的制造者是同一批人,但却忽视了扳倒“帝王式总统”的人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松散的联盟。[注] 许多研究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变革的专著都着眼于水门事件本身,而没有考虑到之前的社会动向与水门事件的关联性,如Bruce Schulman, The Seventies :The Great Shift in American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 New York:Da Capo Press, 2001; Edward Berkowitz, Something Happened :A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verview of the Seventies ,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五、结语
二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国家安全国家”的不断扩张。一方面,它涉及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权迅速膨胀,从而形成所谓的“帝王式总统”。这是20世纪联邦权力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国际局势的发展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维护国家安全与公民政治和公民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权力”与“权利”的紧张关系凸显。[注] 有关“国家安全国家”问题,参见牛可:《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Michael Hogan, A Cross of Iron :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1945-1954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受越南战争影响,美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分裂与动荡之中,各种抗议活动与骚乱频发,美国公众也越发不信任政府,开始质疑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和尼克松政府逐渐将“国家安全国家”——为应对冷战和共产主义威胁而建立的体制——应用于处理国内问题,政府加强对民众的监控,对持不同政见者实施窃听,非法闯入民宅,钳制新闻自由等。[注] 参见Alan I. Bigel, The Supreme Court on Emergency Powers ,Foreign Affairs ,and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1935-1975 , 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pp.151-164。这些举措,无疑激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同时也使美国的宪政秩序面临严重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社会出现了一部分以主流媒体、非政府组织、吹哨者和国会议员组成的松散联盟,他们试图遏制“国家安全国家”的扩张,特别是从美国宪政的分权原则和公民权利着眼,通过立法、司法和新闻监督等方式来制衡不断扩大的行政特权。这批人的意识形态,既继承了美国建国以来“反国家主义”的思想和话语资源,又有其新的目标指向和理路。
在美国历史上,由国家安全问题而引起的宪政争议时有发生,特别是战争年代,如内战时期林肯对执法权(包括压制反对意见)的使用,一战时威尔逊政府实施《反间谍法》和《惩治煽动叛乱法》。但这些争议都没有大到能够借用宪政体制(最高法院)击败总统的程度。这与越战的性质和文件本身的“机密”程度、与尼克松的神经过敏式的处理都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五角大楼文件案引发了一系列十分关键的宪政问题:所谓“安全”是如何以及由谁来界定?总统定义的“国家安全”如何受到钳制但又不至于损害总统需要的决策能力?言论自由的界限与尺度在哪里?如果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自由表达权,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权力滥用又如何受到制约?归根结底,它关系到美国宪政秩序中“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关系,既包括“权力”内部的建构,政府各个分支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权力分配;也涉及权力与权利的纠结互动,特别是公民权利对行政权力扩张的制衡,以及人们通过主张与构筑关于言论、出版、知情的政治权利甚至可以改变政府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五角大楼文件案不单是一个主流媒体如何捍卫新闻和表达自由的故事,还生动地展现了“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这一美国宪政发展的永久性主题。
*滕凯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标签:五角大楼文件案论文; 国家安全国家论文; 权力与权利论文; 美国宪政论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