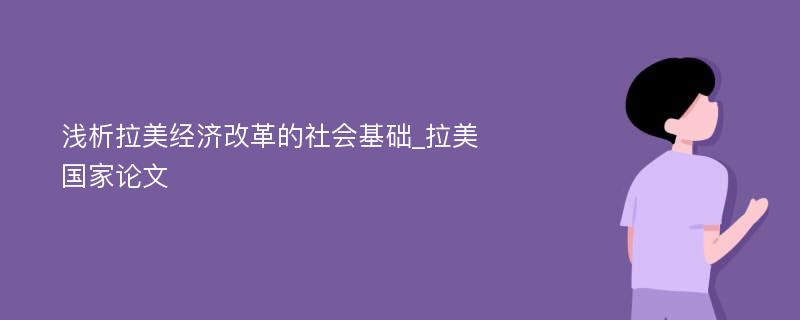
浅析拉美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国家的经济改革都是一个各社会集团和各社会阶层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它必然使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正是这个利益机制的作用,决定着不同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对改革进程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从而进一步揭示出改革本身的社会基础。
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是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和保持货币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关键。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迄今已有10年,改革的利弊都已有了比较充分的表露。改革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是否广泛和牢固,即各个社会阶层对其是支持还是反对以及支持或反对的程度。而不同社会阶层的态度,又取决于改革进程对本阶层的利弊得失。
从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实际效果来看,它顺应了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初步实现了宏观经济指数的稳定,使经济运行走出了80年代持续衰退的低谷,生产得到恢复和连续几年的适度增长。这是不可否定的成绩。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一直忽视社会方面的发展,改革中的各项政策措施基本上是以牺牲社会发展来追求宏观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收入分配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这就使改革中取得的经济成果未能转化成社会效益,即未能使广大民众阶层真正受益,从而削弱了改革进程的社会基础。根据利益机制的原则,分析一下国内外各个集团和阶层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态度,便可证明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一、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达国家是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受益者,因此它们坚决支持改革。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一整套计划,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一些发达国家制定的,并且不区分各国的具体情况,要求发展中国家一成不变地予以执行。
众所周知,拉美国家是在80年代陷入危机、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失去活力并阻碍经济发展的时候走上经济改革之路的。因此,改革是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的。然而究竟以什么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来进行改革,是当时拉美国家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拉美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寻求资金以实现经济增长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便把一套新自由主义的调整计划强加给求贷国政府,并要求各国对具体的宏观经济指标作出严格规定和进行监督,否则就不给信贷。连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承认,拉美国家在进行改革时,是“外国投资商发号施令,强加这种现实,各国没有资金,严重依赖外资,只得承诺改革”[①]。截至1994年,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巴西、乌拉圭、秘鲁、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圭亚那和尼加拉瓜,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它们进一步开放经济、进一步面向市场的压力下,与该机构达成一致,实行了取消政府调节和不顾社会后果的极端自由派模式。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只要它们按照商定的计划使其经济实现自由化,就给它们提供信贷”。1996年,当委内瑞拉经济面临严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以实行放开物价、取消货币管制、放开利率、削减政府开支、廉价出售国营企业的一揽子新自由主义调整方案为条件,向它提供14亿美元信贷,并大力赞许该国雄心勃勃的前期投资计划。同年7月,欧洲联盟提出,对拉美国家新的合作战略的前提是“进一步推行经济开放和私有化进程”。玻利维亚实行这套改革计划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师长的口吻赞扬它是在“完成自己的家庭作业”。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官员号召拉美国家采取第二阶段的改革措施:国家继续减少干预,彻底打败民众主义。总之,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资本优势,以实行它们的方案为先决条件才能提供贷款的办法,迫使拉美国家无法作出其他选择,只能接受它们的“建议”。因此,它们当然坚决支持和极力推行这样的改革。
国际金融机构和发达国家是拉美现行经济改革的受益者。这也是它们支持拉美改革的重要原因。进行改革后,它们可以收回拉美国家积欠的债务和利息;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向拉美大量出口商品和劳务,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市场份额;可以扩大在拉美的投资,进一步赚取投资利润;还可以借私有化之机扩大本国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在拉美的经营范围和经济实力(例如,在玻利维亚石油公司私有化过程中,受益者首先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此外还有跨国公司等;加拿大和西班牙的投资家廉价收买了墨西哥已经破产、重新出售的银行;巴西也有许多企业被外国资本廉价收购)。
二、国内大资产阶级和私人企业主阶层,特别是面向国外市场和与外资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可从现行改革中获取巨大利益。因此,它们对改革也持坚决支持的态度。
改革的中心思想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此,它们设计了一整套取消国家干预、推行完全自由化的政策措施。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改革实践,使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可以彻底根据资本主义市场规律,扩大他们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权,增强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方向,使之更加有利于资产阶级。这是一种无形的长远利益。同时,由于改革措施的实施和拉美国家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大资产阶级也在改革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有形的直接利益。例如,有些国家的官员利用改革和私有化之机,把国营企业低价售给亲友,从中收取贿赂大发其财。而大资产阶级和企业主阶层则通过“知情者交易、情人交易”廉价收买国有企业,将国有资产变为私人资产,扩大自己的资本规模,继而进行再投资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再者,他们从劳动市场灵活化的改革中增强了雇工的主动权,限制和削弱工会的权利,任意解雇和辞退工人,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提高利润率,使社会财富更多地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收入分配金字塔的顶端。据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在拉美,个人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家庭,仅在1990~1991年就从8家增加到20家。而在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执政的6年中,随着私有化的实行,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从2人增加到24人。由此可见,国内大资产阶级是现行改革政策的受益者,以致提出十点“政策改革”主张的约翰·威廉姆逊也说,“墨西哥私有化对那些与显要人物有关系的人来说是滚滚财源。”
由于拉美国家现行的经济改革集中体现了上层资产阶级、大企业主和权势集团的利益,他们自然表示支持和拥护,并希望彻底进行下去,以便无止境地扩大他们的利益和财富。而当改革进程发生不利于自己的变化时,他们便表现出恐惧和担心。在这方面,阿根廷的例子或许能够说明问题。1995年11月,梅内姆总统试图推行激进改革措施,至少要解雇两万名公职人员、关闭100家官方机构、减少高薪公务员的工资时,得到“国内最强大经济集团前所未有的支持”。自1996年2月以来,政府实行以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减少机构和社会福利、取消国家补贴和增加税收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改革,受到工会组织和广大居民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导致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辞职。对此,国内企业主极为担心,特别是“八大财团惟恐改变政策会影响切身利益”。
三、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80年代末,当经济改革刚刚起步时,大部分工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可以分享经济恢复、特别是出口部门明显复苏带来的好处,改善工人和民众的经济状况,所以他们往往通过与政府和资方签订社会协议的方式,同意和支持政府的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工会领导层坚持反对态度。然而在经济改革的进行和深化过程中,取消国家调节、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精简机构、削减公共开支、压缩社会福利计划、实行贸易自由化等各项政策机制,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他们的经济权益和政治地位。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稳定宏观经济的成效,但却付出了失业率不断升高、收入分配更加两极分化、贫困化进一步加剧的社会代价。而这些代价都无一例外地落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头上。总之,他们非但没有分享到改革的成果,反而为改革作出了更大的牺牲,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更加“边缘化”的境地,从而对经济政策产生抵制和反对情绪。进入90年代后,特别是最近两年,这种情绪日益增长和扩大,并演变成各种形式的抗议和反对行动,从一个方面加剧了拉美国家的社会冲突。
(一)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接连不断。面对失业增加、生活条件恶化的现状,拉美工人阶级和各阶层劳动群众开展了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以维护其生存权和劳动权。从1989年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主要工会组织多次发动全国罢工,并伴有土著居民和劳动妇女参加的街头抗议和游行示威。在巴西,工人罢工和农民夺地事件时有发生;1995年2月,群众举行示威,抗议社会保险改革和私有化政策。1996年5月,智利煤矿工人罢工,要求恢复失业救济。1995年,中美洲变成一个“处在爆炸边缘的火药桶”:在巴拿马,群众开展斗争,阻止修改托里霍斯总统执政时期的进步劳工法;在哥斯达黎加,5万名教师举行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减少退休金;在尼加拉瓜,通信公司私有化和消减大学补贴的政策引起社会风潮,造成人员伤亡。1993年12月,阿根廷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市数千名公务员举行示威,抗议拖欠工资和反对腐败,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造成人员和财产巨大损失。1996年4月,巴拉圭发生抗议活动,工会领袖胡利奥·埃斯皮诺萨抨击“全球化导致失业”。
(二)群众斗争提高到反对现行经济政策的高度。拉美国家的人民群众认为,改革中的一些政策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损害了本国的民族利益。他们在争取自身经济权益的同时开展了反对现行经济政策的斗争。在墨西哥,1994年5月,105个群众组织联合示威,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村社土地私有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6年3月18日,7万多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执行石油化工业私有化计划。1994年5月至1996年3月,巴拉圭三个主要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就私有化举行公决。1996年,玻利维亚人民上街抗议,反对石油公司私有化。在阿根廷,自梅内姆执政以来,三个主要工会已举行五次大罢工,反对现行社会和经济政策。其中1996年8月8日的罢工波及首都和其他四个城市,使70%的工厂受到影响,全国70%的公共交通陷入瘫痪。改革中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也引起一些企业界人士的不满。1996年6月,巴西圣保罗工业联合会发出民族主义呼吁,前往首都抗议,得到企业家的响应。
(三)政治冷淡使社会缺乏凝聚力。拉美国家的广大中下层民众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其经济权益和政治要求一直为政府和政党所漠视。这次经济改革的各项政策被迫迎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但也给下层民众造成很大的冲击,使他们的社会处境更加恶化。因此,他们逐渐减少和丧失了对政府机构、政党以及民主制的信任,对国家的政治生活表现出冷淡、抵触和敌视的情绪。这种情绪首先表现为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1995年在拉美几国首都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本国形势表示抵制,认为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全面的社会变革。持此看法的人所占的比重在厄瓜多尔为61%,墨西哥为60%,巴西为58%,哥斯达黎加为57%,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哥伦比亚和乌拉圭为50%以上。[②]另一表现是,在选举期间人民拒绝投票的比重不断上升。1995年秘鲁、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市政选举,海地和危地马拉的总统选举,都反映了这种倾向。在同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地方选举时,最高选举委员会估计弃权率将达40%,而调查公司统计将达65%。这些情况虽不构成对政治局势的直接威胁,但至少可以说明拉美社会缺乏凝聚力,民主制度的基础不够牢固。正如玻利维亚总统德洛萨达所说:“改革减少了民主制度对部分居民阶层的吸引力。”
(四)反政府武装活动有所增加。在罢工和抗议行动不断发生的同时,拉美一些国家一度沉寂的游击活动再次出现,且在近两年间有所增加。1994年1月,墨西哥恰帕斯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与政府军激战,后经11个月的紧张谈判,与政府签署了《关于土著人权利和文化协议》。1996年9月,萨帕塔运动不愿被政府利用去攻打人民革命军,再次停止和谈。墨西哥另一支游击组织人民革命军,于1996年8月底在5个州向军警发动进攻并发表公报,提出了“推翻现政府和现行政治制度,建立自由和主权的祖国”的政治主张。哥伦比亚的游击队10年间一直坚持活动。1996年8月30~31日,该国资格最老、武装人员最多的游击组织——哥伦比亚武装部队,在首都和11个省的26个城市发动武装袭击,对政府的扫毒行动实行“战略报复”,酿成近几年流血最多的事件。秘鲁“光辉道路”在主要领导人被逮捕之后,现在又恢复活动。
综上所述,拉美国家通过10余年的改革,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换,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是以工人阶级和民众阶层失业增加和贫困加剧为代价取得的,其结果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连中等阶层也在不断失势。面对这种社会严重不公的现实,希望破灭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反对“致命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四、一些国际组织、政党和知名人士对拉美的经济改革产生怀疑,对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现象提出批评,并试图寻找新的发展模式。
早在1994年年初,刚刚卸任的智利总统艾尔文就指出,近10年强加的经济学说不能消除越来越大的社会灾难,市场“常常是非常残酷的”“它有利于最有钱的人,加重最穷者的贫穷。”[③]智利天主教工人牧师会主教阿方索·巴埃萨批评说,近几年的“增长是通过对工人的极端剥削实现的,工时太长,达11小时,而工资很低”。“政策探讨小组”的几位经济学家批评说,经济结构调整计划都没有考虑到人民的要求,带来了贫困现象加剧、失业增多和社会解体的副作用,因此“有必要对最近10年执行的经济调整计划作一次认真的检查”,以便“就适应本地区各国情况的目标和战略展开讨论”。拉美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格特·罗森塔尔在指出拉美国家社会福利恶化,穷人增多后告诫说:“如果再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当前形势就难以维持下去。”
在此情况下,一些政党和组织提出改变现行政策,寻找新的模式。1996年8月,阿根廷反对派政党——激进公民党和团结祖国阵线,要求改变卡瓦略执行的经济政策。1996年6月,第四次拉美和加勒比新兴经济会议提出应该设计新模式,注重社会发展,不能只注重富人的利益。同年7月,拉美左派组织和政党在第六次圣保罗论坛会议上讨论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仍是拉美的一种选择。国际组织和理论界的看法和主张,虽不能左右各国政府的决策,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现行改革存在的问题和受到的批评,说明拉美的改革在政界和知识界人士中的社会基础也不十分广泛和牢固。
拉美的经济改革经过10年后已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一些国家的政府准备调整方向,改变发展模式。早在当选之际就认为“新自由主义浪潮几乎在整个地区处于退潮”[④]的哥斯达黎加总统菲格雷斯,于1996年7月再次提出改变发展模式、着力解决稳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主张。同年8月,厄瓜多尔新当选总统阿夫达拉·布卡拉姆说,新自由主义把饥饿现代化理解为现代化,前政府的经济计划是失败的,他的政府将寻找一种与其对立的发展模式。但多数国家的政府仍坚持既定的改革,并针对改革过程中的问题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有的已经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看来,拉美国家如何正确地调整政策特别是调整利益分配,找到一种适合本国国情的、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促进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以便缓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扩大和增强改革的社会基础,使改革在较好的社会环境中顺利进行,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注释:
[①] 乔纳森·弗里德兰:《拉丁美洲努力克服改革带来的不利影响》,转引自新华社联合国1996年8月5日英文电。
[②] 拉美社哈瓦那1996年7月7日西文电。
[③] 尼尔斯·卡斯特罗:《拉丁美洲:这不是民主》,载墨西哥《时代》,1994年3月号。
[④] 同[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