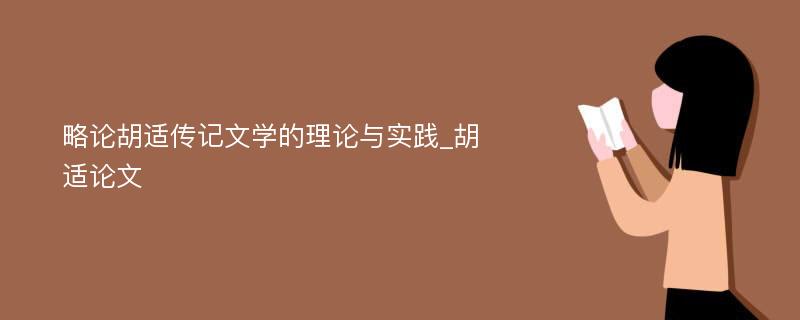
略评胡适的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胡适传记作品集》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传记论文,文学理论论文,作品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时时劝告和督促他的朋友们写自传。他在《四十自述》的序言里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注:《四十自述·自序》,亚东图书馆1933年9月版,第1页。)虽然他们都答应了,但很少,几乎没有人实践他们的诺言。胡适写这几句话的时候是1933年的6月。那就是说,胡适留学归国后不久, 他就开始劝促他所认识的朋友写自己的传记。接受他的劝告的人有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梁启超、林长民、梁士诒、熊希龄、叶景葵、陈独秀等。这些人都比胡适年纪大。最大的张元济要比胡适大24岁,最小的陈独秀也比胡适大12岁。而林长民、梁启超、梁士诒,当时都已去世了。
到了晚年,胡适在得读黄郛的夫人沈亦云的回忆录后,写信给沈亦云,信中感叹道:“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注:见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550页。)从这里看出, 胡适认为写自传需要几种条件,一是要有闲暇;二是要有文学的修养,三还要能自己保存许多“第一手”的史料。以这几条而论,胡适劝告过的那许多老朋友,除了没有闲暇以外,条件都是具备的。而胡适本人,保存“第一手”的史料最多,文学、史学修养皆甚高,也只因不得闲暇,而未能把自传写完。
胡适除了私下里劝告朋友写自传,还多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传记文学。听他演讲的人不免受到鼓励,因而对传记文学感兴趣。胡适对传记文学的提倡不是没有效果的。陈独秀于3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撰写《实庵自传》时,开头曾写道:“几年以来,许多朋友极力劝我写自传,……”(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552页。)这许多朋友,其中最重要者就是胡适,而且可以推想, 那其余的“许多朋友”恐怕也是受胡适的影响才劝陈独秀写自传的。陈独秀的《自传》,只写了前两章。他被释放出狱后,正值抗战爆发,没有了闲暇,无法写完他的自传。据我们现在知道,蔡元培先生也撰有《自写年谱》。梁启超、张元济先生等,虽未曾写自传,但为我们留下了大批珍贵资料,为后人编撰他们的年谱或传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两本很著名的传记著作与胡适有很大的关系。一是丁文江先生主持编撰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是张孝若先生编撰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谁都知道,丁文江是胡适最要好的朋友,而丁氏主编这部年谱稿时正在北大任教授,与胡适往还的机会甚多。胡适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序言》中,未提他在编书过程中是否参与过意见。只提到丁文江死后,他曾得到一部《初稿》油印本,签注意见后退回给梁家了。从保存下来的丁文江致胡适的信中可以看到,丁多次谈到编梁任公年谱的事。蒋观云所存任公的信,在上海由高梦旦主持抄写,抄件曾请胡适阅过,由胡适寄给丁文江。丁氏还请胡适帮忙,从浙江借孙仲愚的日记,摘录有关材料供年谱之用。
在1929年7月8日丁文江给胡适的信中曾具体说到:“任公的信已有二千多封!有用的至少在一半以上。只可惜,他家族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of Letters.”(注: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126—127页。)此信反映出,胡适对丁主持编写梁谱事,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做一部白话的新体《梁启超传》更是丁、胡两位朋友共同的心愿。
张孝若是张謇的儿子,他把撰写他父亲的传记看作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来做。他为此给胡适写过许多信,而且曾多次当面请教,他自认为他作成白话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是同胡适的影响分不开的。所以书成之后,他决定任何人的序都不要,只恳请胡适务必赐一序。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的《序》里未曾提及他与张孝若之间的这些来往,他只说“他(指张孝若——引者)生在这个新史学萌芽的时代,受了近代学者的影响,知道爱真理,知道做家传便是供国史的材料,知道爱先人莫过于说真话,而为先人忌讳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对我说,他做先传要努力做到纪实传真的境界”(注:见《胡适文存》三集卷八,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再版,第1091页。)。这里已可明显透露出,张孝若所作其先父的传记是受了胡适很大的影响。
胡适特别热心提倡传记文学,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够发达。这一点早在留学时期他就颇有所感。那时他已注意到中国旧体传记一则“太略”,二则“大抵静而不动”,即不能写出传主成长进化的过程,三则“多本官书,不足征信”(注:见《胡适留学日记》卷七,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版,第417—418页。)。后来他在讲演或为他人传记写序时有更进一步的发挥,并指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的原因。
胡适认为中国传记文学不发达有许多原因:第一,他认为中国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这一点,我从前在一篇文章里曾有所批评。(注:见《胡适研究论稿》第74—75页。)在古代,中国人最缺少“个人”的观念。一面是芸芸众生,蚩蚩群氓,一面是英雄圣贤。一旦被视作英雄圣贤,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神”,或至少是某种神意的体现。他们是被崇拜的偶象,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对这些英雄圣贤的记叙充满了夸张不实之词,甚至加上许多神秘色彩,根本无法与近代的传记文学同日而语。第二,他认为中国多忌讳,这是很中肯的批评。对先人有忌讳,对时人有忌讳,政治上有忌讳,信仰上亦有忌讳,总之是忌讳太多,无法用真实的材料写出一个人的真实的传记。第三是缺乏保存材料的机关,无史宬,无公共图书馆,无长久不衰的故家世族私人保存史料,再加上无长久的太平,每多战乱,资料容易毁灭。第四是文字上的障碍。什么骈文、古文、碑版义例等等,束缚史家,不容易做到生动传神。第五是,读书人一向把读经、解经、传经视为终生事业,不看重传记文学的价值,故向无传记专家。官修的传记,为官方服务,不重写实传真;私家修传,多为美化先人,故多谀墓的小儒,不足以养成传记的专家。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史籍中和文学中的传记作品就难以与西方国家的媲美,这是很遗憾的。中国历史很悠久,而历史上也不乏具有伟大人格和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为这些人乃至为一些虽平凡而确有可取的人们写传记,于历史,于文学,于人格教育都有极大的益处。
胡适提倡传记文学首先是着眼于保存史料,以补史书的不足,或为各种通史或专史的研究与写作提供基础。1943年,美国人恒慕义在房兆楹夫妇等50多位中外学者的合作之下,完成了多卷本的大书《清代名人传略》。胡适对这项工作极为赞赏,很用力地写了一篇长序。序言中盛称此书由于采用了许多官书不载的史料,尤其是利用了外文资料,所以是非常成功的历史著作,既可补中国官修史书的不足,又可补中国学者记载的不足。“史料的保存和发表都是第一重要事。”(注:《胡适致沈亦云的信(1960.10.4)》见耿云志、 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第1550页。)这可说是胡适的名言。要写历史,总是史料越丰富越好,越充分越好。而史料的保存受种种条件限制,往往是很不容易的。若史料被利用起来,以各种不同形式流传,就增加了长久保存的机会。比如有些古人的著作失传了。但距古未远的人,读过这些著作,把他们经眼的材料收入自己的著作中,那些失传的著作或其残篇便得以流传后世。研究历史可有许多切入点,写人物传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一个人物,特别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往往涉及那段历史的许多问题。所以一篇写得真实而又充实的传记,可以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原料,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例如,《李超传》中所保存的材料,可使人知道中国旧式家庭制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女子地位是如何的低下,进而了解五四时期的青年何以那样热烈地赞成新思潮,反叛旧的家庭制度,追求个人的解放。又如,读《詹天佑先生年谱》里的材料,不能不使人震惊,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路,人人皆知是中国早期铁路史上工程最为艰巨的,而每公里耗资却比外国人主持修建的津浦路、京汉路、京奉路都节省甚多:
以平均每公里用银元比较:
津浦路11.9万元
京汉路9.56万元
京奉路9.46万元
京张路4.86万元
此外谱中还有许多具体材料反映出詹天佑主持京张路的建筑,弊绝风清,为国家节省开支,而所修之路却是一流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在经济上受外国人的剥削有多么严重!由此可见,詹天佑先生,这位爱国的工程师有多么伟大!而这些材料都可为中国铁路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政治史提供很有用的材料。
传记的另一个巨大功用是有裨于人格教育。正因有此认识,胡适早在《竞业旬报》时期就写了很多短篇的传记,把他认为有贡献于国家与社会的人写出来,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他说过,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有“四福音”,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弱音”其实都是基督的崇拜者记下他的言行,以教育后人的。胡适说“《新约》里的几种耶稣传记(即上述的“四福音”——引者)影响了无数人的人格”。古希腊的“布鲁达克(Dlutarch,应为Plutarchos,今译作普鲁塔克——引者)的《英雄传》影响了后世的许多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曾国藩,抛开其功过不说,他的语录、家书、日记(这些都是重要的传记材料)也曾影响了中国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人,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见人物传记有巨大的教育作用,这是毫无可疑的。所以胡适自己曾拟编选传记丛书,一则发挥其教育作用,二则以为提倡传记文学的参考资料。(注:参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第272—280页。)
提倡传记文学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训练年青的历史学者。历史无所不包,马克思说过,我们知道唯一的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大意)。世间一切皆可成为历史的材料,皆可入历史的范围之中。所以搞历史必有一个具体的题目方可入手,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件名物的来历,一项历史活动的发展,一个思潮的来龙去脉,皆可成为专题。而这其中,选择一个人物做为题目,比较最具体,搜集材料,比较有范围可循,材料到手也比较易于整理成一个系统。这是从容易的方面说。从难的方面说,要揭示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展示人物活动的心理过程,显现人物与当时代各种人物,各种思潮,各种运动,各种事件的关联,所起的作用,所生的影响,等等,这就很不容易了。所以,人物传记可深可浅,可繁可简,可高可低,其中差别不啻万千。人物传记从容易入手的方面说,最便于训练青年史学工作者;而从其可深、可繁、可高的方面说,则正是显示大手笔的好场所。胡适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里,在列举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大人物值得为之作传之后说:“许多大学的史学教授和学生,为什么不来这里得点实地训练,做点实际的史学工夫呢?”
胡适对传记著作的第一个要求是必须写实传真。他说:“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为达到纪实传真的效果,他要求“最要能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亚东图书馆1930年10月版,第1088、1089页。)这样的写法,古文是难以做到的,所以胡适极力提倡用白话写传记。
胡适对于传记的第二个要求是必须“抓住传主的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为了说明这一点,胡适把传记与年谱严格分别开来,他认为,“年谱只是编排材料时的分档草稿,还不是传记。编年谱时,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但作传记时,当着重剪裁。”剪裁的方法即如上述,即抓住传主最大事业,最要主张,最热闹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其余的细碎琐事,无论如何艰难得来,无论考定如何费力,都不妨忍痛舍弃。其不在舍弃之列者,必是因为此种细碎琐事有可以描写或渲染传主的功用。”(注:《黄毂仙论文审查报告》,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第679页。)
胡适的这个主张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他关于传记与年谱的区别的议论,尚可商榷。
年谱并非皆是为写传记而预备的“分档草稿”,也不是所有材料细大不捐,完全没有剪裁。现在差不多所有中国的史学家都能承认,年谱是传记之一种,历来出版流行的年谱,都不像胡适所说的“凡有年代可考的材料,细大都不可捐弃,皆须分年编排”,而毫无剪裁。例如胡适先生很称赞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就已作过很大的剪裁。编者曾收集梁任公书札上万封,而年谱所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至于梁先生的著述、活动事迹则更是大量地略而未记。难以相像,像梁任公先生那样一生精力充沛,活动舞台甚大,事迹极多,著述极丰,若按胡适先生的说法去编他的年谱,其卷帙不知要比现在所见的年谱大出几十倍,几百倍!以笔者所见之年谱,稍稍近于胡适所定的标准的,大概只有胡颂平先生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但此书因其缺少剪裁的功夫,而颇受学者批评。有几位学者以拙著《胡适年谱》(注:《胡适年谱》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与之对比,称誉拙著“剪裁得当”,而对胡颂平先生之《长编》颇加苛评。其实,以年谱的功用而论,胡颂平所编之书,自有其特别处,不宜苛责。我将年谱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保存材料而编的,一类是作为传记之一种而编著的。前者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为写传记做准备而编写的。如丁文江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又一种是作者觉得自己功力识力不足,只编年谱,不写传记;或自觉写传记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为保存材料而暂编年谱。胡颂平先生似乎即属于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年谱与传记的区别,似不应以剪裁与否来做主要标准。其标准当别有所在。照我的看法,年谱与传记的主要区别有二:一是体例不同,年谱绝对须按时序编排材料,而传记只须把握大时段,而不拘年月的先后。二是写法不同,年谱一般只记事实,基本不作或极少作分析评论,而传记则容许有很集中的分析评论性的大段文字。愚见如此,当否,尚祈方家评正。
1930年11月,胡适从上海携眷迁回北京。12月6日,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茶会欢迎胡适重回北大任教。在傅斯年致欢迎词后,胡适略作答词,其中说到,他一生抱三个志愿:一是提倡新文学;二是提倡思想改革;三是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定论(注:见《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影印本第10册,1930年12月6日条。)。胡适的这段自白,大体是可信的。 但平心说,“提倡思想改革”一项,不能说“实行无力”。在这一方面,他播下的种子颇不少,收获亦颇可观。这里不赘。我想说的是,在提倡传记文学方面,也可以用胡适自述的八个字来批评:“提倡有心,实行无力”。
粗略统计一下,胡适所写的传记作品大约近百种,约140 万字左右。其中为他人写的最长的传记是《丁文江的传记》,约12万余字。其《四十自述》加上《逼上梁山》一章则只有八万五千字左右。而其《口述自述+-》,作为他与唐德刚合作的成果,其中正文有16万余字,可算是其传记作品中最长的一种了。胡适的传记作品大多是短篇的传记,他本人常以中国只有短篇的传记,而无长篇的传记为憾事,而他自己也甚少写长传,这也是他“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之一证。
胡适所作较长的传记,仍以《四十自述》写得最好。胡适写这篇自传时,正当盛年,思想、文字皆处于“最佳状态”。惜其太忙,而未能按照初衷写成真正的“传记文学”作品,而且也没有写完。其《序幕》一章与后面的正文,风格明显不同,而正文中前两章与后面各章又略有区别。胡适自己说:“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后面还说到,序幕一章“颇有用想像补充的部分”——引者)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注:《四十自述·自序》第4—5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心目中的传记文学,与严谨的传记史学是有区别的。但他从未集中地给我们指出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应如何区别,或者说,传记文学应具备哪些特征。大概其《四十自述·自序》是涉及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一篇文字。这其中有三点可以注意:一是传记文学容许“用小说式的文字”;二是容许“用假的人名地名”;三是容许“用想像补充”。这三条,尤其是后两条,我看很有问题。前面提出,胡适对传记的第一要求是“纪实传真”。如果允许用假的人名地名,允许用想像来补充,岂不违反了纪实传真的大原则了吗?所以照我的看法,传记文学与传记史学不宜加以明确区分,所谓传记文学,只是要求史学家用带文学性的生动语言来叙述真实的人物事迹。这里“文学性的生动语言”,不是忽视“纪实传真”的原则,而恰是为了进一步地达到纪实传真的效果。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即是要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读者如见其人,要使读者感觉真可以尚友其人”。在这些地方,显然是需要一些文学的修养才能做到的。而这样做,并不虚构情节,并不是夸张不实。我想传记文学容许文学的成份,不应超过这个范围,如果超过这个范围,那就必定违反“纪实传真”的原则,那就不是历史了。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传记文学,但没有为传记文学提供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界说,也没有实地完成一个完整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这又是他“提倡有心,实行无力”之一证。
但胡适的传记作品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四十自述》前面已经提到了。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略加评述。
《章实斋先生年谱》,作于1921年,1922年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姚名达先生增补,1931年,出增补本)。此书最大的特点是“不但要记载他的一生事迹,还要写出他的学问思想的历史”。前人作年谱,“单记行事”,不能表现谱主的思想变迁。胡适打破此惯例,于谱中分年编入章氏的重要著述,并注意谱主与同时人的关系,及他对差不多同时代学者的批评。这些皆属创例。其次,前人作年谱,对谱主只作褒扬之辞。胡适对章学诚既有肯定、赞扬之辞,也有批评之语。这也可说是一个创例。故此书出版,很得历史学家们的好评。不特因为它是国内学者第一部研究章学诚的专书,而且因为作者有超过前人的识力,独能表现出章氏对史学的卓越贡献,并揭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章实斋先生年谱》的成功,也证明年谱是传记中可以卓然成立的一种体裁,而并不像胡适在《黄毂仙论文审查报告》中所说,只是为写传记作准备的“分档草稿”。
《丁文江的传记》,此传是为纪念他的好朋友丁文江先生逝世20周年而写的。1955年秋天动笔,1956年3月12日写完,在该年11 月出版的《中研院院刊》第三辑上发表,即以抽印本流行。至1960年,始由启明书局出版单行本。这部传记的最大特点,它是彻底的白话的新体传记,几乎白到不能再白的地步。即以其书名为例,本来《丁文江传记》即可以了,胡先生偏要加“的”字。正如他的日记一定要名为《胡适的日记》一样。再就是体例,他从丁文江的一生中选出17个题目来写,这无疑是新体传记的写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胡适在此传中大发“考据癖”。每就一事,比较有关记载,作一番考据,再得出自己的判断。一般新史家作传记,正文直按自己的判断来写,而把考据文字放在注解里,最多只容纳一些极关重要的考证,而把一般的小考证放在注文里。这样在行文上比较方便。胡先生则视考据极重,故堂堂正正地都作在正文中。
因为此传是应中研院同人要求,为纪念丁逝世20周年而赶写的,加之,胡适在海外,有许多重要的材料都见不到(如《努力周报》,如丁任上海总办时的文电资料,以及丁的信札日记等等),所以这篇传记很不完全,也不够丰满。以丁文江的人格、事业,当得起一部更充实的大传记。
胡适的传记作品以短篇著作更为成功。例如《李超传》,写于1919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狂飚突进的年代。胡适依据很有限的材料写出一个年仅二十三四岁的青年女学生,幼年失怙,在嗣兄的威压之下痛苦生活,求学无路,最后郁郁病死的悲惨命运,使读者不能不对这位“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牺牲者”产生深切的同情。《荷泽大师神会传》,写于1930年1月。 收在当年出版的胡适整理编辑的《神全和尚遗集》中。胡适主要依据他自英、法两国所得敦煌卷子,其中包括神会和尚语录及其《显宗记》等,加上国内原有史料,进行相互比较参证,写出神会和尚如何以南宗的顿悟教义打破北派渐修的教义,逐渐争得群众,并争得朝廷的信重,从而确定了“顿教”的统治地位,完成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但胡适作此传时,似颇注入“气”与“情”(用章学诚的说法)的成份。所以,我在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胡适此文颇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块垒的意味”。《高梦旦先生小传》,写于1936年11月,文仅2400字,但把高先生一生脚踏实地,努力于改革的奋斗向上的精神和他待朋友、待家人真挚而平等的态度写得非常亲切,生动感人。
胡适关于几位思想家、学者的思想评传写得尤具特色。例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等等,篇幅虽不很长,但对于几位传主的行实、思想有非常精要的介绍,尤对其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有很中肯的批评。这些地方最能显示胡适善于分析又能概括的大手笔。
中国传记史学本有自己的渊源和传统,但长期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一是篇幅太短,绝少长篇的详传。二是受“春秋义法”的局限,重褒贬而不重客观的记述,往往陷入谀颂与诋毁,于历史的研究有不利影响。三是文字刻板,不很讲究结构,以至未能发展出近代式的传记。中国新式的传记史学在民国时期才略有基础,而真正繁荣,实始于近20年。这是因为第一,材料的发掘有重大的进展;第二,忌讳减少了,史家比较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三,外国史学的借鉴更多了;四,如今的读书人,大体都能相当纯熟地运用白话的国语作为写作的工具。(民国时期白话固然早已盛行,但史学家们远不是都能很好地运用白话著书。只要检索一下民国时期的史著便可清楚,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有了这几个条件,近年来人物传记出版甚多,其中颇不乏写得很好的。我们现在印行胡适先生的《传记作品集》,一则可以了解前代史学家提倡新式传记的苦心,二则仍可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相信我国的新式传记史学,会有更大的进步。
标签:胡适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丁文江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人物传记论文; 丁文论文; 自传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