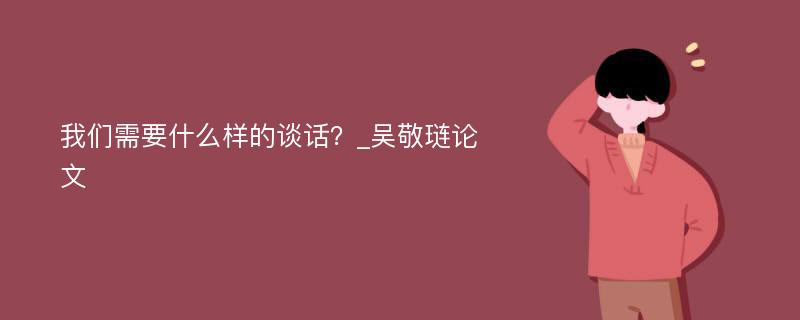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要什么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中国股市的一些言论引起各界争议,而且牵涉的人物日广,口气日重。作为旁观者,对其中发生的许多争议很是不解。
吴敬琏一言毁股?
第一,有人将呈氏言论视为最近股市下跌的“导火线”甚至是根本原因,这让我们大惑不解。吴敬琏是何许人且有如此神通?他是央行行长?当年格林斯潘对美国股市发生“非理性亢奋”的评论,股市不是照样涨?
反之,如果此论正确,那么我们不得不对深沪股市发生疑问:不是说10年来我们的规模、我们的机构力量是如何如何壮大吗?为什么此时又会如此脆弱呢?只要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能一言兴市或毁市,这个市场能够让人信任吗?
退而言之,如果吴敬琏有如此能耐,我建议有关方面一定要对老先生晓以大义,因为我们的股市还有诸如违规资金入市等多种“利空”因素,届时要请他出来说些好话,股市便稳定了,多好啊!
记得2000年春天,吴敬琏对国内网络股热质疑,也引来轩然大波。但不幸的是由于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暴跌,引发了中国网络业的萧条。那次老先生比较幸运,美国的投资人士和经济学家没有将网络业的泡沫幻灭归咎于他,而国内的反对人士也只能无言。不过我们假设,如果没有美国纳期达克的暴跌,吴敬琏极有可能早已惹上麻烦:以反对网络业(其实是网络业的泡沫),就是反对“新经济”而反对“新经济”就是反对“科技兴国”。所以当一些人此次在反击吴敬琏的时候露出此意,我颇为担心,有人要跟他“讲政治”了(庄家吕梁也最喜欢说“讲政治做大势”)。
五六年来吴敬琏一直坚持他的观点
第二,吴敬琏的股市看法其实并不“新”。因为早在1994年第八期的《读书》杂志上,吴敬琏就发表了题为《何处寻求大智慧》的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中国股市的观点,包括现在被人们议论的看法。而且,这些观点很快得到了证券界乃至经济学界的重视,1995年6月开始在《上海证券报》上以“寻求证券市场大智慧”的专题讨论形式推出,共出了30个整版,刊登文章逾百篇,累计文字20万字;后又结集出版,初版很快售完又再版。现在参与争议的人大多或亲自参加或看过这些讨论,想必不会觉得吴老先生是“突发奇想”吧。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次讨论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比较平和的,没有出现诸如对吴先生“清绪化”、“偏激”、“不专业”之类的评价。
问题来了:既然吴敬琏的观点一直未变而且一直在说,偏偏到了世纪之交又被人讨论质疑,是何缘故?
有人也许会说,从吴敬琏当年提出这一观点算起,中国证券市场又已经发展了五六年了,你老先生竟然对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所以要争议一番。但是,如果吴敬琏的观点落伍了,为什么还有如此震撼的力量呢?否则也不必引来反对人士如此大动干戈集会声讨。老先生被央视的民意调查视为中国最有“人气”的经济学家,难道投票的人都那么糊涂?
我认为,这五六年来不仅证券市场在发展,整个中国社会也在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规模的硬件上,也表现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与理念的软件上,换句话说,另一种力量在觉醒。
怎样准确理解学者的思想
第三,我们是否能够在未搞清被讨论者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前,断章取义地挑出几个论点几句话,就大大发挥一番呢?
一个学者,面对不同的语境,用的词汇表述会不同。如面对大众化的电视媒体和小众化的学术杂志表达方式肯定有相当差异。我们讨论要按哪一个文本呢?我想应该按吴敬琏自己的学术性表达为准吧。
第四,因为缺少了吴敬琏较为严格的学术表达,让我们对“全民炒股论”、“赌场论”没法讨论,或者不知从何说起。所以在这里我只能结合《何处寻求大智慧》,对这些带有歧义的观点谈些简略的个人看法。
应该承认,吴敬琏提出的这几个观点并不似表面上那么容易理解、那么浅显。当年我看到《何处寻求大智慧》后,开始认为大致能够把握,所以决定展开讨论。事后,我知道问题绝不那么简单。所以以后的5年中一直在研究学习,读了大量的中外证券市场研究文献,至今仍觉得棘手。
股市像赌场,不是说它的定位和功能像赌场
现代风险管理理论,是当今资本市场投资人士的必修课,但它的缘起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喜欢赌博和数学的法国绅士向著名的数学家帕斯卡提出挑战,让他解决一道难题。这个问题是如何将一盘未结束的赌局的筹码在赌博双方之间分配,其中一方已占据上风。这个问题直接引发了风险概念的核心——概率论的产生。
在以后的风险管理理论发展的历史上,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成为许多学者津津乐道的案例模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看看伯恩斯坦的《与天为敌——风险探索传奇》,它是国外投资界的经典书目,已有中译本。
如果撇开字面联想,我们应该承认股市在许多方面确实像赌场,且不局限于在中国。再说远点,期货市场更像赌场。换句话说,股市弄不好就会呈现出赌场的问题。请注意:我们说股市“像赌场”,并不是说它的定位和功能和赌场相似。惟其如此,我们要警惕股市成为赌场,要有符合股市定位与功能的游戏规则,要有合适的监管。
在这里,让我们引证一些吴敬琏在1994年的《何处寻求大智慧》中对有关股市与赌场的观点:
“总之,证券市场的基本作用,是通过股票转让和股价变动,实现资本的优化重组,并对公司经营做出评价和对经理人员进行监督。证券市场能否实现这些重要的功能,取决于股票的市价是否反映它们的真实价值,即发行股票的公司的盈利状况。为了使股价在不断的买卖中趋近于反映公司盈利性的水平,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的投机者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这种条件下,投机活动有它的经济功能,有利于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证券市场的不完全性决定了股价并不能经常反映公司的盈利水平。当代微观经济学已经确切地证明,股市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市场,它的价位高低往往由人们的心理预期决定,而不存在一个能够保证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均衡点。当股价脱离它的真实价值而飚升时,股市就会为投机活动所左右,成为过度投机的市场或完全投机的市场。单纯投机无异于赌博,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和价值增值,而只是造成财富的再分配,从输者的口袋转到赢者的口袋。再考虑到税费和手续费抽取了一部分,赌输的概率必然大于赌赢的概率。只有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才能稳操胜算。
“与此同时,股市交易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于是有些人就可以利用证券市场的这种特性,运用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操纵造势、进行‘内幕交易’等手法,进行金融欺诈活动,牟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各国无不制定严格的规则,对证券市场进行严格的管理,对非法牟取暴利者实行严厉的惩罚,以保护大众的利益。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诈骗丑闻也是经常出现的。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发生货币过量供应的情况下,证券市场就很容易和房地产市场、期货市场等不确定性很大的市场一样,在人们的赌博心理的支撑下,出现哄抬价格的投机狂热。这时,人们为追逐价差暴利而纷纷入市抢购,于是‘越涨越抢,越抢越涨’,形成‘气泡现象’,似乎财富不吹自胀,所有的人都在一夜之间发了大财,其实物质财富并没有增加,‘气泡’也终有一天会破灭,当出现‘崩盘’的现象时,正反馈的过程完全反转过来:‘越跌越抛,越抛越跌’,使持股者全被‘套牢’,大量的股民破产。‘气泡经济’沿着价格上扬——狂热股机——诡计诈骗——急剧崩盘这样的轨迹运动。不论狂热投机,还是急剧崩盘,都对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冲击。”
《何处寻求大智慧》又引用了美国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说:
“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很高。而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只是有钱人游戏赌博的地方。股票市场当然重要,人们可交易其股份和风险。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筹措用来投资的资金的十分重要的场所。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20年里,新股的发行,远远赶不上企业购回现股的规模,从而资本在股票市场是净流出。具体来说,新股减去回购对追加投资的比率是负9%。在其他发达国家情况好一些,也只有20%左右。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股票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架构,但不是融资的重要来源。”
全民炒股是什么意思
至于所谓“全民炒股论”,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要死抠字眼,那么我们就会陷入统计数字的争论,似乎非得有1亿甚至2亿人炒股,才能处“全民”。还有从字面理解,认“全民炒票”是人民投资多元化的权利,美国人也是这样吗?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吴敬琏的“全民炒股”这个词缘起于像日本和我国台湾等地曾出现的普遍过度投机心态造成的金融泡沫问题。也就是说,“全民炒股”指的是一种忽视实物资本的生产、过分投入金融虚似市场的现象。而如何把握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的关系,不至于让后者影响乃至破坏前者,这个度不好把握。像亚洲金融危机就出现了类似问题。
对这一点,《何处寻求大智慧》是这样论述的:
“从中国文献看,早在1992年10月,正当中国股市牛气冲天,市价/盈利率被炒到了200倍以上的荒唐高价位,某些股评家对它‘辉煌业绩’歌颂备至的时候,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曹宇、汪福安著的《警惕!股市的狂跌!——中外股市风潮实证分析》一书。这本书虽然编写得有些粗糙芜杂,但是收集了中外历史上有关股市投机和金融欺诈的众多案例,并从中引出一系列重要的教训。光是书中‘狂跌必将到来’、‘警惕股市的狂跌’等标题,本来就足以让那些做着‘入市即能发财’美梦的人们警醒。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虽然人们用无数事实说明了股市赌博的风险极大和‘久炒必输’的道理,还是成千上万的人为自己大发横财的利欲所驱策,被某些‘行家里手’所误导,进了圈套。”
《改革》杂志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台湾岛是怎样落入‘金钱游戏’的陷阱的》一文,给人们讲述了80年代末期台湾投机狂潮的惊心动魄:‘六合彩’烧遍全岛、数百万人参加股市赌局,‘地下期货公司’和‘地下投资公司’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肆无忌惮地进行金融诈骗。正在人们为自己旦夕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而欣喜若狂之时,发生了必不可免的投机市场崩溃。那些手握亿万财富的人们突然发现,那纸上的钱财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文章的作者在讲完这些故事以后写道:“本刊1993年第4期曾发表两篇评述日本泡沫经济的文章,连同本文,这三篇文章虽然描述的是发生在日本、台湾的故事,但在中国大陆,在阁下身边是否也显露出类似的迹象呢?”
最后是“市盈率”问题。用市盈率的高低判别股市高低,确实是个经验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股市的市盈率确实高企过到80倍,当时让各路专家目瞪口呆,纷纷研究日本何独特,于是出现了各种解释。但可惜日本市盈率高企的神话很快破灭,从当时的39000点跌到现在的13000多点。
中国时下的高市盈率是否又是个特例?或者高市盈率背后有其特点?这些问题需要今后的事实给予证明。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对此作出判断预测,但目前判别谁对谁错都为时来早。无论如何,将自己的东西(不管是企业还是整个市场)视作经济规律的特例,必须要冒付出沉重代价的风险。日本股市已经付出了10年代价,而且至今没有复苏的迹象。
对话应有建设性
第五,建议大家在相互讨论中,应保持“费厄泼赖”(公平)的精神,不要给对方下一些与学术争论无关的定义,尤其是带着明显情绪化的口气。因为我们在观察讨论中已经发现,不少人给吴敬琏带了不少帽子,帖了不少标签。
——比如“情绪化”,这个词语是种主观表达,因为你无法证明吴敬琏的“情绪”在哪儿,更谈不上“化”。
——比如“感性”。首先,投资市场就是个需要感性或者说需要直觉的地方,所以感性观察市场没什么不对;第二,感性与理性是互补的对立统一,像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科学理论既是理性又是感性的统一,只要大家注意那些简洁的公式是多么富有美学意味就可明白。真正的学术就是歌德所言的“诗与真”的结合。
——比如“不专业”。貌似晦涩的术语未必专业。如果你对它没有真正理解的话,比如说吴敬琏“不专业”的人对“坐市商”等概念就没搞清楚过。股市上似是而非的东西本来就很多,中国的股市的历史还很短,我们都容易犯错误,我们仍需要学习。同样,深入浅出的语言也未必不专业,你没有理解就说对方不专业。
——比如“有资格”。炒过股票的人可以谈股票,没炒过股票的吴敬琏也可以谈股票,这里没有什么“资格”问题。没吃过梨子的人不知道梨子的酸甜,是对的,但未必什么梨子都要尝尝,然后才能了解谈论梨子。
——比如“用道德而不是经济学判断”。首先,经济学和论理学并不截然分开,而且是紧密相关的。古典经济学的的鼻祖亚当斯密对道德哲学的造诣就极为精深。在这里,我不必引经据典,因为我相信像有素养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吧)更能说清这个道理。
最后,但可能是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为讨论对手预设立场,不要将学术观点“泛政治化”,只要你对股市提出一些不同意的看法,就说你否定股市的成就,否定国企改革政策甚至改革开放。
总之,我们倡导建设性的、有规则对话和探讨,没必要掺杂过多的标签甚至似是则非的符号,更没必要预设对立“不爱护股市”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的《何处寻求大智慧》结语今天仍然值得咀嚼:“目前中国股市正处在从狂炒过热的不正常状态转向正常状态的痛苦调整过程之中。我们要做的,绝不是用政府托市、救市行动重新把‘气泡’吹起来,再造虚假的繁荣和再次崩盘的悲剧;而是要真正拿出大智慧来,妥善地、以代价最小的方式实现向良性市场的过渡,形成健康的证券市场,为投资者开辟通畅安全的投资渠道,为企业家创造广阔便利的融资天地,为我国市场经济创设能够促进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证券市场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