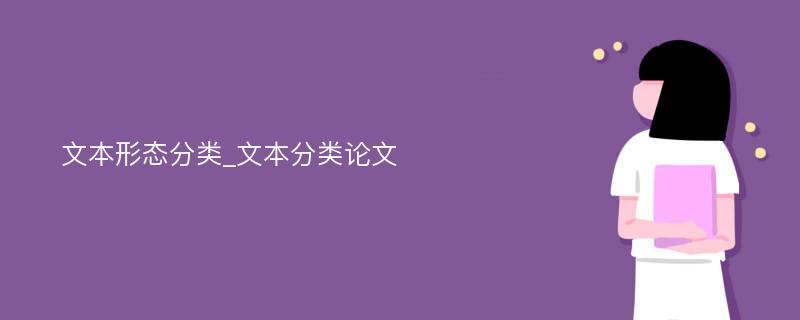
文本的形态分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态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305
根据文本存在的形态,可将文本划分为现实文本、意向文本和理想文本。现实文本是当前存在的文本,或者以往曾经存在于历史上某一处的文本,不管它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之中或之外,哪怕它过去仅存在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意向文本是仅仅作为作者的意向而存在的文本。理想文本则是仅存在于某一解释者头脑之中的文本,是解释者认为作者已创作或应当创作但事实上作者从未实际创作过的文本。
一、现实文本
存在于或业已存在于解释者头脑之外的文本,我称之为现实文本。现实文本又至少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历史文本、当代文本和中间状态的文本。对现实文本所作的这种进一步分类必须与文本存在的时间关联起来。
1.历史文本
历史文本是历史作者实际已创作出的文本。(注:文本的历史作者可能实际上并不只有一人,如《美国独立宣言》。参见作者的《文本及其解释》。)它由历史作者在一定语境中将特定意义传达给读者的历史的ECTs(注:ECTs即“entities that constitute text”(构成文本的实体)的缩写。——译者注)所构成。
当涉及创作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手写文本时,历史文本很少是以其原初的形式存在的,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有一个作者亲手写的文本或者有一个原文本的精确的摹本,那么就表明我们确有这个历史文本。(注:亲笔写的文本是指由作者创作的文本。它最初是指作者的手稿,但也可扩充至由作者创作但并非手写的文本。)而且,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在创作后很快就被作者修订过的文本,即使它最初并不是由该作者写的,我们也可假设我们有此历史文本。例如,在中世纪,由作者修订最初是由学生所作的笔记的这种做法是很普遍的。经过修订的笔记被称为笔录整理(ordinatio),未经修订的笔记则被称为报告(reportatio)。在某些情况下,作品因这些名称而闻名,或许这些名称是用以强调文本对历史的忠实。邓斯·司各脱的《牛津评注》就是如此,它就是作为笔录整理而闻名的,而他的《彼特·伦巴第〈箴言〉评注》的另一版本,则被称为《巴黎评注》。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会表现出可能并非只有一个单独的历史文本,而实际上有数个。托马斯·阿奎那某些著作的文本就是这样的例子。有时候,他亲手写了有关著作的一个文本,然后让一个抄写员抄写文本,并在抄本上修订而不是在亲笔写的那个文本上作修订。确有证据表明,在其一生中的不同时期,他又对文本作过修订。在这样的情况下,并没有关于一个特定作品的单一的历史文本。我们有的是对应于作者对文本进行修订的不同时间的数个历史文本。至于文本的意义是否实际上相同以及由此提出的文本的作品是否实际上相同,则是另一个问题。
2.当代文本
我所谓的当代文本,是指它产生时原来的语言形式可以为我们所获得的文体。一篇译文没有资格被称为当代文本,因为文本的特性包括与组成文本的符号相联系的条件,而文本译文中的符号不同于原文本中所使用的符号。当代文本是由当代的ECTs构成的,而当代的ECTs可在当下被作者用来传载作为历史文本之意义的意向中的作品。关于当代文本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通常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数个不同的文本。当我们涉及的是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本时,情况尤其如此。当然,在产生于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文本中,甚至也有这样的事例。
我们之所以会有数个当代文本,通常是因为有数个可追溯至一定源头的文本传统,以及以产生于不同时间的不同传统为基础的不同版本。例如,现今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就有数个版本,如皮阿那(Piana)版(1570)、利奥宁(Leonine)版(1888~1903)以及奥托瓦(Ottawa)版(1994)。(注:魏胥普尔(Weisheipl),《修道士托马斯·阿奎那》,第362页。)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可用的同一文本的版本之所以互不相同,乃是因为没有现成的作者亲笔写的作品,遗留下来的是整个文本的200多篇手稿(不包括仅有的42个附录)以及另外属于原作不同部分的235个碎片。在此情况下人们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文本,编纂者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手稿的世系图或家族树,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最有可能的文本。
但是,“最有可能的文本”的概念引起了一些需要回答的严肃问题。因为“最有可能的文本”并不必然是由作者创作的那一个文本或最具有历史影响的那一个文本。一个满足重建“最有可能的文本”的要求的版本或许是从未存在的、没有任何历史关联性的拼凑物,因为它在被编纂者重建之前从未像这样存在过。因此,19世纪的许多以形成最有可能的文本为方法论目标而汇编成的有关中世纪文本和古典文本的历史价值是很有限的。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后来许多编纂者致力于这样来编纂文本的版本:专注于一个好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版本即所谓的抄本,尽可能对它少作一些修订,并附上其与其他手稿的不同之处,以供历史学家和解释者们参考。(注:关于抄本概念及其含义,参见坦塞勒(Tanselle),《格雷格关于抄本和美国文献编纂的理论》,第167~229页。)不过,认为最有可能的文本是有选择地将所有可用的文本和文本传统加以完美结合的观念仍在流行。
重申即使是当代文本也很少是单一文本的观点是很重要的。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以各种不同方式相互关联的文本家族,它们的历史精确性依其与历史文本联系的紧密程度或大或小,它们的历史关联性依其历史影响力或强或弱。但是,文本的历史精确度并不必然地和直接地与其历史关联性成比例。当然,如果历史文本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作者亲笔写的文本,那么,在组成当代文本家族的诸文本中至少有一个是历史文本。不过,即使是近来创作的文本,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因为甚至在不仅有作者亲笔写的文本而且作者尚可自己处理的时候,出版商和抄本的编纂者在出版和编纂过程中也总会对文本进行修订。
3.中间状态的文本
我所谓的中间状态的文本,是指我们并不现实地拥有、也非历史文本的文本,但该文本在某一时间曾经存在过并在那时曾作为相对于某一读者的当代文本而起过作用。因此,中间状态的文本是已经毁坏或丢失的文本。它不是当代文本,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拥有它,尽管它在某一时刻相对于某些读者来说曾是当代文本;它也不是历史文本,因为它并不是由历史作者创作的文本。
我们或许知道,或许完全不知道有关该文本的任何事情。该文本或许在它产生后不久就被毁坏或丢失,而那些创作文本的人也并未传递过任何关于它的存在的信息,因而除了文本的创作者之外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或者,可能有一个丢失了的文本,对它的存在我们知道一些情况,因为我们有关于它的一个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该文本存在过,但我们现在并没有这个文本。有时人们找到了这样的文本,于是它们便成为当代文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仍然只是在一些历史记载中被提到。
中间状态的文本有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说明或有助于说明历史文本与当代文本的差异,表明当代文本不是历史文本而且并不直接依赖于历史文本。例如,在重建文本世系图的过程中,即使没有关于其曾经存在过的明确的历史记载,中间状态的文本通常也需要被置于其中。
二、意向文本
意向文本,如其名称所示,被认为是作者意向中要创作而尚未创作的文本。(注:采用这一概念的例子,参见坦塞勒(Tanselle),《文本的批评和解构》,第5页。卡瑞(Currie)在《小说的本质》第119页中将一种文本称作“作者意向中的文本”。)它并不被视为是作者已创作出的文本,因为这样一种已创作出的文本属于历史文本。当某人开始考虑作者在创作一个文本时并非故意犯下的错误时,意向文本的概念就出现了。例如,在口头文本或笔头文本中,作者可能会说出或写下一些并非他们意向中要写或要说的东西,他们可能使用了一些并非他们意向中要使用的词,只是因为他们当时不能想出更好的词来代替;他们可能错误地遗漏了词和短语;他们可能混淆了标点符号,如此等等。在许多技巧方面作者会误入歧途,使他们创作出的文本有别于他们意向中要创作的文本。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想说或写的东西与他们实际采取的方式之间总是不尽相同。一旦他们作了某种表达,它就成为文本的组成部分,尽管作者有时爱说他们所说的是另一个意思,因为在创作文本时他们并未想到他们寻找的那种表达。在他们使用模棱两可的表达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如果有人稍后问他们:“当你说R时,你指的是P还是Q?”作者有时会回答说P,有时会回答说Q,只有偶尔才会回答说R。仅仅当作者回答说R时,我们才可猜测这一模棱两可的表达是有意的。即使如此,我们永远也不能绝对断定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这一点,可能只是事后的认识结果。
作为对意向文本概念的进一步具体化,有人可能会指证这样的事实:作者在创作一个文本后会经常修订它,他们会回过头来把稿子改一遍,有时还会使文本的意义发生极大的改变。这或许说明文本并不精确地反映作者在创作它们时要表达的东西,虽然我们同样永远不能确定到底是作者所写或说的东西与其意向中要表达的东西一开始就有所不同,抑或不过是后来作者改变了他们对其意向中的东西的想法。
所有这些听起来都很合情合理,但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并不存在意向文本这类东西,其简单道理在于,在作者通过写、说或想而实际创作文本以前,他们对其意向中要创作的文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观念。(注:见尼哈马斯(Nehamas),《何为一个作者》,第689页。)他们对其意向中要做的事情至多也只有一个多少有些模糊的观念,或许是一个关于文本应如何被建构的思维轮廓,但文本仅仅在写、说和思考它时才被创作出来。
基于永远不会有意向文本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可能有人会争辩说,意向文本并不先于历史文本而存在。从时序上说情况的确如此,因为一个文本总是一个创作过程的结果,而不会以任何方式先于这一过程。(注:参看威尔斯默(Wilsmore),《文学作品并非它的文本》,第310页。)这是我想要坚持的观点。
我要强调的是,当作者创作文本时,许多因素影响着作者,它们对创作的各个方面起着因果作用。正如艺术客体一样,文本并不单独地源于作者,而是由作者、他或她的工作场所以及其他因素构成的复合体产生的结果。
于是,谈论作者所“意向”的文本而不是作者“历史地”创作的文本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意向文本。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人会争辩说,曾有一个要完成某个文本的计划,但由于作者的去世或某个类似的突发事件,文本没有被完成。但是,这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矛盾。理由有二:第一,当有大纲、笔记和计划时,文本的创作就已开始。实际上,有人认为笔记、计划和大纲就是文本的一个早期版本,尽管在这里没有经过进一步的思考我并不会这样认为;第二,在文本被历史地创作出来之前,关于文本会被怎样完成的,现有大纲和笔记都只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变更甚至丢弃的指导性原则。因此,即使文本的创作由于一些原因而被中断,说某个特定的文本是意向文本也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正如艺术客体一样,文本是已被创作出来的东西,其余的都只不过是多少有些模糊的冥思苦想。(注:我们将会看到,正如赫施(Hirsch)及其他人所说,这就是为什么文本的意义不能被归结为作者的意向的部分原因。)
有关文本和艺术客体的许多例子都可用来说明这一点。高第(Gaudí)留下的、已建造了近一个世纪并仍在建造中的巴塞罗那圣家教堂的建造计划,就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例子。高第留下了许多关于这个建筑建造方式的草图和说明,他甚至在去世前已完成了该建筑的某些部分。但在高第去世后接手该建筑的建筑家们发现,随着建筑过程的推进,他们必须作出无限数量的决定,其中有许多没有或许也不可能为高第所预见到。于是,事情很清楚,如果从一个完整建筑物的意义上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高第意向中要建筑的那个圣家教堂,曾经有过的只是一些关于圣家教堂的观念、计划和草图。
意向文本仅在历史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才作为解释者或历史文本作者的猜想而存在。在这一点上,作者自己或解释者会说作者意向中要写的东西是怎样怎样的,而不是怎样怎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历史文本被创作出来之前有一个意向文本,它仅仅意味着作者可能有一些历史文本遵循或不遵循的观念和意向。
意向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正如许多有着解释学关联的东西一样——源自不同的假设。第一个假设与《圣经》注释有关,后者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神灵是以不完美的媒介来宣示他完美的意见的。因此,尽管在神的意向中要宣示的文本在任何方面都是绝对正确和完美的,但由于是以人作为宣示的代言人,历史上创作出来的文本就可能出错。(注:与之相反的观点也是广为流传的,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是如此地关照他在人间的代言人,以致他们可准确地创作出他所希望的文本。参见布朗(Brown),《解释学》,第606页。)把这一观念应用于非神示的文本,就可作出这样的推论:正如上帝一样,文本的作者在创作文本以前头脑中已有了一个意向文本。
意向文本观背后的第二个假设是:意义即文本。因此,作者头脑中有一组会在作者的头脑之中或之外转化为文本的意义。这一组意义就是作者在意向中要转化为文本的东西,但意义在转化过程中会遭到损毁。与意向文本相等同时东西,正是这些意义。
第三个假设认为,原因必定明显地和实际地预先包含着出现在结果中的任何东西。因此,作为文本的起因,作者在着手创作文本之前,他们的头脑里必定实际上有了他们意向中要创作的文本。
当与第四个假设结合在一起时,第三个假设就显得似乎特别有力。第四个假设是我已质疑过的,它认为作者是文本的惟一起因。如果仅有一个起因,并且该起因必定实际上预先包含着出现在结果中的任何东西,那么很明显,作为文本的惟一起因,作者在创作文本之前头脑中就已有了他们意见中要创作的文本。
这4个假设都是很有误导性的。让我逐一讨论它们。关于第一个假设,让我们假设上帝的确宣示了《圣经》,并且在头脑中有了《圣经》作者已写下的和他们能够写出的文本,尽管作者会犯一些偶然的错误。即使事实如此,这也未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一个人间的作家怎样进行创作的事情,当然也不意味着在实际创作文本之前作者头脑中就有了一个我们已讨论过的意向文本。的确,与某些艺术家(如莫扎特)一样,某些作者(如罗素)似乎在将文本写出来之前头脑中已有了一个完整的文本。但这是一个误导性的反例,因为在这类情况下,他们头脑中的东西是已被创作出来并被存放在他们记忆中的思想文本。他们并不一定非要经历其他作者检查自己的笔头和口头草稿时必须经历的修订之类的过程,因为他们一直要等到思想文本完成后才会将它写出来。在罗素这类例子中,这通常是在某种教育体制下而养成的习惯的结果。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人们不会写出或说出任何不是以良好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些事例并不支持那种认为作者在实际创作思想文本、口头文本或笔头文本之前就有一个意向文本的主张。对于那个神启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作同样的讨论。某人可以说神意向中要宣示的文本并非是一个意向文本,而是一个在神的头脑中实际产生和完成并在宣示过程中被损耗和毁坏的文本。
第二个假设建基于两个混淆。一是作者的意向与文本的混淆。当着手建构文本时,作者就有了传达一定意义的意向,这看来是无可争辩的。(注:参看比尔兹利(Beardsley),《美学》,第17~29页;塞尔,《重申差异》,第202页。)的确,这样一个意向是文本的必要条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头脑中有了一个要传达的文本,因为一般的意向和创作文本的意向都不必然是文本。的确,与作者意向相应的精神现象并没有与文本相关联的特征。例如,追踪一个行为过程的意向并不就是“追踪一个行为过程”的文本的智力图像,而写“2+2=4”的意向并不就是“2+2=4”这一文本。
二是意义与文本区分的混淆。即使接受当作者着手创作文本时他们已有了意向中要传达的意义的观点,也并不意味着同意那些意义就是文本的看法。例如,某人想要传达的“2”的意义不是阿拉伯数字“2”的智力图像或任何其他用以传达这一意义的符号的智力图像。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一个文本不应与当我们认为我们已理解了文本时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即文本的意义相混淆。
在此,我必须指出十分重要而且不可遗漏的一点,尽管它有些离题。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认为在历史文本被创作出之前作者头脑中总是有一个意向文本,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作者在创作文本之前头脑中总是已有了他们意向中要用一个文本传达的意义,这也是错误的。当然,我并不绝对地断言意义依赖于文本。我的看法是,在文本的实际创作之前,作者头脑中已有了一个独立于意向中的文本的意义,虽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有些人会争辩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第三个假设也是颇具争议的,而且不能指望我们在这里解决它的有效性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指出因为作者并非如第四个假设所主张的那样是文本的惟一起因,所以即使我们接受某种观点,我们也不能由此推断说,作者在着手创作文本之前他们的头脑里必定实际上有了他们意向中要创作的文本。呈现在历史文本中的一切,必定实际上预先包含在这些结果的原因总体之中,而只不是包含在作者的头脑之中。因此,认为作者在实际创作文本之前必定已有了他们意向中要创作的文本的结论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第四个假设,我相信以上的论述已足以驳倒它。对此,我们已无需赘述。这样,让我通过再次强调意向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区别是无根据的,来结束这一讨论。最能为人接受的是下列这些区别:第一,历史文本与作者在文本创作之前所具有的某些模糊的、支离破碎的观念和意向之间的区别;第二,实际被创作出来的历史文本与清除了任何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出现于文本中的技巧性错误和誊写错误的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第三,头脑中的历史文本与其在头脑之外的实现之间的区别。实际被创作出来的历史文本与清除了错误的历史文本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是否经过仔细整理或修订的文本之间的区别,它不应被用作庇护关于意向文本的颇具迷惑性的观念的论据。
这样,一个意向文本就可被理解为或者(1)作者完全意识到的文本,或者(2)一组关于文本及其意义的模糊观念和意向。如果是(1),那么它相当于或者(a)历史上的物质文本,或者(b)历史上在物质文本之前的思想文本(两者都是历史文本,因为都是由作者在一个特定时间创作,尽管一个是在头脑中创作而另一个不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文本都表现为现实文本而非意向文本,因而关于区别于现实文本的意向文本的概念仍然无法证明其合法性。于是,惟一可使意向文本的说法变得有点意义的方法,就是依据(2)来理解意向文本。但这样一来,文本就必定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
三、理想文本
理想文本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注:格瑞萨姆(Greetham)认为,理想文本的观念可追溯至古代,并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对这个实际上是附和柏拉图的观念的理解上有若干方式。《〈文本的〉批判和解构》,第17页。)第一,它可被理解为由一个解释者创作并视为历史文本的精确摹本和历史文本的非精确版本。在这个意义上,理想文本之所以为理想文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史文本的历史作者并没有创作它,它是作者以外的某个人通过思辨而作出的推测;其次,它不是历史文本的一个精确版本。实际上,如果它是历史文本的一个精确版本,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它视为现实文本。第一种意义上的理想文本是由解释者创作的,因为解释者确信其所用的当代文本是不准确的。
第二,理想文本可被理解为由一个认为理想文本完美地表达了历史文本没有完美地表达的观点的解释者创作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理想文本之所以为理想文本,是因为它被视为由历史作者创作的多少有些不完美的摹本的一个完美形态(于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理想”就是柏拉图式的),而不是由于已经提到的与对理想文本的第一种理解相关的两个原因,尽管这两个原因也适用于它。这种看法假定:一个作者以文本形式对其观点的系统阐述,通常是以文本形式对其观点进行完美的系统阐述的多少有些不完美的摹本。根据这一假设,当一个作者对公正采取某种哲学立场时,他可能就是以一种不完美、不充分的方式来表达它,尽管总是存在着一个关于它的完美和充分的表达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这与正统的柏拉图主义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对于正统的柏拉图主义来说,观念都是关于绝对完美和真实的东西的观念,而这里论及的理想文本概念则意指能够存在对甚至是不真实并因此不完美的观点的完美的系统阐述。因此,例如尽管功利主义可能是不正确的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美的,但穆勒未能以文本形式很好地系统阐述的观点仍可以以文本形式作出一种理想而完美的系统阐述。
第三,理想文本可被理解为由一个解释者创作的完美地表达了历史作者应当表达的观点的文本,即表达了完美的观点或真实的观点(如果你喜欢用这个词的话)的文本。(注:当然,真理可能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那是完美的最终标准,因为并非所有的文本在功能上都是真理的表达。例如,文本也可表达感情。而且,站在这一立场上看,还有一个程度问题,一些人可能愿意采用“更好”的概念而非“完美”的观点。)对理想文本的这种理解与正统的柏拉图主义相一致。它超越了我们已论述过的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的理想主义,以绝对的口吻将最为完美作为理想的意义。
就其不是历史文本和那些努力建构它的人对它的认可情况而言,理想文本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理解者用于理解、解释和评估某一历史文本或当代文本的校正性概念而起作用的。它的用途在于,通过将文本的作者所做的与他们应做的相比照,说明在什么地方当代文本可能是不准确的,或在什么地方文本的作者可能犯了错误,以及在什么地方没有犯错误,它也可用于解释作者想要说但没有充分说的东西。这样的理想文本是解释学上和编史工作中的一个有用工具,尽管对它的使用会导致滥用。
那些努力重建理想文本的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他们能够在思辨的想象中合理地离开当代文本的程度有关。如果在重建中对当代文本的修订太大了,就会有这样的危险,即理想文本可能未向我们揭示出有关历史文本的任何东西及其要传递的观点。实际上,它所揭示的东西可能更多地属于解释者的观点。
这使我开始考虑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用于选择理想文本的组成要素和作为对当代文本进行修改的依据的标准。这个问题是:这一标准应包括个人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原则吗?采用不同类型标准的理想文本看来确有很大的差异。人们应该使用某套标准而不应该使用另一套标准,这在开始时绝不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如讨论中有的观点所主张的,理想文本的确立应该考虑个人的和文化的因素。文本毕竟总是由特定文化背景下一定的人所创作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产品。因此,将文化上的考虑纳入理想文本看来是恰如其分的。处于某某时代和某某地域的特定解释者创作的理想文本,应当是那个时代、地域和解释者的反映。另一方面,有些人会毫无疑虑地认为,个人的和文化上的考虑与一个理想文本的创作毫不相干,因为文本的功能是引起理解,相应地,用于建构理想文本和修改当代文本的标准应是哲学的标准。
但是,这一语境中的“哲学的”所意指的是什么呢?它是指“逻辑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创作理想文本的工作就在于检查当代文本,清除任何可能潜入它要传达的观念中的逻辑错误,也包括摒弃所有非推论性的东西并提出各种结论,这些结论曾因粗心而被遗漏,但却是从文本观点所依据的前提推出的逻辑结论和文本观点所依据的假设的蕴含。
但是,“哲学的”不仅仅是指“逻辑的”。它的意思可能不仅仅是指清除逻辑错误和使三段论的前提及结论更清楚,而且也指使那些为文本所系统阐述的隐约可见的东西明确起来。这一过程可能包括替代或扩展某些定义,以阐明不同的概念和观点等等。或者,“哲学的”也可被解释为增添一些比在历史文本或当代文本中提供的论据更具说服力,甚至也比以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而对这些文本表达的某些观点所作的修正更具说服力的论据。
当我们超越了逻辑并置身于诸如阐明、补充、替换、修改等步骤的建构理想文本的工作中时,我们也就超越了对历史文本试图表达的多少有些不完美的观点作出完美的系统阐述的任务。我们实际上是在努力建构与某一特殊历史文本论及的特定主题相关的所有文本的理想文本。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期望对不完美的观点作出最好的系统阐述,而是期望能有最好地表达了真理的文本。简而言之,我们已复归于正统的柏拉图主义。
根据所有这些讨论,我们应当明确:正如前文关于文本的例子中所讨论的,理想文本并非只有一个。它可以是相对于个人和文化而言的精确文本,可以是逻辑上正确的文本,也可以是清晰而完整的文本,还可以是表达真理的文本。这样,依其使用的不同标准,至少有4种不同的理想文本,尽管在每一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文本被视为最符合人们所讨论的那个标准。实际上,如果加上已提及的其他类型的标准,还可以有更多种类的理想文本。例如,可以有应用于诗歌文本等等的标准,它会使作为摹本的某一特殊文本的理想发生改变。这类标准应对比拟、隐喻、双关语等的恰当使用作出说明。实际上,我们所讨论的标准是什么或它应包括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所讨论的文本所发挥的功能决定的。
但是,在我们着手讨论功能分类之前,我必须指出的是,理想文本不应与历史文本的意义相混淆。文本和意义并不是一回事。为使问题简化,让我们暂且假设文本的意义是一组观念。这样,我们可以作出推论:已创作出的文本的意义是一组观念,而理想文本的意义也是一组观念。然而,理想文本概念背后的假设是:历史文本所表达的观念正是理想文本所表达的观念的多少有些不完美的摹本。但是,正如不完美的摹本一样,如果一个人接受这一假设,它们也可被视为理想文本所表达的观念。因此,就历史文本的意义应当是然而却不是理想文本而言,历史文本的意义与理想文本并不是一回事。不论意义是否被理解为观念,情况都是如此。
(本文译者:汪信砚,男,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430072;李白鹤,女,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