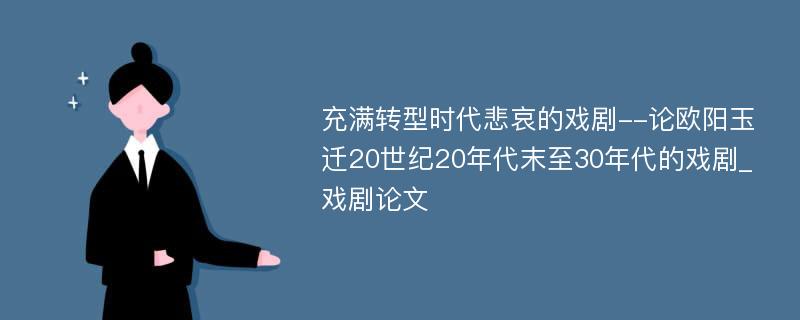
负荷着过渡时代悲哀的戏剧——论欧阳予倩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话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阳论文,年代论文,话剧论文,负荷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张庚先生曾说:“象欧阳老这样的戏剧运动的前驱者,他们从事戏剧活动,其目的往往并不局限于戏剧艺术本身,而是怀着救国救民,启迪民智的目的。”(注:《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序》。第2、48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启迪民智”,欧阳予倩不断调整自己戏剧生活的内容、方向、创作思想与艺术追求的目标。
自1907年19岁的欧阳予倩看“春柳社”演戏到入社、登台开始,他就下定了“挨一百个炸弹也不灰心”(注:《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序》。第2、48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版。)的决心, 选择了戏剧事业。此后,他涉足戏剧的各个领域。自编、演、导文明戏、话剧,期间又学演京戏,演了不足10年即已颇负盛名,此间又接触了桂戏(注:欧阳予倩1909年,在“春柳社”期间始学京戏,1912年正式演京戏,1919年已有“南欧北梅”之誉。1910年到广西接触桂戏——见《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欧阳予倩年表》。),到1927年,在南国社的“鱼龙会”上,他与人合演了自编的京戏《潘金莲》,“此后不再演京剧”(注:欧阳予倩1909年,在“春柳社”期间始学京戏, 1912 年正式演京戏,1919年已有“南欧北梅”之誉。1910年到广西接触桂戏——见《欧阳予倩戏剧论文集·欧阳予倩年表》。),不但演艺内容发生变化,创作精神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他自己总结说:“我从编《潘金莲》起创作思想有所变化,写了一些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短剧”(注:《我自排自演的京戏》。)同年 8月,欧阳予倩又应田汉之约到南京办国民剧场, 结果未能如愿, 他在总结此举始末时又说:“在近十几年来这样瞬息万变民不聊生的时局之下,我们也实在逼得一筹莫展……然而这是一时的,我们的步伐丝毫没有乱,工作一刻没有停,希望仍然十分热烈,心血时常一样的沸腾,我们在艰难困苦中,每每感到斗争的兴味,却随时随地负荷着过渡时代的悲哀。”(注:《自我演戏以来》。)这两段话,一是整体地概括了本时期创作精神的变化,二是阐发了当时的情绪心态。话剧创作体现了这一变化,是这种心绪的载体。
2
创作精神的变化在欧阳予倩的剧作中的具体表现、它带来的积极影响与负面作用是什么?
首先,作家对过去熟悉的题材的开掘,表现了更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纵深感。
《屏风后》是本时期继五四以来,以男女感情生活为题材从道德批判角度审视生活的剧本。但它与五四时期的剧作有了明显的不同。一是剧中被讽刺的对象康扶持具有更明确的政治背景,他先借“女革命党”的名义迫害为他始乱终弃的女学生,在两性关系中肆意使用“政治手段”,后以当时政权的基层社会道德维持会会长的身份出现,俨然维持社会道德的官方要人。无论从过去还是从现实中看,康扶持都不象五四时期的剧作《泼妇》中的以礼、《潘金莲》中的武松那样虔诚地维护旧道德信条。在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到,道德不过是他用来迫害、打击下层人,保护自己为非作歹的工具。这种行为、动机无不体现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剧作对这种人的批评已超过了道德批判的范围。实际上是借助对当时政权的这类社会支柱人格的卑劣、灵魂丑恶的揭露,达到讽刺时政与当时政权的目的。这种批评因为包含着真切的体验,饱满的感情,所以给人以美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二是,剧作的结尾,在充分揭露康扶持行为丑恶而又装腔作势大谈道德的特定情境中,借剧中人之口点明题意:“不要看这屏风小,几千年的道德,全靠这个屏风,会长,你要去这屏风是破坏道德,你要维持道德,你就应当先维持这屏风”。借此把具体的剧情升华,把现实与几千年的文明史联系起来,挖掘了现实虚伪道德的文化根源,增强了剧作的历史纵深感。
《屏风后》与五四时期以道德批判为宗旨的剧作比较,寓意更丰厚,既表述了时代的悲哀,理性判断的层次又有明显提高。这里的理性并非是用作品图解的教条,而是融汇于作家所构制的艺术机体中,成为这个机体的灵魂。《屏风后》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作家创作思想转变产生的积极影响。
其次,作家突破了五四时期热衷的婚姻、恋爱的狭窄题材,创作视野有了较大幅度的拓展。劳苦群众的生活、斗争,上层的腐败,社会的混乱、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在欧阳予倩的剧作中得到展现。本时期,欧阳予倩的剧作大体有三类,一是以下层劳动群众生活为主,并从这个角度写人生的不平、社会的黑暗。有较大影响的剧作如《车夫之家》、《小英姑娘》、《同住的三家人》。二是通过对暴发户、买办等邪恶势力的行径与灵魂的表现、剖析,暴露时政的腐朽。剧作有《屏风后》、《买卖》、《越打越肥》。三是反映社会上的重大事件,如十六景话剧《不要忘了》。
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作家从五四时期带着梦幻色彩的戏剧、文学天国,走向了多灾多难的现实大地。这时作家最先着眼的是“水平线下”劳动者的生存形态与心境。《车夫之家》写的是人力车夫家庭生活的一个片断——在外辛苦奔波的车夫,走进家门看到的是病重的儿子,无药可医,车租无着,女儿被辞,收房租的又来,灾难接踵而至。车夫的心几近破碎,他爱儿子,不能给他以温饱;爱妻子,却无力为她排忧解难;爱女儿,又不能帮她抵御欺凌,反要教给她忍受冤屈的道理。五四以来,写人力车夫的作品并不少见,但胡适在诗中(注:《人力车夫》。)表达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怜悯、同情,郁达夫在小说中(注:《薄奠》。)抒发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情怀,到30年代,欧阳予倩似乎感到怜悯、慨叹的无力,他只以写实的笔展现了下层人在生活的困扰下心力交瘁,已到生活、生命无法维持的境地。
与此同时,作家也探寻了下层人在民族危难中,精神风貌的迅速变化。《小英姑娘》以一个难解的恋爱纠葛开始——两个年青人同时看上了一个女孩小英,小英的母亲将女儿许给了其中的一个,小英却爱了另一个。两个年青人争执不下。至此,冲突没有按着单纯的爱情线索继续发展,作家引入了事外的因素——社会事变的参予,于是,事情的发展有了出人预料的转机。正当两个年青人相持的时候,忽然外边有人说,外国人打死我们的人了,传单要求大家去“齐队”(集合队伍,对付外国人)。其中一个年青人说“也好,把我们的事交给炮子罢!要是打死了我,小英就归你。”后来两个年青人很快明白,去“齐队”是因为“有人欺压我们”,不为私事。两个人一起跑出去,一会儿两个人都负伤回来,不久都因伤重身亡。小英姑娘看着爱人已死,对其尸体说:“报仇是我的事!为了你,为了大伙!”于是,狂了一样跑了出去。剧情也就结束了。不难看出,恋爱的矛盾只是一个引线,借此,作家一要表达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二要表现,在那种时局下,普通百姓迅速懂得将私怨融于公仇的精神风貌。
但整个剧情缺少必要的提炼,对情节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社会事件的介入显得突兀、生硬,人物思想变化也因缺少应有的铺垫、发展过程而显得根据不足,形象谈不上完整鲜明。这与当时“革命文学”强调思想意义,忽视作品的人物、情节有关。同时,这也是欧阳予倩本时期创作精神转变带来的负面影响——急于表述倾向性明确的主观见解,而这种见解还只处于理性判断阶段,未能熔铸成血肉丰满、精神充实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作家在试写下层人之初,手法的生涩。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克服。
1932年完成的独幕剧《同住的三家人》,对人物、事件、情节的处理,就显得自然、和谐、熨贴得多。在这个独幕剧中,作家以具体、丰富的生活细节、个性化的人物及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冲突,概括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透露出时代情绪的悲哀、无奈,并将偶然的事件与生活的本质意义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使剧作既有坚实的精神内涵又富有戏剧性。剧作选择了当时市民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事件——应付房捐。围绕这件事在以王素薇为主的三家人和有产者之间构成了筹捐——逼捐——付捐的冲突。巧的是逼捐的是有产者的代理人——警察,付捐的也是有钱人——暴发户,李十五。更巧的是逼捐人出现的时候,付捐恰好也“如期”赶到。这自然是一种偶然性巧合。但它又联系着生活中有钱人对下层百姓进行多方盘剥的本质。逼捐,为的是钱,有产者盘剥穷苦人的血汗;付捐,为的是人,李十五因对王素薇心怀不轨,才非要替她付捐,实则,就是出钱买人,企图剥夺下层人做人的尊严。从此可知,剧作家对社会矛盾的内容、程度已有准确的把握,并善于把生活中的矛盾,提炼成戏剧冲突。
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已比较熟练地在冲突中写人物,并将人物个性描绘得很有层次感。剧作家赋予主要人物王素薇沉静、稳健、早熟的个性。这一个性在日常生活中有表现。比如邻居家为凑不足房捐而焦躁、争吵时,她虽面临同样的窘境,却始终保持常态。甚至警察为房捐事点名要她到案,她也会临事不慌。这一个性在急难的情境中,描绘得更富有光彩。比如剧中李十五给她解了房租之围,却给她出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去不去赴李十五之约。如若不去,轻则丢了饭碗,重了,就会有失掉自由乃至生命的威胁。此刻,早被吓怕的母亲,劝她屈从,邻居也一味纵恿她就范。她不是不知道利害,可终于还是脱掉李十五派人送来的衣服,宁死不赴约。在剧情发展中,逐步揭示这种性格形成的原因,一是父兄的痛苦经验,让她较早地认识了社会——她的父兄或因得罪权贵、或因参加爱国运动而死于非命。二是现实生活的磨练。在艰难中,王素薇要维持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过度的刺激,王母的精神时有失常状态。王素薇得独立支撑,承受家庭生活的种种负担,面对来自社会的种种打击。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生活促成了这样的性格。在这个基础与前提下,剧作家又描绘了她性格的发展,当她决定不赴李十五之约时,她哭了——她明白,自己将面对更严酷的现实,但是,她又清楚地知道:“要努力跟大家去打开一条出路,我们的围始终要靠我们自己来解!”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遵循了自身的逻辑,令人感到真实自然。
上述冲突的构制、情节安排、人物的塑造构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民不聊生时局下的生活氛围及下层社会民意、人心的归趋方向,富有时代气息。同时,也理解了欧阳予倩当时对生活的理性判断——有产者对下层人的盘剥锱铢以求,压迫随心所欲,大多数人的生存空间已不复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已难以再维持下去。而新世界的到来是不能坐等的,感叹命运、愤激、消极是无用的。更不能指望哪个有钱人来“解围”,普通百姓要想生存下去,只能靠大家从斗争中得来。这个判断与当时的革命作家的见解并无二致。但与当时常见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不同,在《同住的三家人》中,作家对生活的理性判断是从剧情、人物性格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剧本在当时,实属上乘之作。
在瞩目于下层社会的同时,欧阳予倩注意的另一方面就是上层社会的腐败。他把审视、批判的目光凝聚到社会上得意、发迹的人物身上。于是,在他的剧作中出现了五四时期作品中未曾有过的人物——买办、暴发户、基层政权中的小头面人物。借对他们的发迹史、心理、作为的描绘,力图全面展现当时社会面貌。为此,作家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察角度、拓展思路。
《买卖》接触了买办勾结军阀贩卖军火的问题,并进而揭露这些丑类的灵魂,他们为了发财,把什么都拿来做买卖,包括自己亲人、朋友的感情与人身。此中,有对经济制度及政治批判的内容,但道德批判仍占有较重的分量。而《越打越肥》的构思则建筑在将处于社会上、下层中的人物在抗战中的行为、心理作对比的基础上,加大了政治批判的分量。在《同住的三家人》中,这样描绘了暴发户李十五的发迹史,他原是一个破落户的儿子。父亲当过日本买办,亏本后死掉了。到李十五这一辈,已经很穷。但因他父亲的关系,日本人肯帮忙,于是“介绍过一次军火,贩过一次烟土,包过一次赌,几个翻身,他便抖起来了。”以后又“认识了几个要人”“消息灵通……可以骗人。这就是一场大公无私的大翻戏”“近来他是全靠中央纸,每停一次兑,他就赚一笔。这回转一转手就几十万”。这可以说是对社会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大暴露,让人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制度怎样在自己的机体上培养恶性肿瘤,并为它的迅速生长提供各种适宜的条件,这样,世界又怎会不闹到“天翻地覆”,穷苦百姓又怎能不被逼去“住马路边”呢!作家从政治、经济角度观察、反映社会问题,增强了剧作现实批判的力度。这是作家创作精神变化带来的积极效果,也是三十年代重视文学革命与政治、经济关系的思潮对作家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欧阳予倩也重视剧作的时事性。十六景话剧《不要忘了》是一个没有机会付诸舞台的剧本。作家有感于“1·28”事变,根据日本侵略者发动万宝山事件,中经“9·18”“1·28”直至国联李顿调查团来华的事实编写。 剧作对国民党当局各级军官的无能,下层士兵、民众与侵略者决战的精神及有产者卑躬奉迎的所谓“国联调查团”的“和平使者”的真面目予以真实的展现。剧作自然不能算作“不朽之作”,但在时局舜息万变,作家来不及将自己的感情、体验熔铸成艺术形象的情况下,采用了活报的形式,抒发自己的感受,代人民立言,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欧阳予倩在执着、勤奋的艺术实践中,接受了时代与文艺思潮的影响,创作精神发生了转变,以更自觉、深刻的理性意识观察、判断、表现生活,对一种制度培养的丑类予以暴露、挞伐,对处于“水平线下”的芸芸众生的生存状貌、心态及靠集体斗争求生存意识的增长予以展示。其中,揭示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予示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寄予了作家感受到的过渡时代种种微妙难言的悲哀。话剧创作的精神内涵比五四时期更坚实、丰厚,这是本时期创作一个明显的进展。作家以剧作这样的精神,在特定时代“启迪民智”。
3
创作精神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引起艺术的变化。不再编写京剧,作家的艺术趣味就将超越传统的英雄与美人的悲欢;因有更明显的倾向性,他就要把代表了两种不同势力的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与下层人物种种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而写自己原本不熟悉的下层群众,他也需要有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当时的社会情势、人们的审美心理对剧作思想性的要求,因迫切、峻急而造成逼人之势,在这种氛围中,欧阳予倩坚持在艺术上严格律己,本时期在艺术方面显示了过渡时代的特点,也有明显成就。
其一,作家一贯主张“剧本的好坏首先就看它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是否真实,是否有思想、有感情、有血有肉、有灵魂”(注:《话剧向传统学习的问题》。)本时期,欧阳予倩在写人的艺术方面继续推陈出新。
如前述,本时期,在他剧作的人物画廊中出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人物——下层劳动者与上流社会的丑类。作家采用不同的技法赋予他们以血肉、生命、思想、情感。他用传统的技法塑造了一些下层人。在《车夫之家》中,用递进、强化的手法表现车夫遭受灾难的连续性、集中性,在多灾多难的生活中,塑造车夫沉默、多思、忍辱负重的个性。《同住的三家人》则在各种冲突中刻画王素薇沉静、稳健的性格,同时运用对比的手法,写了三个处境相近的工人。汽车司机陈桂卿的愤激、犹疑,阿云的世故圆滑,阿明理智而有远见,在对比中显得更鲜明、生动,同时表现了工人,这一社会群体性格的丰富性。
对社会上的丑类,作家不采用漫画式的夸张,而是选取足以彻里彻外暴露人物的独特方式,传达出他们富有个性的神态与灵魂。《买卖》中的买办陶近朱为自己倒卖军火,勾结洋人串通军阀宋世维的需要,将大学生潘雪圭的爱人梅可卿骗到旅馆以满足宋世维要同女学生“正经谈谈恋爱”的卑鄙欲求。此事,被潘雪圭得知,他带了手枪赶到旅馆。至此,剧情怎样发展呢?按着一般的写法,就是潘雪圭虽然“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但到底不过一介文士,敌不过军阀宋世维,被人三下五除二缴了枪,坏人得逞了事。这样,虽也热闹,但人物精神、品格显得平淡无奇。欧阳予倩没有这样写。在他的笔下,宋世维不仅以力压人,还要同潘雪圭在“情”与“理”上较量。可是,按“理”说,宋世维与人串通倒卖军械,不只是无理,而是违法卖国。仗着这样祸国殃民的行径得到的财势,又要夺人之爱,胡作非为,也不止于无理,实为犯罪。潘雪圭保护亲人,揭露不法,不仅有理,可以说是英雄行为。按“情”说,宋世维拿感情当儿戏,设圈套、用心计,面目可憎。而潘雪圭对爱人一往情深,急难时,挺身而出,情深意厚。可结果呢?双方几经搏斗,宋世维的作为反成合情合理的,潘雪圭却不仅输了力,也输了情与理。这变化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宋世维先借当时的恐怖政治诬陷——夺了潘的枪,以此为据,诬他为危险党人,继而用对当时社会流行的“革命”“自由”等语汇与理论曲解诡辩。宋煞有介事地对潘说:“至于说梅女士,我们是拿朋友的资格待她。革命的女子没有甚么地方不能去,你能断定所有到旅馆里来的女子都是坏的吗?你能够说只要是你的女朋友就不应该到旅馆里和她的朋友谈话吗?你要是不存着私人占有的观念,恐怕你不会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吧?倘若是一个女人要一个这样的男子拿着枪管着,那这个女人就可想而知了。梅女士不见得如你想的那样靠不住吧?”真是巧言令色,黑白颠倒,令人啼笑皆非。好半天潘雪圭说不出话,最后叹道:“啊啊!社会的恶势力这样膨胀,晶莹的月亮也没有光辉,美丽的花也失了颜色,贞洁的女子也只有堕落……叫我说甚么!叫我说什么!”说着竟拿起手枪对正自己的胸口。就这样,经过几个反手,宋世维将罪恶行为解释得情理皆周,并把对手逼到想自杀的地方。唯其如此,才透视出当时是一个怎样是非颠倒的混沌世界;唯其如此,才能精当地展现宋世维骄奢、狡诈的强盗性格;唯其如此,剧作才有“戏剧性”。
其二,本时期欧阳予倩话剧的形式、色调更多样化。本期剧作的结构保持着五四时期已显示出的简明、严谨、集中的特点,线索清晰,层次清楚。叙事原原本本,有头有尾但并不平铺直叙。结构形式较五四时期却更为丰富,五四时期,主要采取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本时期有由点到面、由实而虚的形式,(如《屏风后》)有连缀事件的形式,(《车夫之家》)有的用中心事件贯穿,(《同住的三家人》)也有传统的开放式。(《小英姑娘》)从冲突的性质看,有正剧、讽刺喜剧、闹剧、活报剧。这些表明作家对话剧样式的把握更加得心应手。
其三,作家的讽刺、幽默、笑骂的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在五四时期剧作的否定形象的塑造中,已初步显示了作家这方面的功力。本时期,随着生活本身喜剧乃至闹剧因素的增长,作家的这一才能得到更充分地施展。这一方面表现在作家善于将抽象的思想、感受提炼为鲜明的喜剧形象。《越打越肥》就是作家看到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和他们的亲戚仗着枪杆子走私,趁抗战之机大发横财,他们越富百姓越穷的事实而编写的。对世事的不公平,作家早已心怀不满。因此,当他听到群众中流传着“百姓越打越瘦,阔人越打越肥”的说法引起了感情的共鸣,并触发他的艺术想象,他就把自己抽象复杂的感受、爱憎之情凝聚为“胖子”和“瘦子”的形象,他们都是富有个性特色、富有生命力的喜剧人物。一方面又表现在作家善于提炼富有潜台词意味的语言,产生耐人寻味的讽刺效果。在《屏风后》中有一段“道德维持会”会员们的“妙语”:
吴:好好好,你们知法犯法,我等会长回来告诉他!
周:我们这也是学时髦。
吴:原来知法犯法是时髦?
无垢:不然,犯法要犯得漂亮才时髦。
周:是了,犯法要不让人知道就漂亮。
李:不然,犯法要让人好象知道,好象不知道才算漂亮!
钱:不然,犯法要犯得简直让人知道,可是抓不到证据,才算漂亮。
孙:不然,犯法要犯得让人抓着证据,却把你无可如何,那才叫漂亮。
几句话,把这个“道德维持会”的生活内容、本质、名实矛盾暴露无遗,暴露得如此俏皮,如此有力!语汇、语势、组合排列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在现实中的新发现。
一代先驱的戏剧建树,将永垂青史,留给后人可以借鉴学习的东西是多方面的。本时期尤为令人凝神结想的是,欧阳予倩既把戏剧作为启迪民智的武器,又把它当成无可替代的艺术;顺乎时代潮流,又时时不断地修练、养成、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接受进步思潮,又妥善处理对传统的继承、发展的思路和经验。他的包容、创新、锲而不舍的艺术精神也将永远给后人以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