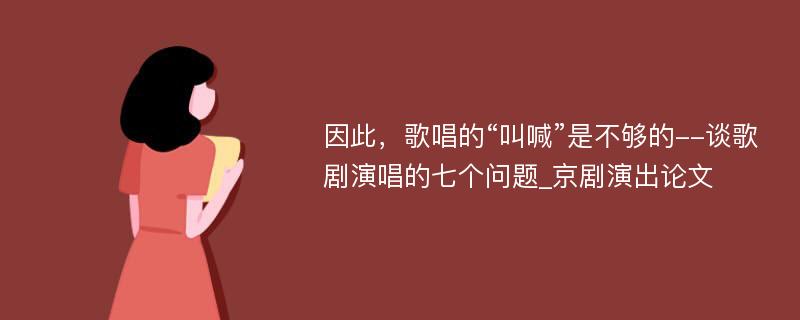
歌唱不足故‘叫喊’之——戏曲唱论七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唱论七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02)04-0070-05
“西唱”中的所谓“美声”,其高度模式化的“千人一腔,万曲一风”的倾向,实乃 一派在欧洲(工业)人(种)文地理中生出的欧洲风范。其各个声种(含不同音区),即不论 男、女,高、中、低音的,迈过喉头(严禁“喉、炸、沙声”等,更不准出现‘叫喊’) 的发声,面罩式共鸣,高而集中统一的共鸣点……高、中、低音区的不准“打架”而尽 量统一,音区间换声过渡的无痕化追求……总之,西唱“美声”所孜孜以求的,是一种 工业(集约)化高度定量定性的“批量(定型)产品”,即其不同声种、音区的独、重、合 唱等的发声,越靠得拢越好——是一种注重共性的极度有序化的歌唱艺术。“中(国传 统)唱(法)”——56个民族(人)的千姿百态的演唱,总体上是小农经济自供自给、“各 自为政”,甚至于是“以邻为壑”的一种自娱自乐——相对强调个性的无序态歌唱艺术 ,一派农业文明的中国风范。曾记否,20世纪末叶,打倒“四人帮”后,当带着“喉、 炸、沙声”的(含20世纪30年代的“靡靡之音”)通俗歌曲“卷土重来”时,在中西文语 音乐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院派(雅乐界),对其也经历了一个“骂、忍、跟”的痛苦过程 ——更有“美声”改唱“通俗”者。产生种种“骂”的诸多原因,宏观方面主要在艺术 趣味,微观方面主要是对其唱法中的“喉、炸、沙声”的讨厌。其实上述“喉、炸、沙 声”唱法,在中国的口语戏曲中更是源远流长,并为百姓们所喜闻乐见。譬如具有点缀 性、色彩性、风格性、情感性、对比性等特征的“喉声”,“集体无意识”地始于梆子 声腔剧种,个体有意识地成为京剧程派演唱的一大长处和主要标志。次如“沙声”,无 独有偶,京剧程(砚秋)派“喉声”是带着“沙声”的,只是因为程派的音色过于丰富而 使其“沙声”不显著,甚至于被其它更富光彩的音色所掩盖而难以引起注意。但在所谓 的“风裹雪”的京剧荀(慧生)派和麒(麟童)派中,“沙声”便成为其显著的流派特征了 。甚至到了无“沙声”则无荀、麒流派的重要地步。程、荀、麒三派中的“沙声”,都 是因为自身条件如此所限而不得以而为之者,是一种不得不如此和只能如此。把不得以 而为之的“沙声”艺术化,似乎比天生一副好嗓子者的演唱,反更能得到听众的热烈掌 声——相反相成,欣赏种种反常的“美”,甚至形成癖好。君不见北京的“豆汁儿”, 长沙的“臭豆腐”,重庆的“烂味”(动物肠肚的腥味)贵阳的“折耳根”(鱼腥草)…… 其实早先的霉豆腐、醋、酒等等,也像戏曲演唱中的“喉、炸、沙声”一样,亦属种种 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反映中国人绝顶聪明的文化遗产。此外,在晋剧中却存在嗓门全无 缺憾的,像《王宝剑》中饰王允的老生演员所唱的,则是另一种故意而为之的“沙声” 与非“沙声”的综合唱法——完全是为着刻划王允其人当时的霸、蛮、横、野、狠等性 格特征而设的。次如戏曲演唱中的“混声”,即一个演员在唱某音时,把多种不同音色 (有的甚至类似蒙歌“呼麦”声音)混合起来使用。这在梆子声腔诸剧种中也很常见,秦 腔《火焰驹》贩马头领所用唱法(上述王允演唱中也存在)即是。这其间,最典型者当数 豫剧包文正扮演者所用的唱法。次如梆子腔演唱中的“夹嗓”,即把“沙声”、“喉声 ”、“(大)本嗓”、“(小)假嗓”、“混声”等夹在一句腔、一段腔、整出戏中使用… …下择“歌唱之不足故‘叫喊’之”等七题,冒昧抛出以求正方家。
戏曲演唱的‘叫喊’化
戏曲在汉语“声、韵、调”基础上,产生了“土(京)白”、“韵白”、“演唱”、“ 叫喊”等四种属于音乐范畴的表演形式。因汉语与生俱来的音乐性,使此四者相对地均 具备一定的音乐美。但其美的程度不同、层次异样、功能互补。在具体运作中,四者相 互转换亦非常自由自在、顺畅自然。特别是其演唱中的“叫喊”,从形式上看似一种由 “唱”向“说”的“倒退”,但实质上却是当唱腔的旋律,束缚曲文表情时的一种“解 放”,且很多时候,还因为种种不同的“叫喊”而形成特殊的“旋律高潮”,戏曲“歌 唱不足故‘叫喊’之”,是一种极其有趣而特殊的华夏音乐(“本源性”的)自然生态现 象。
原生性‘叫喊’古人云:嗟叹不足故歌唱之。其实在语言之前和语言转向歌唱之间, 还应有一种‘叫喊’作为过渡。原始语言源自无语义性的‘叫喊’,这从世上族源、族 系各异的奶娃,多能首先无师自通地把母亲‘叫喊’为“妈——”者可为证。这恐怕也 是一个人类共通的原始人文(生态)现象。孑遗至今的纯四度两声腔贵州苗族[喊歌]、江 西汉族山歌[新打梭标](详见1960年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歌》),以及四川官话区 ,仅用徵→宫(纯四度两声腔)二音演唱的童谣[虫虫虫飞]等,也是此种人类原始事物, 在“集体无意识”行为中,会反复再现的种种活证。如果把目光收缩、集中到口语戏曲 上来观察,戏曲演唱中之‘叫喊’,也多是其原生态的野台环境所使之然——在人声鼎 沸、大锣大鼓喧嚣的旷野唱戏,所有的表演手段都必须尽量夸张、放大以招徕受众。因 此,才有了南方高腔、北方梆子腔的拖腔、拖调的“韵白”,以及‘叫喊’式歌唱。且 其力度方面的层次丰富多样。当下,其‘叫喊’强度,京剧次于高腔,高腔次于梆子, 剧场次于广场,城市次于乡镇,乡镇次于农村……昆曲(雅部)越剧、锡剧、沪剧等,这 些吴语区地方戏声腔戏中的小旦、小生的演唱,总体上虽是雌柔的,但也是存在不同层 次的“雌柔型‘叫喊’”的(绍剧等非乡土的外乡——原生西北的戏种声腔,又属“雄 刚型‘叫喊’”,且影响着越剧)。由茶馆艺术——说唱(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 ”)变来(而粉墨登场)的戏种。如吕剧、曲剧、黔剧……以及摊(册为“说”)簧(为“唱 ”)腔系诸剧种的演唱,其总体上也是倾向于“雌柔型‘叫喊’”的。但二人转(含吉剧 、龙江剧)青海西宁(“贤孝”)平弦剧等,却又是“雄刚型‘叫喊’”。大筒腔系中, 长沙花鼓戏、云南花灯戏、湘西阳戏等,属“次雄刚型‘叫喊’”;广西采(茶)调(如 《刘三姐》)属“中和型‘叫喊’”,余者多为“雌柔型‘叫喊’”。由此可见,在中 国南北两大口语音乐文化板块中,戏曲演唱中的‘叫喊’,亦绝非铁板一块,也是有着 诸多层次的。看来由山歌(野曲)转过来的戏曲(花部诸腔)演唱中的‘叫喊’,更根深蒂 固些。此其一。戏曲演唱中‘叫喊’的第二个原生性,便和汉语“声、韵、调”与生俱 来的音乐性有关。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汉语“去声”字上产生的‘叫喊’。譬如京 剧《借东风》,其孔明所唱“诸葛亮在坛台观看……”中的‘看’字便是。如果总体上 说,戏曲演唱的‘叫喊’,以源于山歌(野曲)者为主,花灯戏次之,由说唱变来的戏曲 更次之,吴语区土戏曲更更次之……但作为一种原始的生态现象,当它们演唱汉语“去 声”字时,也是都要‘叫喊’,而必然概莫能外了。如越剧《梁祝·楼台会》一折中梁 山伯所唱:“悲的是美满姻缘两叉开”中的‘叉’字,便是一种绝望的“雌柔型‘叫喊 ’”……余不赘。
次生性‘叫喊’如果说部分戏曲演唱中的‘叫喊’,原生于山歌(野曲),而其它,如 说唱变来的戏曲、吴语土戏等“雌柔型”的戏曲中,次生性的‘叫喊’,便又比比皆是 了,连雅部的昆曲也概莫能外。此种次生性‘叫喊’,多因为戏剧(含心理)动作(感情) 的需要而发。最明显者,便是在“整(紧)打(拉)散(慢)唱(的[摇板]——借用京剧板式 名称)中。由于强烈的戏剧动作(感情)的需要而唱[摇板],是必然要‘叫喊’的……此 外,当演唱[倒(放下檀板不用——而非“导”)板]、[滚(哭)板]、[散板]等板式,也是 要‘叫喊’的。原生于山歌(野曲)的“‘雄刚’型”戏曲,如京剧前身(花部)徽调、汉 腔中的‘叫喊’力度的斯文(弱)化,又纯是为了满足皇城中听众的需要,而逐渐倾向( 雅部)昆曲的结果。如果说,汉语“去声”(为字正)的‘叫喊’是原生的(有着为‘字正 ’而发生‘叫喊’的‘基因’)。而次生、因戏剧(含心理)动作(感情)之需而发生的, 在各戏种中均广泛存在,且须臾不可离的‘叫喊’,应是一种“情绪型‘叫喊’”。正 因为是“情绪型‘叫喊’”,所以,又多是“倒字型”的(汉语“去声”字上的‘叫喊 ’,为“正字型‘叫喊’”)。戏曲演唱中的‘叫喊’,作为一种汉语“声、韵、调” 的原生现象,除其“去声”外,其它“阴、阳、上声”不倒字是绝对‘叫喊’不出来的 。此类“倒字型‘叫喊’”,在大江南北,关内、关外的任何戏种中,也都是顺手可拈 的。还是以大家耳熟能详的京剧为例。《空城计》中“等候了司马”中的‘等’字;“ 早备下羊羔”中的‘早’字;“打听得”中的‘打’字,本都是214调的折声,因‘叫 喊’而变成了51调的下滑式“去声”。“上声”变“去声”,肯定是一种“倒字”—— 其它又如:《文昭关》伍员所唱:“思前想后我的肝肠断”中的‘想’字;《捉放曹》 陈宫所唱:“马行在夹道内……”中的‘马’字;《搜孤救孤》程婴所唱:“手执皮鞭 将你打”中的‘打’字;《火烧棉山》介子推所唱:“老母叮咛结草衣”中的‘草’字 ……不一而足。如果说京剧大花脸(架子花、铜锤)老旦、老生的唱腔,总体上还是一种 原生态(“正字型”、“倒字型”)的‘叫喊’,其花旦唱腔中次生态的‘叫喊’也很多 。如《红娘》中红娘唱:“看(准‘叫喊’——51调变55调)小姐”中的‘姐’字……余 不赘。就连专演悲剧的程派也‘叫喊’。如《春闺梦》中女主人公所唱:“独自眠餐独 自行”中的第二个‘自’字(“‘正字型’叫喊”)。戏曲演唱中的次生性‘叫喊’,除 因戏剧(心理动作)感情需要而发生者(可称其为“情绪化‘叫喊’”——后详),此外, 似还有“戏种化、行当化、音乐化、动作化、旋律高潮化、综合化……‘叫喊’”(而 前述之原生的两种,又可概括为“环境化、语言化‘叫喊’”)……关东大汉、江南小 囡,其‘叫喊’,本来就天生着雄刚和雌柔之别……南(方)腔(温柔、婉转)北(方)调( 高峻、刚烈),那本是地态、心态、语态、乐态“递为反映所致也——“生就的龙门、 配就的相”,确是“命”该如此。原生‘叫喊’也好,次生‘叫喊’也罢,反正中国近 四百个地方声腔戏种,均自然而然地在不同“色度”的‘叫喊’中演唱。丰富多彩的‘ 叫喊’式演唱,应是中华农业文明中衍生的民间口语戏曲的原生性特征。作为演唱中的 ‘叫喊’,几乎无不具有音乐性。戏曲中的土白、韵白、[叫头],均具有非律化与准律 化的音乐性,特别是[叫头]:“苦——哇——!”确具有一种特殊的音乐美。律化了的 汉语戏曲唱腔音乐,在抒发柔情的同时,又束缚着激情的迸发。这便又要突破乐律束缚 ,来几声艺术化了的(原始)‘叫喊’了。一般来说,“歌唱”多是抒发柔情的,‘叫喊 ’是用来迸发激情的(恰似戏曲中律化的文场与准律化的武场的一文一武),汉语不律化 无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全是律化的音乐无‘叫喊’,又没有了原始的,能迸发激情的‘ 暴力’戏剧手段。律化的演唱中,点缀着原始的艺术化的‘叫喊’,相得益彰,这些确 属一种中华(农业文明)式的特殊音乐构成(汉译的《跳蚤之歌》也‘叫喊’着——“跳 蚤”,但似乎并未构成一种文化印记,似属偶尔为之者也)。以下各句唱词中带着单引 号、着重号的字,即均为“叫喊”——评剧:“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 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婺剧:“开店‘不’求富万贯”;二人转:“为什走得 这样急,能不能够‘留’几天”;阳戏:“站立窑外用目看,尊声三‘姐’听我言”; 。黄梅戏:“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眉户戏:“黑古隆冬天上‘出’ 呀出星星”,(北)京梆(子):“金殿下来了我王‘氏’宝钏”;豫剧:“刘大哥讲话理 太‘偏’……而京剧《坐宫》杨延辉唱——“站在宫门叫小‘番’”,此‘番’字的演 唱,似为一种律化的‘叫喊’;《搜孤救孤》程婴唱——“手执皮鞭将你‘打’,不在 ‘你’字上,而是在‘打’字上‘叫喊’,乃是一种为表现其外恨内痛的伪装性‘叫喊 ’;《空城记》诸葛亮唱——“来!‘来’!来!”属动作性‘叫喊’;《借东风》诸葛 亮唱——“诸葛亮在坛台观‘看’”字上的‘叫喊’,似属综合性——动作性、旋律高 潮性……‘叫喊’。
戏曲演唱的戏种化
所谓“戏种化‘叫喊’”,即只要听其演唱中之‘叫喊’与否,‘叫喊’的程(力)度 如何,便可知其属于何戏种——梆子腔系各戏种:(北)京(河北)梆子、河南(原为商州) 梆子、陕西(原为同州)梆子、山西(原为蒲州)梆子,尽管音色各异、‘叫喊’有别,但 其“热耳酸心、繁音促节”的‘叫喊’,应为戏曲演唱‘叫喊’之最剧烈者,一听便知 是梆子腔。其次重叫喊者,当数高腔,特别是川剧高腔,它的(众)帮(腔);(音色丰富 、反差强烈、大锣大鼓的)打(击乐);(独)唱——(“斗斗壮乃且乃壮”——击乐唸谱)“咦也!……”颇似川江船工喊号子时发出的,那使出吃奶劲、拼老命的‘叫 喊’。因此,但凡熟悉戏曲艺术的人,多能仅凭聆听演唱,便能分辩出戏种的类别。虽 说戏曲演唱,在总体上亦显出“南腔(雌柔)、北调(雄刚)”的特征。但由于“地态、心 态、语态、乐态”四者递为反映所使之然,即便是同一声腔系统的各个戏种的演唱,听 起来仍然是泾渭分明的,——北方梆子腔系诸戏种的旦角演唱;:秦腔婉转,晋剧(疙 瘩腔)华彩,豫剧又特别注重真假声的鲜明对比。同为皮簧腔系的须生腔,京剧因曾经 “内廷承应”而唱“伺候戏”,故它比起其各地各昆仲“山班子”的粗放野气,显得内 敛而精致许多,其演唱,总体上因借鉴昆曲而基本上已日趋有了雅化的倾向。流播全湘 的皮簧(南、北路)腔,其岳阳、祁阳、长沙、常德人所唱,也是大异其趣的,。而皮( 梆)簧腔由粤(语言声调特别丰富多彩)剧演员唱来,更面目全非了——外地人除非十分 专注地闭目审听,甚至连其(上、下)腔(分别落宫、徵音的)格(式),都因其旋律的装饰 太丰富多彩而难以辨清——高度模糊了。
戏曲演唱的行当化
由于戏曲程式化的结果,戏曲演唱也逐渐行当化。,明清时期,(须)生、旦(角)男女 同腔同调的江湖班,是由男人演唱旦角的,为分出生、旦两行,旦行用假(小)嗓,生行 用真(大、本)嗓。待男女分腔之后,方渐开行当分腔之风。以近代京剧为例,旦行用假 嗓,老旦用本嗓,老生用半嗓,(边音),小生用“龙、虎、凤音”,“大花脸——净、 (铜锤)用“脑后音”,小花脸——丑用真假嗓……梆子腔演唱的行当化虽不如京剧细致 ,但其生(用本嗓)、净(用沙嗓)旦(用真假嗓)的演唱,还是行当分明的。,即便是纯坤 班的越剧,其演唱也是尽量追求生(行)刚、旦(行)柔的。“行当化‘叫喊’”,特别表 现在各剧种(特别是梆子诸腔)的大花脸演唱中。试想铁面无私、日断阳(人)、夜断阴( 鬼)的包文正……还有:打鬼的钟馗;枭雄曹操;“吼断桥梁水倒流”的张飞;力顶千 斤闸门、救出瓦岗众草莽英雄的单雄信;同时杀死双虎的李逵;极欲问鼎中原的金兀术 ;能智盗御马的紫脸窦尔墩;满怀血海深仇的李勇奇;指挥部队,在美李匪军集团中穿 插的关团长;满腔怒火的雷刚……真是闻其演唱而知其行当(角色)也。
戏曲演唱的流派化
戏曲中的各个戏种,均以各自独具风貌的演唱,成为其戏种的种性标志。后又因剧目 中角色的增多和程式化需要而行当化。但是,由于艺术最必须的“这一个——恩格斯语 ”(个性化)追求、演员生存发展的需要,以及其自身条件的优劣和变化,又必然要在各 种行当中出现因人而异的流派。这样便有了越剧的“十姐妹”;豫剧的四枝花——常( 香玉)、马(金凤)、,闫(立品)、崔(兰田),。当然说到流派的丰富还得数京剧,因其 真格的得天独厚,更是“江山代有人才出”:旦行——梅派(擅正剧)的雍容华贵,在平 实的表象中,隐含着十分过硬的真功夫(文化);程派(擅悲剧)的出奇制胜,无腔不险, 刻意求新;荀派(小家碧玉)的“美、媚、娇、憨、脆”;尚派(巾帼英雄)的尾腔上挑、 重“立音”而侠肝义胆……南麒(麟童的铮铮铁骨、掷地有声)北马(连良的仙风道骨、 飘逸潇洒)……
戏曲演唱的个性化
尽管戏曲演唱也有门有派,但也是“一师带九徒、九徒九种声”的。同是程派弟子, 王吟秋纤细;赵荣琛凝重;出身大学生的李世济更富个性——大开大阖,腔在奇崛中求 自然;张火丁清纯娇媚,十分重“度”的喉声运用,使程派返老还童;沈阳京剧院的迟 小秋,学“程沙”而不显沙,与张火丁的“淙淙清泉”比,迟显得大气冷傲——有望其 能突破程派只演悲剧的路子。在无腔不学谭中出了余叔岩、杨宝森等新派。特别是高庆 奎,因为其除主攻须生外,还擅长黑、红二净和挺拔高亮的老旦唱法,故而其须生唱腔 是三行腔风的有机混融。裘派花脸传人中的男男女女,有人浑然天成,有人巧夺天工… …
戏曲演唱的情绪化
当戏曲演唱在流派中出现个性化之后,因剧情的需要,随之而来便又有了个性化中的 情绪化追求,以体现同一角色、在表现不同情绪时所特需的不同演唱。譬如:河南省豫 剧院二团所演《三哭殿》,其全剧中银屏公主所唱,即为比较典型的“戏曲演唱情绪化”追求之佳例。全剧中银屏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反差极大的情绪变化。如其首次亮相后的 静态情绪,在大气的雄刚型河南梆子的演唱基调中,通过把歌声“搁”在较高的“位置 ”——共鸣点上,使歌声“飘”起来,在平静的外表中显出高贵、傲气、满足的情绪。 此时,尾腔仍必然要带出梆子腔特有的粗犷的“喉声”,体现了“公主”与生俱来的“ 霸气”。当银屏得知儿子秦英打死国丈之后,出现了第一次情绪陡变。演唱起来,其“ 腭弓”进一步后退,口腔加阔,混合共鸣增加。特别是押送秦英去金殿前,为表现儿子 难免杀身之祸时的惊恐情绪,出现了“炸音”、“喉音”……以加大音色“反差”。待 到了金殿之上,皇后、皇妃、银屏面对皇上“三哭殿”时,银屏公主,既要为绑赴午门 候斩的儿子悬起一颗心,又要求得母后的袒护,乞求姨娘——皇妃的谅解,最后完成由 其父皇下旨赦免儿子死罪的“最高任务”——银屏自身、儿子、母后、皇妃、父皇,五 个不同的人物、四对矛盾关系,以及复杂的戏剧情绪,演员们均能通过不同情绪的演唱 ,予以多侧面的立体式表现,堪称华夏戏曲演唱的情绪化之集大成者。
戏曲演唱的边缘化
还是由于戏曲角色的不断丰富,以及其自始至终“汇通以求超胜”的艺术追求。戏曲 演唱流派的边缘化也是必定要应运而生的。原以满宫满调演唱的谭鑫培,首次自京至沪 演出北归后,受海派京剧演唱的影响和启迪,刻意降低了原汉腔、徽调的高调门,唱来 松快流走、且优美雅致了许多,而由武硬趋向文雅——谭派便是国剧京、海两派(燕赵 悲歌与吴侬软语等)的边缘化结果。京剧须生高(庆奎——弟子李和曾、再传弟子辛宝达 等)派,也是京剧净、生、老旦三行演唱(音色)边缘化所致(高派要求其学唱者的嗓音天 赋条件需极佳)。其实梅派的演唱,历史地看又何尝不可认作“昆乱不挡”之边缘化所 使之然。叶派的小生腔也难免其乃黑头“脑后音”与青衣“假嗓”的边缘化之嫌。难道 不是吗,叶派的“虎、龙、凤音”,其“虎音”和“龙音”,“开放”即为“净腔”、 “生腔”;“凤音”若“关闭”一点便是旦腔。谈到倒嗓后的程砚秋的绝处逢生,当年 ,京剧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四大名旦均出于其门下)帮助程派创意时,也完全可以 说是一种生与死的边缘化——借鉴以“花脸”的“喉声”及“脑后音”为特色的程派, 是恰好应了“要钱要得恶,花脸唱旦角”这句民谚的,程派硬是以隐性的净——“花脸 ”腔(方法)把“旦角”给唱绝了。京剧旦行中除程派之外,任随哪派均是很容易开口学 唱的,唯独程派,若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聆听、熏陶和仔细琢磨,是绝对开不了口的。 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在中国京剧院的李慧芳,出演京剧(移植歌剧)《洪湖赤卫队》 韩英时,其演唱也介乎旦、生、净之间,即其唱中,有旦、有生、有净,但又非旦、非 生、非净,真是难为她了。以“疙瘩腔”见长的评剧新(凤霞)派,在其早期恐怕也是“ 大口落子”与“梆子疙瘩——华采腔”的一种边缘化。到而今眼目下,又一轮艺术环境 宽松的开放改革时代,边缘化的演唱更是花样翻新,刘宾带“美声”的京戏腔,刘欢的 “流歌风”京(剧)歌,戴玉强的“美声化”京剧歌的杨子荣唱段(文革中早有梁美珍— —阿庆嫂……等的交响化的《沙家浜》京剧独、伴、合唱)。当今的山东省吕剧院的“ 京剧“唱法、吕剧腔”的须生腔演唱,更别开生面”。总之,有对立方有边缘,有边缘 方有突破,有突破方有新戏种、新流派、新腔风……这正应了明人王骥德的“世之腔调 ,30年一变”!
总之,中国戏曲演唱中的“叫喊化、戏种化、行当化、流派化、个性化、情绪化、边 缘化”等美学追求,有着丰富的学科意味的内涵与外延。当我们契入其间,探其原委, 究其典蕴,更能体察中国传统艺术,在社会文化大环境中历史传承的优良潜质,并品味 其艺术人文在人类精神与心灵旅程中的出奇制胜。这是作为“华夏戏曲唱论”课题的核 心旨归,也是一种新境界的拓展。中国戏曲理论的科学的形而上提升,此等努力惟愿其以点滴汇为江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