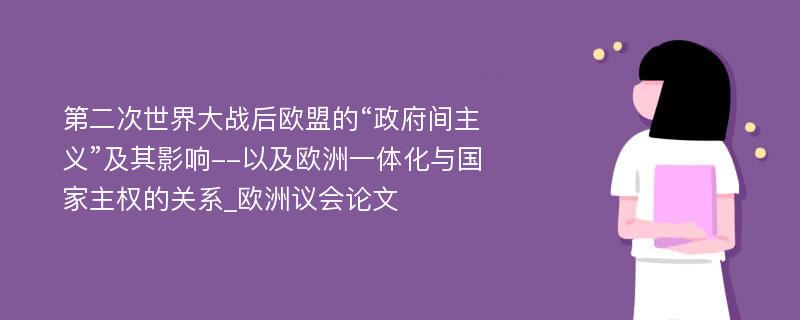
战后欧洲联合中的“政府间主义”及其影响——兼及欧洲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战后论文,化与论文,国家主权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6-0101-0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联合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国家”性质的“一体化”。欧洲“联邦派”(federalist)要求由经济一体化发展到政治一体化,并把国家主权转移给共同体,最终实现“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不过,“联邦主义”经常受到“政府间主义”(intergovernmentalism)的抵制。研究这两种主张及其在欧洲联合进程中的影响,有助于深入和准确地理解欧洲联合的进程和性质,以及当代国际一体化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的关系。本文只对“政府间主义”及其影响进行某些评述。
1
欧洲联合中的“政府间主义”的主张,指主张各国进行联合的同时保持它们的主权的那种联合方式和决策程序。它强调各国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各国在有关问题和领域实行“合作”,反对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即使在不得不建立某种具有“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情况下,也要将其保持在最低限度,反对提高“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而损害国家主权。政府间主义的主张者强调共同体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即共同体国家首脑会议)和各政府间委员会组成的网络在欧洲联合决策中的重要性,强调政府间讨价还价的重要性。按照这种主张,一体化只有与各成员国的利益相吻合的时候,才会发生。它必须置于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之上和框架之内,使各国政府能够对联合进程保持决择权、主导权和控制权。政府间主义主张一种“邦联”(confederation)模式的欧洲联合,因而也称为“邦联主义”(confederalism)。与联邦主义相比,这一派更强调联合体中各组成部分的独立性,相互关系更为松散,联合体机构的权力更为软弱。战后初期的“联盟主义者”(unionist)[1](p81)[2](p52-53),戴高乐的“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英国“欧洲怀疑派”主张欧洲联盟应是“多国俱乐部”(club of states),都属于这个范畴。
在战后欧洲联合的历史中,“政府间主义”始终具有强大影响。具有“超国家”的或“联邦主义”意义的措施,总是要受到政府间主义主张的抵制,引起反复的斗争。
当欧洲联邦主义高涨的战后初期,也同时存在着强大的“政府间主义”的派别。例如在1948年的海牙“欧洲大会”期间,所谓“联盟主义”派就主张搞一个形式最为温和的欧洲联盟,反对把国家主权转移给联邦或者超国家机构[1](p86)[2](p53-56)。一批欧洲国家随后组成“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不是按欧洲联邦派的要求,而是按政府间原则建立的。联邦派提出建立联邦式的联盟,起草宪法和建立共同机构的主张,不为各国政府所接受[3](p62)。
50年代初期欧洲联合迈出了重要步伐,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起来。但是防务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计划都失败了。其重要原因就是煤钢共同体是从有限的经济部门开始的,而防务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则如让·莫内所说,“触及到了国家主权的核心”。然而即使在煤钢共同体的酝酿和建立过程中,在其发起者法国政府内对于是否设立超国家的高级机构也有分歧。一派人主张实行政府间合作,反映了对削弱国家主权的敏感[4](p26-27,31-32)。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反对让高级机构享有过多的权力,要求设立基于“政府间”原则的部长理事会来实行监督。“这将使各国政府发挥适当的作用。归根到底是它们才能负责他们国家的总政策。”[5](p137-139)部长理事会后来实际上成为共同体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的制动器。所以煤钢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新的开端,对于欧洲联邦主义者来说,也只是差强人意。此后,在墨西拿会议及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讨论中,再也不提“超国家”、“欧洲联邦”之类引起争论的词汇,而是提“欧洲建设”。所以1957年的罗马条约虽然确定了经济共同体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机构——共同体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但与煤钢共同体相比,更突出体现政府间原则的部长理事会的决策者作用。《罗马条约》确定:共同体委员会(执行机构)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拥有最高权力,在多数领域它是相对无权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只有在部长理事会通过后才能成为共同体法律,才能付诸实施。欧洲议会则是一个谘询和监督机构。在部长理事会里,政府部长们只是在有限的情况下服从多数的决定,在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保留着国家否决权。权力重心明显地向“政府间”的机构部长理事会倾斜。在发展目标方面,则是笼统提出要实现“一个欧洲各国人民间的日益紧密的联盟”,删除了条约草案中的“超国家”词句[6](p19)。法国谈判代表马若兰说:“谈判中起草的文件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这个词,也没有任何人提到这个词。”[7](p34)与煤钢共同体条约明确规定其“超国家”性质相比,这是“政府间”原则的加强。有人说“在罗马条约中,共同体的创建者们没有让它们中任何一个占上风,罗马条约是两者间的精巧平衡。”[8](p25)罗马条约规定的决策方式是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的独特结合,而这种平衡是极不稳定的[9](p90)。其实,称之为向政府间原则的倾斜更为恰当。“重要的区别在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执行机构与部长理事会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联邦主义推动力的削弱和与独立的欧洲执行机构相对的代表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们的权力的加强。”[10](p8)一位英国作者指出,欧洲共同体的历史,在许多方面就是一部共同体委员会所代表的集体利益与部长理事会和各成员国所极力捍卫的国家权利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史[11](p16)。欧洲议会也一直在为加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努力。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联邦主义”与“政府间主义”两种主张的分歧,但政府间原则始终占主导地位。加强共同体“超国家”权力的努力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1966年的“卢森堡妥协”,规定如果一项决议涉及到成员国的“特别重大的利益”,部长理事会“应努力在合理期限内达成可以为全体成员接受的决定”。法国还特别指出“讨论应继续到达成一致同意的协议为止”[9](p152)。实际上,理事会总是力求协商达成一致,避免使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作决定。人们评论说,“卢森堡妥协”“标志着由一种‘共同体’精神向一种各成员国更加自私、更加实用主义的‘代价——收益’态度转变。”“共同体和西欧国家都向戴高乐的邦联主张靠拢,而欧洲联邦主义者却失去了地盘。”[7](p59)自那以后“联邦主义的潮流就一直无可挽回地后退”[11](p30)。
1969年在海牙召开的共同体国家政府首脑会议提出“完成、深化、扩大”共同体的口号。人们欢迎“海牙精神”。但是在推动共同体向联邦方向发展方面,实际成就却很有限。联邦主义者阿尔蒂诺·斯皮内利写道:海牙会议“除了一个原则声明之外,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雄心勃勃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设想,只是用不堪一击的许诺来实现的,它们是完全不够的,而且很快就被货币危机所推翻。”[8](p71)哈尔斯坦就会议公报中的一些“重要的省略”写道:“我们寻求采取措施实际恢复部长理事会的多数表决制,实行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但徒劳无功。没有规定加强共同体委员会的地位,例如由欧洲议会授予它权力和职能,或规定它在与希望加入共同体的国家进行谈判中的作用。”[8](p72)
70年代经济危机和滞胀,使各国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加之英国和丹麦等国的加入,使政府间原则的影响更为加强。部长理事会在这种条件下即使实行特定多数表决,也难以通过一项决议。一项决定总是要进行反复详尽的讨论达成一致后才能作出。共同体决策困难,据说一个互相承认建筑师资格证书的决定竟拖了17年之久。欧洲联合在向超国家方向“深化”方面乏善可陈,于是有了一个“欧洲硬化症”的说法。
70年代中期共同体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制度化,成为“欧洲理事会”(the European Council)。这提高了共同体决策的层次,有助于加强决策能力。但是,欧洲理事会实际成为最高指导机构和最高决策者,使“政府间主义”进一步加强。因为,“欧洲理事会显然是一种传统的政府间的安排,它处于共同体诸条约之外,不可能从属于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影响。”[6](p24)它加强了从更高层次上对具体领域(例如经济的一些方面)的一体化和主权转让实行总体、宏观的控制,使之在符合各国的主权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之下和范围之内进行。在首脑会议上只能是协商一致作出决定。这与一般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方式,几无区别。
1972年共同体首脑会议确定了建设“欧洲联盟”的目标。为此,1975年的“廷德曼斯报告”提出了不少关于共同体机构改革和加强其超国家性质的建议。但报告的基本框架是“联盟”而不是“联邦”,其中空洞的词句多,有效的措施少,建议也根本没有实施。报告起草委员会主席廷德曼斯说明了联邦派的无奈:“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避开主义方面的争议,它们已给欧洲带来了太多的损害。我在报告中一次也没有提到‘超国家’的字眼……这不是因为在我这方面缺少信念。但是在这方面的怀疑太强大了……在起草报告时,我尽力保持接近政治现实,只提出了一些看来可行的措施而避免幻想……有些建议被放弃了,因为意见不一,其他一些则被描述成过早了……许多东西被加上了各种但书和限制,其价值大打折扣。进行改革,开始一个新的开端,实现一个质的飞跃的想法……在提交给欧洲理事会的文件中几乎无影无踪了……我们行动的能力已经受到了伤害。”[8](p91)
70年代初的《维尔纳报告》要求到1980年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并指出经济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已使各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大受限制,迫切需要在共同体层次上采取行动,把经济与货币领域的责任和权力向共同体转移,修改罗马条约,进行机构改革等[12](p111-116)。但是直到70年代末,才搞了一个“欧洲货币体系”,它只是一个政府间合作稳定货币的机制,与“经济与货币联盟”相差极远,更遑论欧洲联邦了。
80年代,联邦主义出现一个新高涨,但政府间主义仍然强大得足以使其一再受挫。1984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草案”,具有不少加强共同体联邦特点的内容,但没有提出“欧洲联邦”的目标,许多规定仍然坚持了政府间原则。如:成员国在认为自己的关键利益受到影响时可以行使否决权;引入了“辅助性原则”,即只是在那些由共同行动可以比由成员国各自行动更为有效的领域,联盟才采取行动;确认欧洲理事会的权威,拥有决定哪些领域从合作行动领域过渡到共同行动领域的权力;等等。欧洲人民党主席保罗·巴尔比等人当时指出:“这个建议并没有取消我们各国的主权,它不是建立一个联邦”[8](p170)。而且这个条约草案,也没有被各国接受。
80年代后期的“单一欧洲文件”,90年代初的“欧洲联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终于对罗马条约进行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欧洲议会、共同体委员会的权限,扩大了部长理事会实行特定多数表决的领域,但并未削减“政府间主义”的主导地位。任何成员国都没有打算把联盟建设成“欧洲政府”。更重要的是,条约正式确认了欧洲理事会作为整个联盟的最高指导方针制定者,它是严格实行政府间原则的。在“马约”草案中曾有的“联邦式的”字样及内容被取消了,而代之以“成员国和政府间更紧密的联盟”的提法。在讨论联盟条约时,争论之一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司法与内务合作是继续保持政府间合作,还是纳入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共同体框架。一派人主张纳入,从而建立一个单一的结构。但没有如愿。联盟设计成了“庙宇式”而不是“树形”结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司法与内务合作作为联盟结构的“大屋顶”之下与共同体并列的两个新的“支柱”。它们不受欧洲法院的司法管辖,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对它们没有实际干预权。在这两个领域要由首脑会议或外长会议一致决定,只是在采取某些具体行动时才采取“特定多数表决”。
“马约”规定欧洲共同体(包括经济共同体、煤钢共同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等)只是欧洲联盟这所“庙宇”的三大支柱之一,主要涉及经济问题。共同体必须在欧洲理事会决定的总方针范围内行事。共同体本身的主要的决策机构,还是共同体理事会,而不是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条约还强调了“辅助性”原则:“在不属于其专有的权限范围的领域,共同体根据辅助性原则,只有在所建议的行动所涉及的目标不能由成员国有效地实现,并且由于该项所建议的行动的规模和影响而可以由共同体更好地实现的情况下,共同体才得采取行动。共同体的任何行动不得超越为实现本条约规定的目标所必要的范围。”[11](p92)在条约的附件中说,这一原则有助于尊重各成员国的民族同一性和保证它们的权力。它包括的要素之一就是严格限制共同体的行动范围,使它只能在被授权的领域行动,只有在共同体的行动能更好地达到目标的情况下才得行动[12](p238-239)。可见,“辅助性原则”在欧洲共同体的条件下,恰好有利于保持共同体与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的现状,保证各国政府在解决重大问题中的优先和主导作用,限制共同体向“超国家”的联邦方向发展。
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在马斯特里赫特会议前曾说:“联邦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不必羞怯地把它藏到桌子底下去。我们应当大声地讨论我们的联邦主张。”[13](p98-99)但是“马约”还是确认了政府间主义原则。这使有人认为它是“共同体方向的根本转变”,“根本改变了罗马条约中为联合的欧洲确定的蓝图”,是“从联邦主义后退”[6](p30)[11](p92-93,106)。后来,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在修改“马约”,加强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方面进展也不大。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先进行深化改革再扩大欧盟的想法没有实现,而是先扩大再改革的思路占了优势。虽然一些国家主张放弃“一致通过”的办法,但也没有取得实际进展。在共同对外政策方面,仍然只是在重大方针政策全体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在具体实施时才实行多数表决。各成员国可以在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启用“紧急制动器”,阻止决议的实施。这使欧盟在外交、安全和内政、司法方面的联合还是停留在“马约”的低水平上。
2
欧洲共同体国家有的较倾向于超国家主义或联邦主义,有的则始终坚持政府间主义。
政府间主义最坚决的主张者之一,是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政府。戴高乐主张欧洲联合,但坚持认为欧洲联合只能是主权国家间的合作。早在1944年,他就谈到在欧洲联合时“各国的主权不应受到损害”[2](p45)。50年代初,他曾认为煤钢共同体和防务共同体计划是“歪曲欧洲联合的思想”和欺骗人民。原因之一是它们的超国家性质,威胁法国主权[5](p184-185)。50年代后期他重新执政后,没有反对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但更坚决地坚持政府间合作的原则。他提出了“祖国的欧洲”的方针。他尖锐地指出:“欧洲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建设欧洲的支柱是什么呢?实际上,这就是国家,一些彼此的确很不相同的国家……如果以为能够在国家之外或在国家之上建立某种有效的机构而且得到各国人民的赞成,那只是一种幻想。”[14](p192)“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等,我不相信这个欧洲有任何生动的现实性……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的、具有权力的、能担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这些因素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家!……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以外,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夸耀。”[14](p340)“所有要把我国的主权转交给国际最高机构的体制,都是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容的。”[14](p424)因此戴高乐不喜欢共同体的超国家机构。他写道:“它是这样一种机构,技术专家在这里构成‘行政部’,国会议员享有立法权,前者和后者大多数都是由外国人组成的,他们有资格决定法国民族的命运。因此,要对大西洋组织表示热情,虽然这个组织使我国的安全和我们的政策受另一个国家的支配。因此,迫不及待地要使我们国家权力机关的行动服从国际机构的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表面上采取集体讨论的形式,而在一切问题上,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技术、货币等方面,却行使保护人的最高权力。”[15](p177)他鄙视共同体的机构的官员是“没有国家”、“丧失了民族性”的人。他还说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热烈拥护超国家的观点”,但首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德国人。因为他所争取实现的欧洲,正好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他的国家不需付出代价而重新获得因希特勒而失去的尊重和权利平等,然后获得压倒性的影响[15](p198)。
60年代初法国提出欧洲政治联盟的建议,是一个“国家间的联盟”,其决策程序完全是政府间合作性质的。还提出使经济共同体从属于政治联盟,想以政府间合作原则控制有一定超国家性质的经济共同体,引起争论。60年代中期,法国与共同体委员会因共同体自有财源,加强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的财政权力,发生严重争论,引起“空椅子危机”。这都是法国坚持政府间主义,抵制联邦主义和超国家原则的表现。最后达成“卢森堡妥协”,使共同体决策中政府间主义更为加强了。为此戴高乐受到了欧洲联邦主义者的批评。莫内说,戴高乐是以另一个时代的思想指导法国的政策,是回到过时的民族主义道路[5](p330-331)。
戴高乐后,从乔治·蓬皮杜到雅克·希拉克,政府间主义仍是法国在欧洲联合问题上的基本方针。1970年的《维尔纳报告》要求把权力与责任由国家层次转移到共同体层次,设立新的共同体机构并修改罗马条约。蓬皮杜总统不喜欢这个报告。他强调欧洲“只能意味着在现存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由决定协调其政策的国家的邦联”,“只能由各国政府一起共同决策”[16](p89-91)。他说:“假若欧洲不是主权国家的欧洲,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欧洲呢?这些国家自由地承诺缩小分离它们的壁垒,逐步协调它们的农业、货币、工业与社会政策,以现实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小心谨慎地和分阶段地走向统一……欧洲统一要么在尊重成员国个性的情况下实现,要么就实现不了。”[17](p298)他反对加强共同体委员会的职权,反对实行欧洲议会直选和加强其权力。他提出加强“政府间行动”,寻求使共同体国家首脑会议制度化,这一点在1974年实现,它加强了政府间主义的影响。斯皮内利说,蓬皮杜与戴高乐有所不同,但“政府间主义仍是他的基本准则”[8](p69,p73-74)。
以后的德斯坦总统也主张政府间原则,表示“完全赞成欧洲邦联”,即各国在其中保持主权,在政策上互相接近,但谁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联邦欧洲”在他看来则是不现实的[17](p361)。当1975年的“廷德曼斯报告”提出改革共同体的建议,具有超国家主义性质时,法国持“最低纲领派”立场,反对报告中关于共同体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应有更大权力等建议,说它们是“非常不受欢迎的,有太多的超国家主义的含义”[8](p90)[16](p262)。
密特朗总统在1985年曾与科尔一起倡议建立欧洲政治联盟。90年代初他重提欧洲政治联盟的建议。他还提出以欧洲共同体为核心的“欧洲邦联”的建议,但从来不提“欧洲联邦”。根据他的讲话,这个邦联的结构要比共同体松散得多,在其中每个国家都能“在许多方面保持它的个性,它的法律,它的政府以及它的主权机构”[17](p547-548)。在讨论和签订“马约”之际,法国倾向于淡化欧洲联盟的超国家机构。它特别反对给欧洲议会以更大的权力,而是寻求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欧洲理事会。在经货联盟方面,法国不赞成关于欧洲央行独立的主张,也不愿意把货币政策这类主权完全上交,而主张各国保留经济和财政决策权[7](p171)[18](p161)。
希拉克总统也是主张政府间原则的。例如在讨论对“马约”进行修改期间,他撰文指出,欧洲联盟“既不能以一种联邦制为基础,也不能仅限于成为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19](p52)。显然他不主张欧洲联盟走联邦制的发展道路。
坚持政府间原则反对联邦主义的另一支强大力量,是在英国。正如英国学者诺塞奇所说,“联邦道路是一条工党和保守党都不准备遵循的道路”[20](p158)。40年代末,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时候,英国就坚持它只能是一个政府间的合作组织。温斯顿·丘吉尔这位“欧洲合众国”的号召者,也反对联邦派的主张。1950年舒曼计划提出后,工党发表《欧洲统一》的小册子,声明“不会接受一个要使国家政策的重要领域转交给超国家的欧洲代表权力机构的体系”[21](p255)。当时在野的丘吉尔也表示:“如果他问我‘你会同意一个拥有超国家权力的机构告诉英国不要开采更多的煤炭或生产更多的钢铁,而是去生产西红柿吗?’那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不’。”[22](p179)后来当六国成立共同市场时,英国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这只是一个松散的政府间的贸易安排。
后来,英国申请加入了欧洲共同体,但坚持政府间原则始终不变。60年代初英国在决定申请加入共同体时,麦克米伦首相就对议会说:有人想搞一个联邦结构,想使欧洲成为某种“合众国”,但“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类比”。“另一个概念才是唯一可行的,那就是邦联或者commonwealth那样的概念……或者戴高乐将军所称的‘祖国的欧洲’——各国在明确规定的领域内为共同利益而合作,同时保持各自的伟大传统和自豪。”[12](p72)他在一次与戴高乐会谈后曾写道“我们是反联邦主义者,他也是……我们意见一致”[7](p53)。1969年,工党首相威尔逊也明确表示,英国如果加入共同体,要“坚决反对承诺任何政治联盟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邦制”[23](p268-269)。1975年,工党政府在关于与共同体重新谈判的报告中强调“政府不会对任何类型的欧洲联邦式结构承担任何义务”,未来欧洲联合的发展仍然取决于各国政府和议会的决定[12](p134)。
80年代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态度更为坚决。撒切尔夫人对欧洲联合的态度常被比作戴高乐第二。撒切尔夫人主张,一体化不应超过在政府间原则基础上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及协调经济和外交政策的范围。她坚决反对关于修改罗马条约,改革共同体制度,加强超国家机构权力的一系列建议,反对改变部长理事会一致通过的原则。她回忆说:欧洲联合80年代压力很大,“我的目标是确保欧洲各国不至鲁莽地走向联邦主义”。“我别无选择,只得采取与欧共体多数成员都截然不同的路线,高举国家自主权、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的大旗——并且奋战。”[24](p382,487)在讨论1984年反映联邦主义派要求的《欧洲联盟条约草案》时,英国提出了“联合而非联盟”(Unity not Union)。她说,她不知道“欧洲联盟”意味什么,而宁愿在政策方面实际的联合。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英国支持将会增进“联合”的“真实的和可行的步骤”,英国不反对改变,但应当是最低限度的和“实际可行的”[25](p209)。一位英国人写道,英国主张采取具体步骤进行欧洲联合的建设,而不是那种政治象征先行,首先进行重大的共同体机构改革的办法[26](p152)。1986年的“单一欧洲文件”规定的目标,与全面改革共同体机构的建议和1984年通过的“欧洲联盟条约草案”的要求相差很远,人们认为,这是英国的实用主义在欧洲建设问题上对某些国家的“理想主义”的胜利。
随后又提出了建设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计划。德洛尔积极推动加深和扩大一体化,加强超国家机构权力,使共同体委员会空前活跃。英国则步步为营,坚持政府间原则,反对向联邦主义的方向发展。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她所称的“布鲁塞尔的集权倾向”和建立欧洲“超级国家”的企图。她在回忆录中说,她不喜欢“德洛尔那一套具有干涉性质的联邦制度”,并称德洛尔是想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语言、经济等基础上建立起《圣经》中所说的“巴别通天塔”(即指空想的计划),是“联邦主义代言人”,是“我的一大劲敌”[24](p485,494)。1988年6月,德洛尔对欧洲议会说,他预期到1993年时,将有必要建立“初步的欧洲政府”,而共同体的经济、财政和社会的立法将有80%来自共同体[12](p208)。撒切尔夫人对此倾向十分警惕。1988年9月,她在被称为“欧洲联邦主义堡垒”的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建设的五条方针:“我的第一条指导方针就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志愿和积极的合作,是建设一个成功的欧洲共同体的最佳途径。试图压制民族特性和把权力集中到一个欧洲集合体的中央,将是极为有害的……欧洲将会正是由于法国是法国,西班牙是西班牙,不列颠是不列颠,各自都有其自身的习惯、传统和同一性,而更加强大有力。”[9](p243-244)此后,她多次强调这些原则。
在行动上,英国先是反对把经货联盟列为进一步目标,而主张只建设单一的欧洲内部市场。1988年欧洲理事会认可了建立经货联盟的目标,随之提出分三阶段建立经货联盟的“德洛尔报告”。撒切尔夫人说,英国一旦把预算和货币的权力都交出去了,“我们的主权将所剩无几了”。德洛尔报告意味着建立一个联邦主义的欧洲,英国不能接受[11](p77-78)[27](p186)。她自称她对这个报告“从头反到尾”。英国反对单一欧洲货币,只同意欧元与各国货币作为平行货币。在1990年10月罗马首脑会议上,撒切尔夫人不怕孤立,以1∶11反对从1994年起实施经货联盟第二阶段计划,反对建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单一欧洲货币。
1990年法德提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虽然并不是一个超国家主义的“联邦”计划,英国政府起初也持异议。1990年10月,撒切尔夫人在议会就政治联盟问题说,英国坚决维护通过议会管理自己的基本权力,反对牺牲英国议会的权力来加强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她连用三个“不”字,坚决反对德洛尔把欧洲议会作为众议院,部长理事会作为参议院,执行委员会作为共同体的最高执行机构的联邦主义构想[12](p236)。
撒切尔夫人这种态度,甚至引起了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等人的批评。但不仅撒切尔夫人并不动摇,而且她辞职后英国政府仍坚持既定方针。1991年在讨论《欧洲联盟条约》草案期间,外交大臣赫德和首相梅杰都强烈反对在条约中有“联邦目标”的话[7](p172-173)。在《欧洲联盟条约》(即“马约”)签订前,梅杰再次表示,英国决不会同意全面改变共同体的性质,不会赞成使联邦欧洲拥有充分的立法权而各国政府和议会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决不会接受一个把共同体描绘成具有联邦性质的条约”,“辅助性”原则必须写进条约,等等[9](p263-264)。欧洲联盟条约未能在走向联邦的道路上前进,而是在一定意义上“从联邦主义后退”,原因之一是英国的立场。
欧洲联盟建立后,在关于联盟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讨论中,英国仍是坚持政府间原则最为坚决的国家。1995年9月,外交大臣里夫金德强调说,民族国家仍旧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组成单位,相互依存的加强不是主权的终结。英国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即使在一些领域失去对联盟的影响力也是必要的。“正是一位法国政治家号召‘祖国的欧洲’,而这是与我们的想法相近的。”[12](p278-281)1996年3月,英国政府发表《国家伙伴关系》的白皮书,反对“结构严密的、中央集权的、联邦的欧洲”,主张欧盟应成为一个“促进国家间合作的机构”,对“马约”只应进行“最低限度”的修改,反对成员国向欧盟交出更多的权力,反对扩大理事会的多数表决范围和扩大欧洲议会的立法权[19](p52-53)。《阿姆斯特丹条约》在修改“马约”,加深一体化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与英国的这种主张是分不开的。
3
不仅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反对超国家和“欧洲联邦”的道路,其他国家也有相当强大的反联邦主义力量,例如丹麦就是如此[25](p37)。50年代,斯皮内利曾写道:“当欧洲政治家面对欧洲统一问题时,他们采取职能主义方式,只是在迫于必要时才勉强地、半心半意地采取联邦主义的观点,而一旦压力减轻就将其抛弃。”[3](p56)后来皮埃尔·热尔贝就欧洲一体化中的这一组矛盾写道:“欧洲建设的未来掌握在各民族国家手里,它们仍然是唯一的权力持有者,唯有它们才能决定或者协商一致,共同行动,但保留各自的主权,或者把它们的一部分权限托付给欧洲机构。然而,国家的态度是矛盾的。对它们来说,欧洲本身是个目标,但要实现它就有使国家隶属于一个更高权威的危险,甚至有使它消声匿迹的危险,因此各国都拒绝联邦制。”[2](p414)
反对“联邦主义”和超国家原则而坚持“政府间主义”的力量始终存在并强大有力,集中反映了各国对主权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于一体化对国家主权可能的侵蚀进行的顽强抵制。这使“政府间主义”原则始终主导着欧洲联合的进程,联邦主义受到有力的制约。这种斗争表明,虽然西欧是现代化发展最早、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最深、历史和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共同性、区域性一体化开展最早的地区,民族国家和主权原则也远没有过时,其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战时欧洲联邦派提出的“结束欧洲分裂为主权国家的状况”和某些人的“主权国家衰落”论[12](p18-19)[1](p86),也许出发点是好的,在现实中却行不通。在这个意义上说,戴高乐的“祖国的欧洲”和撒切尔夫人的“主权国家自愿合作”原则更加现实,虽然他们有时过于我行我素。
许多欧洲国家都是有悠久历史和民族传统的国家,欧洲是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和原则最早产生的地区,二战期间各国曾为反对法西斯的统治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战后决不肯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轻易作出牺牲。在抵抗运动中曾广泛存在对重建旧的主权国家的怀疑,但“结束欧洲分裂为主权国家的状况”这种激进的欧洲联邦思想、纲领,在战后再没有那样广泛的号召力。各国很快重新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联邦主义者的预期。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原则,克服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但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存的民族国家,取消民族主权。有关国家政府赞成一些“超国家”的一体化,主要不是出于“联邦主义”的理想,而是为了更好实现国家政策的目标和利益而作出的“选择”。只是当国家单独行动、通常的国际合作都不足以实现国家政策的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时,才会选择有超国家特点的“一体化”。而且只在有限的领域内,国家主权为了严格限定的目的而转移到一体化的机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共同体内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过去属于民族国家范围内但现在需要在共同体甚至更大的范围内解决的事情越来越多,也使各国不得不逐渐接受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但这并未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即一体化的开始和发展,都是因各成员国利益的需要而实行的。戴高乐曾说过:“我相信,这个共同体特别会有利于法国。没有利益我们就不会干这件事。”[14](p353)其他成员国也莫不如此。例如德国,首先就是想通过一体化为恢复平等地位创造条件。康拉德·阿登纳曾强调,加入欧洲联合的条件是权利平等,反对对德国煤钢工业的单方面国际管制。维利·勃兰特说德国“不能放弃走向欧洲的决定”,因为“通过欧洲,德国才能恢复其本色,才能恢复其历史性的建设力量”[28](p550)。一些国家所以主张或接受一定程度的超国家一体化,一个始终重要的动机是制约德国,使之成为“欧洲的德国”。例如让·莫内在提出煤钢共同体建议和欧洲防务共同体建议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个目的。此外,共同体有利于开辟欧洲内部市场,成员国都可受益,更是无需赘言。总之正如英国学者米尔沃德所言,正是国家的需要才使一体化成为需要[6](p4-5,p19-20)。
这也决定了各国在一体化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时的态度。主权作为对内统治和对外自主的最高权利,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虽然按莫内所说,主权转移后只是“共同行使”,而不等于“丧失”,各国也不是轻易把主权的任何一部分转移给共同体的。在哪些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超国家”原则,将哪些属于国家主权范畴的权力或“职能”交给共同体,都是仔细权衡利害之后作出的。只有在得大于失或至少得失相当的条件下,成员国才可能同意进行某种转让。违反成员国主权和自愿,强行使国家主权服从共同体的权力,或者转移给共同体,是谈不上的。也不是单方面地把某国在某方面的主权转让出去。正如意大利的斯福尔扎所说,对主权进行限制的“唯一条件是其他国家也同我们采取同样行动”[4](p58)。同时,各国政府只接受从某些“低级政治”领域如经济领域开始的“职能主义”方式的一体化,并设法保证各国政府能对这种权力或职能的转移进行规范和控制。“简言之,欧洲国家在一些领域愿意共同享主权,是因为这样做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然而,尽管它们愿意分享主权,各国政府还是保持着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控制。”[7](p3)一些国家坚持欧洲联合的政府间原则,正是为了保证主权国家对一体化的“尽可能多的政治上的控制”。
战后欧洲联合的进程,是在“政府间主义”和“联邦主义”的两种倾向相互制约、相互竞争而又相互妥协中进行的,是“合力”的结果。要而言之,欧洲共同体的实际情况是:尽最大可能收取一体化的利益,尽一切可能维护国家主权,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在某些领域转移并共同行使主权。在有些领域,即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所谓“低级政治”领域,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超国家原则”。在某些方面,这种因素甚至逐步有所加强。这表明共同体的联合与合作的深度已非一般的国际合作可比,也表明了欧洲国家鉴于历史的教训和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现实,力求克服极端民族主义,避免重蹈覆辙,并为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开辟广阔前景所作的努力。在另一些领域,特别是在政治、外交和国防等“触及国家主权的核心”的“高级政治”领域,仍然坚持主权国家合作的“政府间主义”原则。总的情况是政府间原则仍然占主导地位。“低级政治”方面的“超国家”一体化,也是在政府间合作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受各国政府的主导和控制的。在共同体“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大的同时,政府间原则和主权国家对这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程度的制约,也加强了。有关国家保持了自由决定是否和何时加入某项一体化措施的权利,从而排除了强制性的一体化。无论欧洲共同体或欧洲联盟,都还是“含有超国家因素的政府间组织”。
战后以来,关于国际相互依赖和一体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之一,似乎国际相互依赖和一体化与国家主权的保持是“鱼与熊掌”。有人走向了以国际一体化来否定国家主权的误区。诚然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而且有必要共存、结合起来,“相反相成”。欧洲联合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通过反复权衡,寻找各国间利益的最大共同点,并形成一定的程序和制度,把一定领域、一定程度的超国家一体化(一定的主权和职能的转移和共同行使)与在总体上和大政方针上保持成员国的主权和对一体化进程的主导和控制相结合,使共同体的集体利益与各国的主权和特殊利益相统一,使国家主权原则及其内涵和行使方式的变与不变相统一,坚持和超越相统一。由于努力实现这种结合,才能既最大限度地收取一体化之利而又保持主权国家的自主独立。戴高乐和撒切尔夫人虽然坚持政府间原则,坚持国家主权,却并不一般地反对欧洲联合。撒切尔夫人还曾声称“英国的前途在于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经历了诸多的困难甚至危机,却能逐渐发展,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上的一切事物总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而进入更高层次和形态。国家主权作为历史的产物,其具体内涵和实现形式,在历史的进程中也会实现发展和超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及其作用。各国在当代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加强的条件下,作出自主的选择,参加国际合作和一体化,从中受益,而同时保持自己的主权和独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简单地把坚持国家主权与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一体化对立起来,或借口全球化、国际一体化来否定国家主权原则,而用某种其他的原则取而代之,或是强加于人,在理论上都将是一种误导,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收稿日期:2000-05-08
标签:欧洲议会论文; 罗马条约论文; 欧洲理事会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欧洲一体化论文; 合作原则论文; 国家主权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欧盟论文; 经济学论文; 联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