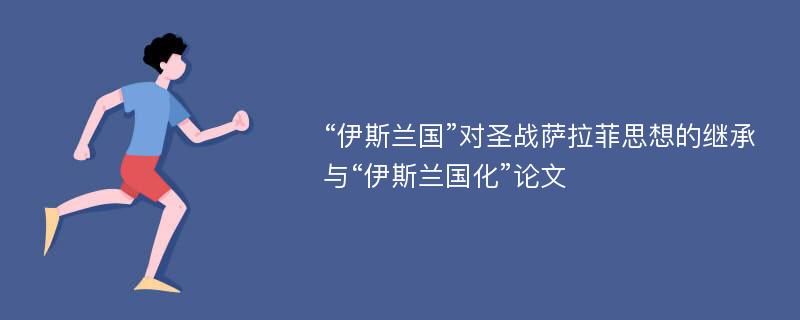
“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伊斯兰国化”*
周 明 雷环瑞
【内容提要】作为“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一部分,了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需要探究其与圣战萨拉菲思想之间的关系。由于涉及大量宗教内容,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讨论略显不足。“伊斯兰国”在继承圣战萨拉菲思想的认知与行动体系基础上杂糅了其他伊斯兰思想,展现出了自身特色,但并未在神学上展示出重大创新。就其产生的国际动员能力以及网络影响力而言,“伊斯兰国”取得了相当成功。但其退出“基地”组织、挑战“基地”组织恐怖主义领导者地位的做法,显现了各恐怖组织之间的矛盾。“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引发其他恐怖组织的模仿,激发各组织间的竞争,进而使整个萨拉菲恐怖主义陷入派系斗争或过于极端,从而削弱萨拉菲恐怖主义。
【关键词】“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圣战萨拉菲思想
自2014年宣布建立“哈里发国”以来,“伊斯兰国”[1]迅速扩张,成为全球破坏力最强的恐怖组织。[2]随着在中东地区的失利,“伊斯兰国”号召非阿拉伯成员回国或就地采取恐怖袭击,[3]至今展现着全球范围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我们除了密切关注“伊斯兰国”的动向外,还应重视受“伊斯兰国”鼓舞的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在2015年与“伊斯兰国”相关的“独狼”恐怖袭击中,有65%是自我激进化,截至2016年7月,这一比例为54%。“伊斯兰国”大部分的外部恐怖行动,也由独立的追随者所制造。[4]由此可见“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宣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也随着其成员的回流威胁各国安全。“伊斯兰国”已经很难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地面行动,但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出,并激进化与极端化独立的个体等,“伊斯兰国”仍将对国际安全与地区稳定产生严重影响。鉴于此,深入了解“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并对其扩张做出有效应对十分必要。为了解“当代圣战萨拉菲主义”一部分的“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5]需要回溯萨拉菲思想与圣战萨拉菲思想的内涵,辨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与圣战萨拉菲思想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分析涉及大量宗教内容,解读难度较高,目前学界并未就此问题开展充分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此类试题,在学生已经掌握一定的思维方法后,通过阅读、理解和分析文字素材或图表等形式,获取题干的信息,充分考查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和批判性。无论是“科学故事”还是科技论文,在命题时还关注学生的生命观念和社会责任的评价,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或热点,渗透价值观教育,理解生物学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一 萨拉菲思想的含义及其流派
萨拉菲(salafi)源自阿拉伯语“salaf”,[6]指“先人”或“前辈”。在伊斯兰教中salaf多指伊斯兰教早期三代先人,即圣门弟子、二传弟子及三传弟子。[7]在逊尼派六大圣训集中的《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先知穆罕默德说‘我的教民中最优越的人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圣门弟子),其次是紧挨他们的人(二传弟子),再其次是紧挨他们的人(三传弟子)’”。[8]萨拉菲思想正来源于对早期前三代穆斯林的一种向往。早期三代穆斯林不仅见证了伊斯兰教的兴起,而且将先知的行为模式确定为正确的生活方式。[9]希冀回归前三代穆斯林信仰与实践的萨拉菲主义者主张严格遵循《古兰经》及圣训,以使他们能够脱离主观以及自利的偏见,真正领悟安拉的旨意。[10]
萨拉菲思想的主张最早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早期教法学派“圣训派”。[11]“圣训派”在教法上主张排斥理性,严格以《古兰经》与圣训为依据。第一次使用“萨拉菲”一词的罕百里教法学派创始人伊本·罕百勒(Ibn Hanbal),与“圣训派”类似,主张回归前三代穆斯林,执着于对《古兰经》与圣训文本的解读。[12]之后,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a)继承了这一主张,并称自己为“萨拉菲道路遵循者”。在《法特瓦大全》中,伊本·泰米叶写道:“赛莱菲耶就是本·穆罕穆德·艾布·伯克尔等人所说:赛莱菲的道路就是只解释《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意义,关于真主的属性避免神人同行同性论,不给真主拟人化的属性,所以我们不说‘手’是力量,‘听’是知识”。[13]
萨拉菲思想可从教义与教法主张入手进行分析。萨拉菲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严格从字面意义解读并遵循“认主独一”(tawhid),包含“认主独一”(tawhid al-rububiyah)、“拜主独一”(tawhid al-Uluhiyah)、“名称与属性独一”(tawhid al-asma’ wal-sifat)。[14]除从文本解读宗教经典、独特的“认主独一”理解以及回归前三代的信仰与实践,萨拉菲教义还主张:第一,与不信者做斗争,尤其与那些以各种形式举伴真主的人做斗争。第二,只承认《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与先知同伴的公议为创制教法的权威。第三,驱除那些他们谴责的、在信仰和实践上有革新的穆斯林。第四,声称一位严谨的教法权威对于经训的解释可以有效引导一切时代的所有穆斯林,而且这些经训都是清晰易懂的。[15]
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萨拉菲思想在教法主张上出现了分歧。伊本·泰米叶面对当时的“创制之门关闭说”,[16]在教法上提倡“伊智提哈德”(al-Ijtihad)即创制,指运用理智、判断求得结论的思维过程,近代多解释为“独立判断”,指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自由、变通地解释教法,不受中世纪传统的约束。[17]当代萨拉菲思想支持者也多提倡“伊智提哈德”。同样遵循萨拉菲教义的瓦哈比教派,则遵循了罕百里教法学派。与泰米叶所提倡的“伊智提哈德”不同,罕百里教法学派拒绝个人意见解释教法问题。[18]萨拉菲重要思想家穆罕默德·纳赛尔·丁·阿尔巴尼(Muhammad Nasir al-Din al-Albani)曾因批判瓦哈比教派遵循罕百里教法学派,而遭到沙特政府驱逐。[19]尽管就时间而言,当代萨拉菲运动晚于瓦哈比教派,但从思想渊源来看,瓦哈比教派是沙特“特色”的萨拉菲思想。
时至20世纪,萨拉菲思想中的纯洁派、政治派与圣战派分别出现,回到前三代穆斯林的“道路”(manhaj)即方法是区分这三个派别的重要依据。[20]萨拉菲三派作为当代萨拉菲思想的主要分支,都强调“认主独一”,拒绝宗教上的标新立异,认为自身教派与其他“离经叛道”的伊斯兰教派不同,并将会在末日独自获救。[21]纯洁派萨拉菲的重要人物、著名的圣训学者阿尔巴尼继承了传统萨拉菲思想,追随“认主独一”、反对标新立异,主张通过宣传、宗教教育净化伊斯兰。[22]在政治上,阿尔巴尼认为除非宗教得到净化、正确的行为得到实施,否则政治行为会导致穆斯林群体产生腐败与不公。在“吉哈德”(jihad)一词的使用上,阿尔巴尼及其支持者将“吉哈德”视为抽象性、精神性的活动,而非物质性活动,并且认为以“吉哈德”为名发动的暴力带来的危害大于好处。因而发动暴力圣战者,哪怕是针对入侵者也被阿尔巴尼及其支持者称为“哈瓦利吉”(Khawarij)。[23]
虚拟网络的消极作用。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严重,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对传统文化戏剧化演绎下缺乏理性地辨别和甄选,导致了大学生无法真正追根溯源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政治派萨拉菲的主要代表为“穆斯林兄弟会”。相较于纯洁派对政治参与的排斥,政治派萨拉菲者为了回归前三代穆斯林的信仰与实践,愿意使用政治手段。“穆斯林兄弟会”是由哈桑·班纳(Hassan al-Bannah)在1928年于埃及创立的伊斯兰组织,而且该组织将萨拉菲观点融入了其政治实践中。具体来说,班纳将“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主要归于三点:第一,伊斯兰教是一个综合的体系。第二,伊斯兰教有两大经典,即《古兰经》与圣训。第三,伊斯兰教在何时何地都适用。对于伊斯兰教其他派别,“穆斯林兄弟会”没有敌意。它主张通过开展会谈、建立党派与建立伊斯兰世界的联盟来复兴哈里发。[24]
随着埃及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关系破裂,“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活动转到沙特阿拉伯。受“穆斯林兄弟会”影响,萨拉菲思想的重地沙特阿拉伯也出现了政治萨拉菲运动——“觉醒”运动。沙特“觉醒”运动领导人之一萨尔法·哈瓦利(Safar al-Hawali)与阿尔巴尼同样主张伊斯兰教需要净化,但哈瓦利并不满足于“出世”路线图。为了清理哈瓦利所认为破坏伊斯兰教的因素,特别是西方思想的传播与中东国家对西方的依赖,哈瓦利主张穆斯林要建立自己的支柱产业与技术,动用包括政治参与的方式净化伊斯兰。“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卫星频道去对抗他们(指西方,引者注)的卫星频道,最起码我们要把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发挥至极致”。“觉醒”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方面大力推动宗教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也凝聚包含律师、工程师等在内的多方力量,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寻求变革。[25]
圣战萨拉菲思想的出现融合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与其他萨拉菲派别的主张。[26]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圣战派似乎接受了政治派的观点。他们认为,纯洁派没有很好地理解当今社会,同时也对政治体制不满,但还没有完全反对政府。政治派与圣战派在这一时期的界限是模糊的。事实上当代圣战萨拉菲思想的源头与政治派(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中的军事派)渊源颇深。
“伊斯兰国”崛起地伊拉克,同样在伊斯兰教的末日思想中有着一定地位,它是伊斯兰教诸多预言里救世主马赫迪(Mahdi)出现先兆中的末日战斗之地。[100]“伊斯兰国”第二代领导人阿布·艾尤卜·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深信着马赫迪即将到来,他的许多决策被认为是源于对于末日思想的笃信。为了在“末日决战”中帮助马赫迪,马斯里在上任几个月便建立“伊拉克伊斯兰国”。[101]伊斯兰教中的末日救世主马赫迪,在伊斯兰经典文本中有着多处叙述。如“谁将会在末日出现,他是被正确指引的哈里发与伊玛目中的一位,但并不是拒绝派所等待的”,“马赫迪来自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家族,安拉将会在一夜之间指引他”。[102]马斯里对末日的笃信,甚至引起了其内部成员的反对。早在2007年,“伊斯兰国”首席教法学家向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头目抱怨,“对于末日迹象的错误理解是‘伊斯兰国’的错误之一。如果问题仅限于此将会很好处理,但这个问题已经扩散到我们相关领域的圣战工作中。例如,他们宣称马赫迪将会在一年内出现,因而扬言在三个月内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并且发布命令直到末日来临,战士不准从战场撤退。这对于我们的兄弟而言是危险的”。[103]
当代圣战萨拉菲有五大特征:第一,强调“认主独一”,主张“认主独一”不仅是信仰的表达,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第二,强调真主主权,认为主是唯一的立法者,只有主能够确立对与错、善与恶、允许与禁止。第三,主张严格从字面意义理解《古兰经》与圣训,拒绝标新立异。第四,认为“塔克菲尔”(takfir)即宣布一个穆斯林是卡菲尔(kufr)即异教徒,是许可的也是必要的。第五,强调“圣战”的神圣性,主张“圣战”是对抗违背神旨意的“异端”政权的宗教义务。[29]在圣战萨拉菲思想的实际运用中,各圣战萨拉菲恐怖组织的主张并不相同。如“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都追随圣战萨拉菲思想,在“圣战”运动中也体现了圣战萨拉菲特征,但二者的意识形态存在诸多不同,“基地”组织与其分支之间也有一些差异。[30]
应用BioEdit录入并编辑核苷酸序列,并使用该软件对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通过Lasergene 7将核苷酸序列转化为氨基酸序列;采用Weblogo在线数据库(http://weblogo.berkeley.edu/logo.cgi)比较 UL144 碱基变异情况;采用MEGA5.05构建、分析和编辑氨基酸序列邻接系统进化树;应用EXPASY服务器的Prosite数据库 (http://myhits.isb-sib.ch/cgi-bin/motif_scan)预测UL144基因编码的蛋白功能位点。Toledo株为低传代临床病毒株,作为研究对比的标准株。
作为“当代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伊斯兰国”在宣传以及实践中体现了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主张,践行着圣战萨拉菲的“圣战”道路。从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五个特征可以归纳出四个核心概念:即“认主独一”“真主主权(hakimiyyah)”“塔克菲尔”以及“圣战”。依据字面意思解读《古兰经》与圣训,更多的是对于经典的解读方式,为三派共享,而且它们的解读方式也无实质区别。能够将圣战派萨拉菲与纯洁派萨拉菲和政治派萨拉菲区分开来的是,圣战派萨拉菲不同于其他两派对于上述四个概念的理解,以及圣战派对“效忠与绝罚”(al-wala wa-l-bara)的独特阐释。[34]为更好地梳理圣战萨拉菲对于这五个概念的独特理解,本文将依照“卡菲尔”“真主主权”“认主独一”“效忠与绝罚”“圣战”的顺序,分析“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
二“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
不仅圣战萨拉菲思想在不同组织间有着差异,萨拉菲思想也展现出多元的景象。正如罗伊·梅杰(Roel Meijer)所言:“他们(即萨拉菲运动——引者注)带着各自的教义、利益、问题及背景,创造了一个多面性的赛莱菲耶,反映了多种张力,从非政治的、非行动主义者趋向、生活方式和认同运动到政治的、行动主义者的运动和暴力的吉哈德网络。这些运动都自认为源于赛莱菲耶,并且与瓦哈比主义分享基本的教义和术语,但它们各有自己的谱系,有其基于地方环境和全球发展而形成的关于赛莱菲耶的独特诠释”。[31]萨拉菲思想在教义上强调回归经典,教法提倡“伊智提哈德”,思想传播倚重非正式的师生关系网络,这些因素促成了萨拉菲思想的多元,也使得萨拉菲思想至今始终没有统一的思想和组织领导。[32]此外,多元的思想也使萨拉菲思想支持者并不严格地遵循纯洁派、政治派和圣战派的主张而行动,而是依据不同的利益、面临问题和所处的背景等进行调整。[33]
蠕虫状链一直是分析DNA等生物大分子常用的模型,也是半刚性和刚性链高分子较为通用的模型.本工作对蠕虫状链模型作一介绍,并对均方末端距推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最后提出解决方法.
式(6)中:σd1为第1层的噪声估计,该阈值规则只需要对第一层的噪声进行估计,大大节省了阈值去噪过程中计算阈值的时间,同时只要挑拣相宜的阈值处理公式,该阈值选取方法的去噪质量将高于其它方法.
“塔克菲尔”即宣布一个穆斯林为异教徒,也即判定其叛教,最早由哈瓦利吉派引入。这是针对穆斯林的纯真性所做的判断。当一个穆斯林被认定为“卡菲尔”,他在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惩罚是“让他忏悔,如果忏悔;否则教法的总执行官因为他的叛教应处死他”。[35]宣称一个穆斯林为“卡菲尔”必须对他的信仰作出判断。哈乃斐教法学派创始人艾布·哈尼法(Abu Ḥanifa)主张触犯伊斯兰教中的大罪也不能否认穆斯林信仰,即“伊尔吉亚”(irja),进而认为通过内心的信念与口中的言谈就可以确定其信仰而无须行为判定。[36]显然,艾布·哈尼法所定义的信仰难以客观判定,导致宣称某一位穆斯林是“卡菲尔”难以实现。鉴于此,圣战萨拉菲者主张信仰不仅是内心的信念与口中的言谈,而且也包括了行为。[37]依据行为判定穆斯林的信仰,为圣战萨拉菲实行“塔克菲尔”奠定了基础。
纯洁派萨拉菲同样认为行为是信仰的一部分,[38]但在对一个穆斯林是否是“卡菲尔”进行判决时,纯洁派萨拉菲主张,“只要一个穆斯林内心有一个原子的重量(an atom’s weight)的信仰,那么就不能永久停留在地狱”。[39]与此类似,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在叛教的判定方面主张:“他们不能判断任何个人或一个团体是异教徒,他们的证据就是伍萨麦•本•宰德•本•哈里萨杀害了一个念了:‘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的异教徒时,他对穆圣说:‘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害怕我手中的兵器’,但是穆圣否认了这种行为,同时没接受他的道歉,穆圣对他说:‘难道你知道他心中的一切!他是真心说呢,还是假意说呢?’即:难道你知道他念作证词时是不是诚心诚意的吗。只有当一个人否认了宗教中人所共知的原则,或违抗了穆斯林大众,并未因这个罪过而向安拉忏悔,这种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断定这个人是异教徒”。[40]纯洁派萨拉菲对“塔克菲尔”的判定主张,显然继承了艾布·哈尼法的观点。而圣战派萨拉菲则主张依据行为给穆斯林作“塔克菲尔”判定,这为恐怖组织打击甚至消除异己打开了大门。如“基地”组织将行为上的反对“圣战”与联合异教徒定为叛教,[41]运用“塔克菲尔”清除异己。[42]
“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思想将行为纳入信仰评价中的观点。如“伊斯兰国”在其官方杂志《达比克》第8期《“伊尔吉亚”——最危险的创新》一文中明确表明了这种观点。[43]在该文中,“伊斯兰国”称“伊尔吉亚”是“削弱伊斯兰信仰的异端创新”,主张行为是穆斯林信仰的一部分。认为如果信仰仅关乎精神,最终将导致穆斯林无法分清正确与错误、信士与叛教者,强调穆斯林需要审视自身的行为以不偏离“正道”。基于此,“伊斯兰国”认为依据行为进行“塔克菲尔”判定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包含“伊斯兰国”在内的圣战派萨拉菲组织对“塔克菲尔”的必要性论述,以及依据行为判定“卡菲尔”的原则与哈瓦利吉派一脉相承。在信仰方面,哈瓦利吉派同样主张信仰包括精神与行为。在“塔克菲尔”的判定方面,哈瓦利吉派主张严重地违背教义的行为剥夺了一个穆斯林的全部信仰,使之成为叛教者,而消灭叛教者,对于哈瓦利吉派而言也是一种职责。[44]也正是因为圣战萨拉菲“塔克菲尔”思想与哈瓦利吉一脉相承,“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塔克菲尔”运用,被纯洁派萨拉菲视为一种滥用,是一种“哈瓦利吉意识形态”。[45]
把可能泄露用户隐私的名词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专有名词,比如,名字、地点等,一类是普通名词,比如,一些隐私敏感的疾病、职业等。 ICTCLAS 2016[15]可以自动的对消息中的名词进行标注,然后利用CN-Dbpedia[16](提供开放API)的资源,把标注的名词的概念跟 CN-Dbpedia中的资源进行关联,借助SPARQL查询语言[17]和语义Web[18]来实现标注名词的语义分析。
“真主主权”关注神权在政治中的地位以及实现方式,与“认主独一”思想中“拜主独一”密切相关。就独遵安拉的指引、践行沙里亚法[46]而言,纯洁派、政治派、圣战派萨拉菲并无区别。萨拉菲三派在真主主权问题上的差异,主要集中于神权的政治实现方式。纯洁派萨拉菲对政治并不热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代政治是满意的。部分纯洁派萨拉菲认为,“安拉的沙里亚法没有获得最高地位,统治机关存在的大量的罪恶,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家与土地处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47]尽管如此,纯洁派萨拉菲并无意去改变政治,他们认为,“真主没有授权暴君统治我们,除非我们自己的行为腐化了……至高的安拉说:‘凡你们所遭遇的灾难,都是由于你们所做的罪恶’(《古兰经》42:30)[48]……所以,如果人民想要从暴虐统治者的压迫中解救自己,那么必须首先放弃压迫本身”。[49]由此可见,尽管纯洁派萨拉菲认同沙里亚法的最高权威,赞同沙里亚法的实行,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他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的改变。而在政治派萨拉菲眼中,真主主权的实现无疑需要现代政治手段。如1991年沙特觉醒运动在“五月信件”(或称“乌里玛信件”)中对沙特王室提出了12点政治改革要求,要求在沙里亚法内保障公正与平等、司法独立,保护个人权利等。[50]总之,在坚守神权的基础上,政治派萨拉菲主张参与现代政治。
与纯洁派萨拉菲不参与政治的姿态和政治派萨拉菲倡导的政治改良路径不同,圣战派萨拉菲不仅宣扬通过暴力方式改变政治现状,而且拒绝走改良路径。“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教父”[51]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将世界分为“伊斯兰世界”和“蒙昧主义统治的世界”,进而将国家划分为“神圣的、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和侵害“真主主权”的“非法政府”。[52]而“蒙昧主义”指的是把人的理性作为最高标准与生活价值。库特布这种将人的理性与“真主主权”对立的主张,实质是对现代政治改良的拒绝。而且基于他对世界的理解,库特布不承认民族国家存在,也不承认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体系及规范,进一步主张伊斯兰的总原则是恢复真主统治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库特布认为“圣战”是永久必要的,进而呼吁穆斯林主动参加“圣战”。[53]在继承库特布思想的基础上,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进一步把“人为的法律”等同于“非伊斯兰崇拜”,宣称当代伊斯兰世界领导人为“卡菲尔”。[54]圣战萨拉菲思想暴力实现“真主主权”,以及对改良路径的拒绝为“伊斯兰国”所继承。在《达比克》第10期《安拉的法律或者人的法律》一文中,“伊斯兰国”称自己为世界上唯一统治独归真主、实行沙里亚法的地方。[55]而民族主义、现代政治在“伊斯兰国”的眼中遵循着人的律法,就是一种叛教与异端行为,[56]而只要“异教”与“伪信”存在,“圣战”就将一直进行下去。[57]由此可见,圣战萨拉菲思想结合“真主主权”概念将“塔克菲尔”政治化的做法,被“伊斯兰国”所继承,为其暴力手段实现政治诉求提供合法性辩护。
“认主独一”是萨拉菲思想的核心,包括了认主独一、拜主独一、名称与属性独一三个方面。对于“认主独一”的内容理解以及地位判断,圣战派基本也持上述观点。依据行为判定是否遵循认主独一、拜主独一、名称与属性独一,是圣战萨拉菲派的特征之一。圣战萨拉菲者较少直接讨论“认主独一”的内涵,更多关注于统治者的行为。圣战萨拉菲者马克迪西将“人为的法律”等同于“非伊斯兰崇拜”,“基地”组织“近敌”派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因现代政权形式而宣称埃及等政权“叛教”,需要对这些政权发动“圣战”。[58]圣战萨拉菲者显然是运用行为判定一国政权是否遵循“认主独一”。
“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对“认主独一”的重视以及阐释。在其官方杂志《罗马》第1期《伊斯兰宗教》一文中,“伊斯兰国”明确将“认主独一”作为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信仰支柱,同时将“认主独一”阐释为认主独一、拜主独一、名称与属性独一。[59]将行为纳入信仰评判之中的主张,使得“认主独一”对于圣战萨拉菲思想而言,不仅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而且融入了生活方式等具体行为,由此成为圣战萨拉菲派实施“塔克菲尔”的依据。“伊斯兰国”对什叶派“塔克菲尔”判定,依据正是什叶派陵墓崇拜、背弃圣门弟子、将神性赋予伊玛目等行为,[60]实际是将“认主独一”行为化而进行的“塔克菲尔”判定。
伊斯兰教中的“圣战”或“吉哈德”,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奋斗、尽力”,“圣战”即为主奋斗。[68]“圣战”分为“大圣战”与“小圣战”。“大圣战”是指内心的“圣战”,包含苦修、履行宗教义务、实践伊斯兰教所倡导的道德要求,抑制各类欲望、随时随地传播伊斯兰原则等;“小圣战”是指为真主而战,即战场上对抗不信仰伊斯兰教者。[69]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口中的“圣战”多为“小圣战”。“小圣战”的实质是维护和传播伊斯兰教,它针对的是不信道者与压迫穆斯林者,具有进攻与防御的双重属性。[70]随着历史的演变,大多数伊斯兰学者认为圣战这一行为虽然是神圣的义务,但已进入休眠状态,即默认作为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的“圣战”已经失效,不再符合穆斯林的利益。[71]与不采取“圣战”暴力方式的纯洁派萨拉菲与政治派萨拉菲不同,圣战派萨拉菲将“圣战”从休眠中复活,如马克迪西主张“圣战”是“效忠与绝罚”的自然结果,是“绝罚”的最高形式;[72]“基地”组织把“圣战”作为信仰的一部分,主张“圣战”的目标是践行“认主独一”,恢复伊斯兰教的荣耀的重要手段。[73]“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将“圣战”视为必要,且是信仰应有之义的观点。如在《达比克》第7期中,直接称伊斯兰教是“执剑而非和平的宗教”。[74]
“效忠与绝罚”概念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原指一个部落将某个成员驱除。[61]这一概念在伊斯兰世界中有着不同含义,曾被认为是一种创新而受到谴责。在沙特阿拉伯,“效忠与绝罚”意味着忠于王室以对抗反抗,还曾有拒绝穆斯林寻求非穆斯林帮助的内涵。[62]后来,“效忠与绝罚”逐渐演化为忠诚于穆斯林群体以保卫伊斯兰信仰,允许暴力对抗穆斯林群体的敌人。[63]在伊斯兰教发展历史上,首次将“效忠与绝罚”作为思想核心的是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信徒对本派成员“效忠”而对其他人“绝罚”,构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64]马克迪西将“效忠与绝罚”纳入信仰体系中,并据此认为沙特王室未能正确“效忠”真主与沙里亚法,“绝罚”非穆斯林而与美国签订条约,因此裁定沙特王室是“卡菲尔”,主张暴力反抗“叛教”的伊斯兰政权。[65]“基地”组织第一次将“效忠”的对象从国家转向组织,要求穆斯林效忠于它。对于没能“正确”实施“效忠与绝罚”的穆斯林,“基地”组织认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伊斯兰的敌人,走向了判教,因而要被消灭。[66]由此,圣战萨拉菲由“效忠与绝罚”思想,引向了不效忠于他们的主张就是叛教。“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的“效忠与绝罚”思想。在《达比克》第7期《灰色地带消亡》一文中,“伊斯兰国”宣称没有灰色地带或中间地带,由此将反对者直接定位为叛教者。[67]实际上,“伊斯兰国”所谓的“判教者”,仅仅是未能“效忠”“伊斯兰国”来“绝罚”“异端”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世界早已是穆斯林与异教徒的战争,保持中立即意味着叛教。
由五个核心概念组成的圣战萨拉菲思想,构成了“伊斯兰国”实施极度残暴行为的理念基础。通过信仰与行为相连,圣战派萨拉菲思想提出了实行“塔克菲尔”的必要性。基于对“真主主权”的理解,圣战派萨拉菲学者将当代伊斯兰统治者以及其他政治力量认定为叛教。“认主独一”的行为化,服务于“塔克菲尔”的判定以及暴力行径。“效忠与绝罚”则为圣战萨拉菲的行动提供了一种简洁的判别标准,倘若穆斯林没能“正确”地“效忠与绝罚”就是叛教。“圣战”地位的抬高,将暴力作为宗教义务以及维护宗教的手段。圣战萨拉菲由五个核心概念形成了一套诊断与行动的体系,为“伊斯兰国”继承。
三“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伊斯兰国化”
“伊斯兰国”继承了圣战萨拉菲思想。就其意识形态与圣战萨拉菲五个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而言,很难说“伊斯兰国”有较大的发展。从对现状诊断的逻辑到行动的方式而言,“伊斯兰国”并没有突破圣战萨拉菲中已有的理解。不过,作为后来居上的恐怖主义势力,“伊斯兰国”在继承既有圣战萨拉菲思想基础上,引入了其他伊斯兰教思想,进一步将圣战萨拉菲思想极端化,打造出现今最为极端的“伊斯兰国”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有学者总结为:“认主独一”,宣扬“圣战”,实行“真正”的伊斯兰教法,以自身领导下的穆斯林团结代替民族主义,强调“天启末日论”以及极端的教派主义主张。[75]其中前三点比较显著地来源于圣战萨拉菲思想。而被认为是“伊斯兰国”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与显著特征的教派主义思想,特别是将什叶派视为叛教者的主张,[76]实际上并没有脱离圣战萨拉菲思想将行为纳入信仰评价与“认主独一”行为化的观点。而在为自身主张做辩护时,“伊斯兰国”选择性地解读《古兰经》、圣训的做法,[77]显然利用了萨拉菲思想在教法方面复兴的“伊智提哈德”,使得本意为使伊斯兰教法能够适应时代变迁所打开的“创制之门”被“伊斯兰国”所利用。除了继承圣战萨拉菲思想,“伊斯兰国”运用其他伊斯兰教思想展现了三大特色:第一,建立“哈里发国”,实现全方位“圣战”,而不仅是“防御性圣战”。第二,更为极端地开展塔克菲尔实践。第三,浓烈的“天启末日论”色彩。
首先,通过扩大“圣战”针对的目标与建立“哈里发国”,“伊斯兰国”走向全方位“圣战”。其一,“伊斯兰国”扩大了“圣战”所针对的目标。恐怖组织为了发动恐怖袭击,需要对自身行为寻求合法化。圣战萨拉菲思想便是恐怖组织寻求恐怖袭击合法化的依托。在“圣战”恐怖袭击合法化的处理上,传统的思想家泰米叶、库特布、法拉杰、马克迪西等人关注的是政权统治者,将未能依据伊斯兰教法统治的统治者通过“塔克菲尔”原则的使用判定为“卡菲尔”,从而合法化对“非法”政权的“圣战”。本·拉登的导师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以及“基地”组织则通过“外敌”的入侵合法化对苏联、美国等国家的“圣战”恐怖袭击行为。尽管“圣战”思想的宣传为“圣战”行为本身以及参与其中的“圣战者”披上了合法外衣,但对于平民的伤害这些思想都不能做到合法化。面对这一问题,“基地”组织将平民与“叛教”政权或“外敌”政权强行判定为合作关系,从而将对政权的“外敌”与“叛教”判定应用平民,认为被袭击的平民与“外敌”或“叛教”政权合作,因而也是“外敌”或“叛教者”,从而合法化对平民的袭击。[78]尽管“基地”组织试图进一步合法化对平民的袭击,但其合法化的核心思想依旧是因政权“非法”或“外敌”攻击而招致“圣战”攻击,平民被视为“非法”政权或“外敌”的一部分。
好教育必须有好的理念,有好的顶层设计;好教育必须要有好的体制机制和有力举措;好教育必须经得起实践检验,要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伊斯兰国”则将“圣战”与暴力对象的扩展推向了极致。在《达比克》第7期《伊斯兰是执剑而非和平的宗教》一文中,“伊斯兰国”称先知穆罕默德降下四把剑,分别是针对以物配主者的剑、针对不信者的剑、针对伪信者与叛教者的剑、针对反叛者的剑,并分别引用《古兰经》文本(9∶5、9∶29、9∶73、49∶9)作为依据。[79]在“伊斯兰国”看来,“圣战”将一直持续进行,直到“异教”与“伪信”的消亡,最终“信仰独归安拉”。同在《达比克》第7期中,“伊斯兰国”撰文《灰色地带消亡》,将与它主张对立的学者、宣教者、教派以及“叛教”的政权和“异教徒”视为敌人。[80]《达比克》第5期发布的《保持与扩张》一文中,“伊斯兰国”更声称“即便所有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偶像崇拜者与无信仰者不屑,‘伊斯兰国’都将会扩展到地球的每个角落”。[81]
除了“非法”的政权、外敌两大传统圣战萨拉菲思想中的“圣战”目标,“伊斯兰国”从个体层面合法化其暴力行径。以对同性恋者为例,“基地”组织将同性恋称为腐化和不道德行为,但没有明确称同性恋者为“卡菲尔”或要求死亡处罚。[82]“伊斯兰国”则主张对同性恋行为者毫无包容,在《达比克》第7期中,“伊斯兰国”歪曲引用圣门弟子的论述,称同性恋为罪行,并应当判处火刑。[83]可见“伊斯兰国”的“圣战”目标是全方位的。从个体层面合法化了对平民的攻击——个体因没有遵循“伊斯兰国”的主张而成为“卡菲尔”,“伊斯兰国”将“圣战”对象扩展到除了自身之外的所有组织与个体。
其二,“伊斯兰国”通过建立“哈里发国”,为开展全方位“圣战”提供“合法性”。在伊斯兰教中,允许发生战争的情况有三种:第一,信士们遭受侵犯。第二,拜主的场所遭到破坏。第三,在真主的援助下,扩展伊斯兰教。[84]但这三种战争不是都需要每个穆斯林参与。在伊斯兰教中,向伊斯兰世界之外扩展伊斯兰是进攻性“圣战”,是一种集体义务,在保证胜利的前提下,不需要每一位穆斯林的参与。而在伊斯兰世界抵御外部攻击的防御性“圣战”,属于个体义务,即每个穆斯林须尽到的义务。[85]“基地”组织通过将犹太人以及美国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侵略者,从而宣称对其开展“圣战”是每位穆斯林的个体义务,[86]以防御性“圣战”作为合法性来源。显然,对于“伊斯兰国”的全面“圣战”而言,仅开展防御性“圣战”是不够的。在伊斯兰教中,除了遭到进攻时“圣战”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体义务,还有两种情况使“圣战”成为穆斯林应尽的个体义务:一种是穆斯林参战,因参战行为使得“圣战”成为“圣战”参与者的个体义务;另一种是领袖要求成年公民出征。[87]通过建立“哈里发国”自称“哈里发”,“伊斯兰国”获得了以“领袖”身份命令穆斯林个体参与“圣战”的“正当性”。而且从伊斯兰教的历史来看,传统哈里发继承制度的实际破坏,以及存在不同的哈里发国家建立方式,使“伊斯兰国”能够利用历史一定程度上“合法化”“哈里发国”的建立。[88]
图6(b)中的悬浮节点形成了不协调的复合网格,它们与其它顶点直接相连则形成图6(c)中的统一三角形网格。当自由度(DOFs)数量为6 784时,从分段插值多边形GBCs有限元法和常规有限元法获得的静电能量分别为9.538×10-11和9.539×10-11J/μm。图6显示了系统能量随着自由度增加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提出的方法在不需要额外处理网格的基础上提高了精度,并稳定地收敛。
其次,“伊斯兰国”的另一特性是对“塔克菲尔”的极端运用,突出表现在其秉持的教派主义观点上。“伊斯兰国”前领袖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认为西方敌人终究会被驱逐,而什叶派则是逊尼派“眼前与危险的敌人”,较之于美国,什叶派的危险与危害性也更大。[89]在《达比克》第13期中,“伊斯兰国”直接宣称什叶派为“卡菲尔”。[90]除了什叶派,在“伊斯兰国”的叙述中,反对者以及不支持者都是叛教者。如在《达比克》第1期《伊玛目的概念》一文中,“伊斯兰国”引用圣训“你们中谁喜悦脱离火狱进入天堂,就让他笃信安拉和末日地归真,就让他对待人们就像他喜悦人们对待他那样。谁向伊玛目宣誓并表示矢志效忠,就让他尽力服从。如果有人出来和伊玛目争权,你们应当砍断他的脖子”,[91]实质上将反对者摆在叛教的地位。同时在《达比克》第7期《灰色地带消亡》一文中,“伊斯兰国”提出没有灰色地带和中间地带的主张,认为不支持它的“伪信者”会“将他们的头埋进沙里,不敢暴露出来……直到大部分阿拉伯人背叛伊斯兰,与叛教者的战争发生时,伪信者蜂拥加入错误的阵营”,[92]进一步将不支持者视为叛教者。“伊斯兰国”无差别地将不支持其主张的人判定为“卡菲尔”的观点被称为“扎卡维教义”。[93]这一判定方式,与萨拉菲纯洁派所继承的艾布·哈尼法思想截然不同。[94]相较“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对于“塔克菲尔”的使用也更为极端。尽管“基地”组织同样使用“塔克菲尔”作为清除异己的手段,但在“塔克菲尔”的裁定与处罚的严厉性方面并不如“伊斯兰国”极端。这是因为“基地”组织始终将团结穆斯林大众视为重要目标,如在写给扎卡维的信中,艾曼·扎瓦赫里(Ayman Zawahiri)反对扎卡维对于什叶派的攻击,要求他团结广大穆斯林,同时告诫扎卡维“大部分穆斯林不能理解甚至不能想象这种行为”。[95]
最后,浓烈的“天启末日”思想,是“伊斯兰国”的醒目特征。末日思想一方面影响着“伊斯兰国”战略的选择,另一方面为其建立“哈里发国”提供思想来源。“伊斯兰国”不遗余力地攻击伊拉克与叙利亚,就深受“天启末日”思想的影响。叙利亚阿勒颇地区是圣训中的“末日决战”之地,“末日来临之前,鲁姆人将驻扎在埃尔玛格(一说是达毕格),[96]当时麦地那的一支大地上最优秀的军队出城阻截……当他们抵达沙姆时,旦札里出世。排好阵列,正准备厮杀,突然有人宣礼,尔撒圣人下降,率领他们礼拜”。[97]这段圣训描写的末日来临前的决战,也正是“伊斯兰国”所说的与“十字军”的决战。受这一段圣训启发,扎卡维首次将美国军队描述为“末日决战”中的罗马人,认为自己代表全部穆斯林在“末日决战”中参战。[98]扎卡维所说的“星火已经在伊拉克点燃,而它会在安拉的允许下旺盛,直至在达比克烧掉十字军异教徒”,[99]已经成为“伊斯兰国”官方杂志《达比克》的引言。而《达比克》以及《罗马》的名称,显然也与这段“末日决战”圣训密切相关。
但在沙特政府开始大规模打击“穆斯林兄弟会”与“觉醒”运动的背景下,纯洁派选择与政府合作。在圣战派的眼中,圣战派是仅存的“诚实”且愿意为伊斯兰教“真理”献身的人。[27]随着伊斯兰世界恐怖主义的兴起,出现了支撑“圣战”运动思想的独立学者之间的松散网络,这些学者对于萨拉菲思想中暴力方面的关注与运用产生了圣战萨拉菲主义。[28]
“伊斯兰国”建立“哈里发国”,也与末日思想紧密相连。被诸多逊尼派圣战者与末日信徒解读为哈里发将会在末日重建的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说:‘只要安拉愿意,先知将会在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他,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只要安拉的愿意,它将存在于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它,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刻薄的君主统治,只要安拉的愿意,它将存在于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它,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残暴的君主统治,只要安拉的愿意,它将存在于你们中间。然后安拉将带走它,如果安拉意愿如此。之后将会出现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语后,先知沉默。”[104]“伊斯兰国”充分利用这一段圣训,在反驳“基地”组织斥责其过于极端时,“伊斯兰国”称“依据经典与先知道路的伊斯兰国度在与你们的敌人战斗,你们要在大地上加强它、荣耀它、援助它、建设它。使它成为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伊斯兰国”宣称建立“哈里发国”之后,叫嚣“在那些屈辱的边界被移除,民族主义的偶像被打破之后,除了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一切都不会留下”。[105]“伊斯兰国”所说的“依从经典与先知道路的伊斯兰国度”和“依从先知道路的哈里发”,显然受到了末日哈里发圣训的启示。通过对伊斯兰经典中关于“天启末日”相关文本的利用,“伊斯兰国”为自身的暴力行径以及“哈里发国”的建立披上了宗教合法的外衣。与此相对,“基地”组织则对“天启末日”观点无动于衷。[106]“末日信仰”的确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关末日的论述更多是使得道德具有绝对性和神圣性,主旨在于劝善戒恶。[107]而“伊斯兰国”则试图构建末日即将来临的图景,赋予建立“哈里发国”的合法性以加强号召力。
“伊斯兰国”在继承圣战萨拉菲思想之余,极端强化了与其他圣战萨拉菲团体的区分,增强了自身的“正统性”,为其进行国际动员能力提供了话语资源和动员工具。“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伊斯兰国化”——用末日思想合法化其全球领导地位,用极端的“塔克菲尔”实践推行全面的圣战暴力,合法化并建立其“领袖”地位,推行极端暴力——使得“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极端程度超出以往的“圣战”组织。“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以及其对恐怖袭击的随意授权,使得全球潜伏着难已评估的恐怖主义威胁。
四“伊斯兰国”极端化的条件以及对“圣战”运动的影响
圣战萨拉菲思想所形成的对现实问题完整的诊断与行动的体系为“伊斯兰国”所继承。萨拉菲思想的教义、教法主张,特别是后者,为“伊斯兰国”所利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其解读宗教文本的权利,以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读。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其他伊斯兰教思想的利用,构成了“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
为防止震动产生噪音污染,尽量选用低噪音设备,设备与基础之间采用弹性连接,将溜槽与设备之间的落差尽量减小,并设置特殊结构或设施(圆弧过度、保留煤堆、橡胶衬里等),以降低噪音。在周围空地种植绿化隔音带,使厂内外噪音都能达到国家有关规定,即厂内小于等于85 dB(A),厂外小于60 dB(A)。随着配套绿化和植被的实施,植被覆盖增加,将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局地小气候,减少风力,提高土壤蓄水保肥能力具有一定的作用,也有利于自然植被的恢复,防止水土流失及土地沙漠化加剧,有利于保护区域生态环境。
数学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生活中,不仅仅是学习和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研究者来说,数学既复杂又有趣,对广大学生们来说,数学是我们从小学起就开始接触的科目.学好数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是培养良好的数学解题思维却对学生学习数学的道路有很大的帮助.
“伊斯兰国”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伊斯兰国化”,是对中东社会变化的把握。进一步展开来看,萨拉菲思想在中东地区的流行,为“伊斯兰国”利用萨拉菲思想提供了大量受众基础。中东动荡的政治环境以及大国的介入,则给予了“伊斯兰国”兴起的政治机会结构。伊拉克较为广泛存在的教派主义、“天启末日”等思想基础则被“伊斯兰国”所利用,吸纳到自身的思想主张中。根据皮尤(Pew)调查中心2012年的调查,教派主义的思想颇有市场,93%的受访伊拉克人(其中逊尼派占42%)认为伊斯兰教是唯一通往天堂的信仰,相应地在接受调查的39个国家中,绝大多数国家穆斯林认为沙里亚法只有一种正确解读。末日思想同样也有广泛支持,98%的伊拉克受访者认为天堂是永久的奖赏,超过半数的受调查穆斯林相信马赫迪将在有生之年来临,72%的伊拉克受访者同样相信这一点。[108]“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对圣战萨拉菲思想进一步“伊斯兰国化”与上述社会环境因素息息相关。
昆明中支强化再贴现在金融机构支小方面的引导作用。明确再贴现工作方向和支持重点(优先办理票面金额5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票据和涉农票据再贴现),引导金融机构从“量、价”两方面着手,充分运用票据融资等工具,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质量和水平。下一步,昆明中支将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完善再贴现管理机制,探索再贴现办理新模式,促进金融机构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将央行再贴现优惠利率政策切实传导至小微企业。
同时,“伊斯兰国”提出极端主张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获取同情群体的支持、与“基地”组织等开展竞争。在支持群体可接受的范围内,极端化的主张可以在次支持群体中赢得更多支持。[109]加之极端化组织的运作,甚至可以创造出利于它生存的社会环境。[110]事实上,“伊斯兰国”也的确通过更极端的暴力,促进了自身的迅速发展。“伊斯兰国”利用穆斯林群体的本体不安全感,通过对圣战萨拉菲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实现了自群体与他群体更清晰的区分,从而为缺乏本体安全的穆斯林提供了更强的群体身份认同,展现了更高的国际动员能力。④
“伊斯兰国”不仅通过极端化获取了更强的动员能力,从其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关注来看,“伊斯兰国”取得了更显著的成功。“伊斯兰国”不仅开创了恐怖组织利用社交网络进行宣传的先河,[111]而且在网络上引发了超越以往恐怖组织的关注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网民对“伊斯兰国”关注甚至远超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尽管在此期间恐怖主义在互联网上引起的关注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峰值。同时,相较“如何加入‘基地’组织、博科圣地或塔利班”,以“如何加入‘伊斯兰国’”为关键词的搜索也创造了纪录。[112]尽管“伊斯兰国”在地面受挫,但它在网络世界中掀起的关注热潮仍未完全冷却,甚至已成为恐怖主义的象征。“伊斯兰国”所激发的全球网民对恐怖主义关注热潮以及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为“独狼”恐怖分子的扩散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与群体身份。[113]自2013~2017年间,在西方国家不断出现的“独狼”恐怖袭击,[114]显示了“伊斯兰国”等“圣战”恐怖组织的影响,其意识形态也可能持续扩散。
但是,“伊斯兰国”组织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以及实践,对于整个圣战萨拉菲激励下的恐怖主义而言并非是一个利好。作为第一个从“基地”组织脱离、并且是第一个对“基地”组织在恐怖主义“事业”中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组织,“伊斯兰国”的极端化使其获益颇丰,[115]但这种受益很难说会促进恐怖主义的发展。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竞争升级”(competitive escalation)指出,群体的竞争将导致竞争各方的极端化。竞争中一方的获益将会导致另一方的反制,因而开启“对抗循环”(protest cycles),使竞争各方走向极端从而导致冲突升级。多纳泰拉·波塔(Donatella della Porta)进一步指出,“竞争升级”将会使宗教恐怖组织陷入派系冲突。[116]与“竞争升级”相类似,“出价更高”(outbidding)机制表明竞争中的恐怖组织为了获取领导力与影响力,展现自身的能力,将会升级暴力行为。[117]史蒂芬·内梅斯(Stephen Nemeth)的研究认为,宗教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更可能发生“出价更高”现象。[118]而无论恐怖组织走向派系冲突,还是“出价更高”实行更极端的暴力,二者都可能使恐怖组织走向灭亡。[119]
“基地”组织高层在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中谨小慎微。哪怕在其分支与“伊斯兰国”发生暴力冲突时,“基地”组织也仅是在口头上对“伊斯兰国”进行批评。尽管双方出现一定程度的“竞争升级”,[120]特别是“努斯拉阵线”与“伊斯兰国”之间,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并没有发动全面的对抗。“伊斯兰国”是否会与“基地”组织联合,其极端化倾向是否会趋于温和,更多取决于“伊斯兰国”未来的发展。“伊斯兰国”所开启的圣战萨拉菲恐怖组织之间明朗化的竞争,对于整个圣战萨拉菲恐怖主义难以说是一种利好。时至今日,尽管“伊斯兰国”不断遭遇打击,但塔利班、“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零零散散爆发的冲突从未停止,一定程度上表明圣战萨拉菲恐怖组织之间的冲突已经形成。“伊斯兰国”意识形态在全球扩散所带来的影响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应对,而这种“圣战”组织间的冲突给圣战萨拉菲带来的影响也值得关注。
[1]“伊斯兰国”最早的组织形态是由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领导的“认主独一与圣战”(Jammat al-Tawhid wal-Jihad),该组织于2004年宣誓向“基地”组织效忠更名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l Qaeda in Iraq),在2006年阿布·艾尤卜·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领导时期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阿布·贝克尔·马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时期经历了两次更名,2013年更名为“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或“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2014年更名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并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家,除非必要,本文在涉及“伊斯兰国”及其前身时,统一使用“伊斯兰国”指代。
[2]参见全球恐怖主义指数,http://economicsandpeace.org/reports。
[3] Julian Robinson, “ISIS Leader Admits Defeat in Iraq and Orders Militants to Flee or Kill themselves in Suicide Attacks,”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4270686/ISIS-leader-Abu-Bakr-al-Baghdadi-admits-DEFEAT-Iraq.html?ito=social-twitter_mailonline.
[4] House Homeland Security Committee Majority Staff Report (2014-2016), “Terror Gone Viral Overview of the 100+ ISIS-Linked Plots against The West,” https://homeland.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6/07/100-ISIS-Linked-Plots-Report-.pdf.
[5]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No. 19, 2015, p. 7.
[6] 萨拉菲思想在学界有着不同中文音译,萨拉菲、赛莱菲、赛莱菲耶在国内均有使用。参见蔡伟良:《赛莱菲耶思潮探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1期,第62-67页;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6-118页;李维建:《当代伊斯兰教赛莱菲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载《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0-174页,C. E. Bosworth, et al.,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8, Leiden: E. J. Brill, 1995, pp. 900-909; Madawi Al-Rasheed, Contesting the Saudi State: Islamic Voices from a New Gen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 Bernard Haykel, “On the Nature of Salafi Thought and Action,” in Roel Meijer, ed., Global Salafism: 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4, 45-47。
[7] Ludwig W. Adamec,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of Islam, Plymouth: The Scarecrow Press, 2009, pp. 77-78; C. E. Bosworth, et al.,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8, Leiden: E. J. Brill, 1995, p. 900.
[8]祁学义译:《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二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9] Robert G. Rabil, Salafism in Lebanon: Form Apoliticism to Transnational Jihadi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2.
[10]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
[11]学者在追溯萨拉菲思想时有不同取向,有学者将其追溯至“圣训派”,如 [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有学者将其追溯至伊斯兰教早期极端教派哈瓦利吉派,如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1-61页。有学者追溯至罕百勒,如Robert G. Rabil, Salafism in Lebanon: From Apoliticism to Transnational Jihadi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蔡伟良:《赛莱菲耶思潮探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1期,第62-67页。
[12]Robert G. Rabil, Salafism in Lebanon: form Apoliticism to Transnational Jihadi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3-25.
[13] [美] 伯纳德·海凯勒:《赛莱菲耶的教义思想:论赛莱菲思想的行为与性质》,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14] 学者们对萨拉菲思想对于“认主独一”的解读基本一致,在其思想的总结上,有着一定差异,参见Robert G. Rabil, Salafism in Lebanon: From Apoliticism to Transnational Jihadi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William McCants, Jarret Brachman and Joseph Felter, “Militant Ideology Atlas: Executive Report,”https://ctc.usma. edu/wp-content/uploads/2012/04/Atlas-ExecutiveReport.pdf;[美] 哈伊姆·马卡尔、刘中民:《圣战萨拉菲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危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5期,第17-31页;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于现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4-91页;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6-118页。
[15] [美] 伯纳德·海凯勒:《赛莱菲耶的教义思想:论赛莱菲思想的行为与性质》,载 [荷兰]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16] 公元10世纪古典伊斯兰教法时期结束,逊尼派教法学家中形成了公议不谬说、创制之门关闭说和遵循传统说,从理论上排除了人为立法和修订法律的权力。面对社会发展需要,伊斯兰教法通过两个途径加以调整:第一,习惯调整,即当人们社会习惯实际上已突破某一法律规定时,则有专职解释法律的穆夫提或大穆夫提就此发表一项“法特瓦”即正式法律见解,给予确认。第二,行政调整,即由封建君主颁布政令,以行政法规和统治者的王权作为沙里亚法的补充。参见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215页。
[17]参见金宜久:《伊斯兰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8]马景:《伊本·罕百里的思想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第60-64页。
[19] Stephane Lacroix, “al-Albani’s R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Hadith,” ISIM Review, No. 21, 2008, pp. 6-7.
[20]比较常见的是依“道路”而区分三派,参见Robert G. Rabil, Salafism in Lebanon: From Apoliticism to Transnational Jihadi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Joas Wagemakers, “A Purist Jihadi-Salafi: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2, 2009, pp. 281-297;包澄章:《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6期,第106-118页。
[21] Joas Wagemakers, “A Purist Jihadi-Salafi: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2, 2009, p. 283.
[22]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17-221.
[23]Jarret M. Brachman, Global Jihadism: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3. “哈瓦利吉”基本含义是“出走者”或“分离者”。哈瓦利吉派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宗教派别。极端主张“真主主权”,暴力对待反对者,“哈瓦利吉”的反对对象甚至包括了五大哈里发之一、什叶派第一代伊玛目的阿里,宣称阿里为“卡菲尔”。哈瓦利吉派被认为通过反对伊斯兰来脱离伊斯兰,为“地狱之狗”。参见金宜久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页;Muḥammad Nāṣir al-Din al-Albāni, “Descriptions of the Khawārij,” http://www.authentic-translations.com/trans-pub/ae_mnaa_2.pdf; 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p. 155-156。
[24] Robert G. Rabil, Salafism in Lebanon: From Apoliticism to Transnational Jihadism,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39.
[25] Jarret M. Brachman, Global Jihadism: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p. 53-56.
[26]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No. 19, 2015, pp. 7-11.
[27] 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25-228.
[28]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No. 19, 2015, p. 9.
[29] Mohammed M. Hafez, Suicide Bombers in Iraq: the Strategy and Ideology of Martyrdom, Washington, D. C.: U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7, pp. 66-70.
[30] “基地”与“伊斯兰国”之间的不同,参见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80-111页;“基地”组织与分支意识形态差异,参见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oration, pp. 7-23,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 RR637.html; Assaf Moghadam, “The Salafi-Jihad as a Religious Ideology,” CTC Sentinel, Vol. 1, No. 3, 2008, https://www.ctc.usma.edu/posts/the-salafi-jihad-as-a-religious-ideology。
[31] [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32]萨拉菲思想并没有统一领导,同样萨拉菲思想圣战派也处于分散状态。参见杨恕、郭旭岗:《圣战派萨拉菲的缘起与现状》,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84-91页;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No. 19, 2015; 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oration, pp. 7-23,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637.html。
[33]这种变化可参考被认为是政治派萨拉菲的“穆斯林兄弟会”在哈桑领导时期的极端化,参见Christine Sixta Rinehart, Volatile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Origins of Terrorism: the Radicalization of Change,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3, pp. 17-48;埃及伊斯兰团的转变,参见[荷兰] 罗伊·梅杰:《劝善戒恶的社会活动原则:埃及伊斯兰团》,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160页。
[34] 圣战萨拉菲的五个核心概念分法可参见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p. 22-27。
[35] 本文所引用沙特阿拉伯王国官方宗教观点,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学术研究和教法解答常务委员会网站。在引用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观点时,出现的《古兰经》、圣训内容,为消除分歧,原引用其网站中文,其网站地址为:http://www.alifta.com。此段参见沙特阿拉伯王国学术研究和教法解答常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alifta.com/Fatawa/FatawaChapters.aspx?languagename =zh-CN&View=Page&PageID=10754&PageNo=1&BookID=3。
[36] 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p.159-160.
[37] 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160.
[38]Nine Rules Concerning Kufr and Takfir, http://www.salafipublications.com/sps/downloads/ pdf/MNJ090006.pdf.
[39] Jamal bin Farihan al-Harithi, “The Khawarij Perform Takfir on Account of Major Sins,” http:// www.salafipublications.com/sps/sp.cfm?subsecID=GSC02&articleID=GSC020002&articlePages=1.
[40] 参见沙特阿拉伯王国学术研究和教法解答常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alifta.com/Fatawa/ FatawaChapters.aspx?languagename=zh-CN&View=Page&PageID=598&PageNo=1&BookID=3。
[41]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13-135页。
[42] Tom Quiggin, “Understanding al-Qaeda’s Ideology for Counter-Narrative Work,”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3, No. 2, 2009, pp. 18-24.
[43] “Irjā’ the Most Dangerous Bid’ah,” Dabiq, No. 8, 2015, pp. 39-56。“伊斯兰国”官方杂志《达比克》(Dabiq)以及《达比克》停发后发行的《罗马》(Rumiyah)均可从https:// clarionproject.org/islamic-state-isis-isil-propaganda-magazine-dabiq-50/获取。
[44] 贾建平:《哈瓦利吉派与伊斯兰教义学》,载《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0-129页。
[45] “Shaikh Abdul-Muhsin al-Ubaykan to Muslims: Fear Allah and Do Not Sympathize with al-Zarqawi and the Takfiri Agenda,” http://www.ibntaymiyyah.com/articles/tsmok-shaikh-abdul-muhsin-al-ubaykan-to-muslims-fear-allah-and-do-not-sympathize-with-al-zarqawi-and-the-takfiri-agenda.cfm.
[46]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法,指《古兰经》中启示,圣训诠释、补充的安拉诫命之总和。沙特阿拉伯官方宗教主张合法与非法是“安拉的《古兰经》、穆圣的《圣训》中确定的两项教法律例”。参见金宜久:《伊斯兰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沙特阿拉伯王国学术研究和教法解答常务委员会网站“关于什么是伊斯兰教中的合法与非法事物”的解答。
[47] “Allaah Does Not Change the Condition of A People Unless…,” http://www.salafipublications. com/sps/downloads/pdf/MNJ110001.pdf.
[48] 除沙特阿拉伯王国学术研究和教法解答常务委员会原引其《古兰经》中文,其余《古兰经》内容源自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9] Ibn Abil-Izz al-Hanafi, “Allaah Empowers Tyrannical, Oppressive Rulers Over the Subjects Due to Their Own Oppression and Corruption,” http://www.manhaj.com/manhaj/articles/aqpld-ibn-abil-izz-al-hanafi-the-oppression-of-a-tyrannical-ruler-results-from-the-oppression-in-the-actions-of- the-subjects.cfm.
[50] Mansoor Jassem Alshamsi, Isla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Saudi Arabia: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Reform, New York: Routledge, pp. 100-101.
[51] John L. Esposito, Unholy War: Terror in the Name of Isl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
[52]金宜久编:《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页。
[53]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40页。
[54] [荷兰] 约阿斯·瓦格马克斯:《激进观念的变化: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的“效忠与拒绝”思想》,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67-68页。
[55] “The Law of Allah or the Laws of Men,” Dabiq, No. 10, 2015, pp. 50-66.
[56] “Irjā’ the Most Dangerous Bid’ah,” Dabiq, No. 8, 2015, pp. 52-56; “The Murtadd Brotherhood,”Dabiq, No. 14, 2016, pp. 28-43.
[57] “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the Sword not Pacifism,” Dabiq, No. 7, 2015, p. 23.
[58] Youssef H. Aboul-Enein, “Ayman Al-Zawahiri: The Ideologue of Modern Islamic Militancy,” https://apps.dtic.mil/docs/citations/ADA446154.
[59] “The Religion of Islam and the Jama’ah of the Muslims,” Rumiyah, No. 1, 2016, pp. 4-9.
[60] “The Rafidah: 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Dabiq, No. 13, 2016, pp. 32-45.
[61] [荷兰] 约阿斯·瓦格马克斯:《激进观念的变化: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的“效忠与拒绝”思想》,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59-60页。
[62] [荷兰] 约阿斯·瓦格马克斯:《激进观念的变化: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的“效忠与拒绝”思想》,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p. 208, 218。
[63] 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 201.
[64] [荷兰] 约阿斯·瓦格马克斯:《激进观念的变化: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的“效忠与拒绝”思想》,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
[65] Joas Wagemakers, “A Purist Jihadi-Salafi: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2, 2009, pp. 288-289.
[66] 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p. 235-246.
[67] “The Extinction of Grayzone,” Dabiq, No. 7, 2015, pp. 54-67.
[68] 张雪峰:《伊斯兰“圣战”——观点比较及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第54-58页;尚劝余:《伊斯兰圣战的理论渊源与实质》,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第9-12页。
[69] 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7页。
[70] 参见尚劝余:《伊斯兰圣战的理论渊源与实质》,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第12页。
[71] 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9页。
[72] Joas Wagemakers, “A Purist Jihadi-Salafi: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2, 2009, p. 293.
[73] Bruce Lawrence, ed., Messages to the world The Statements of Osama Bin Laden, London: Verso, 2005, pp. 14-18.
[74] “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the Sword not Pacifism,” Dabiq, No. 7, 2015, p. 20.
[75]Daniel Byma, “Understanding the Islamic State: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4, 2016, pp. 127-165.
[76] Fawaz A. Gerges, ISIS a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4.
[77] Fawaz A. Gerges, ISIS a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2-34.
[78] “Full Text: Bin Laden’s ‘Letter to America’,” (November 24, 2002),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2/nov/24/theobserver.
[79] “Islam is the Religion of the Sword not Pacifism,” Dabiq, No. 7, 2015, pp. 20-21.
[80] “The Extinction of Grayzone,” Dabiq, No. 7, 2015, p. 55.
[81] “Remaining and Expeanding,” Dabiq, No. 5, 2014, p. 33.
[82] “Lust & Fear,” Inspire, No. 8, 2011, p. 20.
[83] “The Burning of The Murtadd Pilot,” Dabiq, No. 7, 2015, p. 7.
[84] [埃及] 散伊德·萨比格:《伊斯兰教法》,穆斯林青年翻译组译,香港:和平书局有限公司出版2011年版,第818页。
[85] 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页。
[86]Shiraz Maher, Salafi-Jihadism: the History of an Idea, London: King’s College London Department of War Studies, 2015, pp. 102-109;刘中民、郭强:《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从传统理想到现实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92-114页。.
[87] 一般情况下发起圣战的领袖为哈里发或伊玛目,即伊斯兰团体的首领。参见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页;吴云贵:《伊斯兰教法的泛化、极化与工具化》,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第20页。“圣战”成为穆斯林个体义务的情况,参见[埃及] 散伊德·萨比格:《伊斯兰教法》,穆斯林青年翻译组译,香港:和平书局有限公司出版2011年版,第818页。
[88] Hugh Kennedy, Caliphat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pp. 267-276.
[89] 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pp. 13-14.
[90] “The Rafidah : 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Dabiq, No. 13, 2016, pp. 36-43.
[91] “The Concept of Imamah,” Dabiq, No. 1, 2014, p. 28.
[92] “The Extinction of Grayzone,” Dabiq, No. 7, 2015, p. 56.
[93] [以色列] 鲁宾·帕兹:《组织内部的争论:吉哈德——赛莱菲耶关于策略、塔克菲尔、极端主义、自杀式爆炸和启示的意义的争论》,载[荷兰] 罗伊·梅杰主编:《伊斯兰新兴宗教运动——全球赛莱菲耶》,杨桂萍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219页。
[94] 需要注意的是,萨拉菲各派系本身对什叶派的主张并非支持。2007年,沙特阿拉伯前学术研究和教法解答常务委员会成员Abdullah Ibn Jibreen宣称什叶派是叛教者,而非穆斯林,参见“Top Saudi Cleric Declares Shiites To Be Infidels,” http://www.jpost.com/Middle-East/Top-Saudi-cleric-declares-Shiites-to-be-infidels。
[95] “Zawahiri’s Letter to Zarqawi (English Translation),” https://www.ctc.usma.edu/posts/ zawahiris-letter-to-zarqawi-english-translation-2.
[96]埃尔玛格、达毕格(即达比克)都是地名,位于沙姆(Sham),叙利亚阿勒颇附近。鲁姆人即罗马人。
[97] [阿拉伯] 穆斯林·本·哈查吉辑录:《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穆萨·余崇仁译,努尔曼·马贤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98] David Cook, “Iraq as the Focus for Apocalyptic Scenarios,” CTC Sentinel, Vol. 1, No. 11, 2008, https://ctc.usma.edu/posts/iraq-as-the-focus-for-apocalyptic-scenarios.
[99] [阿拉伯] 穆斯林·本·哈查吉辑录:《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穆萨·余崇仁译,努尔曼·马贤校,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740页。
[100] David Cook, “Iraq as the Focus for Apocalyptic Scenarios,” CTC Sentinel, Vol. 1, No. 11, 2008, https://ctc.usma.edu/posts/iraq-as-the-focus-for-apocalyptic-scenarios.
[101]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p. 32.
[102] Al-Hafiz Ibn Katheer Dimashqi, Book of The End: Great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Riyadh: Darussalam Publications, 2006, pp. 50-52.
[103] James Fromson and Steven Simon, “ISIS: The Dubious Paradise of Apocalypse Now,” Survival, Vol. 57, No. 3, 2015, pp. 7-56.
[104] Sayyid Rami al Rifai, “The Syrian Uprising and Signs Of The Hour,” p. 48, https://ghayb. com/wp-content/uploads/2015/09/2nd.Edition-The-Syrian-Uprising-and-Signs-Of-The-Hour.pdf.
[105] Quoted from William McCants, “Islamic State Invokes Prophecy to Justify its Claim to Caliphate,”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4/11/05/islamic-state-invokes-prophecy-to-justify-its-claim-to-caliphate.
[106]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p. 28.
[107] 王广大、曹一俊:《伊斯兰教末世论的思想沿革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6期,第55-61页。
[108]上述数据来自皮尤调查中心2012年调查数据,参见http://www.pewforum.org/datasets/ the-worlds-muslims/。
[109]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Pathways toward Terro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0, No. 3, 2008, pp. 415-533.
[110] 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0-112.
[111] Jytte Klausen, “Tweeting the Jihad: Social Media Networks of Wester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 38, No. 1, 2015, pp. 1-22.
[112] 网络关注度来自谷歌趋势,其网址为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本文共比较两组,时间均从2004年至2017年9月3日。第一组为“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塔利班、恐怖主义,前三个词条类型为“主题”,恐怖主义词条类型为“犯罪组织类型”。第二组为“how to join isis”“how to join al qaeda”“how to join boko haram”“how to join taliban”,词条类型统一为“搜索字词”。
[113] “独狼”恐怖分子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参见Jose Pedro Zuquete, “Men in Black: Dynamics, Violence, and Lone Wolf Potential,”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6, No. 1, 2013, pp. 95-109; “独狼”恐怖分子的行动动力与群体身份的论述参见Sophia Moskalenko and Clark McCauley, “The Psychology of Lone-wolf Terrorism,”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24, No. 2, 2011, pp. 115-126。
[114] “圣战”式“独狼”恐怖袭击2004~2017年在西方国家的变化,参见Teun Van Dongen, “The Fate of the Perpetrator in the Jihadist Modus Operandi: Suicide Attacks and Non-Suicide Attacks in the West, 2004-2017,” icct.nl, January 1, 2004, https://icct.nl/publication/the-fate-of-the-perpetrator-in-the-jihadist-modus-operandi-suicide-attacks-and-non-suicide-attacks-in-the-west-2004-2017。
[115] Tore Refslund Hamming, “The Al Qaeda-Islamic State Rivalry: Competition Yes, but No Competitive Escala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July 2017, pp. 1-6.
[116] Donatella della Porta, “Competitive Escalation During Protest Cycles: Comparing Left-wing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in Lorenzo Bosi, et al., eds., Dynamics of Political Violence, Burlington and Farnham: Ashgate, 2014, pp. 93-114.
[117] Mia Bloom, Dying to Kill: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9-44.
[118] Stephen Nemeth, “The Effect of Competition on Terrorist Group Oper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2, 2014, pp. 336-362.
[119] 有学者提出了恐怖组织消亡的六个机制,并基于此提出了终结“基地”组织的五个要素,而恐怖组织出现派系冲突与走向更加极端都是其中内容。参见Audrey K. Cronin, Ending Terrorism: Lessons for Defeating Al-Qaeda,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8, pp.23-72。
[120] Tore Refslund Hamming, “The Al Qaeda-Islamic State Rivalry: Competition Yes, but No Competitive Escala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July 2017, pp. 6-18.
The “Islamic State” and Salafi Jihadism: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ZHOU Ming and LEI Huanrui
[Abstract]As part of the Salafi Jihadism movement,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lafi jihadism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e religious ideology behind Salafi-jihadism has left the academia’s discussions on this issue fairly inadequate. While inheriting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and the action system of Salafi Jihadism, the “Islamic State” has also absorbed other Islamic thoughts and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ut it hasn’t made any significant the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slamic State”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success in building its international mobilization capabilities and expanding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et. However, its split with Al-Qaeda and its attempts to challenge the latter’s leadership have also demonstrated the existing tensions and conflicts among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e rapid rise of the “Islamic State” may make it an example to be followed by other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giving rise to even more fierce competition among them and thus seriously weakening Salafi jihadism by plunging it into factional struggles and making it increasingly extreme.
[Keywords]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y, Salafi jihadism
[Authors]ZHOU M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ice dean of Institute for Afghanist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EI Huanrui, M. A. Student,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作者简介】 周明,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副主任;雷环瑞,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兰州 邮编:730000)。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4.003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4-0051-25
【修回日期:2019-04-02】
【来稿日期:2018-09-08】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亚萨拉菲与恐怖极端势力的关系及其对新疆安全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号:14CGJ016)与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反恐形势、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5AZD01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号:17VDL003)与2019年度兰州大学人文社科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欧亚秩序与一带一路研究”(项目编号:2019jbkyjd005)及其他类别项目(项目编号:2019jbkytd002、2019jbkyzy029)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三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谢 磊】
标签:“伊斯兰国”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圣战萨拉菲思想论文;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