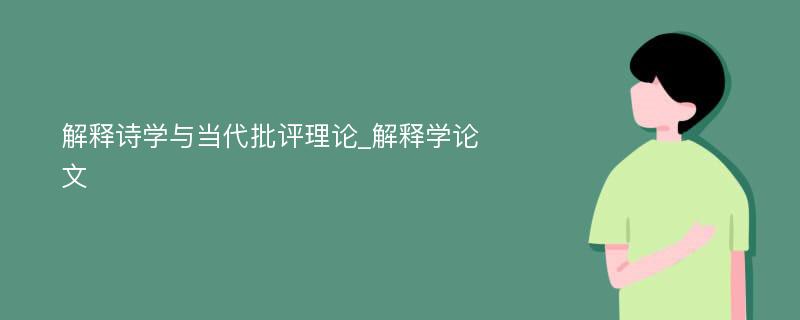
解释学诗学与当代批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诗学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04)04-0001-08
一
在当代人文思想界,解释学(Hermeneutics)的影响无疑不能低估。这门以上帝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命名的学科虽然古已有之,但其正式作为书名出现是在1657年,由一名叫汤恩豪塞尔的学者率先使用。在最初,它的功能既非单纯的传递报道但也无关任何思想内涵方面的解释,而只是属于知识性的寓意翻译。也即以一种明白易懂的方式让芸芸众生借助准确认识《圣经》的意思,来更好地了解来自上帝的那些事关重大的神秘信息。所以,这门以语文学为基础的学科最早主要分为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两大形态,其性质其实是以“文本”为核心、旨在洞幽烛微地掌握其试图说出的东西的“注释学”(exegesis)。也由于其实际操作方式依赖于各种既成规则间的制约与纠缠,所以其学科雏形只是一种“解释文献的技艺学”。用著名学者保罗·利科的话说,解释学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努力想把注释学和古典语言学“提高到一门工艺学或技术学的水准”。但在此,作为其对象的“文本”(text)的概念代表一个能够为最终的正确理解提供更好依据的,一种通常以书面的话语(discourse)形式存在的语言结构的给定物。对于那些手艺高超的解释者而言,主要问题就是:究竟是什么存在于文本之中。施莱尔马赫曾以两句相互关联的话作出精辟的概括:即“解释学是语法的反面”和“语言提供解释学”。无可置疑,解释学的这一发生学背景注定了其归根到底是一种“与‘文本’的解释相关联的理解程序的理论”。而其所承担的任务也就在于努力消除误解,“辨识出说话者将什么样的具有相对单义的信息建立在普通词汇的多义性基础上。解释的首要基本工作是产生由多义性语词组成的某种相对单义的话语,并在接收信息时确认这种单义性的意向。”[1]
按照现今公认的说法,现代解释学是在经历了两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性转折后诞生的。首先由施莱尔马赫通过汇聚客观的语言学解释与主观的心理学解释,而将“局部解释学”发展为“一般解释学”。他强调:“理解只是这两个环节(语法的和心理学的)的相互作用”。因为“解释的需要依赖于写下的话语和讲出的话语之间的差别”,构成解释学把握对象的文本,一方面作为话语样态受到客观的语言规则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它作为“讲话”的凝固最终又是由发话主体的内在精神所决定的。所以施莱尔马赫坚持,虽说理解只有面对语言记录才成为一种达到普遍有性效的阐释,但解释学的基本宗旨却是通过话语/文本实现“对思维的内容的理解”。问题在于这两种解释的有效性无法同时兑现:正如如果更多地考虑共同的语言就只能置作者的特点于不顾,反之亦然,尊重一位作者的个性就是去忘记刚刚过目的语言。只能二中择一的施莱尔马赫,最终将其解释策略定位于“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因为正如狄尔泰所说,对于施莱尔马赫,“解释学程序的最终目的就是比作者理解他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作者”。[2]他以存在着共同人性(精神同质性)的设定来解决其所面对的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而为现代解释学的崛起奠下了一块基石。其次是以狄尔泰为中介,解释学实现了由一门认识方法论向存在本体论的转折。以生命的移入为内涵的“体验”概念的提出以及通过区分“基本理解”与“高级理解”,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作出的定向中而对解释活动作出进一步的定性。他不仅强调了“理解”行为在“解释”活动中的核心作用,而且还明确规定了高级理解是一种“精神生命的整体参与”。在我看来,这事实上已为解释学在日后通过将“理解”不再作为一种“认识方式”而直接作为“存在方式”的转型,来实现由知识理论向实践理论的改变开辟了一条道路。
而由于现代解释学的落成最后取决于同现象学的嫁接,所以在这项工程大功告成时,人们将荣誉归于了海德格尔。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曾明确地表示过: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而现象学描述的方法论上的意义就是解释,因此,“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正如利科所说,在此重要的是意识到解释学同现象学间所具有的“亲近关系”。因为如果说目的在于排除主观偏见把握文本真意的解释学,需要像现象学那样“回到事情本身”;那么同样地,被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里明确界定为重在“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东西那样来看它”的现象学,也需要解释学为它提供客观描述的手段。因为不存在无须释义的自明的事实。著名文化学者格尔兹曾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里引用心理学家赖尔的例子指出,同样是一个眨眼睛的行为,就可能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情形:(1)无意识的作为单纯生理反应的抽动眼皮;(2)有意识地向某个人发出某种约定的信息;(3)出于调笑的动机故意地予以强调的模仿。面对这种情形,那种仅仅起到照相机功能的客观描绘是自欺欺人的说法。为了有效地给出事实,要求我们必须采用一种“深描”的方式,这就是将对象看作—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文本”现象,客观把握首先以借助于真正的想象力的途径深入对象为前提。所谓将对象“文本”化,也就是视其为一种蕴含着特定“意义”的符号现象而非平面实体。这样,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研究手法的“深描”,实质上也就是对现象的文化阐释。所以“一方面,解释学的基础是现象学,另一方面,现象学的构造不能离开‘解释学的先决条件’。”[3](101)解释学通过与现象学的这种联姻意义重大。因为将理解活动看作一种“心理重建”行为的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解释学,不仅只是一种试图与科学研究方法相媲美的人文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客观主义实在论,这种观念将意义视作由作者的思想活动“放入”文本里的一种永恒不变的固定物。
这种虚幻的形而上学立场让理解活动每每陷入一种神秘主义陷阱,无功而返,这也提醒人们,要想真正解决解释学的普遍性问题不能局限于认识论方面,而得由作为对象的意义本身的生成上追究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学自立门户的过程中,一场从“认识自审”的认识论向“意义反思”的本体论的转换也就势在必行。胡塞尔的现象学通过让现象同生命发生关系,而揭开了向这种客观主义挑战的序幕。但由于早期的胡塞尔将这种活动只是定位于感知层面的意向中,最终还是未能从主观的心理方面进入到更为基本的生命实践领域,因而也就未能使这场挑战得以落实。解释学的现象学嫁接的意义就在于:让一度显得无处安置的意义回归到生命实践之中,通过人类生命实践的相互勾通为解释的普遍有效性提供一个人类学的依据。离开了这种由基本的生命实践所构筑的“生活世界”也就无所谓“意义”。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里有一句话: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意义与事件的这种区分意味着意义具有一种“主体间性”,也即它是一种既非纯客观的“物自体”,也非主观的心理意识的内在于生命的现象;以主/客二元论为前提的认识论对于它之所以无能为力,是因为这种意义不是理智“发现”的对象,而是一种生命参与的“生成”物。这种参与行为构成为“解释”,在此过程中,对意义的理解与发生是同步的。渴望回到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追究无疑正体现了这种努力,对于海德格尔,“解释学成为探讨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本体论的思考”。[4]既然理解的目的不再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的某个事实,而是为了领悟事关我们自身的可能性,那么解释活动也就不再属于知识论的认识行为,而是一种生命本身的实践活动。利科认为,只有在由一门“工艺性科学”向“本体论哲学”转型后,“解释学由局部到一般的演变才算真正完成。”因为只有在“解释学不再被定义为对深藏在本文中的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当作由本文所展露的存在世界中的解释”,解释学才能够真正实现其普遍有效性。[3](112)
综上所述,虽说在宏观上解释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三大阶段:即由古代语文学者与宗教人士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权威论(权威是来自传统的未经也无须认定的合法代表),由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天才论(天才是人类的精英分子),由海德格尔开路以伽达默尔与赫施等为代表的当今批判主义实践论;但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得到各路文化枭雄一致赞同的“解释学基本原理”,而只有由一些由各位思想家为代表的各自为政的解释学立场。这些立场的众说纷纭集中体现于关于解释的有效性的认识,但根子却在于对作为解释之源的“意义”性质的理解上。由于归根到底,“如何解释”的问题总是受制于“解释什么”的前提,故而历史上的解释学立场总体而言可划分为两大阵营:认为意义具有一种客观主义的确定性的“作者中心论”,与认为意义是发生于历史过程的产物的“读者中心论”。问题在于迄今存在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薄古厚今的观念。由承认海德格尔为现代解释学的诞生作出的重要贡献,而渐渐滋生起对这位“海大师”的趋之若骛的顶礼膜拜,这种于上世纪末开始在中国文人里如流感似地扩散的现象,如今已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当代学者张志扬先生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路概括为由“前理解”出发经“理解”到“自我理解”为归宿三步曲,是很有见地的。但这里的贡献与局限都显而易见。因为尽管如同利科所说,“正是在自我中我们才有机会发现存在”,[5]自我理解是通过生命实践进入普遍“存在”的华山一条路,但关于生命的领悟毕竟不能以自我领悟为边界。海德格尔无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在后期思想里几乎“完全抛弃了解释学的概念”,而试图借助于语言分析的力量从犹如黑夜般的“存在的包围”中突围。但结果显然未能如愿。伊格尔顿在《文学原理引论》里曾写道:这位“德国黑森林哲学家”虽然有着“意味深长的洞察力”,最终却“令人吃惊地拜倒在存在的神秘性面前”。话虽说得不太恭敬,但意思差不到那去。
二
诚然,透过海德格尔哲学的这番遭遇人们确实可以意识到一种关于解释学的危机,即解释学所要解释的归根到底是不可解释的东西。与著名的“解释学循环”相比,哲学解释学的这个“说不可说”的困扰无疑更为麻烦。事实上这同样也是自觉追随海德格尔的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的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尽管他对其老师的困境有所意识,并以“人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那些终极的问题的不断发出询问,而且还是此时此地何为可行、何为可能、何为正确的感觉”的见解,对海德格尔思想作出了间接批评;但他试图以对“历史现实”的理性辨析取代对“神秘自然”的诗化思考的努力,同样也未能功德圆满。比如无论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他们对“存在意义”的解释学探询的实质,是关于“真理”的思考。用海德格尔在其《路标》一书里的话说:“‘存在的意义’和‘存在的真理’是一回事。”但正像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所指出的,在伽达默尔那部以“真理”为主题的代表作中,令人奇怪的是真理问题并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占据主导地位,而只是在全书结尾部分才有关于它的简短讨论。虽说在书里伽达默尔一直在试图表明,有某种真理隐藏于我们的经验过程之中,但他的这些思考最后仍是在诸如“任何解释学理解都始于事情本身,终于事情本身”[6]这样一种高深莫测的陈述里销声匿迹。除此之外,“解释学危机”也表现于一直作为其根据地的文艺研究方面。伊格尔顿早已指出,解释学的文学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渊源于圣经阐释的传统决定了它侧重于过去的作品,因而“这种批评理论的主要功用是阐释经典作品”,对于那些当代、即时、未有定论的作品无所适从。再是由于强调文本的整体性,使得“解释学一般不考虑文学作品冗长、不完整和自相矛盾的可能性”。[7]这些批评无可置疑,但尽管如此,我要说的是,这只意味着信奉“语言中心主义”的、作为一种本体论思考的解释学哲学的有限性,并不妨碍它以“解释学诗学”的身份为当代批评理论事业作出贡献。
如上所述,解释学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澄清的艺术。如果说“凡在人们所说的东西不能直接被我们理解之处解释学就起作用”,那么我们不仅得像伽达默尔所肯定的那样承认“艺术是解释学的对象”与“解释学包括了美学”,[8](124)而且还应意识到解释学事实上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基础。伽达默尔将解释学视为一切哲学之本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将之作为文学批评的哲学无疑恰如其分。在整个文化事业里人文艺术无疑是解释学最能施展的舞台,首先是因为艺术活动是解释学的目标所向——“意义”的根据地。无论批评家们如今如何界定艺术,有一点无可置疑:艺术总是与意义同舟共济,“艺术有助于使‘意义’问题出场,有助于激发对‘意义’问题的追问,有助于面对‘意义’问题。”[9]这是艺术文化的人文意义之所在,也是其必须与解释学荣辱与共的原因。其次是文学艺术的“陌生化原则”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创造性的永无止境的渴望。狄尔泰认为,“如果生活表现完全是陌生的,解释就不可能。如果这类表现中没有任何陌生的东西,解释就无必要。解释正在于这互相对立的两极之间。”[10]这种情形的最佳体现莫过于艺术文化,在这里,艺术活动依照艺术传统作出的标新立异是第一原则。所以,俄国人什克洛夫斯基从其对托尔斯泰的研究中发现的“审美陌生说”尽管迄今已是思想博物馆里的收藏品,但其生命力犹在。在当年的是是非非均烟消云散后人们更加确认,“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才存在所谓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需要“陌生化”处理。所谓的“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11](10)但有必要补充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在让人耳目一新的创新与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间的张力。事实上不仅在主观方面,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彻底无视陈规进行创作,而且从客观上讲也正如豪塞尔所说,一件艺术品要是完全由独特、严密的元素所构成,那它将是不可理解的。“独创性的体验只有在已经安放好的习规的轨道上才会传播”。[12]
此外,文学批评同解释学的同盟关系也在于艺术文本在表现方面,确实存在着一种被“新批评派”以“诡论”一词来强调的特点。用克林斯·布鲁克斯的话说:“诡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诡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求表达的真理只能用诡论语言。诡论出自诗人语言的本质。”[13]诚然,布鲁克斯此话的本意是指依赖比喻与象征来惨淡经营的诗歌文本,但就“诡论”这个概念的“暗示”意义而言,它无疑是一切以“艺术”的名义出现、有着“说不可说”的表达障碍的诗性话语的共同特质。虽说关于艺术的这一特点早已成陈词滥调,但这个话题之所以被一再提起,就在于问题其实一直并未被完全澄清。著名学者汉斯·昆在其《艺术与意义问题》一书里提出,艺术话语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语义指向的无着落。在他看来,每一位伟大的画家都以他自己的方式超越了可见的东西。这种东西并非真实的事件而是真实的经验,经验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虽能够意会却无法言传,以至于什克洛夫斯基以“书(作品)比爱情更神秘莫测”来形容。象征之路之所以能成为诗性朝圣的一条坦途,是由于象征已不只是一种认识方式,同时也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因为它并不“转达”意义而是“显现”意义;它的具象性和与其所意向的事物的亲和性,使它能够拥有一种让接受者“参与其中”的功能。事情正是这样:“我们在对象征的体验中,实际经验了人的存在的两个层次:即可以说的层次和不可说的层次。对象征的体验使我们获得对不可说的真实的体验。因为正是在象征之中并且通过象征,在我们之间实际产生了对语言界限彼岸的理解。”[14]在艺术活动中,通过文本的普遍象征化而表现出来的这种表达的“诡论性”,归根到底来自于艺术的这种试图通过语言行为来对超语言意蕴作出理解的悖论。由于这种既寄生于话语之中又超越语言的诗性意蕴构成了一切艺术文本的基本精神,所以有“伟大的小说家就是诗人”,以及“诗是一种精神的自由创造,它超越一切艺术又渗入一切艺术之中”这样的说法。[15]
以此而言,离开了对解释学诗学的应用来谈当代批评理论建设是难以想像的,用赫施的话说,“解释是一切正确批评的基础”。[16](179)但反过来显然也可以认为,由于艺术现象较一般文本具有更多的维度因而也更为复杂,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能够说,能否接受来自文学艺术批评的考验关系到解释学的学科价值。因为总体而言,作为一种思想工作的解释活动如同利科在《存在与解释学》一文里所说,主要是“于明显的意义里解读隐蔽的意义”,也即“在于展开暗含在文字意义中的意义层次”。但在一般文本里,这个意义层次主要聚焦于词义—句法层面。比如美国学者却尔曾引用的几个例子:A.他们是访问教授(They are visiting professors)。B.他用枪打死了那个人(He killed the man with the gun)。C.我喜欢我的秘书胜过我夫人(I like my secretary better than my wife)。前两句能分别产生以下歧义:A.他们正在访问各位教授。B.他杀死了那个带枪的人。而第三句既可以被理解成“我喜欢我的秘书胜过喜欢我夫人”,也能够被理解作“我比我夫人更喜欢我的秘书”。[17]不难发现,前两句话的歧义很容易通过上下文关系而“自动”消除,因为它们的歧义主要在于句子本身的表达方面。第三句话的含混虽也能借助于相应的语境得到澄清,但要来得复杂,因为它除了句子层面的含混外还存在着来自讲话者的意思的错综性。比如与前两个句子不同的是,最后得到确认的意思并未能取消前面的不被认可的那个意思,它只是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覆盖”。因为在前后两个不同的意思里仍有着一个共同点:无论“我”是否讨厌自己的夫人,其对这位“秘书”的喜欢是肯定的。这就增生出第三层意思:“我”的这种“喜欢”别有内涵,这种色彩尤其是在“我”对别人的“误解”作出纠正时更容易得到强调。无须赘言,相比起来第三类的含混较之于前两例更多地出现于文学作品,《红楼梦》里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许多对话就是典范。所以,并非是无法确认的“语义含混”,而是丰富多采且难以捕捉的“言外意”与“话外音”才是真正诗性话语的特点,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意趣的基础。
三
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是:什么是解释学诗学所要面对的问题?狄尔泰在《解释学的起源》里将之归为“解释学循环”,也即“一部作品的整体应由个别的语词及其组合来理解,可是对个别部分的完全理解却又以对整体的理解为前提。”众所周知,在海德格尔“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摆脱这一循环,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一循环”这一见解上,伽达默尔在《论理解的循环》一文里借花献佛地予以了最后解决:“解释由前概念开始,并被更合适的概念所取代。”这种不断的结构/建构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运动”。诚然,在艺术中存在着因文体差异所造成的解释形态的区分。比如一般说来,人们对诗歌的解释呈现出一种膨胀性,即“总是在各种不同的方向上扩大诗歌文本的语义,而我们对小说所作的解释则不仅具有简化性而且具有高度的选择性”。[18]但这种差异并无实质性意义,废名当年“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的名言,道出了真正的小说文本的艺术追求。不言而喻,有一个问题聚讼已久,这就是意义的归属。曾几何时,伽达默尔与赫施为此展开过一场激烈的学术交锋。赫施说得对,在解释学诗学中,对正确性的验收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难题。但这位自称“试图在胡塞尔的认识论和索绪尔的语言学中为狄尔泰的某些解释原理寻找依据”的学者,为了追求批评的客观性而将“推测作者原意是什么”作为“解释的基本问题”,[16](235)这确实授人以口实。豪塞尔的批评不无道理:“假如对作品的解释仅仅是为了指出作者的创造意图那将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意图不那么容易被找到,有时连作者本人也不知自己的意图是什么。”[19]虽然这种做法由来以久。所谓“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余悲,悄乎有余思也。”但经验表明却是在一意孤行难定是非。
有记载言,尽管同为大诗人的欧阳修与梅圣俞亲如兄弟,但欧阳修却曾表示:“昔梅圣俞作诗,独以吾为知音,吾亦自谓举世之人知梅诗者莫吾若也。吾尝问渠最得意处,渠诵数句,皆非吾赏者,以此知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20]在此意义上,强调“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伽达默尔似乎占有先手。但他以“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为理由来取消“更好的理解”的做法,却无可置疑地有为批评的相对主义网开一面的危险。因为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并非关于经典的锦上添花的解读,而是在优与劣之中作出区别。这就需要对批评对象作一番追究,合适的理解应该得到来自作品的赞助。事实上期待着一种“交流”的文本总是在向我们“说话”,因而真正的文学批评决非借文本来进行批评主体的内心独白,而是与之进行“对话”,所以批评首先意味着认真的“倾听”。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无疑对此作了及时的强调,问题是倾听什么与怎样倾听。伽达默尔的问题在于将一切归于语言,因为在他看来,理解是与存在共在的,而“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8](104)所以有人妥贴地指出,对于伽达默尔,“‘视界’一词是用以描述释义的情境特征或受语境束缚之特征的”。[21]但在我看来,解释学诗学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如何对诗性文本作出一种“超语境”的审美把握。而在此过程中,赫施的这一提醒具有意义:批评家在其批评实践中不能一味地放任那些片面乃至歪曲的“前理解”,而应该经常对“影响他作出判断的前提和前判断”保持一种警惕。但他分别以“意义”(meaning)与“意味”(significance),来区分由作者提供的文本意思与由读者从中生成的意思,虽然能给人以启迪却与事无补。因为从根本上讲,解释学诗学的挑战并不局限于关于的意义的“层面”上的扩张,还在于“维度”的增生。
语言学家弗里斯曾提出:“‘意义’并不是在言语形式的本身,而是由言语形成的三类关系组成:(1)一类言语形式和另一类言语形式的关系;(2)言语形式和非言语形式的环境(物体、事件)等的关系;(3)言语形式和参与交际行为中的人的关系。”[22]但这三类关系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得到充分显现。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尽管作为信息活动的语言本质上是一个听觉系统,但只有在成为一种书面话语时才能真正进入解释学视野,因为只有在书面作品中,人们方可以在一个本身可理解而无需诉诸他人主观性的有意义的维度内活动。解释学所面对的这一问题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对文学文本而言,其特点正在于对平面一维的书面语义系统的超越。这首先体现于对话语音响效果的强调。虽说人们也都清楚,作为一种声音现实的词与话语不仅总是不可分解地与意义的传达结合在一起,而且在一定情形下发音本身就能“创造出客观东西的灵魂的情调”。但事实上如同著名学者英伽登所指出的,“在一般情况下,语词声音只是理解语词和句子的意思的一个飞快的过渡”。[23]只有在文学作品里,这一事实才真正受到关注。伽达默尔说得好:词在普通的话语中与在文学中的作用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一个文学文本要求以其语言的面目出现,不仅是为了执行其传达一个信息的功能。它不仅必须被读,它也必须被听,哪怕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用我们内在的耳朵来听。”[24]什克洛夫斯基说过:“诗行玩味意义,诗行反复咀嚼声音,欣赏这些声音的美味。”[11](311)我国古人当年曾结合汉语的“四声”特点,以“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的说法,同样也对语音的艺术表现力进行了一番总结。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对此心领神会。
声音与词义的交织能够造势成型绘声绘色,但这不仅仅是增加了一种表意渠道,而且意味着文学话语通过感觉化而成为一种生命的表现。老舍曾指出过,“《水浒》中武松大闹鸳鸯楼那一场,都用很强烈的短句,使人感到那种英雄气概与敏捷的动作。”[25]这里不仅有视听场景还有只能以“内在耳朵”来倾听的一种人生意味。那些被认为有着“朦胧效果”因而需要以侦探般的姿态进行阅读的文本,其实并非真正的文学杰作。比如为一些批评家津津乐道的亨利·詹姆斯的《拧紧螺丝》。无论对于其中充当叙述者的那位家庭女教师的受着幻觉折磨的讲述我们能否相信,这部小说充其量只是一部具有写作教学示范意义的特色之作。这意味着面对文学文本,解释学的问题既不是“解说”(explanation)与“解释”(explication)间的纠缠,也并非即使“不懂”也能“理解”的困扰,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的“拒绝解释”现象。梁启超在当年读了李商隐的《锦瑟》与《碧城》表示:“这些诗,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到一种新鲜的愉快。”作家王蒙也曾道:“少年时代,初读《锦瑟》便蓦然心动,恬然自赏,觉得诗写得那么忧伤,那么婉转,那么雅美。虽不能解,却能吟赏,并给背诵上口。”但他在“诗仍然是需要解释可以解释的”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凭藉自己的文学修养展开了解释。他从第一层“诗的字面上的意思”入手,分别就第二层的“背景与写作动机”、第三层的“诗的内蕴与意蕴”、第四层的欣赏者“个人体会与发挥”、第五层关于此诗的“学问研究”等,作出了全面的阐释。[26]不能说这些分析不到位,它们无疑极大地有助于人们对这首名诗的欣赏。问题是除了第四层外其余多为关于此诗的知识性的说明与文化方面的解释;而第四层的分析虽说十分精彩,但不仅这些作为阐释者个人心得的东西代替不了别人的重读,而且即使这些言说本身似乎也在其成文后失去了一种最可贵的意味。
所以一位美国当代诗人说道:“虽然诗可以像钟表拆成零件,可是当你把他们再拼装起来,它们仍然是无法解释的。它们发出它们的‘黑色声音’,这就是一切伟大的诗所必有的共鸣,一种高深莫测的心灵神秘,我们只能以敬爱之心来接近它。”[27]这也说是锡德尼在《为诗辩护》里曾表示的,如果“意义”是指用语词直接表达的东西,那么诗人无所“说”。显然,艺术文化中的“说不可说”不仅仅针对艺术的生产与创作,同样也适合于艺术的消费与批评。但凡此种种并不意味着解释学诗学在文学批评中无所作为,而只是表明它必须“戴着镣铐跳舞”,对作为话语现象的文学文本作出“超语境”的理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学会了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而上帝却在什么地方发笑,因为它搞不懂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存在也是语言的家园”。这不仅仅是因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已揭示出,“实践”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表明,“作用着的思想有非语言的根源”;[28]同样也在于古往今来的审美艺术实践一直向我们显示着这个道理。什克洛夫斯基说得好:在文学艺术中词语不是让人说的,它们是被经历也就是被感受的。而为了能感觉到词语,人首先得感觉到不可感觉的东西。所以归根到底一言以蔽之:“理解艺术的途径即是认识生活。”[11](140)在这里只需要批评的实践而不需要任何理论,那怕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因为“关于实践的理论仍然是理论而不是实践”。[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