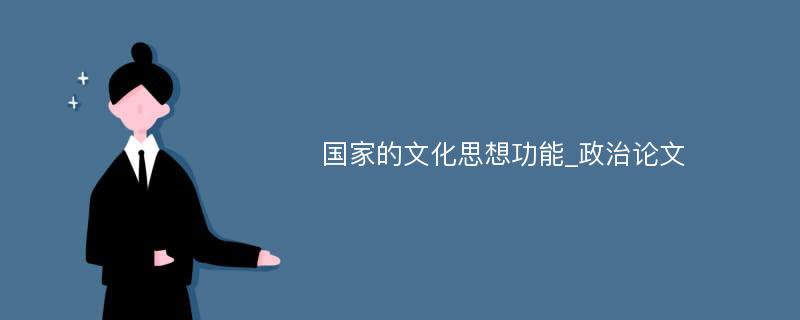
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职能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是指,国家运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与影响人民的价值观念,以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自愿地服从国家的控制和管理。这种职能以意识形态的合法化为基础。对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职能的高度重视是20世纪西方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主要是指,国家运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与影响人民的价值观念,以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从而自愿地服从国家的控制和管理。一般认为,这种职能是与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密不可分的,有些学者甚至直截了当地将它称为“合法化职能”。应该承认,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无疑是合法化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合法化职能已远不再只是韦伯提出的关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①的价值判断问题,它已经扩大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国家为其政治统治赢得大众广泛支持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康纳就将国家花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称为合法化的一部分;美国政治学家费斯克更是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合法化职能,认为这种职能包括:经济上支持大众的消费需求,政治上把各种反抗纳入主流政党之中,文化上建立公共教育制度②。对于这种扩大了的合法化职能我们将在另文进一步讨论,在本文中,我们只讨论国家运用文化意识形态手段争取合法性的各种活动
一
对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职能的认识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意大利思想家莫斯卡在其出版于1896年的《政治学基础》(英文本译名《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曾指出,统治阶级“并非只靠实际占有权力来证明权力的正当性,它还试图为权力找到道德和法律的基础”③。在这方面,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和借助各种政治信条和主张,莫斯卡称它们为“政治公式”。这种政治公式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它使人们感到政治统治不是来自纯粹的物质力量,而是有着道德原则上的依据。1925年,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表达了近乎同样的思想,他认为,在政治中,暴力和同意是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互相依赖,不可分离④。
本世纪初,韦伯对国家统治形式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了“合法性”(Legitimacy)的概念⑤,这一概念对20世纪的国家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伯认为,在任何一种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统治形式中,都包含有最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在政治统治中,这种自愿服从一般出于理想和信仰。韦伯指出,暴力统治可以通过信仰体系获得合法性。这种信仰体系就是说服人们服从统治的理论思想体系,它为统治的合法化提供理论依据。在韦伯看来,任何现存的统治系统都具有合法性根据,不合法的统治系统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被统治者不相信某一统治系统的合法性,那么这个系统必然是不稳固的因而是注定要崩溃的。韦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经验性考察发现,统治者一般根据三种理由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被统治者也同样基于这三种理由来接受他们的统治。这就是传统、非凡的个人品质和法律性,它们构成了人类合法性统治的三种基本形式。
自韦伯以来,合法性这一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普遍承认,它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一个关键术语。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合法性中体现着一种价值判断。法国学者雷蒙·博兰(Raymond Polin)指出:“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众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的。”⑥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S.M.Lipset)也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政治制度要形成并维持这样一种信念:现存的制度最适合于这个社会。“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根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与他们的如何相吻合。”⑦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由于这种价值因素的存在,合法性所包含的意义才远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它还具有某种正统性色彩⑧。正是这种具有正统价值观念的合法性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持久的、最终的来源。
国家力图通过合法性使人们相信,国家的统治之所以受到普遍的认可,不仅是因为人们出于对暴力惩罚和强制的恐惧,而且还由于国家具有公正和恰当的道德信念。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默顿·弗里德(Morton Fried)所说:“合法性的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国家存在的理由并且证明国家的存在;此外,它还证明特定的社会秩序和等级以及维持这些秩序和等级的手段。”⑨合法性这一功能是通过意识形态实现的,“正是通过合法性这一概念,意识形态才与政治得以结合”⑩。换言之,合法性就是要使政治权力在意识形态上获得合理性。
对于意识形态在维护国家统治中的作用,现代西方学者给予了颇多的注意。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领袖都要维护和弘扬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以便说明和论证国家统治的合法性。这是因为,政治权力一旦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就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这种政治权威不仅比赤裸裸的强制可靠和持久,而且还能使统治者用最少的政治资源进行控制。一句话,“与用强制手段相比,用权威手段进行统治要经济得多”(11)。达尔还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和特征做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应该提出道德的、宗教的事实和各种假设,以此来证明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它通常包含评价组织机构、政策和领袖的各种标准、关于政治体系运作的理想化描述以及缩小现实与理想目标间差距的纲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不能由统治者按照自己的心愿随意创造和操纵的,它必须对经验和事实具有一定解释力,而且一旦政治意识形态在政治体系中得到了广泛接受,统治者也必须服从它,否则就会冒破坏自己合法性的风险。达尔指出,政治的意识形态并非是统一的和一贯的,它会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含糊性是它的一大特点,因为正是含糊性才使得灵活和变化成为可能。此外,人们对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也是互有差异的,有些人甚至会坚持与其对立和冲突的意识形态;受到全体社会成员一致赞同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
西方学者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和集团的各种利益和要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政治体系迫切需要一致的舆论和关于正义的共识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基本价值取向,政治制度就会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指出,任何社会归根结底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也就是赋予它以合法性;它必须证明自由和强制的兼而并用对于推行和实施它的分配原则来说是必要的和天经地义的。因此,为了维护政治体系自身的生存,必须创立一种阐述明确的、可以调和个人之间摩擦的大众哲学。贝尔为这种具有规范性的政治哲学规定了两项任务:(1)规定共同的利益;(2)满足个人和群体各自提出的权益和要求(12)。
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了颇为独特的解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人们通过它了解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建立起一种指导行为的世界观,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使执行过程费用减少(13)。意识形态这种节约功能是由它的基本内容所决定的。在诺思看来,所有统治的意识形态都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它旨在说服人们相信现存的规则是与正义共存的。因为,对现存体制合理性的认同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诺思强调指出:“至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都必须克服搭便车(freeride)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14)而只有当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他们才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搭便车行为,才会自觉地遵守规则和秩序──即便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要求他们去违反,维护秩序的执行费用因此也就会大量减少。当意识形态无法使人们相信制度的合理性时,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大量出现,博奕规则的执行费用也将大量上升。一旦执行费用超出了制度所带来的收益时,制度的变迁、国家的兴衰就会随之出现。
二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非常重视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化职能,他们对这一职能的研究是从对本世纪20年代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遭受的一连串失败的思考开始的。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当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国家不仅通过暴力手段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还特别地加强了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操纵,使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接受资本家的统治。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国家的文化职能的最初探索无疑是来自葛兰西。葛兰西继承了意大利的政治思想传统,以强制和同意两分法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他认为,“一个社会集团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它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统治者’和作为‘文化和道德的领导者’。”(15)前者实施暴力强制职能,后者则执行道德教育职能。在葛兰西看来,完整的国家应该包括这两种职能,简而言之,应该是用镇压之盾强化了的领导权。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和,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知识的领导权是由强制力量来保护的,而强制力量也靠领导权来取得合法性。葛兰西得出结论:“国家是一种完全交杂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统治阶级不仅借此证明自己的统治合理合法以便维持这一统治,而且要设法使那些受统治的人积极地同意它的统治。”(16)
葛兰西指出,尽管暴力和同意是以一种有机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并且在彼此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说,当代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用同意的方式维持其统治。葛兰西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道德国家,它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通过教育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职能是通过市民社会执行的道德和知识领导来实现的,它体现在全部教育、宗教、社会团体的各种工作之中。当代资产阶级国家利用这种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通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和日常生活等各种市民社会渠道,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认可现存的社会秩序,自觉地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的理论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职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17)。例如,在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中,意识形态就占有重要地位。阿尔都塞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对意识形态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意识形态对社会再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为了继续存在,就必须再生产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同时还要求将劳动者对现存秩序规范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也就是将劳动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顺从态度再生产出来”(18)。阿尔都塞指出,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不仅向劳动者传授谋生技能,还要保证他们对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服从。这种教育制度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相比。这种国家机器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包括这样一些组成部分:宗教(各种教会体系)、教育(各种公私立学校体系)、家庭、法律、政治(包括不同政党在内的政治体系)、工会、传播机构(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文化(文学、艺术和体育)。这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发挥功能,而后者则更多地使用暴力。但阿尔都塞强调指出,任何一种国家机器,无论是镇压性的还是意识形态的,都是以暴力和意识形态两种方式来发挥功能的,其区别仅表现在程度的不同。例如,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军队和警察为了确保内部团结而向外宣传的价值观念,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在最后的关头总是要辅以镇压性手段,如学校和教会使用的惩罚和开除等方法。
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由于其组织成分的复杂和不同而具有多样性和相对独立性,由于统治阶级不可能象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那样轻易地为意识形态制定法律,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常常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无论在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无论它们的作用方式有多大差别,所有的意识形态最终都要统一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致力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都以最适合于它的方式行事。政治机器宣扬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器灌输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机器教育人们仁慈忍让。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教育机器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将意识形态包裹在谋生技能中长时间、大量地、有系统地传授给人们。
米利本德对阿尔都塞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主要是通过一些不属于国家系统的市民社会机构进行的。把教育、宗教和文化机构统统称为“国家意识形态机构”,会导致对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混淆。米利本德指出,教会、学校和家庭等机构是统治阶级维持自身统治的代理机构,在这些机构中发挥作用的是阶级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正由于此,这些机构并非总是铁板一块,它们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舞台。统治阶级并非象在国家机构中那样完全占领这些市民社会机构,除非是在一些极权主义国家。
但米利本德也意识到,现代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干预在逐步扩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接管了过去由统治阶级行使的那部分思想文化职能,它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使现存秩序合法化的活动。米利本德指出,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国家有可能大规模介入意识形态行业,以便更加直接地干预人们意识观念的形成,影响“公众舆论”的导向。国家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传播企业传播消息、观点、主张和见解,并且对这些东西的传播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国家尽其所能地阻止那种它认为是“无用”的观点和消息的传播。
米利本德指出,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在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采取的形式之间也有很大差别。首先,在极权国家中,不同的意见和敌对思想在所有领域都受到暴力的压制,而在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则要少得多;其次,极权国家本身承担着传播官方所认可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它不加掩饰地宣传自己的思想观念,压制不同的思想。
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阿尔都塞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对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治统治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1980年,德国政治学家格兰·特尔博恩(Go-ran Therborn)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政权》,该书对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做了更加细致的研究和论述。
特尔博恩把意识形态的建构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这就是:(1)确认现实的意识形态,它告诉人们“什么东西是存在着的”;(2)表明应当的意识形态,它告诉人们“什么东西是美好的”;(3)指出可能性的意识形态,它告诉人们“什么是可能的”。这三种模式构成了意识形态从属和限制的基本结构,在被统治者用来维护既定秩序的稳定方面,它们形成了一条重要的逻辑链条:第一,确认现存制度具有哪些东西和不具有哪些东西,比如说,存在着富裕、平等和自由,而没有贫穷、剥削和压迫;其次,假如这条路行不通并且被迫承认现实中存在着贫穷等消极现象,那么也可以说,存在的就是正当的,因为穷人的不幸是咎由自取,没有人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它与制度的公正无关;第三,即使最终不得不承认存在着不公正,也还可以说,只能接受它,因为不可能有更为公正的制度了,或者至少目前不会有(19)。
特尔博恩指出,过去学者们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权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疏忽和缺陷。自由主义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通常只关注第二种建构方式,即只注意美好社会的概念和政权形式,而忽略掉对现实的认识以及希望和恐惧的形成问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意识的研究偏重于前两种意识形态建构方式,缺乏对于可能性的认识。事实上,无论是被统治阶级还是统治阶级,在现实中都无法摆脱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于前者来说,它们体现在履行生产剩余劳动的工作、指出阶级统治的不公正、寻找变革的可能性;而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进行剥削活动、为剥削辩护、捍卫剥削制度。
特尔博恩认为,意识形态的统治方式是非常复杂的,从上述三种模式出发,可以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意识形态统治概括为六种类型。这六种服从类型是:适应(ac-commodation)、必然意识(sense of ineuitability)、代表意识(sense of represen-tatiow)、依从(deference)、恐惧(fear)、屈从(resignation)。事实上,这种类型划分只是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现实经验中,这六种方式时常是错综复杂地绞在一起,共同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统治。
应该指出,对文化意识形态作用的强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著名论题:“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今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试图弥补它的不足。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并不是绝对的,完全占据着优势的,在这一领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更加精巧、复杂,它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体育、流行音乐这一类大众文化之中。这些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避免用简单的决定论的方式看待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
总而言之,如前所述,对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职能的高度重视是20世纪西方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治统治中的作用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者所注意,也引起了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极大兴趣,他们都把合法性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发展了自己的国家理论。
注释:
①韦伯:《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13页。
②奥康纳(J.O'Conor):《国家的财政危机》(The Fiscal Crisis ofthe State),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3年版,导言;费斯克(M.Fisk):《国家与正义》(State and Justice),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PVII页。
③莫斯卡:《政治学基础》(Ruling Class),伦敦1936年版,第70-71页。
④克罗齐(Benedetto Croee):《政治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s),伦敦1952年英文版。
⑤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概念的历史更为悠久,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罗马和中世纪时代。
⑥博兰:《合法化思想观念的哲学分析》,《政治哲学年鉴》,巴黎1967年版;转引自雷斯尼克前引文。
⑦李普塞特:《政治人》(Political Man),纽约花园城,双日锚出版社1960年版,第77页。
⑧在英语中,Legitimacy一词既有合法性又有正统性含义,而Legality则仅指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学者们还为这两者的差异找到了实际的例证:魏玛共和国就只具备法律上的合法性而没有正统的合法性,而戴高乐在伦敦领导的法国战时抵抗力量则只具备正统的合法性而没有法律的合法性。一般说来,前者的寿命要短得多。
⑨⑩弗里德:《国家的概念》,《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15卷。
(11)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7-79页。
(12)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8-309、315页。
(13)(14)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3、59页
(15)葛兰西:《政治著作选(1921-1926)》,(Selections from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伦敦1978年版,第57-58页。
(16)葛兰西:《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伦敦1971年版,第244页。
(17)米利本德和阿尔都塞都提到过葛兰西的这项开创性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葛兰西的思想。参见米利本德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7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载于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04页注。
(18)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第155页。
(19)格兰·特尔博恩:《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政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中文版,第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