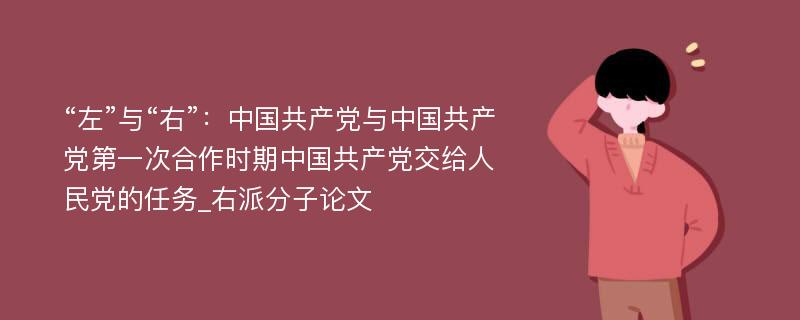
“左”與“右”: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國民黨的派別劃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對國民黨论文,派別劃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K2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5)04-0189-10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此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專門致唁國民黨表示:“偉大的集合體指導革命,比偉大的個人指導革命將更有力”,“今後的國民黨必然仍為中山的革命主義所統一,一切革命分子必然因中山之死更加團結一致,這種內部的統一是中山死後防禦敵人進攻的必要保證”。①中共雖然表示相信國民黨不會因孫中山的離世而發生內部分裂,但實際上自孫推行“聯俄”與“容共”政策之後,國民黨內由此導致的內部分化一直呈加劇趨勢。中共一直密切關注,受到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影響,逐步引入“左派”、“右派”等概念對此現象進行闡釋與解讀,並根據兩黨關係的動態變化不斷調整鬥爭策略與劃分標準,對不同的派別,分別採取團結、爭取或排斥、打擊的政策,從而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話語體系,對二十世紀中國影響深遠。② 一、中共最初在國民黨內引入“左派”、“右派”概念 1920年代初期,蘇俄為了保證在遠東地區的國家利益,先後派出幾個代表團同北京政府談判,以期建立中蘇之間的外交關係和經濟關係,尤其是爭取獲得北京政府的正式外交承認。另一方面,蘇俄代表團也與中國各派勢力密切接觸,尋求合作者,孫中山進入了他們的視野。但蘇俄對當時國民黨組織渙散與派系林立的狀況很不滿意,因此在決定向孫提供物質援助的同時,亦不斷提醒後者應該注意健全黨的組織建設與思想政治宣傳,並敦促其進行改組。在這一過程中,蘇俄逐漸形成了一套策略,即通過劃分國民黨內的不同派別,改變國民黨的組織構成,培育一支“親俄”的“左派”勢力,支持其改造國民黨,進而控制國民黨,最終影響中國政局,最大程度實現蘇俄在華利益。蘇俄及共產國際在國民黨內劃分派別的理論依據是政黨的階級構成學說,重要標準是對待蘇俄的立場以及相應的對待“帝國主義”、“軍閥”和工農群眾的態度。最初,蘇俄的分化思路只是一個雛形,直到國民黨“一大”召開之後,這一策略才在派別劃分的理論、方法及實施途徑等層面得到落實。③ 蘇俄及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分化策略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中共對此有一個領會、執行的過程,並在實踐過程中多有發揮。中共對國民黨的左右劃分在國共合作政策醞釀之初就已經開始,最初以國民黨人對共產黨的態度為主要標準,隱然將國民黨內部區分為不同的派系。不過,這種劃分還只是源於一種自發性認識,中共很少公開提及,與後來主動構建國民黨內左派、右派的做法有明顯區別。此時,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內的反共群體雖有對峙,但有孫中山的居間協調,雙方矛盾尚未激化。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改組”,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國共關係日益明確。大會結束後,中共立即召開會議,形成了一份決議案,對日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工作態度與工作方法做出了具體的指導與規定。對於國民黨內那些反對與共產黨接近的分子,中共最初反應比較溫和,並不認為他們是所謂“右派”,同時還要求共產黨員對這部分人“多方加以聯絡,以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無論國民黨的舊黨員與新黨員,他們比較疏遠我們,還曾經一二次反對我們的主張,他們不一定對我們有惡意,或者是不瞭解我們的原故,我們不要遽目為右派,把這樣的黨員目為屬於統一的一個派別,因而嫌惡疑忌他們。因為這樣,必致惹起他們的反感,促成他們的實際聯合。這將不但使我們與國民黨的合作發生困難,且徒然使革命勢力內部發生些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國革命的發展,而使國民黨不能免左右之分歧,我們應採種種策略化右為左,不可取狹隘態度軀[驅]左為右。”④此時,中共從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出發,態度上比較低調,在黨內文件中要求自己的同志努力工作,盡職盡責,採取謹慎、穩健的策略,爭取更多國民黨員的信任,淡化國民黨內的左右之分。 不過,作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對國共合作起到重要促成作用的俄國人鮑羅廷顯然沒有如此樂觀。“一大”尚未結束之時,他就在中共一次內部會議中提出,參加國民黨“一大”的代表可分為左、中、右三派,其中,中派的數量最多,是左、右兩派爭取的對象,“為了戰勝右派,就必須使孫逸仙能感覺到有一個強大的左派作基礎。只要這個左派還沒團結起來,並且不在實踐中大顯身手,那就不能指望孫同右派進行堅決的鬥爭。”⑤同樣,在另一位俄國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維經斯基看來,在國民黨內保持絕對的統一而不發生左右派衝突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國民黨內有一部分黨員是“商業資本”的代表,他們有可能更改孫中山的既定方向,共產黨人“應表現自己有能力支持國民黨左派,揭露民族主義者可能出現的脫離群眾的些微錯誤”,共產黨的任務,就是“要在國民黨內爭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國民黨左派有較大的迴旋餘地”。⑥兩位俄國人都提到了要極力壯大“左派”在國民黨內的力量。 實際形勢的發展也印證了鮑羅廷和維經斯基的判斷。“一大”之後,隨著共產黨人對國民黨實際工作的介入逐步加深,兩黨的矛盾與對立日益激化。國民黨內部分黨員堅決抵制“容共”政策,拒不接受共產黨人的“跨黨”行為。1924年4月,陳獨秀發表《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在中共方面較早提出了國民黨內的左右分化,其中表示,國民黨在“實際的政治運動未認真活動以前,也斷然沒真的左右派之意見發生”,“但將來國民黨在政治上實際運動豐富時,左右派政見不同,也是不能免的事”。⑦ 1924年5月中共召開擴大會議,開始在公開文件中正式提出國民黨內已經出現了兩派力量,“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此時,中共並不主張立刻機械式地開除右派,或對其採取人身攻擊,只是要求在輿論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錯誤(最重要的,就是迴避反帝國主義的爭鬥)”。會議制定的主要策略是,採用種種方法,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國民黨左翼”,“減殺右翼勢力”。⑧此後,中共對國民黨的左、右劃分逐漸從自發性認識轉入主動建構的自覺狀態。 國共實行黨內合作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開展工作,孫中山並不允許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發展自己的組織。但中共基於“組織獨立”原則,一直告誡其黨員要時刻注意保持自身的自主性,在國共合作之初就開始在一些國民黨組織中建立自己的“黨團”。為此,1924年6、7月間,上海、廣州等地的部分國民黨人提出彈劾案,聯名向國民黨中央施加壓力,檢舉共產黨人“違紀”,反對共產黨人“跨黨”,要求共產黨“分立”,其中一項指責就是“在國民黨原有的黨員中,吸收所謂階級覺悟的分子,成立一個國民黨的左派”。⑨ 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內“反共”分子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國共關係日趨複雜。中共逐漸轉變對國民黨的態度,調整策略,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開始在國民黨內著力發展左派力量,並強化對國民黨的左右之分。1924年7月,鮑羅廷在廣州致信瞿秋白,表示“我們的整個方針應該是召集和組織國民黨左派”。⑩中共中央也在向黨員發佈的通告中要求,“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於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我們同志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今後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入國民黨”。(11) 當國民黨內“反共”勢力的活動日甚一日之時,孫中山對此雖有壓制,但並未表現出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共對此很不滿意,認為孫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1924年7月,陳獨秀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判斷:“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此時,他修改了5月擴大會議上的提法,把孫中山定位於“中派”:“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裡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裡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和另外幾個領導人是中派,而不是左派(即便戴季陶也不過是左翼理論家)”。因此,他建議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支持“不能沿用以前的形式”,應該“有選擇地採取行動”,“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不久之後,陳還在另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建議共產國際提醒鮑羅廷,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容易進入他的圈套。(12) 陳獨秀對孫中山的定位也代表了中央的態度,此後,中共不斷批判國民黨“中派”的“游移”。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孫中山應邀北上,期間雖發表了一系列“反帝”、“廢約”主張,但在中共看來,“此宣言純粹代表國民黨中派的觀念,措辭含混,大有與各軍閥妥協之餘地,且語多抽象,並無代表人民利益的具體要求,彼此次北去受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兩面之包圍,結果恐甚危險”。(13)“中派”既可以偏“左”,也可以向“右”,在當時的語境中,這種定位明顯表明中共對孫中山的批評態度。 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上,中共中央指出當時一些同志所犯“右傾”錯誤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以為“應該幫助整個的國民黨,不必助長左右派之分裂”。同時,對國民黨內左派、中派、右派包含的範圍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做出了明確認定:“國民黨自改組大會以後,左右派之分化已成事實,在沙面罷工,在商團事件,在江浙戰爭中,兩派中間都發生了劇烈的衝突。左派的成分是工人、農民及知識階級的急進分子;右派的成分是軍人、官僚、政客、資本家……國民黨中派,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中革命分子,他們在數量上雖不甚重要卻站在國民黨領袖地位,他們總是立在我們和右派之間,操縱取利……中派的領袖們,因為受了我們的指摘,頗想引用右派排擠我們,然他們自知其力量不及右派,在種種實際利害上,又不得不和我們有相當的聯合,以發展己派的力量。”為此,中共認為自身在國民黨內的工作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應採取新的工作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是在民眾宣傳上擴大國民黨的左派;對於國民黨中派領袖及一切左右派間游移分子,應該在具體事實上,糾正其右傾政策之錯誤,使之明瞭右派行為違反了革命主義,使之離開右派,從事不妥協的爭鬥。”(14) 從最初盡力避免國民黨內的左右分歧,到盡力擴大國民黨左派勢力,聯合中派向右派進攻,這種鬥爭方針的變化與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處境密切相關。在孫中山推行“容共”政策的過程中,部分國民黨員一直持強烈懷疑態度,並屢起風波。尤其是一批“老同志”以及海外華僑對此非議頗多,但孫兼顧左右,不僅以其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對此壓制,同時也進行了安撫,但國民黨內由此引發的分歧一直沒有徹底根除,反而隨著共產黨人對國民黨工作介入的逐漸加深,雙方的對立也愈演愈烈。而一直扮演居間調停角色的孫中山在進入1925年之後病情惡化,對國民黨工作的控制力明顯下降,由此對國共關係也產生了重要的連帶影響。 二、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新右派”的出現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作為長期的、唯一的領袖,孫的離世使國民黨驟失重心,群龍無首,黨內因“聯俄”與“容共”政策推行所導致的分裂趨勢也進一步加劇。 國民黨內部的分裂以及孫中山逝世之後留下的權威真空引起了鮑羅廷與中共的重視,鮑氏認為這是清除國民黨右派、由左派掌握權力的最好時機。中共也下發通知,要求立即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公開徵求黨員,借機擴充左派數量,以便“壓迫中派使其必須與我們合作”,並爭取在日後召開的第二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和右派“競爭選舉”。(15)此後不久,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爆發,中共在組織上迅速壯大,一改國共合作之初所確立的“低調”姿態,開始積極謀求在國民革命中的“主動性”。在國共合作的框架中,中共姿態的提升勢必會對國民黨造成衝擊,由此也引發了國民黨內“反共”群體的進一步反彈。 中共對國民黨的左、右劃分有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在國共合作之初,中共雖然已經注意到了國民黨內因“容共”政策而產生的內部分化,但採取了穩健步調,對右派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意在不給自己樹立過多的敵人。總體而言,中共仍認同與那些“右派”同屬一個革命陣營。不過,隨著兩黨合作進程的深入,中共與國民黨內反共群體的矛盾不斷加深。尤其是孫中山逝世之後,兩黨關係更加緊張。中共對國民黨的派系劃分日益絕對化,信奉“不左即右”,沒有中立的餘地,嚴厲批判“中派”立場,對右派的攻擊性也日漸加強。以“戴季陶主義”與“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新右派”出現之後,中共將其定義為“反動派”,視其已經脫離了革命隊伍,不復有革命的資格。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呈現出“向左轉”的趨勢。掌握重要人事任免權的中央政治委員會躍居黨內核心部門,鮑羅廷作為該委員會高等顧問,對國民黨內決策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被中共認定為左派的汪精衛、廖仲愷的黨內地位也向上提升,汪更是借助於鮑羅廷的鼎力支持,成為廣州國民政府的首任主席,並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己失去孫中山絕對權威的背景下,他們在國民黨內繼續推行“容共”政策遇到了越來越大的阻力,由此引發了更加高漲的“反共”聲勢。 1925年6月至7月間,曾被陳獨秀稱為“左翼理論家”的戴季陶有感於國民黨內部思想的不統一以及基本政策的“含混不清”,先後完成《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文,在試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同時,也對“容共”政策提出了質疑,不僅要求共產黨人停止在國民黨內的“黨團行為”,而且聲稱要在思想上真正戰勝共產主義者,國民黨內的派系分歧更加複雜。戴氏的觀點拋出之後,迅速陷入共產黨人的文字圍剿,並被冠以“戴季陶主義”。《嚮導》週報社出版《反戴季陶的國民革命觀》,聲稱要揭露戴季陶“三民主義真信徒”的假面目。中共認為,戴季陶曲解孫中山的思想,已經背叛了“中山主義”,並將戴氏劃入國民黨“新右派”陣營。“戴季陶主義”出現之後,“新右派”概念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中共的各種政治表述中。 1925年8月,作為國民黨“左派”重要人物的廖仲愷在廣州遇刺身亡。這一事件不僅沒有削弱“左派”勢力,反而擴大了他們在國民黨中央權力格局中的份量。由於參與刺殺的嫌犯多與胡漢民有瓜葛,甚至還包括他的堂弟,胡氏因此而捲入其中。汪精衛、許崇智與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處理此案,結果是胡漢民以“養病”與“考察”的名義遠赴莫斯科。除此之外,一批長期堅持反對“容共”的國民黨人也怕受到牽連,一時不敢拋頭露面。汪精衛取代胡漢民,成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主席,集黨權、政權於一身,鮑羅廷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也更加穩固。按此趨勢發展下去,國民黨中央最高權力有可能落入蘇俄和共產黨人之手。在此情形之下,那些被排擠、逐漸邊緣化的老一代國民黨人進一步聯合起來。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林森、鄒魯、覃振、石瑛、謝持、石青陽、沈定一、茅祖權、傅汝霖等人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在北京西山召開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全會”。會議通過了《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開除汪精衛黨籍之判決書》,宣佈停止“容共”政策,解除鮑羅廷的顧問職務,取消凌駕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上的政治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 從西山會議內容分析,除反對“聯俄容共”外,還包括對汪精衛行為的嚴重不滿,這實際上是國民黨內部權力鬥爭的進一步激化。會議以自認合乎“黨統”的形式另立黨部,與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分庭抗禮,選取孫中山靈柩置放處作為會議地點即有明顯的象徵意味。12月4日,汪精衛、譚平山等人在廣州發表通告,聲討上海黨部的分裂行為,否認其合法性。這一時期,廣州、上海兩個國民黨中央互相指責,各自宣示自身的正統性,國民黨內部的深刻裂痕一時無法彌合。 中共對於西山會議的召開一直密切關注。西山會議尚未結束之時,中共就聲稱:“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已和從前的右派相等了,他們在北京開會,表面上雖然是反共派,實際上是要推翻廣州的國民政府”,為此,共產黨人“急須助左反右”。(16)幾天後,中共再次在通告中強調,西山會議的召開是國民黨“老右派”(謝持、居正、覃振、石青陽、石瑛、茅祖權等)和“新右派”(戴季陶、鄒魯、邵元沖、沈定一、張繼等)相互勾結的結果。(17)此時,中共劃定的“新右派”與所謂的“西山會議派”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西山會議派”幾乎已經成為“新右派”的代名詞。 “西山會議派”的出現,使國民黨內對“容共”政策持異議的黨員日益呈現“組織化”、“群體化”的特徵,雖然“反共”還不能涵蓋這部分群體的全部主張,但由此引發的排斥共產黨的風潮則日甚一日。中共組織黨員連續對“西山會議派”展開集中輿論攻勢,不僅指陳其違反黨紀的“非法性”,而且延續先前的論述策略,剝奪西山會議派的“革命資格”。毛澤東就將西山會議的召開視為國民黨右派“由革命地位退入不革命地位,由不革命地位退入反革命地位”的必然結果,因此,同西山會議派的鬥爭“實乃繼續革命與放棄革命之爭”。(18)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前夕,中共明確表示,不再視“右派”的產生是國民黨內部分裂的結果,而是“舊有之反革命分子”不斷被淘汰的過程,“因為他們的利益與革命是相反的”。(19)同年3月中共發表《告中國國民黨黨員書》,在批駁馮自由、西山會議派“右派”思想的同時,再次提出了國民黨的左右分裂:“一派企圖向左結合無產階級,一派企圖向右結合資產階級。企圖結合無產階級,遂不得不採用容納共產派聯俄擁護工農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圖結合資產階級,遂不得不修正聯共聯俄政策及提出階級調和的口號”。(20)此時,中共區分國民黨左右派的標準不僅更加具體,並且已經出現了後來被廣泛熟知的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初步提法。11月4日,陳獨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對“國民黨中究竟有沒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們聯盟的對象”的問題時回答:“我們可以肯定說是有的”,左派的政綱是“迎汪復職,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21)在12月的漢口特別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22)在這樣一種邏輯關係中,“三大政策”成為區分國民黨左右派的標準。 需要注意的是,在論述自身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時,中共的態度也有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最初,中共將自身定位於國民黨左派的一部分。但之後,中共的獨立意識和獨立性日漸增強,開始強調自身的“存在感”,努力與國民黨左派“劃清界限”,蔡和森就表示“不願居國民黨左派的美名”,而是要“時時刻刻準備幫助國民黨左派”。(23)中共要求黨員與國民黨“左派”結成緊密聯盟,“幫助他們發展國民黨並且反對右派”,“但是我們自己不可以代替左派”。(24)1925年11月《政治生活》上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將國民黨左派等同於共產黨的認識是一種誤會。“在國民黨中,有一個共產派,這是無容隱晦的。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不能自認為左派,亦猶國民黨左派黨員不必自視為共產派一樣。國民黨中不能不容納無產階級與農人分子,因此不能不有共產派的黨員與專重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政策。左派與共產派是絕對應當分別的,但在目前的行動上,乃至為國民革命而奮鬥的長時期中,左派與共產派應有親密的聯接。”(25) 1925年底,陳獨秀對這一問題做了更明確的表述。他指出,認為共產黨是國民黨左派的想法非常錯誤,“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行動上,固然站在左派的政策上面,然而共產黨是共產黨,國民黨是國民黨,國民黨自有他自己的左派,如何能以共產黨做國民黨的左派呢?國民黨左派的思想與政策,無論如何左傾如何急進,終究是國民黨不是共產黨。”他還舉例,當時國民黨左派的領袖,如汪精衛、蔣介石、胡漢民、譚延闓、程潛、于右任、徐謙、吳稚暉、李石曾、顧孟余、丁惟汾、王勵齋等一班人,“沒有一個是共產黨黨員”。(26) 三、蔣介石的崛起與中共劃分策略的新變化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時,反對“容共”政策的一批“右派”老黨員已經以“西山會議”的形式另立旗幟,一度被認為是“中派”的重要人物胡漢民也遠走異國,“作為廣州中央的領袖人物,此時汪精衛的左傾化程度也達到了極至。”(27)被中共認為趨向“左傾”的蔣介石在黨內的地位開始上升,左派及共產黨人的勢力明顯增強。會議選舉產生的新一屆國民黨中委80人,其中中央執行委員共36名,中共黨員佔8名;候補委員24名,中共黨員有6名。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的選舉中,中共黨員佔據了9名中的3名;在國民黨中央黨部9個部門中,中共黨員取得了3個部長、8個副部長的職位。(28)如果考慮到此時鮑羅廷的影響力,可以說共產黨人已經開始衝擊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維經斯基在向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中稱:“共產黨實際領導著國民黨,小小的共產黨處於國民黨的機構之中,在組織和發展國民黨。”“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很難劃清兩黨之間的界限,幾乎所有領導權都掌握在共產黨人手裡。”(29)中共也認為,國民黨“二大”召開期間,“右派反動派並無力搗亂,而左派與共產派的關係非常之好”。(30) 不過,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二大”之後,形勢急轉直下。3月20日發生了著名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因懷疑汪精衛與蘇聯顧問季山嘉有一個聯合“倒蔣”的“陰謀”而在廣州部分地區戒嚴,派兵佔領中山艦,逮捕海軍局局長李之龍,並暫時拘禁了一小部分共產黨黨代表。汪精衛在此事件後“負氣”出走海外,致使“左派”實力在廣州國民政府中削弱。隨後,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開始嚴格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權力與活動。通過這一系列動作,蔣介石開始染指黨權與政權,乘機控制了廣州政局。 蔣介石是1926年上半年國民黨內這場權力結構變動的最大受益者。面對蔣的崛起,中共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從國民黨“二大”以後至“中山艦事件”之前,廣州國民政府是左派執政,“中山艦事件”本身是“國民黨中派右派聯合向左派與我們進攻的表現,結果左派政權轉移到中派手裡”。此後,廣東整個政局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武裝中派專政,右派乘機向革命勢力進攻”。(31)在同年7月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中共提出國民黨內部已經分化為四種勢力:反動的右派(李福林、馮自由、馬素、古應芬等)、共產派、左派(汪精衛、甘乃光等)以及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蔣介石等)。蔣介石代表資產階級的改良勢力,被定位於“新右派”,亦稱“武裝的中派”。中共認為,汪精衛離開之後,尚無其他人可以統御國民黨,同時,為了維持國民黨的“左傾”態勢,又必須借助於蔣。此時,中共對蔣的態度在“聯合”與“反對”之間搖擺不定。為此制定的相關政策是“聯合左派並中派,向反動的右派進攻”。(32) 在這次會議上,中共還反思了自身工作的策略失誤,即過於束縛國民黨左派,不使左派管理黨務以及參與反對右派的鬥爭,導致中派與右派在全國範圍內攻擊中共,“我們自己造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的形勢,而使實質上是左右派之爭的性質隱蔽起來。同時我們既不使左派在政治上及組織上自己形成起來,當然國民黨的發展便因此遇見妨礙,不能充分吸收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33)同年底,陳獨秀再次指出了黨內同志的這種現象,即“包辦國民黨”,雖不是有意為之,但包辦的結果是既沒有國民黨,也沒有共產黨了。不僅如此,還要包辦“一切民眾運動”,“包辦的結果,國民黨沒有群眾,左派的群眾和左派領袖隔離了,於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沒有一個有力的左派和我們合作向右派爭鬥,其結果自然只有我們單獨的領導群眾和右派的軍事、政治勢力直接衝突”。(34)為此,中共再度提出要注意發展國民黨內的“左派”力量。 1926年7月,蔣介石出師北伐,迅速佔據兩湖,劍指江西,三個月不到即佔領武昌,進展超乎預期,成為影響南北權力格局的大事件,《大公報》評價:“無論戰局變遷如何,北洋正統從此已矣”。(35)但是,在北伐軍節節推進的同時,革命隊伍內部的分裂之象也日益顯露。蔣介石利用軍權統御黨權與政權,聲勢煊赫,在中共的描述中,“蔣所在地,就是國民黨中央所在地,國民政府所在地;蔣就是國民黨,蔣就是國民政府,威福之甚,過於中山為大元帥時”。(36)為了抑制蔣的“一家獨大”,分解其黨政權力,中共與部分國民黨左派人士發起“迎汪復職”運動,敦促汪精衛早日銷假回國,重掌國民黨“黨權”,以期恢復左派對國民黨及廣州國民政府的領導權。一時間,“促汪銷假”的通電在《漢口民國日報》上鋪天蓋地。同時,為了不動搖北伐的有利局面,中共提出了“汪蔣合作”的口號,仍然維護蔣作為中央軍事領袖的地位,表態“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我們向蔣誠懇的表示,汪回後我們決無報復行為,決不推翻整理黨務案”。此時,中共仍對蔣介石心存幻想,“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37) 此時,圍繞“迎汪復職”、遷都之爭以及“提高黨權運動”,國共兩黨之間以及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多有角力,蔣介石則處於漩渦中心,成為各種矛盾的焦點人物。9月北伐軍進佔漢口之後,蔣為了加強國民黨中央對武漢的控制,提議國民政府應從廣州遷都於此,中共擔心,“因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則左派群眾的影響越少,政策愈右,行動愈右”,因此反對蔣的提議。(38)11月7日,北伐軍佔據南昌,蔣介石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設於此。此時,鮑羅廷與中共都認為,戰爭形勢日漸明朗,國民政府必然將向全國發展,同時,遷都武漢也是一個從蔣介石手中奪回國民黨中央權力的重要途徑,因此改變先前意見,同意蔣的遷都之議。11月底,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正式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2月1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武漢宣佈成立。“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接管了原廣州國民政府的“最高職權”,在形式上奪回了蔣介石的黨政權力。 面對國共兩黨關係的諸多新變化,中共認為有專門討論的必要,因此於1926年底召開中央特別會議。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指出,由於湘、鄂地區農民運動的突起,國民黨中的一些游移分子“因恐怖而表現右傾”,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表示很右”,因此應該對國民黨的“右傾”化保持警惕。(39)陳的擔心很快成為事實。1927年1月3日,蔣介石趁張靜江、譚延闓等中央執委路過南昌北上武漢之際,宣佈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會議,將中央黨部的部分職能留在了南昌,與“武漢臨時聯席會議”分庭抗禮,此舉使國民黨中央政權產生了兩個權力中心。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發出通告指出:“現時蔣介石已成為右派反動勢力的中心”,應立即開展反蔣宣傳,在鬥爭中,共產黨應“勇敢的立在主體地位,使左派來幫助我們”,而不能像過去那樣“要左派為主體,我們去助他”。(40) 3月中旬,在鮑羅廷和國民黨左派勢力的掌控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召開,力圖用“黨權”指揮“軍權”,通過的一系列決議都將矛頭指向蔣,蔣的權力在形式上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此時蔣已經統領北伐軍攻克滬寧,軍事力量進一步膨脹。面對黨內左派勢力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的進一步威脅,其態度日漸明朗,社會上不時傳出共產黨即將被驅逐的風聲。鮑羅廷與共產黨人改變之前的態度,口號從提倡“汪蔣合作”轉為“迎汪倒蔣”。3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成立。3月底,汪精衛回國。4月4日,陳獨秀與汪精衛以兩黨領袖的身份發表聯合宣言:“我們應該站在革命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互相尊敬,事事商協開誠進行,政見即不盡同,根本必須一致”。(41)4月10日,汪到達漢口,受到熱烈歡迎。 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清黨”,隨後在南京召開政治會議,接續南昌之政治會議,建立南京國民政府,形成“寧漢對峙”之局。武漢政權建立之後,內部紛爭不斷,不僅遭致右派勢力的連續攻擊,亦不能得到左派勢力的支持與擁護,遂在三個月之後宣佈“分共”。國民黨在一度分裂之後重新走上形式上的左、右合流,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終結。 1920年代初,蘇俄、共產國際及中共引入左、右概念,將國民黨內因“聯俄”、“容共”政策所引發的內部分歧解讀為左、右之爭,並將其與“革命”話語關聯,經過不斷宣傳與闡釋,建立起了“左派”與“革命”、“右派”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對應關係。 在陳獨秀的界定中,“採用革命方法的是左派,採用妥協方法的是右派”,“左派是革命的,右派不是革命的”。(42)趙世炎認為,一切國民黨分子都要在“革命與反革命”(即左派和右派)之間作出選擇。(43)彭述之也持相同觀點,“所謂國民黨左右派的區分完全是站在策略上之革命與非革命的區分”,左派是“贊成並運用革命的策略”,右派是“反對革命的策略”。(44)汪精衛在悼念廖仲愷時也曾有“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國主義的向右去”之說。(45)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將領的李品仙後來也回憶,北伐前後這段時期,共產黨幾乎在國民黨內造成了一種輿論勢力,只有左傾才是革命。共產黨是左傾的,也就是革命的,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人,都是反革命。(46)在“革命”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當性的激進語境中,多方都努力追逐與爭奪“革命”的身份,被貼上“右派”的標籤無異於被推上了“革命”的“審判台”。“反革命”不僅是一個“汙名”,甚至成為一項“罪名”。(47) 中共對國民黨的分化策略確實發揮了一定威力,擴大了國民黨本已存在的內部裂痕。胡漢民也在“清黨”之時批評共產黨,“第一、就是給我們製造了一批非常能幹,又會看風使帆,又會吃西陂口沫的左派;第二、又給我們製造了一批五花八門的右派、新右派、新新右派、新軍閥、新官僚、工賊、昏庸老朽、老朽昏庸等等。似乎中國國民黨,除了這些就什麼都沒有了。”(48)或許是認識到“左派”、“右派”概念對於國民黨的破壞力,蔣介石在“清黨”後宣佈禁止使用這些“怪名詞”:“年來共產黨分化我黨政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於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魘,立即癱瘓而退。”(49) 值得注意的是,當初針對國民黨的“左派”、“右派”概念在不久之後就被中共引入自己黨內的派系鬥爭,並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都是中國政治的關鍵詞,二者的內在關聯值得重視與挖掘。從這個意義上說,考察中共對國民黨的左、右劃分,不僅是檢視國民革命時期兩黨關係的重要樣本,同時也為探究中共自身歷史提供了重要線索。 ①《中國共產黨致唁中國國民黨》,廣州:《嚮導》,第107期(1925年3月21日)。 ②對此問題有價值的研究可參見蔣永敬:《鮑羅廷對國民黨的“左運”工作》,收入氏著《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年;蘇維初:《國民黨左派歷史之研究》,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學報》,1994年第2~3期;楊奎松:《武漢國民黨的“聯共”與“分共”》,北京:《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楊天宏:《蘇俄與20年代國民黨的派別分化》,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楊天宏:《加入國民黨之後共產黨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馮筱才:《“左”“右”之間:北伐前後虞洽卿與中共的合作與分裂》,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金富軍:《中共早期反帝理論與策略研究(1921-1925)》,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86~108頁。本文主要從中共對國民黨的派別分化角度切入,希望能進一步揭示中共早期革命策略的複雜性。 ③有關這一問題的詳細研究,參見楊天宏《蘇俄與20年代國民黨的派別分化》。該文還指出,當蘇俄企圖以其方式改造國民黨時,首先通過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國民黨的派別劃分和批評而表現出來。 ④⑧(11)(13)(14)(15)(16)(17)中央檔案局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181~182、186~188、223~224、240、278~279、328、451、452頁。 ⑤⑩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60~461、511頁。 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編譯:《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31~32頁。 ⑦陳獨秀:《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廣州:《嚮導》,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⑨獨秀:《我們的回答》,廣州:《嚮導》,第83期(1924年9月17日)。 (12)(34)(39)陳獨秀:《陳獨秀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4~85、119頁;第564頁;第568頁。 (18)毛澤東:《革命派黨員群起反對北京右派會議》,廣州:《政治週報》,第2期(1925年12月13日)。 (19)(21)(22)(24)(30)(31)(32)(33)(36)(37)(38)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6年)》,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第5、281~282、391、120、16、211~212、116~117、119~120、242、222~223、228頁。 (20)《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日告中國國民黨黨員書》,廣州:《嚮導》,第146期(1926年3月17日)。 (23)和森:《何謂國民黨左派》,廣州:《嚮導》,第113期(1925年5月3日)。 (25)樂生:《怎樣分別國民黨的左右派》,北京:《政治生活》,第56期(1925年11月1日)。 (26)獨秀:《什麼是國民黨左右派》,廣州:《嚮導》,第137期(1925年12月3日)。 (27)王奇生:《中政會與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輪替(1924-1927)》,北京:《歷史研究》,2008年第3期。 (2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53~455頁。 (2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4、60頁。 (35)榆民:《回頭是岸》,天津:《大公報》,1926年9月4日。 (40)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頁。 (41)陳獨秀:《陳獨秀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7頁。 (42)獨秀:《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廣州:《嚮導》,第62期(1924年4月23日)。 (43)羅敬(趙世炎):《革命與反革命》,廣州:《嚮導》,第110期(1925年4月12日)。 (44)述之:《國民黨中之左右派的爭鬥與共產黨》,廣州:《嚮導》,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4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年,第486頁。 (46)李品仙:《李品仙回憶錄》,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5年,第85~86頁。 (47)王奇生:《北伐時期的地緣、法律與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國的緣起》,北京:《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8)胡漢民:《清黨之意義》,南京:《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4月)。 (49)《蔣介石言論集》,第4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內部清樣版,第258頁。轉引自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年,第74~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