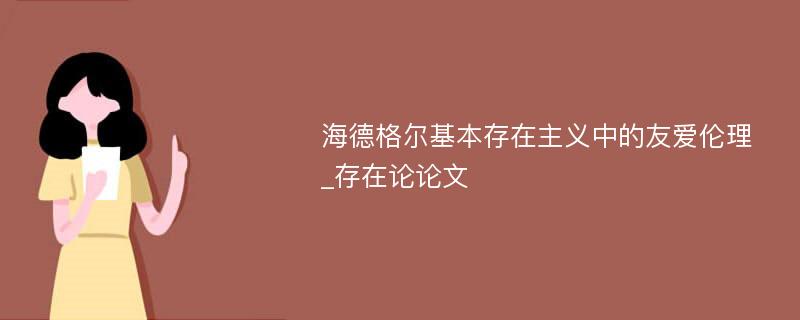
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的友爱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友爱论文,伦理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及其之前的各种讲稿和谈话中(简单来说,就是“现象学的十年”时期)所构建的基础存在论具有极其丰实而复杂的思想资源,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尤其是《尼各马可伦理学》)是其中格外突出的灵感源泉。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鉴于“友爱”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那么以这种伦理学或实践哲学为特殊源泉的基础存在论如何处理友爱问题?当然,这种提问方式可能会遭到一些诘难: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解读属于存在论的改造和挪用,而友爱问题属于伦理-政治领域,后者乃是存在者层次上的,那么其对友爱伦理的探究是否是一种“层次错移”?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占用属于创造性的诠释,不是对文本的全面系统解释,是否需要对其中的每一论题作出回应?等等。 面对这些可能的诘难,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海德格尔虽然总是拒绝对基础存在论的任何道德主义和哲学人类学的解读,但是他仍然认为,依循这种基础存在论而来的哲学人类学或伦理学是可能的。换言之,他并不否认他的基础存在论将对“成为人(to be human)意味着什么”提供一种框架。①第二,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海德格尔也坚信,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是密切相关的,并且伦理学必然奠基于形而上学之上。所以,基础存在论虽然被看作是对恰当言说“存在”问题的形而上学所作的一种准备工作,可是它必然也构成了对继后的适宜(geeignet)之伦理学的准备,尽管这种准备可能是间接性的。第三,有鉴于海德格尔所特别强调的本真性生存概念明显地涉及人类存在者的生存之善,他并不排斥对某种好的人类生活的连贯性解释,而友爱在通常的情况下,每每构成了值得向往的一种品格、德性或人类生存关系。并且,无论就海德格尔个体生活经验还是就其哲学文本而言,他对“朋友”或“友爱”这一类观念并不陌生。譬如,《存在与时间》的题献就是“埃德蒙特·胡塞尔——为了敬重和友爱”,而且他在文中先后写道:“倾听也构成了此在对它最本己能在的源初而本真的敞开状态,犹如在倾听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的朋友的声音”②;“具有决断性的此在可以成为他人的‘良知’。只有通过在决断状态中本真地成为他们自身,人们才能本真地彼此共在(Miteinandersein),而不是通过模棱两可、心怀妒忌的约定和在‘常人’及其想要从事的事情中,夸夸其谈地称兄道弟(Verbrüdertung)”③。又如,他在1952年还写道:“我们的语言把朋友的本质内涵、源自朋友的东西称为友好之物。相应地,我们现在也把本身有待思虑的东西称为可思虑之物。”④基于这些认识,当我们询问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友爱的可能空间及其形态之际,也并不是十分“唐突”或“离谱”的事情。 不过,当我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很快就发现,有关这一论题的关注和讨论十分稀缺。譬如,在哈特(Lawrence J.Hatab)那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伦理学与有限性:海德格尔对道德哲学的贡献》中,友爱或朋友的论题丝毫没有进入他的讨论视野。⑤而在另外一些零星研究中,譬如,在道斯达尔(Robert Dostal)的论文中,探究的结果也多具有明显的悲观意味,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政治的替身是民族英雄。海德格尔在预备性的此在分析中所建立的根基在这方面的无能,不是由于它受限于形而上学的语言(正如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而是部分地因为没有为友爱提供空间。按照他的解释,我们不能离开工作间去和朋友围坐起来”⑥。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友爱的可能空间及其形态”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聚焦于《存在与时间》及其之前的部分讲稿与谈话:首先,借助对此在、共在和言谈等概念及其相关性的深入分析,着力揭示友爱伦理在基础存在论中的可能空间;其次,通过对本真地存在、死亡与良知的召唤等论题的进一步考察,探究基础存在论为友爱伦理保留的空间中所可能呈现出来的友爱形态;最后,在与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部分性比较中,对于基础存在论中友爱的可能空间及其形态尝试给予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 一、此在、共在与言谈:友爱的可能空间 如所周知,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笛卡尔以来近现代西方哲学中意识主体概念的一种反动和抗争。在他看来,意识主体概念设定了一种错误的心灵观念,按照这种观念,我们首先乃是固封的、闭锁的、孤立的存在者,不能直接、明见地感知和确认他人的存在,因而遭遇到“他人心灵”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这种封闭的主观世界中把自身解放出来,必须让自己的心灵“走出来”,其途径就是以同情或移情(Einfühlung)的方式来感知和确认“他人之心”。不过,这种克服唯我论、解决主体问性问题的思路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困难。首先,类比逻辑上的不严谨性。因为同情方式的辩护进路是,“我”的心灵是与“我”的身体及其行为相耦合的,其他类人的生物具有和“我”的身体及其行为相类似的身体及行为,那么这样的生物必然具有与“我”的心灵相类似的心灵。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心灵以类似的方式附加到其他那些身体及其行为上面,即使在我们的身体形式和行为之间存在着再多的相似性,也不能证实这一点”⑦。其次,伦理后果上的不恰当性。因为这种解决进路最终仍然是把他人的存在奠基于“我”自身的存在之上,以自我为优先和标准。最后,这种处理方式也不合乎现象学的“事情本身”。按照现象学的眼光,我们自己的存在和他人的存在一开始就具有根本的相关性,并且是同等源始的。 根据海德格尔的分析,在现象学的视野中,我们作为此在总是卷入了某种周围环境世界,在此周围世界中,上手性的各种人工物或用具(Zeug)不仅向我们显示为它是指向某一目的——即具有某种“何所为”(das Wofür,in-order-to)结构——的存在者,而且显示为它必然具有某种设计者、制作者或潜在的使用者。这种显示方式表明了两点:一方面,此在正是通过与上手之物非凝视、非怀疑的打交道而展开自己的能在,并且是带着某种“实践性操心”而开始“去存在”(zu-sein),开始“自我理解”⑧。另一方面,在与上手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促使某一此在不断觉识到其他主体的在场,因为上手之物或用具也将自身显示为:它包含着对其他主体的指示或指引(Anzeige)。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对我们近旁周围世界——例如,手工业者的工作世界——的‘描述’,表明了一点,即随同在工作中发现的用具一起,他人也得以照面,而‘工作’的进行就是‘为他人之故’。在这个上手事物的存在方式中,亦即,在其因缘中,具有一种本质性的指引联系,指引向可能的使用者。”⑨ 这样一来,作为“去存在”的此在并不仅仅必然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这里的“世界”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是指那种能够使得作为此在一个构成部分的每一周围环境世界得以可能的东西,而且它在其本性上已经包含着其他此在。也就是说,此在并非仅仅偶然地与他人相关,仿佛与他人的关系只是我们所拥有的任何其他属性之一种,而我们没有这种属性仍然能够是其所是。事实上,此在与他人的关系就是此在的关系化本性之实现,就是此在的本性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写道:“此在的世界所开放出来的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它不仅和用具与物根本有别,而且按其作为此在这样一种存在的方式,它是以在世的方式‘在’世界中的,并且同时它又在这个世界中以在世界之内的方式来照面。”⑩由于既不同于非人类的存在者又不等同于我们的此在之他人,与我们同样源始地在世界之中存在,那么,此在的世界必然是共同世界(Mitwelt),世界必然“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亦即,“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11)。 我们与他人在世界之中共同存在,那么我们如何与他人“共同存在”?这涉及到此在的展开状态。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言谈(Rede)构成了此在的三种展开状态之一——其他两种分别是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和理解(Verstehen)。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存在者本性的一个规定,即zōon logon echon(人是具有logos的生物)。不过,他的具体解释比较独特,logos被译解为“揭示性的言谈”。在他看来,我们既不应该追随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之时髦,将这种言谈理解为单纯的声音,也不能随便将之理解为我们自身存在的结构,因为“言谈总是关于某物的言谈,关于某物的表达,并且总是和某人言谈、对某人言谈。经由言谈,所言谈之物揭示出来并且让他人得以通晓”。(12) 从这里我们可以初步看出,至少就形式而言,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仍然为某种形式的友爱伦理提供了想象空间。首先,由于我们在本性上与他人共同存在、一起存在,甚至我们的此在与他人之在是相互规定、相互蕴含的,那么我们与他人的各自存在活动或存在本性的展开及其兴盛之间必然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或影响。其次,由于言谈是一种语言方式,并且在言谈中我们就某种共同的事物进行言说,这表明我们愿意和他人分享某种东西,而不是暴力的、敌对的关系。最后,言谈作为一种语言形式,也是此在的三种展开状态之一,并且这种展开状态是与理解的展开状态密切相关的,因为正是在言谈中,我们相互表达出自身——对某物之存在的理解也体现了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认知。而这三点,即相互性、善意和认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恰恰构成了任何类型友爱的三个最小条件。 二、本真地存在、死亡与良知的召唤:友爱的可能形态 在这种看起来仍然比较宽广的可能友爱空间中,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友爱伦理可以呈现出何种形态?要探究这一问题,首当其冲的一个争议性概念就是本真性(Eigentlichkeit)或“本真地存在”及其所涉及到的“死亡”(Tod)论题。 如上所述,此在在其本性上就是与他人共在。这个根本性的“共在”(Mitsein)特征构成了友爱伦理的可能基础,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它也被看作是此在之“非本真地存在”的源泉。按照他的观点,共在虽然表明此在之存在的社会本性,但是此在的另外一个基本性质即“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也不容忽视。“向来我属性”具有两个基本含义。(13)其一,此在的存在对其自身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作为“去存在”的此在,关于要去实现的生存可能性所给出的每一种选择都一定是关于它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生活形式而作出的选择。其二,每一此在都是一个个体,都可能拥有真正的个体性而不能相互替代或还原。依据“向来我属性”这一特征,与他人共在的此在在具体的生活中可能就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形式是本真地存在。在这种存在形式中,此在能够认识到它的生存是分离式地自我决定的;能够认识到它内在的自我区分,即当前的所是与能是之间具有某种非一致性,进而也能够认识到应该把他人作为真正的他人与其发生关联,而不是简单地委身于他人。另一种形式是非本真地存在。在这种存在形式中,此在丧失了发现自身并维持自身的基本能力,把自身看作与个人无关的单一化“常人”(das Man)。作为常人之一或常人式自我,我们做常人所做的事情:常人以某一种方式讲话,以某一种方式行动。这乃是一种匿名的、日常的、平均的、逃避个体责任的生存方式,使得我们与真实的本真存在远离开来。(14) 那么,如何从非本真状态过渡到本真状态,从而把能够表达每一此在之个体性的存在可能转化为现实?这涉及到“死亡”问题。根据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析,此在总是向着各种可能性筹划自己,而死亡就是此在最极端的可能性,即作为全然不存在(not being)之可能性的存在可能性。(15)对这种意义上的死亡来说,一方面,作为此在之绝对不可能性的可能性标志着此在的超越性筹划的有限性,是此在之存在的界限;另一方面,死亡作为此在之最本己的、非关系性的、不可逾越的、悬临着的可能性,逼迫此在朝向它的存在可能性而行动,向着它的诸存在可能性敞开存在,从而本真地生存。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于着力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探究友爱伦理的可能形态的任何尝试而言,这将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因为,海德格尔在这里似乎真正看重的,是此在如何能够通过“先行到死中去”或“向死存在”(Sein zum Tode)而获得一种决断状态,从而开启本真的存在之旅,(16)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无关乎他人,甚至他人的意见、观念和存在方式倒是构成了需要强力排除的障碍和负担。譬如,伽达默尔就认为:“按照海德格尔展开存在问题之准备的那种方式,以及他制定此在最本真的生存论结构之理解的那种方式,他人仅仅在其自身的生存中将自己显示为一种限制性要素。”(17)关于这种“本真性”以及相关的“死亡”概念对于友爱伦理的现实可能性所带来的困扰,还有学者干脆写道:“我们看到,此在是孤离的和孤寂的。这不是对共同体(或社会性)的一种否定,而是反映了一种有关建基于死亡与超越而非爱与友爱的人类共在之理解。”(18) 那么,是否可以断言,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虽然表面上为友爱伦理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可能空间,但实际上这种空间是虚拟的,是一种“幻象”,因为他随后已经排除了任何友爱伦理的现实可能形态?我们认为,在一种略微修正的意义上,某种形态的友爱伦理仍然是可以设想的。为此,现在需要推进到“良知的召唤”这一观念。 如上所述,在先行的向死存在中,海德格尔揭示了此在由非本真状态向本真状态过渡的可能性。不过,为了进一步确证这种可能性,他试图提供一种存在者层次暨生存上的见证。而这种见证最终落实在“良知的召唤”中。按照他的观点,为了筹划、展现此在最本己的存在可能性,此在需要中断与存在者的日常牵连,需要从常人式自我的喧嚷、好奇和模棱两可之“在家的”沉沦状态中摆脱出来,而这种情形只能出现于良知的无声召唤或愿有良知(Gewissenhabenwollen,wanting-to-have-a-conscience)中,即在沉默和倾听中去自我筹划,由此进入“决断状态”(Entschlossenheit,resoluteness)。 那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种“良知的召唤”从何而来?一方面,海德格尔强调,“此在本身作为良知从这种在世的基本存在中召唤”(19)。这似乎是说,“良知的召唤”乃是此在曾经被压制但没有被完全摧毁的寻求真实自我之能力发出的声音。但是,“如果那种能力真正被压制住的话,它如何能够发出声音?如果它能,那么它受到的压制必须已经解除了”(20)。如何解除?难道是遮蔽着自我寻求本真性之能力的那种能力自我解除?这听起来显然不是一种可以想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讲道:“呼声恰恰不是而且绝不会是由我们本身计划的,或准备的,或有意作出的。一声呼唤,不期而至,甚至违乎意愿。另一方面,呼声无疑并不来自某个与我一道在世的他人。呼声源出于我而又逾越于我”(21)。按照这种说法,“良知的召唤”不仅具有不可预测、不可把握的偶然性或突发性,而且具有一种可以感受到的外在性和陌生性。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来协调由此凸显的困难? 我们的解释方案是,“良知的召唤”必然来自于常人式自我之外的他人,而它能否真正起作用的决定性条件仍然在于此在自身。首先,虽然海德格尔反复强调,“良知的召唤”“并不来自某个与我一道在世的他人”,但是,与其说“良知的召唤”不来自于任何自我之外的他人,不如说前者不可能来自于非本真地存在的常人,因为芸芸众生“首先并且通常”都属于常人式存在。其次,尽管大多数世人“首先并且通常”处于浑浑噩噩、人云亦云的迷失状态并且“乐不思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世内存在者都无例外地始终处于这种状态中,他们中的某些人或少数人无论由于何种原因,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本真个体性而生活。再次,能够按照本真自我进行生活的卓越之人,有意无意地会形成一种示范,这种示范将会发挥一种激发性作用,即给仍然处于真实自我被遮蔽状态中的人带来一种刺激,激发“他”或“她”去积极地寻求自我的个体性。最后,带来某种召唤的他人虽然自身体现了某种值得赞赏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容并不一定就是我们必须效仿的东西。毋宁说,这种生活方式促使我们觉识到,我们自身之内也可能存在着自主寻求个体性的那种能力。并且,我们最终是否能够响应这种召唤,真正把这种召唤作为召唤来对待,从而使之富有成效,这仍然取决于我们自身。也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召唤者的召唤代表着对我们寻求本真性的最本己可能性的召唤,“这一召唤在当前被压制着但仍然构成着我们最内在的自我;在那种意义上,她的声音将是从我们内部发出来的”(22)。 如果上述解释方案是可接受的,那么,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某种形态的友爱伦理仍然是可以设想的:首先,朋友双方或者已经、或者正在尝试按照某种本真性方式来过一种自我负责的个体性生活,他们互不隶属,也不能相互还原。换言之,他们都将具有个人不能抹煞的独特性。其次,朋友中的一方在另一方寻求个体性之能力的发挥中、在后者自身之中扮演着一种形式上的“他者”。也就是说,在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现成的自我遮蔽了本真的潜在自我,或者说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在体现了本真个体性的朋友的激发下,我们将有可能或有机会发现那种本真的潜在自我,并把它看作与现成的自我不完全等同的他人,也就是注意到并努力维持自我内部的不完全一致性。再次,朋友中的任何一方,譬如更早开始追求属己个体性的那一方,并不能保证自身一旦踏上了寻求个体性的道路就将一劳永逸或一帆风顺,相反,倒是有可能随时再坠入个体性被遮蔽的迷失状态——正如海德格尔那富有争议的个人生活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就意味着,朋友间的稳定关系是脆弱的,尽管这种关系十分可贵而难得。最后,如果说朋友之间最大的一致性在于他们都献身于追求本真的个体性,那么在这种个体生活的具体内容方面,他们并不必然如此,反倒可能呈现出多姿多彩、各有不同的局面。 这样一幅友爱伦理的可能形态虽然很大程度上出自于我们从文本而来的逻辑推演和理论思辨,但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并非没有直接的文本依据。譬如,当海德格尔讲到此在与他人在世界中的交往方式即“操持”(Fürsorgen)之际,虽然他表示日常的共处方式“显示出多样的混合形态,对这些形态加以描述与分类则非本书范围以内的事情”(23),但是他仍然比较细致地提到并分析了操持的两种极端可能性——代庖(einspringen)控制和率先(vorspringen)解放——并且明显更倾向于支持后者。就前者而言,它是指“为他人把有待于操劳的事情揽收过去。于是,这个他人被抛出原地,退步抽身,以便事后把所操劳之事作为停妥可用之事承接过来,要不然就是使它自己完全脱卸其事”(24),这种操持方式所构成的乃是一种控制-依附的人伦关系。就后者而言,它是指“为他人的能在作出表率(vorausspringen);不是要从他人那里揽过‘操心’来,倒是恰恰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给回他人。这种操持本质上涉及本真的操心,亦即,涉及他人的‘生存’,而不是涉及他人所操劳的‘什么’”(25)。我们认为,这种示范、激发而不具体干涉或强迫的关系,正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可以构想出来的友爱伦理之主要模式。 三、一种比较性的分析和评论 毋庸置疑,相对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史上很少有哲学家在哲学理论和政治社会生活中给予友爱伦理以更重要的地位和更精深的研究,而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实践哲学的存在论阅读。那么,当初步勾画出海德格尔友爱伦理的可能空间与形态之后,我们将尝试在与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部分性比较中进一步分析和评论之。 第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友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即幸福(eudaimonia)之重要构成部分,甚至它本身就是通向幸福的重要途径。他讲道:“人是政治的生物,其本性就是要过共同的生活。所以,幸福的人也是同他人一起生活;因为,他拥有那些本性上就是善的事物。与朋友和好人共度时日显然比与陌生人和碰巧遇到的人共享更好。”(26)对海德格尔来说,代替“幸福”概念的乃是“本真地存在”或后来的“适宦地栖居”(geeignet wohnen)。不过,为了这种“本真地存在”,与他人的友爱伦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倾听也构成了此在对它最本己能在的源初而本真的敞开状态,犹如在倾听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的朋友的声音”(27)。 第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在最佳类型的友爱即德性的友爱中,朋友间由于德性品格而相互吸引和祝福,但是,一个朋友也可被看作另一个自我,前者是我们自我认识、自我成长的一面镜子。(28)这样一来,友爱的基础就在于自爱,友爱的必要性必须在个体自我之幸福的框架内来获得辩护。不过,由于这种自爱中的主要关切之物乃是各种高尚的德性,(29)并且德性的友爱是两个好人或趋向于成为好人的人之间的事情,所以,作为友爱之基础的自爱不仅使自己受益成为高贵的人,也使得朋友从中受益成为高贵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式德性的友爱具有利己主义的性质,那么它也是一种高尚的利己主义。同样,在海德格尔那里,友爱伦理的基础也可被理解为某种“自爱”,因为,一种真实的友爱伦理的形成,不仅需要能够勇于追求个体性自我的此在去响应“朋友”所发出的“良知的召唤”,而且这种响应的动因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如何有效启动或实现属己的本真存在。 第三,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哲学中,尤其是在德性的友爱伦理关系中,朋友之间需要彼此的祝福、互动的帮助行为和密切的共同生活,并且所追求的幸福在内容上大体是一致的,即最值得欲求的幸福属于一种“客观化”状态。不过,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一方面,他虽然不是一个激进的个体主义者或自我中心的反社会论者,但是由于受过近现代自由主义的洗礼,所以,尽管他反对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可是他仍然对任何来自个体之外的力量抱有高度的警惕和怀疑,(30)进而导致他比亚里士多德更加强调朋友间的差异性,相应地严重削弱了朋友间的实际互动性。另一方面,由于海德格尔仅仅单纯强调朋友们的生活在形式上的某种一致,即都积极地献身于寻求本真的个体性以及相应的决断状态,这使得我们在判断“一个人在什么程度上采取了适宜自身而又具有正面性社会价值的决断性行动”时,遭遇到特别的困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二战后人们纷纷就海德格尔此前的“附逆”行为予以谴责之际,他自身却令人难堪地保持缄默。 第四,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相对于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在内的实践科学,作为理论科学的形而上学被看作第一哲学,并且,以存在问题为核心的理论沉思构成了幸福生活的首要部分,但是,伦理-政治生活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复杂性仍然受到了高度重视。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问题几乎构成了哲学的唯一性问题,并且他人虽然在为存在问题而准备的此在之生存论阐释中具有一席之地,不过,总体来说,首要的仍然是个人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他人一起遭遇存在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向来倾向于首先维护和追随海德格尔路线的伽达默尔也批评说:“对海德格尔而言,共在乃是他不得不作出的一种退让,但是他从未真正地拥持这一退让。……实际上,它是有关他人的一种弱观点,更多地是让他人存在,而不是本真地‘对他人有兴趣’。”(31)这自然也导致他的基础存在论所可能提供的友爱伦理形态在应对现实的伦理政治生活之际,显得比较局促。例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不仅谈到个体性友爱的三种类型,即快乐的、利益的和德性的友爱,而且讨论了在城邦政治范围内保障个体幸福、促进社会繁荣的那种政治友爱或公民友爱,后者虽然可以说是一种弱的德性友爱,但仍然具有某种节制的利己主义特征。(32)反观海德格尔,在他提及友爱或朋友的少数几个场合,明显对于任何包含利益或快乐的交往形式都不屑一顾。(33) 总之,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实践哲学之创造性解读发展而来的基础存在论,对于友爱伦理这一论题仍然提供了比较广阔的可能空间,并且具有某种可设想的特殊形态。不过,就其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友爱哲学相比较而言,虽然这种可设想的友爱伦理在其内在的自爱基础、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同前者有着诸多可以沟通或互诠的地方,但是,在朋友间的实际性互动、优秀人格的评价、应对现实伦理政治生活的复杂性等领域仍然显得比较局促。 注释: ①②③⑨⑩(11)(15)(16)(19)(21)(23)(24)(25)(27)(33)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Max Niemeyer,1976,S.310,S.163,S.298,S.117-118,S.118,S.118,S.250-251,S.298,S.277,S.275,S.122,S.122,S.122,S.163,S.298. ④参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36页。 ⑤Lawrence J.Hatab,Ethics and Finitude:Heideggerian Contributions to Moral Philosoph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0. ⑥(18)Robert Dostal,"Friendship and Politics:Heidegger's Failing",Political Theory,1992(3),pp.399-423,p.403. ⑦(13)(20)(22)S.马尔霍尔:《海德格尔与〈存在与时间〉》,亓校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71页;第71页;第170页;第172页。 ⑧(12)Heidegger,"Wilhelm Dilthey's Research and the Struggle for a Historical Worldview(1925)",in Supplements:From the Earliest Essays to Being and Time and Beyond,ed.John van Bure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p.163,p.164. (14)Martin Heidegger,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Vittorio Klostermann,1979,S.338. (17)Hans-Georg Gadamer,"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 and Person",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2000(3),p.284. (26)(28)(29)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ed.Jonathan Barn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1169b17-20,1213a20-26,1168b15-1169a14. (30)关于海德格尔哲学中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折中协调关系之相关研究,参见Lawrence J.Hatab,Ethics and Finitude:Heideggerian Contributions to Moral Philosophy,pp.169-194。 (31)Hans-Georg Gadamer,A Century in Philosophy:Hans-Georg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with Riccardo Dottori,trans.Rod Coltman and Sigrid Koepke,Continuum,2004,p.23. (32)参见陈治国:《论亚里士多德式政治友爱的类型、性质及其当代定位》,“西方政治哲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南大学,2011年10月14日-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