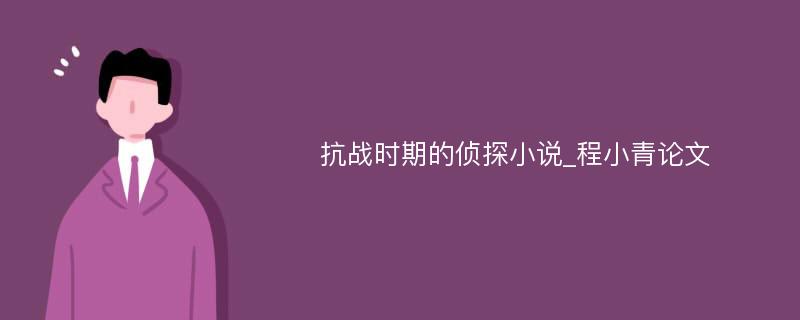
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滑稽论文,侦探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通俗小说各个类型之间的互动消长中,侦探小说“付出”多而“收入”少。其主要原因是侦探小说类型化程度较高,类型特征是其生命线,没有侦探,没有疑案的侦探小说是不能成立的。突出类型特征的内在要求决定了侦探小说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兹韦坦·托多罗夫曾列举了八点侦探小说的类型特征:
1.小说最多只该有一个侦探和一个罪犯,最少有一个受害者(一具尸体)。
2.罪犯不应该是一个职业犯罪者,不能是侦探,必是为了一些私人理由而杀人。
3.爱情在侦探小说中没有位置。
4.罪犯具有某种重要地位:
a)在生活中:不是仆人或贴身侍女。
b)在书中:是主要人物之一。
5.一切都须以一种理性的方法来解释:幻想作品不被接受。
6.心理描写与分析并不重要。
7.必须遵循连续的同一性。至于故事中的情况则是:“作者:读者=罪犯:侦探”。
8.必须避免平庸的境况与结局。(注:托多罗夫·侦探小说的类型学·环球文学,1990(1))
上述八点概括并不十分准确,擅长理论发明的托多罗夫显然对侦探小说史尚未熟稔到专家的程度。但这个概括却大体上合乎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印象”。可以一眼看出,这八点“印象”充满了否定词和限定副词,也就是说,排他性极为强烈。这意味着,侦探小说是一种技术化要求很高的艺术。社会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的作者只要知识广博或有某项专长即可,而侦探小说的作者却非得是“本专业”的行家里手才行。所以,尽管有人说“侦探小说的历史和侦探的诞生都起源于《圣经》”,(注:[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但真正成为一个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却公认是到1841 年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 in the Rue Morgue)才起步。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始于晚清,水平虽然幼稚,但类型意识很浓。1906年吴趼人辑34则笔记为《中国侦探案》,实乃公案变体,并非现代侦探。吴趼人尚订凡例6条, 按他所理解的类型特征,严加删削,“所辑各书内所载事迹,或不仅如所辑者,则其前后事,皆无关于侦探,故皆不备录。”(注:中国侦探案·凡例)也正是类型的技术要求太高,清末民初一大批涉笔侦探创作的作家不数年内便纷纷知难而退。刘半农云:“侦探困难,作侦探小说亦大不易易。”(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转引自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329 )中国第一份侦探小说刊物《侦探世界》只办了一年就因稿荒而关市大吉,赵苕狂在最后一期的《别矣诸君》中说:“就把这半月中,全国侦探小说作家所产出来的作品,一齐都收了拢来,有时还恐不敷一期之用。”一直坚守侦探小说这个码头的实则只有程小青、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而已。故现代侦探小说繁荣程度,并不如某些书中推许得那么高。还是范烟桥先生讲的比较客观:“中国的侦探小说创作并不甚盛……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的为多。”(注: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同上:337)
侦探小说与社会言情、武侠相比,“并不甚盛”,这不能仅从类型特征上去找原因。同一时期欧美和日本的侦探小说都“甚盛”,欧美侦探小说到二战前,除正统派外,还衍生出神奇、荒诞、幻想、犯罪、惊险、科幻等多种次类型。而中国只有“东方福尔摩斯”和“东方亚森罗苹”两个主要模式。此中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土壤”。中国的现实社会科学与法制都不够昌明,缺乏一个侦探活动的“公共空间”。因此,中国作家的侦探故事大多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来自外国作品的启发。而在借鉴外国侦探小说时,中国作家有两点偏误。一是把侦探推理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简单地归结为“启智”,企图以小说来作科学精神的宣传品。程小青说:“我承认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通俗教科书。”(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68)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读者阅读侦探小说的消遣动机。 意大利学者莱奥纳尔多·夏夏论道:
一般的侦探小说读者以及这类小说的最好读者,简单地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看作侦探的对手,并不想预先解答问题,“猜出”谜底,查出作案人。而几乎所有的侦探小说作者也努力避免读者积极参与侦查,为此他们给侦探配备一个戏剧中所说的“配角”:一个副手或者朋友,他表达的是普通人、普通读者的思想、疑惑或猜测。……(注:[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
“启智”大于“移情”是第一个偏误。第二是把本来不够充分的“移情”功夫集中到情节上,忽视人物塑造,从侦探身上看不到时代性与民族性,不了解外国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其实不是凭空而降的英雄,而是与其所生长的“典型环境”有着丰富的血肉联系。阿蒂利奥·贝尔托卢奇论述世界三大名探时说:
如果说杜邦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主人公,克夫是维多利亚王朝范围内的一个喜剧丑角,那么夏洛克·福尔摩斯就已经是一个用长长的白晰而敏感的手指把针头旋进注射器,以便给自己注射多少多少剂量的百分之七的可卡因溶液,并且到音乐会去聚精会神地欣赏德国音乐的唯美主义者了……(注:[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
可惜至今中国学者仍不理解这一点,还认为中国的霍桑“不打吗啡针,只吃吃香烟,没有抽上雅片烟。在程小青笔下,霍桑比福尔摩斯更完美。”(注:吴承惠·程小青和〈霍桑探案〉·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侦探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7)
这一“完美”的代价是失去血肉,作家的创作始终竞争不过自己的译作。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低潮阶段,到了抗战时期,现代侦探小说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视野的拓展。
抗战以前,侦探小说作者在理论上并非不重视社会内容。例如程小青的《请君入瓮》中讲道:
我又想起近来上海的社会真是愈变愈坏。侵略者的魔手抓住了我们的心脏。一般虎伥们依赖着外力,利用了巧取豪夺的手法,榨得了大众的汗血,便恣意挥霍,狂赌滥舞,奢靡荒淫,造成了一种靡烂的环境,把无量的人都送进了破产堕落之窟……
但是在创作实绩上,情节仍然是作家们的第一兴奋点。张碧梧说:“侦探小说的情节大概不外乎谋杀陷害和劫财等等。”“要做良好的侦探小说,必须善用险笔。”(注:引自汤哲声·张碧梧评传·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之三·南京出版社,1994:338—339)张碧梧闭门造出的险笔都有几分勉强,他又想出一个办法,把外国作品的人名地名缩短为只有两三个音,“仿佛是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这导致侦探小说与中国社会进一步隔膜。他们把《福尔摩斯探案》奉为至宝,却不明白“这些故事的魅力不仅在于搜寻罪犯过程对读者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福尔摩斯所处时代的生活,社会情况以及风土人情等。因此,有些人还通过福尔摩斯探案集,研究书中人物的原来模特、当时的铁路情况等。”(注:日本自由国民社·世界推理小说大观·群众出版社,1990)即使被誉为中国柯南道尔的程小青,也多把案情集中在中国家庭内部,有时把气氛渲染得“山雨欲来”,最后却不过是家中某个成员的恶作剧。因此,拓展社会视野,是侦探小说的一个迫切课题。
如果说抗战以前侦探小说的盟主要推程小青的话,那么到抗战时期侦探小说风格变化的代表作家则要数孙了红。
孙了红二十年代即开始侦探小说创作,但到抗战时期才进入他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这里比较一下他两个时期的两篇名作——《燕尾须》和《囤鱼肝油者》,以见其社会视野的拓展。
这两篇作品的可比性在于,它们不但都是成功的名作,而且后者是根据前者重写的。《燕尾须》1925年9月发表于《红玫瑰》第2卷12、13两期,小说分三节。第一节“疑云叠叠”,写珠宝商杨小枫在昏沉状态中入一菜馆,发现浑身装束已被换过,并且自己的燕尾须不翼而飞,面容年轻了十岁。旁边有一青年反复提醒“有人要和你过不去!”又见一凶汉虎视耽耽。杨小枫担心被绑票,结帐而出,却摸到袋中有一手枪。这时几人扑过来,杨小枫发枪不中,失去知觉。第二节“太滑稽了”,写杨小枫苏醒,发觉被铐在室内,有两人在谈抓获他的经过。杨小枫得知这里是警署,便申明身份,不料反被认为是冒充和做戏,断定他是某巨犯,百口莫辩,尤其是没有燕尾须作证,一筹莫展。第三节“最新绑票法”,写次日晨杨家乱成一团,忽来一青年自称绑匪,以燕尾须为凭,索五万元而去。杨小枫的五个同行得到匿名信,前去保出杨小枫。大家猜出是鲁平所为。鲁平致信杨小枫,说明因杨宣布要联合警界捕捉鲁平,特此报复,教训杨“以后勿大言,勿管鲁平的事”。故事结束。
这篇小说显然是以有趣的情节取胜,要捉人者反被人捉。结构近于传统的“谜语小说”,主要篇幅用来描写杨小枫的可笑的窘态,但杨并不令人可恨,反到令人有几分同情。鲁平的出场很简略,顺利得钱而去,其“绑票”动机,仅是为了报复加恫吓,虽借警署之手,却也与真正绑票相去无几。社会意义在文本中基本没有位置。
写于1943年的《囤鱼肝油者》在《燕尾须》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动。小说没有分节,只用空行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开头是较长的评述性叙述干预,使用“你”、“你们”直接与受述者交流。然后夹叙夹议地展开故事,其中一段写道:
记着,这故事的发生,是在时代开始动荡的时节。都市之夜不同于以前的情调。时代的晦黯,正自钻进每一个街角;街角的晦黯,也正自钻进每一颗人心。于是,在这一种晦黯的背景之下,却使我们这个晦黯的故事,更增加了一重晦黯的色彩。
在不断渲染的时代的晦黯中,主人公余慰堂迷迷糊糊走在街头,作者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他种种混乱而模糊的心理状态。在迷蒙与恐怖中,有个声音指引他走进咖啡馆,作者继续展现他混乱的感觉和回忆。那个声音提醒他留心,结果他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换了装束,而且“最尊贵的八字小须失踪了!”作者介绍余慰堂“是这个镀金大都市中的一个老牌闻人”。这时有一凶汉进来,余慰堂感到危险,结帐离去。在衣袋中摸到一只手枪。几个人追来,余慰堂开枪不中,被抓上汽车,失去知觉。
第二部分没有继续写余慰堂被抓到何处,而是转到余宅:“一宅五楼一底美伦美奂的住宅中。那座华丽的屋子,当然不属于那些专门仰仗二房东先生代领户口米票的凄惨朋友之所有。告诉你:它是我们的闻人余慰堂先生的不动产之一。”然后说这广厦里囤着大量的食品、用品、药品和人。叙事者用老练的调侃描述余宅因主人一夜未归而发生的混乱。这时一不速之客来访。来客绘声绘色讲述主人在外另开一小公馆,如何是一位“囤积界的天才”,昨晚却被一位囤积鱼肝油的犹太人劫走,然后挑明自己就是“绑票匪首领”,开价一百万。余家讨价还价,以八十万“成交”。来客在余宅连吃带睡,风头出尽,携款逍遥离去。两仆人跟踪,在警署门口见老爷被两位闻人拥出,一是纱业巨子,另一是药业巨子。最后,叙事者总结幕后,抖出绑票动机:一是勒赎,因为“近来他又很穷”;二是余慰堂曾说:“像这样的一个恶魔,为什么警探界不设法把他捉住了关起来?而竟眼看他在社会上横行不法!”结尾说:“他是和现代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
两相比较,《囤鱼肝油者》把重点由“须”转到了“囤”。字里行间时时提到经济问题,描写一个钻石领针,也说“在近午的阳光里闪射着威胁穷人的光华”。环境描写和对话中不时展现出时代特色。被绑者余慰堂并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囤过米,囤过煤,囤过纱”、“无所不囤”的大奸商。来客调侃道:“他打算把全市留存的各种西药,尽数打进他的围墙之内。他的志愿真伟大:他准备把全市那些缺少康健的人,全数囤积进医院;他又准备把各医院的病人,全数囤积进坟墓。”调侃中包含着无比的愤怒。孙了红自己正身患肺病,《万象》杂志代他募集医药费。他这篇小说除了艺术技巧的提高外,充满了对社会丑恶的揭示、嘲讽和痛恨。作者把《燕尾须》中杨小枫在警署的一段滑稽戏完全删掉,把重点放在“来客”如何在余宅痛快淋漓地揭发、谈笑自若地耍弄上。“趣味”与“意义”得到了高度结合,读者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侠盗故事,而且是一幅生动的社会漫画。
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以充实社会内容重新赢得了读者。
第二,打破封闭式格局。
以程小青为代表的战前侦探小说,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封闭式。侦探重视指纹、痕迹、凶器及各种科学检验,依靠推理查明案情。程小青的秘诀是:“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通到抉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注: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68)这是典型的英国侦探小说的路子。“英国型的侦探小说的特征是:故事在一个家庭或者村庄的圈子里展开,重视三一律,不限于唯一的一种犯罪行为。”(注:[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 ))这路小说无疑是古典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象征,但普雷佐利尼发现,它们的主人公“举止总是一样的……侦探没有发展。……侦探不会变老,他没有孩子,也没有弟子。每个案子他都从头开始。”(注:[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程小青、张碧梧、俞天愤、 陆澹安等人的作品,优点和缺点便都在这里,它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闭锁自身的艺术世界。”(注:吟峰·霍桑探案集编后·群众出版社,1988)有时为了逻辑上的自圆其说,不得不过分依赖巧合。如程小青的《舞后的归宿》,人物被刀刺死,另一人又打来一枪,子弹偏偏正入刀口。《案中案》里,陆全用刀杀死作恶多端的孙仲和,后来得知,行刺时孙已服药自杀,这样,“好人”陆全就减轻了法律上的罪过。作者刻意的安排太多,使小说类似一个精心设计的理化实验,现代科学表明:“在一个理想的测量过程中,一个系统可以被准备得使某一给定测量的结果可以预言。”(注:普里戈金,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77 )小说如果也如此,就会减少其可信性和刺激性。所以,打破封闭式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抗战时期的侦探小说在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侦探由一个“自然科学家”的形象转向“社会科学家”。程小青此时翻译了美国范·达痕(S·S·Van Dine1888—1939)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和艾勒里·奎恩(Ellery Queen)的《希腊棺材》等名著,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范·达痕笔下的斐洛凡士,“与福尔摩斯那种在地板上来回地爬着寻找物证的归纳推理相对照,他更重视罪犯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注:日本自由国民社·世界推理小说大观·群众出版社,1990)这正是方兴未艾的悬念推理小说的一支。程小青这一时期的《王冕珠》、《两粒珠》等作品便留下了这一影响的痕迹。例如《两粒珠》的案情,起因并非是犯罪,而是一个“犯了急性求恋症”的少年的莽撞行为所致。霍桑破案的主要依据不再是物证。而是明察秋毫地分析了一个青春期少年的心理,得出“祸患生于轻忽”的结论。而且,霍桑还推翻了对一个仆人“诚实可靠”的考语,指出:“你也研究过行为心理,总也相信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力量是相当大的。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人,平日的行为本很谨严,可是因着意志薄弱,或是理智不清,所以一遇到试诱的机会,往往不能自制,就也有行恶的可能。”
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两粒珠》的开头本来就是两件互不相干的案子交错进行,后来才合成一个。在情节上不守成法最甚的是孙了红的《一○二》,小说一共17节,直到第7 节以前,根本不像一篇侦探小说,没有案情、没有疑团、没有侦探,讲的尽是一个海派小戏班里的男女调情。悬念出现以后,作者又扯到万里之外菲律宾战事上去,让主人公徒劳而可笑地钻研那个岛国的地理、交通、物产、战况,将“八打半岛”中的“八打半”硬解释成“一○二”。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侦探小说的固有看法。
在正统的封闭式侦探小说中,的确如托多罗夫所云,没有爱情的位置。而封闭式格局一旦打破,作为人生重要内容之一的爱情,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侦探小说的家园。《两粒珠》的案由就是那位少年“为情魔所驱,丧失了理智”。在孙了红的作品中,更是普遍地涉及到爱情问题。《紫色游泳衣》写了一个失恋者的报复,女主角在丈夫和旧情人之间进退失踞的心理刻划得十分细腻。《血纸人》的复仇故事中,同时包藏着一个爱情悲剧。《三十三号屋》的数字谜团,来自一对小情人的暗语,小说以他们盛大的订婚典礼结束。至于《一○二》,完全可以看成一个言情小说。侠盗鲁平19岁时,热恋的情人罗绛云死于劫盗的刀下。从此他更加痛恨人世黑暗,无情惩罚那些恶徒。18年后,他偶遇面容酷似罗绛云的花旦艺人易红霞,遂痴心追逐——但只是精神上的,想把易红霞创造成罗绛云那样的“完人”。易红霞因家境贫苦,不得不周旋于众多的追逐者中,并也染有一些轻浮习气。追逐者之一绝望之下枪击易红霞,化名奢伟的鲁平得知这一危险后,赶去用身体挡住了子弹,受了重伤,而易红霞为了给他输血最后也病重不治。鲁平生命中最珍视的两位姑娘都死了,他经过悲伤、迷惘,最后仍决心继续走下去,“铲除掉一切人世间的弱肉强食的不合理的事和强暴凶恶的蟊贼!”
孙了红的作品中还有一些调情场面和女性身体的描写,很难肯定这究竟是受国外侦探小说的影响还是受国内其他类型小说的影响。二战以后的通俗小说中,性的成分增多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小说类型之间的互相综合与世俗生活的演变所共同造成的结果。
第三,武侠因素的引入。
侦探与武侠本来就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体现某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虚构的偶像。“虚构的侦探,甚至十九世纪的攻击者也喜欢指出,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并不十分相符。相反,他们似乎代表着以自己的理解反映生活中比较黑暗的社会隐喻的一种方式。”(注:拉里·N ·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87)在中国,侦探的形象开始是不同于武侠的,他们尊重法制、不尚暴力、讲究绅士风度,带着欧化色彩。但有正则有奇,在这主流之外,也出现了一些“不守规矩”的侦探。除了孙了红的东方罗苹外,就连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也有自掌正义之时。霍桑在《白纱巾》案中,没有将误杀奸商的白素珍送交警方,他对助手包朗说:
我们探案,一半在乎满足求知的兴趣,一半在维持公道。所以在正义范围之下,往往不受呆板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便自由处置。这是因为在这以物质为重心的社会之中,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
在《案中案》、《虱》中,霍桑也都有类似的处理。这便具备了一些“侠”的性质,“他代表的不是官方准则而是绝对法则”。(注: [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但霍桑基本上是与警方合作、按法律精神办案,从警方立场来看,他的存在是对“计划体制”的有力补充。这个文质彬彬的绅士是被按照社会楷模的理想塑造的。他公正、善良、智慧、机警、守法、文明、勤奋、朴素……然而他太“纯净”了,于是可敬却不那么可亲。中国读者需要一种离他们生活更近的、带有侠气的本土侦探。
孙了红虽然在20年代就创造了“侠盗”鲁平的形象,但那时的鲁平,“侠”少而“盗”多。这一点从《燕尾须》和《囤鱼肝油者》的比较中已经可见。侠义精神之于鲁平,到40年代才格外焕发出光彩。
40年代的鲁平,真正实施了“劫富济贫”的原则。在《血纸人》中,他保护杀人者去继承不法豪绅的财产。在《三十三号屋》中,他惩治两个不法奸商。在《紫色游泳衣》中,他本来混进郭府行窃,当得知女主人正受到敲诈时,他将计就计,反从敲诈者手中敲诈了一笔,同时保护了受害者。在《窃齿记》中,他用敲诈杀人者得来的钱财想使一个可怜的女孩子“补受一些较高的教育”。他做这些时,眼中毫无“法律”,只有一个绝对的“公平”。在《三十三号屋》中,他致信囤米巨商:“你想吧,屋内有着过剩的米,而屋外却有着过剩的饿殍,你看这是一个何等合理的情形哪?”于是他以巨商之子要挟,逼迫巨商“慨助赈米五百石”。这样的事霍桑是绝对不做的,霍桑顶多抓到了鲁平再悄悄放了。鲁平只管“合理”而不管“合法”,这便是侠。
孙了红因鲁平这一形象而被称作“反侦探小说家”。其实鲁平并非要反侦探,而是要反“绅士”。他总是跟绅士过不去,一再戏弄、惩罚之外,他还用自己怪异的举动对所谓“绅士风度”进行解构式的嘲讽。他衣饰华丽,却花哨刺眼,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拜访绅士也递上名片,却临时用笔写上几个潦草不堪的乱字。他用出自己的洋相来出绅士界的洋相,他用赤裸裸的敲诈、绑票来投射绅士们暗中的无恶不做。他不是以绅士派头为本份,而是以之为乐,有一种亵渎的快感。同时,他“劫富济贫”从来不白干,首先要济自己之贫。“一切归一切,生意归生意”(《血纸人》),他居然懂得把个人利益与天下利益统一起来。而这正是符合现代市民阅读趣味的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莱奥纳尔多·夏夏在论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笔下的比利时大侦探波瓦罗时说:
波瓦罗知道自己是一个侦查天才。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和狂妄骄横在他身上比在福尔摩斯身上使人更能忍受一些,这还要归功于影响到他的外表的嘲讽措辞。(注:[意]莱奥纳尔多·夏夏·第一个侦探是先知但以理·环球文学,1989(6))
自嘲和反讽意味使侠盗鲁平不那么可敬,然而却可亲。人物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缩短了,人物对社会的批判便显得格外真切有力。
侦探的侠义化也与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动向有关。继正统侦探小说之后,硬汉派侦探小说和托多罗夫所称的“黑色小说”等许多新的模式相继涌现。这些小说经常对社会及法律持批评和嘲讽的观点,侦探本人往往介入案情,“须拿他的健康甚至生命来冒险。”(注:托多罗夫·侦探小说的类型学·环球文学,1990(1 ))于是侦探本人的性格和命运成为作品魅力之一。他们蔑视常规、自掌正义,经常遭受警方和罪犯的两面夹击,在蒙冤受屈中用超人的勇气战胜邪恶,完成人格的修炼。这样的侦探当然也可视为现代化的侠客。
滑稽小说在沦陷时期也是个自成一家的类型。早期的滑稽小说只求博人一笑,往往恶谑百出,流于浅薄庸俗,不但被新文学所蔑视,在通俗文学家族里亦不受高看。自林语堂、老舍等人推广幽默,国人乃知幽默与滑稽不同,而滑稽小说作者亦以更高境界要求自己。抗战时期的滑稽小说,第一个普遍特点是深化了社会意义。他们不再仅仅依靠编织笑料来迎合世俗,而是能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可笑的因素。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系列,十二则故事中有十则关联着“钱”的问题。李阿毛的种种生财之道,让人读来又好笑又辛酸。例如《请走后门出去》一则,他让两位失业朋友分别在前后门各开一个理发店和一个生发药店,顾客进门后却让他们“请走后门出去”。结果街上的人见到头发蓬乱的人进了理发店,出来便一头光亮,而因秃顶走进生发药店的人,出来个个长出了头发,于是两店生意兴隆。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逗笑,而是颇有卓别林风格的匠心独运,从作者的艺术夸张中分明能感受到经济萧条已经把普通市民压迫到何种地步。在《日语学校》一则中,人物直接说出“一样样统制的统制,缺货的缺货”,发泄了对统治当局的愤恨。整个《李阿毛外传》就是一幅上海下层市民在贫困线上挣扎图,全篇回荡着一个声音:“我要吃饭!”滑稽处理虽不如正面揭示有力,但长处在于回味隽永,“以乐景写哀”,倍显其哀。
第二个特点是滑稽趣味有所提高。以前的滑稽小说市井气息过浓,如吴双热的“滑稽四书演义”,汪仲贤的《角先生》等,令人笑而不敬、笑而不爽,包括程瞻庐《唐祝文周四杰传》那样的名著也有许多粗俗无聊的恶趣,将知识分子流氓化,迎合市民的庸俗文化观念。徐卓呆、耿小的之所以能以滑稽小说家而受人尊重,在于他们自觉把握了滑稽的档次,耿小的专门著文探讨“滑稽”“幽默”“讽刺”三个概念的异同,他的小说则力求在滑稽和幽默中蕴含着讽刺。他们不再满足于从人物的外表去制造笑料,而追求从心理层次上挖掘出“笑根”。耿小的《滑稽侠客》中的两个武侠小说谜,并不是真的对武侠小说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是为了在女同学面前逞英雄,加上失恋的打击,才弃学出走。因此他们一路的荒唐行为也多与“男女”之事有关,心病是他们可笑的根源。徐卓呆笔下的小市民的可笑则来源于他们急于发财又经常破灭的白日梦:想偷钞票结果搬回家一具尸体,想从中揩油结果一赔到底。因此,滑稽中增添了几丝苦涩,趣味隐隐指向了哲理。
第三个特点是与其他类型互相综合。滑稽小说本来就是以风格而不是以题材得名,耿小的、徐卓呆都涉足多种题材,只是比尤半狂、胡寄尘、吴双热、汪仲贤等更钟情于“滑稽事业”而被视作专业笑匠。其实他们的小说不自觉地吸收和运用了其他类型的许多东西。社会言情方面的自不用说,这是最广阔的笑料基地。侠义和侦探因素也时有所见。徐卓呆笔下的李阿毛的行径与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颇有几分相似,只是一大一小而已。鲁平向敲诈者反敲诈一笔,李阿毛善于反占小偷的便宜;鲁平惩治大奸商,李阿毛则作弄贪财的二房东;鲁平是劫富济贫,李阿毛则专门帮助穷哥们。耿小的《滑稽侠客》、《摩登济公》、《云山雾沼》等作品大写侠义精神与时代风气的不谐和,很有“反武侠”的味道。孙悟空自愿下界治理人间,众神仙都盼他快去,“天上还可以清静一时”,同时也等着看他的乐子。济公来到人间,见书场里正说《济公传》,结果说书的和听众不但不认得他,反一齐嘲笑挤兑。这样的滑稽小说已近于讽刺小说的境界了。
不过,滑稽小说没有专用题材,加之审美品位不高,故终不能蔚成大观。它更多的意义在于为其类型贡献了许多锦上添花的技巧,并成为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之间一个良好的过渡。
抗战时期的历史小说有半壁楼主的《国战演义》、罗逢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和杜惜冰的《中国抗战史演义》以及张恨水的《水浒新传》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羽翼信史”的传统创作准则,“现实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明显的要求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意图。尤其前三部小说所叙“历史”是几与“现实”同步进行的,于是,一方面纪实性、宣传性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则有“创造历史”之嫌。张恨水《水浒新传》虽有若干史实依据,但实质上不是“借古喻今”,而是“造古喻今”。如将宋江毒死李逵一场,改为宋江誓死不愿跟随张邦昌归顺金国,而与李逵双双服毒自尽。抗战,揭开了民族历史的新篇章,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需要对历史进行崭新的巡视和剪裁,新的历史观决定了历史小说创作新面貌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