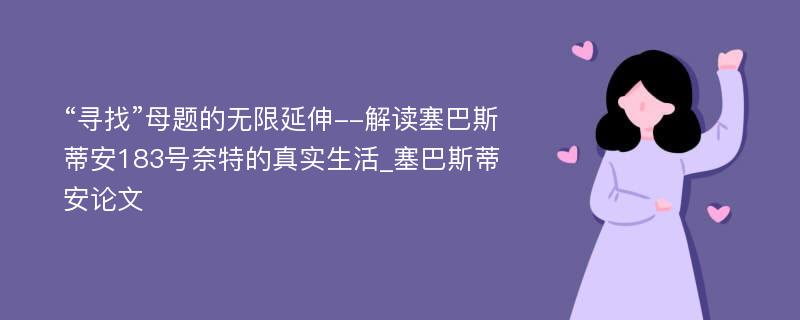
“寻觅”母题的无限延伸——对《塞巴斯蒂安#183;耐特真实的一生》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斯论文,真实论文,蒂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弗·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的后现代性已引起许多当代批评家的瞩目。倘若不是考虑到他最不喜欢谈论作家的相互影响,大家大约早就将他誉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俄国舅父”了。(注:Maurice Couturier,"Nabokov
in
PostmodernLand",Critique,vol.34:2(Winter 1993),pp.247—260.)他漫长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美国阶段”是以《塞巴斯蒂安·耐特真实的一生》(The Real Life of Sebatian Knight,1941,以下简称《塞》)(注:耐特(Knight)是塞巴斯蒂安英国裔母亲弗吉尼亚的姓。作者大约是在借此暗示其母亲祖上的悠久历史和显赫家世。虽然此姓意为“骑士”将它直译为汉语反倒会令人产生误解。1993年台湾出版的一部纳博科夫作品中译本在“作者简介”中便将此书名误译为“塞巴斯蒂安骑士记”。)开始的。这部传记体小说故事情节平淡无奇,主题神秘莫测,“是一部几乎没有被纳博科夫评论家们探讨过的书。也许这是因为同他后来部头更大的作品相比此书显得简单,抑或因为它是纳博科夫第一本用英文写成的小说。 ”(注:Anthony Oicott,"The
Author's
SpecicalIntention:A Study of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in A Book ofTbings About Vladimir Nabokov(Ann Arbor.ARDIS,1974),pp.104 —121.)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已得到充分关注的今天,我们有必要由新视角审视这一已显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端倪、 凸现全新认知行为的作品。如果说《洛丽塔》(Lolita,1955)、 《微暗的火》(Pale Fire,1962)和《埃达》(Ada,1969)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注:Maurice Couturier,"Nabokov in Postmodern
Land",Critique,vol.34:2(Winter 1993),pp.247—260.)纳博科夫以传记形式写出的玄学侦探小说(metaphysical detective fiction)便是后现代主义的先声了。
一、现代版的俄底浦斯神话
《塞》在基本顺叙的大框架下试图以一个个头绪纷乱、支离破碎的倒叙和解说片断重构俄裔英国小说家塞巴斯蒂安·耐特“真实”的一生。第一人称叙事者是书中人物,主人公的同父异母弟弟V。 他力图从文本和证人的证词两方面发掘塞巴斯蒂安短暂一生中的种种曲折隐情,为此仔细研读了塞巴斯蒂安留下的所有作品(《七色宝石》、《成功》、《失去的财产》、《可疑的水仙花》、《古怪的山峦》等五部长篇和三个短篇)和曾担任塞巴斯蒂安秘书的古德曼先生为塞巴斯蒂安撰写的第一部传记《塞巴斯蒂安·耐特的悲剧》,又不辞辛劳地造访了这位同父异母兄长的至爱亲朋。V 最终发现他的调查结果完全同调查过程重叠在一起。换言之,这是一场无法令人满意的调查,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中仍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仍存在不少尚不为人知的隐秘:
不论他的秘密是什么,我总算也明白了一个秘密,即灵魂只是一种存在的姿态,而并非一种始终不变的状态。随便哪一颗心灵都可能是你的,只要你找到它并紧跟它颤动的节奏。(1925页)(注:出于《塞》的引文均由笔者译自Vladimir Nabokov,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Knight(London:The Shenval Press,1960.)
奥科特(Olcott)等人发现小说中暗藏着“象棋意象”(
chessimages)和绵绵不断的对“巧合”(coincidence )等影射技巧的运用,如 36 这个数字在塞巴斯蒂安的一生中多次出现。 (注 : Anthony Oicott,"The Author's Specical Intention:A Study of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in A Book of Tbings About
Vladimir Nabokov(Ann Arbor.ARDIS,1974),pp.104—121.)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观点。 但是他同时亦引用书中V对塞巴斯蒂安的作品《可疑的水仙花》的评价,认为《塞》是一部主题不鲜明的作品,是对诸多主题的“玩弄”, 使它们“碰撞或狡黠地混合在一起, 表达隐藏的意义……”(注:Anthony Oicott,"The Author's Specical Intention:A Study of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in A Book of Tbings
About Vladimir Nabokov(Ann Arbor.ARDIS,1974),pp.104—121.)
利奥塔(Lyotard )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即是对知识话语的强调。为了验证自身的合理存在,知识日益依附于“叙述”,直至最后同叙述混为一谈。纳博科夫在《塞》中阐发的主题正是现代人在处于“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话语迷宫中徒劳地跋涉,却不知两者的分界线在何处,执拗地寻觅根本不存在的“真实”。
“寻觅”是西方文学中的传统母题,而“寻觅”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认知英雄”(cognitive hero)更是永远受人景仰、爱戴的人物。这是一个与西方哲理思维和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并行不悖的文学母题,也是反映“寻觅”过程的写作纷纷以侦探小说形式充当载体的根本原因。的确,我们很难想象其他的主题能与这一文类(genre )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如《等待戈多》无论怎样也无法成为一部侦探剧。《塞》中最主要的原型意象是希腊神话中有关俄底浦斯生平的传说。作为侦探先驱的俄底浦斯对自己身世的调查是西方文学中记述过的人类最早的侦探行为之一。纳博科夫对这一原型意象加以改写,在已有的“身份迷惘”情怀中增添了早已告别远古时代的现代人的苦恼,即对以历史文本形式呈现的知识是否真实可信的质疑。或者,套用为新历史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术语,这便是对“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的质疑。破解作者有意设置的种种“障眼法”后,读者不难发现它所刻意表现的基本思想仍是俄底浦斯式的、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周围的客观世界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迷惑不解。俄底浦斯神话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并派生出许多各具时代特色的现代版本,正是因为它既发人深省地反映了人类认知世界的必要性又揭示了这类认知活动的局限性。故罗兰·巴特把所有的叙事文本都视为俄底浦斯故事的翻版。“所有的故事都旨在寻根,都表达了人与规训对抗时的心境,都反映了爱与恨的纠葛。”(注:Roland Barthes,The
Pleasure
of
Text, trans.Richard Mill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75),p.36.)
俄底浦斯毕竟是成功的,他探明了有关自己生世的真相,虽然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他相比,《塞》中的V则不那么幸运。在此,经典侦探小说赖以赢得读者的三个基本因素完全被颠覆了,即基本顺序性、悬念和结局。侦探小说将事件按照容易分辨的次序排列,采用“碎裂”(fragmentation)叙事技巧把故事人为地分为若干部分, 再使它们散布于话语之中。它既可以再现过去的事件,也可以延缓对这些事件的了解。这样一个依照时间顺序、呈线性发展的情节往往以罪犯对秩序的破坏作为开端,随即描写侦探为恢复秩序而作出的努力,最后以罪犯被遏制收场。因此,托多罗夫把侦探小说分为两部分:犯罪的故事和侦破的故事。(注:Tzvetan Todorov,The Poetics of Prose,trans.R.Howard(Ithaca:Corneal University Press,1977),p.88.)读者在《塞》中看到塞巴斯蒂安的活动(抽象意义上的“犯罪的故事”)和V 对其活动的调查(抽象意义上的“侦破的故事”)被分割成一个个来源于不同渠道、无序排列的片断,呈犬牙交错状。这里的时间关系是任意的,而且每一特定时间并不保证附着于它的事件完全真实、可靠,如博尔赫斯在诗中发出的感慨:“时间是遗忘,也是回忆。”(《阿尔伯诺兹的米隆加》)例如第一章以描述塞巴斯蒂安出生那天的天气开始(根据奥尔伽的日记),以塞巴斯蒂安本人对其父参加决斗那天及前一天家庭和学校生活的追忆结束(转引自塞巴斯蒂安的作品《失去的财产》)。夹在这两段叙事中间的则是V 少年时期从母亲那儿听来的有关他父亲第一次婚姻的轶事(调查结果)。
书中根本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最扣人心弦的场面莫过于V 在病房里耐心地等候塞巴斯蒂安从昏迷中醒来,以便同他倾心交谈的那一幕。但是机敏的读者读到V 同在医院里看更的法国老头儿的对话时便悟到这注定只是一个“情景反讽”(situational irony), 一个不成悬念的“悬念”。
玄学侦探小说惯用的“无结局”(nonsolution )叙事策略在《塞》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读至卷终的读者不仅对神秘人物塞巴斯蒂安的生平不甚了了,而且产生了新的疑惑,即塞巴斯蒂安与V 是否本来便是同一个人。笔者认为,纳博科夫对俄底浦斯神话的现代阐释正体现在对自我的放逐和迷失的思考,一个永远新鲜的话题。在此纳博科夫让V完成了由认识论思维向本体论思维的过渡, 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本源的质询替代了如何认识、解释具体客观世界的疑问。小说以V 对塞巴斯蒂安这一“他者”身份孜孜不倦的调查开始,以对自己身份的质疑结束。
塞巴斯蒂安·耐特1899年12月31日生于我祖国的故都。(1页)
作品的第一个句子便开宗明义地把传主同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传记作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向也具备侦探身份的读者提出挑战。何以不明确申明主人公生于“俄罗斯故都”?“我”与塞巴斯蒂安仅仅是同父异母兄弟吗?这个故弄玄虚的谜始终因扰着读者,使他直至掩卷处仍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叙事者多项选择题式的解释只是再度把结局引向开篇的又一个“能指”:
结局就是结局。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日常生活里去(克莱尔也重返她的墓穴),然而主人公却留连忘返。这是因为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无法走出自己扮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紧贴在我的脸上,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无法洗去的。我是塞巴斯蒂安,或者说塞巴斯蒂安是我。或者也可以说我俩都是另一个人,一个我俩都不认识的人。(192页)
读者从这样一个并非结局的非理性“结局”中无法享受在颂扬理性的传统侦探小说结尾处所体会到的欢愉。在对同父异母兄长的身份调查过程中,V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疑惑。 苏格拉底号召其弟子“认识自己”、“照顾自己的心灵”,从此以人本身的存在作为衡量世间万物尺度便成为不言而喻的金科玉律。古往今来认知英雄们的业绩均在以“认识自己”(也包括认识自己而身于其中的客观世界)、使自己心安理得地在为终极目的的“寻觅”过程中建立。伊阿宋寻找金羊毛的探险、哈姆雷特对其父暴死的调查、现代侦探的鼻祖杜宾为找回失窃的信而进行的缜密推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对深藏在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恶感的探究……我们从这些形式大相径庭的认知活动中看到寻觅的对象经历了由具体到抽象、由客体到主体、由特殊到一般的演变过程。纳博科夫对这类母题做了“互交式”借用,同时也阐发出前辈作家不曾探讨过的新意。《塞》中的叙事者为重构传主一生的不懈努力同时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探寻”:对塞巴斯蒂安生平的探究旨在澄清事实,是具体的,针对“他者”的,个别的;而另一方面却颇具反讷意味地以对抽象的、关于自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存在状况“后认知”(post-cognitive)式的质疑结束。仍因循对往昔神秘事件重新建构的传统侦探小说程式,作者十分巧妙地嵌入所谓“解合法化”(de-legitimization )式的对这一建构过程的消解。
侦探行为无疑是“寻觅”的现代模式之一。V是《塞》中的侦探。作为一部引证各种材料的传记,《塞》可谓内容翔实,这应归功于V 的努力。在展开调查活动之始,V并不称职,后来才渐渐进入角色。 他不谙与人交往,在与传主一生中重大事件的见证人打交道时常常败北。如他去见克莱尔·毕舍普(塞巴斯蒂安在伦敦生活时的女友),却被克莱尔的丈夫三言两语便打发开。在博蒙特旅馆,V 竟无法说服旅馆经理把1929年夏天的住宿登记簿拿给他看,而他已确信使塞巴斯蒂安伤心失意的最后一位情人尼娜当时曾在此下榻。很难设想福尔摩斯、波洛或钱德勒的“硬汉”私家侦探在这类场合下就此罢休。
然而经历了挫折和磨难后,V终于成长为干练的侦探。 他不满足于凭蛛丝马迹重构兄长的一生,希望以科学而又精确的调查超越另一位传记作家古德曼先生。他同所有可能了解传主生活中的某一阶段、某一侧面的人会面,诸如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师、塞巴斯蒂安母亲唯一尚健在的亲戚斯蒂顿、塞巴斯蒂安在剑桥时的好友普拉特、曾为塞巴斯蒂安画过像的画家、孩提时代的伙伴罗沙诺夫兄弟,等等。
在寻找塞巴斯蒂安的俄国情妇尼娜过程中V表现不凡, 其机敏和应变能力堪与经典侦探小说中的一流大侦探媲美。根据退休职业警探塞尔伯曼提供的名单,V启程去拜访所有可能认识这位俄国女郎的知情人。V遇到的一个女人在谈话中无意间提到一位擅长逆向签名的人,而V不久前曾见到过这个人,听说他是俄国女郎前夫的亲戚。但是V 疑心她便是自己苦苦寻找的这位神秘俄国女郎。为了证实自己的揣测,他漫不经心地用俄语对另一位客人说女主人后颈上有一只蜘蛛。出于本能,这位自称是法国人的女郎果然立即伸手去拂自己脑后,可以想见,这是V 从经典侦探小说中学来的识别对手真实身份的方法。
V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所用的语汇也日益符合自己的侦探身份, 如他把调查活动中的目的地称为“猎场”,而搜集到的有关传主生平的资料则成为“线索”和“猎物”。在查询某一知情人地址时他甚至承认自己用过“福尔摩斯手法”。
《塞》中的另一有趣现象是作为侦探的V与作为作者的V在语词密林中相互追逐,这场游戏既消解了侦探故事的“真实性”,也消解了所有叙事与子叙事的可信性。言语和写作是作者的专利,思考和行动则是侦探的本份。V声称自己准备为塞巴斯蒂安写一部新的传记, 所有的侦探行为均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我们看到在这位侦探成长过程中,那位作者暂时隐退到他身后。起初他的行为表明他在潜意识中对文本(尤其是别人的文本)的不信任,如对古德曼的传记的攻击。无论是对传记作家还是对侦探而言,应塞巴斯蒂安的要求烧毁两位情妇致传主的信件都是无法弥补的错误。后来V亦萌生了悔意, 但他为自己开脱道:“我遗憾地说我身上较为善良的一面占了上风。”(35页)摆脱“信件”这一文本的束缚不仅使他的侦探活动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使他得以构建自己的文本。这当然也是在暗示文本的存在是虚妄的,毫无“真实性”可言。
V 识破以法国贵妇身份出现的女人正是当年的俄国女郎后便立即辞别她离去,彼时一段精彩的“内心独白”既是对侦探小说笔法的戏拟,也借对文本、写作和自己的作者身份的再次确认提醒读者注意摊在眼前的文本的虚妄,从而揭示所谓关于“真实的一生”的叙述只是对虚构的再次虚构。
我用我们气度不凡的俄语说:“你非常、非常聪明。你一直叫我以为你在谈论你的朋友,但实际上你是在谈论你自己。若不是命运捉弄了你,你这小把戏还能再玩一阵子呢。现在你把奶酷洒啦,因为我恰巧见过你前夫的表亲,那个会倒着写字的人。于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我在一旁嘟囔了一句俄语你便下意识地听进去……”不,这些话我连一个字也不曾说出口。我只是鞠躬退出了花园。她会收到这本书。她会明白的。(162页)
类似关于该书写作的提醒多次出现,如塞尔伯曼先生答应为V 展开调查后不要报酬,只要V寄一本书给他便可(121页)。V说, “如果他真的看到《塞》,我希望他读到我是多么感激他的鼎力相助。 ”(124页)
可以想见,V 未对尼娜做的这类解说在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或波洛和罪犯之间都是免不了的。这些大侦探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卖弄本领的好机会。
叙事者以双重身份交替出现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巴赫金(M.Bakhtin )认为小说本来就是“多音齐鸣 ” (heteroglossia)的文类,纳博科夫在此将这一概念明晰化,他让V从不同的身份、视角出发去臧否人物,将话语权力让同一人物的两种角色分担,从而使“虚构之虚”与“虚构之实”的相互对比更加鲜明。对《塞》的存在的不断提及实际上是在提示读者注意这一对照。侦探身份与作者身份此消彼长,最终仍以本原的身份的迷失结束。
(二)V 的身份在故事中的随时变更也是使“事由”(motivation)陌生化的一种努力,是情节设置的需要。这部以“传记”形式出现的伪传记本身当然是一种“事由”。V 不满足于仅仅从死的文本中发掘写作传记的素材,于是伪传记或为作传记而写的札记中便又嵌入侦探故事的形式。V的旅行和调查活动均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三)叙事者兼人物(他总是被排斥在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生活范围之外)的双重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互为“他者”,而摹写事物本质的愿望只与主体产生关联。这一微妙的身份是否在暗示中介者的不存在和认知对象的不可知?
二、虚与实之间的文本策略
以往的《塞》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作品能否构成一部完整的传记或自传,即使这是一部虚构的传记或自传。这是由于他们均被叙事者预备为塞巴斯蒂安作传的声明所迷惑, 又拘泥于对小说主题人物(titular hero)生平的探究中而不能自拔。
葛拉贝斯(H.Grabes)很实在地把V 的叙事视为塞巴斯蒂安的一部基本可信的传记,(注:Herbert Grabes,Fictitious
Biographies:Vladimir Nabokov's English Novels(Paris:Mouton,1977),p.36.)尽管有很多证据表明V是一位拙劣的传记作者, 如他鲁莽地烧毁了曾在塞巴斯蒂安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情妇的来信,又不负责任地从传主的小说中摘取片言只字,对其进行断章取义的解释,以迎合自己作传记的需要。而这正是为他所不齿的塞巴斯蒂安的第一部传记作者古德曼先生惯用的手法。当亲身采访和文字材料均无法提供传主的某段经历时,V会毫不踌躇地以自己的臆想去填补空白。 葛拉贝斯还落入作者预先设置的另一圈套,认为若要消除V 不是一位拙劣的传记作家的疑惑便得设法证明叙事者与塞巴斯蒂安是同一个人。读者的确会发现在叙事过程中V的风格同传主的笔法越来越相像, 如两人均以感人的诗化语言描述鸽子从凯旋门上腾空而起的情景。然而这类考证仍无法证明这个既给想象提供驰骋的旷野、却又永远无法得出结论的假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积极启发、诱导、 训诫“典型读者”( modelreader )的“开放式”(open )文本。 (注:Umberto Eco,The Role of
the
Reader: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s( 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 Press,1979),p.114.)它本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答案,寻找这类答案的企图当然不会成功。
菲尔德(A.Field)揣测V也许是塞巴斯蒂安臆想中的一个虚构人物, 塞巴斯蒂安本人才是作品中的真正叙事者。 (注: Andrew Field,Nabokov:His Life in Art(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67),pp.26—32.)这样《塞》便成为经主人公改头换面后抛出的一部自传。自传可算是一个后现代悖论,它同“死亡”密切相关,除非假设自己已经死去,否则便无法作传。这一悖论亦是对中国成语“盖棺论定”的绝妙注解。
也有人认为V 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对塞巴斯蒂安小说的研读和吸收变成了塞巴斯蒂安本人。波依德(M.Boyd)附合这种观点,他认定V 的传记旨在使死者“复活”的同时也试图证实作者在自己作品中的存在。但是纳博科夫失败了。“防止失败的措施是使V 和塞巴斯蒂安成为同一个人。如果V可使传记变成自传,纳博科夫也能。事实上V在传记和自己的生活中重构了塞巴斯蒂安的灵魂,也即他的‘存在姿态’,这使V 和塞巴斯蒂安的确成了同一个人。”(注:Michael Boyd,The ReflexiveNovel:Fiction as Critique ( Longdon and Toronto:AssociatedUniversity Presses,1983),pp.154—55.)
这些可大致归纳为“传记说”的观点把《塞》视为(1)传记, (2)自传,(3)传记兼自传。应该承认,这些看法均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尤其是对作品体裁及主题的理解。但是研究者同时也落入了作者的“寻觅”陷井而不自知。其实作为“关于叙述的叙述”的《塞》主要讲述的是为撰写传记而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对所有文本中的文本的研究和对知情人的采访。两者皆是广义上的侦探行为。纳博科夫的先锋性体现在对侦探行为与阅读行为之间形而上的相似性的刻意凸现,从而把读者引入这一层峦迭嶂之中的语词迷宫,比托多罗夫等人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联系早了三十多年。
即使仅仅把《塞》作为“阅读性”(readerly)文本,也不难看出贯彻小说始终的隐性侦探小说笔法。“这是侦探小说程式的重复:一具尸体、一位侦察员、几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和被烧毁的信件、一两个神秘的女人、 若隐若现的线索……”(注:Page Stegner,Escape intoAesthetics:The Art of Vladimir Nabokov(New York:The Dial Press,1966) ,p.35.)若考虑到它企图表现的“自我观照性”(
self-reflexivity )、 “不确定性”( indeterminacy )、 “参与”(participation)、“反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 “开放(open)、“分离”(disjunction)等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以及上文论及的对传统侦探小说形式的全面颠覆,将《塞》归入“玄学侦探小说”这一次文学(subgenre)也许更恰当。不妨认为纳博科夫在传记作者V 和传主塞巴斯蒂安的身份问题上布下迷魂阵的根本目的便是把读者引入这个“书写性”文本,向他已习以为常的依赖心理提出挑战,诱导他展开想像的双翅去建构自己的结论。巴特认为无法卒读的文本才是体现文学终极目的的文本。虽然《塞》尚未到达此境界,将它置于后现代主义文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衡量,我们发现它仍是一部文体游离于实(传记类写作)与虚(侦探故事)之间、宣泄作者自身感受的独辟幽径之作。( V 恰好是纳博科夫的名字 “ Bладймир ” 转写为英文Vladimir的首字母。)
如果将作为传记/自传的《塞》与作为侦探小说/玄学侦探小说的《塞》视为实与虚的相互印衬,V 的侦探活动与他的陈述便是物体与其镜中影象的关系。V的叙述中语焉不详之处甚多, 如他虽交代了塞巴斯蒂安的出生地和出生日期,他们的父亲在战争期间的情况、父亲的第二次婚姻等基本“事实”,虽从未按照侦探小说的惯例说明这些资料的来源。这已在暗示根本不存在真相。书名本身更是显而易见的反讽。“真实”是对何而言的?对其他文本,从古德曼的传记到假托于塞巴斯蒂安名下的“作品中的作品”。如果V的文本尚不足信赖, 更遑论这些镜中之镜所折射出的虚妄影象了。V 预备写进传记里的许多素材均来源于这些作品,如关于塞巴斯蒂安和他自己家庭背景的趣闻轶事(传记作者和传主又一次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一个往往为读者忽略的反讽是,V 用整整一章的篇幅集中火力攻讦古德曼先生和他的“纪实性”作品《塞巴斯蒂安·耐特的悲剧》,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说作者该为这部本应起名为“《好好先生的闹剧》”(“古德曼”意即“好人”)的垃圾之作“脸红。”(P.59)“简而言之,古德曼先生本该挨一通臭骂的,不料反倒受到了鼓励”。(58页)然而V 自己也毫不踌躇地从塞巴斯蒂安的虚构作品中搜集材料,如有关他们父亲的性格、第一次婚姻、因捍卫荣誉而举行的决斗及死亡等绘声绘色的描述均源于此。
“故事中的故事”是投入一潭死水中的一颗石子,在水面上形成一串同心圆的涟漪,由里向外,逐渐扩大。它以玩笑式的戏拟嘲弄作者,嘲弄以往的经典文学作品及其模式,最后也不免嘲弄自己。(如婚外恋和由此引起的决斗均是19世纪俄国小说经常涉及的情节。)
根据V 的转述我们知道古德曼先生在他的作品里洋洋自得地记述了传主青年时代在英国求学期间的一些逸闻趣事。其中有些故事是传主自己亲口讲给古德曼听的:
第三个故事:塞巴斯蒂安谈到他的第一部小说(从未出版,并且已销毁),说它叙述的是一个肥胖的青年学生在外地旅行后回到家里,发现母亲嫁给了自己的叔父,而正是这位以耳病专家为职业的叔父谋杀了父亲。(61页)
迟钝的古德曼先生没有觉察到塞巴斯蒂安是在拿他寻开心。这是《哈姆雷特》中的“戏中戏,”英语国家的中学生也耳熟能详的故事。剧中的丹麦王子用这出“戏中戏”影射叔父的罪行,如今古德曼又在懵懂中把它用在传记中,使之成为另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为了说明古德曼不学无术,V不惜第三次复述这个用滥了的情节, 使之成为“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揶揄古德曼之余,塞巴斯蒂安本人也被挖苦了一番。尼娜曾说塞巴斯蒂安惯于让自己沉溺于“梦、梦中梦、以及梦中之梦里的梦之中”。这个拿秘书寻开心的陈腐故事也许是又一钩沉索隐式的玄想。当然,这一“元影射”(meta-allusion), 也是针对日趋僵化、程式化的侦探小说的。
不难看出《塞》中的退休警探塞尔伯曼(Slibermann)是影射塞巴斯蒂安的短篇小说“月亮背面”中的塞勒(Siller)先生的。塞勒在等车时帮助了三位旅客,塞尔伯曼则在去斯塔斯伯格的车上与V相遇。 两人名字拼法相似,相貌也相仿。应V 的要求提供那份包括塞巴斯蒂安的情妇在内的名单时塞尔伯曼先生甚至用发音不标准的英语告诫V “我觉得这没有用。你看不见月亮的背面。别去找那个女人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123页)
对经典侦探小说俗套的嘲弄在另一“故事中的故事”中达到高潮,这就是塞巴斯蒂安的“反侦探小说”(anti-detective fiction)《七色宝石》。
一所公寓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贩卖艺术品的G.Abeson先生。警方请一位福尔摩斯式的伦敦私家侦探来侦破此案,但他因在路上不断出事而姗姗来迟。与此同时警方调查了所有房客,发现他们彼此间都有血缘、姻缘或职业上的联系。这一段冗长的调查结果使小说不再像一个破案故事。
伦敦来的侦探终于抵达了,于是小说又言归正传。正当他预备在大庭广众之中揭露凶犯之际,一个警察闯进来报告说尸体失踪了。一阵沉寂之后,案发后进来询问有无空房出租的老头儿Nosebag脱下假发, 摘下眼镜说自己可以解释其中的奥秘:“你们瞧,谁也不喜欢被人杀掉”。原来尸体并未被人肢解, 老头就是G.Abeson 先生。 Nosebag 是 G.Abeson的逆写。(86页)
V对这篇文字游戏评论道:
塞巴斯蒂安·耐特将戏拟当作跃入严肃情感之最高领域的跳板……他以差不多是狂热的憎恶心理翻捡出一度新鲜活泼、现已破烂不堪、夹杂在有生命力的事物中间的僵死的玩艺儿。这些东西冒充生命,虽被人再三摹画仍为那些懒得动脑筋思考、对骗局茫然无知的人所接受。也许这一陈腐的观点本身是十分单纯的,也许继续去发掘这个或那个完全用滥了的主题或文体并不是什么罪过,只要它令人开心、欢悦。可是在塞巴斯蒂安·耐特那儿,采用侦探小说常规一类不起眼的琐事亦会演变为一具肿胀,发臭的尸体。(85页)
这番评论反映了V (也即纳博科夫)对这一日益僵化的文类的看法。同样,这一戏拟在《塞》中也再度遭到戏拟。塞巴斯蒂安有一次躺在书房的地上喊道:“我没有死。我刚刚构筑了一个世界,这是我的学术休假。”(69页)
V同样不能胜任古德曼无法完成的使命, 两人的写作俱是对已逝去的时光进行徒劳的剽窃,是在无可奈何的心境中发泄“悟以往之不谏”式的悔恨,也是对过去做过某事或未做某事的懊悔。“重构过去”是荒唐的念头。“小说”的基本涵义正是“虚构”。那么对虚构进行再度虚构实际上是放弃传统的“艺术模仿生活”文学观。“小说是一种假装。但是,如果它的作者们坚持让人留意这种假装,他们就不是在假装了。”(注: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29页。 )我们今天审视这部半个世纪前写就的小说时倘若仍拘泥于对其虚构的可信度和形式的探讨,便会像前人一样误入歧途。小说中的“真”与“假”只是虚构之“真”与虚构之“假”的区别。针对这一传统的认识论思维方式,马丁(W.Martin)质询道,“说作家实在地描写一个假装的世界(传统的看法),或者说作家假装描写一个其实在性无关紧要的世界,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何在?”(注: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32页。)作为玄学侦探小说的《塞》拒绝并摒弃真与假(或者说虚构的现实与虚构的想象)的二元对立,从而迈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本体思辩范畴。“在哲学和批评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适用于正在进行的各种争论中的许多概念、方法和立场,但是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真实与非真实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的,也即对意义、真理和历史的建构,以及主体性和同一性所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注:Paula Geyh,etc,ed.,Postmodern American Fiction:A Norton Anthology( New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8),p.x.)(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以寻觅始以迷失终的《塞》所表露的正是这样一种含混、暧昧的关系。这是“失去天真”(注:埃科(U.Eco )在《〈玫瑰之名〉后记》中以一个生动的事例说明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失去天真的时代,话语、写作很难再是第一手的、创造性的。“我认为后现代观念即是一个爱上一位很有学识的女士的男人明白自己无法对她说‘我疯狂地爱着你’,因为他明白对方知道(而她也知道他明白这一点),巴巴拉·卡特兰(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曾被誉为“爱情小说女王”——笔者)已这样写过了。”)的时代的悲剧。
纳博科夫曾借《礼物》中的人物康乞维也夫之口表明真正的作家写作时心目中只有未来的读者。今天笔者认为以往对《塞》的阐释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但这并不表明我们这一代读者就是作者心目中的“未来的读者”。同V的“寻觅”尚未结束一样, 笔者也预感到在这个复杂的文本以及文本中的所有文本中的“寻觅”还将继续下去,无限地向前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