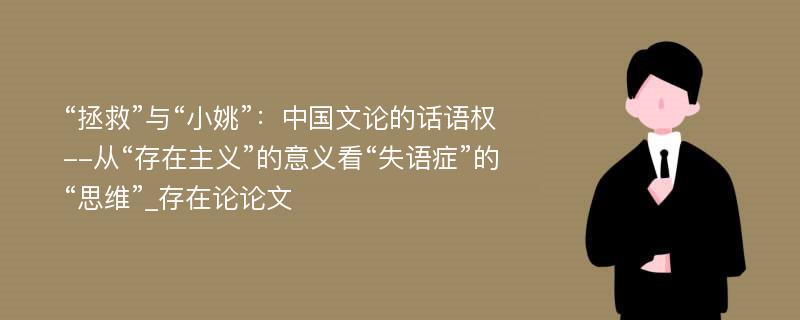
“拯救”与“逍遥”: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力——从“存在论”意义对“失语症”的“思”的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失语症论文,文论论文,中国论文,逍遥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04-0115-04
对于文学理论,我们似乎已经讲得够多了。文学已经被我们诠释成多重意义众说纷坛的令人惊奇的东西。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非但没有清醒地透视文学,反如奥古斯丁诠释时间那样变得更加糊涂了。我们讲得太多却没有回身以更大的精力去思考那些必须思考的比诠释更为先在的东西:我在思吗?我的思的界限是什么?我真的在“言说”我的思吗?于是众多的“本文”并没有因其浩繁与丰富而成为“文本”。哪怕在当前,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美学文艺学界的学者,别出新意在对我国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现状热衷于命名,这种现象只说明我国人文学者患了“失语症”后,重新恢复了语言能力,有了强烈的话语欲望,但是不是患上了更严重的“失语症”呢?因此,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作如此的思索,并进一步追问思的本性。
一
文学理论的根本性的问题,似乎在文学理论本身无法求得解决,文学理论自己不能拯救自己,更不用说达到“逍遥”的境界,它需要从哲学这一“别处”借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然而我们并没有审慎地怀疑借得处是否已经出了问题,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种种困境,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哲学。哲学绝不是庸俗化的总结与概括。否则它除了给予我们一大套僵化的抽象概念的教条以外,将空空如也。但哲学的确在给予,哲学的给子是对事物思后的阐释。哲学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精神方向,于艰难处提示并开辟道路。人类生存困境是哲学不得不直面的根本性问题。哲学必须阐释人的生存,并且哲学的一切生命由此而始。
面对人类生存,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因为哲学不允许它的视野远离人的生存。哲学有权力拒绝那些远离人的生存的思考。面对生存难题的哲学的无批判性,毋宁说哲学已由性灵老化为一具僵尸。哲学的生存必须以关注人的生存为方向和前提。这样,不仅将利于我们从知识论哲学的抽象概念里超拔出来,而且哲学从而艺术哲学将显现一个崭新的精神方向,哲学除了帮助人们寻找精神家园以外,没有多余地搭配给人类一套知识。“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生存的手段”。[1]阐释生存,哲学才真的在思,在言说。理解是真正的人类生存的需要。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解释是为了避免误解。而狄尔泰则认为解释能够使个体生命体验拓展从而历史(精神世界)具有普通意义。海德格尔则进一步认为哲学应从阐释的端点开始,理解是为了解释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从而使理解具有本体论意义。而解释则构成海德格尔现象学描述的方法上的意义。胡塞尔的现象学要旨在于按照理性原则重建事实,海德格尔批判了这一观念,让现象以照面的方式得以解释,所以海德格尔认为通过解释此在的意义在世间得以显现,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已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域宣告出来”[2],因此说到底,“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2]。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具有三层递推的意义:首先,诠释使意义澄明,从而“为进一步对此在式的存在者进行种种存在论研究提供境遇”[2]。这种诠释学的意义在于开辟通向现象的生存解释的道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即:“整理出一切存在论探索之所以可参的条件”⑤。海德格尔的这层意义显然有胡塞尔的影子。第三层意义是诠释学的方法论意义,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又与狄尔泰极其相似:“……诠释学作为此在的存在的解释就具有特殊的第三重意义:它是生存的生存论状态的分析工作——从哲学上来领会这重意义又是首要意义。这种意义诠释学作为历史学在存在者状态上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在存在论上把此在的历史性构建起来;只有是这样,那么,只可在派生方式上称作诠释学的那种东西,亦即历史学性质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化,就根据于这第三重意义上的诠释学。”[3]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具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到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就被完全放置于超越精神科学单纯方法论的本体论上的角度上。他说:“理解和解释并不是从方法角度训练的与本文的关系,而是人类社会生活进行的方式。”[4]
从对哲学诠释学简单地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诠释学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已经将其视野投向于实践本身。理解与诠释是一种参与性的事物,“直面于事件本身”与“事物照面”很难说不是实践的观念,后期海德格尔干脆称其诠释学为实践哲学。如果我们本着诠释学的理念审视文学现状,我们会发现我们并不真正地理解文学理论,当人的生存困境在文学领域“失语”时,文学的本性其实已被合法化的堂皇话语层层叠叠的掩蔽起来。
而人的生存困境在文学领域的“失语”并不是说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是我们用现有的知识无法言说生存真相,敞亮其间的诗性意义。正象有学者指出那样:“汉语学界的学者对中国文化与文化在‘话语学’层面的内涵非常重视,而对它在‘存在论’意义上的内涵认识则相当不足,实际上,中国文化与文化的‘失语症’绝不仅仅是一个‘自身传统话语丢失’或‘在世界文论界没有自己的声音’这样一个‘文化身份’和‘话语权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本世纪以来汉语学文化与文论由于从‘存在论’传统转向‘知识论’模式而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真相和通达特性意义的问题”。[5]
我们的文学理论虽然没有放弃对人生存困境的思,但“思”的方式被截断了,从而生存意义不仅没有呈现反被掩蔽了,用海德格尔的话讲,我们并没有为我们生存的可能性作出筹划,因此我们所见到的就不能不是失落“悲剧意识”的教条哲学。哲学解释学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真理不是康德所持反映论的认识与对象的一致而是显现,即成为人们可视可见的东西。哲学从文学理论借以显现的是人们的生存从而完成生存的“去蔽”过程。所谓生存论无非是使生存的问题得以显现和澄明。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在于我们必须耐心细致地剥去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知识论哲学厚重的外壳,方显出生命的本真状态!
生存问题的“失语”意味着生存的放逐。所谓阐释生存,即指突破知识论哲学远离人的生存的困境,以生存为起点与归宿,建立生存危机的合法性。简言之,即让生存完整地表达自身,而不是我们强行构造某种知识体系去概括和把握。“解释并不是把某种‘意义’抛掷到赤裸裸的现成的东西上,也不是给它贴上某种价值标签,而是随世内照面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直已有某种在世界中展开出来的因缘关系,解释无非就是这种因缘关系释放出来而已。”
中国传统文论与文化是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之上,它关心人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但这种传统在近现代受到西文知识理性的颠覆,产生了断裂,走上了另一条理路上。但我们是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存在论”呢?不是,中国传统论与文化的“存在论”基础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也同样无法独立承担言说我们生存真相和敞亮诗性意义的重任。这只是其中一个知识资源的出处而已,另一个资源就是西方近现代发展而来的存在哲学。
二
生存问题只有通过对生存活动的理解才得以显示。真正的思必须留心于存在的真理。思的意义是“去蔽”。人文学者作为“思”主体存在,文学阐释有其独特的知识占有者与教诲者。人文学者通过占有知识而控制接受对象,知识成为一种权力。同时这种权力的社会动作真理般地向人们表明它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因此人文学者所自觉接受的不是如何反思其权力动作而是如何谨慎且微妙地控制知识的占有权。
我们强调人文学者的思,是指人文学者的“我在思”。我在思意味着文学真理的澄明。文学真理的遮蔽正因为我们无思。海德格尔说:“最激发思的事是我们至今还不思,甚至还尚未思”。当应被思的远离了人的生存,这些思实际上正是思的远化。所谓非本真状态的思,是指我的思乃在思他者之思,而我貌似在思而其实正在排斥思的到场。
首先无思者善于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来证明话语制作的精心与精良。对文学本质的探讨,经典名著的广泛使用已经证明其实我们不在思而历史语言在重新告诉我们那已经是的东西。文学本质的威严面孔使得私人几乎无权力在其研究领域制造出一个“私人事件”。个人湮没在时代的海洋里,诸如文学本质与规律的权力话语几乎包容了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体性成为话语时尚。结果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追问与思并不表明历史理论已经风一样地吹过已不再有任何作用,而是思要求我们在必须思之处追问与思。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在精致玄妙的面纱下面收视一个个生存事件,直面于教育进行着思。描绘传统与全盘拒绝权力话语不仅不够策略,而且是真正的无知,真正的思超越。事实上文论的权力话语的存在是历史性的,妄图进行非历史的研究权力话语同样地是不在思。真正的思追问存在的真理。从历史的层累中呈现出生存的意义来,是真正的思!
又,中国文论界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失语症”。这并非耸人听闻,西方理论的大量登陆不但占领了我们的桥头堡而且深入腹地,因学术自律的丧失而导致自我阐释权的销声匿迹使得我们广阔的文学理论园地成了西文理论的试验场,姑且不论东西方文化有着如此的差异以至于容不得任何未经再诠释的泊来品所带来的言语和思想的混乱,单是这样带有“文化下乡”意味的所谓文化交流就已经使得我们的人文学者感情与理智面临挑战和危机。然而,无可奈何!译介式的、比较式的研究西文成为我们不少人文学者的时髦话语,似乎接近西文理论便意味着接近真理、与国际接轨,处在学科前沿!我们不得不在随权力话语威严同时艰涩地咀嚼着这一套我们其实并不太懂的时髦语言。时髦话语成了炫耀品。我们认为从它处借得火来,是必须的与必要的,但借之前思考这“火”的性质同样重要乃至更为重要。后现代话语已经充斥了整个文化市场,对于这样一个具有精神方向性质的文化思潮,不加思索的译介乃至向文论领域的生搬硬套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不仅东西方文化有着差异的问题。争夺中国文论的话语空间,理性地坚持文论思想的自我阐释权,才能实现东西方平等的文化交流。否则,我们只能借别人的脑袋讲话,其结果将是,我们创造性地吞食自己!
再者就人文学者个人的学术命运而言,自觉地接受学术制度及权力话语的支配从而达到自觉的体制化,成为阻碍我们思的又一“在者”。知识分子的宿命也许就是当他最希望站在历史的边缘时却偏偏处于历史的中心。知识分子自其产生起便注定了他的悲壮与苦难。当我们将知识分子的沉沦因素考虑在内的时候,这种悲壮与苦难就更显得意义非凡了。自觉地追求体制化使得人文学者不自觉地走进历史文化的中心。我们不能否认人文学者不得不接受学术制度的一切特征来艰难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人文学者实际上在自觉地使用一套权力话语。我们可以从某个时期的大量文论文章里读出相同的味道来。大家似乎并不考虑这锅肉该不该煮,值得不值得煮,而是一味地向里加料。权力话语充斥君临整个学术界。抵抗软弱,批判肤浅,自觉参与。路漫漫其修远兮,岂非自己一手造成的吗?追求被容纳必须牺牲自己的某种精神为代价。可叹的是,这种精神往往可贵!接纳权力话语意味着不得不接受时下流行的话语系统,否则将有人指责“难以沟通”。因此我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用一套官话、套话、惯用语甚至一些早已腐朽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并不深刻的思想。改造文学“文本”,必须从语言神圣地位的重塑开始,丰富文学思想必须通过活泼生动的语言来“言说”,千篇一律的文论文章究竟意义何在,不得而知。人们常虑于克隆人所带来的伦理危机,“精神克隆”岂不更为可怕?!
我们不得不在生存问题这一必思处进行着思。我们期待的思的澄明,甚至是被思者所引导。“思的最大困境在于今天还没有一个足够伟大的思想家说话,在直接地以清楚成形的方式把思带到思之质的核心从而也就把思引向正途。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有待思想之事的伟大处是太伟大了。我们也许最多只能努力沿着所行不远的狭窄小路为过渡到待思想之事稍事修建。”思期待着善思者,可是“思亘古如斯又倏忽闪现,谁的惊愕能深究它?”
三
如果追问今天中国文学理论的最大尴尬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下事实:即当我们谈论文学越多时,我们离文学真实就越远。文艺理论工作者励精图治地“言说”非但末能使中国文论从低谷中走出来,反而使它进一步滑向了抽象概念的深渊。知识论哲学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割不断、理还乱的影响。五四以后东渐至我国的知识论哲学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乃至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冲击。物我两离,主客二分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在各大大小小的文献与日常行为中比比皆是。我国传统的生存论文学理论面临着灭顶之灾。工具理性、“技术替代论”充斥泛滥了整个文学领域。对知识论哲学有着深入研究的俞吾金先生曾对知识论哲学做过如下判断:“二千多年来,西方文化一直在知识论哲学的旧靴子中打转。知识论哲学规约着人们的伦理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把整个文化生活淹没在抽象的概念之中。主要是借助于上世纪和本世纪的少数伟大的思想家的卓越洞察和批判力,西方文化才得以从知识论哲学窠臼日中超拨出来,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寻求意义的世界。”[6]超越知识论,是时代的命题。同样如何使中国文论超越知识论迈向意义的世界,是生存论文学理论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去思的问题。
人生活于中的不是一个知识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价值与意义的世界。但是“知识作为权力”为基础得以动作的文论似乎“理所当然”地把世界解读为一个知识的市场。因此,活生生的生活,意味盎然的生活体验被一套(乃至一大套)精致的抽象概念“抽象”地抽取与把握。人——文学——社会——文化——政治的理论范式几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范式”,亦几乎渗透到人文学者的潜意识之中。这种理论范式必然地以追求权力文化的合法性为目的,因此,中国文论不得不成为一种教条,而将生存价值的思拒之门外。生存是具体的活灵活现的,当然也是充满苦难的,貌似威严的抽象要领无论多么精致与美妙都无法透视生活的激情与萧瑟。惟有审慎地拒绝那些因抽象而显得中庸的东西,伟大的思才能有“路”可来。
中国文论话语权力的失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我们“母语”的汉语无法言说我们的生存样式和诗性意义。中国文论的拯救之路是从西方“存在论”处借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使中西方文化和诗学以不同的路径走向一种更高层次的融合,使中西文化和诗学在更高境界上向各自能够通达存在时意的原初“母语”的回归,进入“逍遥”之境,这是中西方文论的共同前景。
收稿日期:2001-02-02
标签:存在论论文; 失语症论文; 知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文学论文; 认识论论文; 现象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