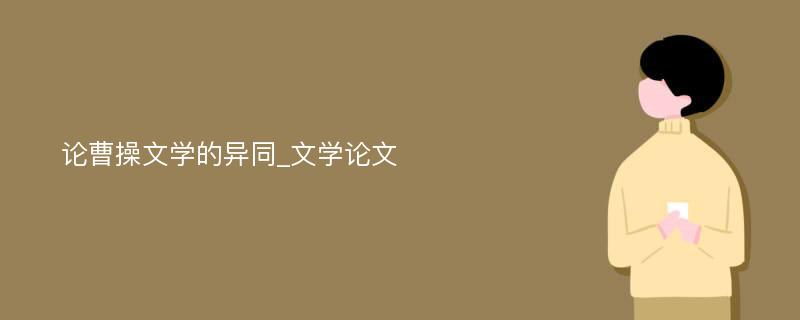
二曹文学观异同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曹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曹丕曹植文学观的异同,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有过这样的概括论述:
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这几句话主要针对二曹的文学价值观,并着重分析了曹植的现实心态,认为他们的文学意见其实是貌离而神合。对照历史事实,应该说鲁迅先生的这一评价是极其深刻、极为准确的。然而,由于先生未对二曹的文学观展开全面的分析比较,迄今人们对这一问题还存在模糊认识,有人视其为绝然相离,有人则看作完全相同。本文即从文学与文学家、文学创作要求、文学价值三个方面,对曹丕曹植的文学观念作较全面的分析比较,以图达到对古代作家及古代文学理论的较准确把握。①
一、文学与文学家
从文学创作的实际发生过程看,文学作品的形成产生必然要依赖于文学家的首先形成产生,因此,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明显的密切的联系,而且对这一联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揭示和探讨,也一直是文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涉及文学本质及创作规律的文论,都要首先解答这一问题。曹丕曹植也尽可能明确地阐述了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钧,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这里所谓之“气”具体何指,人们还多有争议,但“气”必然与作家有关,这一点则几乎无歧异。而曹丕说“气”又具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独特性和个体性,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作家才情和个性的代名词,于是文学作品不仅与文学家密切联结,而且这种联结实际上便是通过作家对某种独特生活的独特领悟和创造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其实即是作家自身具有的这些颇具特色的内容,文学作家就是决定、影响文学创作的主要因素。而且在曹丕看来,创作主体才情个性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作用更突出地体现在作品的结构形式及风格特征上,因此,他在同篇论及建安作家时,说徐进幹 “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在《与吴质书》中又讲“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不同的人擅长于不同体裁和题材并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质,都与其自身的气质才性直接相关。曹丕这种从文学家天赋的气质、个性、才能来评论作品风格的批评方法,显示了他对文学本质以及作品与作家关系的独到理解,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曹丕之前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与作者的关系问题实际也已有较明确的认识,如“诗言志”说和“文德”说就分别代表了文学反映作家心志情态、作家须有良好个体修养这样两种观点。然而,在此漫长时期里,文学所言之“志”基本是受礼仪规范严密监控、为天理人道浸泡了的集体意志,没有多少个人的色彩。而“文德说”所反映的作家品格对创作的影响,也主要指道德品质的影响作用,作品地位的高低也常常随品德评价而分为“君子”之作和“小人”之作。如王充说:“德弥盛者文弥繁,德弥彰者人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②整个文学创作从内容到风格,都被视为一种伦理道德的自然映射过程,而作家的个性特点以及特殊的技巧才能,则几乎未被考虑。所以,曹丕“文以气为主”观点便具有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充分尊重作家独创性的文学自觉意义。
与曹丕相比,曹植对文学创作中作家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似乎不很突出,但他散布于各处的思想同样表达了一个观点:文学是作家的一种独特创造。他首先认为,文学创作的动机源出于作家对人、事、物、景等现实生活的感悟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触类而作”。③他的许多作品在“序”中明确说明是因某人某物某境有感而写,这实际已隐约透露出对创作主体因素决定作用的认识。其次,曹植在各种场合也表现过对才情、学识、想象力等因素的赞赏和倚重态度。《三国志》本传记载,曹操曾怀疑他是否请人代作文章,曹植回答:“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于慷慨陈辞中可见他对自己创作才能的自信和倚重。同时,他从自己南北随征、东西游涉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无尽裨益中,也体会到了积学阅历对作品的影响作用,因而盛赞王粲“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④在《与杨德祖书》中称:“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另外,他也描述进行想象活动时的感受“独驰思乎天云之表,无物象而能倾”,⑤表明他已开始对想象的作用及特点予以注意。创作动机关涉到作家的主体心理活动,而才性、阅历、学识、想象则直接属于作家的个性结构因素,所以曹植实际上与其兄一样,也是十分尊重作家个性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的。只不过,他涉及的问题比曹丕更具体,但表达的形式没有曹丕那样概括明确。
二、文学创作要求
与文学是作家个性情志的创造性表现这一认识相联系,二曹对文学创作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具体要求。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其所归纳的“四科八目”的风格进行比较时,提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丽”在这里标示的是作品的整体特点,但从根本上说,它又要落实到语言色调上,从而“诗赋欲丽”的创作要求就是,充分运用富于色彩和音响效果的词语,烘染出一个华丽动人的艺术氛围,即给人、物的色、音、形、貌等方面加施一些富有动感的特征,使其更具形象可观性和美感想象性。这是因为色艳、响繁、形动、貌丽的事物,比之色淡、声清、形静、貌常的事物,未必更富审美蕴含性,但往往更易调动人的听、视觉活动,更能令人恍入一个缤纷璀粲的艺术境界。比如人们向来指斥艳画淫乐“不堪入目”,“不堪入耳”就正好说明它们最容易入目、最易于入耳。也正由于“丽”有如此之魔力,崇尚“诗言志”及讽世劝谕原则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对它始终很警惕。它害怕人们为华丽语言所创制的乐园所迷惑,去作自由无拘的心意驰荡,反把劝戒教化的意义抛得精光。古代文学理论尤其认为对人物形貌的着色绘彩,更会令人见色起淫,导致人心涣散,男女伦序失常。这就是人们一直推崇《国风》好色而不淫又放逐郑卫之声的主要原因。如此态度在对待汉大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所作的宫苑、游猎赋,极力铺写宫苑之弘丽、宫女之秀丽与物产之富丽、场面之壮丽,令人仿佛身入其境,又恍惚神驰天外。这把古代文学理论家要文学使人们心意回收的初衷打得粉碎,比如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本来应该规劝汉武帝停止媚神求仙,但由于文章“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武帝读了之后“反飘飘有凌云之志”。⑥于是,许多人便竭力予以制止和匡救,扬雄、班固、皇甫谧、挚虞等人相继抨击否定汉大赋,共同谴责丽辞侈语悦耳目、迷心志的“罪行”,甚至连颇有背叛精神的司马迁也认为讽谏作用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责任。他们普遍不满于丽辞对教化作用的湮没,又不甘退回到质木无文的起点,便想了一个对“丽”加以约制的办法——以《诗经》的“好色而不淫”为原则,既保留“丽”又坚决清除“淫”,此即“丽以则”。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对语词色彩的态度实际也反映了对文学价值作用的认识,而对丽辞侈语的严密防范,显然只能限制文学创作的手脚,扼杀文学发展的动力。因为文学从最初级的意义上讲是要让人观赏的,只有人的听视觉等感觉器官受到刺激,方可引起心灵的颤动,因而,当曹丕张起“诗赋欲丽”的大旗,从理论上放纵丽辞的运用时,他也就表现出了对文学以美、以悦耳悦目为基本价值的朦胧意识,并在不知不觉中解除了束缚文学发展的陈旧铁链。
曹植对文学创作中语言色调的运用,也没有形成多少理论的表述,但从一些零散的点示及他的整个创作情况仍然可以看出他与曹丕观点上的一致。他在《七启·序》中讲到该文创作动机时,就称枚乘、傅毅、张衡、崔骃等人的“七体”之作“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说明他是提倡并追求对华丽词藻的运用的。在《酒赋·序》又讲:“余览扬雄《酒赋》,辞甚瑰伟,颇戏而不雅,聊作《酒赋》,粗究其始终”,自然也是肯定扬雄对瑰丽语词的奇思妙用。《与吴质书》说吴质的书信“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申咏反覆,旷若复面”,于总结文章风格中也饱含赞赏之意。至于曹植在创作中对瑰奇华美词语的运用,更是达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特别是像《美女篇》、《杂诗·南国有佳人》、《洛神赋》等诗赋,把人物形貌描写得光彩照人、艳丽非凡。他的作品还多用幻想、比喻的手法,开拓出广阔自由的意象天地,再加以对偶、炼字等方法的运用,使语言风格整体上形成了“丽”的特点。因而,历代评价他的作品几乎都少不了这一条,如吴质曾叹其“文采之巨丽”⑦左思慕其“擒翰则华纵春葩”,⑧《诗品》说他“词采华茂”,《艺苑卮言》甚至惜其“辞太华”。
所以,在对待文学创作的具体要求上,曹丕曹植共同提倡并强调词采之华丽。若说有不同,只在于曹丕的观点主要以理论概括的形式提出,而且更富有比较勇敢的突破精神,曹植则更多地在创作中去运用,以创作来体现,因而观点的鲜明程度不及其兄。
三、文学的价值
对文学价值或作用的认识,同样是关系到认识文学本质规律的重要问题,而二曹文学观念在文面上的最大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因此,分析他们在此问题上认识的异同不仅十分必要,也须格外审慎。
对于文学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曹丕是站在治国传人的高度予以肯定的。他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其意即谓文章(包括文学)是有着经世教化和传人扬名的双重积极作用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把曹丕的这一认识视为对文学地位及作用的空前提高与肯定,并进而当作文学自觉的标志。这其实是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简单因袭,也是对鲁迅先生有关论述的严重曲解,无论从文学自身的真正价值来看,还是就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曹丕这里所总结的文学价值作用,仅可说是对其作用与价值的肯定,但还不是其真义的揭示。因为文学固然有助于治国济世,也能够使作者的名声随之传于久远、达于不朽,但这些仅仅是文学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是外在价值部分,眼光只盯在这上面,势必会使文学背上沉重的外在负担,最后发展为毫无生气的死躯怪胎。因而,它永远不是文学自觉的标志。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开始逐渐廓清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迷雾。
曹植对文学与作家的关系、文学创作要求的认识都比较含混、笼统,关于文学价值及作用的论述似乎要明确些。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这与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相比,似乎是极力否定和贬抑文学的作用与地位的。实际的情况则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识。
第一,如鲁迅先生所言,曹植成功之处是文章,而他所追求的目标则在政治方面,出于创作得意与政治不得意这两种心态,很自然地说了“文章无用”的话。就创作成功而踌蹰满志这方面讲,曹植诗文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结撰艺术,都堪称当时文坛第一,尽管刘勰曾对人们扬植抑丕表示不满并力行匡纠,但就作品的流传情况看,曹丕除一首《燕歌行》外其他多不为人所提,而曹植的作品则多被人捧为佳篇并广泛流传,所以,钟嵘《诗品》仍然将曹植列为入上品的建安三作家之一,而且置于刘桢、王粲之上。曹植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功加上他恃才傲物的性格,就很自然地要表现出对文学似乎是不屑一顾的姿态。这实际也是中国文人的一个常见现象。看汉代扬雄视汉赋为“雕虫小技”,固然有幡然改悔之意,但也不可完全排除他因世人对其赋作盛赞而产生的得意感。所以,曹植说辞赋是小道首先是出于得意的一种表面轻视。若就政治失意而心生不满这方面讲,虽说人们历来将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立言”视为“三不朽”之一,汉代以来也逐渐抬升其地位,但在当时文学还未普遍独立、人们对文学的作用还未真正了解的情况下,“立言”还仍然处于“立德”“立功”之次,文学创作实际上被作为“修身为政之余”来对待的,这一种普遍的人生价值观念,再兼以曹植实际上的文学创作成功与政治生活的失意,使他极其自然地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作为一生的追求目标,希冀以“立功”而达于不朽,于是,就把辞赋创作看作君子不为的小道了。但这并不表明他对辞赋作用的彻底否定,相反,倒正好暴露了他要提升其地位的急切心态,如果他已经知道了其兄关于文章地位与作用的论述,并在实际生活中看到文学确实有助于建经国之大业、成不朽之盛事,那么,我们想曹植也许就不会这么说了。
第二,既然曹植说“辞赋小道”是“违心之论”,是表面上对文学的否定,曹植实际上就该有他肯定文学作用的意见。搜检其诗文,情况确实如此。曹植首先很注意文学的托志言情作用,如他所说:“歌以咏言,文以驰志”。⑨他在《七启》中说“夫辩言之艳,能使穷泽生流,枯木发荣,庶感灵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就已隐含了对文学感荡情志作用的认识。《赠白马王彪·序》谈该篇创作原因说:“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解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客观上也揭示了文学排遣、渲泄情感的职能。另外如“何以赠终,哀以送之,遂作诔”,⑩如“铭以述德,诔尚及哀”(11)等都是表达这一意思。其次,曹植也很关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文人驰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12)他在《画赞序》中说:“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忠臣孝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何如也”。这里虽然论的是绘画的认识教育作用,但依据诗画同源、诗画同理的艺术原理,同样也可以看作曹植对文学作品的教化经世功能的认识。他以蝉、神龟、槐、芙蓉等为题作赋,固然是自喻自况,但其中显然也有劝戒讽谕之用意,如《柳颂序》所道:“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所以,曹植并不是把文学看作完全无用的,相反则是很看重它的固有功能的。
曹丕曹植关于文学价值与作用的认识,从本质上看并无矛盾或明显的差异。曹植说辞赋无用之小道却又指出其言情教化作用,这只能更显示他复杂的心态和不安的心灵,而他这些观点既包含了对文学内在价值的揭示,也混进了对文学外在作用的偏爱,揭示内在价值是他区别于曹丕的进步,偏爱外在作用则是他苟同于其兄的不足。因此,在此一点上,说二曹毫无差别固不符合事实,而认为他们绝然不同同样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二曹的文学观念绝对对立和完全混同都是不正确的,他们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相同的是基本认识上的几乎一致,不同的是某些枝节上或表现形式上的偏全与明暗,因而是大同小异。通过这种分析理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启示:
1.曹丕的文学观念以明确的、概括的理论形式提出,显示了他一个帝王兼理论家的特点,曹植的文学观念以隐约的、零散的谈语形式呈现,更多的是通过具体创作实践来展示,这体现了他一个蕃侯兼作家的风格。在此意义上,二曹文学观念的比较,也可以说是帝王与蕃侯观点的比较,理论家与创作家观点的比较。
2.曹丕曹植关于文学的某些理解,比如尊重作家的个性创造性、提倡作品华丽可观等,的确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个人的果敢,而他们对文学经世度人作用的珍重与偏爱,又同时表现了惰力的顽固和个人的庸陋,这种复杂现象再一次具体展现了历史渐进性和人类社会发展中个人作用的有限性。
注释:
①本文在写作中,参阅了卢佑诚《曹丕文学价值观新论》(载《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部分材料则取自于拙作《〈典论·论文〉文学贡献新论》(载《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及合著文《略说曹植的文学观》(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②《论衡·书解》
③曹植:《前录自序》
④(10)曹植:《王仲宣诔》
⑤曹植:《七启》
⑥《汉书·扬雄传》
⑦吴质:《答东阿王书》
⑧左思:《魏都赋》
⑨曹植:《学官颂》
(11)曹植:《卞太后诔》
(12)曹植:《娱宾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