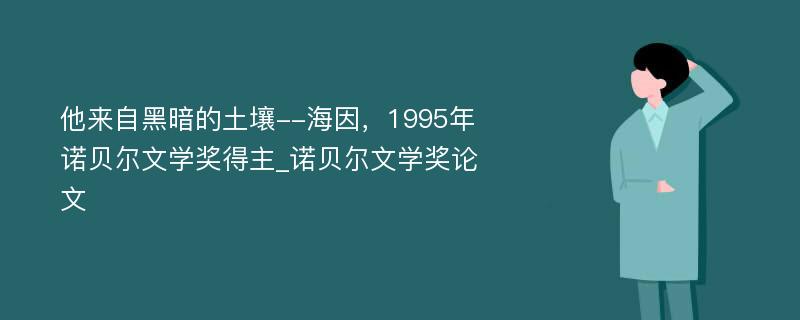
他从黑暗的泥土中走来——199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泥土论文,奖得主论文,黑暗论文,年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希内得奖,是人们意料之中的。甚至可以说,是期待之中的。199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瑞克·沃尔科特当年就曾表示,应该得奖的是希内,而不是他自己。至晚自80年代以来,山姆斯·希内就已被公认为“自叶芝以来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也是当今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
他是从北爱尔兰黑暗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
千百年来,那里的人们一直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默默地咀嚼着从冻土里挖出来的土豆。只是到了他这一代,人们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他,山姆斯·希内(Seamus Heaney),1939年4月13日出生于德里郡毛斯邦县一个虔信天主教、世代务农的家庭。6 岁那年进入阿那霍瑞什小学。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被乡里的长辈们尊称为“学者”。不过,他受的是正规的英国教育,学的是英国语言和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染。希内至今还能记诵许多他们在上学路上大声唱念的歌谣。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你的土豆干了么,
可以挖了么?”
“把铲子插进去试试”,
脏脸麦克基根说。
这就是他最初所知的“诗”。他说当时只是唱着好玩儿,并不懂其中的猥亵含义。那些“诗”虽然格调不高,但生气勃勃,在乡间学童中间广为传诵。他们无需死记硬背。
当然,还有被迫死记硬背的诗。11岁的希内已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拜伦和济慈的诗作了,但对其意义仍不甚了了。他后来回忆说,这些选自英诗经典作品的“文明语言”是填鸭式的硬塞给他们的。它们的内容丝毫不反映爱尔兰人的生活经验、语言也不似爱尔兰民族语言那么生动感人,所以读起来索然寡味。诗歌课简直就像教义问答。
那时,他还受到第三种诗歌训练。那就是当亲戚来访或孩子们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希内常常被叫出来背诵一首爱尔兰爱国歌谣或西部叙事诗。这些正统的口头文学虽说没有童谣中的低级趣味那么引人入胜,却也没有拜伦和济慈的崇高深奥那么令人生厌。这使诗歌在这个农民家庭中有了一席之地,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
12岁时,希内升入德里郡圣寇伦伯学院寄宿学校。从此,希内渐渐开始在以前他所厌恶的英诗的海洋中轻松地游泳了。莎士比亚、乔叟、渥兹渥斯、霍普金斯、阿诺德、罗伯特·弗罗斯特等等,这些大家都在课程安排之列。但是,希内只是在课外自己阅读时才真正体验到顿悟的快乐。
中学即将毕业的时候,希内熟悉了拉丁语诗歌。他开始写一些摹仿之作,常常在课堂上让同学们传阅格律工整的拉丁语六音步诗句。
在大学期间,他又对古英语和中古英语头韵诗以及马娄和韦伯斯特的戏剧发生了浓厚兴趣。这时期他写了一些诗,但据他说仍然是“极具摹仿性的”。1961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英文系。
可以说,希内自童年起就体验着“没文化的自我”和“有文化的自我”的人格分裂。没文化的自我“拴系在小山丘上,埋藏在那里多石的灰色土壤中”,而有文化的自我“慕恋‘列王’之城/在那里艺术、 音乐和文学才是上品”。〔1〕这种根源于文化的“人格分裂”确乎给他带来迷惘失落之感,但更重要的是为他的诗创作提供了独特的题材和风格。循着希内创作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有一条“寻根”的轨迹。他的根属于爱尔兰民族。与许多民族的先觉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同胞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最终归结为一种更深沉的爱。他在1990年9 月致笔者的信中写道:“这些诗的作者(希内自称)是50多年前在山地乡间的一个农场上开始生活的。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基于对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的记忆。”
大学毕业后,他在一所中学任教。这时他才开始阅读帕特里克·卡文纳、特德·休斯、R.S.托马斯、约翰·蒙塔古、托马斯·金塞拉、理查德·墨菲等现代爱尔兰和英国诗人的作品,并且从中找到了把他所学的英国文学传统和在德里郡乡间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的途径。希内的“土豆”成熟了。他写道:
土豆发霉的冰冷气味、砸碾潮湿泥炭的
噼啪咔嚓声、锋刃在根茎上
草率的割痕在我头脑中苏醒。
可是我没有铁锹,不能跟他们一样干。
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
停歇着矮墩墩的钢笔。
我要用它来挖掘。
这是希内的第一本诗集《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1966)中的第一首诗《挖掘》的最后两节。这首诗展现了诗人与其家庭传统的关系。坐在窗前写作的诗人听见窗外老父亲掘地的声音,回忆起童年时看父亲挖土豆和祖父切泥炭的情景。由此他意识到传统的农家生活渐渐离他远去,但是他要用笔继续挖掘,去认识自己的过去,发现与父辈共同的存在,从而把自己与家庭乃至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在这本诗集里,诗人回顾了自己从农家子变成诗人的成长过程。童年的乡村生活经历是贯穿全书的中心题材。例如,标题诗就以客观具体的描写暗示从童年跨入青春期的心理突变,同时也暗示人与自然的告别:作为小学生的发话者酷爱养蛙,然而有一天他在水坝下边看到大群发情的牛蛙,形象猥亵,于是顿生恶感,从此新的意识觉醒了。没有新的自我诞生,旧的自我是无法认识自身真面目的。希内并不否认现在,尽管他把目光投向过去。过去的他曾经“像大眼睛的纳西色斯,凝望泉眼深处”, 而现在“我写诗/是为了看见我自己,让黑暗发出回声”(《个人的诗源》)。诗集中的这最后一首诗似在表白:诗人写作犹如童年游戏,是出于自恋。通过诗,他似乎实现了“自我对自我的显现,文化对其自身的回复”。〔2〕
为了进一步探寻自己的根源,希内向着爱尔兰黑暗的土壤深处挖掘。第二本诗集《通向黑暗之门》(1969)向发达社会的读者敞开了一幅幅陌生的图景:喑哑的土地,沉睡的泥沼,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向大自然之神献祭的野蛮仪式等等。也许有人会说,在这些图景背后可以感受到浑沌未开的自然性灵和原始生命力的脉动。的确,这本诗集中有以写实和象征笔法描写的纯为传种接代而进行的动物交配(《非法者》)和为恢复生命之源而做的人工努力(《春之祭》)。但是,从诗人客观冷静的笔调里我们又能看出多少赞美之意呢?“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扇通向黑暗的大门”(《铁匠铺》)。这黑暗是现实,却古老得像神话。作为从中走出来的诗人,希内对它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要重新走回去,记录它的过去和现在,以尽自己作为爱尔兰诗人的传统职责。
1966—72年,希内在母校女王大学任现代文学讲师,亲历了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为争取公民权举行示威而引起的暴乱。他的诗歌观念因之有所改变:“从那一刻起,诗的问题便从简单地获取令人满意的文字图像转向寻求足以表现我们的苦难境遇的意象和象征了”。〔3〕第三本诗集《在外过冬》(1972)便是这一寻求的结果。这本诗集中的作品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探索了当今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敌对的深层背景,而没有流于肤浅的政见表白。例如诗人有感于不同宗派的人们划地而居、互不往来的现象,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和地名的诗,如《阿那霍瑞什》、《图姆》、《布罗阿厄》等。这些诗不仅描写地方风物,而且考证了方言地名的原义,从而揭示了原始居民对自然的认识。希内认为,这些诗有助于统一他对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使他一方面忠实于英语的特性,另一方面忠实于自己的乡土本源。与地方有关的有两首以北爱尔兰特有的泥炭沼为题材的诗。《托伦人》反映了古时候以青年男子投入泥炭沼向大地女神献祭的风俗。《泥炭沼地》则描写泥炭沼能够保持落入其中的物体(包括人的尸体)长久不变质的特性。泥炭沼把过去与现在、神话与现实联系了起来,成为爱尔兰民族意识的象征。希内的诗也和泥炭沼一样,成为储存爱尔兰苦难历史的“记忆库”。处在动荡的政治旋涡之中,诗人不愿宣称自己属于哪一派,而是坚持站在艺术家的高度,以克制的态度目击着这“盲目的土地”(叶芝语)上所发生的一切。
然而诗人却很少被人理解。随着局势的变化,舆论界开始对希内“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作品感到不满,而呼吁他拿出反映当前恐怖动乱的作品来。希内虽然坚持诗人应有其独立意志,但确也感到必须说点儿什么的压力。于是,诗集《北方》(1975)便应运而生。这本诗集分为两部分,分别由不同类型的诗作组成,一为象征的,一为白描的。第一部分的框架建立在分置首尾的两首取材于古希腊神话的诗作(《安泰》和《赫克勒斯与安泰》)上。安泰是大地之子,被赫克勒斯从地上举起而击败。这一方面暗示殖民者对爱尔兰的入侵,另一方面暗示公众舆论对个人意志的压力。夹在这两首诗中间的诗作叙述了从古到今爱尔兰及北欧充满侵略和暴力的历史。第二部分则是站在天主教徒立场上对北爱尔兰时局的“解释”。这表面上有些迎合公众舆论的意味,但是谁又能肯定诗人的“时事报导”不是违心之言呢?据说伦敦的评论家就几乎无人能弄清这些诗中对时局的观点究竟如何。诗集中最后一首诗泄露了诗人的隐情:“我不是拘留犯也不是告密者;/而是一个内地移民, 变得头发长长,/心事重重;一个山林流寇/自大屠杀中逃脱”(《曝露》)。这既暗示了希内的非政治倾向,又透露了他对北方悲剧命运的绝望和逃避意图。事实上,在这本诗集问世之前,1972年,诗人已偕妻儿南迁至爱尔兰共和国威克洛乡间暂住。现在,他们定居在首都都柏林。
远离动乱的平静生活使希内得以重新思考艺术家的责任以及诗的功用等问题。是服从社会需要,去接触现实,还是走自己的路,去追求艺术——这类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他。诗集《野外作业》(1979)虽仍充满诗人的疑问,但作为对政治压力的反动,其中显示了艺术至上的发展趋势。在开卷第一首诗里,诗人就暗示不再受黑暗的历史困扰,而追求艺术的独立和自由的愿望:“休憩/在晴光里, 像自大海漫来的/诗或自由”(《牡蛎》)。诗人又退回到个人经验的世界里, 眼光从过去收回到目前,乡间和家庭生活的见闻和感受充当了诗集的主要题材。处于诗集中心位置的十首《格兰莫尔十四行诗》以其古旧的乡野意象给人一种远离现代都市的闲适恬淡的印象:“如今好日子可说是在田野里穿行/艺术是新耕土地的/词形变化表。”然而,田园生活可能只是一场短暂的美与和平之梦,“我们露湿的睡梦中脸上的小憩”,因为诗人不可能一下子忘却刚刚离开的那片土地上持续百年的黑暗现实。诗集中还收有一组关于恐怖动乱的作品,它们不同于以往的应景之作,而多写对在动乱中受害亲友的悼念哀思,是激于义愤的真情流露。也许他对英国诗人奥登所说“诗不会使什么事情发生”有同感,相信艺术无法直接干预行动,因而保持它的独立性,只对事情的结果作评注;以期对历史有所交代。这本诗集标志着希内的诗艺开始走向完美,个性已经成熟,分裂的人格已经趋向统一。希内作为英语世界当代重要诗人的地位从此确立。
嗣后,他又陆续出版了《苦路岛》(1984)、《山楂灯》(1987)、《幻觉》(1991)等诗集。这些诗基本保持了希内的一贯风格,仍旧忠实于他所谓的“事物的纹理”。但是诗人逐渐更多地把幻想和抒情的因素与实际经验和记忆揉合起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评论他的作品“具有抒情美和伦理深度,使日常的奇迹和活生生的往昔得到升华”,可谓切中肯綮。
希内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他的成功也许可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凑巧所致。在英国诗坛上,继40年代新浪漫主义的滥情狂热和50年代运动派的经验主义以及60年代休斯、普拉斯等的极端主义之后,希内朴实平易的诗风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他的作品不仅一开始就受到评论界的注意,多次荣获各种文学奖,而且一直深受普通读者的欢迎,销路甚畅。这种情形在过去和现在的西方诗界都不多见。
80年代以来,希内应聘于哈佛、牛津等著名学府,教授英语文学,在国际学术界和文艺界均享有很高的声誉。
注释:
〔1〕〔3〕见布·莫瑞森:《山姆斯·希内》,梅修恩出版公司,1982年版。
〔2〕见P·R.金:《当代九诗人评介》,梅修恩出版公司,197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