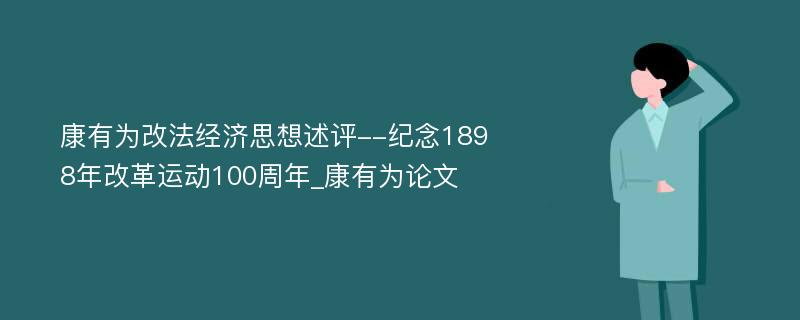
评康有为变法图强的经济思想——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戊戌变法论文,康有为论文,图强论文,周年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维新运动不是少数历史人物的神来之笔,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背景。具体说来,从经济角度上看,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的彻底破产,封建统治者在勒索商民“捐输”的同时,不得不放弃李鸿章等禁止民间使用机器的规定,使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要求。从思想角度上看,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文化,特别是社会进化论被引进,且维新派人士创办了近代报刊,大规模地制造社会舆论,为戊戌维新的到来准备了思想条件。从政治上看,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危机加剧,加强疯狂地进行争夺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悲壮的一幕。
尽管康有为和绝大多数近代历史人物一样,在他的晚期跟不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思想由进步退化为保守、落后,但是在整个变法维新运动期间,他的思想是先进的,是变法维新运动的一面旗帜。本文拟从康有为经济思想角度,从康有为的变法图强,对洋务派的否定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和目标三个方面,阐述康有为在变法维新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一、变法图强的思路:从变器、变事、变政到变法
针对当时中国人的国贫民弱的状况,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认为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农商业,广开利源,否则,“其穷至是尚不思所以变计,是坐而待亡也。”(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农工商总序》,《日本书目志》卷七,第2页。)那么, 如何进行“变计”呢?在康有为看来,“变”有四个层次:变器、变事、变政和变法。“购船置械”,引进列强先进的机器设置,达到船坚炮利的目的,这只能算是“变器”。“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物,曰学堂,曰商务,”(注: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戊戌变法》(二), 第215页。)这些也仅仅是“变事而已”。变事比变器范围要大,力度要深,但两者只是在经济领域作文章。康有为通过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变事是必要的,但不是最根本的,而最重要的变革必须从政治领域着手。但是,“改官制,变选举”,即进行小范围、局部的政治改革,这仅是所谓的“变政”,还不是康有为心目中的变法。只有“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才能称得上是变法,才是“存亡强弱第一关键”。(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转引自《历史研究》,1980年3月,第170页。)也只有实行变法,才能“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亿臣民之心态,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风从,故为政不劳而易举”,(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转引自《历史研究》,1980年3月,第175页。)才能抓住当时中国的关键问题,争取国家富强的问题才有希望解决。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只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主张“制炮造船”,以此来抵御外国侵略;魏源则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光辉思想,要求仿设外国新式军事工业,并且“从仿造新式枪炮联想到制造其它民用产品”,(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中华书局,第11页。)他们只能算得上是“变器”。洋务派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主张开矿设厂,两者的区别是洋务派主张这些企业要么官办(军事工业),要么官督商办(民用工业),需要政府来插手,而且洋务派依靠国外势力,有买办性质;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却基本上主张新式工业企业应由民办,“公家不过而问”,这些只能算得上“变事”。郑观应长期参加官督商办的实际工作,逐渐认识到封建官僚势力的“保护”是靠不住的,因而他提出“开议院”,设“商部”的主张,试图为资产阶级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保护其经济利益,这只称得上所谓的“变政”,算不上变法。不唯如此,康有为已清醒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若仅补罅漏,弥缝缺失,则千疮百孔,顾此失彼,连类并败,必至无功。”(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第178页。)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则亡”,(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第179页。 )疾呼要变就必须“全变”。(注: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麦仲华编:《戊戌奏稿》(下)。)
为了实现“全变”,康有为向光绪建议,通过建立“制度局”来“统筹全局,以图变法”。(注: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麦仲华编:《戊戌奏稿》(下)。)由制度局总变法之纲,再设十二个与原有的“部”、“寺”相当的分局,即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游会局,矿务局,陆军局和海军局,分担变法之事。为了使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康有为主张选拔一批同情和支持维新的人才,来担任制度局和所属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制度局就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戊戌变法》(二),第197页。) 成了名副其实的维新内阁了。维新派企图通过这种另建领导班子,来抵制旧势力与旧机构对变法的阻挠,使变法能够顺利地进行的做法,当然会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击,军机大臣们就明确表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53页。)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 康有为这种试图回避守旧势力的做法当然是行不通的。
康有为回避矛盾的做法,包括他对按照他所设计的维新效果,即所谓“迟以十年,诸学如林,成才如麻,铁路罗织,矿产洋溢,百度举而风俗成,制造极精,创作报众,农业粗新,商货四达,地无余利,人有余饶,枪炮船械之俱巧,训练驾驶之俱精,富教既举,武备亦修”,(注: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二),第186页。 )都表明康有为对守旧势力的顽固和中国的国情认识不足,有点盲目乐观。而且,康有为的“全变”主张的实质,只是在“好皇帝”的框架下实行资产阶级改良而已。但是,康有为清楚地认识到经济改革(变事)与政治改革(变法)之间的关系,只有变法才能“富国”、“养民”的认识,已经比他以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高了一大步。
二、否定洋务派:从局部到全盘的否定
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洋务派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许多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对洋务派的反动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对洋务派还存在着幻想。因而他们对洋务派的否定是局部的、枝节的。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典型的态度是反对洋务派的官办;但对民用工业所采用的官督商办,许多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存着幻想。例如,王韬站在维护私人资本利益的立场,认为“开掘煤铁五金诸矿”及“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注:王韬:《重民中》,《韬文录外编》,第22页。)都应民办。但是,王韬对于非军事工业所实地的官督商办,还抱有很大幻想,希冀这些企业得到洋务派官僚的保护,就可使“衙署差役”和“地方官吏”不敢“妄行婪索”。郑观应早期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务制度也进行宣传鼓吹,把其描述成为最为合理的企业制度:即如果新式民用工业“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侍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而官督商办可以使“二弊俱去”。(注:郑观应:《开矿》,《盛世危言》,初编,卷五,第3页。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种幻想,表明还没能通过客观实践对洋务派的政治获得较深刻的认识;另外,洋务派的买办的、垄断的本质还没有充分的暴露。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官办、官督商办逐渐显示出其狰狞面目,资产阶级改良派尝够了被“保护”的滋味,他们对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的政治有了切实的了解。由于官办企业主要是军事工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无法涉足,他们所经营的是民用工业,因此,焦点逐渐集中在官督商办企业,对官督商办政策的态度,由初期的称颂,转而对官督商办提出了否定。严复就批评洋务派办了几十年企业,只是“糜无穷之国帑”,结果仍要“仰鼻息于西人”。(注:严复:《原富》按语,第509页。)郑观应参加许多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担当“总理”、 “帮办”和“总办”等高级职务,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盘剥商人有了透彻地了解,最终发出了:“名为保商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商因此不及人,为丛驱爵成怨府”(注:郑观应:《商务叹》,《罗浮侍鹤山人诗草》,宣统元年上海著易堂印,卷二。)的慨叹。他们对洋务派的看法,道出了洋务派的垄断的买办的本质。
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弊端提出了种种批评,要求将一切民用都要“纵民为之”,甚至有人主张将现有的官局也交商民经营。但总的来说,资产阶级改良派阵营中的意见并不是统一的,有些人并不否定官督商办,对官督商办的本质认识不清。比如经元善,他一方面批评洋务派所办企业,除电报、开除煤矿等少数几个外,“余均一败涂地”;另一方面,他又主张新创办企业时,可先借官款开办,等取得一定成效时,再招商股,交还官款。另外,由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与洋务派有千丝缕的联系,有的直接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对洋务派的批评不是直接,而是采取间接的做法。如薛福成仅从理论上论证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比洋务派的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优越,但未直接批评官督商办企业。这些都反应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与局限性。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的思想家们,对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提出了彻底的、全盘的否定。认为这些企业“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注: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1页。)因此,康有为主张, 除了发行货币和邮政仍由国家经营外,其余的一切工业,甚至包括军事工业,都应当“一付于民”,“纵民为之”,让老百姓自由经营。除此之外,国家还应废除洋商与华商不平等,即“洋商可以三联票免厘,而内商则百重抽剥”的税收政策;撤除“贫农工之源”、“损商之实”(注:康有为:《奏请裁撤厘金片》,《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66页。)的厘金制度; 消除“贫官暴吏虎狼而强食”的积弊。不仅如此,国家还应建立学会、翻译书籍、实行专利制度,在培养人才等方面给予奖励、帮助和保护。这实际上是主张自由放任的私人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中自由发展。
从上述的批评和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康有为对洋务派的本质——垄断的和买办的——有了较清楚地认识,从而提出彻底地、全盘地否定洋务派对新式工业垄断,大力发展自由的私人资本主义主张。“这是康有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较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另一重大的质的提高。康有为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当时条件的产物,是甲午战争后洋务派政策的破产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注: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下),第696页。)
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三大特点
在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康有为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相比,有三个明显的进步:在如何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康有为明确地提出了“富国”、“养民”十纲,比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更为完整;在发展的目标上,康有为提出了“立为工国”的目标,改变了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商立国”,以流通为中心,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目标;在论述发展大机器工业时,康有为提出了机器大工业对“开民智”的巨大作用。
首先, 康有为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 早在1984年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提出了“富国”、“养民”的十项主张。“富国”包括“钞法”、“铸银”、“铁路”、“机器轮舟”、“开矿”和“邮政”六项纲领;“养民”包括“务农”、“劝工”、“惠商”和“恤穷”四项纲领。不难看出,这十项主张实际上构成一个较为完整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钞法”和“铸银”是要求建立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银行制度;“铁路”、“邮政”和“机器轮舟”是发展新式交通运输业;“开矿”则更是制造业的基础和前提。上述三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关键、最基础的行业和部门。这里的“务农”与中国封建社会一再强调的“重农”不同,要求学习西方“讲求树艺”,建立“农学会”,(注: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 144页。)采用先进的机器和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了。“劝工”和“惠商”是按照西方列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验,“设考工院”、“许其专利”,设“商部”、“商会”,并且对“大会、大公司,国家助之”,(注: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6页。)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恤穷” 一方面要达到稳定统治秩序外,另一方面还要“择其所能,教以艺业”,(注:康有为:《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8 页。)达到为资本主义生产训练劳动后备军的目的。
在康有为之前,上述主张基本上被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到过。如黄遵宪论述了铁路的修筑“便生民,兴国产”,(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四,第21页。)其利无穷;按照日本开矿的做法,会给民众带来很大的利益,因此提出了劝工惠商。陈炽提出了“务农殖货”论,建议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另外,鉴于当时出现的镑亏,他还提出仿效英国,自铸金镑的主张。但康有为所提出的“富国”、“养民”十纲,比初期的改良派不仅系统,并且这些主张是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其影响不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可同日而语的。
其次,康康为明确提出了发展机器大工业为目标的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变化有一个清晰的主张:从抨击重本抑末的封建教条,到“恃商为国本”、(注:王韬:《遣使》,《外编》卷二,第56页。)“以商立国”,(注:郑观应:《商务》,《盛世危言》,初编,卷三,第9页。)强调流通的重要性,进而升华到以机器大工业为中心, 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期法家所倡导和推行的。自汉宣、元时期,桓宽的《盐铁论》成书之后,重本抑末逐渐被儒学化,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三大教条之一。这种保守的经济思想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更是成为反对新生事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多数都对重本抑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且提出“恃商为国本”、“以商立国”等与重本抑末以农立国相对立的观点。
由重本抑末转为以商立国,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传统思想教条,反映了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但以商立国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多寡取决于生产而不是流通。生产和流通这两个环节中,生产严格地制约着流通的规模。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这种片面的认识,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直观地看到西方船坚炮利,工业产品先进;海外贸易发达,对华贸易有巨额盈利,因此他们片面地将商业看成是致富之源;加之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知之甚少,因而他们无法对生产与流通、对资本主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初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视野也不是仅仅是船坚炮利。随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接触增多,资产阶级改良派逐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商业背后的大机器工业对国家富强的作用。薛福成认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注:薛福成:《振百工说》,《庸海外文集》,卷三,第40页。)已经在具体形式下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关系问题。郑观应所谓的“商务”、“商战”,其范围不仅限于商业,他也很重视大机器工业的作用,但“从总的方面来说,郑观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突出地强调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注: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下),第299页。)总之,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没有把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摆正,更没有把实现工业化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根本目标。
与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一样,康有为早期也没有摆脱重商倾向。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他提出还是“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注:康有为:《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45页。)的思想。但是, 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的贫富对比中,康有为认为当时已入工业之世界,而且是“日新尚智”的世界,如果清朝政府“以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6页。)那么,离亡国已不远了。因此, 康有为逐渐认识到发展机器大工业的意义,因此提出了中国应“定为工国”作为“国是”(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6页。 )的见解。这是中国近代最先提出的把中国“定为工国”的设想,表明康有为关于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作用的认识,已经明显超越了早期改良派。
最后,康有为除了极力论证发展机器大工业对增加一国财富、增加国民经济实力有作用之外,还认识到“物质大进”与“民智大开”是有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机器大工业对“开民智”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认为如果大力发展机器工业,一个国家就会出现“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6页。)。康有为明确提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 国尚工则日新日智”(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变法》(二),第226页。)的论断,认为如果中国在列强环伺的情况下, 依然墨守成规,把着“老本”不放,不积极发展机器大工业,则民众“必不能苟延性命”,而国家也无法保持完整,离亡国不远了。
康有为关于机器大工业对开民智的促进作用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在康有为以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们,强调建立和发展机器大工业重要性的不乏其人,但这些思想家们都是从物质角度论述这一问题,而看不到机器大工业对扫除守旧封建残余的巨大作用。正确地认识机器大工业与“开民智”的关系,是康有为经济思想高于其同时代思想家的又一个闪光点。
标签:康有为论文; 洋务派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