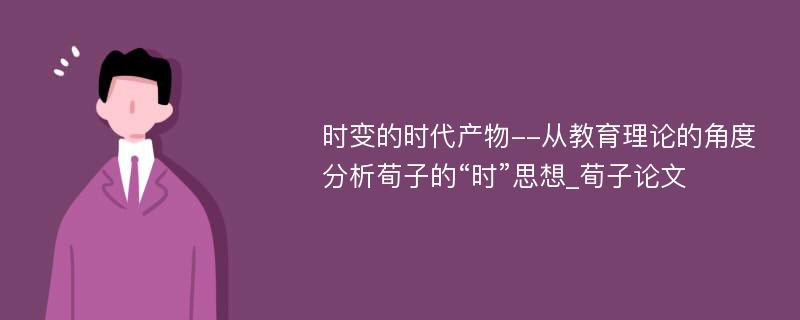
时中#183;时变#183;时积——教化论视域下荀子“时”的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子论文,视域论文,探析论文,思想论文,时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5-0063-08
教化的本质就是个体在这个现实当中让人的行为、思维、存在和他的善的本质和终极实体保持一致。对于性善论来说,由于人内心本有善端,只需修养以复明本性,而对于性恶论来说,却需教化来复返其初,这也是荀子和黑格尔所致力成就德性的必由之路。黑格尔以教化人性、抑制冲动在于回到人之初的自在的不善不恶的伦理境界,而荀子以礼乐涵养性情复归其朴的君子人格,因此其成德的思维可谓“异曲而同工”。荀子的教化理论源于其自身的情感自证,而礼乐本身缘情化性的特质与功能又赋予人矫情化性的德能。由于性本身不能自化,因而知性的德性教化只能在自然的情上用功而使其处于有所止的时中、时变、时积状态,在情感与理性、善与恶的冲突中实现自身与社会的相契与和谐。这一思维理路与荀子的知性性格一脉相承。
一、时中:德性教化原则的秩序确认
礼既为教化之纲,又要发挥主体的意志自由,在家庭、国家、社会的不同层面进行教养,从而达到礼的形上意境,对于人生而言,能够矫情养欲,规范行为;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能够序长幼、等贵贱、分亲疏而明人伦;对于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层面,以教化洗涤心灵尘弊,涵养伦理精神,提升道德境界。在不同的道德境遇中,对礼有所损益,因时而动,遇君则修臣下之礼,遇乡党则修长幼之礼,遇长辈则修弟子之礼,遇朋友则修辞让之礼。这就是荀子所谓的“中”或“中道”,也就是礼仪。中是礼的内在精神和原则,礼是中的外在表现和形式,故荀子曰:“曷谓中?礼义是也”(《荀子·礼论》)。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而不及,恰到好处。所以荀子把有益于理的事情称为“中事”,把有益于理的观点成为“中说”。其实,“中”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据唐兰先生考证,“中”在甲骨文中本为旗之类,后引申为中间之义。①至晚在西周时期,中间、中央之义已上升为一种美德,成为“中道”,是礼教思想当中一个具有独特内涵的范畴。在《周易》经文中也多次出现“中”,其中“中行”五见:
《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避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复·六四》:中行独复。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迂国。
《夫·九五》:苋陆夫夫中行,无咎。
参考西周初年的其他一些文献,这里的中行应该含有伦理的意义。中行即中道,依中正之道而行的意味。正如惠栋的《易经学》所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周易》经文中“中行”包含“中道”“时中”的思想,它把中与人事的吉凶祸福联系起来,以天道言人事,立中正仁道之极,建立起立静无欲的道德标准。后来《易传》在解释《易经》时,对其中所蕴含的“中道”“中行”思想加以发挥。《乾·文言》说:“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高亨先生注:“李鼎祚曰:‘庸,常也。’按庸由正中而来。正中者,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也。正中之言乃为庸言。正中之行乃为庸行。”②中,教人趋吉避凶的道理,要人行中道之德,达到崇德广业,有所事功的目的。其实,“中道”也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后来子思所作的《中庸》对孔子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是战国时期学者论述礼仪的一篇重要文章,说明中已成为礼的重要思想。《礼记·檀弓上》引孔子之言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这是说制礼的原则要符合中。《礼记·仲尼燕居》引孔子言:“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问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孔子曰:“礼乎礼。”由此可见,孔子对礼与中作了循环论证,说明孔子《中庸》在思想内涵上是一致的。荀子言“中即礼”与孔子所谓一脉相承。在荀子的伦理思想中,礼主分,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庸、中道思想,这说明礼并不是绝对地区别等级之间的差异,它在辨明等级的前提之下,又主张时中、权变,注重礼的灵活性,在等级差别之间找到一种中庸的和谐。荀子《儒效》云: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凡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
荀子《礼论》又曰:
故其立文饰也至乎窕冶;其立粗衰也,不至于瘠弃;其立声乐恬愉也,不至于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于隘慑伤生。是礼之中流。
文饰、声乐、哭泣、言说是人的情志与行动,中流、中事、中说是人的情感、意志所达到的一种无所偏倚、不过不及的状态,这种状态是礼对心灵的涵养和教化,涵厚人的德性,规约人的行为,使知、情、意三者相互涵容、陶养、化通才能达到。否则,人的情感将流于隘慑,声乐将流于惰慢,德性将流于卑俗。因而,中是一种行为处事的方式,是伦理的基本原则,是伦理的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中,也是行为的目标,体现人类对价值追求的源头和归属。荀子在道德教化中以中释礼,反映了礼为教化之纲,具全德之名,人的德性的形成是对礼规范的心灵体征、感悟,因而在礼德关系中,以礼释德,认为礼是社会道德生活和人道的最高准则。“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规矩是方圆的准则,无规矩无以成方圆,无礼则无以成人,礼是人道的准则,是人之为人的标准,礼规范德,体现德,合乎礼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荀子·王制》曰:“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一旦事亲、事兄、事上本根于礼,则这些行为便显现出道德理性的智慧,分别具备孝、悌、顺诸德。《荀子·大略》曰:“仁有里,义有门。仁,非其里而处之,非仁也。义,非其门而由之,非义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仁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仁如果不合乎礼的要求去做,就不能叫做仁;义,如果不合乎礼的要求去做,就不能叫做义,而在《劝学》中明确指出礼是道德之极,“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指出仁义不能脱离礼而独自存在,礼是决定仁义之为仁义的本质所在。《荀子·礼论》曰:“存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圣人君子的敦厚、大度、高尚、明察来自于遵循礼、实践礼的积累和施行呈现在个体身上就是德,实践先王之道以成就仁义忠节,就是实践礼以完成、完善仁义忠节诸德。荀子强调“礼义辞让忠信并举”,辞让忠信属于德,此处的礼仪应归于德。该篇又曰:“人之所恶者何也?曰:污漫争夺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污漫、争夺、贪利是邪恶行为,荀子列举之作为无德的象征,与之对应并形成鲜明对比的礼义忠信应该属于其反面——道德,更何况辞让忠信本来即为德。在此,礼显示出德的象征。礼不仅是道德之一种,而且还是包括诸多具体规范的人生大德,更是在诸德之中处于优先的地位。即是说,礼为德,又非普通之德,“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忠孝等是道德的个别,礼是道德的一般,是最高的道德。孔子在人生诸德中有标举仁为人生大德的倾向,孟子沿着这一倾向继续发展,凸现仁为人生最高之德,荀子便在众德中指定礼为统摄一切德目的最高理想。“很有可能是荀子受其所抨击的思孟学派的浸染,而在潜意识里接受其影响的结果。”③
荀子德礼的本质是个体与实体、单一物与普遍物的关系。礼作为全名的道德规范,是让受到教化的人的行为成为普遍规范的具性,使人的心灵具有普遍性的性质,能感受到人情的适中之处,不再污漫、争夺、贪利,而是变得宽广、舒展、理智起来。礼仪规范的作用就是把人们的心灵情感引入正常轨道,确认价值,获得对礼仪的体认,使人们知孝敬慈爱之情,辞让忠信之德,贵老长幼之伦,并内化于心形成仁德,表现于外形成义行,使个体在具体的境遇中表现为义之所在,行为合宜,情感适度。圣人制定礼乐缘于人情,人情是礼的根源,礼是缘情而作。荀子认为人之情莫过于生死,他说:“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杨倞注引郑玄曰:“称人之情轻重而制礼也。”这样,在礼与情的关系上,荀子总结说:“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荀子·礼论》)所以,荀子的礼,以人情的实际性质为基础,并注入了一种伟大的道德情感和人文感受,从而能把人的情感表现归融于其中,使之得到某种文饰。虽然人情不美,但是如果忽视礼之文饰,那么道德教化必然偏枯、僵死而行之不远。因此,口、鼻、耳、目、体的欲望必与情相对应,用以养口的有刍豢稻粱,五味调番;用以养鼻的有椒兰芬苾,睾芷香草;养耳的有钟鼓管磬,琴瑟竽笙;养体的有疏房、檖邈、越席、床弟、几筵,生活中的种种缘饰无一不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合乎人情的要求。“称情而立文”既是人性中审美的要求,也是制礼的出发点,满足了这个要求,就便于以文来规约情,使性与情经历外铄教化的过程,达到情与礼的相洽和谐。
因此,荀子所谓的礼仪规范相对于德性来说,绝不是一些干瘪的普遍行为规则,而是要能感发人们的道德情感,使之得到提升而文明焕彩。礼仪虽然对人情有所约束,但是这种约束不是窒灭人情,而是涵而化之,文以明之,使文与情得到很好的统一,才有价值上的合理性,这就是“文情理通”,只有这样,个体才能获得德性。从形上来说,荀子的礼又具有普遍性实体的性质,是整个的个体,又是一般的个别,它具有诸德的普遍性特征,内涵深厚、宽广,是个体精神的异化和观照,以分辨为形式,以仁义为目标,个体成就恭敬、孝弟、辞让、忠信之德就是分享了礼的普遍性的精神而异化为自身的德性品质。“先王之道,仁义之隆也,比中而行之”(《荀子·儒效》),礼实行起来中正恰当,是仁义的经纬蹊径,仁义作为一种抽象原则是虚而不见,礼作为规则则是实而可操,仁义贯穿于礼之中,依礼中而行就是对仁义的践履。礼是独立于性情之外的礼之理,具有道德理性的知性特征,这种知性不是脱离情感欲望的抽象理智,它的智能正好就表现在把可教化的本能情感和欲求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种可塑的、发展的普遍性的整体,故荀子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
可见,由于持性趋恶论,荀子必然明确地走向道德规范主义。他身处一个即将结束诸侯分立国家一统的时代,处理各种利益冲突需要一个普遍准则。他认为礼起源于对利益冲突进行处理所作的伦理秩序的构建,以合乎礼义的时中状态分别确立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从而有利于维护等级尊卑的社会秩序,因此,不是心性的血缘情感仁爱而是知性的自然情感的礼义成为荀子的理论关切。而礼仪为圣人所制,礼仪系统对普通人来说有着优先性和外在性,它是教化大众唯一可操持的工具。从性恶论出发,的确突现了圣王教化的必要性,并从教化施与者的角度确立圣王所制系统的绝对权威。
二、时变:德性教化境遇的价值认同
“时”就是要“与时俱进”,荀子德性教化思想既固礼守中,亦重权应时。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这是孔子所说的学者渐进之次第,其中权是最高层次。《淮南子·汜论训》也引孔子此言,高诱注曰:“权,因事制宜,权量轻重,无常形势,能令丑反善,合于宜适。”④
春秋战国时期礼学的重要发展之一就在于“变礼”的出现,礼学从思想到仪式都主张随时而变,这样就增加了礼的灵活性和适应性。⑤制礼有变礼,因时而动,随时而变是制礼的一条重要原则。“礼,时为大。”(《礼记·礼器》)《周易》中明确提出“时”这个概念有多处。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时是人们行动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坤·文言》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豫·彖》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轻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艮·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时的观念贯穿于整部《周易》,其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待时而动,顺时而行;要时止则止,与时偕行,与时偕极。人们要依据不同的时境进行修业,这是古人对自然和社会人事规律进行抽象概括总结的智慧结晶。孔子也很重视“时”,“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因此孟子说孔子“圣人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中庸》则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治乱持危,朝聘以时”,“时措之宜”,这说明《中庸》也主张随时而变。后来孟子吸取了远古以来月令系统的思想,主张依时而作:“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孟子·梁惠王上》)《礼记·礼器》明确提出:“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也。”道家也讲时,如老子说:“动善时。”(《老子·第八章》)就是指的要依好的时机而行动,庄子说:“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就是指安于时境,顺应自然。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先秦儒道思想中,时的观念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根本方法。人们随自然界时间节律的变化而进行劳作休息,因此时的观念又引入到社会人事中被引申为“时机”、“时势”,指人们在社会事务中行动时,要把握恰当的时机,审时度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一种把时间观念纳入到自然和社会变化发展的吉凶祸福的因果链条之中的思维方式。”⑥这一思想为荀子所继承吸收,成为君子处事应变的基本准则。《荀子·不苟》言: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陷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尧舜,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法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应变,知当曲直故也。
这段是荀子言“时变”的具体论述,其意概指:君子推崇别人的德性,称颂别人的美好之处,不是为了阿谀奉承;公正坦率地指出别人的过错,不是为了诽谤挑剔;说出自己的美德,并与尧舜相比,和天地相配,不是狂妄虚夸;随着时势的变迁而能屈能伸,柔弱顺从,不是胆小怕事;刚强勇敢坚毅,从不向人屈服,这不是骄傲凶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君子能够依礼为原则,随机灵活应付变化之故。由此可见,“与时屈伸”、“以义应变”是荀子的应变之道。“与时屈伸”是《周易》“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思想的延续;“以义应变”则是春秋以来礼制思想的损益。“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乎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春秋繁露·玉英》)。礼有经,有变,说明礼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完善了礼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扩大了礼的运用范围,因此,变礼与变法具有相同的意义。诚如刘丰指出:“春秋战国是礼乐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礼崩乐坏’只是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西周礼制而言,从总体上看,经过这次转型以后,礼学思想,礼之义得到空前的发展,礼学发展到更加丰富、成熟的形态。”⑦
由此,在经权关系上,荀子以义解经也是对西周礼制思想的发挥和创造。孟子以仁义并称,义有对仁节制的意味,但孟子还没有把义与礼完全等同;而荀子则礼义并称,以义为内在的价值表征。他说:“义者循礼。”(《荀子·议兵》)“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其实,在荀子思想中,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1)是指等级差别的规定。如“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顺,是天下之通义也”(《荀子·仲尼》);“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这里是讲尊卑贵贱各得其所就是义;(2)是指调节社会伦理关系的原则。“义者,内节于人而外接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荀子·强国》)(3)是指各种道德的根本。他说:“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荀子·强国》)笔者认为,荀子言“以义应变”之义当取“分”意。因为在荀子的思想中,义本身即含有“礼为经”的意蕴,所谓“义者,礼也”,这是道德教化所遵循的基本规范,同时,义之分从道德哲学的角度诠释其本意是“宜”,即适当、恰当、正当、合宜之意。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教化过程中通过分而辨尊卑贵赋,人伦规范,而使行为合情、合理、合宜,体现了道德的意义和价值。义作为一种潜在的德性,可以成为礼的合宜的、感性的人格化身,是通过努力修养、自我教化才能达到。
因此,在道德教化中,荀子既主张“固礼守中”,“以礼为经”,又主张“与时屈伸”,“与时迁徙”,从而把礼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孟子以具体实例说明礼要灵活变通。不知道变通的礼“犹执一也”(《孟子·离娄上》);“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离娄上》)“在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德性化为德行,规范内化为德性,总是在不同的实践生活场景中实现的,任何行为的践行都离不开具体的境遇中如何处置具体的道德规范。”⑧现代境遇伦理学认为在一个具体的境遇中面对的问题有七个“什么”为何?何人?何时?何处?何事?何如?⑨这种将具体的道德行为化约到具体的境遇中,体现实践伦理的特点,并且弗莱彻在《境遇伦理学》一著中,以其基督教伦理学的立场,将爱的原则作为其具体境遇的最高原则,肯定了任何道德判断都是价值判断,从而将人自身的价值摆到了至上的地位,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中处理规范和行为的关系,这对理解荀子的教化思想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荀子·修身》曰:
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节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节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遇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
对于性格刚强的人,要进行柔从化导;对于潜藏深沉的人,要进行平易善良的教导;对于凶猛乖戾的人,要对其进行引导使其不越轨;对于敏捷快速的人,要对其控制而使其平和安静。总之,人的个性特征是影响教化效果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在培养和塑造以温柔敦厚为主要特征的君子型人格时,具有中庸温和个性的人更容易教化成功,而那些极端或偏执个性的人,接受教化就困难得多。因此,教育者应该及时了解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观察其言论,考验其行为,针对教育者的个性特征,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和教化手段,做到因材施教。故荀子曰:“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而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而后可与言道之致。”(《荀子·劝学》)
可见,荀子以遵礼为前提,在具体的道德境遇之中,针对不同的情况而采取合乎权时的行为,这种权时的行动是以尊重人的价值为先导;同时,在处理经权关系时,把经所依据的道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本,而荀子的道就是礼道。在此礼道的规约下,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恰当地处理道德行为,是孟子所说的“圣之时者也”,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应遵从稳定的道德规范以及对一定人伦之则的认可。
三、时积:德性教化意志的自我迁化
作为其对存在的追问过程中贯穿的根本方法,海德格尔以其对新的时间境域的开启而实现的对存在的澄明启示人们,“必须把时间摆明对存在的一切领悟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遇,这意味着只有将问题置入时间境域之中加以透视,才有可能透过表象,找到认识歧异得以形成的根源,进而才能更深入的把握问题的精髓和实质,所以,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把捉存在。”⑩当然,“以善为追求的目标,道德或伦理并非仅仅在消极的意义上‘保持存在’,毋宁说,道德的更本质的特点,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提升或转换,换言之,它总是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为指向。”(11)因此,在荀子的德性思想中,“时”作为到场或延异的境界既蕴含了对自然存在的理解,又凝聚着人对其自身生存价值的确认,并寄托着人的在世理想,而主体的人格、德性可以看作是主体在“时”的境遇中自我迁化的显现,这就是“积”的道德实践。《荀子·性恶》曰:
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不可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相为明矣。
以上文字围绕如何解释“圣人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这一现象而展开,揭示了其“时变”理论在具体生活情景中,的确存在着道德主体选择行为以及成圣成德的困境。亚里士多德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至于说到公正还是不公正,都需要有意地来做。如若是无意的,那就不是做不公正的事,也不是公正作为,而是机遇。”(12)公正在亚氏是作为最高的德性,即使是如此,也受到机遇的挑战。在荀子看来,礼固然重要,但人心之一本要求人们做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而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因此,“圣人可积而致却不可积”的关键是“可以而不可使”。王天海疏证:以犹“为”也,可以,即可为,或可以为,说见《古书虚字集释》。使,通事。《管子·侈靡》“不择君而使”,许维遹云“使与事,古为一字”。不可使,即不可事。事者,治也,为也。故“可以而不可使”,即“可以为而不可使之为也。”(13)在把“可以而不可使”解作“可以为而不可使之为”这一点上,拙文的意见是一致的。纵观荀子的论说,他对可与能作了细致的分疏,还讨论了可而不能的原因。依荀子,可以为而不为,乃是因为不肯为;所谓不肯为,即不愿为,也即孟子所说的“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至此可以说,荀子已经涉及道德行为中的意志或意愿或志与功的问题。人作为道德主体,其向善的意愿及行为不是被决定的,而是主体自身力量的体现,道德既属于精神追求,也属于一种内在的觉悟,一种诉诸主体心灵的意志,人在这一点上完全应当由自主作主宰,有权确认人有行为的能力以及向善的意愿。诚如孔子所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孟子的思想揭示了人的主体的自由性质,并认识到了德性自由的特征,进一步发挥了孔子为仁由己的理念。德性涵养如何,主体究竟能否在道德上达到理想的境界,这不是由天命所左右的,而主要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努力。为此,他谴责那种对善和道德不追求的“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上》)“自暴”、“自弃”完全是主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反之,求仁向善也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离娄上》)
荀子承孔孟之意,认为在道德教化中既要守礼之经,又要行时之变,赋予道德主体在践仁行礼中心智的充分自由,因而,成人成德的教化之功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不愿的问题。荀子的心是知性心,泛指主体意识,又兼指与之相关联的德性意志品格,其本身有向善的趋向,意志的指向,“心容,其择也无翠”(《荀子·解蔽》),心的选择是自由的自禁、自使、自行、自止,能够在现实的时变境遇中自断、自决地选择自己的道德行为。心有所可,有所不可。心之所可即心所肯定的,反之,则是心所否定的,有所可有所不可都是意志的作用。荀子认为心必须依礼才能有正确的选择,“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荀子·正名》);“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
由此观之,“在道德教化中,荀子是志功统一论者,既重视礼仪的涵养,又注重自我的迁化,肯定道德的自觉能动性,从而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14)从理论的层面看,主体的知性自觉意识使德性向德行的转化具备了自觉向善的方向,“尚志”所造成的坚定的意志品格又为道德行为提供了内在的力量之源,志功一致从主体自身的德性出发使德行具备了自然的向度。在外在礼仪的规约下,德行出现自觉、自愿而又自然的特征,使主体在自身德性迁化的过程中,通过道德境界的不断充实而使人格境界获得了提升。故荀子谓“德操能定能应”,修德且持守德行,才能应万物之变而成伟业。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德性自愿性和选择性的两个特点,在亚氏看来,“自愿和非自愿的行为决定了德性和邪恶的归属,只有自愿的行为才可以用德性和邪恶来判分,而非自愿的行为是被强制的或由于无知。”(15)同时,他将主体自身的选择能力看作是更为根本的品质,选择是对可能的东西的选择,是某种具体德行的选择,“做一个善良之人还是邪恶之人,总是由我们自己。”(16)这些言论实然体现了与荀子在道德教化中意志自由理论的相似性。
而黑格尔则在精神境界与荀子的意志自由理论相契相应。黑格尔肯定恶的历史作用的目的,主要是肯定恶能促进善,恶是获得善的手段,并且在和恶的斗争中人类走向至善。“止于至善”才是恶的最终目的和人类的终极追求,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意志的绝对目的,即善,”(17)自然意志扬弃的自由意志是善,扬弃的过程是自由的自然性、特殊性、抽象性不断走向自由的物质性、普遍性、现实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与自然意志相对应的可能出现的恶,获得了它的对象的定在——善,恶与善就是在自然意志的自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否定、扬弃、超越自己而实现它的外在的现实性,即从恶的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过度,走向自由意志善的自在自为的自由。
在德性教化领域,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是自由,它的对象就是它自身,是某种“内在的东西”,也就是说道德意志把人格作为它的对象,所以道德意志使人成为主体性,成为能动的独立自主的道德主体。对于黑格尔道德意志主体的自由论,荀子则从另一角度进行诠释,体现了中西哲学伦理精神的相容、共通的一面。荀子提出“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把人从天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序四时,裁万物”,道德主体在面对复杂的伦理境遇或性命两难时,虽然个体常常无法支配生活的一切遭遇,但是,主体可通过道德修养而做到道德高尚,并且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体人格的提升上,主体却拥有外界无法左右的自主性、能动性:“若夫心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荀子·天论》)在此,荀子实际上肯定了在道德领域,主体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存在,在荀子看来,主体意识的基本特点在于能够自由的思维和选择;人的形体固然可以被强制,但其意志的自由选择却是外力无法改变的,一般而论,道德行为的前提即是意志自由,如果主体缺乏自主选择能力或因外界强制而不能作出自己的决定,那么对其行为很难作出善恶区分,就此而言,道德自由首先表现为意志自由,荀子以自禁自使为主体意识的主要特征,显然有见于此。可见,无论是黑格尔或是荀子,都强调道德领域道德意志的主体自由,并把它作为自己人格上的沉淀,由自己进行道德选择、善恶区分,而自由是道德意志的本质,自由只有作为主体,才是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
但黑格尔和荀子的自由理论又有所区别,黑格尔是在善恶概念的辩证和精神的发展中去把握主体的道德意志自由,道德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因而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无限性不单纯是潜在的,而且进而达到了自觉的阶段,它是自身内部的普遍性环节和特殊性环节的对立统一,是“在自身中的反思”和“自为地存在的统一性”。“而荀子的自由更多的表现在处理天人关系上对自然神秘性的认识和对天命的节制,既强调了人的化性起伪的主观能动性的‘制天命而用之’,又强调了遵循自然规律的‘聘能而化之’,实际上肯定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主体便逐渐实现了自身的自由。”(18)这种自由,已不再是黑格尔所指的个体的精神上的道德意志自由,而是在本质上展开为人类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不断进取的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
注释:
①唐兰:《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第82页。
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第89页。
③陆建华:《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④刘文典:《淮南鸿烈集释》,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4页。
⑤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1页。
⑥孙熙国:《中国哲学早期重要概念研究》,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⑦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⑧戴兆国:《孟子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⑨[美]弗莱彻:《境遇伦理学》,程立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⑩[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3页。
(11)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第56页。
(12)(15)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51页。
(13)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5页。
(14)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16)苗力田编:《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1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44页。
(18)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