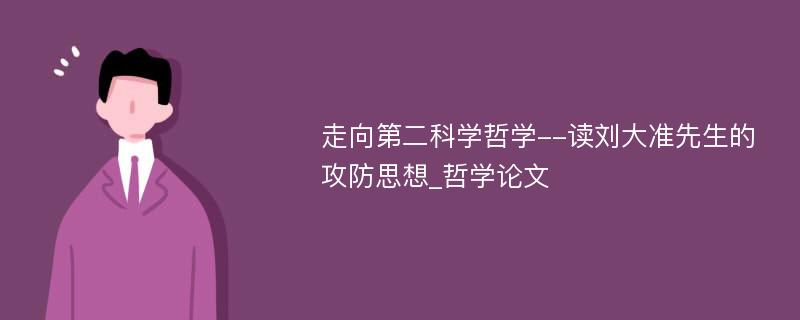
走向第二种科学哲学——读刘大椿先生《思想的攻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攻防论文,第二种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3)06-0004-07
大椿老师命我为他(和他的高足刘永谋)的作品《思想的攻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写一篇评论,以参与《哲学分析》杂志发起的对当代哲学家哲学思想的研讨活动。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上海社科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分析》杂志每期辟出专栏,讨论一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我认为非常有意义。哲学本来就是追问和批判的事业。哲学作为爱智慧的要义,不是把真理当成一块铸币取来揣在自己怀里,而是“爱”智慧、“追求”智慧,批判、论证、辩护因而成为哲学的常态。中国文化讲和谐、中道,不喜欢争论(攻)、反驳(防);在学术权威面前,更是为尊者讳,不敢发问,不敢质疑,这无疑阻碍了哲学这种自由学术的发展。刘大椿老师是中国科技哲学界的权威,他愿意加入这种“攻防游戏”,把自己置于批评的聚光灯下,为转化中国学术界的风气率先垂范,我觉得尤其值得称道。
我愿意参与的第二个原因是,《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以下简称《思想的攻防》)所述评的那些“另类科学哲学”,似乎正是我多年来鼓吹并致力于推动的“第二种科学哲学”。1996年,我在自己主编的《自然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上发表了文章“第二种科学哲学”,提出恢复广义的“科学哲学”,在正统科学哲学之外,建立第二种科学哲学。从2007年开始,我们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力图在分析的正统的科学哲学之外,发展现象学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多少年来,我们的工作另类边缘、和者甚寡,多数时候是自得其乐。如今有刘老师以科技哲学权威之尊出版论著,系统引介陈列“另类科学哲学”诸家学说,令人颇有吾道不孤之喜。
但我是在困惑缠绕之中读完本书的。我不是指的一些令人生疑的细节,比如把海德格尔归入人文主义哲学传统①,把彭加勒归入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②,把《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归于康吉兰③,说“从历史上看,中世纪宗教神学排斥科学”④。我主要困惑的是本书立论与论证之间的失衡。《思想的攻防》的主体尽管是评述另类科学哲学,但在封面、封底、前勒口等显要位置反复提醒提示,要从辩护的科学哲学,越过批判的科学哲学,走向审度的科学哲学。所谓“辩护的科学哲学”指的是英美主流正统的以分析哲学为底色的科学哲学,主要致力于解释科学为什么是合理的,通过澄清科学的合理性为科学辩护、捍卫科学。所谓“批判的科学哲学”,指的是对科学进行质疑和否定的哲学态度。所谓“审度的科学哲学”,是对前两者的超越,“其基本观点是: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我得承认,初读封面封底的这些句子,让我一时颇为糊涂:不知这本书是要讲第二种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还是要讲第三种科学哲学(审度的科学哲学)。
我本来很想追究一下究竟什么是审度的科学哲学。“审度”是“审时度势”的简写,其意思是“观察和评估时势”,以便顺应潮流、见机行事、与时俱进,等等。去掉时势之后的审度,有那么一点局外人的感觉,仿佛要把对象“悬搁”起来:审度某种东西,意思是先等等看看,不要急于做结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科学是否可行呢?科学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都“已经”生活在科学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之中了。因此,就是否接纳科学而言,拒绝是不可能的,辩护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接纳了科学。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接纳的程度有多深。哲学反思的任务是要澄清我们已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科学化的世界)的逻辑,认清我们的处境,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准备。哲学不是态度(世界观),而是艰苦的思维厘清工作,当然它会影响表态。
但读完全书,我反而觉得有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值得仔细探讨一下,那就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真的已经有一批另类的科学“哲学”,以至于我们可以讨论它们的“兴起”和“演化”,从而“超越”吗?我的意思是说,我当然不否认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多种思想运动中,存在着丰富的另类的科学哲学思想资源,但是这些思想资源好像还没有被整合起来,铸造出有自身“范式”的第二种科学“哲学”,以至于我们能够谈论这种科学哲学的演变,以及对它们的超越。《思想的攻防》也承认:“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对科学的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点仅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它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强烈质疑。”⑤但是,《思想的攻防》在不同的地点,对“另类科学哲学”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断言。比如说“大多数另类秉持的彻底否定主流科学的理念也只能是另一个极端”⑥,说“另类科学哲学是怀疑主义、历史主义中的另类倾向走向极端的产物”⑦,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指出哪位哲学家真的符合这些断言。因此我觉得,问题还不是超越“批判的科学哲学”直奔“审度的科学哲学”,而是要在哲学意义上,把另类科学哲学(第二种科学哲学)建立起来。在本文的余下部分,我愿意结合《思想的攻防》一书的一些观点,为第二种科学哲学做一些辩护,并谈谈如何走向(而不是走出)批判的科学哲学(第二种科学哲学)。
一、科学与哲学
任何一种“科学哲学”总是要首先澄清这个问题:什么是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给出一个定义就能了事的。问题的实质是在何种语境下提出问题。我觉得应该在三个语境下讨论“什么是科学”:第一个是胡塞尔的语境,第二个是正统科学哲学的语境,第三个是海德格尔的语境。
胡塞尔的著作标题中经常出现“科学”这样的词汇,比如“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欧洲科学的危机”,“现象学与科学的基础”等等。这里的“科学”是德文Wissenschaft的翻译,与后两个语境所说的科学是很不一样的。后两个语境中的“科学”通常指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即16、17世纪在欧洲诞生的,由伽利略、牛顿等人奠基的那种以数学加实验的方式来模拟构造自然,并最终诉诸技术应用的知识。胡塞尔意义上的“科学”取的是希腊文episteme的意思,即确定性的知识,纯粹而绝对的内在性知识。因此,胡塞尔的“科学”根本上就等同于作为西方思想之核心的“理性”。无论是哲学、数学,还是近代自然科学,都属于确定性知识的行列,其中哲学的追求目标最高。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中说:“哲学的历史目的在于成为科学中最高的和最严格的科学,它代表了人类对纯粹而绝对的认识之不懈追求。”
我提及胡塞尔语境下的“科学”,一方面是为了把后两个语境中的“科学”纳入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和思想传统中来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澄清“哲学”。先说后一方面,以后再说前一方面。
哲学作为哲学,本质上是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一种内在演绎。并不是每个文明都有哲学。那些被贴上非理性主义标签的哲学家,像叔本华、尼采、萨特、福柯,本质上仍然活跃在西方思想的范围之中,是理性生活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完善的一个环节。极端的片面之所以是深刻的,就在于它开辟了理性世界新的可能性。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作为思想家难道不是在讲道理、以理(说)服人?反对宏大叙事,不是反对一切叙事,而是回到微观叙事;反对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不是反对理性,而是要分析具体的理性。
就像海德格尔那样被认为是彻底颠覆性的哲学家,要刨西方形而上学老底、告别“哲学”的思想家,不还是要在“思”字上做文章?《思想的攻防》正确地认识到:“海德格尔把真理遮蔽看做最高危险,显然是西方文明自苏格拉底以来求真传统的再一次体现,即把真作为最高目标和最深的根源……虽然海德格尔采用一整套新术语以划清和传统的界限,但最终还是落入窠臼之中。”⑧但是,《思想的攻防》没有认识到,这正是西方文明自我拯救的唯一之道。任何一种文明在危机面前都不能简单放弃传统,另寻救命捷径,恰恰相反,都只能回溯自己的源头,并通过再次激活源头处的活力,才能为眼前的危机寻求出路。西方文明如此,中国文明也是如此。因此,认为“寻找西方文明的出路,还需借鉴其他文明的智慧,真正放弃‘求真之志’和以‘思’为唯一出路的空想”⑨,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放弃了求真之志,也就没有哲学了,谈何科学哲学呢?
第二个语境和第三个语境中的“科学”指的都是近代自然科学,但区别在于,第一,前者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活动,在理论与经验观察的互动层面上做文章,后者则把科学看成是一种特定存在论背景下的理论—实践活动,着眼于存在论模式来理解科学;第二,前者认为科学与技术之间界限分明,后者认为科学与技术并无截然界限;第三,前者认为科学之为科学在于其拥有独特的方法论,因此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方法论,后者认为近代科学的本质不在科学而在现代技术,现代技术的本质先行支配着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只是现代性的逻辑后果,因此科学哲学——如果可能的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的存在论,即研究现代科学得以出现的各种先验根据,特别是存在论预设。因此,第一种科学哲学与第二种科学哲学的根本区别并不是前者捍卫科学,后者拒绝科学——那样的话,就属于同一范式同一传统了——而在于,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而且在我看来,后者比前者更加彻底。
正统科学哲学语境中的科学或许可以看成是“求真的科学”,而海德格尔语境中的科学可以看成是“求力的科学”。这并不是说他们讨论的两种不同的东西,而是对同一个近代自然科学之本质的两种不同看法。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在海德格尔那里,求力与求真相互内在,揭示了现代理性中权力意志的主导作用。福柯进一步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而正统科学哲学所谓求真,实际上只是形式的逻辑的真,显得单薄而苍白。因此,第二种科学哲学与第一种科学哲学相比,并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更加深入、更加全面。
二、批判科学:从认识论到存在论
“批判”一词在古代汉语里意思是“批示判断”、考察分析,很文雅的词,在20世纪下半叶被演变为“否定、打倒”,余毒至今。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最先打出“批判哲学”的旗号,因此让“批判”(Critique)一词拥有其稳定的哲学含义。对康德来说,“批判”的意思是“厘清边界、确定条件”。这是理性的自我反思能力的逻辑展开。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任何知识均有其条件,只能在此条件下成其自身。因此认识论的任务,不是论证认识是否可能,而是指出其何以可能,即发现其得以可能的条件。就此而言,正统科学哲学也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哲学。正统科学哲学所谓“辩护”,是与“发现”相对的,是在康德框架下的自我哲学期许,说白了,“辩护”即是哲学批判,而“发现”是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的范畴,不是哲学。逻辑经验主义取“辩护的逻辑”而不顾及“发现的心理学”,这一自我约束的确是在体现一种哲学品格,谈不上为科学唱赞歌。事实上,正统科学哲学并没有说科学可以包打天下,也不必然导致科学主义。虽然它在知识论上肯定是科学主义的,但他们并不认为科学可以包办、替代一切其他的人类文化。
但是,由于正统科学哲学只着力于发现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条件,而没有进一步去探讨它的存在论条件,因而是不彻底的科学批判。
正统科学哲学默认了自然科学作为合法知识的典范地位,默认了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论地位,这两个“默认”使得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和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论地位成为未经反思的。胡塞尔毕生致力于克服的自然主义指的就是这两个默认。自然主义并非错误的,而是一种非反思状态,或者说是一种不彻底的哲学反思或哲学批判。要将“批判科学”进行到底,就必须要进入科学存在论。也就是说,近代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地位和科学世界图景的本体论地位,均是奠基于某种关于科学的存在论之上,我们需要澄清的首先是,近代自然科学基于何种存在论。
这种存在论的澄清工作是哲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一般所谓科学主义,实际上就是把在自然科学中胜任的方法论外推到自然科学外的一切领域,包括哲学反思的领域。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彻底地批判科学并不是反对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主义,尽管科学主义常常是科学共同体的自我哲学认同。美国现象学家柯克尔曼斯说得好:“的确,现象学从一开始便反对对科学持一种单面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解释。然而,现象学所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之中蕴涵的自我哲学理解。因此,现象学所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科学主义,不是经验研究及其成就,而是对科学的实证主义解释。”⑩《思想的攻防》说大多数另类科学哲学彻底否定主流科学(11),我觉得相当的含糊和笼统,没有区分究竟是否定科学的成就,还是否定科学主义。
三、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近代”科学基于何种存在论?这里已经预设了某种历史性,即近代科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并不能像正统科学哲学那样,把科学看成一种超历史的存在,因而只做共时结构的逻辑分析。第二种科学哲学所致力的存在论必定是历史性的。这便引出了哲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哲学就是历史,历史就是哲学?
前面提到,正统科学哲学强调“辩护”和“发现”的根本区分,其实就是强调“哲学”与“历史”的根本区分。尽管这个教条最终被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所打破,但是哲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以至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被认为事实上并没有创立一门新的科学哲学,而是解构了科学哲学本身:用科学史代替科学哲学,使科学哲学学科名存实亡。《思想的攻防》在批评福柯时,也秉承的是这种哲学与历史的截然二分逻辑:“如果主体是被历史地建构出来的,它就不能作为知识不变的基础;如果主体要作为知识不变的基础,它就应该是不变的。……所以,以历史或历史性作为真理、知识的基础,实际是取消了知识的基础。”(12)我觉得,要建立第二种科学哲学,建立科学存在论,就必须澄清哲学与历史的关系。
自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就把哲学与历史做了区分,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与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博物学)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知识路线,并且历史从属于哲学,或者说由哲学确证历史。笛卡尔也是这个路数:我思(哲学)故我在(历史)。康德虽然把时间性引入知识论中,给理性做了一次限定,但他的先验主体仍然是非时间性的,因此康德哲学中仍然缺少历史这个维度。把历史提到与哲学一样高度的是黑格尔。黑格尔突破了康德对于理性的限制,通过思辨的辩证综合,完成了一个理性的绝对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所以在黑格尔这里,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哲学本质上就是哲学史。如果按照黑格尔的逻辑,我们似乎也可以说科学史本质上就是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本质上就是科学史。
逻辑经验主义作为正统的科学哲学,继承的是康德这一非时间性、非历史性的哲学传统,而黑格尔则遭到了严厉的拒绝。因此,在正统科学哲学那里,科学史是无关紧要的。历史主义学派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互惠关系。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但这个说法多半只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一厢情愿,多数科学史家未必买账。而且,多数科学哲学家笔下的科学史,都写成了为某种科学哲学做见证的案例,使人们怀疑这种科学史的史学品质。总的来说,在正统科学哲学的框架之上,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恰当的澄清。
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一开始就试图把理性的事业从杂乱偶然的历史事件中剥离出来,但是他并没有回避“历史”问题,而且毋宁说,现象学一直着眼于真正的历史性。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书中胡塞尔指出:“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这里的“起源”、“开端”都是历史性的,但却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所说的那种经验的历史。通常所谓的历史学,跟近代科学一样,也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支配着现代性的,是某种更深层的“历史”和“起源”,雅各布·克莱因称之为“意向历史”(intentional history)。
现象学提出的意向历史概念解决了哲学(理性)与历史(起源)的二分问题。以探讨现代科学的存在论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如何与历史交互运作。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是一定有它的构成的历史和意向的起源,追溯它的构成的“历史”和意向的“起源”就是科学存在论的任务。这个构成的历史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罗列的偶然事件,而是它的意向结构。这个意向结构包括近代人的重塑,近代数学的转型,自然概念、宇宙概念的更新,事实作为事实的确立,以及历史观念的出现等。这个意向结构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历史”,是因为意向结构本身就是被内时间性的绝对之流所构成的,内时间性是意向起源的普遍形式。对胡塞尔来说,历史就是在不同层面上对这种普遍形式的不断唤醒,是起源的不断重复。胡塞尔本人在《几何学的起源》和《欧洲科学危机》中分别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伽利略物理学做了起源的现象学分析,为科学存在论的开拓研究提供了示范。
通过现象学澄清了哲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之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内在关联就是不言而喻的。(近代)科学的存在论问题与近代科学的历史起源问题,可以看成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不同提法。在这个过去为正统科学哲学所无视的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中,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主题空间。
做哲学就是加入一种哲学传统,学会一种哲学话语和叙事方式。做正统的科学哲学需要进入他们的范式,做另类科学哲学也是如此。我在去年纪念库恩《结构》出版50周年时写文章说,库恩“摧毁了旧的范式,而新范式进入常规还有待时日。我们仍然处在科学哲学的反常时期”。建立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科学哲学,正逢其时。但究竟是走向还是走出批判的科学哲学,我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希腊精神,直抒己见,以就教于大椿老师。
注释:
①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页。
②同上书,第8页。
③同上书,第158页。
④同上书,第295页。
⑤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前言。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7页。
⑧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第59页。
⑨同上。
⑩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
(11)同上书,前言。
(12)同上书,第182页。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存在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现象学论文; 胡塞尔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