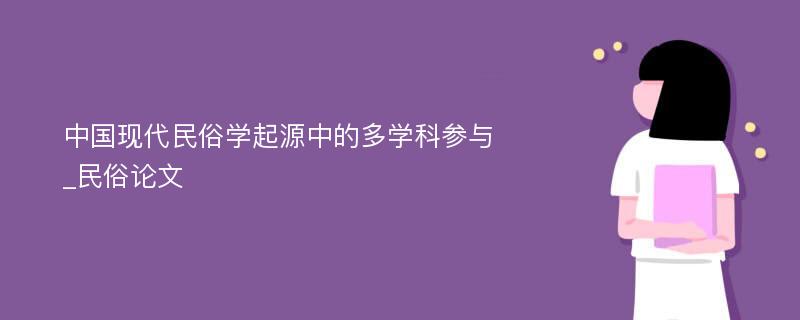
中国现代民俗学初创时期的多学科参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俗学论文,中国论文,多学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了解中国现代民俗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门学科的初创时期,其主要参加者和代表人物大都来自于民俗学以外的学科。这种多学科参与的性质和特征,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这种参与和影响究竟应该作何评价,回首80年的坎坷道路,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如果把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开端,那么刘半农、沈尹默和蔡元培是三位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正是刘半农的首先提议,得到沈尹默的响应,最后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使这场运动开展起来的。但是,刘半农和沈尹默虽是歌谣运动的发起者,却专攻语言文字学,并没有在《歌谣》周刊和以后的其它刊物上大量发表民俗学的、至少是歌谣研究的文章。蔡元培大力支持这项研究,是他的新历史观的必然结果,所谓“新体之历史,不偏重政治,而注意于人文进化之轨辙。凡夫风俗之变迁,实业之发展,学术之盛衰,皆分治其条流,而又综论其体系,是谓文明史”。(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史学论集》第13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但他毕竟主要是个教育家,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去研究民俗学。
当然最能代表这批人特点的是胡适。他本身是学哲学的,后来因为倡导文学革命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但正是因为他鼓吹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使他与民间文艺研究联系了起来,撰写了《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与《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等著名文章。他强调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和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注:《歌谣·复刊词》,1936年4月4日。)我们看到,当时推动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新青年》的编辑们,包括钱玄同和李大钊,也正是《歌谣》的主持者或支持者。因此,提倡新文学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改造和变革,是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要成为新诗人或新小说家。这样,北大的歌谣征集活动最初也许同样只是从文学运动的需要考虑。所以胡适自己曾说:“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这一班人,都不完全是弄文学的人”,“我们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载1958年5月5日《新生报》(台北)。)就民俗学而言,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这批先驱者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地位之重要,就在于他们都是本学科的伟大的改革家和创新家。像蔡元培之于教育、刘半农之于语言学、胡适之于文学和哲学,都接受了新的学术立场和方法,他们都试图用本学科出现的一些新观念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他们对于民俗学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本身对这门学术有多少研究,而在于他们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先进的思想,“发现”了这门学科的重要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并且把它告诉中国人。
接下来的一批人则是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周作人应该算是一位文学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注:《周作人自述》,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这样,作为一种比较主要的业余爱好,周作人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许多重要的民俗学思想(如柳田国男的乡土研究作品,再如他介绍江绍原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等),不仅较早地倡导了儿歌、童话的征集,还写作了大量民俗学内容的短文(见《歌谣》周刊、《语丝》等刊物)。更重要的是,他还对民俗学的性质、对象、功能等问题较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周作人确实没有在民俗学领域做出专深的研究,但在当时的国内,他对于国际民俗学发展的了解,可以说是较早和较清楚全面的。加上他的作品的读者群较大,所以在使民俗学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和认识方面,他的确具有不可抹杀的贡献。
与周作人同时对民俗学早期发展作出贡献的还有常惠和顾颉刚。常惠是学法文出身,但曾是编辑《歌谣》周刊的中坚力量,所以在1936年曾被胡适戏称为“研究歌谣的‘老祖宗’”(注:《歌谣》第2卷第8期,1936年5月。)。尽管他在2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但与当时在《歌谣》上发表的其它文章相比,他的文章一方面较具研究性,董依宾关于《看见她》的著名文章实际上就是受了他的文章的启发,另一方面,他比较赞同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歌谣,这与当时多数研究歌谣的人见解不同。这些方面当与他学习外文,熟悉外国情况关系密切。顾颉刚则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他是从改造史学的角度进入民俗学的大门的。正是他对民俗文化的关注,使他改变了许多以往对历史的看法,使他得出结论说,“这种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注:《〈古史辩〉第一册自序》,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册,第38页。中华书局,1988。)这位历史学家对于民俗学的贡献至少有三:首先,他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为研究民众而大声疾呼、身体力行,从北大到中大,积极创办刊物,出版丛书,率先进行田野调查;其次,他对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对妙峰山的研究、对
除此之外,从文学角度切入民俗学的还有茅盾、赵景深等人。郑振铎虽也主要从文学方面做出贡献,但他的《汤祷篇》等却与顾颉刚的意图类似,是“应用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为中国古史学另辟一门户”。(注:见《郑振铎文集》第4卷,周予同“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而从史学入手的还有容肇祖,他虽以研究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为主,但因较早追随顾颉刚而热衷民俗学,后在中大又主持过民俗学会和《民俗》周刊的工作,使他对民俗学的思考也日趋成熟。他的《我最近于“民俗学”要说的话》一文中的见解,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注:《民俗》周刊第101期,1933。)当然,除了上述的这些传统学科以外,对当时民俗学发展推波助澜的生力军还来自于人类学和宗教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所关注的研究主题、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与民俗学相当一致,因此尤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其中,江绍原、黄石、杨成志、林惠祥等人的民俗学作品,无论是专著、译著,还是论文和概论性教材,在当时都具有较高水平。比如江绍原对礼俗迷信的研究(典型代表著为《发须爪》)、黄石对于女性民俗的系列论文,都是结合本土文献和国外相关理论的个案研究,杨成志、林惠祥则在介绍国外研究动态和进行田野研究方面贡献很大,像江
最后需要我们投放目光的一类人——钟敬文、娄子匡、张清水等等——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延续功劳最著,因为他们从一开始踏上民俗学研究之路,就再没有退缩,始终心无旁鹜、执着坚定地在民俗学园地中耕耘。张清水家境不好,一直在家乡(广东翁源)生活,常常不顾生计的需要而坚持进行民俗研究,直至抗战期间病逝。娄子匡自20岁时出版《绍兴歌谣》,长期研究民间故事,特别是在《民俗》停刊之后注意建立民俗学的阵地(如《孟姜女》),在抗战期间于后方联络民俗学界的同行,近几十年来还着重注意民俗学研究资料的建设。钟敬文虽自文学切入民俗学,但自1924年开始与《歌谣》周刊发生联系之后,就一直努力把他所同样钟爱的文艺学和民俗学结合起来,至1935年首创民间文艺学,而至1992年又发展为民俗文化学。他力图用民俗学去改造文艺学,创造融入民俗学学科理论的一种新文艺学,也即民间文艺学;逐渐地,他又力图用民俗学去改造文化学,倡导一种注意文化的民间发生、以及上下层文化互动的新文化学,也即民俗文化学。这种独特的学术心路离不开钟敬文独特的学术选择,他与胡适、赵景深不同,后者始终用文艺学的角度观察民间材料;他也与顾颉刚、容肇祖等人不同,后者并没有因为对民俗学的兴趣而把自己的研究路
无论如何,我们所感兴趣的是,尽管这些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各有专攻,却并不妨碍他们在共同的兴趣之下团结合作,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中国新生的民俗学事业增砖添瓦。他们总是谦虚地说,他们只是些业余爱好者,都不是民俗学的专家,但他们总是在为民俗学建设的基本问题热情、激烈地探讨、争论和奔忙。这无疑说明,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民俗学事业需要多学科的合作和互补,需要一种宽容、开放的心态。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中国现代民俗学才在诸多困难之下发展了起来。
以上,我们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一些具有不同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分析,了解了他们是如何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学术兴趣出发,走上民俗学研究之路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民主思想广泛传播并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他们也许是为了提倡中国的“文学革命”,但却浇灌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之花;他们也许是为了利用民俗学来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但却引发了对中国传承已久的民俗事象的深入探讨;他们当中有的是因受了西方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把西方民俗学介绍到中国来,力图在中国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途径;也有的是自幼深受中国乡土文化的熏陶,希望努力开垦这一块长期为人忽视,甚至轻视的沃土;他们或者从不同的学科汇聚到一起,开创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天地,然后又回到他们各自熟悉的研究领域;或者坚持不懈,始终在民俗学园地中耕耘,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这个新生的事业,或者殊途而同归,或者同归而殊途,但中国现代民俗学正是这样产生发展起来的。没有用平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的“文学革命”,没有改造帝王将相家史的新史学思想,没有对身边的民间文化的挚爱,没有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理想,没有对西方民俗学、人类学学术价值的认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现代民俗学创始时期的这种多学科参与的特点,究竟给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新学科诞生的时候,是由这个新学科的专业人员进行催产的,而都是原来从事其它学科专业的人开创,再培养起本学科的专业人员来的。就拿民俗学来说,赵卫邦说“科学的德国民俗学,首先由莫瑟尔奠定了基础,后来由赫尔德、格林兄弟与里尔加以发展,直到民俗学会的活动与斯帕莫教授出版的《德国民俗学》,几乎用了一个半世纪,民俗学才成功地建成一门完整的科学”,(注:赵卫邦《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王汝澜中译文见《民俗学译丛》第1辑,中国民间文艺家研究会,1982)其中赫尔德是个哲学家,格林兄弟是语言学家,里尔甚至是新闻工作者或政治家,但他们都在德国民俗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其次,民俗学本身又是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不像哲学、历史学、文学、地理学等等那样从古代就已形成,有自己的明确边界。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既可以被分别置于历史学、文学这些古老学科之内,也可以与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比邻而居,因此它的产生就在于不同学科的人就研究民间文化的传承而言形成了共识,它的边缘性和学科交叉性就决定了它在诞生时必须依赖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而在它成熟以后,其专业人员又必须同时是多学科的专家。
第三,20世纪初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诞生的时候,正是新的学科领域被大量引进,开始在新的教育体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时候,也是传统学科分类依然具有巨大影响、对新学科具有较大排斥力的时候,简言之,正是新旧交替的变化时刻。当时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人无不感到压力极大,无不感到自己是在披荆斩棘,很难被人认可。如果不是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人、比如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民俗,不是把民俗事象视为传统学术中被忽视了的部分加以发掘,中国现代民俗学将更举步维艰;如果倡导者不是那些已经在学术界有相当地位的人,民间文化研究将仍然是一股学术潜流,而不能成为一种显学,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因此,正如赵卫邦指出的,“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起点还是不充分的。主要缺点是,那些民俗学研究工作的创始者们没有一个人充分熟悉民俗学这门科学的性质、理论和方法。……很难立刻拟定出一个恰当的计划”。“从我们现在的有利地位来观察全部问题,我们可能要责难那些民俗学研究的先驱者,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造成的错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所取得的十分有价值的成就”。(注:赵卫邦《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王汝澜中译文见《民俗学译丛》第1辑,中国民间文艺家研究会,1982)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对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引进需要一个消化、吸收和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国自己历史和现实中的民俗事象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了解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开始走上正轨的时候,又遇到了战争和政治干扰的不幸,因此中国现代民俗学体系建立和成熟的相对迟滞,绝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早期民俗学从事者的多学科背景。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些背景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积极影响,那就是,西方近代学术把学科领域划分得过于细碎、过于明确,到今天已经出现弊病,于是自20世纪中叶又开始了学科交叉、科际整合的新趋势,而中国现代民俗学可以利用其创始时多学科合作的传统,跨过这个调整、纠偏的过程。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早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除了多学科的参与之外,也确实存在像钟敬文、娄子匡、张清水这样从一开始就投身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并一直在这个领域中耕耘的人。在当时,即使是北京大学或是中山大学,也没有专门设立专门的民俗学系,中央研究院中也没有专设民俗学研究所,因此不可能培养出民俗学的专门研究人才,只有中山大学组织过民俗学的培训班,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因此这些地方的民俗学组织和专门刊物就肩负起了培养专业人才的责任。钟敬文、娄子匡、张清水等人一方面是具有搜集研究民间文化材料的兴趣,就像中国古代的许多前辈那样,另一方面则是北大《歌谣周刊》、中大《民俗周刊》等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培养起来的学生。他们往往没有或失去了进高等学校的某一系科进行专业学习的机会,但却因此而未被束缚在某一学科领域之中,使他们得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始终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事业中发展,而不会时时兼顾或者最后转回到原来学习的本专业。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人,中国现代民俗学才能在历经战争和社会的劫难之后不绝如缕,重新振兴,这也算是中国现代民俗学事业之万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