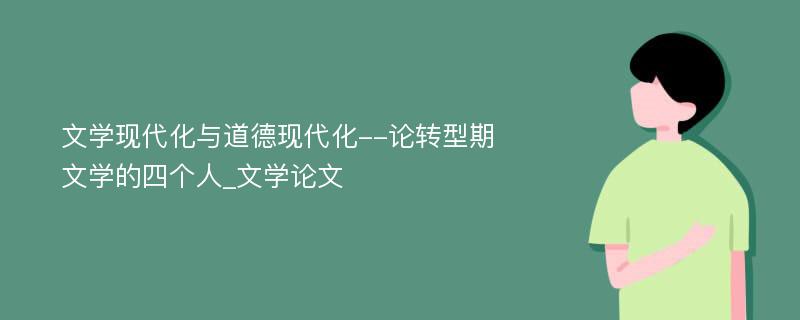
文学现代化与道德的现代化——转型期文学四人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文学论文,四人论文,化与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转型期文学发展的混沌与无序是一种必然现象。表现在道德方面存在着作家社会责任感弱化、浮躁媚俗的倾向,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出现了道德的真空。对此,这篇谈话从:一、社会道德现状与文学的使命;二、道德转换与艺术家的人格重建;三、转变前景与批评的任务这样三个方面对当前文学现代化与道德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了前瞻性的批评与总结,提出道德重建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和传统以及已出现的新道德因素;文学界和批评界应当建立起现实的、理性的心态,宽容地对待多元化的现实和多元化的文学;遵循艺术规律,在道德重建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等观点。
一、社会道德现状与文学的使命
吴秀明(以下简称吴):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已愈来愈呈现出转型的特色。转型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混沌和无序,这恐怕是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环节。文学的这种混沌无序,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生活在井然有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并深受其影响制约的人来说,自然感到有些不适。为此,如何改变传统思维观念,以求与变化了的时代形势相谐同步,已切实地摆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混沌无序本身也存在着许多负面因素,尤其是在深层次的精神道德方面问题更为突出,有的已达到颇令人担忧的程度。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社会责任的艰巨和重大。如果我们安于自身观念的调整而不能或不敢对文学道德的负面进行有效的批评和抑制,那么将有失于人文工作者的天职,也愧对于我们的时代。
陈一辉(以下简称陈):是的,社会转型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基本框架的冲击的确是巨大的。因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和道德的现状不仅闪烁陆离,而且相当可忧可叹:社会为物质所异化,心灵悬浮,道德空缺;文人面对市场尽失操守,随处可见媚俗的嘴脸,堕落的身影。在80年代曾经充满生气、高扬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日渐妥协败退,让位于武侠、言情、破案、商战、隐私,一时间,似乎文坛恶俗泛滥,垃圾充斥。面对此状,不少文人与批评家也呈现一种晕眩不知所措的境况:或恐惧忧愤,或持以批判的冷眼,或封闭于“历史的空间”,或沉缅于世俗的欢乐,甘居于自娱娱人的卑微境界;或“玩”或“痞”,力避政治功利;或涕泪交流,神往于宗教的高洁。
郑淑梅(以下简称郑):讲到当前文学在道德方面的缺失,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弱化。不少人缺乏积极参与变革的自觉性,抱着旁观者的态度,无所谓的态度,丧失了对时代大潮进行深入观察和真实反映的热情,放弃了作家应承担的时代使命。第二,对于大众缺乏真诚关怀和热切引导。作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隔膜,文学的贵族化与庸俗化的两极错误倾向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第三,追名逐利,金钱至上。受金钱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作家露骨地或变相地做了金钱的奴隶,为了金钱,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媚俗玩世,甚至装疯卖傻,什么都有。
苏宏斌(以下简称苏):我同意各位对于文学和道德现状的描绘,但我以为当务之急在于努力寻求评价现状的合理尺度。在我看来,当前存在的道德失衡与无序状态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无序和混乱正是道德观念嬗变的征兆。应该看到,目前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多元道德观念共存的时代,其中既有革命和战争时代形成的崇尚牺牲与奉献的道德观,也有近代以来传自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更有我国传统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仁义道德。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来了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道德沦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对于自身的道德立足点有清醒的意识。比如近期大谈特谈的人文主义精神究竟有何确切的内涵?如果以为它就是五四以来讲求民主、科学的精神,那么这实际上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它和现代科技文明同源一体,这种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规范未必能为当今的道德失落指点迷津。因此,我以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澄清各自道德话语的确切指向,在此前提下展开平等、宽容的对话,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寻找到合理健全的道德规范。否则,固守旧的一元道德观念,我们不仅会感到无所适从,而且可能抹杀建立新的道德观念的契机。
陈: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应该正视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的颠覆,然而我们却不可因道德的义愤而影响视力,干扰判断。随着中国全面地走向市场经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得文学作品的内在精神、结构与功能,以及进入市场的姿态、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真实文化背景下来看待种种变化,我们也许可以多一份理性与宽容,多一份心平气和。
郑:造成目前文学道德状况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文学自身的原因外,更多的是由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决定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上一些人漠视中央权威的风气影响到文学上就是文学和时代主潮在某种程度上的游离。金钱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现实使不少人的观念发生了位移。现在有一句话似乎很流行:“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说白了,这恐怕是金钱万能论的翻版。难道真的是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吗?我看不一定。据说路遥生前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他照样写出了无愧于我们时代的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倒是早些年声称赚足了钱再来创作的下海者,现在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当然,作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苦行僧,问题是追求什么样的价值,以什么方式体现自己的价值。这里就有一个道德问题。当然,在忧于文学面临的危机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文学的生机和希望。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新体制的逐步建立,作家将获得更多的创作自由,文学艺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还是可以期待的。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矛盾和痛苦,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近年来,作家主体意识普遍觉醒,大家都懂得了怎样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身的利益,这也是好事。不少优秀的作家始终坚持严肃的文学追求,认真地做人为文,不随波逐流,固守着文学工作者应有的道德防线,奉献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佳作。随着新秩序的确立,相信会有更多的作家在经受了现实的洗礼之后回归到对文学自身价值和社会使命的崇尚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苏: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能动表现,当然会迅速地反映出社会道德秩序的转变。我以为新时期以来文学中道德意识的演变过程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对于文革的反思所导致的对于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元道德观的怀疑,这种怀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传统价值观的合理性。当然,由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并没有简单地导致传统价值观念的回潮,比如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神鞭》等作品反而更多地鞭挞了传统文化的痼疾,但寻根的失败也为价值观、道德观的失落与虚无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改革文学竭力歌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占据道德舞台,但同时,随之传入的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性解放等又导致了对西方价值观的怀疑。这两方面的怀疑精神在先锋文学中达到高潮,导致了《你别无选择》等作品中的价值虚无主义的出现。文学中的道德真空至今尚无从填补。新写实小说,苏童等人的新历史小说,乃至近年的新状态文学,新都市小说似乎都无意于担负起道德重建的任务。因此,我认为相对于当今社会的道德混乱和无序状态,文学中的道德真空和价值观念上的虚脱也同样怵目惊心。如何使文学艺术重新担负起自身的道德使命,对社会价值观念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无疑是文学界和一切有识之士应该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吴:道德从本源上讲,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过程而逐渐形成的。人类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两种。因此,道德从一开始就分两条路线发展:一条是紧紧追随人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发展起调节人类的这种活动及其由此形成的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体系;另一条则紧紧追随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发展起调节人类的两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体系。综观当前转型期文学中的道德风貌,它在总体上也是沿着上述两条路线发展,并脉胳清晰地经历了一个日趋偏至的三部曲。从第一条路线看,自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这一阶段文学对道德思考还较多地停留在政治层面,很少涉及伦理学本身意义的道德内涵。至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等作出现,因为感受到社会变革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作家在产生道德困惑的同时才开始对道德持清醒的理性反思。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特别是此后王朔等作,由于接受了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加之本身固有的对虚伪道德戒律的痛恨以及受商品大潮的催化,在理论与创作上,他们便有意无意地否认人的本质与外在社会的联系。至此,文学对道德的思考也由前一阶段的道德困惑、理性审思转向了对传统道德的彻底否定。从另一条路线来看,在建国后十七年几乎沉默窒息的爱情文学也大体走过类似的三个阶段。最先,以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为代表,通过爱情这一特殊角度竭诚歌颂美好的人性和人情。继之,是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用前所未有的大胆之笔,将写性与写社会结合起来,填补了长期以来文学“有情无性”的历史。最后,是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尤其是贾平凹的《废都》以及为数众多的通俗文学,其对性的探讨虽不乏意义,但由于孤离于社会伦理准则或缺乏艺术美的观照,结果致使情爱、性爱描写失去了激发人们对美好的情感向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文学的声誉。
由上述两条路线的创作可以发现,随着社会转型的日趋深化,固有道德在文学中的位置发生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惊人蜕变,道德失衡已成事实。有智者言,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此言过矣!但物欲横流,观淫成癖,精神正在被欲化蚕食,却是一个显见的现象。
二、道德转换与艺术家的人格重建
吴:文学转型既混沌无序同时也是一个选择与生成的过程,必然的并不等于都正常。须知,中国目前尚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性社会二元并存的历史阶段,传统道德文化虽已解体,但它仍在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积极的和消极的),而新的道德文化的构建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现代性社会还没有完全形成,现代道德文化所依赖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和完善起来。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使原本十分复杂的文学现代化与道德现代化显得更加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问题的探讨,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也许是不合适的。
但这样说绝非意味我们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无所作为。关注现实,参与现实,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相应积极的、能动的选择见解,这才是每个严肃作家应有的态度,也是我们讨论文学和道德转换的基本立足点。事实上,不少作家已经这么做了,他们恪守自己信奉的真理与理想,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假、恶、丑的批判与抗争。不过,同样是批判,这之间他们却有明显的区别。一种批判可以称之为是“滞后态批判”,它站在过去的立场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旧有的文化范式评价当下的文学与道德,试图用传统道德来拯世。如张承志、张炜大体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在世风日下的商品社会中保持人格的独立——这的确让人肃然起敬,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单靠传统道德文化是拯救不了当下道德滑坡的。历史不可倒退,道德与政治、经济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因此,这种批判除了唤起怀旧心理外,它在现实面前总显得苍白无力;批判者虽然慷慨激昂,但其内心深处往往不无孤独和痛苦。另一种批判叫作“瞻前态批判”,它用前瞻的观点审视历史和现实的文学,即将目前文学中的道德失衡纳入历史——现实——未来这一机制予以观照。因为融入了未来学的因素,所以这种批判就带有预见性、构建性、开放性,在对义与利、个体与集体、娱乐与教化等关系上,包括文人经商下海等,就比较宽容。真正理想的批判,应该是这种“瞻前态批判”。这也是衡量作家有无现代意识的重要标志,是我们讨论作家人格重建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郑:说到人格重建,我以为艺术家的职业道德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商业工作者有商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演艺界有演艺界的职业道德,文学工作者也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这是我们今天来思考文学在道德批判和道德重建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时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也是一个自我拯救的问题。如果作家群体的道德秩序是混乱的,那么文学在建立健全和维护适应我们民族发展需要的现代道德秩序方面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早在五四时期,成仿吾就说过:文学是时代的良心,作家当是良心的战士。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则是相同的,文学不能逃避对社会的道德批判和精神文明的建立,这是文学艺术必须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功能,是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当前,我国的现代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已经走上了快车道,经济发展的势头尤其迅猛,但精神文明的发展却呈现滞后的迹象。这就尤其需要文艺工作者们发挥自己的作用,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通过其艺术作品向人们传输正确的思想、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媚俗、不惧恶,正确地评价是非善恶,坚持不懈地批判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以使一个处于急剧变动中的社会得以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定向,为大变动中的社会提供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推动人类生活向着至善至美的境界前进。
因此,我们说,道德批判和道德建设是文学工作者的职业内容,是份内的事。并不是谁硬性摊派的额外负担。任何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都具有对世界作出道德评价的意义指向,这也是文学的一个本质属性。
陈:固然,社会政治经济向现代化的迈进并不以牺牲传统的道德价值为必要代价;我们也充分肯定文学界、理论界对重建价值、呼唤道德理想的热切期望。然而,如果离开了大的文化背景去奢谈道德与价值的标尺,其立足点也未必能理足气壮。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后期,当代文学确实洋溢着生机勃勃的青春气息。承袭五四以来的冲决一切的批判精神,刚刚从文革恶梦中走出的人们急于舒展被压抑的人性、尊严、价值,以深深的理性与反思精神审视我们所走过的历史与即将面对的未来。文人们大多具“为天下师”的伟岸心态和普罗米修斯般的殉难精神,独立、创造、严肃、审美、崇高弥漫在四周,此时的文学感觉真好,真无愧于相生相伴的时代与社会。而进入90年代,市场经济这一现实即以冷酷无情的面孔涤荡浪漫的梦境。有人说:“80年代文学主要面对的是政治文化的挑战,90年代文学主要面对的是经济文化的挑战;80年代文学主要是面对民族国家因历史政治所形成的独特主题,90年代文学的主题力图超越物欲和感官的压抑,追寻生命价值和生活的意义”,我赞成这种概括。
苏:我以为当前文学中道德意识的危机在于作家自动放弃了自身的道德使命。原因在于作家本人丧失了坚定的道德立场和明确的价值标准。而这,则有着艺术观念与社会变革两方面的因素。从艺术观念上来看,新时期文学在探索和发展中逐渐发现,既有的艺术观念负担了过重的道德和政治要求,使艺术所应有的审美特征受到了损害,因而逐渐倾向于接受先锋文学所倡导的西方现代派的艺术观,有意识地解除自身的道德重负。从社会现实的影响来看,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文学的轰动效应不可挽回地丧失了,通俗文化、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无情地蚕食着严肃艺术的接受市场,艺术家本人开始面临市场法则的考验。这使艺术家连道德怀疑和批判的立场也无法坚守,直接放弃了对现实作出严肃评判的责任。比如苏童、格非等先锋文学的代表也毫无愧色地走出“象牙塔”,为张艺谋撰写同名小说《武则天》。这一事件赤裸裸地表现出严肃艺术向金钱缴械的悲惨景象。由此可见,艺术家道德信念的失落是文学艺术出现价值真空的根源。反过来,艺术家道德人格的重建也是文学转型的关键一环。
吴:刚才大家较多地对文学道德现状的负面作了批判,那么“重建”呢?所谓“重建”,按我的理解,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动态过程。它有始无终。这里的“始”,首先就是上面所说的传统道德文化,文学现代化与道德现代化虽不单靠传统文化赋予,在这方面,我们与日前颇有市场的新保守主义是有分歧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现代价值目标的观照下发现内中那些超历史性的积极因素,经过价值转换作为“重建”的重要参数之一。我认为中国人的道德转换是不能离开中国特有的文化基础和传统的。我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之后再移植来一整套全新的东西。其次,讲道德“重建”,我们还不能忽视现在出现的新道德因素,如有些同志概括的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懒向勤、由依赖顺从向独立争取、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变化就是。这些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是历史的传统,一个是现实的新质,有了这样两个方面,我们“重建”新道德就有了希望。
郑:我也不赞成对新道德的建设持过分的悲观态度。我认为建立新的道德秩序主要有三方面的源泉:第一,是全体民众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随着新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在社会实践中必然会产生新的观念、新的规范,成为建构新道德秩序时最具活力的因素。第二,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适应今后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民族解放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等优良传统。第三,是吸取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积极的文化成果,包括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
苏:文学中价值观念的真空既是道德危机的表征,又是道德嬗变和文学转型的契机。能否把握契机并促成转变,艺术家无疑是关键的一环。当然,今天的艺术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昔日的优越地位,他们也必须和芸芸众生一样在商海中浮沉。而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也难以期望艺术家重新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精神导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艺术家担负起重建道德秩序和观念的先导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我们切不可忘记,艺术家在其整个历史中从来都不是优悠自得的,从西方的贵族保护制到中国古代的科举取仕,艺术实际上始终是在社会的夹缝中生存,而艺术家也只能或侧身于官场仰人鼻息,或遁迹于山林以求解脱。但优秀的艺术和艺术家却始终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其重要的根源就在于艺术家能够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道德使命显然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今天,艺术家尽管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这不应该成为他们放弃社会责任感的理由。应该看到,今天的艺术家们所感到的困惑、忧虑和无所适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刚刚从几十年的政府供养体制中走出来,因而必然要经历一种重新调整、寻找自身位置的过程。而从根本上来看,过去的体制恰恰疏远了作家与社会的关系,使他们无法从切身的体验和经历中感受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的变换与更迭。因而对作家来说今天的阵痛就是一个必需的学习过程。只有当他们经过学习,重新建立起自身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构筑起健全的道德人格时,文学转型才会展现出希望的曙光。
三、转变前景与批评的任务
苏:如果说作家是填补文学价值真空的关键,那么批评家无疑应当充任其中的桥梁和中介。首先,当作家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和道德困惑之际,批评家应该积极地帮助作家清理自身的价值意识,协调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使他们尽快地寻找到自身的位置,恢复自身的道德信念。其次,当艺术作品中出现了新的富有前途的道德意识的时候,批评家应该能够适时地加以发现、阐释,从而促使这种价值观念走向成熟。这些无疑都给批评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批评家必须首先健全自身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意识,在社会的观念变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超前的意识,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宽广的胸怀,既有严密的理论思维又对现实的变革保持敏锐的感受力。只有这样,批评家才能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充当起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未来转换的桥梁。另一方面,现实的变化也要求批评家重新调整自己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既不能板起面孔充当作家的老师,又不能甘心作亦步亦趋的随从和跟班,而必须与艺术家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在多元对话中发挥自身的理论优势,促使作家道德观念的转换早日完成,从而为文学事业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吴:由转型文学的道德问题探讨,来对近些年文学批评进行反思,我觉得有一点需引起注意:这就是在道德与审美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不讲群体规范原则约束的唯美主义,又要防止偏离文学属性的一般道德说教。关于唯美主义问题,近期有些同志联系文学现状指出其症结在于片面武断地排斥社会功能,这颇精当。它说明了我们理论的自省。我这里主要想说的是文学中的道德描写不能偏离文学属性。在我看来,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虽然不言而喻地受到外部社会的规定,但它毕竟是情感性、形象性的。正因此,我们所讲的文学道德其实所指就是文学功能圈的范围,它与社会学、经济学所说的道德是“异质同构”,而并非一回事。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在反对唯美主义之时,很有可能走老路,象过去不少作品那样,将道德不加内化地引进作品,导致文学的概念化;或者,将文学中的道德描写简单斥之为反历史的道德化。后种现象,前些年在评价“寻根文学”时就曾出现过。当时有些文章批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与改革时代相左”,这种看法主要就不是从文学而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着眼。文学相对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它学科,更乐于关怀人的健全、尊严和自由,并且对失败者不幸者满怀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人道主义胸怀、悲天悯人的思想,恐怕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作家。所以,当改革大潮袭来之时,作家最初报以热烈的掌声,但不久,却为之感到忧虑和不安,陷于“两难”困境。作家的这种变化是创作深化的标志,同时又何尝不是他们忠于文学天职的具体表现!我们切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地按照历史的逻辑斥责之。
郑:近年来,一些评论家视道德批评为落伍,放弃了对作家、作品和读者在道德方面的监督和引导,无论是在宏观建构还是微观操作方面都显得有些茫然失措。一部作品出来,要么是一片叫好声,要么是一片沉默。对一些新的文学现象不能作出及时恰切的评价,更不要说有所预见。批评跟着创作走,批评者成了可有可无的帮闲。这种状况无疑是对文学界的道德滑坡起了加速作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批评家自身道德精神归属的迷茫。
现在批评家手中掌握的方法是空前的多样、驳杂。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理论,你方唱罢我登场,似乎是谁的方法最新潮,谁就最有发言权,跟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后面亦步亦趋,脱离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由于缺乏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观照,产生了对文学道德教化功能的冷落和排斥。如果我们牺牲了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么任何理论都会缺乏生命力,也就丢失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所以批评界自身也需要批评,要建立起批评与反批评的健康机制。要改变文学批评被动滞后的局面,首先要从拯救批评自身开始,从加强批评家的修养开始。要意识到中国文学面临的危机和困境的严重性。批评家肩负着建立起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庄严使命,要重铸中国人文精神的浩然魂魄,使中国文学从迷茫的飘移中走出来,结束精神的流浪。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任何一位批评家都应当是一个政论家。”新的道德秩序的建立需要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站在时代的前列,用自己的热情、智慧和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引导理论界、创作界和读者探索前进。19世纪,俄国有一批优秀的批评家,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同时又是思想家和政论家,他们的批评实践对推动俄国文学的发展和俄罗斯民族的解放都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虽然批评家不是救世主,但每一位批评家都应当有严肃的态度、深刻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有献身的热情,对现实社会走向和文学的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
苏:很显然,文学的现代化和道德的现代化都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整个社会的积极参与才能完成。就文学而言,要在世纪之交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换,既需要作家、批评家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宏观的社会背景。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得以完成,社会体制的变革得以实现,道德与文学的现代化才有切实的社会基础。但另一方面,作家、批评家在社会变革面前也决不是被动无为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静待社会变革来重新赐于我们一个井然有序的新的道德体系和精神家园,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现实的挑战。据我看来,旧的一元化的道德秩序已经不可挽回地趋于崩溃,新的道德体系只能在多元对话中建立。所谓对话就要求一种平等的态度和宽容的胸怀,要求我们承认人类所建立的一切价值体系的合理之外,同时又积极地回应现实的要求,在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对话、碰撞及交融中构筑起新的价值体系。因此,我们既应该对当前的道德混乱状况保持清醒的认识,勇于面对现实,同时又要避免敌视现实的价值虚无主义态度,或者试图用旧的道德观念去削足适履地规范现实,约束现实。当然,我们今天还无法许诺和描绘新的文学观念和道德体系的清晰轮廓,但我相信,一种正确的态度、健康的胸怀本身就是产生新的、健全的道德观的必要前提。
郑:现在的文学界需要有鲜明的精神旗帜作为号召。五四时期,在“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下,众多流派和作家创造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峰巅;30和40年代,民族的解放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曾发挥了重要的旗帜作用;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对文学的发展有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文革后的人本主义也曾汇集起一代文学主潮。现在呢?我们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学精神的统一,常常是只见旗旌不见军队,这不能不说是当前文艺理论建设的一大遗撼。这样说并不是抹杀多样性,相反,应当有多流派的繁荣发展。我们希望能够确立共同的文学精神,流派间、作家间多些真诚,多些步调一致的努力,少些门户之见、派别之争。理论家、批评家应当在这方面进行有规划的探讨。
陈:在我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固然带来了一些道德上的负面。然而我们也不可否认人的精神世界、文化欲求也得到了真正释放。从虚空到务实,从百花凋零到五色杂陈,从唯意志论到承认发展生产力是目的,从萎缩、依附、忍从到渐渐生长出独立人格,文学表现的空间应该说更为丰富、更为深邃了。因此,我们的文学现代化与道德现代化正在进入一个继承扬弃、吸纳重铸的新时期,这就需要文学界与批评界建立一种现实的理性的健康心态。走出“中心”,走出“象牙塔”,宽容地对待多元化现实与多元化的文学。文学家与批评家在道德重建中的责任,首先不是去预设一种先验而高玄的规范,以此去削足适履,重建一种新的精神压抑,而应当唤起自己的良知与勇气,勇敢地面对现实、拥抱现实、让她漫过我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又不让物态主宰自己的心灵,同时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真实地而不是虚幻地表现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态,表现出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的激烈冲突——这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与跋涉,然而其艰难与魅力共在,中国文学新世纪的曙光必将在这艰难的选择与跋涉中到来!
吴:就我们现实的生存空间而论,文学现代化与道德现代化可以说是一个前瞻性的话题。因为是前瞻,我们的讨论当然带有构想、理想的成份。我们不必讳言理想。当文学与道德太世俗、太实在的时候,是应该讲点理想的,更何况从本义上讲,“现代化”就是一种充满理想的追求。当然,这种理想不是乌托邦,它是建立在准确把握转型期文学历史方位的基础之上,并且是合历史合逻辑的。我不敢说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但我们的确是在努力认真地探索和实践。愿谨此与我们的同行共勉。
标签:文学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道德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道德观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