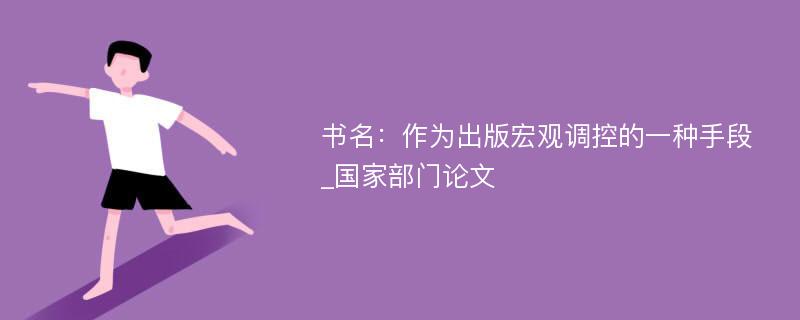
书号:作为出版宏观调控的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号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09)01-0054-04
2007年1月1日新版《中国标准书号》开始实施,是我国出版业在出版物数码识别和数据信息技术方面与世界全面接轨的重要步骤。网上书号实名申领,作为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的折子工程项目,自2008年7月15日开始在56家第一批试点出版单位实行,2009年起将在全国实施,这是我国书号管理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1]。那么,书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对此专门予以讨论。
1 书号及其功用
书号,司空见惯,它是一个符号,一文不值却又千金难买。的确,这组冰冷的数字符号不只作为一个图书的标识物,它也可以作为出版管理的手段,有时说它承载了人生百态、功名利禄也毫不为过。
1.1 书号的含义
中国标准书号由标识符ISBN和13位数字组成,其中13位数字分为EAN·UCC前缀、组区号、出版者号、出版序号、校验码五部分,是“为在中国的合法出版者所出版或制作的每一出版物及每一版本提供的、国际通用的标识编号”[2]。
书号有中国标准书号和书号条码两种识读形式,中国标准书号在出版物上应表示为机读条码。它的适用范围包括图书、电子出版物以及其他非印刷形式的出版物,如互联网出版物等。
1.2 书号的基本用途
首先,书号是出版物的一个基本标识项。它和书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地、出版年、版次项、开本、印张、字数、定价等都是对出版物特征的描述义项。因此,书号也是出版物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其次,书号是文献出版的确认。只有赋予书号,文献才算正式出版,书号对文献具有“唯一性、专用性和永久性”[3]。它也是出版物得以发行、公开进入流通环节的许可“昭示”。书号还是出版物馆藏组织的入口词,是检索查阅出版物的途径。
第三,书号是行业特许经营的表征。只有国家批准设立的出版机构才能获得书号,而可否拥有、使用书号是出版单位合法性与否的标志。它代表了权利、责任、义务,也是获准授权从事出版经营活动,取得经济利益并承担经营风险的条件。
第四,书号还是出版管理部门进行出版宏观管理的重要杠杆和手段。根据“一书一号”的原则,书号的数量即是出版物的品种数。书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发放,发放多少、给谁发放、什么时候发放,也即是对出版物的规模、流向及流量等的调控。
2 书号用于出版宏观调控
出版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书号管理是一种行政手段。相对于同样作为一种行政手段的出版单位的审批、停业整顿、中止经营等的管理,书号调控作用于出版的基本单元产品,因而更详尽、更经常,效果也更直接和明显。下面我们研究运用书号可以在哪几个方面进行出版宏观调控,并简约分析一下调控的效果。
2.1 出版总量控制
目前我国年出版图书总数已超过20万种,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是大而不强,“在国际出版市场上占的份额还很小,影响力也不大;出版业的整体实力还不是很强”[4]。这是中国出版业的基本现状。
有关统计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年出书种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7年出书种数骤然降至历史的最低点。即便如此,倘若以该年为基点,这种逐年上升的趋势也是丝毫没有改变的[5]。图书品种的增长是出版业不断发展和走向繁荣的表现,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出版物品种总量的增长速度和增长幅度也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它应与知识的生产能力、出版能力、图书市场的容量及图书消费者的接受度等相适应,否则就有可能是“泡沫”“滞胀”。一旦出现异常增长,出版管理部门势必实行必要的宏观调节。我国从1994年起对全国出版单位的书号使用总量进行宏观调控。
田智根据权威的官方资料整理出《1981-2005年全国图书种数、总印数、每种平均印数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25年的图书种数从25607到222473,每种图书的平均印数从21.8万册降至2.9万册,总印数则基本上在60亿册(张)上下波动[6]。老出版家巢峰提供了1978年至2003年人均购书册数情况,即基本上在5点几册,“人均购书册数二十几年没有明显增长,近年又呈下滑趋势”[7]。可见,我国出版物种数的长期持续增长,既非出版总量(总印数)与发行总量的增长,也非社会读者占有率(或阅读率)的增长,倒更像是单书销量的稀释。
书号使用总量实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出版工作的有效管理,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8]。当出版业的发展需要靠膨胀的品种来支撑,当出版物质量由于粗放经营而开始滑坡,当出版效率和效益与品种的扩大背道而驰时,出版管理部门别无选择地应擎起书号紧缩的大旗。
2.2 出版社经营管理
出版社的书号有基本量和增发量。年基本量按有发稿权编辑每人5个来计算,这种办法开始于1994年[9],时至今日已很难执行,比如随着出版社人事制度的改革,合同制普遍实行,编辑人员进入的闸门早已放开,因此管理部门更趋向于用各社往年的书号量或平均数来确定这个基本量。而增发量或追加量则复杂得多,它取决于增加品种的理由、出版社的声誉影响以及管理部门的有关考核指标和依据等。
新闻出版总署书号的拨给分为正常发放、增发、奖励和罚减。对优秀、良好出版社可适当追加书号,国家重点图书及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外文版图书可少量追加,受到停业整顿处分的出版社核减书号,对于存在超出批准书号使用总量出书、虚报编辑人数、将申请追加的书号移作他用、超专业出书、买卖书号及其他违规问题的出版社给予批评、缓发书号、扣减书号直至停发书号,对出书结构不合理、图书质量及其他问题的出版社压缩书号总量[10]。
从上述关于书号发放的原则和方法我们不难看到国家管理部门对书号的使用已经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简而言之就是奖优罚劣。那些遵纪守法,经营业绩突出的出版社受到政策性倾斜,反之则受到限制。书号发放办法甚至联系到具体的图书品种以及出版物的质量,可谓至微至细。书号的使用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配额管制,成为指导、调控出版社经营管理的利器。
2.3 出版发行市场管理
书号是出版物的“准生证”,是图书走向市场的“通行证”。出版物市场管理中的图书产品准入、发行活动监管、发行单位年检、违章违法处罚等都可以看到书号的作用和影响。书号的存在,给非法出版物的流入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是市场管理部门监督违规违法经营活动简便有效的工具,据此也可做出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
书号用于发行市场管理的根本表现在于它是市场管理的一项重要依据,这个依据是发行活动秩序的基础。书号的唯一性、专用性、永久性,使其成为出版物最有效的识别标志,是维护发行市场及其行为,保障发行工作的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现实的发行实践中,盗用书号、一号多用、多书一号的情况屡禁不止,对图书市场冲击不小,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市场管理者应切实发挥书号作为管理手段的作用。
2.4 出版业区域发展布局
据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公布的“200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07年我国现有出版社578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拥有出版社数量不等,各地区出版业发展不平衡,其中中央在京出版社就有220家。各地出版业的规模可以粗略地由出版社的数量来表征,如果再进一步也可以粗略地用某地年出书总量,即书号量来表征。中国标准书号每年由新闻出版总署核准发放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书号管理也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进行宏观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
既然国家对书号的使用实行总量控制,那么通过调节各地的书号数量(包括与之相关的批准设立出版社)是可以调控区域出版业布局的。比如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可以优先对西部地区书号的投放。又比如考虑出版资源的不平衡也可以调控书号量以实现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作为整体的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当然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书号在各地的投放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调控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有赖于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从出版业发展的全局利益出发。
2.5 出版物的学科门类构成
出版物学科门类构成比例反映了出版信息流的比重。从某类出版物种数占当年出版物总数的比例可以大体知道该类图书出版情况,如2006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占总品种的0.17%。从某类出版物占当年销售总量(册数)和金额的比例可以大体了解该类图书的流通和消费情况,如2006年教材教辅分别约占销售数量的80%,销售金额的64%[11]。
出版物总体的学科门类构成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片面的逐利动因、盲目的重复出版都会导致结构失衡,为避免出版结构不合理,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书号的发放予以调节。有两种途径,一是对相关出版社书号的增减,二是直接对相关类别图书书号的放宽与紧缩。对出版物学科门类构成的调节是宏观管理可为而且应有所为的内容,遗憾的是这项工作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市场自发调节的问题,但市场调节的效果又是怎样呢?况且出版活动还远没有完全市场化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3 书号管理策略
在对书号的作用,尤其是作为出版宏观调控手段的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来研究书号管理策略问题。
3.1 提高对书号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书号管理的科学性
如前所述,书号量或图书品种数无疑是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既可以代表出版业的繁荣(如规模壮大、发展迅猛),也可能说明行业的畸形发展(如“品种膨胀性增长”[12]、“增长主要靠品种扩张拉动”[13])。现状表明,后一种情况表现得似乎更令人担忧。“我国图书出版种数大幅增长,但是印数却下降,退货增加,库存暴涨,效益下滑,种种现象为出版业敲响了警钟,是我国出版业表面繁荣、实则危机四伏的不良先兆。”[14]
我国出版业图书品种的强劲增长趋势非一朝一夕,政府管理机构从1994年起也已开始进行总量控制,但何以导致今天的局面,甚至被称为“滞胀现象”呢?笔者认为,对书号管理的认识和方法都是值得反思的。
首先应提高对书号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正确认识书号作为出版宏观管理手段的巨大作用,认真地去研究它,掌握其变化和发展规律,才能熟练地运用这一手段,并通过该手段驾驭出版活动的进程。
其次,应加强书号管理的科学性,使书号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书号管理制度应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它是刚性的,那就是促进和保障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它同时又是弹性的,要能不断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需要,及时做出调整以顺应出版实践的变化。应立足于国家知识生产和著述活动的规律性、国家出版总体能力,以及社会受众的需求和消费容量来确定一定时期适宜的出版规模,规划书号投放的流向和流量,主动而不是被动地管理,避免听之任之、走一步看一步或随性而为的决策行为发生。应建立有效的监控系统,及时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大书号手段作为出版宏观调控工具的力度。
3.2 严格书号管理是维护出版秩序的关键
书号违规违法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盗用假冒出版单位的书号、一个书号用于多种出版物、买卖书号等,其中买卖书号的隐蔽性更强、危害和影响更大,买卖书号是出版业的毒瘤,此患不除出版工作必将受害无穷。何谓买卖书号?“凡是以管理费、书号费、刊号费、版号费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费用,出让国家出版行政部门赋予的权力……放弃编辑、校对、复制、发行等任何一个环节的职责,使其以出版单位名义牟利,均按买卖书号、刊号、版号查处。”[15]
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对买卖书号现象十分重视,处罚严厉,1980年代以来出台了有关“通知”和“规定”数十个,但何以令行不止呢?出版单位认识不够、抱有侥幸心理是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驱动使然。有时一本书从头忙到尾还不一定赚钱,但“一号万利”,更别说与书商“合作”变相买卖书号发行印量硕大的图书所得到的更大的回报(殊不知最大的赢家永远是不法书商)。买卖书号是国家专营权的恶性让渡,使国家税收蒙受巨额损失,导致图书滑坡乃至坏书得以生息;而出版单位收获的恶果不仅是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削弱,而且是赖以生存的图书市场的丧失,因此它无异于慢性自杀。
买卖书号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出版活动的冲击和危害有目共睹,它已经严重影响国家正常的出版秩序,严格书号管理是维护出版秩序的关键。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正确的政策和制度,而且还要有强劲的执行力;不仅要管好市场,还应将触角伸向出版的源头,要常抓不懈,重拳出击。我们欣喜地看到即将全面实施的书号网上实名申领重大管理举措的出台,确信其在宏观调控及切实规范出版行为,有效打击侵权盗版活动,治理买卖书号、“一号多用”等违规行为方面的积极意义。
3.3 书号管理改革势在必行
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格局的不断变化,经营模式和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书号管理的方式方法的改革势在必行。比如按照现行的书号分配制度,以发稿权编辑人数作为书号基本使用量的办法就不尽合理,因为对出版社来说增加编辑已不再是难事了。又比如《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但只要我们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还是有问题。它规定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科技方面的学术著作、经国家教委批准的全国统一教材、外文版图书等四类“不限书号”[16]。我们还不论早已没有所谓的统编教材,那么科技出版社或民族出版社的书号岂不是没有了边际(即便是作为追加数亦同)。
笔者认为,书号分配保持宽严相济的原则是正确的。实行分类管理,有些类型的图书(如学术著作)应放松量的限制,而有些图书(如中小学教辅)则应限制书号用量。同时对学术出版应明确允许自费出版,这对于利用社会资金加强学术著作的出版是有积极作用的(看看老师们的项目经费用途很多都赫然列有“出版”一项)。当然前提应是出版社不放弃出版的任何一个环节。
书号有条件地开放也应在研究和考虑的议题之中。我国《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买卖书号、刊号、版号”[17],但那些风声水响的民营书商谁没有“自己的产品”?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彻底清场,另一个是可否考虑使之由暗到明,纳入某种管理模式,以保证质量,保障税收。有人提出由管理部门注册专门公司的办法[18],可以作为借鉴的思路。
此外,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实行量化和专家评估的方法,“书号发放要看社会效益”[19],这也不失为省级出版管理部门进行书号宏观调控的有益尝试,值得推介。
注释:
[1]王坤宁.明年起书号将全面网上实名申领[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06-27
[2][3]姚贞.认真贯彻执行《中国标准书号》为出版业信息化建设奠定基础: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中国ISBN中心)负责人答记者问[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12-20
[4]周鲁,王珊珊.中国图书出版对外交流活跃:中国图书进出口呈明显逆差[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8-29
[5]何皓.面向21世纪的中国出版业:机遇与挑战[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149-149
[6]田智.我国书号调控政策探析:以图书种数与平均印数的比较为视角[J].出版科学,2007(1):40-47
[7][12]巢峰.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兼论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N].中华读书报,2005-01-26
[8]佚名.书号使用总量即将实行宏观控制[J].出版参考,1994(9):1
[9]新闻出版署.关于对书号使用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通知[OL].[1994-05-26].http://chinabook.gapp.gov.cn
[10]新闻出版署.关于加强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OL].[1998-12-02].http://chinabook.gapp.gov.cn
[11]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2006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OL].[2008-10-16].http://chinabook.gapp.gov.cn
[13]周蔚华.也谈中国图书出版业的“滞胀”现象: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看出版改革的症结所在[N].中华读书报,2005-04-13
[14]郝振省.2004-2005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
[15]新闻出版署.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S]//图书出版管理手册(修订本).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16]新闻出版署.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OL].[2008-10-01].http://chinabook.gapp.gov.cn
[17]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OL].[2008-10-01].http://chinabook.gapp.gov.cn
[18]欧阳向英.假如书号放开出版社该采取什么对策[J].编辑之友,2006(1):8-10
[19]佚名.书号发放要看社会效益[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