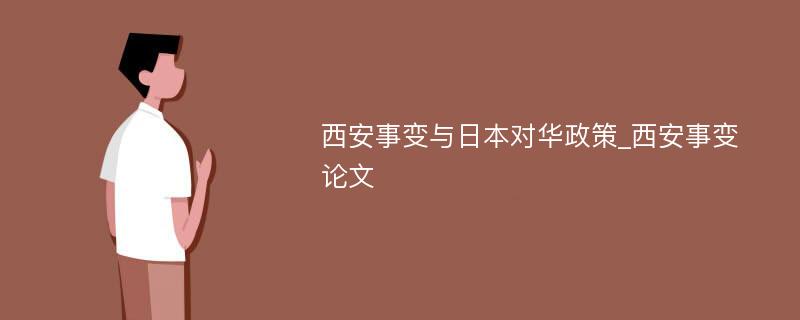
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日本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安事变发生70年来,我国学界侧重于对事变本身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放在事变对于扭转中国国内时局的影响方面,而对于其国际意义的研究,则非常不足。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于日本加剧侵华之际,它所提出的“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与行动,是否发生过影响?影响力如何?这应该是研究其国际意义的重要问题。然而,可能主要由于日文资料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学界除了对于西安事变期间日本的态度与对策等问题有过一些论述之外,总体而言,迄今的研究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①本文拟在拙著有关论述的基础上②,结合笔者在日本东京访问所得的档案史料,围绕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进一步论述西安事变的国际意义。
一、西安事变以前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和初步实施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到1936年8月,日本终于全面确立了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并在西安事变之前,初步付诸实施。
1932年8月27日,斋藤实内阁“阁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的方针》。③关于对华政策,规定了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的原则。关于“对中国本部政策”,它虽然在正文中规定了“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性能”的方针,但同时又规定当前要按照附件甲号的文件进行处理。而在附件甲号的“对中国本部政策”中,则具体规定:“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该文件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与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
上述文件表明日本在即将结束“满洲事变”后④,将仿效伪满洲国成例,对中国本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它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已由“满蒙政策”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也预示了新的对华政策的开端。10月5日,陆军次官以“陆满1489号”电报,向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通报了上述阁议决定的《对中国本部政策》。⑤军部的这个并非曲解的通报,其实更好地反映了该政策的本质所在。
1933年元旦,日军发动了热河—长城作战,开始了新的侵华步骤。2月23日,内田康哉外相致电驻华各总领事,重新解释了阁议决定的上述对华政策。⑥他说这不过是把以前的一贯方针,重新以阁议的方式加以决定,陆海军方面已经予以贯彻。他把上述文件中的对华政策内容加以综合,取消了附件的形式,改为《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要》,其要点共有5项,由驻华官员加以掌握。内田外相的这个并非多余的解释,消除了原来文件中正文与附件的矛盾,从而使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一步完善起来。
“满洲事变”告一段落后,斋藤内阁以广田弘毅就任外相为契机,从10月3日开始,连续五次召开了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就新形势下的外交方针问题大体达成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21日,斋藤内阁召开“阁议”决定了《外交方针》,分别制定了日本对于中国、苏联、美国等国的政策方针。首先制定的是“对华方策”,规定其方针为“在帝国的指导下,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以此确保东洋和平、增进世界和平”,还针对华北局势的变化,制订了一些对策纲要。⑦由于该文件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概括,五相会议同时还秘密决定了“关于具体方策,应在有关各省之间随时协商的基础上加以确立”的原则。⑧
此次《外交方针》之“对华方策”中的“在帝国的指导下”一语,言简意赅地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内在本质,因而最终导致了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天羽声明”的出笼。⑨该事件告一段落之后,按照五相会议的秘密决定,外务省及陆军、海军省的有关课长围绕“中国问题”进行协商。6月1日,外务省成立东亚局,其主管中国事务的第一课,具体承担与陆军、海军省军务局军事课之间的协商。期间,尽管斋藤内阁垮台,7月8日冈田启介内阁成立,但由于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大臣的继续留任,上述过程并没有中断。经过半年多的协商,12月7日,上述三省的有关课长之间终于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⑩
该文件是日本政府的具体决策部门制订的第一份完整的对华政策文件。它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宗旨是:(1)“使中国追随日本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确保东亚和平的方针”;(2)“扩张我国在中国的商权”。该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各项方策的纲要。其中,既有一般性的方策,也有对于南京政权、华北政权、西南派及其他地方政权的方策,还有关于扩张商权的方策。(11)它既是前年阁议决定的“对中国本部政策”的现实化,也是去年五相会议决定的“对华方策”的具体化,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同时,它还把去年《外交方针》中的关键词“在帝国的指导下”修改为“以帝国为中心”,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是使中国依附日本。这份文件成为1935年日本各方在华北制造各种事件、进行经济扩张的政策依据。
1935年上半年,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主导的南京政府,展开与日本的亲善、提携活动。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2)之后,6月间,广田弘毅外相命令外务省东亚局,筹拟全面调整日中国交的基本对策方案。(13)东亚局奉命与陆、海军省军务局进行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10月4日,冈田内阁的外、陆、海三相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的文件。(14)
该文件首先确立了与1934年12月7日文件基本相同的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为了应对中国方面提出的三原则,提出了日本关于调整日中关系的三项原则(15),后来由广田外相在1936年1月21日的第68次帝国议会发表的演说中对外公开(16),遂被称为“广田三原则”。三大臣在决定该文件的同时,还通过了一份由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陆军省军务局长(今井清)、海军省军务局长(吉田善吾)共同决定的附属文书。该文书特别规定:1934年12月7日《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在今后尚未制定出可以取代者之前,应与本谅解文件并行而继续有效。(17)上述文件及其附属文书,不但把上年12月7日由三省课长之间的决定上升为三省之间的决定,而且进一步延续、重申了其内容。这些文件得到贯彻以后(18),继续成为1935年底日本各方配合进行“华北自治运动”的政策依据。
华北事变后不久,日本认为有必要单独确定作为国策的“华北政策”。1936年1月9日,参谋本部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总结了华北事变,并提出今后的目标是“使华北明朗化变成现实”,并要使华北自治运动“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19)据此,13日,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了《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对于华北政策进一步明确规定:主旨在于援助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自治;自治的区域为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目前首先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二市的自治,其他三省自动与之合流,支持冀东政府的独立性。(20)17日,陆军省又向驻华官员通报称:外务、海军方面对于上述文件的宗旨,没有异议。(21)这样,以上述《处理华北纲要》为标志,华北政策正式成为日本的国策。(22)
如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把“满蒙政策”独立于对华政策一样,华北事变后“华北政策”作为国策的单独制订,是日本对华政策上的又一个重要变化。它意味着,日本将仿效扶植伪满洲国的做法,经由华北自治,进而分治中国。因此,日本军部与政府共同达成的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所确立的分离华北的政策(23),“是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4)。
1936年“二·二六”事变之后,日本国内政局剧变。3月9日,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4月2日,前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在面临所谓1936年的国际危机之时,在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化的影响下,随着“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日本军部更加左右国策。6月初,日本陆、海军共同决定了第三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获得天皇批准。30日,它们又共同决定了《国策大纲》,提出了日本“南北并进”的对外国策,并要求政府据此制定相关的政策。(25)在军部的支配下,日本的对华政策迅速全面确立下来。
8月7日,广田内阁首先召开了“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基准》,规定了日本“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的根本国策。随后,又召开了除藏相之外的“四相会议”,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了日本遵循上述国策的对外政策;关于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规定要参照1935年10月4日的对华政策决定,而当前对华政策的重点则规定为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并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还要使整个中国反苏、附日。(26)
根据上述外交方针,11日,广田内阁的有关各省之间又决定了《对华实行策》(27),同时还决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28)。《对华实行策》是关于当前对华应该采取的措施,共分为“对华北施策”、“对于南京政权的施策”、“对于其他地方政权的施策”、“对内蒙施策”四项。在“对华北施策”中明确提出了“华北五省分治”的目标。在《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中,对于“华北政策”又进行了专门的规定:进一步确认了“华北五省分治”的目标,规定了对于冀察政权、冀东政权以及山东、山西、绥远政府进行内部指导的措施,还规定了华北经济开发的政策。此外,关于开发华北经济的政策,则在通过《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的同时,广田内阁的有关各省又通过了两份附录文件:第一件为当前对于冀察政权方面(冀东政府亦适用之)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经济政策,包括关税处理、金融政策、关税以外的中央税的处理、交通通信等;第二件为提示华北国防资源中应迅速加以开发的项目,包括铁矿、炼焦用煤矿、盐、棉花、液体燃料、羊毛等“国防资源”,以及为开发上述资源所需要的交通设施,等等。(29)
8月7日和11日,广田内阁关于日本的国策→→→外交方针→→对华政策→华北政策的一系列文件的制订,标志着其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
上述政策确立以后,从8月中下旬开始,日本各方配合、多管齐下,企图在中国全面付诸实施。陆军以中国驻屯军为主,继续加紧实施华北分治政策。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于9月15日拟订了《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规定了分割、占领华北的计划,从而将日本的华北政策及其实施,进一步具体化。(30)关东军则加速实施“内蒙政策”,策动伪蒙军,制造了“绥远事件”,西向入侵绥远省。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日军在华北的行动,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在南京开始了关于调整日中国交的谈判。日本海军还借口广西北海发生的事件,在中国华南沿海采取旨在侵占海南岛的积极行动,以配合华北陆军和南京的谈判。日本大有志在必得、一举成功之意。
但是到了12月初,日本的侵华行动却遭到了初步的失败。先是中国军民的绥远抗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在谈判期间就已经开始转变对日政策的南京政府(31),于12月7日主动停止了对日谈判。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否定了宋哲元被迫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签订的华北经济提携的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中国面临着是继续实施既定的对华政策、还是放弃上述政策的抉择。西安事变就在这样的外部背景下爆发了,它首先打乱了日本的侵华步骤。
二、西安事变期间日本的对策与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事变,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对于蒋介石“为最后之诤谏”的八项主张。(32)这八项主张的核心“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33)作为事变主角的张学良,在晚年的1990年,打破50余年的沉默,首先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NHK)到台湾的独家采访,苦劝日本应该记取历史教训。(34)随后他来到美国,向历史学家坦承:自己与蒋介石冲突的根源在于“攘外”。(35)以“一致抗日”为目标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凸现了日本侵华政策对于中国政局的影响。而日本文部省2005年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增加的“西安事变”一节,竟诬称西安事变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这不但辜负了张学良的上述苦心,也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36)
12月12日深夜,西安“兵变”的消息传抵东京。13日东京的晨报,均以头号大字,刊载来自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消息;各日报也发出多次号外报道;许多关心中国的日本人也到中国大使馆探问不辍。(37)
西安事变爆发后,从12月13日起,日本在华的外交官员们就予以高度的关注,不断地向东京的外交大臣报告中国方面的舆论和新闻论调。(38)日本国内的一些府、县,对于当地华人社会对此事件的反响情况也十分关注。(39)尽管现存日本外交档案中关于西安事变最重要的“陆海军情报”已经缺失(不排除被人为毁坏的可能)(40),但是以下一些仅存的日本文书和来自中国方面的外交情报,仍然可以证明日本决策当局的态度与对策。
13日,日本政府做出了最初的反应。一是海军省于下午召开首脑会议,决定了《关于西安兵变的我方对策纲要》,并由军务局长以“机密第675号电报”,发给在华的第三舰队参谋长和驻南京的海军武官。该电报指出:日本方面在加强在华警备兵力的同时,要采取光明正大的态度,而且要“利用此次兵变,以期推进对华政策(但应注意不要玩弄区区小策)”,并规定了一些具体对策措施,最后特别指出“该电报的宗旨,已经获得了外务省、陆军省的同意”。(41)这是日本官方的第一反应。二是外务省于晚上6-10时召开了首脑会议,半官方宣布的会议决定是:须等待正确的消息,不应采取利用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于招致误解之任何行动,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避免积极行动;并声称上述方针已获得陆军、海军二省的完全谅解。(42)同日,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也致电陆军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主张“要根据帝国的既定方针,寻找逐渐完成华北分治的好机会”(43)。
在海军方面与外务省已有对策、驻华日军已提出建议的情况下,14日,陆军省决定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提出的对策方针是:“日本依然坚持并希望实现既定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要以特别公正的态度对待此次事变,以期掌握中国的民心。但如果南京政府及其他地方政权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抗日、反日思潮,侵害日本侨民安全或在华权益,则须毫不犹豫地发动自卫之权。”在“纲要”部分中,又将上述方针具体化为6条,主要为:“对于此次事变,不必改变以往的方针,而要沿续并推进既定的外交方针和对华实行策,监视事态的发展”;对于华北则希望“实现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并相机将防共协定的范围扩大到五省”;对于内蒙,则按照既定方针采取措施,同时要通过内部政治工作,引导绥远政权走向反共,阻止苏联的潜在威胁等等。(44)由于日本陆军是在华拥有主要势力的集团,陆军省在吸纳了海军、外务方面意见后作出的上述决定,其实是一份最为全面的日本关于西安事变的对策文件。它所提出的“沿续并促进”既定对华政策的原则方针,无疑具有更大的代表性。
在海军、外务、陆军三省均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后,15日,陆军、海军省的军务局长及军务课长,与外务省的东亚局长及中国课长,共同在外务省召开了会议。在听取了陆军省军务局长矶谷廉介关于上述对策的说明后,经过协商,三省的主管官员们一致同意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沿续并促进”的方针。(45)
可见,西安事变之初,在消息不明确、蒋介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与军部确定的对策就是要在1936年8月份既定的对华政策基础上,以西安事变为契机“沿续并促进”之:既不为事变所动,毫不动摇地贯彻既定政策,又要尽可能地利用事变,以促进既定政策的实施。这显然就是一种“火中取栗、趁火打劫”的态度,表明了日本企图借机促进与扩大中国的内乱,继续实施其侵华政策,以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但同时,日本也在情况不明之时,为自己的对策预留了活口,那就是以外务省为主的对华持静观待变立场的外部表态。
根据上述方针,17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时表示:“由于此次事件对于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予以重大的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对于那些主张容共联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他们迅速消失。”18日,外务省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的非正式声明,再次公开表明了日本政府的上述态度,并指明中国方面对于张学良的容共抗日之举“必须采取严重、适当的措施”。(46)这是日本最初表达的强硬态度。
但是,日本政府的上述对策,首先受到了来自国内的反对。15日,日本社会大众党发表了对华方针的声明,指出西安事变是日本转换对华政策的绝好机会,要求政府清算、转换以前的对华政策,对于中华民族之统一国家建设,采取援助方针。东京的日本知识界多次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国的局势,提议日本应利用目前良机,对中国表示友善,而谋根本调整两国将来的关系。日本的普通民众也认为西安事变为日本重新检讨其对华政策之重要时机。(47)其次,由于事变以后,中国各地并未发生内乱且南京政府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由于16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蒋介石仍然健在”的声明,17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的手令到达南京,使得局势更加明朗化,再加上其他各国态度的影响等因素,日本被迫迅速改变原来的立场与对策。
18日,日本对于西安事变“神经过敏之揣测已大见冷静”。有田外相在阁议席上,报告了中国方面的统一情况和中国报纸对日本持静观态度的赞扬,引起了各位阁僚的注意。(48)19日,有田外相主动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特别关注蒋鼎文携带蒋介石手令回到南京一事,并甚为关心“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还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当许声称不会妥协后,他又表示对于中国政府处置事变的奋斗努力“深切同情”。(49)
19日以后,当宋子文、宋美龄相继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即将出现时,日本马上命令因此前的外交谈判失败而回国的驻华大使川越茂返回中国。21日,川越到南京拜见外交部长张群,重申了有田外相的上述意见,并代表日本政府对于蒋介石此次被困表示慰问。23日,川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表示了对于西安事变的关切与慰问之意。(50)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广田弘毅23日在枢密院会议上表示“对西安事变决采不干涉方针。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51)日本在声称不干涉方针的同时,其实仍然不忘的是干涉南京政府的“容共”。
尽管如此,西安事变迅速和平解决的最后结局,并不是日本所能够左右的。12月25日蒋介石飞抵洛阳,26日回到南京。26日早晨,东京各报“以为陕变之和平解决,为中国人民热诚拥护统一之结果……眼光远大之日人,表示意见谓,中国统一之基础已极稳固,西安事变,即为其显著的试金石,今后惟有更趋巩固耳”;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因陕变发生,稍有改变……痛诋日政府对华观察错误者,颇不乏人”。(52)
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了“沿续并促进”的对策方针,企图趁机继续实施全面确立的对华政策;在情况明确以后,又被迫采取静观待变的态度,但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下,却坚决于预中国的“容共”问题。尽管如此,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阴谋。因此,日本《战史丛书》所谓“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的说法(53),应该是有违于历史事实的饰非之语。
三、西安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再确立
1936年底,中国绥远抗战的胜利,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宣告了日本贯彻实施对华政策企图的全面失败。因此,绥远事件和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为两个“决定命运的事件”(54)。受其影响,1937年初,日本政局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二次大动荡。同时,伴随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国内形势的剧变,日本朝野兴起了“对华再认识论”的潮流,并要求调整、修改1936年8月确立的对华政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日本在1937年上半年仍然继续关注该事变的善后及其在中国内部的反响。(55)由于1936年下半年日本对华外交上的失败,日本政府特别是有田外相,最早受到了来自各方势力的攻击。1937年初,广田内阁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终因难以调和军部与政党的正面冲突,于1月23日宣布总辞职,“有田外交”随之告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配着广田内阁的陆军,成为此次倒阁的主力。日本陆军不但搞垮了该内阁,还不惜使用拒绝推荐新陆相入阁这个“杀手锏”,使得统制派首领宇垣一成的组阁计划也流产了。(56)2月2日,日本组成了林铣十郎内阁。林内阁因此成为军部占主导地位的内阁,事实上也是“更加坚实的法西斯化”内阁。(57)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并做出了“四项保证”。15-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无论如何他是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58),“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59)。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国内团结抗战的局面基本形成。对于这次全会及其可能带给中国和日本的影响,日本同样寄予了高度的关注。(60)
早在1936年下半年,日本国内的舆论界,就提出了“中国再认识论”;西安事变后,“中国再认识论”进入了第二阶段。(61)1937年1月的《中央公论》出版了名为“学良兵变和支那”的“新年特大号”特辑,其中尾崎秀实写于12月13日的《张学良兵变的意义——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爆发》,认为南京政府不会因为蒋介石的突然离去而土崩瓦解,因为该政府多年来建设统一国家的政策得到了相当多民众的支持,而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将在日本的压迫下更趋强烈。但波多野乾一的《蒋介石的继承人?!》则认为蒋氏没有继承人,中国将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时代。(62)来自日本学人的上述两种判断截然不同,但波多野的观点在当时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中却很普遍。
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也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逐渐发生了变化。在1937年2月号的《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的《中国问题的所在》,开头明确指出“西安事变的戏剧性效果所鲜明表现出的形势,就在于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抗日态度的强化”。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前进中的民族国家的统一建设的中国来认识”;平贞藏的《南京政权与抗日外交》也指出西安事变给日本人的启示是“要重新认识中国”,“必须开拓日中双赢的道路”。(63)上述表明,在日本的媒体议题、公众舆论之中,已经形成了新的“中国再认识论”,并且这种论调已经发展到要求政府修改既定的对华政策的地步。
与此同时,“二·二六”事变后主宰日本政局的军部势力,以陆军的石原莞尔为代表,也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主要从对苏防备的战略出发,要求重新认识中国,并反思8月制订的对华政策。1937年1月初,参谋本部第二课(战争指导课)拟订了修改上述既定政策的文件,海军军令部也决定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直到林内阁成立前后,军部在支配政局的同时,继续推动对华政策的调整。(64)
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之下,林内阁成立之后,就开始考虑调整以往的对华政策文件。
在林首相兼任外相期间,日本政府就针对广田内阁1936年8月制订的两份对华政策文件(《对华实行策》、《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进行了初步的修改和调整,并由外务省有关当局与陆军、海军方面基本达成了协议。3月3日,佐藤尚武就任外相,奉行对华外交的新理念(65),推行所谓的“佐藤外交”,并继续调整对华政策。在外务、陆海军三省协商的基础上,4月16日,林内阁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共同决定了取代上述政策文件的《对华实行策》和《指导华北方策》。(66)
《对华实行策》遵照的是1936年8月7日的《帝国外交方针》,并且是鉴于1936年8月11日的《对华实行策》实施以来的情况和中国当前国内形势的走向而制定的对华措施。它虽然把“对南京政权的施策”放在首位,但是在政策内容上并没有太大、太多的改变。此次修改最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在于对华北的施策,在该文件中虽然有所规定,但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的《指导华北方策》(67)之中。
与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相比较,《指导华北方策》在华北政策的宗旨上,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分治政治”,但其目标仍然是一致的,即“使该地区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的地带,获取国防资源,并扩充交通设施,从而一来防备赤化势力的威胁,二来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基础”。为达到该目的,当前的策略主要是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以及文化工作,同时要尽快解决华北的走私贸易以及自由飞行问题。为此,外务省在与陆军协商的基础上,还在5月10日制订了关于解决冀东走私贸易及华北自由飞行问题的文件。(68)
与“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政策上经历的“内田外交”、“广田外交”、“有田外交”相比较,“佐藤外交”主导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在华北政策上,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调整了以往的实现华北自治——华北分治的宗旨,改为主要依靠经济与文化的策略手段,实施对华政策,并在一些焦点问题(主要是日本在冀东的走私与华北的自由飞行)上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这是我们应该首先看到的。这些修改,与其说是日本方面的主动,倒不如说是被迫,而中国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及其带来的国内一致抗战局面的形成,无疑就是重要的外部因素。
但是,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这次调整对华政策仍然有限,主要表现在:(1)日本在对外政策的大背景上,仍然是遵照广田内阁的《帝国外交方针》,而且这个方针关于对华政策已经有了原则的规定;(2)军部特别是陆军的主张仍然占有主导的地位;(3)不管在华北实施以前的以分治为主的政治工作,还是现在的经济与文化工作,日本在华北要达到的政策目标并没有改变。因此,“佐藤外交”关于对华政策的调整,其实并未改变日本以往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69),只不过是对华策略与手段的某些改变。它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过是日本在大战以前施放的烟幕。(70)
直到5月上旬,林内阁关于调整对华政策的有关文件才准备就绪。从5月下旬开始,外务省东亚局、陆军省、海军省军务局,分别派人向驻中国的各机关传达贯彻。但就在他们的现地传达过程尚未结束之际,伴随着5月31日林内阁的总辞职,“佐藤外交”也夭折了。这样,上述调整后的对华政策,并未付诸实施,它们还只是停留于作为文书的状态。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内阁成立。曾在林内阁之前长期担任过外相并一度担任过首相的广田弘毅,再次出任外相,开始了第二次“广田外交”。近卫内阁成立后,在对华政策上将如何进行选择?如果继续实行“佐藤外交”的政策,就等于自我否认。何况,上述政策在制订和贯彻过程中,一直受到关东军的强烈反对。(71)而关东军又是“九·一八”以来在华北政策上最有发言权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近卫内阁可能的选择,一是回归一年以前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二是制定本届内阁的新政策。
近卫组阁之际,蒋介石就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近卫组阁……必较历来强固,对华之政策,亦当更坚决与积极也。”(72)当时奉命收集日方情报的王芃生,在经过分析后,也于6月19日电告蒋介石说:日本内外将有重大变化。(73)中方的预言,很快就得到了日方的证明。
6月12日,近卫首相在西下的列车上表示,对华政策最好还是广田内阁时代的三原则。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随后进一步明确表示:要采用广田内阁时代决定的《对华实行策》及《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74)广田外相本人的意见,则体现在6月20日给驻华大使川越茂的归任训令中,他指示:“侧重对华自主积极的推进,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75)从他们的上述表示可以看出,否定“佐藤外交”的对华政策,而回归到上年8月全面确立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已成为近卫内阁在对华政策上的当然选择。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近卫内阁于7月6日召开了“阁议”,以讨论确立施政方针问题。广田外相在会上表达了下述见解:日本的对华外交方针,虽然与以往相比并无改变,但并不准备强行采取对华亲善;而在当前抗日、排日的潮流中,即使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有成效。日本方面诚然不能不对此表示不满,但是,除了毅然推行正确政策之外,别无他途。广田的意见得到了全体阁僚的一致同意。(76)虽然此次“阁议”的文件迄未见到,但是广田外相提出、全体阁僚一致同意的“毅然推行正确政策”的意见,应该就是近卫内阁要将以往的对华政策付诸实施的先声。这已经到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
1937年上半年,日本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迫重新认识中国,并在本国政局出现大动荡后,林内阁期间以“佐藤外交”修改与调整对华政策。但是,由于日本不可能根本改变对华政策,对华认识严重不足,被迫进行的这次政策调整非但十分有限,而且迅速夭折。近卫内阁再次推出了“广田外交”,并迅速回归到1936年8月既定的对华政策,终于在卢沟桥事变后,将全面侵华政策付诸实施。
通过以上论述,就西安事变的国际意义,特别是它对于日本的影响而言,笔者可以指出的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逐步确立侵华政策,并在1936年8月全面确立了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随后即初步付诸实施;西安事变的爆发,不但打乱了日本的侵华步骤,也使得“一致抗日”成为中国最具国内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目标。西安事变期间,日本最初采取了“沿续并促进”的对策方针,企图趁机把全面确立的对华政策,进一步加以实施;在明确情况以后,被迫采取了静观待变的态度,却又坚决干预中国的“容共”问题。但是西安事变的迅速和平解决,最终打破了日本的企图。西安事变后,中国国内团结抗战局面的迅速形成,迫使日本统治集团重新认识中国,并导致了日本政局的大动荡。林内阁期间,日本虽然企图以“佐藤外交”调整既定的对华政策,但由于日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既定的对华政策,它对于西安事变后中国的认识仍然严重不足,“佐藤外交”迅速夭折,近卫内阁重新回归于该政策,最终在“七·七”事变后走向了全面的侵华之路,中国人民也奋起走向了全面抗战。日本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对华政策,又难于正确地认识现代中国,其历史教训同样也是深刻的。
附记:本文曾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日照,2006年8月)及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延安,2006年11月)。值拙文发表之际,笔者再次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荣维木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李云峰教授在会议期间的评议和指教,并特别感谢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西村成雄教授,他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重要的日文资料。
注释:
①目前的相关论文只有罗平汉《试论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事变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探索》1997年第1期),该文虽然也着眼于西安事变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并对事变后的日本侵华政策进行了较好的论述,但因其日文档案史料的运用很少,论证上仍然有较大的局限。此外,史滇生、史习基《西安事变前后中日海军的动向》(《军事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论述了日本海军对事变的反应;孙乃伟《西安事变与日本》则利用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日本东洋协会调查会和满铁总裁室弘报课在1937年1月编辑的资料,考察了日本方面的反应(李仲明:《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最新的专著只有周天度等著《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中华书局2002年版),对于事变期间的日本对策有所论述,但篇幅很小,内容十分有限(第707-709页)。2006年11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3篇论文涉及这个课题,其中两篇根据一般性的中文资料和日本人在中国沈阳办的《盛京时报》,对于日本的态度和反应进行了论述(许述、张冬梅:《日本与西安事变》;王志刚:《日本对西安事变的一些观点和反应——从〈盛京时报〉角度的分析》);另外一篇是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提交的,他根据日本学人在媒体上的论述,研究了日本的对华认识问题(西村成雄:《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的中国再认识媒体话语》)。
②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9-273页。
③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东京,原书房1978年版,“文书”,第206-210页(以下简称《主要文书》下卷)。
④中方所称“九·一八”事变的下限为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所称“满洲事变”的下限为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
⑤《满密大日记》昭和8年24册内之18,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⑥《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关系一件》(松本记录,第1卷),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外务省记录,A.1.0.0.10(本文中所引“外务省记录”均收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以下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⑦《主要文书》下卷,第275-276页。
⑧1933年10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的公开发表稿。但发表的内容与原件的差别很大,而且也删去了“在帝国的指导下”一语。《帝国ノ对外政策关系一件·五相会议关系》,外务省记录,A.1.0.0.6-3。
⑨1933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就中国的国际援助问题发表了非正式谈话(《主要文书》下卷,第284页),是为“天羽声明”,又称“四·一七声明”。
⑩关于以上过程,参考《关于中国问题与军部的协商之件》(1934年12月27日亚一调书),《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关系一件》(第3卷),外务省记录,A.1.1.0.10。
(11)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22-24页。
(12)中国方面最先由国际大法官王宠惠在1935年2月20日路过东京时,向广田外相提出了三原则。6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次长唐有壬在会见新任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以及6月17日新任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在会见广田外相时,均表示了中方的上述意向。
(13)广田弘毅传记刊行会编集、发行:《广田弘毅》,东京,1966年版,第158页。
(14)以上过程,参考《对支政策决定ノ经纬》(外务省东亚局一课调书),《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关系一件》(第4卷),外务省记录,A.1.1.0.10。
(15)《主要文书》下卷,第303-304页。
(16)《主要文书》下卷,第324-326页。但应该指出的是,广田公开的三项原则,与该文件的表述有差别;他还在演说中谎称“中国政府已赞成此原则”。
(17)《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108页。
(18)1935年10月10日起,外务省派遣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守岛伍郎,先后到中国的上海、南京、青岛、天津、北平、长春,召集当地的各使领,进行了传达;后来又由汉口总领事召集长江上游各公馆长会议、由广东总领事在香港召开华南各公馆长会议,分别继续传达。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冈村宁次、军令部第六课课长本田忠雄,分别赴华,召集各地陆、海军各武官会议,进行了传达。《帝国ノ对支外交政策关系一件》(第4卷),外务省记录,A.1.1.0.10。
(19)《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128-134页。
(20)《主要文书》下卷,第322-323页。
(21)《陆满密缀》(昭和11年第7号),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
(22)《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349-350页所收录的该文件,系日本政府的决定,并含有陆军省军事课的方案。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86·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66页:“1936年1月13日,日本政府决定了(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恐非笔误。
(23)因为1936年8月11日日本又决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故1935年1月13日决定的《处理华北纲要》被称为“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
(24)〔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5页。
(25)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8·大本营陆军部(1)昭和十五年まで》,东京,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88-389页;《战史丛书91·大本营海军部 联合舰队(1)开战まで》,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297-298页。
(26)《主要文书》下卷,第344-347页。
(27)《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366-367页。
(28)《主要文书》下卷,第347-348页。
(29)《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369-371页。
(30)参见拙文《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31)1937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人说:国民党政府转变政策“是在张群与川越的谈判期间开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33)《张学良、杨虎城告全体将士书》(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0页。(34)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年 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5)张学良1990年在美国接受唐德刚采访时说:“我与蒋先生的冲突,没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一点没旁的冲突。”《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2001年10月28日台湾《联合报》。另参见〔美〕唐德刚访录、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646页。
(36)臧运祜:《日本教科书歪曲西安事变》,2006年12月15-21日《国际先驱导报》,第4版。
(37)中央社东京电(1936年12月13日),朱文原编:《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台北,“国史馆”1993年版,第362页。
(38)《西安事件·舆论并新闻论调》(外务省记录,A6.1.5.10-1)收录了1936年12月13日—1937年6月17日的报告多份。
(39)《西安事件·府县报告》(外务省记录,A6.1.5.10-2)收录了1936年12月14日—1937年1月22日的报告多份。
(40)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总目录(战前期)》别卷,东京,原书房1993年版,“消失外务省记录”,第91页。另参考拙文《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41)《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外务省记录,A6.1.5.10-4。注:《现代史资料》7“日中战争”1第286页所引资料,与该原件有些差误。
(42)中央社东京电(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367页。
(43)《现代史资料》7“日中战争”1,第631-632页。
(44)《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外务省记录,A6.1.5.10-4。注:陆军省文件的“纲要”部分原有7条,后吸取了外务省的意见,改为6条;修改后的这份文书,又载《现代史资料》7“日中战争”1,第608页。
(45)《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外务省记录,A6.1.5.10-4。
(46)《西安事件·参考资料及调书》,外务省记录,A6.1.5.10-4。
(47)同盟社东京电(1936年12月16日)、中央社东京电(1936年12月17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384-386页。
(48)中央社东京电(1936年12月18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388-389页。
(49)中央社东京电(1936年12月19日)、许世英致孔祥熙电文(12月19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390-391、404页。
(50)中央社南京电(1936年12月21、23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393、397页。
(51)许世英致孔祥熙电文(12月23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404页。
(52)驻日大使馆丁绍伋致外交部电(1936年12月26日)、中央社东京电(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第1册“重要函电”(上),第397-398页。
(53)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17页。
(5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420页。
(55)《西安事件》(外务省记录,A6.1.5.10)收录了1937年1月1日—6月17日驻华各使领的报告多份。
(56)林茂等编集:《日本内阁史录》(3),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版,第423-427页。
(57)李凡夫:《从广田内阁到林内阁》,黑白丛书社1937年版,第47页。
(5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5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60)在此次会议前后,作为日本对华决策中枢机构的外务省与陆、海军省就收集并发表了大量的资料。小林龙夫、稻叶正夫、岛田俊彦、臼井胜美编:《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版,第257-312页。
(61)西村成雄:《“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的中国再认识媒体话语》,“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延安,2006年11月。
(62)《中央公论》1937年1月号,第406-414、418-422页。
(63)《中央公论》1937年2月号,第4-17、103-115页。
(64)参考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第276-277页。
(65)佐藤向林首相提出的就任外相的四项条件之一,就是“必须以平等的立场,与中国进行和平的谈判,以调整国交,缓和两国之间的利害冲突”。佐藤尚武:《回顾八十年》,东京,时事通信社1970年版,第354-361页。
(66)《主要文书》下卷,第360-362页。
(67)该文件原本接续以前的文件而称“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最后接受了海军方面的建议,而改称《指导华北方策》。
(68)《主要文书》下卷,第362-365页。
(69)《日本内阁史录》(3),第436页。
(70)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1937年5月2-14日于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针对党内对“佐藤外交”的模糊认识,明确指出:“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就在我们面前。”《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5页。
(71)关东军的意见书,参考《支那事变关系一件》第30卷(石射文书),外务省记录,A.1.1.0.30。
(72)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中央日报社译印:《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出版部1986年版,第200页。
(73)《国民政府档案(二)·国民政府对日情报及意见史料》下册,台北,“国史馆”2002年版,第159-161页。
(74)转引自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版,第227页。
(75)中国驻日大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电(1937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1966年版,第128页。
(76)《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