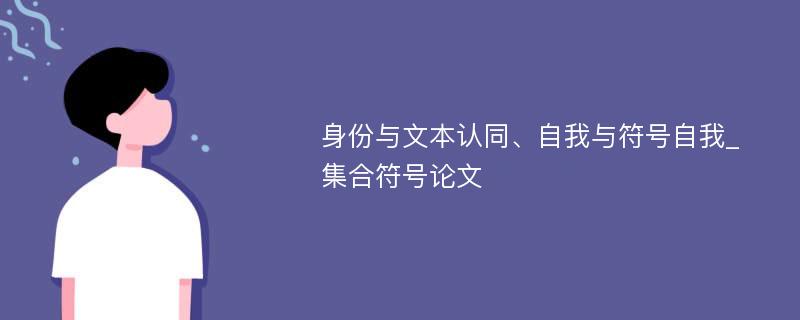
身份与文本身份,自我与符号自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我与论文,符号论文,文本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我与身份
理想的符号表意行为发生在两个充分的自我之间:一个是发送自我,发出一个符号文本给一个接收自我。发送自我在符号文本上附上了它的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携带着意义,接收者推演出他的解释意义。这三种意义常常不对应,但是传达过程首尾两个自我的“充分性”使表意得以顺利进行。
在这里,“充分性”并不是对自我资格能力的考量,而是指有足够的自觉性处理意义问题。自我意识并不是意义对错或有效性的标准,而是表意活动双方是否互相承认对方是符号游戏的参加者,只有承认对方,表意与解释才得以进行,而承认对方的“他者”自我,是自我确立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出现表达的意向。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说:“表述是一个志愿的、坚定的、完整的意识到意向的外化。如果没有使符号活跃起来的自我意向,如果自我没有能赋予符号一种精神性,那就不会有表述。”①
这样的自我,是相互的,是应答式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自我并不能单靠冥思而建立,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建立。自我是一个社会构成,靠永不停止的社会表意活动构筑自己。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区分自我与身份。身份是任何自我发送符号意义或解释符号意义时必须采用的一个“角色”,是与对方、与符号文本相关的一个人际角色或社会角色。身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如果面对的完全只是自己,可以将自己幻想成任意身份,那么身份就可以随意变化。除非是精神分裂者,他在自己心中,用同一身份传送并接收符号。
人一旦面对他人表达意义,或对他人表达的符号进行解释,就不得不把自己演展为某一种相对应的身份。对于一个特定的人,他有可能或有能力展示(或假扮)某些身份,而无法或很难展示另一些身份。老人不便“装嫩”,无知者很难展示学者身份,男子很难装女子身份。但是身份是有弹性的。写作时的性角色(例如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用男人身份写作),可以有真有假;同性恋中的性角色,就难以说是假的,因为没有“真的”性别身份。对身份不能轻易谈真假,或者说,没有身份是“本真”的。
但是身份是表达或接受任何符号意义所必须,是表达与接受的基本条件;自我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依托一个身份才能进行。我们可以以教师身份对学生说话,以法官身份对疑犯进行审判,以观者身份迷恋一部电视剧。不可能想像不以一种身份进行社会表意或解释。面对同样一条命令,发号施令者的身份不同(父亲、长官、法官、教师),一个人就不得不采用对应的身份(儿子、士兵、犯人、学生)应对。他的解释,也就在这个身份上建立。他可以拒绝采用这些身份,采用另样的(例如逆子)身份,这样父亲的话就失去了命令的权威性,同样的符号文本,意义就会不同。因此,意义的实现,是双方身份对应(应和或对抗)的结果,没有身份就没有意义。
人的任何活动都采取一种身份,人不可能以纯粹的抽象的自我进行意义活动。在表达或接受一种意义时,任何自我都无法逃避采用一种身份,社会把这些符号交流身份分作很多类别范畴:性别身份、性倾向身份、社群身份、民族身份、种族身份、语言身份、心理身份、宗教身份、职业身份、交友身份等等。随着文化局面的变化,还会有新的身份范畴出现,例如最近出现的网络身份(online identity)。
自我是各种身份的出发点,也是各种身份的集合之处。那么自我是否就是个体的各种身份之集合?有的学者似乎是如此考虑的。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的描述极为通俗:“自我”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例如身体、能力、房子、家庭、祖先、朋友、荣誉、工作、地产、银行账户。② 的确,每一个“拥有”都涉及身份问题。查尔斯·泰勒也认为认同构成自我,而人的社会行为不得不不断地作认同。③
身份似乎是每次表意或解释的临时性安排,但是一个人有一个自我作为他的各种身份的出发点,这些身份就有了三种特征:“独一性”(uniqueness),即该自我有充分自觉的选择能力;“延续性”(continuity),各身份均符合该自我的一贯性;“归属性”(affiliation),这些身份导致该自我的社会关系。
这三种关系实际上是三种“感觉”。身份取决于感觉,是自我“觉得”如此,因此最好称之为“独一感、延续感、归属感”。自我是这些身份感觉集合的地方。一旦自我消失(例如死亡,例如昏迷,例如“随波逐流”拒绝思考自己为何采取某种身份),这些身份感觉也就无以存身。
身份与自我有明确的区分:身份必是社会性的,自我是个人性的。两者结合成社会性自我。正因为身份的社会性,它能够被偷窃借用(例如假新娘,例如双面间谍,例如假冒他人进大学)。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假定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的个人性,不能让它随心所欲地变化——只有这样的自我才能对一个人采取的真真假假的身份负责。
自我是如何获得这些身份的?人际互动的身份建立过程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范畴化”,即是把相对于自我的他人贴上标签,如要把自我定位为中产阶级,首先要把相对自我的他人贴标签为打工族;第二步是把集团与集团进行比较,例如把商界、官场、学界进行比较;最后二步是认同,把自己归于某个集团,例如归属于学界集团。范畴化、比较、归属,这三步实际上都是排除——我认为我是什么人,取决于我认为我自认为不是什么人。
如此获得的身份很可能是多重的。哪怕在同一次表意/解释行为中,自我也不得不采取多重身份。例如在教研室同事聚会时,自我的身份可能同时是一个青年教师,一个思想倾向上的新左派,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本地人,一个某足球俱乐部的球迷,一个喜欢喝蓝剑啤酒的人,等等。这些身份可能,在同一次表意行为中出现,并且对意义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可以看到,只有在做特定意义交流时,才需要特定身份。不谈足球时,不需要球迷身份;不谈全球化进程,不需要新左派身份。因此,各种身份必然是符号身份。把某种身份用得超过对方认可的程度,所谓“三句不离本行”,往往构成交流障碍。
很多学者认为在身份理论中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与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的区别。本质主义认为自我有确定的本质,例如男女、种族,因此身份有普遍性与恒常性。反本质主义认为身份随着文化条件变化而变化,因时因地而异,可以重新塑造。如果从身份的复杂性来说,的确有相对较难变动的部分(例如生理性别,例如肤色)、可以变化的部分(例如性倾向,例如族群认同)以及容易变化的临时采用的身份(例如工作时,回家后,休闲时,身份不断变化)。就此而言,本质主义倾向与非本质主义倾向的身份都会出现。
正因为身份可以有非本质的部分,而身份累加整合成自我,自我就是一个变动不居的集合。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是必要的,至少在一定时期一定文化环境内,不许有自我作为各种身份的依托。同时,一个自我会在它采取的身份压力之下变化,例如身份从雇员变成老板后,自我会变易。
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尽可能不讨论所谓“主体”问题。首先“subject”意义过于复杂,而在任何意义上都并无“做主”的意思,相反,它是臣服。其次,“主体”一词的主动意味太强,而我们接受的许多身份经常是被动无奈的,或是无意识的、不由控制的。由各种身份集合起来的主体,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主体性”(full- fledged subjectivity)
也有的学者认为自我与身份形成互动关系。柏格森提出“深度自我”与“表演的角色”之间有张力。④ 自我是思维自我,各种身份是其文化阐释,因此各种社会文化身份是健康的自我延伸,但是他们也能与病态自我构成冲突,形成竞争。⑤ 一个带来社会责任的身份(例如父亲身份)能使一个沉溺的自我清醒一些。
应当说,除了各种身份的集合之外,自我尚另有一个比较抽象的能力或向度——一种关于自身的感觉与思考,或者称为对自己的身份的“自我解释”。⑥ 我们可以称之为“意识”或“自觉”。有些学者认为各种身份及其文化属性构成了自我的“第一等级”。第一等级是不自觉的、杂乱的,是康德说的“不可知复合体”(unknowable manifold),而只有心灵才能给予这些材料可知性与意义。⑦
反过来说,所谓自我,是隐身在身份背后的意识,对他人来说不可捉摸,对自己来说也不一定容易理解。身份可以加强“自我感觉”(sense of self),对保持自我有利。这样得到的自我,虽然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局面,但也在变动演化中取得相对稳定。在这个身份集合基础上,才能获得一定的自我意识。各种身份的选择,是从自我的认识(及上文说的排除能力)出发的,因此自我就是对自己采用的身份做出的判断。
正因为符号意义交流才需要身份,自我也就必须在符号交流中才能形成。拉康说交流构成自我:“当发出者从接收者那里接到反方向传来的自己的信息……语言的功用正是让他人回应。正是我的问题把我构成为自我”,因此“构成自我的是我的问题”。⑧ 我对我在符号交流中采取的各种身份有所感觉,有所反思,有所觉悟,自我就在这些“自我感觉”中产生。
文本身份
既然身份与符号表意相关联,是符号发送者的意图的一部分,那么符号文本本身就被染上身份色彩,而这种身份是社会性的。符号文本是发出者主体的抛出物。主体Subject一词,源自拉丁文前缀sub-(面向,接近)以及动词jacere(抛出),⑨ 即向某个方向抛出一个携带主体意图的符号文本,反过来说,符号表意是主体性的延伸。
但是意义不可能被抛出,抛出的必须是一个感知,因此代替意义出现的是物或空白休止这样可感知的实体。中介这个词的定义,就决定了它只是实物的替代,它们只能构成需要解释的“替代性”符号:文字、图画、影片、姿势(例如聋哑语)、物件(例如沙盘推演)、景观(例如展览台)。偶尔我们可以看到“原件实物”出现在表意中,例如博物馆的“真实”文物,军事演习用实枪实弹帮助“叙述”一个抵抗入侵的战斗进程,消防演习中真的放了一把火,法庭上出示证物帮助“讲述”一桩谋杀案。这些“实物”都是替代品。手枪只是“曾经”发出杀人的子弹,呈交法庭作为证物时它已经不是杀人状态的那把手枪。脱离原语境的实物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物”,只是一种帮助表意的提喻。
符号再现的替代原则,决定了表意的一个基本原理:既是表意本身把被表述世界(不管是虚构性的,还是事实性的)“推出在场”,表意是自我的一种带有意图的“抛出”,而符号文本则是抛出后的形态,因此,作为符号表现体的感知,并不是自在之物,并不是一个中性的形态,它是一个意义携带者,与表达意义的人一样,它必须有个身份。这一点不难理解。一支枪作为证物,作为威胁,作为自我保护的安慰,作为挂在墙上的摆设,作为非洲战乱国家儿童的“玩具”,意义完全不同,远远不是枪作为物的形态能决定的。
任何一个表意的文本,都具有某种身份——不是表意人采取的身份,而是文本具有的“文本身份”。文本身份,是符号文本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联系。各种符号文本的身份,严重地影响符号的表意。文本身份与发出者、解释者的身份有关联,却并不等同于他们的身份;文本身份是相对独立的。一段文字,可以是政府告示、宣传口号、小说的对话、网上的帖子。相同的文字,意义可以有极大不同。它们的文本身份,成为发出者与接收者建立意义交流关系的关键。反过来,如果没有文本身份,任何文本几乎无法表意。没有神圣身份的经书,不是圣经;没有四书身份的《春秋》就缺少微言大义,只是鲁国宫廷的一些记事,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⑩ 没有五经身份的《礼记》是一批杂乱的文字合集;没有指挥身份的红绿灯无法要人服从;没有学校权威的铃声无法让学生回到课堂上去;没有帝王墓碑身份的“无字碑”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刻上字的碑石,并不藏有说不尽的秘密意图。一个文化中的符号文本身份,可能比该文化中的人能采用的身份更复杂多变。
文本身份究竟是发出者有意赋予的,还是符号文本的社会属性加上的?应当说,发出者的意图有相当的作用(例如,一幅画要加上发出者的意图才成为对某个题目的宣传),但是意图本身是文化范畴的产物,意图并不是完全按照自我意志行事,文本身份与发出者意图可能会有很大差距——文本本身是文化直接作用于符号表意的结果。一旦符号文本形成,文本身份就独立地起作用。
例如,某种广告,产品市场目标是女性,意图定点在白领女性消费者,这就规定了它的文本表达内容不得不是女性内容,迎合女性的各种喜好。但这只是它的表层身份,女性化妆品广告经常具有隐藏的男性身份——女子为取悦男性而美丽,取悦男性以后就能得到幸福。而广告表层的女性身份与隐藏男性身份实际上都不取决于发送者(广告设计者,广告公司,电视台),而是取决于整个文化的各种控制方式,如消费主义、阶层分野、男性主宰等等,这些都给予文本独立于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身份。
文本身份是文本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样也加入到社会关系的网络中。某种身份的文本,吸引某种特定的人接受。而且,因为符号的媒介有时空跨度,符号文本的身份就相对独立于原先的发出者,符号文本的身份成为它本身(而不一定是发出符号的人)与其他人构成社会的“抱团”(togetherness)。喜欢某种电影的人,喜欢某种网上交际的人,喜欢某种麻将牌戏的人,喜欢某种科学理念的人,他们走到一起来的原因,是对某一类符号文本身份的认同,而不一定是对某个自我的认同。所有这些人都是符号的接收者,因此符号文本的身份在人类文化的构成上应当比自我所认同的各种身份更为重要。
例如歌曲有性别身份:男性歌是男对女唱的歌;女性歌是女对男唱的歌;男女之间歌,是男女互唱的歌;既男又女歌,即男女通用的歌;非男非女歌,是没有明显性别身份的歌。可以看出这些歌的性别身份与发出者的自我意图有一定关系,因为人的性别倾向就有这五种(male,female,both sexes,intersex,nonsex)。(11) 不过我们立即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别:一个社会上具有“既男又女”与“非男非女”性别身份的人,没有那么多,而歌曲中此类文本身份,就再多不过。再者,文本性别与创作者的性别身份没有相应的关系。男性词作者、谱曲者、出品人,完全能写出“女性歌”。许多宋词就是男性文人“为歌女写曲”,因为歌曲演唱者(歌曲文本发出的最后环节)往往赋予歌曲文本“性别”身份。我们觉得宋词文本性别混乱,只是因为脱离表演把歌词当诗来读。歌曲文本性别身份之复杂,可见一斑。
再深入一步看歌曲的文本身份。文本性别常常携带着文化对性别身份的看待方式,而这些看待方式常常是人们觉得自然而然理应如此。女性歌往往包含着文化对女性的各种期盼、想法、偏见(例如女性必须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独立而不傲慢,女性必须美丽,女性最好年轻等等)。这些并不一定是歌曲制作集团(符号的发出者)有意为之,但是符号文本经常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其身份的处理方式也往往是在文本产生之前就已经决定,词曲作者本人在身份上无从挑选。他们必须是对女性有偏见者,歌曲要流行就只能如此写。
如果见到的只是文本,而不知道创作者的身份,也不知道他的意图,那么如何判别文本身份呢?应当说文本本身携带着大量有关信息。歌词中有措辞、代词使用等因素,音乐中有曲调的作风、曲式的安排、配器的种类、节奏的强弱,歌唱者有处理方式、速度的缓急等等。除了文本风格,还有隐文本的安排:某一类歌曲的型文本、某一首名曲的次生文本、某一种典故或名字的前文本、同一张歌碟里的其他歌曲形成的超文本等等。这些因素合起来,往往使文本身份的组成异常丰富,比创作者本人的身份带来的信息更复杂。
进一步说,“无性别歌”(动员歌、宣传歌、公司企业歌、校歌等)不一定是真正的无性别。批评家如果对性别控制敏感,往往可以从中发掘出潜藏的性别身份。“宏大叙述”往往压制了女性意识。正如性别理论专家里弗在研究儿童游戏后得出的结论:人类文明往往让“男孩子培养了扮演广义他者角色的行为能力,女孩子发展了扮演具体他者的移情能力”。(12) 这不仅表现在男孩与女孩身上,更表现在他们热衷的游戏的“身份”上。“女性”游戏身份往往是具体的阴柔的,而“男性”游戏身份却往往不具有明确的性别特征。
因此,文本性别往往比符号发出者的自我性别更具有“流动性”,更明显地形成一个从极端男性到极端女性的多样变体连续带。而且每个文本的身份也只是在某个阶段的某个文化中相对固定,它实际上漂流移动,不容易被文化的规定性锁住。例如,“既男又女(intersex)”在社会上难被容忍,在符号文本中却相当自然,在歌中如此,在各种刊物、广告、衣装中都很常见。人具有生理性别,往往把他们的性别身份强行决定,而文本身份却更依靠社会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对文本性别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为什么文本身份的研究应当构成一种独立的课题。
普遍隐含作者
上面说过身份集合、构成自我与自我。但是从文本身份构成的自我,并不一定真会有此自我。虚构作品、历史描述、档案积累,都能给我们足够身份材料或是提喻性符号来构建一个类似自我的复杂人物。福尔摩斯、林黛玉,都是虚构的自我。当我们把一个个特殊的身份综合进一个发生过程,我们对这些“自我”的了解甚至多于了解一个真正存在的自我,这很有点类似歌迷影迷球迷从大量零星材料建构被崇拜对象。但是这样建构出来的毕竟不是自我,这种文本身份集合成的自我,可以称为“类人格”(quasi- personality)。
布斯提出的“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理论,实际上就是从文本中寻找作者身份,从而构筑一个与任务相仿的类自我,一个假定能够集合各种文本身份的出发点。布斯是在《小说修辞》这本名著中提出“隐含作者”这个概念的,至今理论界没能将其讨论清楚,却无人认为可以摆脱。布斯在提出这个概念40年之后,在去世前最后一文中,依然在为此概念的必要性作自辩。(13) 其实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更清晰的定义。
从符号学观念来说,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并不限于小说。只要有文本卷入身份问题,而文本身份需要一个“类自我”集合,那就必须有一个“隐含作者”。一座楼房,一首歌,一组信号弹,都必须有个作为价值集合的“隐含发出者”(implied addresser)。
这种“类作者人格”,到底是否具有真正的自我性(也就是说,是否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格)?布斯以及至今讨论隐含作者问题的人,一直没有论辩清楚。布斯认为这个人格是存在的,他说这个类自我可以是作者的“第二自我”。也就是说,在写作这本小说时,作者的“代理自我”,就是我们能从文本中总结出来的“隐含作者”。这样一说,集合在这个类自我概念中的文本身份就有了真实自我的源头,即作者的“代理自我”。在布斯去世后的文集《我的多个自我》中,他坚持文本身份集合而成的类人格(隐含作者)与文本产生时的作者自我(执行作者)重合。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具有特定时空中的自我性,哪怕是暂时的自我性。(14)
施蛰存在《唐诗百话》中指出,一般批评者容易犯把文本身份与作者合一的错误。比如武则天的《如意娘》一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很多“考古者”认为,此诗是武则天写的,写的是她为唐太宗的“才人”时与太子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的感情经验。施蛰存认为:“这是由于误解此诗,认为作者自己抒情。但这是乐府歌辞,给歌女唱的。诗中的‘君’字,可以指任何一个男人。唱给谁听,这个‘君’就指谁。你如果把这一类型的恋歌认为是作者的自述,那就是笨伯了。”(15) 这里,文本身份指向的只是一个“类自我”,一个隐含作者。
因此,歌曲有“隐含歌者”,楼盘有“隐含建筑师”,服装有“隐含设计人”,广告研究者发现品牌后面的人格可以发展成“角色、合伙人、个人”(16)。任何符号表意,都有“隐含表意者”,他们不是真正的符号发出者,而是文本身份的价值观体现,是文本可能被解释出来的各种意义的寄身之处。正如一个人的自我,是此人所采取的各种身份的集合,“隐含发出者”是符号的“文本身份”的集合。这个人格只与符号表意有关,因此只是个“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不具有超出这个范围的精神品质,也不可能具有肉体的存在。
问题在于,这个由文本身份集合起来的自我具有潜在的具体化可能,有时候也真的会具体化,一如隐含作者有与作者相互转换的潜在可能性。不能说《黑暗的心脏》与康拉德完全没有关系,康拉德的确是个保守主义者,心里有《黑暗的心脏》隐含作者的各种思想,这些思想倾向在别的作品中有时也冒出来。
我们在其他符号表意中,也看到符号自我与人格自我之间部分相通的潜在可能性。例如各种交通信号的文本身份,指向了一个具有指挥权威的“隐含发出者”,这个人格有时候会以值班交警的身份冒出来,但在更多时刻只是一个隐而不显的人格。但是这个人格对我们的威慑并不取决于其现身与否。福柯再三强调“监视与惩戒”。惩戒只是一种可能使用的威胁,纪律本身就体现了社会意志:法律、政令、教育、文化习俗、社会共识。(17) 这些文本身份,都通过社会意志这无所不在的“隐含自我”建立权威。
因此,本文强调,布斯的“隐含作者”应当是个普遍概念。只要有意义表达,就必然有文本身份;只要有文本身份,就必然有符号自我;符号自我可以人格化为“隐含自我”。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不久就看出这个城市的建筑风格、车流交通、街头雕塑、商店布置、风俗习惯、运动会的气派、人们的谈吐行事,都指向“隐含自我”。这个人格不是一个人,不是一届或若干届领导,不是一代或若干代人民,但是它的确是个可以觉察到的人格。不然怎么会有《笑说上海男人》、《成都女人》这样的书出现?英超足球强调身体对抗,西班牙足球强调技术流畅,脚上功夫有观赏价值。同样是足球,背后的“隐含自我”不同。阿森纳的教练温格弄错了路子,使他的夺冠梦一再破裂。这位著名法国籍足球教练,没有能与英国足球的隐含自我对上路,失败的只能是他自己。
符号自我的纵向与横向位移
很多学者把自我等同于“自觉的心灵”(the conscious mind)。笛卡尔传统把“我思”当做自我存在的唯一依据,一种完整的自我,这个观念已经被现代自我理论否决了。但是如何能达到自觉?当一个人对自己及世界进行意义追寻的时候,自我的经验开始形成。因此,一个自觉的自我,必然也是一个符号自我,因为他思考世界的意义,反思自己的意义,寻找的是自己存在于世界上的意义。
这个过程产生了自我的感觉(sense of self)。自我感觉并不是均一的,而是一系列关于自我的形象(self- image),关于自我的评价(self- esteem),关于自我的知识(self- knowledge)。这些自我的成分能不能合成一个具有同一性的自我,是很可疑的。自我感觉,就是自我表达意义的感觉。
关于自我,据说定义有12种之多。(18) 自我到底是落在个人意志这一端,还是落在社会决定这一端,各家观点不一。经过许多学派的辩论,从米德的人类社会学观念到泰勒的自由主义观念,到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关于自我的各种概念形成一个上下延伸的连续带。一端是人内心隐藏的本能,即所谓自由无忌毫无担待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此时的自我可以是非理性的、“非自我的”(克里斯蒂娃称之为“零逻辑自我”zerologic subject)。(19) 而另一端可以是“高度理性”的、由社会和文化定位的个人(socially- situated self),甚至笛卡尔式的世界中心自我,或是胡塞尔的负责任自我。各家定义的不同自我,落到这个轴线上下之间不同的位置上,就像我们个人意识到的自我也是在这个轴线上移动。(20) 我们的表意和解释行为安排了许多身份,它们包含了不同的隐含自我。因此,自我一直在寻找它基本的符号意义定位,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的移位。
意义的追寻首先造成了“主我”(I)与“宾我”(me)的区分。符号学家威利指出,一个人在考虑过去的经验时,找到对象自我;一个人在考虑到他的思考之后果时,面对未来自我。这样就出现了自我的水平组合:人在思考自身时构成符号自我,过去的我是这个符号的对象,未来的我是这个符号的解释项,解释项在自我思考的进一步时间延伸中成为新的自我,形成的一个符号展开过程。塔拉斯蒂也举过一个例子:一个人拿自己的血样去医院检验,他既是自我又是对象。我从这个例子推论出时间向度:检验的对象,哪怕是自己,也是已经过去的自我;而检验的结果是对自己的解释,却是未来向度。整个检验,作为符号过程,要推出的意义是回答“今后怎么办”。
自我思考在时间轴上的横向展开,已经被很多论者讨论过。卡普兰总结说:“经验主义着重回顾,从源头分析一个观念;实用主义展望前景,注意的不是源头而是结果,不是经验,而是尚待形成的经验。”因此皮尔士这位实用主义开创者把自我看成“未来事件的非固定性原因”,“意义是一个理念的影响或后果”。自我与反思的对象形成阐释性对话。而社会行为主义开创者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认为自我的思索是逆向的,自我的内心对话是现在的我朝向过去的我;而科拉皮艾特罗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组成三个三联式,即当下-过去-未来,与I-me-you相应,也与皮尔士的符号-对象-解释项相应。(21)
的确,自我思考的过程往往是审视过去的经验,期望未来会有某种结果。对自我这个符号的解释,总是有待未来决定是否有效。塔拉斯蒂引用克尔凯郭尔:“对于一个自我,没有比存在着(existing)更难的事了,他不可能完全是,他只能以此为目标。”(22)
自我符号的纵向位移也有很多人讨论过。德国社会学家卢曼首先提出自我的复杂层次论。他认为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分成六个层次:一个“心理的”个人,向上成为“(人际)互动的”,“组织的”,甚至“社会的”,向下可以成为“有机生物的”,最后成为“机械的”。(23) 这样就有上下六层自我,它们都是自我的一部分。深受符号学影响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瓦尔(Jean Wahl)最早把超越(transcendence)分解成两种:向上超越(trans- ascendence)与向下超越(trans-descendence)。符号学家塔拉斯蒂则把瓦尔的向上超越解释为“外符号性”(exosemiotic),把向下超越解释为“内符号性”(endosemiotic)。而另一位符号学家威利则把前者称为“向上还原”,把后者称为“向下还原”(所谓还原,指的是用一种更普遍的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实际上这些都是弗洛伊德与拉康讨论过自我的上下层次,只是卢曼等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讨论而已。
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运动,都是自我本身的位移,都没有脱离自我符号行为本身的范围。因此,弗洛伊德和克里斯蒂娃的向下位移,承认自我可以进入非理性的范围。他们并没有否定自我,正如拉康所坚持的,无意识是“按语言方式组成的”(structured like language)。(24)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无意识是“按符号方式格式化的”(semiotically formatted)。但是如果自我继续下行,向生物和“物理-化学”方向(也就是向“信号-反应”的机械方式)过分位移,自我作为一种意识会渐渐失去意义。
另一方面,向上的位移使自我变成“他人的自我”,社会文化的自我,这使自我丰富化、理想化,充满了超越意义。但是自我的上升位移也可能有危险,有可能使自我变成纯粹理性的自我,或是让自我丧失独立性,被吸纳进社会意识形态。这正是福柯与阿尔都塞所批判的:不存在个体的自我,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自我。
但是符号自我的位移,至少说明了自我可以围绕心理-符号的中间上下位移,那样的话,自我本身不是受责问的对象,自我是我们处理意义的一个过程。皮尔士提出的“人是符号”命题,就得到了当代主体符号学的支持。
注释:
①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
② 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1959,vol.II) 291.
③ Charles Taylor,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m Identity(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④ 转引自William Ralph Shroeder,Continental Philosophy:A Critical Approach(Oxford:Blackwell,2004) 456。
⑤ Norbert Wiley,The Semiotic Self(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6.
⑥ Fernando Andacht,“A Semiotic Reflection on Selfinterpretation and Identity”,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5,no1(2005) 51-75.
⑦ Harold Garfinkel理论,见Norbert Wiley,The Semiotic Self,81。
⑧ Jacques Lacan,The Language of the Self(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8) 62-63.
⑨ T.F.Hoad(ed),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London:Guild Publishing,1986) 469.
⑩ 《宋史·王安石传》:“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於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11) Anne Fausto-Sterling,Sexing the Body:Gender Poli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New York:Basic Books,2000).
(12) Janet Lever,“Sex Difference in the Games Children Play”,Social Problems(April 1976) 481.
(13) 韦恩·布斯:《隐含作者的复活:为何要操心?》,见《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原书(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Oxford:Blackwell)出版于2005年,布斯于该年十月去世,因此此文几乎是布斯一生最后一文。
(14) Wayne C Booth,My Many Selves:The Quest for a Plausible Harmony(Logan:U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4-725页。
(16) Jennifer L.Aaker,and Susan Fournier,“A Brand as a Character,A Partner and a Person: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Question of Brand Personality”,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1995,22(1).
(17) 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London:Allen Lane,1977) 88.
(18) Jennifer L.Aaker,“The Malleable Self:The Role of Self Expression in Persuasion”,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9) 8.
(19) Julia Kristeva,Stranger to Ourselv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98。克里斯蒂娃是在讨论狄德罗的《拉莫的侄儿》一书时提出这个概念,显然她的出发点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分裂自我。
(20) Gordon Wheeler,Beyond Individualism:Towar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Self,Relationship,and Experience(Hillsdale,NJ:Analytic Press,2000) 67.
(21) Vincent Colapietro,Peirce's Approach to the Self:A Semiotic Perspective on Human Subjectivity(Albany:SUNY Press,1989).
(22) Eero Tarasti,Existential Semiotics(Berlin &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2000) 7.
(23) Niklas Luhmann,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 72.
(24) 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London:Tavistock,1966) 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