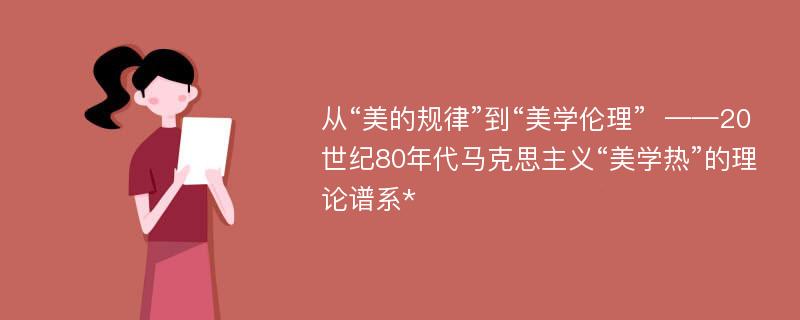
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理论家纷纷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思前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在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上进行了论争,试图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论据,从而确定“美学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朱光潜、李泽厚等从“自然的人化”理论出发,建构起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主体观与实践观。同时,也带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热潮。理论家们认为审美不仅构成了主体实践的一部分,更是参与到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人的解放”进程。“美的规律”问题的探讨则完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自我建构和主体性美学延展的目标,成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深化。当美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主体性为核心、以人学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框架,从而具有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美学热;“美的规律”;“自然的人化”;人道主义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学热”的兴起正是伴随着主体内在自由的表达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勃兴而进行的,美学自身的学科属性和也契合了主体自由的追寻,所以,“美学热”就为意识形态领域之外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提供了开拓的空间,也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美学热”对主体性自由的追寻和人道主义话语的延展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中进行,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著作中获取人道主义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同时,知识分子和美学家们经历“文革”的摧残和话语的放逐,在80年代新时期之初,改造和参与社会的理论热情已经远远超越了学科理论自身的内涵,获得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们迫切需要以“流芳千载任风雪,独呈丹心报中华”的态度重拾知识话语。而美学一方面具有以主体自由为核心的超越性,与人道主义的思想脉络具有同构性;而另一方面,美学也“指向”社会现实,在从“边缘”到“核心”的意识形态走向中,实现重塑学术立场和学术道德的旨归。所以,“美学热”的开端也正是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论争开始的。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带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新时期以来,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刘纲纪等美学家们纷纷将视角转向了马克思前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并在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等问题上进行了论争,试图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人性发展和人的自由的论据,从而确定“美学热”的合法性存在价值。与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论争不同的是,参与论争的各派都是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从《手稿》中发现能为自己所用的理论资源,而论争的美学问题的实质也是人道主义和人的自由问题。
一、“自然的人化”、主体性与《手稿》的中国阐释
《手稿》作为马克思早年的哲学著作,主要涉及经济学和哲学的问题,并重点研究了作为类的人与自然、人的自身以及劳动实践等问题,并非专门研究美学的专著。但是在异化劳动和自然的人化等观点上却透露出美学思想。因为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依然是人,所以《手稿》中对人本身的界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都涉及了美学的基本问题。《手稿》是1927年才被人们从马克思的遗著中发现,1932年德文版在苏联和德国得以首次发表,全文发表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引起了震惊,甚至有学者认为该篇论文中的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1]。而在中国,《手稿》最先发行则是在1956年由何思敬翻译、宗白华校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1979年,刘丕坤主要参照1956年前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俄文本翻译,并参考了多种译本,同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收录的《手稿》也是在此版本的基础之上,经过朱光潜和中央编译局的相关专家共同校订而成,并成为截至目前为止使用较为广泛的版本。后来,自1985至2000年,人民出版社也先后三次出版《手稿》的单行本,但基本上还是与《全集》中收录的相同。《手稿》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得到重视,并作为“美学热”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该著作中透露出大量的人的实践、人的属性以及人的劳动异化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中包含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问题则引发了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虽然对于其的研究并没有定论,但是给自觉思索的理论家们以“黎明的曙光”,从而具有在体制意识形态内探索人性问题的可能。首先从《手稿》中分析美学思想的仍然是朱光潜,他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以及1980年发表在《美学》第2期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都肯定了《手稿》中对人性和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从文艺和美学的角度上肯定了主体性的价值与个体性的自由,实现对僵化政治统摄下文学的调整和纠正。论文中有关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与美感的关系、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大量的争论,由此形成了“手稿热”。“手稿热”作为“美学热”的组成部分,从美学的问题角度而言,主要集中在自然的人化问题,美的产生的问题以及美的规律问题等方面;从理论视野和流派倾向而言,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是从唯物论视野出发来探讨美的问题,以蔡仪为代表;第二个是以实践论视野为主要理论取向,进而探究美的主体性、实践性和关系性等问题,以朱光潜、李泽厚、刘纲纪、蒋孔阳、周来祥等为代表;第三个是以价值论为主要视野,以人本主义和人的生存价值为旨归,进一步探究实践观点之后主体本身的美学问题,以高尔泰、刘再复、王一川等为代表,这也正是新时期美学以来的认识论、实践论和后实践论美学的代表。可以看出,不仅仅《手稿》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维度的美学思想,更是在理论家的论争中不断丰富了人道主义和相关视域中的美学思想,使得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得以深入人心、蔚为大观。人道主义思潮和人性人情的存在论价值也在美学和美学意识形态中得以长久地延续和彰显。
因为针对《手稿》论争的前提首先是着眼于人道主义和主体性价值的问题,所以论争主要也是围绕“自然的人化”观点展开的。在对“自然的人化”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是否产生了美与美感以及美与美感的关系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光潜提出“自然的人化”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只有人自身全面、综合的发展,并在自然界中反观自身存在的“本质力量”,自然也就具有了属人的性质。所以,人性正是人的本质力量最大程度的彰显,“人性论和阶级观点并不矛盾,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2]。朱光潜重新发掘马克思《手稿》中对人类自然主体和实践主体的论述,显然是有其理论价值取向的,因为“人化”的途径不仅仅包括物质实践,还涵盖了精神方面的本质力量,两者的辩证统一共同完成了“人性”的建构。“人性”除了包含物质实践性和阶级性,也包括了个体性、精神实践性和自然性,这正是回归了人道主义的理论起点。所以,从马克思经典论著本身出发,探究人性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就具有了理论的合法性价值。当然,该观点引发了另一些学者的理论质疑,一方面是人性与《手稿》中“自然的人化”是否有联系,而另一方面是“自然的人化”根本就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唯心主义的表现。蔡仪正是主要的质疑者,并且认为“自然的人化”不能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中,是青年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彻底影响,并且自身也并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反思和批判。“人本主义原则的特点,就是以唯物主义为它的出发点,而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它的归结点了。”[3]蔡仪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手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地位和意义,这样也就直接消解了所谓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了;同时,《手稿》中对于带有自然性的人的本质以及从“感觉”出发的人与自然的互涉本质,这些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蔡仪的观点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大量的争议,朱光潜、程代熙、李泽厚、陈望衡、刘纲纪等学者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整体上来看,他们普遍支持“自然的人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用绝对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阵营来给理论分类,而是应该深入到“自然的人化”理论深层,探究主体通过劳动实践如何建构了自身和历史。当然,这些学者中间同样有争议,但是在面对“自然的人化”和人道主义的关系之时,却都表现出热情的支持和积极的态度,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众多的理论家中,刘纲纪和陈望衡直接提出了与蔡仪相异的学术观点,他们一方面肯定了“自然的人化”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也高扬了人感性存在的自由形式以及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价值。陈望衡主要从“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入手,来证明“对象化劳动”的意义与价值。“对象化”劳动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正是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以自然和人之间的观审、改造与反观,完成了对人类本质的理解;而人类劳动正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环境中,才变成了“异化”劳动。所以,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自然的人化”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蔡先生这个理解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他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对象化’与‘异化’等同起来了”[4]。在确立“自然的人化”合法性价值之后,又进一步区分了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人类学原则)之间的不同,发掘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改造和该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性质。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中也使用了诸如“人的感觉”“自然界”和“类本质”的概念,但是其立足点却已经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和“情”的感性基础转移至主体性实践第一位的原则,从而确立人的本质。显然,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原则绝非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是自然性和实践性、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融合与统一。建构起“自然的人化”合法性价值之后,刘纲纪以更加激进的视角高扬了该理论的基础性和本体性价值。在他看来,“自然的人化”不仅仅是人通过实践活动与自然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关系,而且主体通过实践进一步反观和确认到自身的自由存在。“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的哲学前提,同时也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前提”,主体通过劳动实践,使自然呈现出“人化”的色彩,而主体也在自然中直观感受到自身本质力量。这种对自然的感性直观正是美学产生的基础,经由实践活动产生的感性物质形式也正是美的形式。刘纲纪不仅只是肯定了“自然的人化”理论的合理性存在价值,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态度将其与美的产生和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经典理论中生发出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思想。美和自由都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促使人的才能、力量和个性的多方面发展。在和蔡仪的理论进行商榷的时候,刘纲纪同样认为劳动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是普遍的并且适用于一切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不论私有制下的或消灭了私有制的社会下的劳动都是人的对象化,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在异化的形势下存在的,后者则消除了异化”[5]。所以,刘纲纪在建构自身的理论中,也延展了美学理论的延展空间,使美学、人道主义和自由真正结合在一起,并在《手稿》“自然的人化”中获得了合法性的价值。
在对“自然的人化”合理性价值进行论述之后,其他的理论家将视角转向了该理论本体内涵,从实践的观点和主客观统一的理论出发,进一步探究美和美感的产生。朱光潜、李泽厚、程代熙、高尔泰等人正是其代表。他们虽然在“实践”的内涵,美与美感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是都肯定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实践性和创造性,《手稿》中对人的本质问题的阐释也对美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具体来讲,“自然的人化”作为主客观统一的观点,直接指向的主体的劳动实践,而主体也正是在实践中确立的存在的意义和本质属性。可以看出,主体性的确立其实也正是人道主义思潮产生的前提,众多理论家之所以从《手稿》中进一步发掘出实践观点,一方面是深入研究理论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源自改造现实和重塑知识分子话语的热情,他们希望在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以一种“合法性”的方式促使“美学热”的生成,从而实现美学意识形态的反拨效应。朱光潜、李泽厚作为实践派美学的代表,在《手稿》讨论和“美学热”前期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朱光潜仍然从劳动与艺术的关系出发,来建构其美学思想。朱光潜认为“自然的人化”不仅仅体现了人的本质,其过程也正是劳动实践的过程。此种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实践并非仅仅是物质劳动实践,而且也包含精神和审美实践,美感和美正是在精神和审美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自然的人化”实践过程中,大自然和世界万物具有了人和社会的意义,一方面是物质实践使得自然成为了人类劳动生活的必备,而另一方面的精神实践也在情感层面上“附着”了人的色彩,使得草木可以含笑,山川可以含媚。“人与自然(包括社会)绝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对立面,而是不断地互相斗争又互相推进的。”[6]在朱光潜看来,劳动实践并非仅仅是物质劳动,同时也是精神和艺术创造,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并非仅仅是被动的对现实意识的反映。审美和艺术作为实践的一部分,从感性的维度实现了“自然的人化”以及人的本质属性,最终通达自由和解放的最终目标,这也正是人道主义的最终目的,“人发挥了他的本质力量,就是肯定了他自己,他的本质力量就在改造的自然中对象化了,因而也日益加强和提高了”[7]。朱光潜的实践美学观点从马克思的《手稿》出发,并以“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与自由来重新研究和审视马克思经典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并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在此,朱光潜仍然是延续了其人道主义、人性和人情的理论线索,只不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以心观物”式心理学美学转化成为新世纪主客观统一的实践论美学,但是对主体价值和自由的关注一以贯之。朱光潜不仅赋予了“自然的人化”以合理性价值,甚至将“艺术与审美精神”也纳入实践本身,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美学存在的合法性空间。同样,李泽厚也是从“自然的人化”理论出发,系统地建构起主体论实践美学体系,其美学关键术语“积淀说”“主体性”“美是自由的形式”等都是从“自然的人化”开始进一步探究的。在李泽厚看来,“人化”不仅是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说明,更具有主体性的历史价值。在“内在”和“外在”的双向维度中,感性的自然形式成为“美的规律”,促使了主体的建构和自由的彰显。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在主体本质力量下的表现等都被纳入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范畴,自然不仅是客观的存在,更是人类发展的参照物;伴随着主体和社会的发展,自然物以其表面的感性形式吸引着人们,使得主体获得了无功利的美感愉快。经过“自然的人化”的积淀,人们不仅仅能够欣赏直接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对象物,还能欣赏日升月落、花开花谢、暴雨闪电、峡谷沙漠等自然场景,并且感觉到类似于康德所认为的“崇高”和“优美”,比如昆明石林,比如三潭印月,这些奇特的自然景观已经暂时剥离了与主体之间的价值或利害关系,而纯粹以美好的感性形式使人们产生美感和美。这也正是主体“积淀”的结果,而艺术家和美学家正是敏锐地发现了这种美的“规律性”,以“自然的人化”生发出实践美学蔚为大观的场景。但是,李泽厚不同意朱光潜对“实践”和“自然人化”的内涵界定,认为朱光潜扩大了实践的范围,把本应属于人的意识和认识领域的“审美”与“精神”也看作实践的领域。与此同时,李泽厚认为社会美是美的本质的主要承担,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主体通过实践力量反观到美的形式,这也正是“沉淀”的含义,“积淀就是人性的历史生存,即人的自然性、生物性情感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被社会化、‘人化’,审美心理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8]。虽然朱光潜与李泽厚所理解的“自然的人化”内涵不同,所产生美的基础和途径也不同,但是都确立了主体性价值和人性、人道主义思潮的合理性,共同将美学从单一维度的“反映论”“物学”视野转移到主客观结合的“实践派”“人学”理论。无论审美是构成了主体精神实践的一部分,还是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感性意识,都确证了“人”对美学的生成、建构和促进作用。
学界在对“两个尺度”的论争中,同样是围绕主体与客体关系,以及主体实践与意识的关系层面对“两个尺度”的理解有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首先是蔡仪的理解,在他看来,两个尺度其实都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只不过有外在和内在的区别。“物种的尺度”是指事物呈现于外的普遍性或者本质性的特征;而“内在的尺度”则是包孕在事物内部的本质特征,二者指的都是事物普遍意义上的属性,并没有所谓的主体和客体的区分,更消泯了主体的特有属性,这也是和蔡仪一直以来的客体论美学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无论从语义上看或从实践上看,并不是说的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2]。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美的规律”就基本上排斥了主体性的作用,而是成为客体内在的、固有的属性。其二是朱光潜的观点。朱光潜在“美的尺度”问题上和蔡仪观点有类似之处,将“内在的尺度”作为对象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这在朱光潜自己对《手稿》的节译文本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动物只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物种的标准和需要去制造,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标准来生产,而且知道怎样把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因此,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13]所谓“尺度”正是物种生存的“标准”,“外在的尺度”就是指每个物种生存在世界上并且作为“主体”的标准;而“内在的尺度”则是对象本身固有的标准,相比较前者而言更高更复杂,也就是各种对象本身的固有的客观规律。从对“两个尺度”的阐释而言,朱光潜基本上一方面肯定了事物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客体属性,另一方面认为“两个尺度”中并未涉及美学问题,也没有说明美的客体性、主体性或者实践性特质。朱光潜将问题的核心放在人“知道怎样”把对象固有的标准进行再次自由地“制造”,这其实仍然体现出来“实践”的观点。比如蜜蜂建造巢穴和人建造房屋都是各自依据自身的类别的物种的需要进行建造的,但是差别正是在于人不仅仅能够建造自身居住的房屋,还能够自由地按照蜜蜂的需要和标准来建造、改造蜂巢,这正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改造和运用。此种改造和实践仍然涉及精神性和创作性的改造,这正是文学创作的各种因素和素材,“就创作方法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所要求的正是现实主义,……都要包括在‘美的规律’之内”[14]。所以,“美的规律”从最高价值取向上而言,仍然是作为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自由和对外在世界的把握,虽然朱光潜和蔡仪在“内在尺度”的定义上基本一致,但是将其重心放在了“自由的改造”方面,使得美学依然呈现出“实践性”的特色。其三是李泽厚、刘纲纪、朱狄等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把“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分为了对象和主体两个层面,“物种的尺度”正是自然客体和外在对象的内在规律,而“内在的尺度”正是主体内在的、有目的改造自然的尺度,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体自由能动的实践规律,并在物种尺度的基础上获得美感。李泽厚认为“内在尺度”正是主体的实践,在实践中反观到了自然界“物种的规律”,体现了主体自由能动的活动。“内在尺度”也正是指“实践的目的性”,也就是主体的内在目的。而美的诞生正是主体在现实的实践中获得的,是以“内在的自然化”和“积淀”的方式完成美感体验。这不仅为实践美学奠定了基础,更是与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说进行了区分。主体通过历史的实践,最终将合规律的形式逐步内化、沉淀至人的内心深处,成为认知性的三种心理主体架构,分别是“理性的内化”“理性的凝聚”和“理性的积淀”,而这三者分别相对应“智力结构”“意志结构”和“审美结构”,最终在康德理论的影响下,李泽厚建构其主体性实践论美学。“内在的尺度”“美的规律”都与主体的物质实践密切相关,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美及美学的理论。刘纲纪对“两种尺度”区分得更为明显,认为“物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决然不同,前者是自然外物的尺度,后者是人的自由的、能动的、属人的维度。实践派美学家们试图将“内在的尺度”理解为主体具有历史性质的劳动实践,且这种实践是区别于动物的有意识的、自由的活动;而主体性实践美学也恰恰是建立实践之上并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新工科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加入新元素”,就项目开发而言,很多项目涉及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课题,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例如我们的无人车项目,需要使用图像处理技术。而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开设这类课程,或者这类课程设置在高年级。因此我们首先进行了相关课程的补充。通过基础
b)当C(px,y)==C(px-1,y)且C(px,y)==C(px,y-1)时,如果Label[x,y-1]≠Label[x-1,y]则表示产生了标号冲突,此时需要更新元素Label_common[Label_index-1],记录等价标号关系;否则不需要更新数组元素。
马克思的《手稿》和关于《手稿》的论争作为“美学热”的前导,其理论影响和对美学学科的发展推动是多方面的,从美学学科的建设而言,实现了对机械唯物主义和反映论美学的反拨与调整,也实现了自“美学大讨论”以来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认识论美学的再次转型。对于美的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美的本质等哲学层面的问题,而是将人的能动性、实践性和感官性介入美学研究,使之成为既有理论思辨,也关照艺术现象的研究方式。实践论美学、后实践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在“手稿热”之后风生水起,美学逐步恢复了其感性学和审美自由的原初之意。而“手稿热”更为重要影响的还不仅在美学学科层面,其“两个尺度”“美的规律”“异化”等问题的论争更是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在《手稿》的论争中,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将传统以“阶级性”为主要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作为“异化”人性的根源,并配合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对其进行批判;而人道主义思想和关于人情、人性的反思则成为一种价值范畴为人民大众接受。通过《手稿》的讨论,人们不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马克思,而且在“主体”“感官”“自由”“实践”“美的规律”等关键理论点中感受到了“告别历史”维度下前所未有的理论活力。通过《手稿》中对美的问题的再次认识与讨论,实践论美学逐步深入人心,人的问题和美的问题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并且最终发展成为“美学热”的重要理论维度。
二、“美的规律”、美感与审美主导性的再发掘
记则W(0,T)是一个Hilbert空间,具有范数[9]‖w‖W=‖w‖L2(0,T;H1(Ω))+‖wt‖L2(0,T;H1(Ω)).
2)听障类微课重视听障学生语言康复及生活心理教育的较多,针对培养听障学生信息素养能力,培养他们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协助下康复训练、发表观点、交流感情、沟通合作以及解决日常生活、学习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与信息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较少。
从“两个尺度”到“美的规律”,正是各派美学家们对人的本质问题讨论的根本目的。“两个尺度”的论争表面来看是对客体性和主体性以及二者关系的探讨,但实际上仍然是对美的产生和美的本质问题的理解以及如何将人的主体性与美学结合起来的问题。其实,马克思提出“两个尺度”的思想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主体性和实践性背景的,也是试图从人的能动性出发,完成自然和人的双重改造的目的。从“自然的人化”到“两个尺度”都体现出人的实践化本质与人区别与动物的自身化建构,只不过在具体的理解过程中,理论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生发出不同的价值观点。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实践派美学,正是从《手稿》的“自然的人化”和“内在的尺度”出发,以人的实践性联系自然外物和主体本身,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生产出了物质资料和生活产品,更是从意识和精神的维度使人反观到主体的“内在力量”,美和美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美的规律也正是和人的劳动实践规律相互协调。这是实践美学的主要理论支点。当然,在具体的理论构建中,对于实践的内涵、美感的产生和异化劳动等方面产生分歧,但是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发现和重视却一以贯之,“美”真正和主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美的创造实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理性和感性、物质和精神、对象和主体的统一”[15]。这正是对“客观论”美学和机械反映论美学的反拨,促使美学更加关注主体的实践性和感性能力,这不仅是美学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人道主义思潮和思想解放的美学意识形态需要。把马克思的人的本质主义观点和“美的规律”问题一同考察,发现主体存在的价值和能动的实践能力,是当时学界流行的观点。尽管在具体的内涵上可能稍有分歧,但是试图对马克思进行人道主义阐释并且借助美学来完成其人道主义目的,成为众多美学理论家的选择。从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到“美的规律”,都是首先从意识形态经典中找到美学和人道主义存在的“合法化”依据,实现理论的突破和进一步延展,而实践论美学正是契合了外部的审美意识形态需求和内在的主体性价值诉求,从而在“美学热”和“美学热”之后焕发出长久的活力。
其实,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针对《手稿》的争议绝非仅仅是美学自身的问题,也和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对“自然美”的界定大相径庭,其真正目的仍然是思想解放中对人道主义、人情和人性的肯定。创造和争取理论话语的激情已经远远超越了理论本身。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美学家而言,如果想穷尽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中“人道主义”话语的研究,是具有一定难度的,甚至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是,论争正是打破了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化”和“正统化”的理解,实践派美学家们希望从《手稿》中找到人道主义的突破口,并以此建构主客观统一的实践美学,从而确立人的生存性、主体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地位,进而以“美学意识形态”的视角完成对“文化大革命”的纠正,重塑知识分子话语权。“‘美学热’的产生正是试图将美学从政治规训下的客体论、工具论和反映论窠臼中释放,使美学具有一定自身的学科场域和言说方式。”[9]这种借“政治经典”告别历史的策略不仅仅逐步扩大了美学理论的言说空间,也使得人道主义思潮从“边缘”迈向“中心”得以可能。
对《手稿》以及“美的规律”的论争不仅仅只是着眼于美学学科的层面,更是成为人道主义思想在美学领域的深化,并且与宏大意识形态规律形成张力关系。当美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主体性为核心、以人学为价值取向的美学面貌,这一方面构成对僵化反映论美学模式的反拨与调整,另一方面也是人道主义思潮以及相关理论家们不断取得话语权的进程。美学天然的人文性与意识形态性则承担起历史使命,继续在“边缘”话语中完成人道主义的思想脉络。马克思的《手稿》以及对《手稿》的论争恰恰具有了主体性的彰显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双重功能。美学家们在“美学热”之初之所以选择《手稿》作为理论的生发点,正是希望借马克思思想和经典文本重塑人道主义和人情人性的合法性地位,以美学意识形态的方式实现“从边缘到核心”的话语言说。其实,对于《手稿》的美学论争主要还是集中在“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与美的规律等涉及“人学”与美学的关系上。对于在论争中的大多数学者而言,都是将主体的能动性、实践性和自由性等等与美学进行了关联性思考,试图在主体和主客体结合的维度中,找到美的规律。
在经历对了对《手稿》“自然的人化”问题讨论之后,“美的规律”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又一个热点问题。如果说“人化”问题还集中在人道主义、人的实践和主体性方面,那么“美的规律”一方面作为对人的问题的再次深化,另一方面则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层面谈论进入了对美的问题的探讨,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美学热”的重要论题。之所以会对产生美的规律问题进行再度发掘,依然是实践派美学家们试图重新彰显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将美和美感的生发都集中在主体的领域,恢复主体在审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僵化的“客体论”美学和“反映论”美学进行调整与反思。所以,《手稿》中“美的规律”就成为众多美学问题的出发点与核心,也是理论家在特定时期进行理论阐释与生发的依据。其实,该问题在西方并没有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相反在中国的美学大讨论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却显示出强大的活力。据统计,对《手稿》中“美的规律”一部分的翻译版本有21种之多[10],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刘丕坤、曹葆华、朱光潜和李泽厚的译文,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主要参照的正是刘丕坤的译文。就目前学界的习惯而言,更多是以《全集》中的版本作为权威版本。其实,马克思在《手稿》中探索的仍然主要是人的本质、人的实践和劳动的问题,而美的规律虽然只是对人的问题的补充,但是对于美学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规律”作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本质和必然联系,有其内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所以,事物的发展规律就决定了其本质意义上的存在;同样,对于“美的规律”的探寻,也正是试图对美的本质、来源和发展问题进行讨论,“规律与本质是同一层次的概念,规律即本质,因此,弄清了美的规律,也就弄清了美的本质”[11]。马克思在《手稿》中把“美的规律”和“人内在的尺度”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人内在的尺度”就为主体实践论美学提供了创设的契机,实践美学的理论家们试图将“内在的尺度”与“自然的人化”密切联系,在自然与人的结合中以实践的方式反观人的存在,以“内在的尺度”衡量美学的发生。所以,有关“内在的尺度”内涵的论争就成为关键。马克思通过人的尺度与对象的尺度的对比,完成了美的规律的“建造”途径。但是“两个尺度”究竟是作为对象的尺度,还是作为主体的人的尺度呢?对此问题的争议并不仅仅是学科内在的问题,更是如何树立美学的主体性价值和人道主义话语的问题,所以就呈现出更加多元和丰富的理论成果,也初步呈现出美学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2.2.5 进镜与膀胱镜检 视频监视下置入电切镜,观察全尿道。进入膀胱后进行细致、全面的膀胱镜检,评估肿瘤及可疑病变的数目、大小、位置、可能浸润深度及其与膀胱内标志,尤其是与输尿管口、膀胱颈口或膀胱憩室的毗邻关系。耻骨上膀胱按压与适当程度的膀胱充盈有助于观察膀胱前壁。
三、人道主义与新时期美学伦理话语的建构
朱光潜作为对人道主义、人性人情等理论进行首先阐释的学者,将美的规律和美的生发问题重点放在了主体对对象客观规律的把握中,这种把握和改造以实践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所以实践既包含了物质产生实践,也包括了艺术和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不仅仅是人按照规律的自觉生产,更是体现了本质力量的自由。那么,这种“按照尺度”的精神生产也正促使了审美的产生,“美的规律”的真实涵义也正是在于此。朱光潜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美的规律”内涵,但是通过对“两个尺度”的理解,进而确立了人的全面、实践和自由的审美方式。比如朱光潜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中指出,“美的规律”以及“对象本身固有的标准”等和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规律”相似,运用到现实的文艺创作中也正是“典型与个性的统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规律,这也直接将美学理论同文学想象结合了起来,符合朱光潜一直以来的理论表达路径和学术习惯。同时,他也高度肯定了艺术创造的实践性和审美活动中的感官作用,全方位肯定了人的实践能力对美的创设作用,“文艺主要靠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的基础正是掌管感性认识的各种感官”[16],“形象思维”、“艺术创造”等,这些都构成主体性实践的一部分,并成为人的整体、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总体看来,朱光潜将“美的规律”等同于艺术创造和审美活动的规律,注重将美学理论同现实的文艺现象和文艺活动相联系,将抽象的理论表达与感性化的例证进行结合,凸显了从人的感性到理性、物质到精神、形象到抽象的全面实践性本质,给实践美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泽厚仍然是着眼于主体的实践性来阐发美的规律,但是更加注重美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属性,从而和朱光潜的理论有相异的方面。李泽厚认为人的生产实践主要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艺术和精神生产是属于上层建筑和思想形式领域,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美并不是属于精神实践的一部分,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在“真”与“善”的统一关系中产生“美”,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美的规律”。“真”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善”是人类主体能动作用于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人通过按照自身的理想改造世界,实现对象化了的“真”和人化了的“善”,美的规律由此产生,“美”本身正是社会的、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和情趣的变化而转移。由此,李泽厚完成了实践基础上的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建构,但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忽视主体对美的感受和建构作用,“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自己实践的被肯定,于是必然地引起美感愉快”[17],“美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产生起来。所以,李泽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物质生产实践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主体全面、综合的实践能力和意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美的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蒋孔阳和陈望衡则在人的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维度探讨得更为充分,认为人能够通过“美的规律”通达自由之境。美和美的规律不仅有其不同于其他规律的“特有”属性,而且是具体形象的、自由的、愉悦的审美感知。所谓的“自由”是指目的性和创造性的人类劳动,“自觉”则是人具有自己的意识、按照人类自身的规律进行创造,正是在此两者的前提下,美的规律得以产生。同时,美的规律还具有个性和具象的特质,是人的独特活动。美作为主体特有的人的解放活动,是对自由生存问题的关照,这也恢复了美学学科自西方诞生以来的“感性学”原意,契合了人道主义的话语诉求。蒋孔阳的理论一方面发掘出马克思《手稿》中的人道主义元素,另一发面又以实践论为契机,提出了美学和主体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可见,在“美的规律”问题的探讨中,理论界大致分成了四派,其一是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认为美的规律是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典型化特质;其二是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将主体的精神和艺术活动纳入实践的范畴,成为对象本身内在规律的能动作用;其三是以李泽厚等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家的观点,一方面肯定实践的物质属性,同时也在“美”的客观性、社会性和“美感”的主体性辨证关系中,发现美的规律;其四是以蒋孔阳、陈望衡为代表的美的自由说,他们将美的规律和其他规律进行区分,侧重对美的特质和自由属性的发掘,是在实践美学基础上的进一步思索与生发,确证了美的规律和主体自由生存之间的关系。其实,对美的规律的再次发掘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诉求,更是美学学科意识的进一步彰显和知识分子理论热情的高扬,使得美学呈现出“救赎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对美的规律的考察一方面从《手稿》中发掘出人道主义的理论资源,以“美学意识形态”促使思想解放和社会救赎的进程;另一方面也逐步使得美学学科呈现出“独立”的风貌,试图恢复美学的感性学、个体化和自由化原意,在感性超越和审美体验中反观人类存在的价值,重新回归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席勒等审美主义的话语阐释。“等到想象力使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18],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人都强调了个体美学实践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凸显了审美“解放”个体和人类的合理性价值,美学学科也在20世纪80年代为知识分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所以,关于《手稿》美的规律的再次发掘和美学热的兴起,都是与人道主义思潮和对人性、人情的诉求密不可分的。
首先,把美学作为人自由自觉生存的体现,比如:“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9]所以,人在实践中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也正是使自身得以“澄明”的过程,而美的规律恰恰是其中的重要一维,在对自然感性的直观和劳动实践中,所获得的自由和愉悦形成了美感和美。这样,美感、美和美的规律都是通过自然的人化和劳动实践完成的,李泽厚等美学家们着重发掘了主体实践和美的规律之间的辨证关系,重新确证了主体性在美的规律中的能动作用。劳动实践不仅仅改造了自然,获得的物质上的财富,更是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人在改造自然、劳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以及自身力量的呈现。在此过程中,主体的心灵世界和审美能力得以提升,而所创造的客体形象也使得主体感受到自由和愉悦[20]。
其次,对《手稿》的讨论真正实现了将美的探讨和美的问题置于历史性的劳动实践之上。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和“两个尺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基础,也肯定了劳动实践和人的感知能力对美的生成的关键作用。动物的生产是本能的生存需要,是固定地按照“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而人的劳动却是自由自觉的,是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内在的尺度”运用到自然客体之上,所以人不仅使自然呈现出“美”的特质,而且也不断地提升自己实践的能力和创造美的能力。这样,审美就不仅是实践创造出来,更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和历史的需要。所以,《手稿》中所有美学问题的论争都可以看做是以主体性实践和人的存在为核心的美学观的争鸣,这一点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截然不同。美学大讨论实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宏大意识形态话语的美学“改造”过程,试图以认识论美学的张扬和美的本质问题的统一来实现意识形态的规约;那么,新时期的“美学热”和“手稿热”正是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破除僵化反映论和一元式话语的进程,以崭新的美学意识形态和审美现代性的“信心”重塑知识和话语的面貌,这也是人道主义话语权的另类彰显。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话语的绝对统摄之后,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获得了一定的理论重塑空间,而人道主义和美学就成为了“告别历史”的首要选择。而以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手稿热”和“美学热”成为了无法替代的历史承担,也是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诉求,对人性复归和人性自由的理念成为“文革”之后的反思主线。马克思的《手稿》和美学的学科属性为重新架构意识形态提供了可能。对于这一终极理想的追求和人的价值再发现都促使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人们重新反思主体性和自由性的历史存在。文学和美学天然地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美学也成为理想和现实之间有力的协调与沟通。“审美主义是对理性主义的反拨,它主张审美可以达到至真至善的境地”[21],美学自诞生之初就为高扬人的感性自由而努力,也在启蒙现代性的统摄中为主体生存提供意义,并时刻以反思的姿态促使人全面、自由地发展。而这些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思想解放、知识分子诉求和马克思经典论著《手稿》均相互契合,所以也就为知识分子们所重视,并且成为一门“显学”,“这是一种自由,但不是康德们和基督教士们以惩罚、责任、罪和救赎为目的和内涵的自由意志,而是纯粹自由的精神”[22]。知识分子们将人道主义思潮、美学的自由诉求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三者进行融合,在意识形态的合法化的空间中进行“美学意识形态”和“审美伦理”[注]“审美伦理”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是伴随知识分化和艺术自律的历史进程出现的,主要指涉一种更加独立、激进的美学价值观念。审美伦理的第一层含义是审美场域的独立,康德对主体审美判断力的论证、席勒的审美教育思想以及唯美主义的感性纯粹等,都给主体的感性和审美的艺术确立独立的场域空间。审美伦理的第二层含义是美学救赎的现代性方案的确立。通过审美场域的独立,美学以激进的姿态渗透到宗教、道德、法律、社会等诸多领域中,成为诸如“以美育代宗教”的救世策略。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批判、现象学美学的审美超越等,都进一步拓展了审美现代性的对抗价值。审美伦理的第三层含义是美学渗透进人与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协调和反思主体日常生活、感性精神、主体交往等维度的重要表征。此种含义主要体现在后现代文化语境,并表现出对审美现代性的延续。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韦尔施的生活美学等都将美学纳入主体日常生活,呈现出美学介入主体生活的力量。可见,审美伦理一方面指涉美学本体的独立意识和自律理念;另一方面则成为反思、批判主体生活的有效策略,给艺术和审美实践活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余虹:《审美主义的三大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林国兵:《艺术自律与审美伦理》,《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等等。的调整与反抗。审美、文学和美学作为人类终极价值的体现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一元化的集体论、反映论出现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美学以人道主义和人性、人情的面貌成为对抗“极左”意识形态的前沿,这也构成了整个时代告别历史、思想解放的知识运作措施之一。而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也大致包含两个维度上的意义价值取向,首先是现实性和阶级性的维度,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实践之上的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认知和意识体系,但是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阶级性和欺骗性。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更为明显,并进而与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往往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欺骗,拉法格激进地认为“每一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人民的情感与情欲上,印下它独有的形态。”[23]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和审美仍然是以意识形态政治工具的面貌出现的,美学也被取消了特有的反思性和人文性价值。其次,意识形态还具有总体性的维度,是作为普泛意义上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比如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艺术、宗教、哲学和伦理等等,文学和美学的意识形态正是在其学科自律的基础上,完成特有的理论与情感指向,这也正是美学意识形态的真实含义,其功能并非仅仅是对于政治“传声筒”式的工具论含义,更是在审美和美学独立的基础上,以其内在的感性特质对理性、社会、话语、霸权等进行反拨与调整。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文学和艺术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正是美学意识形态的表达。在他们看来,否定的辨证法、“反艺术”的审美理念、“单面人”的批判等都是在艺术自律、审美伦理和工业技术的语境中,以审美理念的内在性品格完成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和意识形态批判。在此基础上,美学以审美超越和审美独立的方式完成了对社会深沉的关照和历史性的反思,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也可以将思想、理念有机地融入美学的感性话语和价值体系之中。所以,在美学和美的规律中体现着主体的思想信仰和理想意图,成为一种具有独特规则和逻辑的话语表征实践。因为艺术和美学作为主体实践“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其中之一,体现出自由自觉的风貌和情感、理性、思想、信仰等价值选择,而在此种内蕴中,美学意识形态就成为了文艺活动的必然结果。意识形态性不应当成为文艺创作和活动的“出发点”,而应该成为具有审美价值和历史内蕴的文本。由此来看,美学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作为社会批判理论而出现,更是具有反思历史的价值。所以,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和“手稿热”的出现从外在政治社会角度而言,正是知识分子希望以“美学意识形态”完成人道主义的建构和他们对新时期思想的美学改造。
在从“文化大革命”政治异化的社会时期走向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美学热”的出现以及对人道主义、自由价值和人性人情的关注,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时代象征意味。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以来,整个社会转向了对人诗性价值的肯定和充满亲切感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思历史并且重塑信仰就成为美学以及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思索的问题。这种途径正是美学,美学由此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自民间到政治、自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的话语诉求,更是对尊重人性的、新生活的渴望。颇有意味的是,美学理论家们在“美学热”产生之初,面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手稿》),纷纷呈现出“六经注我”的方式,这恰恰内蕴着各自理论取向的美学意识形态智慧;知识分子和理论家往往从各自的角度,预设了一个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框架,然后在马克思经典文本中寻求阐释的空间,他们的具体理论细节可能不同,但是其实践性、人文性的基本价值取向较为明显。比如朱光潜在论述“美的规律”和其主客观统一的美学观点之时,就重在发掘《手稿》中有关“实践”“感性”和“主体”相关的段落,加强了对“人性”的论述,“对象化了的人性的眼睛”“具有音乐感的耳朵”“感官对象与人的现实界的活动”“有意识的物种存在”等,这是在预设了一个理论前提之下,对马克思思想进行重新考证之后的“再阐释”。朱光潜从《手稿》中发掘出美不是孤立物静止的,而是在人的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和重塑自身的结果,精神和艺术实践也构成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美正是人与世界之间产生的一种审美关系,这也正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感官能力、形象直观的体验以及社会属性都对于美的产生和人的改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生成的全面、自觉的生存和劳动,总体而言就是人性。而朱光潜有选择地重新节译《手稿》中的部分章节,依然是把“人性”“人”“主体”等词语广泛地运用在译文之中,例如“作为人性的生活的占有,就是一切异化的彻底废除”,“只有在社会里,对人原是他的自然的存在才变成他的人性的存在,自然对于他就成了人”,“因此,废除私有制就是彻底解放人的全部感觉和特性”[24]等。与我们经常使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译本相比,朱光潜大大提升了人性在译文中的比重,加强了对主体实践性、能动性和感官性的表述,这本身就体现了特有的意识形态取向。朱光潜在理论表述中仍然延续了其一以贯之的对艺术实践、个体理想和艺术修养的关注,当学习和引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后,便将主体的实践性同主观性进行了糅合、将“以心感物”转化成为精神和艺术实践,这种潜移默化的改造一方面延续了其长久坚守的美学理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在新时期为自身争取了更多的话语空间,构架了新时期美学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介入。对于蒋孔阳而言,其“美是自由的形象”将美学的本体属性与“审美伦理”联系起来,审美的自由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学在历史的进程中时刻以“自由”“感性”和“解放”的力量调整着主体理性的霸权和现代性的弊端,以心灵自由体验的方式通达生命中自由的冲动。这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美学意识形态的效果。蒋孔阳正是将“本质力量对象化”和“人化”同美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联系起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规约中,建构起崭新的美学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人的本质力量”其实也正是主体的自下而上、自感性到理性、自愉快到自由的审美体验,大力加强了精神化本质力量的涵义。同时,蒋孔阳在理论的建构中也更加重视现实的艺术实践和审美形象,将“自然的人化”与审美形象进行融合,在对审美形象的感知中试图通达自由的境界。“人化”有两个维度,其一,是按照人的思想与情感需求来创造形象,例如太阳在不同的情景中具有不同的形象,风和日丽、杲杲日出、烈如铄金等,这些都给予了主体不同的心灵体验,而它们之所以以丰富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中,正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移情”和“外化”的表达。[25]其二,审美形象也绝非主体单纯心灵感知的结果,更是渗透在文学中成为超越世俗社会与物质束缚的自由理想,这种自由感正是通过形象的综合积累和“恒新恒异”的创造来完成的。而李泽厚的“积淀说”、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刘纲纪的“美的自由的感性表现”、周来祥的“美是和谐”等,都是在肯定发掘美学自身内涵和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从美的自身规律出发进而实现对社会普遍起作用的思想能力,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美学热”的浪潮。在新时期之初,审美恰恰扮演了对理性压抑、文化权威和道德压抑的感性解放角色,并在人性的自由彰显中完成思想解放,这也是美学意识形态存在的真实涵义。伊格尔顿在论述美学意识形态之时,正是将审美和主体性的身体、存在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对话语霸权的反拨,“审美的非功利性包含着主体的极端的非中心化,它克制对他人的感性交流中的自我尊重”[26]。而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和伊格尔顿的理论语境有着类似之处,知识分子和美学家们在面对共同美、人道主义、形象思维、美的规律、自然的人化、艺术实践、主体性等问题时,已经深刻体察到美学意识对思想解放、人类自由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美学意识形态和“美学热”也相互促进,共同形成了告别历史的自由景观。2008年,李泽厚在与马国川的笔谈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毁灭美。十年内乱,丑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一些野蛮的、愚蠢的、原始的行为也被说成是革命的,给人们的教训太深了。这样,寻找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就是为了寻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研究美学的。”[27]
其实,李泽厚所描绘的“美的人生理想”形象地体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青春体”学术和“激情化”的人生理想,对美的渴求和人道主义的信念构成了独特的历史风貌,从而构筑了面向未来的强烈憧憬和热切希望。“美学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质:第一,是理想化和感性化的价值取向。“美学热”作为一种“青春体”学术争鸣,众多理论家在建构理论本身时有一种告别历史、否定现实的进取精神。尽管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力度依然强大,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体制还没有完全系统地建立,但是他们却以前所未有的反思精神和大胆热情的创新精神,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通过相对感性化和自由化的学术争鸣,推动人道主义理论脉络的深入。所以,由美学所构造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改良诉求一方面体现出知识界的热情,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明显的“空想”式风貌。人道主义思潮和美学感性特质的发掘正是西方由封建国家向世俗化现代国家转向的产物,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从“文革”到思想解放,二者有着相类似的历史场景和思想转变脉络。而在新时期“后革命”的语境中,虽然对曾经的“极左”思想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与质疑,但是对美好乌托邦的远景想象以及意识形态实践中的“一元式”话语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只不过在现实实践中以更加务实的“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所承担。所以美学作为“自由的王国”也仅仅是为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释放心理能量的空间和重塑梦想希望的话语,其介入现实的实践也与意识形态发生数次拮抗,最终只能在美学的领域中延续“超越”和“解放”的话语。第二,“美学热”体现出知识分子为寻求主体合法化存在的努力。在经历“文革”对知识的摧残之后,知识分子选择美学这一既具有审美性、纯粹性,又具有哲学性、思想性的学科作为“创造个人工程”的社会性潮流的一部分。而这一过程也是他们重拾话语空间、以“美学无功利”关注现实社会的努力,所以,在“审美独立”和“审美救赎”之间如何找到良好的平衡点,也是一直要思索的问题,正如李泽厚描绘的初唐诗人:“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与悲伤,一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28]笼罩在“康德的幽灵”之下的主体性美学与哲学也成为破除政治压抑的一种替代性美学想象,而这也成为知识分子话语启蒙的重要一维,最终在人道主义启蒙和社会历史批判的双重维度中开启了“美学热”的潮流。与此同时,当社会的新经济秩序和市场伦理逐步深入之后,作为社会启蒙和思想解放引领者的“知识分子”的美学表述和主体性话语将逐步让位于更加专业和深入的“学术化”话语,而此时的“人道主义”也从告别历史的激情想象转化为特定知识阶层的主体性情结和特定学科的知识谱系,进而转化为具有特定学科内涵的“人学”。与“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相比,固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传承性,但是更加强调了知识的生产体制和特定阶层的意识形态渴求,最终也将在学科领域内发挥着坚守和独立的力量。但无论是从激情的启蒙到深刻的人学,从“青春体”的现实介入成熟的知识分子认同,美学意识形态都以自由、解放、反思和人性的维度时刻提醒主体对生存价值的确证和对现实世界的精神超越,给意识形态统摄或商业伦理压抑的社会提供了一抹人文主义和理想不灭的亮色。
[参考文献]
[1]朗兹胡特,迈耶尔.历史唯物主义: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集·前言[M]∥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3.
[2]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J].文艺研究,1979(3):39.
[3]蔡仪.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J].文艺研究,1982(4):33.
[4]陈望衡.试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美学[M]∥美学王国探秘.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2.
[5]刘纲纪.关于马克思论美[M]∥美学与哲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44.
[6]朱光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一些误解[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29.
[7]朱光潜.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35.
[8]李泽厚.美学四讲[M]∥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510.
[9]裴萱.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理论谱系与价值重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194.
[10]杨庙平.《巴黎手稿》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形态建构[D].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22.
[11]陈望衡.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92.
[12]蔡仪.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M]∥美学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51.
[13]朱光潜.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98.
[14]朱光潜.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500.
[15]潘知水.马克思“美的规律”刍议[J].国内哲学动态,1981(10):32.
[16]朱光潜.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77.
[17]李泽厚.美学三提议(1962年)[M]∥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62.
[18]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49.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20]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10.
[21]杨春时.存在显现难题与海德格尔的审美主义转向[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7.
[22]赵广明.论尼采的“整体性”真理[J].江苏社会科学,2011(4):6.
[23]拉法格.浪漫主义的根源[M]∥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罗大冈,编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32.
[24]朱光潜.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M]∥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97-500.
[25]王赠怡.意象的方法论意义与诗画互补之美学意蕴的形成路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121.
[26]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8.
[27]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M]∥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11:54.
[28]李泽厚.美的历程[M]∥美学三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30.
From the Law of Beauty to Aesthetics Ethics:The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Marxism Aesthetic Boom in the 1980s
PEI Xuan
(The Center of Literature Theory,Henan University,Henan 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980s in the new period,theorists such as Zhu Guangqian,Li Zehou,Jiang Kongyang,Liu Gangji have turned to the research of Marx’s early writings of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and had made debate on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 and the principle of beauty,trying to find arguments from the manuscripts humanitarian,hum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freedom,and to determine the legitimacy of the Aesthetic Boom’s value.From the theory of natural humanization,Zhu Guangqian and Li Zehou had constructed a new concept of Marxist subjectivity and practice.At the same time,i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research boom of Marxist aesthetics.Theorists believe that aesthetics not only constitute a part of the subject practice,bu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liberation as a practice of social history.The discussion on “law of beauty” had complete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aesthetic ethics and extended target of subjectivity aesthetics,which had become a deepen language of humanitarian thought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When the essence of beauty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problems are closely together,it has become Marxism aesthetics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forms the core of subjectivity and the value of humanism orientation,it also has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intellectuals cultur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Marxism;Aesthetic Boom;“the law of beauty”;“naturalness”;humanitarian
中图分类号:A811.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9)01- 0087- 13
doi:10.3696/j.issn.1672- 0598.2019.01.011
* [收稿日期]2018-03-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10BZW002);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方法论转型”(2016CWX02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空间美学的建构与后现代美学理论新变”(2016-qn-08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59227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7T100527)
[作者简介]裴萱(1985—),男,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博士后,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责任编校:杨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