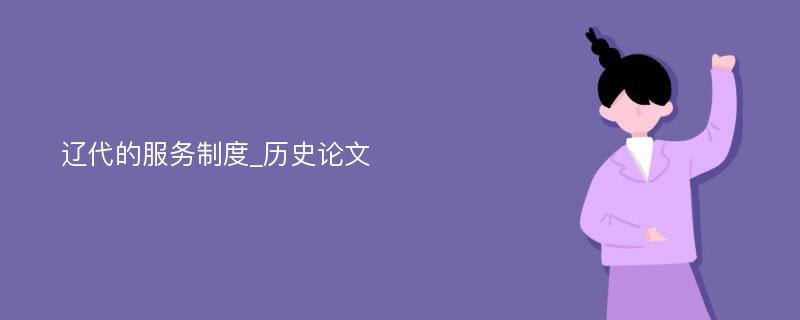
辽代的赋役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役论文,辽代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3)01-0064-06
辽初建国,即制定了赋役制度。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辽代各族人民要承担各种名目繁多的赋税,同时还要承担朝廷摊派的各种力役,如兵役、修城役、修河堤等。辽代的赋税制度分为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三种类型。辽朝依据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因此州县、部族与属国、属部的赋役制度有所差别,轻重有所不同。
一、赋税制度的制定及其依据
辽朝境内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渔猎经济三种类型。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为辽的南京道、东京道、中京道、西京道。上京道地区也有农业,但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或半农半牧。
辽代的赋税制度的制定,是在辽建国之初,其后几经厘改,形成有辽一代的赋税制度。《辽史·食货志》记载:“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时,又依据户丁之数重新加以改订。穆宗时“省徭轻赋,人乐其生”(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减轻了原来的税率。对辽赋税制度全面进行厘改的,是辽圣宗。当时因对宋战争,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大臣上言“宜轻税赋以来流民”(注:《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于是对西京道的赋税进行了改订。统和十三年,又“增泰州、遂城等县赋”。泰州在辽上京道,为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隶属延昌宫。可能先前所征赋税较轻,因此有所增加。第二年,“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注:《辽史》卷13《圣宗纪》。)。在此前,南京、上京、泰州似乎都增加了税额,但因增加的税额过重而又下令减少。这是对西京、上京、南京等地区的赋税全面加以重新改订,轻者增之,重者减之。之后,辽代税法基本上稳定下来。
辽代赋税征收的依据,一是“计亩出粟以赋公上”(注:《辽史》卷59《食货志》。),即以土地多少出赋税。私田征税,官田收租,土地越多,征税越多。因此,贵族、地主想方设法逃避赋税。统和九年,“复言燕人挟奸,苟免赋役,贵族因为囊橐,可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从之”(注:《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可见,贵族与地主相互勾结,企图免交或少交赋税,贵族与地主逃避赋税的现象可能经常发生,朝廷因此才有通括户口、检括户籍之举。
征收赋税依据之二为户丁与民产。辽太宗时,曾“籍五京户丁以定赋税”(注:《辽史》卷59《食货志》。)。辽圣宗统和年间,曾多次通括户口。统和八年,下诏括民田,次年,通括户口。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这是由于辽朝以户丁为依据而征收赋税,因此出现隐匿户口不报的逃税现象。朝廷采取通括户口、查验户籍的办法,搜寻隐匿的人户。马人望在南京任警巡使,“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它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注:《辽史》卷105《马人望传》。)可知,检括户口与登记民产相结合,是辽朝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民产主要为房屋、田产、畜产。辽道宗时检括户口,登记民产,对纳税者重新登记,是为增加赋税而防止隐匿户口、田产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杨遵勖为枢密院都承旨时,曾“奉诏征户部逋钱,得四十余万缗”(注:《辽史》卷105《杨遵勖传》。)。户部主管户籍与人口及征税,也有拖欠不交赋税之事存在。
二、隶属州县民户的赋税
辽朝赋税征收的对象,一是从事农耕的州县民户,二是隶属辽代部族的契丹等族的部民,三是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
隶属州县的民户,是从事农耕的汉族、渤海族等州县的农民。朝廷每年征收正税(田地税)两次,即夏六月至九月为一次,秋十月至十一月为第二次。《辽史拾遗》卷15记:“契丹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榷麹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这说明,辽代税制沿袭后唐旧制,实行夏、秋两税制。
此外,在《三朝北盟会编》等宋人编纂的史书中,对辽代实行夏、秋两税也有记载:“收复之后,番汉一等待遇,民户除二税外,应该差徭科率无名之赋,一切除放。”(注:《三朝北盟会编》卷50。)这是宋朝占领燕地后,当宋朝与金朝议燕地赋税问题时,谈到民户所交的“二税”问题,同样证明了辽朝实行夏、秋二税制。
辽朝的赋税主要包括正税、匹帛钱、鞋钱、地钱、榷麹钱、农器钱、户丁税、盐铁钱、义仓税等。上述所列杂税,多为沿袭中原王朝的税法。如匹帛钱,是在纳税以外,每匹帛再纳钱若干文。地钱是在正税外每亩另缴若干文,鞋钱是照地亩数再纳军鞋若干双而规定的钱数叫作鞋钱。盐铁钱为盐税与铁税。盐铁自汉唐以来,始终为国家专卖,辽也不例外。辽境内产盐很多,上京有广济湖盐泺,西京有丰州大盐泺,南京有香河、永济两盐院。上京设盐铁司,用以管理国家盐铁税收事宜。辽朝曾多次下诏严禁私贩盐、铁,但是却屡禁不止。道宗时的宰臣张孝杰,即以“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注:《辽史》卷110《张孝杰传》。)而被革职。铁亦为国家专卖,辽境内产铁地区有沙河、千山、首山、柳湿河、铁州、柳河馆等。《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载:柳河馆“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打造部落馆“惟有蕃户百余,编荆为篱,锻铁为军器”。《辽史·地理志二》记载,东平县“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文中的300户专事炼铁,但需交纳铁税。辽朝铁禁甚严,私货铁或将铁输于外境,都要治罪。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因被告发私藏兵甲而被杀(注:《辽史》卷110《耶律乙辛传》。)。
辽朝的酒为官卖,严禁私酿酒。辽在上京、东京、南京设麹院,有麹院使、麹院判官等,以管理麹务。《辽史·地理志》头下军州条记载:“官位九品之下及井邑商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
辽朝在沿边诸州各设和籴仓,“每岁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石”(注:《辽史》卷59《食货志》。)。文中的“收息二分”,是收取借贷者的钱作为义仓税。
辽代的赋税,各地区间有所差别。东京道原属渤海人聚居的地区,其中的酒税可以免征,盐禁也较松弛。“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麹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以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注:《辽史》卷59《食货志》。)辽东地区为渤海人所居之地,对辽东地区赋税的征收,较其它地区为轻,这是为安抚渤海遗民而采取的特殊政策。辽圣宗时,冯延休、韩绍勋主管辽东地区税务,欲按燕京地区的税率征收,辽东民众不堪重负,大延琳乘机为乱,平叛之后,朝廷免征增加的租税,才使民心安定下来。
头下军州民户的赋税征收,与一般州县有别。关于头下军州的赋税,元好问在《中州集·李晏传》中提到:“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免为民。”即头下军州内的民户要向头下主和官府各交纳其租税。像头下户这样既输租于官,且纳课给其主的,还有寺院二税户。《金史·食货志》谓:“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因此,辽代的二税户,不但指州县头下户,还包括寺院的二税户。辽朝崇佛,皇室贵族乃至地主和普通民众,都尽其所能,把田产、钱财、房舍、人户捐赠给寺院。寺院的田产、房产因此而逐年增多。兰陵郡萧夫人捐资创建的静安寺,“延僧四十人……施地三千倾,粟一万石,钱二千贯,人五十户,牛五十头,马四十匹,以为供亿之本……敕赐曰静安寺。”(注:《全辽文》卷8《创建静安寺碑铭》。)其中的“人五十户”,是指随同田产一同捐赠给寺院的民户。他们依附于寺院主,每年收成所得,要输租给官府,还要纳课给寺院主。辽朝的二税户,一直延续到金朝,至金大定初年放免为民,二税户才从历史上消逝。
三、契丹、奚族等部民的赋税
契丹、奚族部民隶属于辽内部族,也承担辽朝的赋税。《辽史·耶律挞烈传》记载,耶律挞烈在应历初,升为南院大王,他“均赋役,劝耕稼,部人化之,户口丰殖”。这说明契丹部民从事农耕者,要向朝廷缴纳赋税,出劳役。应历年间以前,曾有过赋役不均的现象,在耶律挞烈任南院大王后,这种现象有所改变,均平了赋役,而受到部民的赞誉。
兴宗朝,萧孝穆曾“表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又陈诸部及舍利军利害,从之。由是政赋稍平,众悦。”(注:《辽史》卷87《萧孝穆传》。)。又一次均平徭役与赋税,因而受到契丹诸部的拥护。
对契丹、奚族等部民的赋税征收,除粮食外,还有“俸羊”。《辽史·耶律室鲁传》记载,耶律室鲁任北院大王时,“以本部俸羊多阙,部人空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岁易南中绢,彼此利之”。可知,俸羊为契丹部民每年所缴纳的赋税之一。契丹部民除缴纳“俸羊”外,还要缴纳其它杂畜。《辽史·萧观音奴传》记载:“先是,俸秩外,给獐鹿百数,皆取于民,观音奴奏罢之。”萧观音奴为奚六部大王。可见,契丹、奚族等部民,不但要承担朝廷官员的俸秩供给,还要担负俸秩外杂畜的供给。直到统和十六年,才部分免除了部民所承担的官俸:“振崇德宫所隶州县民之被水者。丁未,罢民输官俸,给自内帑。”(注:《辽史》卷14《圣宗纪》。)崇德宫为承天太后的斡鲁朵,因水灾才罢免了民输官俸这项税收。
辽朝部民所输租税,要折合钱币计算。“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注:《辽史》卷84《耶律抹只传》。)耶律抹只为统和年间云内州开远军节度使。他奏请斗粟由折钱五改为折钱六,这对于部民来说,是有益的举措。
四、边远地区的民族及属国、属部的赋税
地处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居于辽内地的居民不同,他们每年只须向朝廷提供土特产品——貂皮、马匹、骆驼等,但数额也不小。在东北地区,《辽史·圣宗纪》记,开泰七年三月,“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马三百”。西北地区阻卜诸部,每年向朝廷的岁贡也有定额。开泰八年七月,“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注:《辽史》卷16《圣宗纪》。)。其它如乌古部、敌烈部、鼻骨德部、于厥里部、室韦部、术不姑部、女直部,每年都要向辽朝进贡数额较大的土特产品。这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部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圣宗因此于统和六年下诏减免部分贡品:“诏乌隈于厥部却贡貂鼠、青鼠皮,止以牛马入贡。”(注:《辽史》卷69《部族表》。)圣宗统和十五年,“罢奚五部岁贡麇鹿”,“罢奚王诸部贡物”(注:《辽史》卷69《部族表》。)。这说明辽朝对少数民族部族的贡赋,时有减免。
辽朝赋税征收数额的多少及轻重程度,史书无明文记载。据《辽史·耶律隆运传》记载:“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获,以其半给收者。”这当是对分制的田租。由于史书对地亩税率无明确的记载,因此对于辽税是轻还是重,看法分歧较大。现参照北宋的税率,大致估计一下辽代的税率。北宋的北方农田单位面积产量,平均亩收近一石(即100升),其税收为每亩田秋米八升,约为收成的十分之一弱。而辽朝的税率,据出使辽朝的北宋使者路振的记述:“(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围桑税亩数倍于(中国),水旱虫蝗之灾,无蠲减焉。”(注:《宋朝类苑》76引路振《乘轺录》。)
与此相反,北宋的另一位出使辽朝的使臣苏辙却说,汉人“赋役稀少”,“赋役颇轻”,只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持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多动遭鞭箠,富家多被强取,子女玉帛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注:苏辙:《滦城集》卷41。)。
上述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同是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与苏辙所得的结论完全相反。究竟哪一种说法更附合辽朝历史的真实情况?我认为,后一种说法,相对来说更接近辽朝的实际情况。理由是,在《辽史》中,多处记载辽朝免交或减少租税的史实。如“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注:《辽史》卷59《食货志》。),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统和九年正月,“诏免三京诸道租税,仍罢括田”(注:《辽史》卷13《圣宗纪》。)。统和五年,耶律隆运“上言山西四州数被兵,加以岁饥,宜轻赋税以来流民,从之”(注:《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大康元年九月,“以南京饥,免租税一年,仍出钱粟振之”(注:《辽史》卷23《道宗纪》。)。大康二年,“南京路饥,免租税一年”(注:《辽史》卷23《道宗纪》。)。大安三年,“出钱粟振南京贫民,仍复其租税”(注:《辽史》卷25《道宗纪》。)。
根据以上史料,我们认为,辽朝的赋税相对来说,应该是较轻的。虽然实际税率无记载,但从耕种荒地免交十年租税以及岁饥之年减免赋税的情况看,与苏辙所记“赋役颇轻”的说法正相吻合,是较为符合辽朝的历史实际情况的。
五、徭役及其种类
辽代的徭役,主要有军役、戍守、侦候、治公田、杂役、修堤、筑路、运输、驿传、生产等各种名目繁多的种类。
军役、戍守、侦候 辽代国民有担负军役、戍守、侦候的责任与义务。“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注:《辽史》卷34《兵卫志》。)其中的契丹本户,多隶宫帐、部族,即隶属御帐亲军、宫卫骑军。汉人隶兵籍者,被称为“番汉转户”。据《辽史·兵卫志》记载:“三京(指上京、中京、东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番汉转户为多。析津(南京)、大同(西京),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这是契丹、汉族、渤海族等服兵役的情况。辽建国初至辽圣宗时期,战事较多,每户男丁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辽朝留传的诗中有“父子尽从蛇阵殁,弟兄空望雁门悲”(注:《全辽文》卷12《无题佚句》。)之句。
辽朝分派徭役的原则,一是以户丁多少为摊派的依据。“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注:《辽史》卷104《耶律昭传》。)这是以户丁为分派徭役的依据。除年幼和年老者外,每户中的成年男丁大多都要服徭役。
服徭役的另一个原则,是“以贫富为等差”。“诸部皆有补役之法……近岁边虞数起,民多匮乏,既不任役事,随补随缺。苟无上户,则中户当之,旷日弥年,其穷益甚,所以取代为艰也。”(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脩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傭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求假于人,则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偿者。或逋役不归,在军物故,则复补以少壮。其鸭绿江之东,戍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丽合纵连衡,不时征讨。富者从军,贫者侦候。”(注:《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这些史料说明,辽朝服徭役“以贫富为等差”。实行先上户,次中户,再次下户的补役之法。无丁之家也要雇旁人代替。同时,选富民防边,贫者侦候。
从上述记载还可看出: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所承担的徭役,要比内地繁重。辽西部边疆的边界线较长,疆域辽阔,戍守的任务较重。“方今最重之段,无过西戍。”为此,耶律唐古曾向兴宗上疏:“自建可敦城以来,西番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注:《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但朝廷没有同意。
驿递 驿递是在各个驿站间传递情报,为较重的徭役之一。由于驿站与驿站之间有相当的距离,驿递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很远的路程,民众以此为患。《辽史·马人望传》记载:“民所甚患者,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之役,至破产不能给。”
马牛 马牛也是辽朝繁重的徭役之一,尤其是在战时,不但契丹部民、汉人,就连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要括马,以供军需。辽圣宗东征高丽,开泰八年七月下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开泰九年,“括诸道汉民马赐东征军”(注:《辽史》卷16《圣宗纪》。)。
运输 运输之役,是把皇室所需的生活用品,运送至行朝,或把军队所需之物,运送至军中。“契丹之粟、果、瓜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瓜以马送之虏廷。”(注:沈括:《熙宁使虏图抄》。)这是饮食的运送。果、瓜等易腐烂的食品,要求快速到达。在炎热的夏天,是较苦的徭役。此外,还有取暖、炊事所用的官炭。官炭产于神山县与滦河县。两县的县民,承担运送官炭的任务。“岁运泽州官炭,独役松山。(马)人望请于中京留守萧吐浑,均役他邑。”(注:《辽史》卷105《马人望传》。)
修护河堤之役 辽境内有西拉木伦河、潢河、太子河、混同江等江河,每当汛季,都要修护河堤,预防水灾。《辽史·大公鼎传》:“时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全辽文·贾师训墓志》:“寻扈驾春水,诏委规度春泰两州河堤,及诸官府课役,亦奉免数万工。”
行在(朝)役 行在役就是供皇帝行朝所需的各种杂役,如衣、食、住、行、渔猎、侍鹰、围场等各种杂役。《全辽文》卷9《贾师训墓志》:“徙同知永州军州事。既上,日夜经画民事利病。奏减其部并邻道龙化降圣等州,岁供行在役,调计民工三十余万,奏课天下第一,上嘉之。”从上文可知,辽朝每年提供契丹皇帝行在的各种徭役就达30余万人次。
诸宫杂役 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两位摄政皇太后各置一宫,皇太弟耶律隆庆置一宫,圣宗时期的宠臣韩德让置一文忠王府,共计十二宫一府。这十二宫一府有自己的民户、兵马,因此也有各种杂役。有时,也会免除部分杂役。耶律仁先“奏复王子班郎君及诸宫杂役”(注:《辽史》96《耶律仁先传》。)。
冶铁之役 冶铁主要为锻造兵器或造钱币,从事冶铁劳作,也是徭役之一种。《全辽文》卷11《丁文逳墓誌铭》:“旋出为景州龙池冶监。其冶铁货岁出数不供课。比来为殿罚者殆且十数人。皆谓公性疏放,况能庀于是耶。身族为累,其兆于此。公泊至,督役勉工,亲时铸炼,所收倍于常绩。复更征商榷酒等务。烦剧皆办,所莅称最。”
丁文逳任景州龙池冶监,“督役勉工,亲时铸炼”,可知冶铁也是辽朝徭役之一。担任此种劳役的多为渤海人。《契丹国志》卷24《王沂公行程录》记载:“七十里至柳河馆,河在馆旁,西北有铁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炼得成铁。”
筑路修城役 筑路修城为辽朝常见的徭役。室昉任工部尚书,“诏修诸岭路,昉发民夫二十万,一日毕功”(注:《辽史》卷74《康默记传》。)。修城役也是辽朝常设的徭役之一。辽初,汉人康默记任左尚书。“神册三年,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
建陵役与守陵役 修建皇陵与奉守皇陵,也是辽朝重要的徭役之一。担任建陵与守陵徭役的,既有契丹人,也有汉人、渤海人,其中以汉人、渤海人为多。康默记曾任太祖朝皇都夷离毕,“既破回跋城,归营太祖山陵毕,卒”(注:《辽史》卷74《康默记传》。)。可知,康默记曾负责营建太祖之陵。此外,还有奉守皇陵的徭役。辽兴宗为其父辽圣宗建永庆陵,“置蕃、汉守陵户三千户,并隶大内都总管司”。改隶山东县的渤海永丰县民,被辽穆宗从永丰县拨出,作为辽世宗陵墓的守陵户,隶属辽世宗的斡鲁朵积庆宫(注:《辽史》卷37《地理志》。)。
承担各种徭役的,多为契丹部民和州县民众。契丹贵族及少数民族部族的首领,可免除徭役或以部曲代行。辽道宗时曾下令:“诏二女古部与世预宰相、节度使之选者,免皮室军役。”(注:《辽史》卷69《部族表》。)除了免除军役,戍边及宫内祇候事也可以部曲代行。《辽史·兴宗纪》:“北枢密院言,南、北二王府及诸部节度侍卫祇候郎君,皆出族帐,既免与民戍边,其祇候事,请亦得以部曲代行,诏从其请。”对那些契丹部族中摊派的徭役较重而人户又少的,朝廷给予减免,或以富户代出赋役。“统和三年三月乙巳朔,枢密奏契丹诸役户多困乏,请以富户代之。上因阅诸部籍,涅剌、乌隈两部户少而役重,并量免之。”(注:《辽史》卷10《圣宗纪》。)
辽朝对契丹民户似乎格外优遇。除上述文中记载的可减免赋役外,有时对其它部还要给予“助役”。耶律仁先为北院大王,“奏今两院户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从之”(注:《辽史》96《耶律仁先传》。)。两院是指北、南大王院。隶属北、南大王院的民户,承担的徭役可由别部助役,这是辽朝廷对两大王院人户的特殊待遇。
隶属皇帝斡鲁朵的民户,其承担的徭役也实行赦免或减免。辽道宗对隶属其父辽兴宗斡鲁朵的春州、泰州民户的徭役,给予赦免:“曲赦春州役徒……赦泰州役徒”,“曲赦奉圣州役徒”(注:《辽史》卷25《道宗纪》。)。
除皇帝有权赦免役徒或大臣上奏免赋役外,地方长官也有增加或减免赋役的权力。圣宗朝的于越耶律休哥被任命总南面军务,负责幽燕地区的军政事务。幽州历经战乱,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休哥以燕民疲弊,省赋役,恤孤寡”(注:《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休哥有权力“省赋役”,可以推断各地区地方长官也有权决定赋役额度。其赋役额度有较大的伸缩性,地处西北地区的敌烈部,“数为邻部侵扰,民多困弊,命萧乌野为敌烈部节度使,恤困穷,省徭役,不数月,部人以安”(注:《辽史》卷92《萧乌野传》。),说明各地区长官有自行调节赋役额度的权力。免去贫困部民的力役负担,是节省民力、与民休息的正当举措。
也有的地方实行募役之法,年老体弱者和不能承担力役者可出钱,官府为之募役。南院枢密使马人望,“使民出钱,官自募役”(注:《辽史》卷105《马人望传》。)。这样,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于国于民都有益。
综上所述,辽代赋役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的。辽代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间几经厘改,而基本内容并无大的变动。辽代的徭役,种类繁多,契丹、汉、渤海等族人民,是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因俗而治,沿袭中原之制又有所创新,是辽代赋役制度的基本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