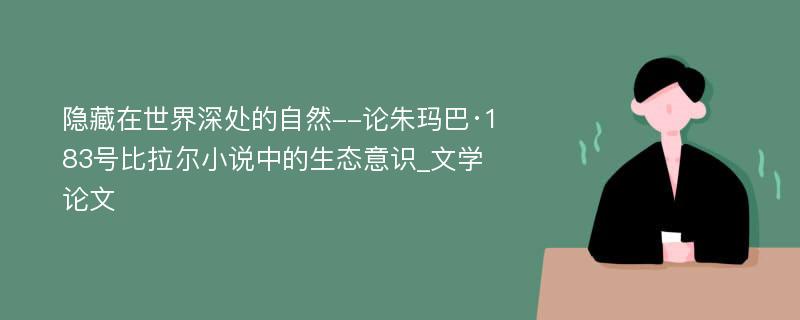
隐匿在世界深处的自然——试论朱马拜#183;比拉勒小说中的生态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深处论文,意识论文,生态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50120.1341.01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01-20 13∶41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5)01-00-07 一、引言 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文明很快步入一种变轨式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如同一副复杂而多变的面孔,不时地露出一股阴郁之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至今,既给人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享受,也滋生了亟需解决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自然的‘人化’,这种‘人化’是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全面割裂、疏远和冲突为代价的。”[1]自然生态不断恶化,人类精神也危机四伏,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当代危机?如何将现代人的精神追求与自然生态世界有效对接?多数作家选择以笔为武器,积极投身到唤醒人的精神自觉、关注生态危机的文学创作中去。以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为发端,一大批浸透了作家个人生态意识与世界情怀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现。他们常常以一种独特的生态叙事,借助这些作品来主动关注自然世界并思考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命运与未来,以此来揭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现世情态。而对于“生态意识”这一概念,最早由前苏联学者Э.В.基鲁索夫于1983年提出,即“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2]换句话说,生态意识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发生关系时植入的一种主体精神,一种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内涵之一。从生态哲学层面来理解现代生态意识,“其实质乃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过程中饱尝工业文化负面效应的时代产物。”[3]针对人类自身生存环境而言,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也急切地呼唤人类整体生态意识的提高,更要从生态价值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最终目标。 用哈萨克语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朱马拜·比拉勒,是当代哈萨克族作家中首批创作中、长篇小说的代表之一,其小说大多叙写的是哈萨克民族直面世界、敬畏自然的博大胸怀与生存智慧,其已成为独具哈萨克民族特色的文化标识符。一个个温润简约的文本犹如一幅幅饱含绿意的自然生态画,将大自然的百态玲珑剔透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给当代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草原之风。1956年从事文学创作的朱马拜,先后出版了《深山新貌》《原野小鸟》《同代人》等4部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集与散文集,其中有4部中篇小说和近20篇短篇小说被译为汉文发表,受到学界一致好评;作品曾获国家民委、中国作协的“山丹奖”、“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学奖”,卓越的文学创作成绩一度引起研究界极大的关注热情。当代诗人兼评论家沈苇曾说,“朱玛拜正在通往经典的道路上,他超越区域走向普遍,超越个性走向共性,超越民族主义走向世界主义。他在人类主义、忧患意识和对普遍命运的真诚关注中上升,并逐步跨入优秀小说家的行列。”[4]例如《棕牛》《白马》《蓝雪》等文本,立足人类面临的当代危机,通过对发生在动物世界里的残酷争斗和人类社会中复杂保守的风俗民情的深度剖析,思考人类与动物、与自然如何达到和谐共存,外来文化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如何在多元世界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精髓等问题,不断探寻实现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有效过渡的路径或方式。朱马拜试图通过其小说中独具特色的生态叙事,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危机、民族伦理品性以及基本人性的现代呈现,进而唤醒那些尘封于人内心深处、有益于协调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和谐发展的生态意识。 二、从动物叙事视角谈起 “借物言志”一词,古已有之,即通过对事物的客观描写与刻画,间接表达作者内在的思想情感。而此处所言的“物”,指的是动物。短篇小说《棕牛》是朱马拜从动物叙事视角出发,借“牛群”中因生存需要而引发的残酷争斗来对照人类自身,并对生存这一主题做了一些思考。作家以动物叙事这一视角作为切入点来反思当前人类遭遇的尴尬境地与生存危机,其叙事策略具有相当的先验性,并以此来探寻哈萨克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可以说,这种动物叙事视角突破了一般文本仅限于对“人”的叙事,体现了一种万物平等的表达姿态,即动物与人类一样有权分享自然、体现个体。小说中,作家隐去了人的主体性,以动物的思维方式、逻辑习惯去行文布局,带给世人不一样的叙述感觉,“通过对动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述这些有关动物的形形色色的故事,进而更加深入到对社会、文化、人性等更深层面上的探求。”[5]作家将个人的生活阅历、价值判断、审美体验、思维模式以及哈萨克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融入到动物叙事中,以动物的口吻来言说对生命、对世界的诸般思考,以动物面临的生存困境来昭示人类社会乃至哈萨克民族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彰显了小说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棕牛》讲述了一个同类相残的故事。文中主角是一头小棕牛,曾备受人类的虐待与折磨,好不容易脱离了苦海,获得自由,并试图主动融入到同类世界中去生活,不想却遭遇灭顶之灾。小棕牛起初靠近牛群时,因身上有股“流浪汉”的陌生气味,激怒了整个牛群,并遭到了牛群的反感与仇视。遭遇尴尬的小棕牛,毫不示弱,打败了牛群里前来惹事的挑衅者,由此得到了牛群暂时的接纳。然而好景不长,绿冈上的另一牛群中的头领——一头体格硕大的棕色公牛向小棕牛发起了挑战。迫于地位及体格上的巨大悬殊,小棕牛只好委曲求全、极尽谄媚,向这个“庞然大物”献殷勤:舔舐他褶皱的皮肤,帮他除虱,梳理皮毛等等,如此这般讨好,小棕牛不仅没有得到棕色公牛的认可,反而招致它莫名的反感与愤怒,还将小棕牛顶翻在地。也就在此刻,整个牛群蜂拥而至,大甲虫般向小棕牛迎面扑来,在同类如雨点般的脚蹄下小棕牛瞬间变成了一堆肉泥。秋去冬来,寒冷异常,绿冈上的牛们相继死去,那头“大块头”的棕色公牛也未能逃脱厄运,终而命丧屠刀之下。整体而言,小说情节简单紧凑,叙述笔调冷峻斐然,作家以异常冷静的眼光注视着牛群里发生的一切。在叙述者看来,牛群中为个体生存而发生的钩心斗角、相互厮杀是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常态,这种常态同样发生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从这个层面看,牛群如同人群,这种视角的选择体现了作家对自然、对动物及人类自身的一种态度;关注牛的世界如同关注人的世界,呈现出作家对当前人类生存现状的一种忧虑。在这里,作家是凭借对“牛群”的叙述来表达自己的一种价值判断与情感取向,这种叙事是切入小说文本最佳视点,帮助人们发现隐匿在文字背后的某种存在——生态意识。人类在整个自然生态体系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作家通过牛群里发生的一切来对照人类世界,其深层次的诱因来自作家潜在的生态意识。 以动物世界来映衬人的世界,让动物成为小说叙事、情节发展的主导者,叙述人却从台前走向幕后,成为隐匿在文本背后的潜在推手。赋予动物与人类一样的思想情感、心理情态与情感指向,这种叙事策略的运用将带给人们一种强烈的阅读冲击,激发人们来换位思考,反思发生在人类社会里种种残酷的纷争,进而引发人们关注自身、思考人与人之间该如何和谐相处下去。以动物的眼光来观察、体悟周遭的环境,去探寻自然世界里发生血雨腥风的缘由;通过呈现动物特有的思维方式及丰富的内心世界来营造独特而新奇的现代审美效应。小说中,作家以换位体验的方式,通过动物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冷漠、残酷与血腥来回应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以动物世界的冷暖荒凉来呈现人类的世态炎凉。可以说,作家以一种生态全局观去观照、叙写日益荒芜的人类世界,这种别具一格的动物叙事视角展现了作家从“人”到“动物”、以“动物”喻“人”的互动势态。在这里,作者放低了“人”的姿态,抬高了“动物”的品性,试图去寻求与自然世界达成某种默契的路径。尽管在文本叙述套路上,还略带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向,但这种动物叙事视角的选择明显呈现出一种平等、和谐的自然温情。 小说《棕牛》中的牛群可视为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另类缩影,人类社会里发生的激烈竞争也是如此残酷,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生存的压力、种族的繁衍引起人与人之间普遍存有一种紧张与恐慌,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日益局促,人的情感也变得日益麻木,无暇顾忌他人,更无法换位思考,替他人着想。“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固然是自然界的定律,多数情况下迫于生计,人却在不同程度上“误伤”他人、与世界发生冲突而浑然不觉,有如《棕牛》中的“庞然大物”棕色公牛及牛群里其他的成员,偶尔被一种莫名的情绪激怒,冷不丁地杀死了自己的同类,可又在事情发生之后,为自己的残暴与无知而懊恼不已。小说中小棕牛无心危害棕色公牛的利益,它的存在并没有威胁到棕色公牛“头领”的地位,何况从一开始小棕牛就向老公牛极力讨好。作家借此来隐喻人类世界里人与人交往时所面临的信任危机,带有强迫症式的狂躁与焦虑,错把朋友当成对手,造成对他人无法愈合、无法弥补的伤害。可以说,短篇《棕牛》是作家直面生态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的一种姿态与表达,通过揭示动物界中的残忍与冷漠来回应当下社会的某些扭曲、嘈杂的现实,进而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良知与正义。若是依旧我行我素,只顾一己之利,无底线地相互倾轧,缺乏和谐相处的共识,人类终将无法避免小说结尾所描述的带有因果报应意味的结局——牛群里的牛相继被冻死。文本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再现了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小说结尾处如此处理,略带有几分讥讽,饱含一种宿命意味,然而牛群的集体死亡却是触目惊心的,带给人们震撼灵魂的巨大冲击力。 从动物叙事视角出发来展开小说情节的叙述策略,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也有显现,然而这些文本尚停留在较为浅层次的诉求探讨,而朱马拜却有更进一步的深度探寻,他试图打破以往仅以个人的主观臆断就妄下评论的固有模式,深入挖掘“借物言志”的内涵,并融入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文学较为盛行的一种倾向——带有人文关怀的生态意识。作家着力刻画动物们在自然生态法则下的各种表现,以此来触动人类的精神世界,激起人们更多关注自身的生存困境与环境危机。“朱马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敏锐地感受到草原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在当时不能不说有一种醒世惊俗的前卫性。”[6]在《棕牛》中作家始终在做一种尝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桎梏,采取一种“第三方”的叙述立场,较为客观地为世人展现一幅接近真实、自然而然的动物生存图景。“以平等的笔触去观察、描写动物,不再把它们看成低等存在物。但在动物性格和命运的安排上又明显会有作家的意图介入其中,目的并不仅是‘以物代人’,而是通过动物真实的际遇把民族引入更深一层的对种族、对命运、对生态危机的思考中。”[7]就朱马拜的写作视野而言,早已突破区域、民族与国家的限制而放眼整个人类,勇敢地肩负起应对自然生态危机与人类精神危机的双重使命,把生态意识灌输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为人类谋划出一种令人向往的、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未来。 三、民族命运的一种隐喻 用母语——哈萨克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朱马拜,其作品中自然脱离不了对哈萨克民族命运及传统文化的深切关照,对哈萨克族民族特性、文化品性及民族精神的书写成了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用文字向世人淋漓尽致地展现哈萨克民族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事实上,这也是动物叙事视角在内涵上更深层的延伸,这种将动物世界里的伦理规约与人类的伦理诉求有机衔接的交互式叙事模式,衍生出动物与人、与自然“三位一体”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伦理架构,其目的在于“展现出作为人的思想意识的一个侧面的当代动物叙事其所能展现与诠释的民族志式的各民族整体精神风貌与伦理品格,进而达成对民族思想与内在情感意识流向的真正的凸显与洞悉。”[8]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逐水草而居是自然生活的常态,长期受到不同于农耕文明的游牧文化的熏染,使他们与大自然有种浑然天成的默契,他们亲近自然、亲近自然中的动物们。多数情况下动物们会成为游牧的哈萨克族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成员或得力助手,同时由于受到民族宗教信仰及动物图腾崇拜的深度影响,从本能上他们与大自然、与动物们形成一个息息相关的“生态共荣圈”,而这在本质上和动物与人、与自然“三位一体”的伦理架构是相契合的。可以说,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以动物为塑造对象来构建一个民族的主体伦理品性,进而呈现本民族主体伦理品性及其价值观念的形成过程。万物皆有灵性,这很大程度上与本民族古老的原始情感介质相吻合,体现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承与历史积淀。 小说《白马》讲述了从祖上起就厌恶美洲马的库特克依一家,曾拥有过两群几乎清一色的白马。然而,这个让库特克依家族引以为傲的纯种白马却陷入濒临绝种的危境,尤其在哈吉拜(库特克依的长子)死后境况日渐惨淡,“马群失的失,散的散,渐渐变得混杂不堪,后来只有一匹白马,作为马群的后代生存了下来。”为了保持白马种群的繁衍,牧人软硬兼施,用欺骗的手段驱使那匹白马与同种母马发生交配。然而,哈萨克族有个传统说法:好马是不找自己同种马做配偶的。[9]当白马明白了发生的一切后,带着满腔的悲愤与羞耻感狂奔而去,在坟前告别已故的主人哈吉拜后,径直奔向乌尔塔拉克最高的一座崖顶,腾空而起,纵身跃下涯去,用毁灭肉体来拯救生命个体灵魂上遭受的挑衅与屈辱,以自杀的方式终结了纯种白马种群延续的可能与希望。从叙述结构来看,文本简约却意蕴丰富,值得研究者去细细品味;从创作意图来看,作家试图通过阐述纯种白马的命运悲剧来表达自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未来前景的担忧,并呈现出对人性复杂内涵的自我反省。正是牧人的愚昧无知、急功近利,导致纯种白马种群延续的期望落空,这是“一首纯粹而高贵的物种走向衰亡的无可奈何的挽歌”[10]。在这里,作家借纯种白马的故事向世人发出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诉求:遵循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盲从“人定胜天”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否则,无知愚蠢的行为终将妨碍人类自身的进步与未来发展,无视自然规律的粗暴行为也将给自然界、动物界带来不可逆转的残酷后果。朱马拜通过文本呈现出动物品性的伦理指向,并以此作为哈萨克民族文化品性的某种参照。白马种群濒临灭绝的危境也预示了哈萨克民族也将面临传统文化消失的现实危机,这种将民族特性与物种个性对接起来关照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心中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作家将个体的生态意识与基本人性、民族品性相互参照比对,并将物性与人性、民族性与自然性糅合在同一个文本中,彰显其强烈的生态倾向与自然色彩。 “哈萨克民族长期的游牧生活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民族性中对自然的天然崇拜和热爱成为哈萨克作家创作不可或缺的主题。”[11]在朱马拜看来,哈萨克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一种悖论式的生存困境:如果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采取近亲繁殖的方式延续自己,其文化终究走向死胡同;若是盲目地接受外来文化,本民族传统文化势必会迎来触及民族灵魂的深度改革,而这也难以保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再者,忠诚、信仰及生命尊严等与人性相通的精神内涵与特质在现实中已然缺失,这也是文本里暗含的一种深刻的隐喻: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虽带给人们极大的物质享受,却让人的精神世界陷入日渐寥落的困境,虚无的恐惧感在人的灵魂深处滋生、蔓延。利欲熏心的人类早已被物欲迷失了双眼,抛弃了仅存的忠诚、诚信与生命尊严,这将造成人们在信仰上的根本性缺失,这也是目前人类灵魂失去方向、无法找到理想栖居地的危机所在。如此这般,人们会变得空虚、百无聊赖,甚至丧失,生命全部的尊严。对个体而言生命尊严是极重要的价值存在,“尊严会加重生命的分量,提高生命的价值,增添生命的美感,升华生命的境界。”[12]哈吉拜生前最看重的是尊严。为了维护老主人生前的信仰与死后的尊严,白马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捍卫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 就创作特点而言,“朱玛拜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常透出思辨色彩,颇具哲人风范,但又不是刻意为之。”[13]质朴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温情的警世是作家自然书写的基本特征。而就题材选择而言,“眼前的新疆不是陌生而冷酷的,而是饱含着温情与纯朴,这种令人感动的边地情怀融入到作家每一部作品中去。”[14]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对人类命运的动情关怀以及对哈萨克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是朱马拜小说关注的重要母题。作家以“物”为“人”代言,将动物与人同置于大自然中,书写动物与人彼此交错的生命场,借助动物的眼睛来透视人类的愚昧与无知,以动物的命运来预示民族的未来,都体现了作家内心深处平等、博爱、和谐且带有强烈生态意识的文学创作观。朱马拜小说世界里的动物们,不再是工具性的一种存在,而是被赋予了与人类一样的情感、一样的平等地位,享有与人类一样的思考权利。可以说,动物的命运、自然的命运和人类自身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而这些也是动物与人、与自然“三位一体”生态伦理架构的价值所在。朱马拜在动物与人、与自然有机结合的“生态共荣圈”中融入了自身朴素、平和的生态意识,将哈萨克民族的未来、命运与动物种群的未来、命运捆绑在一起,带有生态主义色彩的写作姿态对当今人类社会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四、人性深处的生态自觉 鲁迅先生曾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15]把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推向世界,是当今世界作家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种自觉追求。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固然令人怦然心动,人们有感于它们的厚重与新奇,但它也有局限性,存在禁锢作家创作视野的可能性。因此,唯有突破区域的、民族的视野限制,主动参与到共同构建全球精神价值体系的进程中去,以一种关切全体人类成员的胸怀去书写普遍人性与人生主题,才能让文学书写发生影响,进而促成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有其作品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的机会,但是只有那些不仅在本民族范围内产生发散性影响,而且同时对其他民族的精神生活产生辐射性影响的作家作品,才具有世界文学意味,或者说进入世界文学圈内。”[16]作家们立足本土传统文化,汲取本民族文化的优质精髓,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一系列具有丰富延展性与普世价值的优秀作品。唯有如此,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才会达到地域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微妙融合。 1988年荣获《民族文学》“山丹奖”的小说《蓝雪》,是一部以少数民族民俗风情为创作题材的作品。小说讲述了貌美的年轻寡妇胡尔丽海莺在丈夫死去不到十个月便另寻新欢,其行为触犯了当地部落的族规,要受到严格的惩罚:被“呛水”。究其原因也简单:一是亡人尸骨未寒,寡妇如此行径,让亲人们愤怒;二是作为游牧部落,受固有的生活传统规约,寡妇若改嫁其他部落,会使原先部落的财产受到损失。“越轨”的寡妇胡尔丽海莺受到了所谓的“惩罚”——一种带有仪式性质的象征性惩罚,咒语一般地念出“长头发的魔鬼!幽灵!这就是对你的惩罚!”“竟然没有一个人出言辱骂什么,那一对年轻人也不喊叫,更不见‘刽子手’动手打他们。人们只是在这清晨,在这丛林下的小河边,看到了一场威严的‘审判’。”可想而知,这种“审判”意味婉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严酷审判。实际上,胡尔丽海莺仅被看似盛怒的家族中壮汉象征性地浸入冰水中,便被迅速护送至家,唯恐冻坏了她。一个月后,她的幸福如期来临。婚宴上,全阿吾勒的重要人物都来了,族中长老宣布一对新人成婚,并说了缘由:“脚上的靴子,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穿的,胡尔丽海莺的事就这么算了。她家毡屋上冒出的炊烟,毕竟还是我们阿吾勒的。”[17]全部落的人都向他们俩表达了真诚的祝福。胡尔丽海莺的幸福来得如此简单、直接,不是什么人都能穿上阿吾勒部族的“靴子”,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生活哲理,即两人之间的婚姻如同各自双脚找到了适合的靴子,如果靴子曾经的主人逝去了,还可以选择另一双合适靴子的脚。 小说《蓝雪》虽结构简单,文本内涵却十分丰富,它把对叙事内容的展示置于复杂现实与真实人性的彼此纠葛之中。朱马拜小说的行文一向不喜雕琢,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淡雅之气,即使在描写胡尔丽海莺受到“呛水”惩罚时,仍是一种平铺直叙的语气、波澜不惊的平常心,而这些与作家特定的少数民族身份及信仰密不可分。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揭示是文学最具生命力的主题之一,对人性这一主题的书写也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人性的理解与阐释却因民族不同、地域差异与时代有别而各显不同。朱马拜运用独具哈萨克民族特色的叙述方式,通过深入挖掘本民族的人性内核,向世人展示了古老的哈萨克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精神信仰及伦理习俗。通过小说,人们可以看到:当古老哈萨克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正常的人性需求之间发生冲突时,陈旧的传统陋习则让位于普遍人性;这里“不应该是传统文化扼杀了人性,或者人性冲垮了传统文化的堤坝,而是在相互调和中给对方存在的权利,最终实现和谐共存,并因对方的力量而得以茁壮。人性因传统文化熏浸而更加内蕴深邃,传统文化因人性滋润而格外情怀温厚,给现实中的人更多心灵的抚慰,避免使我们变得浅俗和生硬。”[12]这种相互交融的方式体现了朱马拜对个体生命的温情关照和对普遍人性的理解关怀。人类是自然生态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重要部分,惟有合乎自然规律、顺从普遍人性的需求,才能构建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和谐共融的默契关系。 还应注意到,小说开篇对整个山村自然环境的描写,也称得上是一种生态书写,“山村,长长的冬夜终于走到了尽头似的,慢条斯理地揭开黎明的序幕。沙度沟口山坡上卧着的马群,纷纷站立起来,抖抖身上的寒气,然后悠悠地四下散去。新雪后平滑的旷野被它们踩得零乱不堪。它们的拼命地用蹄刨着大地,翻出往日黑糊糊的脏雪——寒冬的饥饿,几乎使它们啃食光乌琅哈依尔的每一根茅草。”“一条小河,向坡下白茫茫的开阔地流去。小河两岸的丛林边上,结着厚厚的、浅绿色的冰。河道中央的陆地上有一片丛林,林下有一个锅口大的小水洼。哗哗的浪花簇拥着一块在水里裸露着脊背的岩石,一只白脖颈的水鸟落在那块岩石上。它不安地摇晃着尾巴。谁知道,它向这条贫瘠的小河希求什么呢?”[17]一种近乎白描式的景物描写,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极力渲染出一种水墨画般的美感;简约的民族语言传达出浓厚的乡土生态气息,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之感油然而生。《蓝雪》文本是用一种单纯、精粹与优雅的语调展现了柔和的生存场景,其间腾起浓郁的诗意氛围,这种原生态的叙述方式进一步体现了作家内心世界潜藏的生态意识,这种对普通人性的尊重与关怀也彰显了朱马拜对自然生态未来的美好期待。 五、结语 文学作品中生态意识的显现具有十分重要的能动意义,“在认识方面,它反映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反映人类活动和生产的生态化规律性,这是人类认识的新领域。它作为人类有目的的、主动的、创造性的认识过程,将进一步完善人对世界的认识,使人类意识更接近于现实世界。”[18]朱马拜作品中或多或少显现出这种带有浓郁生态色彩的自觉意识,“小说家不是政治家、科学家,不可能提出解决生态恶化问题的具体方案。……作者更多的则是从人和动物的关系着眼,采用虚拟的手法,写出生态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的关系。”[6]朱马拜以动物叙事视角来叙述,固然无法回避人类中心主义之嫌,却能完成从“人”转向“物”,发生这一重要位移行为的本身已表明作家并非将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来俯瞰动物界与自然界,而是以一种平等的视角来关照自然、关照动物、来反思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生态问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可视作是向生态文学勇敢迈出的第一步。学者曹文轩曾说,“动物小说的不断写就与被广泛阅读……显示了人类无论是在潜意识中还是在清醒的意识中,都未完全失去对人类以外的世界的注意与重视。那些有声有色的,富有感情、情趣与美感甚至让人惊心动魄的文字,既显示了人类依然保存着的一份天性,又帮助人类固定住了人本是自然之子,是大千世界的一员,并且是无特权的一员的记忆。”[19]作家对普通人性、民族品性的深度挖掘与细致刻画很大程度上显现出作家潜意识之中存在一种生态自觉。朱马拜以质朴无华的小说语言、平静的自然书写以及水墨画般的环境叙述,使人沉寂于浸透了强烈的生态意识的自然之中,让人流连忘返。朱马拜小说创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将生命个体的生态自觉与人性、物性、自然性、民族性有机地融合起来,用一种平等、平和的心态去讲述那些被人们忽视的自然界中重要的关系,进而为重新审视朱马拜小说中隐匿在世界深处的自然之美提供了一种观察与思考的新视角、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