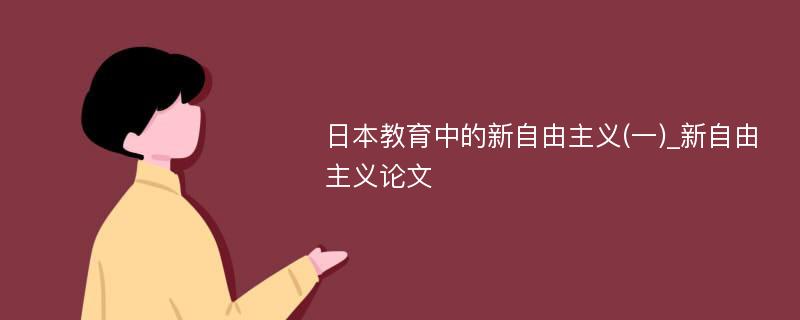
日本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3/57/3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0)11-0001-09
一、作为开端的临时教育审议会
(一)教育一线的贫困化
笔者在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的全国教师研修(教师自主研修)中做合作研究者(建议者)已经20年了。全国各地的教育实践首先在“日教组”的各支部层次进行讨论,然后在县教师研修集会上进行研讨,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教师研修报告,并在全国大会上发言。因此,虽然发言时间只有15分钟,但其背后却包含着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实践。
在“日教组”的全国教师研修中,笔者参加的是“出路保障与选拔”分科会,这里研讨的主题是如何保障儿童们的出路。现在,虽然高中的入学率已高达98%,可是依然有百分之几的人希望上高中,但不能升入高中。他们许多人是智力障碍儿童,被高中入学考试筛选了下来。应该保障全部希望入学的人都能升入高中、为此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一直被各地的教育实践提到全国大会上来,基于此,全国大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是20年来我们分科会一贯的经历。
但是,从今年开始,“日教组”的全国教师研修集会增加了一个新论点,这就是贫困。许多报告的内容是由于得不到奖学金,或者无法还债,而难以保障儿童的出路。而且,近来由于面临少子化的形势,再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恶化,所以学校合并迅速推进。随之,远距离通学造成交通费的负担增加,这给高中的升学和上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经济高度增长以来一度不太显眼的贫困,在今年这次全国教师研修集会上成了显著的问题。
一份全国性报纸以《高中重组需“考虑通学”——日教组报告通学距离拉大使家庭负担加重》为题作了如下报道(记者宫本茂赖):“以行政(部门)的财政状况和少子化为背景,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公立高中的合并。由于当地没有能够就学的高中,不得不到远处的高中去上学,所以,苦于交通费负担的家庭不在少数。要求行政当局改变轻易进行(高中)‘重组’、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进行交通费补助等的呼声正在高涨。”[1]
下面对宫本记者当天在我们分科会采访的各地的状况摘要性地介绍一二。
1.大分县。“当地县立高中的商业科从今年开始停止招生,当地的高中只剩下了普通科,想上职业类高中然后就职的学生必须到距离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因此,所需要的公交车月票费每月至少2万日元。有一个学生,由于经济不景气,父母的家业经营面临窘境,正在为是否应考不想上的当地的(高中)普通科而犹豫不定。‘学校合并发展下去,难道不是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了吗?’”
2.长崎县离岛。“从停止招生的高中的所在地到其他高中去上学,公交车的月票费大约每月2万日元。虽然公交车公司卖给高中生的月票可以半价,但这种优惠措施能持续到何时尚不可知。‘远距离通学(给学生带来的)体力问题也是存在的,(学生)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时间也不得不受到了制约。’”
3.北海道。“1999年度,公立高中有275所。计划到2011年度,(公立高中)减少到238所。北海道教育委员会制定了这样一项制度:从今年当地市町村的高中停止招生时,如果通学费和借宿费每月超过1.3万日元,则对其实行补助。但是,由于在制度上补助金要到10月份以后才能支付,所以北海道教职员组合指出:‘半年(4月至9月——译者注)的补助金领不到是不行的,要制定一个更加容易实行的制度。’”[2]
(二)国家方面的说明与贫困化的真相
前面仅列举了几个贫困化的案例。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小泉纯一郎内阁推行“结构改革”路线所造成的不均衡化。与小泉首相一道推行这一政策的时任总务大臣竹中平藏作了如下发言:“应该议论的不是不平等,而是贫困。虽然贫困扩大到一定程度在政策上不作出反应是不行的,但是作为非解决不可的大的社会问题的贫困,在我国是不存在的。”[3]
当时的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回答:“不能购买生活必需品的绝对贫困率,(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是居最低水平的。”[4]
但是,据汤浅诚披露,得出上述结论的根据仅是“海外民间团体只向700人进行电话采访所听到的主观回答式的调查”。[5]
汤浅诚在《反贫困——摆脱“滑梯社会”》一书中对“贫困化”作了阐述,下面试引用其一段:“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不景气以后,从正式工到非正式工的雇佣更迭迅速发展,非正式工人在这十年间(1997~2007年)增加了575万人,正式工人在同期减少了419万人……现在,全体工人的1/3(1 736万人)是非正式工,在年轻人阶层(15-24岁)中,非正式工的比例达45.9%,至于女性,其比例则超过了5成(达53.4%)。”“另外,地方上的商店街变成了‘百叶门街’,米价也暴跌……,自营企业主的生活的严峻程度已暴露无遗。所谓自由职业者的平均年收入约140万日元……根据国税厅发表的数字,2006年,工资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的达1022万人……如今‘只要认真工作就能吃上饭’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用作为劳动的代价得到的收入来支撑生活这种过去日本社会‘想当然’的事情,已经变得不是‘想当然’的了……”[6]
(三)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新自由主义
前面以“日教组”全国教师研修报告为例,探讨了不均衡化所导致的教育贫困的背景,也指出了其元凶是小泉纯一郎的结构改革。但是,日本不均衡化的源流必须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内阁时代。下面对这一历史过程作以阐述。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50%,高度信息社会到来了。巧妙地把握这种结构变化并企图转换战后教育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曾根内阁时代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1984年成立)。众所周知,“临教审”所采用的政策理念是新自由主义,即把新自由主义运用到教育之中。那么,新自由主义是什么?这里想以最近受到关注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阐述作以说明:“所谓新自由主义,无论如何,它是主张在以强有力的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范围内,使每个人的企业活动的自由及其能力得到无限的发挥,因而人类的财富和福利最大限度地增大的(一种)政治经济理论。国家的作用就是创造并维持符合这种实践的制度框架。”[7]
从常识上讲,新自由主义又可以换言为把市场视为万能、强调自助性努力和自我负责、趋向于“小政府”的理念。但是,大卫·哈维曾提请注意:在把握新自由主义上,不能仅单纯地把握其“市场原理主义”的侧面,在把握其理论的同时,还要把握“阶级权力的复兴这一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侧面”,要从这“两个侧面”来把握其“总体”。[8]渡边治把自己给新自由主义所下的定义作了如下阐述:“所谓新自由主义,它无论如何不是意识形态,是为了恢复全球企业的竞争力而试图对对此造成妨碍的现有的政治制度进行全面改变的运动和体制,是为了导入市场优先的制度而不惜采取强有力的国家干预。”[9]正像渡边治所承认的那样,这个定义与大卫·哈维的定义是同样的。笔者也认可这个想法。
(四)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背景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是由英国的撒切尔政权(1979年5月成立)、美国的里根政权(1980年5月成立)所主导的。但是,我们应该想到,在此之前,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英国有在“自由放任”的名义下开花结果的历史。可是,“通过上帝的意志对私人利益与公共善之间加以调和”这一古典经济学的理念并没有持续很长久。对此,省略详细的说明,结论是因为发生恐慌,造成大批工人失业,这使“调和”崩溃了。
众所周知,为了平息上述事态,主张一定的政府干预不可缺少的凯恩斯经济学出现了。作为划时代性的转折,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经过10年的思索,于1936年公开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此后,这种范式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主导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用一句话说,就是“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实现。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加强公共事业,抑制失业,另一方面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概括地说,修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稍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这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
但是,从日本经济转为负增长的1974年前后,在看上去顺利发展的修正资本主义中出现了阴影,坦率地说,就是出现了资本积累的危机。其原因在于通过阶级妥协实现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就是说,通过修正资本主义来延长性命的政策走到了尽头。为突破这种状况而做的尝试就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具体地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一方面彻底地弱化工人运动,降低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推行“毫无例外的管制缓和”和“市场主义原理”。这种政策由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发端,经过美国的里根政权(里根经济学),而后被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内阁所继承(因而,大卫·哈维指出:“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把1978~1980年看作是世界社会经济史的革命性转换。”[10])。
需要指出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因此,他们宣称膨胀的福利预算会招致慢性赤字,倡导“小政府”是不可缺少的。这样,主张“为了纠正不平等,政府要不可避免地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不受欢迎了。
(五)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临时教育审议会
如前所述,临教审认为,“新自由主义”适用于教育政策。另外,临教审还企图推行针对前面述及的伴随战后日本社会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儿童、青年的变化的改革。否则,临教审也不会得到广大国民的支持。临教审的改革是所谓“恰逢其时”的改革。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下面分两点来阐述临教审所要解决的问题。
1.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也就是说,日本从划一性、均质性的笼统地对待大众的时代转向了寻求差异化、多样化的人占多数的时代。为此,提倡学校和教育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转换是与时代合拍的——当初临教审就提出了“教育自由化”的口号。从“终身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换就是这种转换的一个例证。对此,下面将作以说明。
公民在想学习某种知识的时候,并不像过去那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把“学习”作为一种手段,而是认为学习本身就是愉快的,以掌握知识本身为目的而开展“学习”。日本已经到了持有这种“学习观”(从被动学习到自主学习)的人迅速增多的时代。巧妙地把握这种时代的提法就是“终身学习”。这一术语包含着从实行“教育”的教育者(教师)中心向进行“学习”的学习者(儿童)中心的意义转换,而且还简洁地表达出了进行教育和学习的场所已不仅限于“学校”这种激进的思想(学习是终身的)。临教审的“(教育)自由化”路线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人们期待着改变此前工业社会型的学校,为明治时代以来国家统治(官僚主导)色彩浓厚的日本教育打开一个通风孔(当时,全国性报纸的“社论”中也表明了这种期望)。“终身学习”在这一方向上,若沿着其提倡者(保罗·朗格朗、埃托雷·捷尔比)的思想得以实现的话,对于日本来说,不啻为划时代性教育时代的到来。但是,事实未至于此,其原因可在探讨下一点中寻求答案。
2.临教审提倡教育“自由化”(后来改为“个性化”)是为实现新自由主义,而将“市场”的自由导入教育之中,并积极地推进之。这正像“电电公司”转换为“NTT”那样,将“公共”教育移管为“民间”的教育。其想法是在教育方面,尊重学习者的“积极性”和“自由”,让民间分担教育产业,导入市场的“竞争力”。从已经指出的作为财政赤字对策的逻辑上来说,这一点应该说是临教审的主要目的。
这样,虽然口头上说是为了尊重学习者的学习“自由”,但事实上这种自由被限定为有自主学习积极性的人、有自我负担能力的人,即能够进入被限定在一定框架内的社会强者的“自由”。而且,弱势群体被抛弃了。这被视为实行自由的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坦率地说,就是促进教育中不均衡的扩大(阶层分化),抛弃弱势群体。这样,前述终身学习的理想意义当然就丧失了、被狭隘化了。这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第(一)部分中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教育的贫困化是由上述临教审提出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发端的。
(六)小结与今后的问题
笔者认为,正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以呼吁“战后政治总决算”上台的中曾根政权成立的临教审是日本教育中新自由主义的开始时期,而后这一政策被小泉内阁彻底化了。当然,在笔者看来,此后第14届、15届中教审对这一路线进行了若干修正(特别是第15届中教审提出了“宽松教育”),但是其基本路线并没有改变。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经过,渡边治作了如下阐述:“从结论而言,中曾根政权的新自由主义不是日本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它至多是早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尝试。诚然,中曾根康弘及其智囊团佐藤诚三郎、公文俊平、香山键一等已经了解到英国和美国开展的改革具有改变现存福利国家体系的新的性质,并意图将它们的做法引入到日本。然而,与美国、英国不同,当时的日本没有出现发达国家中为早日克服不景气、渡过第二次石油危机那样的深刻的(资本)积累危机……(于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真正开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细川(护熙)政权时期。而且……其演进是不可避免的曲曲折折的。新自由主义的真正推进是到小泉政权时才开始成为了可能。”[11]对此,这里省略详细的说明。简要地说,渡边治的见解是,由于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并不那么坚固,资本积累没有受到大的阻碍,所以日本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要比英国、美国晚十余年。
渡边治从经济、政治方面所作的详细分析的观点应该去充分地倾听。但是,笔者断言,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仍然是以临教审为开端的。原因何在?的确,正像前面所言及的那样,临教审之后的第14届中教审承认“不均衡”是教育病理,并建议通过“特色化建设”来加以矫正。仅从这一点来看,第14届中教审似乎是反临教审的。但是,对于由竞争而产生的不均衡,“特色化建设”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在高中“特色化建设”中设立艺术类、体育类学科可以成为对抗不均衡的计划,但是普通科由于升大学的原因,而完全未能发挥出这种效果来。此后的第15届中教审提出了“宽松教育”的建议,其理念是值得正面评价的,然而,曾长期试行的学校五日授课制和综合性学习终于得到真正地实施,2002年突然出现“学力”低下的强劲论调,形势发生逆转,出现了为提高“学力”而竞争的逆流。也就是说,第15届中教审通过“宽松(教育)”培养“生存能力”的理念,在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而增强国力、为此而加强市场的灵活性、提高“学力”的呼声面前彻底消失了。
以上所作的只是不充分的例证。然而,在教育上,临教审是新自由主义的开端,其改革构想被此后的历届内阁所沿袭,教育政策中不断地引入市场主义,比如,缓和中小学课程标准,缓和教科书审定,缓和对择校的管制,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开设教育特区等。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在小泉内阁时代出现了“胜利学生群”和“失败学生群”这种流行语,这如实地反映出“不平等社会”的到来。
进而想指出的是收入差别的扩大与学力差别具有相关性问题。也就是说,教育文化水平(文化水平)与经济水平具有相关性。关于这一点,引用以《希望不平等社会》而有名的山田昌彦的话作以说明来结束本部分:“即使学力是相同的,但教养、好奇心、交往能力在由知识分子家庭培养的人和由非知识分子家庭培养的人之间有很大差别……学校可以发展(学生的)学力,但是(学校中)没有发展可以用纸笔测验测量以外的能力的系统。培养这种能力的场所,现在除了家庭以外,是几乎难以想象得到的。”[12]
二、作为一定修正的第14届中央教育审议会
(一)作为教育病理的不均衡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临教审强烈地追求明治时代以来日本近代型学校、教育的转换。其咨询报告提出的口号是教育自由化、多样化或个性化。这使许多国民抱有这样的期望:为因受官僚统治而处于闭塞状况的教育界打开一个通风孔。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但是,正如前面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临教审所指向的自由化是通过新自由主义推进教育的市场化。在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考虑的前提下,在“自由”的名义之下,贯彻能力主义强化了不均衡的扩大倾向。经济评论员内桥克人根据严峻的现实所作的如下说明值得参考:“所谓缓和管制是什么?一般国民所朴素地接受的缓和管制好像是消除由行政、官僚制定的规章和规则,与过去看着上面的意向而行动的日本人的生活形式相诀别,从而使得自立的自我负责的社会的到来。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缓和管制的本质在于认为只要一切都按照市场机制行事就能顺利进行下去,无论大小、强弱,一切区别都不需要的‘市场竞争原理至上主义’的经济学”。[13]因而,如果将“缓和管制”换作“自由化”,将“经济学”换作“教育论”的话,那么内桥克人的批判可以当作是对临教审的批判。
临教审之后的首届中央教育审议会是1990~1991年的第14届中教审。第14届中教审集中审议了高中问题,其受到瞩目之处是,它公开宣称学校之间的“不均衡”是造成教育病理的原因。政府的审议会论及“不均衡”并公开言明这是问题,是从来没有过的。笔者认为,这种认识(诊断)是得当的。而且,它所开出的处方是,提倡通过高中内容的进一步多样化(特色化),同时选拔方法也实行多样化,任由多样化的学生进行选择,自然地就会形成由“能上的学校”(通过偏差值进行分流)到“想上的学校”(学生自我选择)的流变。
(二)儿童逃学及其背景
第14届中教审提出上述建议时的教育状况,可以用笔者的旧文来阐述。
“根据文部省1996年度的学校基本调查,小学、初中的不上学儿童达到过去的最高点,近8.2万人。(当时)不上学的标准是一学年缺席30天以上,按照过去的标准一学年缺席50天以上来看,与1985年度相比,1996年小学生的不上学者是1985年的3倍,初中生是1985年的2倍,特别是初中生中的不上学者连续21年一直呈增长趋势。”“在小学,500名学生中就有1名不上学;在初中,70名学生中就有1名不上学。顺便说一下,高中的中途退学者约10万人,近几年稍微有所减少,但仍然有1/50的中途退学率。按这个比例计算,每年将消失近100所有1000名学生规模的高中。”[14]
关于逃学的原因,需要作详细的研究,但当时笔者指出了以下两个时代状况。
1.“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记得当时流行‘分众’(被分割的大众)和‘少众’这种词语,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富裕的结果,虽然还没有达到个人化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了用统括性的大众不能说明的价值分化、选择多样化的地步。”“这种状况也反映在了儿童和青年的感觉和意识之中,他们讨厌划一性的学校,逃学倾向显著也不是没有道理的。”[15]
2.“(过去)多数国民都拥有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忍受现在的艰苦的精神,这支撑着日本的学校。然而,随着日本的大国化,作为样板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光辉暗淡下来,失去了曾经有的魅力。”[16]日本被迫需要自己建立新的价值和理念,但追赶型的日本的教育和学校已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了。这是孩子们逃学的主要原因。当时,笔者是这样想的。果真如此的话,准备实行“多样化选择”以适应这种要求的第14届中教审的处方就是可以接受的。
(三)高中教育多样化的现实——神奈川县的案例
第14届中教审所建议的高中教育“多样化”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内容”的多样化;其二,入口(即“选拔”)的多样化。
1.高中“内容”的多样化,一方面是设置多样化的专门(职业)学科和实行课程制等。专门学科和课程制的特征比较鲜明,想报考者也容易理解。另一方面是普通高中的“特色化建设”。这是比较困难的。仅从当时笔者听到的情况看,得到的回答仅是广泛开展俱乐部活动、使教学容易听懂、重视英语会话、重视志愿服务活动之类的做法。许多人都认为,这些做法是每所高中都需要的,普通科的特色化建设是困难的。这也是当时笔者的判断。
2.对于选拔的多样化,由于篇幅关系,研究全国的各种案例是不允许的,所以这里根据当时全国性报纸的报道介绍一下笔者居住的有许多教育工作者的神奈川县的情况。
“使学校由‘能考上的学校’变为‘想考上的学校’(这也就是说,不依据‘偏差值’来进行升学指导,而是使学校特色化,使其有多种选择枝,让学生去选择。这是第14届中教审的纠正不均衡的方针。——作者注)。取消过去以学习成绩测验作为选拔资料的选拔方式,从今年开始实行新的高中入学考试制度。”“新的(选拔)方式废除学习成绩测验,导入能让考生选择第二志愿的复数志愿制。其中包含着这样的(政策)目标:通过制定发挥学生个性的多种多样的选拔标准,同时推进特色高中建设,抑制高中中途退学率的增加(虽然说政策企图是‘抑制中途退学率’,但其重点是通过推进多样化来‘纠正不均衡’。——作者注)。”
但是,结果又怎么样呢?“(实行新选拔方式的)第一年(1996年)的结果是,名额未招满的学校有59所(641名学生),这一记录仅次于过去最高的1983年。另外,私立学校的平均竞争率达到过去的最高点,出现了学生向县内、外的私立学校流出增加的新现象。”[17]
作为参考,这里先记述一下神奈川县高中生选拔的变化情况。过去,全日制高中选拔新生时,80%的名额利用学校内部报告积点(占50%)、学习成绩测验(占20%)、学力测验(占30%)来选考;剩下的20%的名额作为“综合性选考”,参考调查书等来决定考生合格与否。然而,从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神奈川方式”的特征是:导入复数志愿制;从选拔资料中废除学习成绩测验;各高中公开“重视的内容”。下面引用《每日新闻》的报道作以说明。
“从第一志愿的考生中录取招生名额的80%,从第二志愿的考生中录取招生名额的20%。(判定)合格与否的标准是:对于第一志愿中70%的考生(占招生名额的56%),利用学校内部报告积点(占60%)、学力测验(占40%)进行选考;对于剩下的第一志愿中的30%的考生(占招生名额的24%)和第二志愿的全体考生(占招生名额的20%),根据高中方面公开的‘重视的内容’,综合性地进行选考(仅限于全日制普通科,专门课程和学分制高中除外)。”
正如所见到的那样,废除与通过“偏差值”排名次相关的“学习成绩测验”,引入“多次考试”,进而在选拔中采用“重视的内容”,当然是应对“多样化的”学生的高中“入口”多样化的一环。对此,作为实施主体的神奈川县教育委员会方面作了如下说明。
这是一项“多方面地把握每个学生的个性、不仅仅依据调查书评定和学力测验等的所谓数值来判定、而着眼于学生的特性和优点、学生能基于自己的出路期望进行学校选择”的制度。另外,“通过实行利用多种尺度的入学者选拔,使个性丰富的学生入学成为了可能,高中的特色化建设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18]
上述制度所期望的流程应该是:“学生自主地选择高中→各高中实行有特色的选拔→招收个性丰富的学生→高中的特色化建设得以推进”。[19]其中的枢要是“选考时所重视的内容”。因为根据上述选拔标准,将有44%的招生名额是通过综合性选考来招收的。
那么,这些受重视的“内容”具体是指什么呢?关于受重视的“内容”,半数以上的高中都以“高中特色化建设”为出发点,所列举出的除了学力以外的各种要素是班级活动、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的状况等。也就是说,这就是作为高中“特色化建设”之一环的内容的多样化。[20]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以选拔上的内容的特色为前提的。
(四)高中教育多样化与应试体制
即使认为“高中特色化建设”到这种程度是好的,那么一旦把上述要素作为录取时判定合格与否的材料来使用,就会产生问题。因为,由于做法的不同,会产生很大的主观性。即便是为达到客观化而实行分数化,其中也有不协调的“内容”。比如,班干部和学生会干部的“分数”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分数”怎样进行比较呢?它们能够进行客观比较吗?结果,各学校制定了各项“内容”的比较、换算表,煞费苦心地制定了详细的选拔标准。[21]
在日教组全国教师研修集会上也多次报告了这样的事例:在作为选拔“多样化”的典型事例而被寄予期望的“推荐制”中,标准非常难定,学生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强。为了接受推荐,学生方面的压力非常大也是不难想象的。下面引证一个神奈川县的例子。
“……她从(初中)二年级的秋天异样地开始注意班主任的目光。在(高中)入学考试制度的转换时期,在应试的同时,由于学校内部报告积点比过去更受重视了,再加上‘选考时重视的内容’的出台,不知道日常生活的哪些内容是和新的调查书评价相关连的,因此变得非常神经质。”“由于新的(选拔)方式中选考的标准不透明,所以调查书容易成为学生的精神负担。”[22]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有的高中在“重视的内容”中加入了“学力”。一位学区一流班级的高中有关人员这样指出:“我们高中在升大学上很厉害。学生(因为)正期待于此而报考我们学校。应对这种期待也是重要的使命。这必然要在今后的教学中重视学力。”大型升学私塾的代表也指出:“即使有以学力和大学升学率高为特色的高中也是好事,因为实际上想上这种公立高中的学生有许多。”[23]
这明显地是反对通过推进“多样化”来纠正用偏差值分流的一元序列化(不均衡)的第14届中教审的理念。事实上,一部分教师也有这样的反对意见:“结果,在追求学力方面没有变化。(学生中)有想进入大学升学率高的高中的强烈需要,有的高中试图想阻止它。(神奈川)县教委说了高中没有序列、不排序等漂亮话。但是,又有的高中重视英语、重视数学,总之就是只追求学力。对此,县教委予以追认也是事实。这被说成是新(选拔)方式的实况也是没办法的事情。”[24]
确实,即使再强辩只重视一部分科目(多样化的一例?),但在追求学力上是不变的,概括地说,给考生留下这是“重视学力的高中”的印象也是不可否定的。而且,前述大型升学私塾的代表的评论和笔者的印象几乎是相同的。“在这次入学考试中,志愿都涌到了大学升学率高的高中,高中之间的不均衡确实扩大了。进而,制度上有多个‘重视的内容’等不透明之处。结果,终至非志愿入学、目标和现实完全相反的学生比过去增加了。我想,如果要真心地消除高中的排序,除了削减学区内高中的数量以外,没有别的渠道。”[25]
由于神奈川县今年初次实行新的选拔方式,所以出现各种混乱或者有值得肯定之处都是可以允许的。但是,由于导入了“重视的内容”,可以推测有的学校非常重视“学力”,而有的学校不重视“学力”,高中的两极分化会进一步扩大。
一位教师的如下分析是中肯的:“如果把‘重视的内容’作为学力以外的多种多样的选拔标准来设定并使之与消除高中间的不均衡相联系,这只是一个原则。升学型学校已经用‘重视的内容’把重视学力的姿态摆在了前面。新(选拔)方式的目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高度维持一部分升学型学校的水平,防止学生向私立的升学型学校流动,阻止(他们)逃离公立学校。我认为,两极分化的结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情况。”[26]
(五)第14届中央教育审议会的问题所在——代小结
以上以神奈川县为案例,比较详细地论证了第14届中教审为纠正“不均衡”、消除逃学所采取的方法的现实。仅从笔者参加的神奈川县各地的教师研究集会上来自一线的报告和日教组全国教师研修中各县关于“推荐制”的理念和现实的报告来看,可以说神奈川县的情况决不是特殊的暂时的现象,而几乎是全国性的共同的事态。前面引用了神奈川县的教委、一线教师、大型私塾和考生的话语,其要点应该明白了。为了明确起见,这里试作总结如下。
1.临教审的意图是想用新自由主义打破官僚统治下的教育,这可以肯定有其道理,但是所采取的方法是教育的市场化。因此,弱势群体被抛弃、不均衡扩大就成为当然的了。
2.第14届中教审是以高中作为中心议题的,指出教育病理的原因在于不均衡化,提倡改善高中教育的不均衡状况。笔者认为,第14届中教审对问题的诊断(现状分析)是正确的。
3.第14届中教审提出的问题改善方法(处方)是学校、教育的多样化和特色化建设。具体地说,就是学校的内容和入学考试选拔的多样化,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试图消除和纠正偏差值下的一元化所导致的学校之间的不均衡。
4.专门(职业)科乃至课程制在性质上与普通科的差别是容易理解的,其本身就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但是普通科的“特色化建设”比较困难。普通科的特色化建设至多只是强调俱乐部活动(特别活动)等的“特色”。这种做法除一部分学校以外,各学校大同小异,难以与其他学校形成差别。
5.从现实来看,普通科要追求升学,其特色不得已也主要在于升学率,坦率地说,就是以“学力”为中心。特别是,升学型学校更是如此。
6.这样,第14届中教审所追求的消除由偏差值所导致的一元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能光指责高中方面。这是因为大学、企业甚至整个社会都是以“学力”为中心组成的,高中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7.如果想真正地消除和纠正不均衡的话,正像前面有关私塾人员所述及的那样,只有“减少学区内高中的数量”,即实行小学区制,或者在多所高中间实行综合性选拔,这即是按照成绩顺序向各高中分配学生的“综合选拔”。但是,采取这两种方法的县和地区迅速减少,现在全国几乎没有了。
正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第14届中教审尖锐地指出了被临教审所忽视的不均衡化。也就是说,第14届中教审的诊断是对的,但是只要教育病理是深深根植于日本现代社会的,那么谋求学校差异化的处方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疗教育病理的。
如上所述,第14届中教审承认了不均衡的弊病,仅从这一点来看,它是反对临教审及其新自由主义的。但是,第14届中教审提出的应对方案是多样化(特色化建设)。在以应试、升学为目的的高中普通科,结果,所谓的“特色”是与其目的相一致的,把“学力”作为了中心,在纠正不均衡上是无力的。正因为如此,第14届中教审的政策与临教审路线又不是相对抗的。为了从根本上纠正不均衡,教育要从国家管理转变为公民社会的共同管理。
(六)补论:对综合学科高中的期待
在本部分的最后,想说一下在第14届中教审的建议下开始设立的综合学科高中。综合学科高中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以谋求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的综合化为目标;2)想开辟通过多种选择使学生自己决定所喜欢的出路的道路;3)扩大、加深学校之间的合作,甚至学校与社区的交流。
从这些特色来看,这种学科不应仅在高中设置,设置这种学科的学校有发展成为选择性学校(alternative school)的可能性。笔者赞赏其理念,验证了全国各地的案例,唤醒了为一些学校实现该理念的热情所感动的记忆。
根据上述经历,当时笔者提出了针对综合学科高中的以下三方面期望或建议:1)虽然许多学校是为了“生存”而转换成综合学科的,但希望它们能认识到其选择性的性质,不要为当前的成败所左右,致力于其理念的实现。为此,行政部门在预算上予以重点分配是不可缺少的;2)为了实现其理念,希望实质性地废除高中入学考试,编制初、高中一贯制的课程,培养与应试学力不同的“生存能力”;3)从终身学习的观点来看,高中仅拘泥于3年是不必要的。希望让理解迟缓的学生继续在中学学习、允许有积极性的学生到大学和短期大学学习成为可能,改变以理解的进度差别来区分优劣的做法,积极地创造认可选择性差异和个性不同的风潮。这些建议在此后的教育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实现。
本文系翻译文章,“参考文献”部分中照搬了原文的参考文献信息,或者是根据作者的提示所作的参考文献信息。特此说明。
[收稿日期]2010-07-12
张德伟,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张德伟(1966-),男,河北衡水人,东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ZHANG Dewei,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注释:
① 本文是在日本长野大学黑泽惟昭教授的授权下,对其发表在日本《社会主义》(月刊)杂志上的系列论文(共4篇)的翻译文。这4篇论文分别是:[1][日]黒沢惟昭.教育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義——(1)はじまりとしての臨教審——[J].社会主義,2009,(9):88-95;[2][日]黒沢惟昭.教育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義——(2)一定の修正としての一四期中教審——[J].社会主義,2009,(11):102-109;[3][日]黒沢惟昭.教育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義——(3)教育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羲再考——[J].社会主義,2010,(3):45-52;[4][日]黒沢惟昭.教育における新自由主羲——(4)「ゆとり教育」の再審、改革のデザイン——[J].社会主義,2010,(4):100-107。本文分为上、下两篇,本期刊载的上篇是对原文(1)、(2)的翻译,下篇是对原文(3)、(4)的翻译。文中的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系译者所加,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系本刊英文翻译根据汉语翻译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