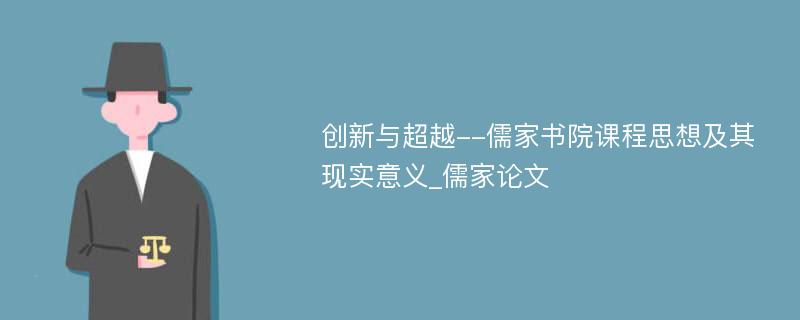
自新与超越——儒家书院课程思想及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书院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思想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创新已经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前途命运的核心词。在教育领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早已成为近些年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都在“新”字上做足了文章,着眼于怎样标新立异、怎样花样翻新、怎样耳目一新,为求新而新的教育实践活动不在少数。这样一来,那些看似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课程与教学实践,其实只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的改头换面,或是无关痛痒的点缀装饰。在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教育实践工作者对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一种基本态度,那就是对传统的信赖和对创新的怀疑。尽管广大中小学教师从不言明这一态度,但是在他们的实际做法中,怎样让学生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才是“正餐”,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可能只是“餐后甜点”。由此一来,那些看似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做法就很可能充斥着既鼓励又压抑学生创新精神的两股力量。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博弈,往往被少数学生创造出的新事物而掩盖,也常常在现实环境的升学压力下被遗忘。 创新,并不仅仅是形式样态上的面目一新,而是继承与突破传统中的超越。传统不是创新的排斥物,而是创新的内在物;传统是创新的主要原料,也是创新的意义旨归。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主题是如何让学生在继承传统与突破传统中实现超越。超越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专注于超越的目标的生命变成了有理性的生存。”[1]超越,意味着学生在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中探寻到自我发展的潜能,意味着学生在追寻完满的生活现实中挣脱文化环境的约束,意味着学生在不断摒除浮尘杂质中认清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独特。超越,让创新成为可能,也让人成为创新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反观我国古代儒家书院课程,在知行贯通的课程形态背后展现出虑敬相生、自然更新的课程心理结构。重思以自新为特征的儒家书院课程,不仅有助于揭示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中,继承与突破传统之间的辩证统一,而且有助于洞见自我超越所面临的阻力。 一、知行贯通的课程形态 官学课程在科举制度的怂恿下,间接强化了学习者的利己私欲,“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朱文公文集·白鹿书院揭示》),使得儒家思想不仅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批判能力,而且常常在社会动荡不安之时备受质疑。与此同时,另一支复兴儒学的思潮也正在不断酝酿成熟。理学在批判性接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基础上,为呼应赵宋政权内忧外患急于重整纲常加强文治的政治需要,以倡导“讲明义理以修其身”(《朱文公文集·白鹿书院揭示》)为特征,逐步取得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与之相应,书院作为理学思想的传播基地也开始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朱熹作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他兴修白鹿洞书院起,就将知与行作为两种并驾齐驱的学习要素统领学生的内在学习活动。正如《朱文公文集·白鹿书院揭示》中写道:“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这里的穷理即是知,笃行便是行。这篇作为白鹿洞书院课程标准的“揭示”将以往儒家课程中若隐若现的有关知与行作为学生内在学习活动本身的序和要明确地标示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序和要所标明的正是学生学习活动本身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学习活动其实是对知之穷理、行之笃行的意义探寻。将学生的学习活动还原为对联结知识与人的发展之间内在关联的意义追寻,使学生的学习从钓取功名利禄的遮蔽状态中解蔽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儒家课程史上的里程碑。在朱熹看来,学问不外乎就是两件事,一是知,二是行。“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朱文公文集·答吕子约》)而且,这两件事本身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行。”(《朱子语类·卷九》)由此,以朱熹为代表的书院课程就呈现出知行贯通的课程形态。 (一)知之穷尽 知行贯通的书院课程,将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作为课程的意义。在如何生成这一意义的语境中,知行贯通课程形态中的知主要指的是穷理。什么是理?“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朱文公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理’是事物之规律。朱熹认为,‘理’为事物之‘理’。作为规律,是不能脱离事物的。”[2]由此,所谓穷理,就是对这个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理的把握或领悟。 从课程的视角看,这个理本身并不是研究的着力点,倒是这个穷理的过程才是知的展现。当朱熹将这个理附着于天下之事后,置身于课程中需要穷理的对象也就变得包罗万象。也就是说,在知行贯通的书院课程中,课程内容其实是没有教科书这一边界的,生活处处是课程,万事万物皆课程。可见,学、问、思、辨,就不仅仅是局限在书本知识上的穷理,也可以推而广之运用到个体与外界事物发生关联时的穷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近思录·致知》)为此,朱熹从《大学》中开掘出格物致知作为对穷理更为广义的注释。 格物致知包含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外界产生联结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格物。“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足格物,须是穷尽到得十分,方是格物。”(《朱子语类·卷十五》)将尽训诂穷,意味着如果说对一个事物的认识程度有十分,那么只了解了三两分不叫格物,只有穷尽到得十分才算是格物。这个尽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夸美纽斯提出的教与学的彻底性原则。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知识能够彻底地被获得。不同之处在于,夸美纽斯为这种彻底性寻找到了根基,这里的根基一方面来自于唤起学生对学习本身的基本需要,“每门功课都应该这样开始,使它能引起学生的真正爱好,做法是向他们证明,它是如何的美好、有用、快意,是如何需要。”另一方面让学生的学习从一般概念开始以首先把握所学内容的整体结构,然后在这个整体结构的界域内实现对知识的彻底获得,“应当在仔细学习一门语言或艺术以前,先把它的一般概念告诉学生,使他刚一开始就能明白它的目标、限度和内部结构。”[3]而朱熹则更愿意探索这种穷尽背后人之发展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集中体现在格物致知的第二阶段:致知。“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朱子语类·卷十五》)具体什么是要彻骨都见得透,没有可把握的整体结构,有的是对自己虚明广大的天性之知的无限追寻,“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要当极其至耳。”(《朱子语类·卷十五》)因此,在知行贯通课程形态中,个体对穷理的筹划全部来自于一个宏伟志向的指引,“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朱文公文集·谕学者》)这个志可不是诸如美好、有用、快意这样的人之基本需要,而是诸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般宏愿伟志的高级需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志的树立不是课程所要解决的任务,完全依赖个体在进入书院课程之前就自行完成的。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在书院课程中延续,“正趋向以立其志”(《白鹿洞书院志·主洞胡居仁规训》)。 (二)知始行成 知行贯通的书院课程认为,行与知在人的内在学习活动中是并驾齐驱的,也是知始行成的内循环。这体现在知与行之间关联的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知行循环。从人的内在学习活动看,首先是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接着是行,“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间,事之所遇,物之所触,思之所起,以至于读书考古,知所用力,则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为力行也,岂但见于孝弟忠信之所发,行于事而后行乎?”(《朱文公文集·答潘子善》)也就是说,行是知之所用力处,是知之所发而行于事。然后又回到知。“人于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道理未有尽耳,不当咎其不可行,当反而求尽其道。”(《朱子语类·卷十三》)当行之不能时,寻找问题出现的根本不在行本身,而要返回到知上去找原因。如此一来,知与行就构成了一个解释循环。王阳明在《传习录·徐爱录》中将这一解释循环概括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可见,由知行构成的学习者内在循环系统,在知与行两者的互相转化中构成了不断促进知之透彻、行之有成,推动着知与行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发展。 第二个维度:知行互补。“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朱子语类·卷十四》)也就是说,知与行是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行不仅是在追逐笃的意义,也是在推动知走向明;知不仅是在探寻明的意义,也是在促成行走向笃。而且,当两者互相生发、齐头并进时,“如左脚进得一步,右脚又进一步。右脚进得一步,左脚又进。接续不已,自然贯通。”(《朱子语类·卷十八》)何谓贯通?“渐进之意甚明,结果为广大贯通。”[4]也就是说,知与行并不是可以分离的两个阶段,而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融合过程。这种融合一方面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外也是个体内部不断在与外界发生关联的过程中向外界敞开,对内在更新,以至内外合一,“合内外之理”(《朱子语类·卷十五》)。 二、虑敬相生、自然更新的课程心理结构 知行贯通课程所强调的是学习者个体在与外界交往过程中自身的独立性和整体性。“在知行二者相须相发的交互作用中,逐渐由知之浅行之小者,以成其知之深行之大者,最后达到善与我、心与理的完全合一。”[5]这种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建立不是外在力量的驱使,而是人自身自然而然的必然过程。这是知行贯通课程对人的发展的基本理解。“为学勿责无人为自家剖析出来,须是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要自见得。”(《朱文公文集·总论为学之方》)在朱熹看来,学习本身是个体自家去里面讲究做工夫,这个做工夫的过程本身是没有人可以剖析出来的,只有依靠自己做学问的工夫,这里的工夫对外即是虑的工夫,对内则是敬的持守。这就是知行贯通书院课程的课程心理结构。知行贯通课程强调学生内外工夫中两种心理因素的共同参与。“这种能动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认知,一个是情意。”[6]从认知的角度看,突出虑的工夫,是对以往儒家课程对人的发展的理解的秉持和发展。从情意的角度看,凸显敬的持守,却是古代儒家课程思想在对人的发展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尽管以往的课程理解中总是会穿插一些关于情意方面的认识,但是并没有像知行贯通课程形态这样将这些渗透在人认知活动中依赖感觉加以比较和区分的主体能动因素独立出来看待。一旦将这些情意因素独立出来,不仅丰富和完善了对人的发展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解将帮助课程更为精细、深刻地构筑知识与人发展之间的关联。那么,虑的工夫和敬的持守是如何得以实现知行贯通的呢?朱熹提到要自见得。知行贯通课程以自新释义自得,这就意味着在虑的工夫和敬的持守之间,真正贯通知行、融合内外的是新的自然。具体而言: (一)虑的工夫 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到“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进学解》),注重思考在学习活动中的重要地位是儒家课程的传统。知行贯通的书院课程不仅秉持了这一传统,更将思推进到了虑。虑源于思,但和思不同的是,“虑是思之重复详审者。”(《朱子语类·卷十四》)也就是说,虑所强调的是人在思考中重复详审,这样一来,有两个蕴含在虑中的关键因素就浮出水面。 虑的第一个因素是反思。“虑,谓会思量事,反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当是也。”(《朱子语类·卷十四》)这个反思,是对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当是的反思,更是将天下之事与自己建立关联的纽带。如果对天下之事所穷究的义理是与自己毫无关联的,那么就无法萌动出真正的反思,即使是有问题可能也只是无关痛痒、人云亦云的问题。只有将自己与周遭事物建立起关联,并在这一关联给自身造成或不符、或阻隔、或横断的内在体验处,才会萌动出真正的反思,才能引起人的深思熟虑。因此,《墨子·经说上》中写道:“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也就是说,这个虑中蕴藏着学习者的求知,这种求知指引着学习者的学习线索,并凝结着学习者的学习所得。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周密。“虑,谓思无不审,莫是思之熟否?曰:虑是思之周密处。”(《朱子语类·卷十四》)这里的周密展现出的是在虑中关系性思维的建立,看待任何事物并不是孤立地看待,而是始终将其置于一种由空间、时间、人事建立起来的复杂关系网的联结处。只有从这些关系的联结处着力思审,才能条理顺畅,才能思之周密,也才能穷极其理。 朱熹在给学生讲学《论语》时,就非常注重学生自学时虑的工夫。在《朱文公文集·论语课会说》中写道:“诸君第因先儒之说以逆圣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诸日用,必将有以自得之,而以兴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请得为诸君言之。诸君其无势利之急,而尽心于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为有余,推之以及一乡一国,而至于天下,不为不足。”朱熹首先对学生听、教师讲这一教学形态进行了批判,以突出学生的自学。接着,以孜孜焉蚤夜以精思突出学生虑的工夫。然后,当学生有所得后,教师再参与到学生的学习活动中,与学生讨论辨义。一旦学生有所得就要守之以善其身。 (二)敬的持守 如果说虑的工夫是知行贯通课程对人认知发展的理解,那么敬的持守就是对人情意发展的理解。“持敬是穷理之本。”(《朱子语类·卷九》)朱熹将敬作为人学习的本体,突出了对人发展理解中以情为本、以情发知的基本思路。当然,敬本身并不是朱熹的发明,“只如夫子言非礼勿视听言动,‘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笃敬’,这是一幅当说话。到孟又却说‘求放心’,‘存心养性’。《大学》则又有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至程先生又专一发明一个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参错不齐,千头万绪,其实只一理。”(《朱子语类·卷十二》)但是,朱熹将这个敬引进课程,并作为指引学生知行贯通的尺度。“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朱文公文集·答程正思》)这一尺度尤其表现在对学习者自身气质之性的约束上。 例如,朱熹讲《大学》,“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叙之以君臣夫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则天下之理,固己无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气之身,则不能无气质之偏以拘之于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于后。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乱其伦理而陷于邪僻也。”(《朱文公文集·经筵讲义·大学》)在朱熹看来,仁义礼智之性是人的天性,但是由于受到血气之身中气质之偏的干扰和周遭世界中物欲之私的影响,人原本的天性就会变得乱其伦理而陷于邪僻。为此,敬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对气质之偏拘之于前,对物欲之私蔽之于后,从而使人恢复到人本有的天性中。因为人只有恢复本有的天性,才能真正做到穷理笃行。 那么,究竟什么是敬呢?“敬只是一个畏字。”(《朱子语类·卷十二》)畏什么?“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其实,作为一个学习者究竟要畏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畏本身带给学习者的一种情感体验。当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受气质之偏干扰、受物欲之私影响的时候,能够在一种畏的情感作用下对这些干扰进行排除,对这些影响进行清理,时刻保持着一种如果不及时排除干扰、清理影响,内心就会不安的情感状态。这份不安就会让学习者恪守着将敬作为知行贯通的尺度,就会让学习者在敬中实现知行贯通。 (三)新的自然 虑的工夫和敬的持守是知行贯通课程对人在认知和情意发展上的理解。人的这种发展所追求的是对自我的更新,“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近思录·为学》)新是处于知行贯通课程中人的存在方式。 作为自新存在的人,其呈现方式是“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这里的新取自“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强调新是建立在故的基础上的新,是在时时温习中日积月累、反复经历虑与敬的打磨后生成出的新得。但是,“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朱子语类·卷一》)也就是说,新得本身并不是温故的目的,或者说,学习不是奔着追新逐异去的,而是在自我知行贯通的反复研磨中自然而然生成的。作为自新存在的人,其展开方式是“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近思录·致知》)也就是说,人在时时温习中所反复研磨的是对义理本身不断产生疑惑,不断从已知中发现未知,然后在疑惑的指引下不断濯去旧见,不断在发现新知中又产生新的未知。然而,这种新在虑的工夫和敬的持守作用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穷理者,非未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然脱然有悟处。”(《朱子四书或问·大学或问》)新,能让人豁然开朗,能让人广大澄明,能让人觉悟贯通,但是这一切全凭借日积月累中的自然而然。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一个人为干预的过程。 这种新的自然不仪表现在新得的自然而然,也表现在知行之间得以贯通的自然而然。“集知则自然行得。”(《朱子语类·卷十八》)这就对进入知行贯通课程的学习者原有的虑的工夫和敬的持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句话说,资质较高的学习者在知行贯通课程形态中可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资质较低的学习者在这一课程中则可能腾云驾雾、一无所获。 三、历史的积淀与封闭的世界 贯通知行、融合虑敬的自新是儒家书院课程的主要特征。自新,即自我更新,源于对传统的继承,强调学习者在接受和吸纳历史的经验教训中,通过不断检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更新对事物普遍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不断规约自己行为的笃实和坚定。在儒家书院课程中,自新是知行贯通的意义指向,是虑敬相生的内在机制,也是学习者力求超越的重要表征。在自新中蕴含着历史的积淀和封闭的世界,这不仅展现出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中,继承历史传统的重要意义,而且显露出在继承与突破传统之间实现自我超越的阻力。 (一)历史的积淀 在儒家书院课程中,知行贯通的主要原材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卷十》)这些经验教训古之圣贤已有提炼概括,学习就是对这些凝练历史经验教训的道理深思熟虑、琢磨玩味,将其中蕴涵着的对事物的普遍规律性认识挖掘出来,然后再基于这些认识和理解指导言行。对这些承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认识、理解和情感积淀在日常的生活习惯中。学习者的自新就是在不断积聚历史中付出重复历史经验的努力,就是在不断重复努力中形成习惯。“我们生活在形成习惯的过去之中,不断形成和打破习惯是我们此在生成的坚实基础,没有习惯为底蕴,我们精神的每一进步将是不可能的。”[7]以习惯为底蕴,强调历史经验的不断内化是自新期盼获得的精神进步。 儒家书院课程尤为看重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匹配,而这一匹配的结果就是习惯的形成。例如,《朱子语类·卷九》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朱熹与学生的对话。“或问:‘心之体与天地同其大,而其用与天地流通’云云。先生曰:‘又不可一向去无形迹处寻,更宜于日用事物、经书指意、史传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里,融会贯通,而无一理之不尽矣。’”这段对话是朱熹和学生就如何理解和运用历史经验而展开的。学生的提问着眼于理的本原,尝试着运用抽象思维展开形式逻辑以探寻理。也就是说,在这位学生看来,既然我们所要追寻的那个理是贯通万事万物的普遍之理,那我们在探寻这个理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将自己放置于天地自然的整体中,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去认识世界;是不是就应该总结并依循自然之理的公理法则指导实践。面对学生的这一探索,朱熹首先否定了这种与日常生活实际有一定距离、看似“无用”的抽象思维,不鼓励对自然公理之形式系统的建立,而是引导学生在日用事物、经书指意和史传得失上做工夫。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关于人事关系和现实成败的具体经验,比脱离实际、了无形迹的抽象理论重要得多。与其花时间去琢磨这些个“无用”的东西,不如老老实实在史传记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中琢磨成败得失的原因,在经书的微言大义中参悟避免损害的成功经验和立于不败的恒定规则。随着这些点滴经验教训的积累运用,学习者需要不断在这些零散的历史经验中区分哪些是精髓的、切中要害的经验,以及在应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时如何将这些错落的历史经验融合起来集中解决当下的问题。由此,学习者就将学习重心放在了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的匹配中,一方面以现实生活作为理解历史经验教训的背景,在对历史经验教训的不断重新解释中获得新意;另一方面以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判断现实生活的依据,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断评估价值中获得新得。这些新意和新得就是历史经验与现实生活之间匹配的结果,也是学习者形成的习惯。 凭借积淀历史经验教训形成的习惯,儒家书院课程可以让学生者获得一种实用理性。“实用理性强调历史的积累和文化对心理的积淀,认为从这里生发出客观性及普遍必然性的绝对标准和价值,重视历史成果。”[8]由此一来,学习者就形成了对使用和制造关于人体活动的物质操作工具的认识,这些认识不仅能让学习者避开各种可能的现实危险,而且能在重复前人成功经验的行进道路上不断有新意和新得。这些新意和新得既是普遍必然的标准,也是个人不断超越自己以追寻为天地立心这一至上之理的价值体现。 (二)封闭的世界 儒家书院知行贯通的课程形态让学习者在历史的积淀中实现对旧我的超越,然而,这一自新却始终拘囿于封闭的个体世界中。虑敬相生、自然更新的课程心理结构,不仅让学习者在保持内循环中实现自新,也让学习者在封闭的内循环中阻隔了与周围世界的关联。 例如,《朱子语类·卷九》中写道:“学者须常存此心,渐将义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进,即且把见成在底道理将去看认。认来认去,更莫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缘这道理,不是外来物事,只是自家本来合有底,只是常常要点检。如人一家中,合有许多家计,也须常点认过。若不如此,被外人蓦然捉将去,也不知。又曰:‘温故而知新’,不是离了故底别有一个新,须是常常将故底只管温习,自有新意:一则向时看与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则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则因这上面却别生得意思。”朱熹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强调对义理的认识不是借助外来物事,而只是自己的工夫。这一工夫既需要周密思考、反思量事的虑,也需要敬的持守以保证常常对自己的点检。从这个角度上看,学习者的自新就是在不断点检自己中改过自新。同时,在虑的工夫和敬的持守中生发的自新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已有历史经验的故底中温习出来的。这个故底,不仅是发生在他人身上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历史经验教训。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都需要全部转化为自己的故底才能得以温习。由此,温故而自有的新意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同样一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看是不同的,在这种不同的比较中就能澄清认识。第二,在已有的历史经验中蕴含着以前没有关注到的认识。第三,同一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反复的理解和运用也能生发出不同的解释来。这些表征学习者自新的结果一方面展现出在个体如何在继承传统中积淀来自历史经验的理解和情感,另一方面也将学习者个体框定在一个拘泥于历史经验本身的狭小空间中。 看起来,这些历史经验是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匹配式关联让学习者无法超出历史经验存在,无法将自身真正嵌入到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整体世界中。学习者无法走出被历史传统限制着的自身,无法逾越历史经验将个体与外界分开的鸿沟,无法真正敞开自身,无法去接受作为整体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种超出存在者之外的存在状态,我们称之为超越。”[9]当学习者无法超出历史经验而存在的时候,就无法真正做到超越,就无法在对世界的可能筹划中展开创造。与此同时,儒家书院课程心理结构中敬的持守,又在不断强调克制学习者气质之性的私欲中,将个体为追求个人幸福而萌动的反叛激情全然扼杀。“创造性活动从这种反叛中诞生出来。创造性不仅是我们青年和童年时期天真的自发性活动,而且也一定和成年人的激情有密切联系,这是一种想要使生命超越其死亡的激情。”[10]缺乏充满激情的渴望和想象,儒家书院课程中的学习者就无法真正投入自己的意志力量,就无法真正体验到实现自己潜能的心境,就失去了与世界交会的意义。此时,学习者就只是作为追求自新结果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自新的目的。当人沦为创新的手段、而非创新的目的时,人就在封闭世界的束缚中失去了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独特,更失去了存在的原初意义。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中,继承传统是突破传统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历史经验并不能成为某种现成的模式去封闭学生的世界,或是压抑学生的激情。人得以发挥自己天赋潜能的表达方式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更是反叛现实的勇气。儒家书院课程在回归人的现实需要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如何在此基础上保护学习者个体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量值得今人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