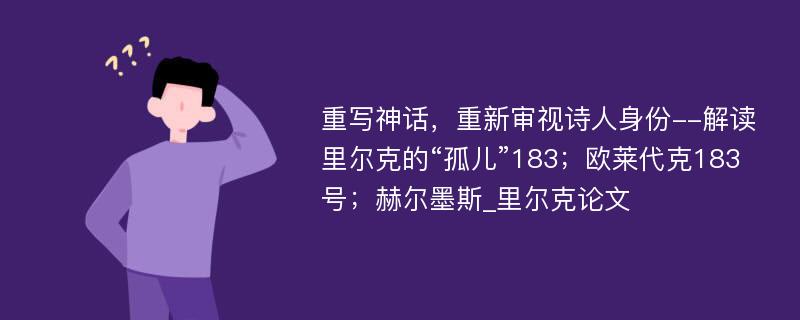
重写神话与重审诗人身份——解读里尔克的《俄耳甫斯#183;欧律狄刻#183;赫耳墨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写论文,诗人论文,身份论文,神话论文,里尔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耳甫斯是谁?品达说:这人是一个魂影之梦。对于诗人而言,俄耳甫斯的神秘身份正是他的无穷魅力之所在。无论是其扑朔迷离的身世、能够聚集树木和野兽的歌声,还是他奇异的地狱之行、哀婉的爱情经历,乃至于他的充满暴力而又离奇的死亡,都给后来的艺术家们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吸引着历代诗人不断重写俄耳甫斯的神话,让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人物在自己笔下复活。 在重新书写俄耳甫斯神话的艺术家中间,德语诗人里尔克是独特而耀眼的一位。里尔克用深邃的目光开掘出俄耳甫斯神话的丰富内涵,用天籁般的诗歌艺术表现出它的多重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在里尔克那里,俄耳甫斯神话不只是诗歌创作的一个素材。里尔克通过重写俄耳甫斯神话的方式重新确认俄耳甫斯的身份,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里尔克探索和确认他自己的诗人身份与使命的过程。里尔克的中期诗作《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耳墨斯》①展示了男性身份的俄耳甫斯的生存状态及其艺术力量的不真实,表达了里尔克的“学会观看”的诗艺理想;后来,在其巅峰之作《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那里,里尔克呈现了一个转变之后的俄耳甫斯,一个有着更深的自我认识并经由死亡重获巨大力量的歌者,一个赞美者、肯定者、保存者。通过这个找回了自己声音的俄耳甫斯,里尔克完成了由“观看”向“歌唱”的转变,确认了他自己作为一个有着神性直觉和权威的诗人身份。 因此,解读里尔克诗歌中的俄耳甫斯形象,有助于理解里尔克的诗歌成就和诗艺理想。限于篇幅,本文集中探讨里尔克的中期诗作《俄耳甫斯》,由此走近《新诗集》时期的里尔克及其艺术世界。 一、赫耳墨斯的视角 里尔克的《俄耳甫斯》一诗写于1904年,收入其中期代表作《新诗集》。里尔克将他在1902至1907年间创作的诗歌命名为《新诗集》,因为他意识到这些诗作代表了他的诗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新诗集》之“新”,一方面在于它更加精确地描绘了许多具体的事物,其中包括神话人物、宗教故事、艺术作品、动植物、建筑、风景和生活场景;另一方面,从德语抒情诗发展的背景来看,《新诗集》呈现出一种新的抒情风格,一种现代抒情诗的风格。它吸取了十九世纪后期的艺术特别是视觉艺术(绘画和雕塑)的经验,②试图用一种新的眼光来观看事物。此外,《新诗集》的作品还探索了语言的物质性,以及语言在视觉方面呈现事物的建构性角色。里尔克把这些“新诗”称为“物诗”、“眼目之作”。③“物诗”所描绘的“物”,并不是感知的“对象”或者屈从于人类的意志而被人化的“对象”(Objects),而是那些凝结了自身内在生命的“物”(Dinge/things)。而“眼目之作”这个说法则表明,与里尔克的早期作品不同,这些“新诗”创作的指引力量,不再是浪漫主义的“想象”,而是“观看”。里尔克意识到,正是这种“观看”引导他走出早期的浪漫主义感伤之作,步入诗艺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诗集》的这些“眼目之作”中间,《俄耳甫斯》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首诗贯彻了里尔克在这一时期的“观看”之道,贯注了他对于浪漫主义诗歌的反思。 《俄耳甫斯》重新描写了俄耳甫斯入地狱带回欧律狄刻的经历。爱与美的毁灭总是能激发人们心底埋藏最深的情感,俄耳甫斯那铸成大错的回头一瞥亦是艺术家们挖掘不尽的主题。当里尔克面对这段经典情节时,他的处理方式表现出明显的视觉性特征:重画卷式的场景展示而轻戏剧式的情节叙述,重旁观式的冷静描摹而轻置入性的情感抒发。全诗由目光贯连:直入读者眼帘的是走向地狱之门一行人的全视性远景,接着依次聚焦于三个人物(俄耳甫斯、赫耳墨斯、欧律狄刻),最后又回到全景视点,定格于俄耳甫斯在地狱门前的回头一瞥及其引发的反应。诗人的目光深邃,对三个人物的观照细致入微,同时却又不动声色,几乎没有任何情感渲染,笔调冷静而客观。一如那尊同主题的阿提卡浅浮雕,情感表达绝不溢出动作刻画的界限。 “观看”不仅主导着这首诗的题材处理,还渗透到诗歌的内部结构之中。这首诗的视角既外在于事件进程,有时候也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呈现事件与人物。这个从内部展开又外在于事件进程的第三方视角正是“赫耳墨斯”这个人物的功能。 赫耳墨斯是神话中的信使之神,商旅之神,奔走于神人之间传达神的意旨。在传统神话中,赫耳墨斯被看作是月神,他站在宇宙的中心,处于光明和黑暗之间,连接生命和死亡、外在和内在世界。在《俄耳甫斯》这首诗中,赫耳墨斯同样是一位中介者,连结俄耳甫斯和他的妻子欧律狄刻。从情节设置上来讲,赫耳墨斯是灵魂的引导者,作为神使行走于两个世界之间,指引欧律狄刻的灵魂走出地狱,引领她与丈夫相会。从诗歌结构上来看,赫耳墨斯的出场正好是在诗歌的正中间位置(94行中的42—46行),紧接着全视性的远景之后。赫耳墨斯的目光逐次聚焦于单个的人物,引领着读者的目光经过俄耳甫斯,然后转到欧律狄刻。 赫耳墨斯的观看视角不仅起到结构性的作用,而且还将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形象纳入进来。赫耳墨斯的凝视穿透二人外在的动作和姿态,并且进而让读者“看见”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内心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赫耳墨斯的位置和视角同样位于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这两个神话人物与读者之间。作为里尔克的代言人,赫耳墨斯的视角蕴藏着里尔克创作这首诗的真正主旨。那么,呈现给读者的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分别是怎样的形象呢? 读者可以看到(通过赫耳墨斯的视角),神话传说中的那个神奇歌手俄耳甫斯——他曾经能够用美妙的琴声和婉转的歌喉使不倦的猛犬入睡、使冷漠的冥王动情——在这首诗中仿佛失去了他的“魔力”,完全是一个尘世间的无助的丈夫:焦急、紧张、迟疑、敏感而脆弱,甚至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牢固地长在左手上/有如玫瑰卷须长在橄榄枝上”的竖琴。竖琴是俄耳甫斯的神奇魅力的源泉,是其通神之灵性的象征物,忘记了竖琴的俄耳甫斯此时此刻已经不再是歌手、不再是诗人,只是一个凡人。现在,他拥有的只是失去爱人的苦痛和重新得到她的强烈欲望,以及在死亡(再一次失去欧律狄刻)威胁面前的无能为力。死亡对于俄耳甫斯来说,无疑意味着界限、痛苦和分离,即使他可以勇敢地下到地狱,赢回妻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战胜死亡,死亡逼迫俄耳甫斯不许回头,让俄耳甫斯无法确定妻子是否真地跟随着他返回。 读者顺着赫耳墨斯的眼光看到的欧律狄刻又是怎样的呢?死亡将她带入了一种全新的存在,“一个新的处女期”,在这死亡之中,没有女性/男性的分别,没有自我/他者的对立,这是一种甜蜜的黑暗,一切都融合在一起:“被松散如长发,/被委弃如降雨,/被分布如百货。”——“她已变成了根”。“根”意味着黑暗和死亡不可分离的一体,所以,当赫耳墨斯“说出了这句话:他回头了——,/她却什么也不懂,轻声说道:谁呀?”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俄耳甫斯的在场,也认不出他来,她对自己的被爱、被渴望一无所知。这个欧律狄刻此时完全处于她自己的存在状态,一种更自由的、无性别的状态。 与文学传统中的欧律狄刻形象相比,里尔克的欧律狄刻显得非常特别。例如,在维吉尔笔下,欧律狄刻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恋人。当俄耳甫斯忍不住回头,死亡再次来临的瞬间,她如此哀叹:“——怎样的疯狂,俄耳甫斯啊,让你丢了我,让我丢了你?怎样的疯狂?残酷的命运第二次将我往后推,让我身处无边黑夜。我把无力的手伸向你!咳,我不再属于你!”④这个欧律狄刻虽然身在地狱,但是没有失去对爱人的记忆,在俄耳甫斯尽力赢回她的同时,她也在奔向他,相依相属是他们彼此理想的归宿。与维吉尔的《农事诗》对这个戏剧性高潮的渲染相比,里尔克的《俄耳甫斯》呈现出一个完全异样的欧律狄刻:她不再是那个伤心的“妻子”,无论是在身份和情感的意义上,还是在言辞和想象的意义上,她与“悠扬于诗人歌篇的那个金发女人”毫不相干。里尔克关注的显然不是作为恋人的欧律狄刻的情感,而是在地狱中的欧律狄刻具有的那种神秘而又自足的死亡状态。 二、欧律狄刻的形象 赫耳墨斯(里尔克的代言人)为何如此看待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呢?对欧律狄刻形象的挖掘可以让我们理解《俄耳甫斯》一诗的深层意蕴。 里尔克笔下的欧律狄刻蕴藏着死亡与女性的隐秘联系。里尔克常用果实和果核来比喻死亡的完满自足,果实意味着丰富、完满、孕育与重生,因此,死亡并不是仇敌,而是伟大的解放者,让人达至(回归)整全。⑤在他看来,女人和孩子更容易达到这种果实的成熟状态。里尔克在他同一时期(1908年)的悼亡诗《为一位女友而作》中写道:“于是你还看见女人像果实一样,/还看见孩子们,从内部生长/成它们的实存的形式。/最后还看见你自己如一枚果实,/把你从你的衣服里取出来,把你/带到镜子前面去,让你进去/直到你看见自己;你的身影在镜前很大,/却没有说:这是我;不:是这个。”⑥女人,尤其是年轻女人,代表了那些本能地拥有“真实”意识的人,与男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掌控倾向相比,女人活得更为内在,她们观看事物的目光更为“成熟”,这种目光在观看自己的时候也不是侵占性的:纳西索斯看见镜中的自己,为自己的自我分裂而痛苦,与此相反,镜子前的女人不会因自己的影像而感受到一种本性的分裂。因为女人所见的“自己”既外在又内在于自身,它不是通过在对象物那里的投射而获得一种存在肯定的“我”,而是作为“物”(Ding)的在场,一种对于“存在”的直接肯定。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女性的孕育也被赋予一种内在性和神秘性:生育创造出一个生命,同时又怀着这个生命的死亡,一种还未显明的命运,一种难言的死。因此女性与身体、黑暗、本能、不可知、无法言说、神秘、死亡等等元素相关,是男性目光无法穿透的、真实地存在于男性目光之外的“他者”。 正是出于对女性特质的深刻体认,里尔克“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欧律狄刻。这个新的欧律狄刻形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符合她在神话本源中的面貌。在前文学的神话中,“欧律狄刻”是一个通用的、形容性的名字,适用于任何一个神,意为“广大的统治者”,代表了自然的本性、大地的统治者和丰饶的季节。⑦有学者考证说:“欧律狄刻(Eurydice)的字面意思是‘统治遥远国度的’或‘无边国度的’。……所谓无边的国度,就是地狱,亦即亡者的世界。欧律狄刻说不定是色雷斯地区的亡灵之后,所以,她其实永远不可能随俄耳甫斯回到阳间,因为她的世界就在无边的地下。”⑧尼尔森(Erika M.Nelson)更加详细地表明了欧律狄刻的神话来源:在地中海的神话中,欧律狄刻是一个进入地下世界的女性,她与死亡和阴影之神相联系,代表着“月亮的黑暗面”。她还是一个与语词的神奇魔力相联系的神,是不可回返的地下世界的女主人——与冥后珀耳塞福涅一体。并且,欧律狄刻被蛇咬而身亡,这也象征着她进入了生命—死亡—重生的永恒循环,因此,蛇咬暗示着欧律狄刻进入地下世界之后的自我变形,她不需要被拯救,相反,是俄耳甫斯需要懂得重生的秘密,需要被拯救。 简而言之,欧律狄刻属于原初的黑暗、自然的节律、生命的死亡—重生的女神传统,她不仅代表这种非凡的死亡,也代表着非—生这种超越男性意识的不可知的状态。她象征着与自然及其节律协调一致的女性元素,持续地生长、变形,超越最初的存在,并且处于永远的“生成”状态。后来,宙斯—阿波罗所代表的男神崇拜逐渐取代了这种女神传统,这种更替意味着光明驱散了世界的原初黑暗,秩序取代了混沌,理性成为世界的立法者。 在里尔克看来,与欧律狄刻在地上活着相比,她的“死亡状态”反而是更加真实的现实,因为在这种死亡中,她重返自己的本源,生与死在此合为一体。这种死亡不是入地狱寻妻的俄耳甫斯所能够理解的(此时他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而不是神奇的歌手、那个半人半神的希腊英雄),对他而言,死亡犹如一道坚壁,一道深渊,无法穿越,也无法触及。犹如《新诗集续编》的“被爱者之死”所说的那样,“他只知人尽皆知的死:/只知它拖走我们并投入缄默。/但当她,并未为它所劫持,/只是悄然从它的目光挣脱,//滑了过去滑进不可知的阴影”。⑨这种不可知的死亡(阴影,黑暗)对于俄耳甫斯来说已经成为绝对的界限,也是凡人们恐惧和极力逃离的东西。与此相应,生命则是人们极力保存的东西,必死的人生在根本上意味着匮乏而非富有。正是出于这种匮乏,出于想要抓住某种稳固可靠的东西的渴望,俄耳甫斯才会在地狱门口那最后的一刻忍不住向后观望。这向后的一瞥标志着真正的分离——在生者与死者的世界、可知与不可知的世界、俄耳甫斯/男性的分裂世界与欧律狄刻/女性的完满幸福之间的分离。在这个层面上,里尔克的诗歌与传统的俄耳甫斯神话讲述着同样的含义:俄耳甫斯神话是记忆和遗忘的神话,由于俄耳甫斯忘记了自己的神性起源(他的母亲缪斯卡利俄佩是记忆女神墨涅谟绪涅的女儿,因此,俄耳甫斯可以直接凭借神谕言说,他的歌声拥有咒语般的力量),他从半神落入了一个凡人的境地,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死亡迎面而来,成为无可跨越的界限。遗忘意味着丧失了那种与原初整全的同一状态,并且导致匮乏。 里尔克用浓重的笔墨来描绘欧律狄刻的死亡状态,突出了这个欧律狄刻与俄耳甫斯所爱恋和渴求的欧律狄刻的差异,最终导向质疑俄耳甫斯作为歌唱者的神奇能力,质疑俄耳甫斯作为爱恋者的身份。俄耳甫斯对他所爱恋的这个女人的回忆和哀悼,曾经给他带来了某种力量,“以致从悲伤中产生一个世界”——通过吟唱欧律狄刻的名字,唤起她的在场,俄耳甫斯再一次经验到一个和谐完整的世界,一个只因这个被爱着的女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女人实际上却和随后出场的那个在其自身之中的欧律狄刻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出于匮乏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俄耳甫斯的悲伤更多意味着欲求不得满足的痛苦,这些情感来自于人对于生存的残缺和不确定的深深恐惧,尽管这些情感强烈到足以产生一个世界,但是,那个在其自身之中存在的欧律狄刻不属于这个世界——俄耳甫斯所爱恋的欧律狄刻只是俄耳甫斯的情感投射,一个幻影。俄耳甫斯的歌唱没有真正等同于存在,他所歌唱的主角、真实的欧律狄刻并不在场。 三、俄耳甫斯的限度与诗人身份的重审 里尔克的《俄耳甫斯》重新回到公元前四世纪的俄耳甫斯—欧律狄刻神话的主题。真实的欧律狄刻与俄耳甫斯所歌唱的欧律狄刻的形象错位、俄耳甫斯对其神性本源的遗忘以及在地狱之门的回头观望——里尔克重新书写的这些场景,蕴含着他对于俄耳甫斯的诗人身份和诗歌的真实性问题的反思。 俄耳甫斯的地狱之行,是“为了重建与已失去之物的联系而与未知的死亡和意识的‘他者’之域的遭遇,它同时也是一种向着一切创造之源的返回,一种向着已知和熟悉的却被放逐到黑暗和遗忘之中的事物的返回”⑩。当里尔克的俄耳甫斯站在那个对他至关重要的门口之时,他遭遇到这样的事实:欧律狄刻不认识他,甚至不需要他。爱人对他的拒绝意味着他作为爱恋者的身份、作为一个男人的地位得不到承认,“伴随着她的一声疑问,‘谁?’,欧律狄刻质疑了俄耳甫斯的身份,因此开启了他朝向‘认识自己’的行动”(11)。而且,这种认识的经验不在俄耳甫斯的理性/音乐之中,而在欧律狄刻的死亡/神秘那里。 在里尔克笔下,这种认识的经验富含现代意味:《俄耳甫斯》这首诗开头的两段景物,暗示着这场旅行不仅是发生在地下世界,同时也像是发生在内在的灵魂世界:“这是灵魂的奇异的矿山。/如同静静的银矿,他们作为矿脉/穿行于它的黑暗之中。”这个“意识的‘他者’之域”是用我们熟悉的事物来描绘的,但却依然显得奇异,并且难以理解:灵魂的矿山、根与根之间涌动着的沉重如斑岩的血液、空洞的树林、架空的桥、灰暗而盲目的池塘、苍白条纹的道路……这些画面的色彩对比鲜明,整个气氛却是朦胧而神秘的,这些隐喻与其说是对于意识的清晰捕捉,还不如说是一种对于无意识或梦境的含混表现。在这种实在/心理的双重背景下展开的场景同样处于一种可见/不可见的双重境地,可见的是俄耳甫斯的回头观望和欧律狄刻的逝去,不可见的是对于这回头一瞥的思考,以及重见爱人(这爱人已非旧相识)所引发的心灵风暴。可见的事件之结束,意味着不可见的、真正重要的事件之发生:俄耳甫斯再次撞在死亡的坚壁上,这次碰壁更加不可避免,更加无法挽回,他不得不从命运的哀叹中转过身来,将目光深入自我意识的黑暗之域、深入死亡,开始真正的灵魂之旅。(12) 在《俄耳甫斯》一诗中,俄耳甫斯是一位失败的浪漫主义诗人—歌手。他试图用悲伤的情歌挽救欧律狄刻,结果却是徒劳。这种充满了情感和回忆的男性的歌唱所创造的不过是虚影(女人是被造的另一个自我),真正的欧律狄刻在俄耳甫斯的语言之外,在无法分离的死亡中。俄耳甫斯的失败正是其不会“观看”的后果——应该看的没看到,不该看时却回了头。毋宁说,在《俄耳甫斯》这首诗中,赫耳墨斯表现了里尔克的理想诗人的形象,因为赫耳墨斯的观看更加成熟。他居于两个世界(生与死、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同时也是俄耳甫斯、欧律狄刻与我们(读者)之间的使者,传达着“真实”的消息。 里尔克对于俄耳甫斯神话的重新书写,并非只是诗人的个人事件,而是一个涉及诗歌乃至艺术本身的事件。探索俄耳甫斯形象的含义、挖掘俄耳甫斯的身份,就是探讨诗人和诗歌艺术的命运。 借助于俄耳甫斯的形象,里尔克一方面反思了现代人分裂的生存状态、反思了主观自我的脆弱性及其编织的世界图景的虚无性;另一方面,这种反思也关乎诗歌与艺术本身。如果将俄耳甫斯拯救妻子理解为拯救诗歌、语言、文化价值向虚无的沉落之行动,那么,他的失败就意味着日神状态中的俄耳甫斯(诗歌、艺术)不可能真正弥合诗人与被爱者(实际上是一个“他者”)、形象与客体、言说与存在之间的差异,因为这些差异正是俄耳甫斯的“拯救”行动的前提。所以,在《俄耳甫斯》的末尾,俄耳甫斯站在明亮的出口前目送着欧律狄刻返回黑暗,实际上真正被放逐的恰恰是俄耳甫斯——他的面貌“远得看不清楚”,“不可辨认”。而赫耳墨斯和“举止轻柔,却不急躁”的欧律狄刻仍然处在自己的真实的存在状态。被拯救者反过来成为引导者,拯救者才是需要拯救的人。 因此可以说,俄耳甫斯的限度正是诗歌(艺术)的限度。艺术家需要记取俄耳甫斯的失败的经验,需要在创造性的激情和自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需要有耐心、克制和寂寞,需要持续不断地工作、学习观看以及锻造物质性的语词,要让诗歌的语言构建出坚实的存在,而不是生成一个自我投射的无限世界、一个情感的虚影。 里尔克刻画了一位失败的俄耳甫斯,这表明他自己已经从俄耳甫斯的拯救行动中觉醒,感受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普遍的失语症,并试图用一种“言说着的凝视”来取代诗意的想象,试图走出男性中心封闭性的视觉幻象。但是,这种言说着的凝视是否真能达到语言和视觉之间的理想化的平衡,语词能否达到它们意指的实在事物?里尔克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语词与事物、观看的目光与被观看的“物”之间的那种无时不在的张力,换言之,走向观看的里尔克依然面临着诗人自我身份确认的困难:在其“物诗”中,事物(Dinge)成为诗歌的真正主题,诗人的主体性被召唤来解放事物而非自身,因此,诗人的自我就在当前和记忆的感觉印象的川流之中消解了。在与《新诗集》差不多同一时期写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体小说《马尔特手记》中,(13)主人公马尔特试图通过写作确认自我的存在,最终遭遇了失败。观看主体一方面想要掌控语言,另一方面想要任由事物进入观看者的血脉(“只有当它们转化成了我们体内的血液,转化成了眼神和姿态,难以名状,而又跟我们自身融合为一、再也难分彼此”,“一首诗的第一个句子才会从其中生发出来,成为真正的诗句。”(14)),想要说出事物自身的语言,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可超越的矛盾再一次将马尔特/里尔克带回到失败的俄耳甫斯附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最终正是这种困境促成了里尔克的更进一步的蜕变:里尔克从观看深入到对于观看本身的反思,这一次,这个“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在伟大的女性的引领下进入一个更本源更内在的开放空间,达到了真正的光明:歌唱即存在。诗人里尔克也在歌唱中达到了自我完成;在《马尔特手记》之后,历经十年的沉潜,里尔克终于完成了他“心灵的作品”(15),他的巅峰之作,即《杜伊诺哀歌》与《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 ①以下简称《俄耳甫斯》。本文引用的这首诗,采用的是绿原先生的译文,见里尔克:《里尔克诗选》,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336—340页。 ②See Karle.Webb.Rainer Maria Rilke and the Visual Arts.New York:Camden House,2001,p.264.Helen Bridge.Rilke and the Modern Portrait.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Vol.99,No.3(Jul.,2004),pp.681—695. ③转引自张海燕:《漫游者的超越——里尔克的心灵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④转引自吴雅凌编译《俄耳甫斯教辑语》,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⑤早在《定时祈祷文》中里尔克就开始采用这个果实的隐喻:“因为我们只是皮壳和叶片。/每人身上所含有的伟大的死,/这才是人人围着转的果实。”(《里尔克诗选》,第217页)另外一些将死亡的完满自足状态比作果实的诗作还有《新诗集》中的《诗人之死》,《杜伊诺哀歌》的第四首哀歌。在《新诗集续编》的《光轮中的佛》一诗中,里尔克则直接将佛比作果核,“一切中心之中心,核仁之核仁,/……宇宙万物直至大小星辰/都是你的果肉:这里向你问好”(《里尔克诗选》,第426页)。 ⑥⑦里尔克:《里尔克诗选》,第257、359页。 ⑧Nelson,Erika M.Reading Rilke's Orphic Identity.Bern:Peter Lang AG,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2005,pp.125—126. ⑨吴雅凌编译《俄耳甫斯教辑语》,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⑩(11)Nelson,Erika M.Reading Rilke's Orphic Identity.Bern:Peter Lang AG,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s,2005,pp.103,115. (12)里尔克在随后的《被爱者之死》(1907年)中提到,“这时他才认识了死者,/仿佛通过她而与每个/死者亲密亲近;他让别人说着//却不相信,而将那境界称之/为无限甘美的福地——。/并代替她的双足摸索开去。”《里尔克诗选》,第359页。 (13)《马尔特手记》又名《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笔记》,里尔克于1904年2月开始创作,1910年出版。《新诗集》于1902年开始写作,1907年12月出版,《新诗集续编》是在1908年完成并出版。《马尔特手记》、《新诗集》和《新诗集续编》的写作是交替进行的,其内容上也有互相对照之处。 (14)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曹元勇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15)见里尔克1914年的《转折》一诗(绿原译《里尔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92页)。这首诗为理解里尔克的“观看”之诗到“歌唱”之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