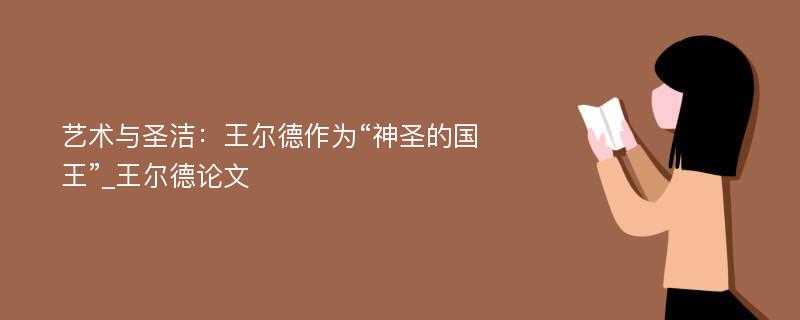
艺术与神圣——作为“圣王”的王尔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神圣论文,艺术论文,圣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692(2008)01-0108-05
文化史上发生在19世纪末伦敦的“审判王尔德事件”,不仅毁掉了王尔德这个人,还终结了唯美主义的美的历险,破灭了文学艺术的“神圣”价值之梦。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对审判王尔德事件反思较多的是其道德价值,而这一事件作为文化事件,更准确地说作为文艺事件,却少有深刻的反思。在这个反思现代性的时代,借助对现代性的思考回望王尔德事件,其所预示的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值得重新估量。
本文拟借助法国思想家巴塔耶通过对原始和古代宗教的探索所重新定义的“圣性”,来反思贯穿王尔德其作品、其生活的圣性情怀:从其作品对奢侈的描写所彰显的超越理性辛劳的圣性,到审判王尔德事件中王尔德违禁后的自毁,此种死亡欲念所隐含的对圣性的渴念。
在展开对王尔德事件的分析之前,先就巴塔耶所谓的圣性、违禁、滥费、消尽诸概念做一说明。
人化:动物性与圣性
巴塔耶所谓“圣性”,相关于他所理解的“动物性”。在黑格尔看来,人的原初状态就是“动物状态;事实上,天堂原本是一个动物园”①,成为人意味着超越动物状态。但与黑格尔从文化的立场否定动物性不同,巴塔耶寄予动物性肯定价值。在他看来,人类对动物性的疏远使“人类自己创造出自己”,人成为“人性”的人、文化的人;但人并不就此止步,他要重新接近被疏远的动物性——这种无限反复其实又永不能到达原初动物性的过程就体现了人对圣性的企求。②这样,圣性大约就是文化之后的动物性或自然性,是一种超越世俗文化性存在的神圣意向。在此,人性、文化性、理性诸概念内涵大致相近,与动物性、自然性、非理性相对称。
可以说,对动物性的疏远所描述的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理性觉醒,这是对上帝的理性的觊觎和僭取,因此由此而始的人化之旅充满艰辛和苦恼。不过,巴塔耶要强调的不是人化,是人化的逆向。据他分析,人化对动物性的否定采用了禁忌、禁止的文化形式,这一禁止运动从一开始就孕育了另一种逆向的侵犯运动:“所谓‘禁止’,并不是不做被禁之事,并不是完全放弃。一方面使之服从‘限制’,为之确立规范,另一方面又以打破这些限制与规范的样式进行。所谓的‘禁止’同时又敢于打破禁止,侵犯禁止之事。而一度被拒斥、被疏远的部分由于‘被禁’这种感情还被附加了不可思议的魅惑力,并作为更能唤起欲望的事物被召唤回来。这已不是单纯被嫌恶的动物性了。一方面感到这是‘动物性’,嫌恶之情依然如故;但同时又作为‘带有某种圣性的事物’被接受下来。可以说,这是一种‘圣性的’动物性。”③侵犯运动的对象是被否定的动物性,是对否定的再否定。此种基于双重否定运动的圣性的动物性其实又是文化的产物。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巴塔耶分析,无论人化,还是人化的逆向,均是人的顽强的自由意志之外化;而圣性之为圣性,还在于人化之人对内在于逆向运动中的自由意志——不想依存于任何事物——没有知觉。由此看来,亚当和夏娃的人化之旅并不是回归天堂之旅,④而巴塔耶所指认的逆向侵犯运动才是可能的回归之路。这条可能的回归之路导向的虽不就是失落的天堂,至少比纯粹的人化之旅离天堂要近得多。也就是说,巴塔耶所谓的圣性比起理性化的基督教,其实更贴近理性化的基督教也同样渴念的天堂。⑤
问题在于,人化具体指什么?对人化的超越,亦即圣性的动物性如何达至?
在巴塔耶的分析中,人化大致就是人的理性辛劳,是人有计划、有目的的世俗劳作,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禁忌、秩序、规范、法等,它们所针对的正是动物性的茫然无为和混乱无序。在原始时代,对世俗劳作的超越以祝祭、献牲中的滥费实现,在后来的时代,大约只能以近似滥费的奢侈相模拟。相较而言,后来时代对禁忌的违反比原始时代更频繁,也更公开,比如本文将涉及的同性恋。不过,无论是违禁还是滥费,都被认为是圣王的权力,是超越人化的圣性企图。
圣王的权力
关于滥费,巴塔耶由对原始宗教性运动的祝祭、献牲的分析引申出来。
据他分析,原始的“宗教性”运动是一种意欲否定“以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世界”的逆向运动,以生产活动为中心的世界是理性辛劳的人化世界,因此,此逆向运动就是人化的逆向。原始的祝祭、献牲作为“非生产性”的滥费,亦即作为非功利性的“纯粹赠予”打开了“圣性事物”的维度。所以,此种非生产性的滥费不仅仅与经济、经济学领域相关联,还与对“谋划”、“功利”进而对“理性”这类问题的重新追问相关联。具体说来,这就表现为人性的人对理性的超越,对谋划、功利的唾弃。
具体而言,“祝祭”就是以滥费的形式突然要否定使“俗事物世界”得以成立、持续的规约,突然中断进行劳作、合理化行动时不可缺少的谨慎、保留的行为方式;欲从有效掌控的规律化的行为模式中脱离出来,力图导入平时所讨厌的、欲避开的混乱和无为,把积无数辛劳生产的物品(如畜牧成果羊、农耕收获稻等)以“白费”的方式作为“祭品”消费掉,这就是滥费,其集约化的形态即是“献牲”(sacrifice)。⑥换句话说,原始的宗教性运动以庄严隆重的仪式实际上掩盖着一个奢侈、狂欢、颠覆的“大阴谋”,这里奢侈本身就是颠覆,是对谋划和劳作的否定以及对秩序的轻视。而滥费的极致——消尽,比如献牲中的死亡,就是对俗性的彻底否定了。
所以,“纯粹赠予”的维度实际上映照出了人的隐秘的愿望……在心灵的极深处,人期望着(明知不可能而又欲望着)将自己理性劳作创造出来的所有物品终究毫无保留的消尽,亦即“纯粹赠予”这一维度把人类无论如何欲超越“有用性”的循环,超越实在性与庄重性,从而达至虚空、轻狂的纯粹“非功利”辉煌这一终极的,却不可能到达的目的奇迹般地开示出来……尽管只能在那一瞬间。⑦因此,祝祭、献牲就是以滥费、消尽的方式对俗事物世界的断决否定,是比违反个别的禁忌更全面的违反,是更深入地回归圣性动物性。与此同时,也使物由从属于有用性的俗事物世界归于其本来的灵性存在样态之隐秘世界。也就是说,物摆脱人所赋予的物性,成为圣性的物自己。
依据前面对圣性的分析,滥费的内在动机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滥费之为圣性行为也在于人对此种自律的不自觉;不过,虽然不自觉,但人化的人对人化赋予滥费的狂欢式魅力,又深感迷恋。这是原始宗教性运动的祝祭、献牲,在后来的时代,祝祭所指向的超越性就仅仅保留为圣王的特权,再后来,大抵只有以奢侈的形式对圣王权力的模拟了。而王尔德的奢侈,如果联系到他后来的消尽式的自毁,就很可以看作是一种滥费的形式。
当然,王尔德的受审其直接起因是他的“性倒错”行为:他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对同性恋的暗示以及在生活中对道格拉斯勋爵“错位”的爱。这种性倒错在王尔德时代显然是对性禁忌的违反。
对于违禁色情,巴塔耶在《色情史》中有专门的讨论。他认为,原始人类把动物性的“性”(性倒错是自发的动物性的性之一种)视为使自己依从于自然所赐的粗蛮之力,视为使自己服从于本能图式的狂暴之力而嫌恶、畏惧之——把动物性“欲求”之贪婪,不能不即刻快乐作为“兽性”拒绝之;同时把与动物不同的满足方式作为人化的差异遵从之……通过拒斥动物性的方式创造出人性。正如前面提到,“不想依存于任何事物”就是原始人类对于动物性抱有嫌恶与恐惧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追求自律、自主,拒绝他律。由此建立起规约人的性行为的禁忌与法,而禁忌与法正是嫌恶、恐惧这种心里上的抵抗、情念性的约束在人化的生存中的显像。
但是,对动物性“欲求”的拒绝而确立的人化之禁忌、法,随后又变成人的第二自然,人在对第二自然的遵从中重又感到已被超越的他律,从而萌生出对禁忌、法的侵犯,其内在动机仍然是不被觉知的自律意志。对被摈弃的动物性欲求的接近,显然并不能真正回到原初的动物性,却也不要求原初的动物性,而是在这种接近中体会违禁的圣性情感,从而赋予自己的违禁色情一种文化意味的圣性价值;同时这被诅咒的违禁色情,由于被诅咒的感情而拥有了某种奇妙莫名、令人眩晕的魅惑力。⑧也就是说,与滥费相似(不导向生育的违禁色情也是一种滥费),对违禁色情的迷恋,除了内里的自律意志外,还有文化所赋予的魅惑。这是具有圣性倾向的天性难以抗拒的。因此,王尔德就不仅在作品里,还在生活中去求取这样的违禁色情了。而正是这个违禁色情,将他引向了滥费的极致——自毁之路。
所以,王尔德的受审表面看来是因为同性恋,而在内里,这不过是他对世俗价值的怀疑与挑衅,对人化的戏弄与厌弃。因而,尽管后来有机会逃避世俗之法的制裁,他还是选择了自毁、成圣。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圣王的权力,违禁和滥费可以相互阐释。因此我们将看到,王尔德的违禁色情和他的滥费是交织在一起的。
奢侈与滥费
王尔德讲究享乐、追逐极乐。实际上唯美主义者们都是迷醉于享乐的,比如于斯曼。于斯曼的《逆向》在王尔德接受卡森讯问时被问及,并引述了《道连·格雷的画像》中提到的此书对道连道德堕落的影响:读着此书,“他觉得,仿佛全世界的罪恶都穿上了精美的衣服,在柔和的笛声伴奏下默默地从他面前一一走过。……这本没有故事的小说仅有的人物——巴黎一青年——以毕生的精力试图在十九世纪再现过去各个时代的一切欲念和思潮,从而集世界精神所经历的种种情绪于一身。他既能玩味被人们荒唐地称作德行、实为矫情的自我克制,同样也能欣赏被贤哲们称作罪恶的天性反抗。……感观生活是用神秘哲学的术语加以描写的。读者有时摸不透,他看到的是一位中世纪圣者精神上的极乐境界的缕述呢,还是一个当代罪人病态的自供状。”⑨道连受其影响,感觉那个身上奇特地糅合着幻想家和学者气质的巴黎青年是他自己的原型。他也要经历各个时代的一切欲念和思潮,以锤炼集世界精神所经历的种种情绪于一身的独特个性。他怎么经历的?
接下来王尔德用了整整一章津津乐道道连对各种享乐奢华的品玩:他的宴会的排场;各种香精及其制作的秘密,各种芳香对感官的不同刺激以及这些不同的刺激所对应的不同情绪状态;各种不同个性的音乐,各具风格的音乐会,各种古怪的乐器它们奇怪的演奏方式以及各自特别的音色;形形色色的珠宝它们变化多端的迷人色彩,各自独特的奇闻秘史,传说中和历史中高贵者那些名贵珠宝夸耀式的气派;各种最珍奇的绣品和壁挂它们精美的做工以及富丽堂皇的构图;各种华美的法衣等等。
读读王尔德对珠宝的铺陈:
“……他(道连)曾像法国的海军将领安·德若耶斯那样穿了一件缀有五百六十颗珍珠的衣服参加一次化妆舞会。……他常常玩弄收藏在首饰匣里的各种宝石,搬来搬去,理了又理。其中有金绿宝石,它的橄榄绿颜色在灯光下会转成红色;有镶着银色纹理的乳光宝石、淡黄中微泛绿色的橄榄石、玫瑰红和醇酒色的黄玉;有鲜艳夺目的红玉,其中闪烁可见一颗颗四角的星星;有红得火辣辣的钙铝榴石、桔黄色和淡紫色的尖晶石;有红蓝闪烁的紫晶。他喜欢日长石的金红、月长石的珠白、蛋白石的虹晕。他从阿姆斯特丹物色到三颗大得出奇又晶莹可爱的绿柱玉,还有一颗采自古老岩层的绿松石,是行家无不啧啧称羡的极品。”⑩
这种烦琐无比的缕述与道连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风格,以及王尔德那种细腻而奢华的生活趣味倒是很相宜。实际上,上面引文所出的这一章可以说最能代表王尔德唯美主义生活的理想和唯美主义创作的格调,值得细细玩味。他如此忘情于那些流光溢彩美轮美奂的滥费:放纵感官的生活遗忘了物的有用性,深深沉醉于物自身的灵性、自身的美之中;流连于对物的无穷无尽的细节的触知、感受与抚爱,还物以物自身内在的终极性。这正是巴塔耶揭示的圣性的极限体验。超脱出俗事物世界功利性循环的人在那一刻接近了迷离的动物性,体会着无以言表的忘我的无力与慵懒。而且据巴塔耶分析,此种经验与基督教神秘家们的经验极为相似,只是途径不同:与所谓的行动、工作或生产活动正相反,神秘家们通过修行,冥想等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要拥有什么”,而是通过“消除”自己的力和能量的运动,打破“自我”的外壳,经历着“出离到自我之外”似的经验。实际上可以认为,“十字架上的信徒约翰”以及“阿维拉的圣特雷萨们”,必定达到了极其强烈的“失魂”状态,脱自体状态(忘我)。(11)其实,严格的禁欲主义和彻底的放纵欲望一样,都是感官体验的极致,是对俗事物世界理性规约的否定:前者以消解自我的方式忘记自我,后者借助客体忘记自我。这就是中世纪圣者与当代(王尔德时代)罪人内在精神的深刻一致。
王尔德自己有一段针对这种生活的算不上反思的评议,很可以说明所谓的罪恶与圣性的两面性关系:“关于他(道连)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离奇的流言蜚语,已传遍整个伦敦,成了俱乐部里议论不休的话题。但即使那些听到过极端不利于他的坏话的人,只要一看见他,就无法相信任何有损他的名誉的事情。他始终像个身居浊世而纤尘不染的人。人们本来在谈论秽闻亵事,道连一进来,立即鸦雀无声。他的纯洁无邪的面容有一种使人感到内疚的力量。只要他在场,人们就会慨叹他们也曾是无暇的白璧,但被自己糟蹋了。”(12)如果说道连体现的圣与罪的依存因为“画像”的介入还比较勉强,那么,《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中的这段话就无可怀疑了:“……这一头金发使她(温德米尔夫人)脸上显示出圣徒的形象,却也掩饰不了她罪人的魅力,确是心理学研究的奇妙对象。她年轻时就发现一条真理:最最与天真烂漫相似的莫过于放荡不羁了。”(13)王尔德以戏谑的方式暗示出他对违禁、滥费与圣性之关联的心领神会。
不过,对王尔德这样的唯美主义者而言,以“无所事事”的形式表现的滥费更有代表性。无所事事是比奢侈更具唯美性质的滥费,是古典式奢侈的现代形态,它与“有用”和“有效”这类信念根本对立。王尔德那篇《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的文章其副标题就是兼论无所事事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将一个流行的俗见“做一件事比说一件事更难”颠倒为“说一件事比做它要困难得多”。他说,“别,别提行动,它是一种受外界影响控制的盲目的事,被连自己也一无所知的冲动推动着前进。它是一种本质上有缺陷的事,因为受到偶然因素的限制,并且对自己的方向一无所知,总是和目标相左。它的基础是想像力上的匮缺。它是那些不知道该怎样梦的人的最后资源。”(14)这似乎是调侃,却满有深意:与做梦相比,人化的行动可以说贯穿了确定的逻辑和理性意志;行动的盲目在于外界以“偶然因素”这种方式介入揭示出的人类理性的有限。这种有限理性就是王尔德所谓的想像力的匮乏。梦的好处在于卸去了行动必须承担的有用性承诺,自由地满足人的任性狂想,满足人超越人化成为圣王的隐晦心理渴求。
就这样,王尔德凭借私秘的滥费与违禁色情自我放逐了。以离弃世人的方式领悟了这个世界之外和这种世界的自我之外的那些迷离恍惚、意味无穷的圣性生活。也就是说,他通过自我流放成了神圣的高贵者——圣王。当然,这还因为他不是只在创作中展示、玩味奢华,鉴赏罪恶,他还在同性恋生活中极尽奢华之能事:在一封写给道格拉斯的信中他提及金钱和炫富的消费在他们两个人共同的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他告诉道格拉斯,他在萨瓦旅馆的帐单是每周49英镑;而据爱德华·雪莱——王尔德为他的“希腊式的爱”(15)结交的一位社会地位不算太低的少年——自供,他有时一月仅靠4英镑几便士维生。(16)这之间的差距大概就是无益的滥费,虽然这种滥费也夹裹着世俗性的物欲迷醉。王尔德的《从深处》(17)一再抱怨道格拉斯浪费了他太多钱财与时间。这是他被迫接受监狱改造、经过理性炼狱洗礼后的“忏悔”之辞,我们可以不必理会。它其实向世人昭显了这位神圣之王在生活中对他们敬若神明的“有用性”的羞辱。
不仅如此,在王尔德,创作和生活几乎是连成一片的。甚至可以说,艺术本身就是他的滥费形式之一。按照巴塔耶的分析,“精神”又一次力图切断、打破对“世界”的依从,想以此而重建自己的“自律性”这种“逆向”运动,总体上看是理解圣性事物的显现——祝祭与献牲、色情以及文学艺术——的关键,是领会正相反的价值感情一面相互对立、一面又并存而形成一体化这一情状的关键。(18)也就是说,巴塔耶根本就将文艺划入了与献牲、色情一样的圣性领域。这其实也就说明,文艺本来就行走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上:虽然文艺也服务于俗事物世界理性内容,但它更应该关注超越俗性的领域。这与人化的人的悖论性处境完全相宜,但这里圣俗共在的前提同样是对动物性的接近内含着的自律性不被觉知。“逆向”运动一旦被理性的反思穿透,光晕就无迹可寻。这是实存更高阶的悖论。
这种意义上,王尔德就以一位神圣的王的姿势诠释了纯正的文学性。
自毁与成圣
然而,王尔德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不公开的神圣的王,他漫不经心地让那个社会了解了他的圣性,从而也使此事件所隐含的“艺术与神圣”这个问题彰显出来。
王尔德控告昆斯伯里侯爵诽谤罪这件事,对他个人和对文学艺术的确都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表面看来,王尔德是要以这个社会的理性之法,维护他假想的安身立命的名声:1895年2月28日,亦即《认真的重要》在伦敦首演成功后两周,他在阿尔玛特俱乐部收到昆斯伯里侯爵留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题有:“致奥斯卡·王尔德,装模作样的好男色者。”王尔德据此以诽谤的罪名把昆斯伯里侯爵送上了被告席。两年后,他异常痛心地承认,“我一生中最可耻、最无法原谅的事就是竟然不得不允许自己向社会求助,为的只是不受昆斯伯里侯爵的侵害。”
被告方要证实王尔德确系“好男色者”实在简单不过。4月初,经开庭审讯,昆斯伯里无罪开释,而王尔德反因有伤风化的行为被捕。经过两次审问,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根据1885年通过的一条针对男同性恋的刑法修正案判处王尔德两年徒刑。这次是世人离弃了他,是世俗世界对他的放逐,一次献牲式的放逐。这次放逐成全了王尔德的神圣之名——“臭名昭著的牛津圣奥斯卡,诗人,殉道者。”
看看明理的世人怎么看这件事:
王尔德在法庭上为自己与道格拉斯的关系作过一番表白,他力图表明,那是一种柏拉图式哲人与朝气蓬勃的年轻学生之间纯洁完美的感情,正是这种为俗世所不理解的高尚情操充溢于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字里行间(王尔德用想象笔法写过一篇讨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文章《W.H.先生的画像》,提到莎士比亚所爱的是一位年轻男性演员)。这种辨白,与其说感人,不如说可怜。王尔德缺乏真正的勇气来面对一条条查有实据的指控。他和道格拉斯之间感情上的依恋绝对不是“忠贞”一词所能形容的,在猎取男色方面他们是友好的对手和搭档。……在王尔德和为他提供性服务的年轻男子之间处处是卡莱尔所说的“货币关系”(王尔德还数度被敲诈大笔款项)。……王尔德的这些行止到头来只是使得他的辩解乃至他一贯标榜的至高无上的美更显滑稽。
当然,类似的恶行在伦敦上流社会甚至内阁要员中绝非罕见。要说当时的社会是在一种伪善的道德观驱使下像猛虎扑食般抓住一位艺术家的过失不放则有失公允了。当王尔德的真相逐渐暴露后,物议沸腾。有关方面不得不予以追查,不然法官就要承担掩盖丑闻(该案还涉及当时首相罗斯伯里伯爵)的法律责任。(19)
从一个认同俗事物世界法规的人的视角,此番评议显得务实而且还很有保留:他们首先确认同性恋是“恶行”,为此破费纯属“货币关系”,谈不上有什么情感或者别的什么不同于货币的价值。讽刺的是:货币关系本就是功利社会的尺度,人们却要将所谓情感假惺惺地排出在外。既将情感排出在外,却又要情感服从某种根本上与货币关系之本质相一致的秩序。这是世人顽固的理性情结。
这里还暗示,社会也许对艺术家是仁慈的,只不过因为要首先考虑社会地位在艺术家之上的政界要员和法官本人的利益,艺术家就不得不扮演替罪羊的可悲角色了。看看这里,理性社会的逻辑有多混乱:似乎艺术家可以有某种不一样的、这个社会秩序逻辑之外的特权,但又有一个按照社会等级序列来分配的特权。艺术家的特权遭遇这个特权的等级序列就失效了——艺术家是个令理性社会头疼的难题。这都因为艺术在圣与俗之间的“尴尬”。
王尔德就这样被以明晰性为理想的社会以不明不白的逻辑,明明白白地宣判为罪人,不仅以法律的名义而且凭着人们的习见。但这场官司的本质是什么呢?王尔德遭遇了什么?他当然缺乏真正的勇气来面对一条条查有实据的指控,他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生活。但这只能说明艺术家也活在俗事物世界,活在世人中间。然而那不是艺术和艺术家生活的全部,根本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可人们却要以谨严的节制和明晰的秩序干干净净地抹消圣性。
实际上,王尔德走上法庭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必须接受这种世俗的逻辑,他的败诉当然是注定的。在明确分断的世界不能明确地命名的事物不使人放心,暧昧就意味着罪恶。说得更直接,触及圣性就意味着可能犯罪。人们实际上以赋予理性对非理性的无上权利成全了王尔德的神圣性,当然也是王尔德自己将自己送上理性的断头台的,他要祭祀的是文学性,是文学的圣性价值。从对某些禁忌的违犯到全面对抗这个社会的根本逻辑,从秘密的违反到公然的挑衅,他以“自毁”为圣性的祭坛纳上无价的新贡:从控告、被控、受审到判刑,整个一出文学式的模拟献牲的戏剧。这是最华丽的献牲,是对俗性的根本否定。因为献牲是奢华的极致,它滥费掉昂贵无比的生命。死亡禁忌是保守的坚持,是一个人化的理想:对死亡禁忌的违犯在令人难以忍受的黑暗与虚空中渴求着极度的奢华——以将祭品纯粹赠予的方式,在消尽的瞬间,破除俗事物世界的谋划之运营,以无法完成之形态悬搁于无边的虚空和黑暗中。王尔德模态式的献牲“朝向死的虚拟式的接近”与献牲中的死一样,是一种发生于人内在精神中的深刻的消尽。被分裂开来的俗事物世界的王尔德目睹了神圣的王尔德的“死”。自那以后,神圣的王尔德的确死去了,只剩下一个没有神韵的形式的王尔德。
在世人看来,王尔德“献牲”主动机是一个难以破解之谜:“为什么王尔德要打一场打不赢的官司以致引火烧身?为什么他要用遭他激烈批评的道德价值为最终诉求来证明他根本不存在的清白?也许王尔德太糊涂,也许一直就反抗父亲权威的道格拉斯在旁积极怂恿。不过王尔德一种微妙复杂的心理不能忽视。他幼年时就渴望在‘女王诉讼王尔德’的官司中出场,他隐隐有一种自毁的冲动。”(20)说王尔德糊涂显然不通。艺术家虽然对无形有天然的亲近,他对形式也有强烈的敏感,而形式能力足可以保证俗世的安全。至于道格拉斯对王尔德行动的影响,此说也很牵强。王尔德并不热衷于世俗权利,无论是反对还是获取之。他对俗世的反抗并不从对权利的反抗进入。他那比较软弱又迷醉于享乐的性格更习惯于消极的方式。自毁是他行动的深层的心理动因,虽然习见以世俗的有用性尺度为其赋予了否定的价值情感。
那时,王尔德就是饰满鲜花走上祭坛的神圣之王,这自毁,这庄严而奢华的“献牲”仪式,是他文学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他以创作、以生活、以生命,精彩地诠释了文艺的神圣价值。
[收稿日期]2007-12-29
注释:
①Hegel,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one volume edition) ed.,P.C.Hodgson,trans.R.F.Brown,et al.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14.
②巴塔耶对“圣性”的分析,主要参考了[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对巴塔耶思想的介绍。特此说明并致谢。另参考[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法]乔治·巴塔耶,《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论文选》,汪民安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③参阅[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87页。
④基督徒将其一生设想为寻找伊甸园的过程,他们试图有所作为,以便将来有资格重返家园。这是中世纪理性化的基督教的救赎方式。事实上,即使在笃信理性救赎的中世纪,寻找“信仰”与“善工”之间的平衡也是人们反复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动物性与人化,非理性与理性在救赎中的作为。而且,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改革。参阅[英]G.R.埃文斯,《中世纪的信仰》,茆卫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2页及其它。
⑤关于此问题,俄国思想家舍斯托夫也认为,以理性路径接近神圣不过是南辕北辙。他指出,雅典对耶路撒冷的改造使犹太—基督教丧失了非理性维度,上帝的理性取代了上帝全能的意志。他试图恢复这一非理性之维。而巴塔耶的不同在于,他定义的圣性超越了理性但又囊括了理性。参阅[俄]列夫·舍斯托夫,《雅典与耶路撒冷》,张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另外,关于上帝的理性和上帝的全能意志的讨论可以说在中世纪从未完全停止过。在早期,希波的奥古斯丁对“原罪说”的完善就涉及信仰与善工问题;而后期,奥卡姆的威廉的革命性神学就给予了上帝全能的意志以绝对的优先权,其效果同样是对被忽视的非理性之维的强调。而且,奥卡姆的神学对路德的宗教改革起了关键的作用。See Markc.Taylor,Confidence Games:Money and Markets in a World Without Re demp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pp.80-82.
⑥参阅[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75页。
⑦参阅[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13页。
⑧参阅[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71页。
⑨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134页。
⑩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144页。
(11)参阅[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六部分:《色情的组成形式》,Ⅲ:《神圣的爱》。
(12)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136-137页。
(13)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243页。
(14)[英]奥斯卡·王尔德,《谎言的衰落》,萧易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第115-116页。
(15)王尔德以“希腊式的爱”为自己的同性恋行为辩护。他认为,米开朗琪罗和莎士比亚的伟大艺术就贯透了这种完美的精神之爱。See Anne Varty,A Preface to Oscar Wilde,Be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p.28-29.英国文学名家导读丛书影印本。但是严格说来,“希腊式的爱”在古希腊并无圣性之美,因为希腊社会并未视此为违禁。See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 tran.,Robert Hurle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90.
(16)参阅孙宜学编译,《审判王尔德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99页。
(17)参阅[英]王尔德,《王尔德狱中记》,孙宜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一、狱中记。
(18)[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89-190页。
(19)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9-10页。
(20)赵武平主编,《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荣如德、巴金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