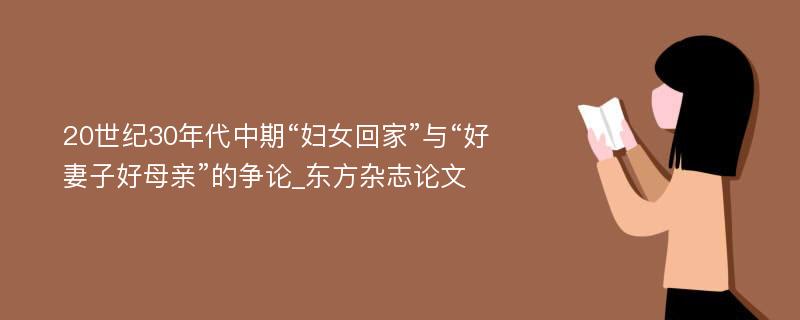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贤妻良母论文,妇女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不论在男女之间还是在男女内部,对于女性与家庭、社会关系的看法都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迄今学界对此次论争虽有涉及(注:涉及这次论争的论著,主要有臧健:《妇女职业角色冲突的历史回顾——关于“妇女回家”的三次论争》,《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岳庆平:《家庭变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5页;陈功:《家庭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78页;欧阳和霞:《回顾中国现代历史上“妇女回家”的四次争论》,《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15卷第3期,2003年6月。),但缺乏具体细致的考察。本文现根据学术界尚少利用的一批史料,侧重于考察论争发生的背景及两性观点的歧异,希望能藉此增进认识,进而引起关于此问题的再思考。
一、论争的发生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活动的范围被局限在家庭。儒家文化素重家庭,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必先齐家,家齐而后国治。而齐家的关键则在于家庭里的女性做“贤妻”与“良母”。但把“贤妻”与“良母”联系起来,形成“贤妻良母”这一特定概念,实际上是近代以后的事。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创办女子教育的热潮,日本的“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思想随着学习日本的潮流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女性标准“贤妻”、“良母”一拍即合。1905年前后,中国人在讲演、文章中开始使用“贤妻良母”或“贤妻良母主义”的词汇。(注:参见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李卓《中国的贤妻良母观及其与日本良妻贤母观的比较》,《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一般来说,贤妻良母代表一种妇女形象,贤妻良母主义代表一种思想。
关于贤妻良母问题的讨论自晚清已开始。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严重。甲午战败后,更加面临亡国的危险。贤妻良母这一口号刚在社会上流行,便遭到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1909年,《女报》上刊登的《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一文指出,贤母良妻“实则男子之高等奴隶耳”,呼吁女学界“勿以贤母良妻为主义,当以女英雄女豪杰为目的”(注: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83-484页。)。以秋瑾为代表的一部分先觉知识女性挣脱家庭的牢笼走到社会上,她们振兴女学、创办报刊、组建女性团体、办实业、投身反清革命、争取男女平权,使女界呈现一派活跃气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反对一切旧道德、旧观念、旧信仰,倡导人格独立,男女平等。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离家出走的娜拉,成为知识女性崇拜的偶像。极端者甚至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正式给贤妻良母主义宣布了死刑(注:一丁:《贤妻良母主义的复活》,《北平新报》副刊《妇女》第52期,1936年9月10日。引自《从“一二·九”运动看女性的人生价值》,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版,第256页。)。一大批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冲出家庭投身到争取个性解放的社会活动中。
关于妇女回家的讨论发端于30年代中期,同时伴随着对贤妻良母问题的争辩。
自1929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德国,希特勒执政后,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男子失业恐慌问题,腾出更多的就业位置给男性,大声疾呼“妇女回到家庭去”、“妇女的天职在教养子女”(注:《希特勒演说妇女天职在教养》,1934年9月11日《申报》。)。这种声浪弥漫到世界上很多国家。而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却高喊妇女“从家庭里走出来”,鼓励妇女参加社会工作。苏联广大妇女离开家庭,与男子一样在各种生产部门工作。源于德国与苏联的这两种思潮冲流到中国之后,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也分成为两大营垒:“有的请妇女们还是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去罢,用不着向社会里跑了,有的却以为这是落伍,开倒车,不合乎时代的要求”(注:丁昌文:《从妇女生活改进组织到家庭新生活化》,《新运月刊》第37期,1936年9月15日。)。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起了一场“重新估定人生价值”(注:蒋宋美龄:《新生活与妇女》,《妇女新生活月刊》第1期,1936年11月。)的新生活运动,以复兴固有道德文化,提倡礼义廉耻为核心。随着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社会上复古思想高唱入云。时人评论:“妇女回到家庭里去,三从四德也抬头了!新生活运动竟被人误解作复古运动,竟被人用做压迫妇女的工具,未免太可惜了!”(注:远宜:《敬告误解新生活运动者》,《妇女月报》第1卷期第7期,1935年8月1日。)《妇女共鸣》编辑、国民党员李峙山替女性鸣不平,她认为:提倡礼义廉耻的新运,“足以助长复古的心理”,一切压迫妇女的势力,日渐伸张。更加上希特勒的妇女须回到家庭,回到厨房,回到摇篮的主张等,无不表示妇女今日环境的恶劣!凡我清醒的妇女,谁不愤慨填胸?谁不图谋反抗?(注:峙山:《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之感想》,《妇女共鸣》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升级,威胁整个中国的生存。在国家民族的生死关头,救国呼声日益高涨。进步的知识女性坚决反对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的论调,号召妇女大众离开家庭的奴隶生活,从事抗敌救亡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族的独立生存。上海妇女救国会理事及《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驳斥:“什么‘妇女回家’,‘贤妻良母’,只是法西斯蒂麻醉妇女愚弄妇女的毒药,没有拿来医治半殖民危症的必要”。“我们知道贤妻良母教育施行的结果,必然地会养成无数驯服的羔羊”。“我们要救亡图存,需要的是救亡教育。我们应教育出一大批猛虎似的战士,决不需要任人宰割的羔羊”。(注:兹《新妻母学校》,《妇女生活》第2卷第5期,1936年5月16日。)也有女性提出一种折衷的观点,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在大谈“妇女还是回返家庭,还是跑进社会呢?”主张前者的人,极力喊着女子回到家庭去,主张后者的人,极力呼喊女子跑进社会去。其实主张女子应绝对留在家中和主张妇女应绝对跑进社会者都太偏,太走极端(注:志敏:《再论新贤妻良母》,1935年9月4日《中央日报》。)。
这场关于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问题的讨论,从1933年开始,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才暂时平息(注:1939年到1940年代初期,随着各机关借故禁用女职员,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再兴。详情另文论述。)。参与者包括文化界、教育界、妇女界甚至政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政治身份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救国会成员等,论辩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央日报》、《申报》副刊《妇女专刊》、《妇女生活》、《女声》、《妇女共鸣》、《妇女月报》、《新运月刊》、《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由于议论纷纭,头绪不一,笔者拟将两性的主张分别予以梳理,以便为了解这场论争提供一个基本线索。
二、男性的言论
男性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认为操持家务、教养子女是妇女应尽的天职。1935年3月,《国闻周报》上刊登了一篇李赋京撰写的《无论如何女子总是女子》,作者明显带有性别偏见,认为“女子总是女子”,“女子养育孩子,就是为社会服务尽责任,其他的都是次一等的”(注:李赋京:《无论如何女子总是女子》,《国闻周报》第12卷第9期,1935年3月11日。)。1936年2月,林语堂在接受《申报》副刊《妇女专刊》记者访问时说:“一个女人,必须做贤妻良母。”“好出风头的女性,都是坏蛋!大凡优良的女性,不喜出风头的,只是在家里不声不响的教养子女,尽她天赋的使命。新贤妻良母,是多么高贵的天职?”(注:寄萍:《幽默大师林语堂夫妇访问记》(下),《申报》副刊《妇女专刊》第6期,1936年2月22日。)可见,林语堂强调母职的重要性,不赞同女性的解放必须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工作。老舍也认为婚姻问题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唱高调。1936年9月,他发表《婆婆话》一文,谈到男人娶妻的标准:“一个会操持家务的太太实在是必要的。假如说吧,你娶了一位哲学博士,长得也顶美,可是一进厨房便觉恶心,夜里和你讨论康德的哲学,力主生育节制,即使有了小孩也不会抱着,你怎办?听我的话,要娶,就娶个能作贤妻良母的。尽管大家高喊打倒贤妻良母主义,你的快乐你知道。这并不完全是自私,因为一位不希望作贤妻良母的满可以不嫁而专为社会服务呀。假如一位反抗贤妻良母的而又偏偏去嫁人,嫁了人又连自己的袜子都不会或不肯洗,那才是自私呢。不想结婚,好,什么主义也可以喊;既要结婚,须承认这是个实际问题,不必弄玄虚。”(注:《老舍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1页。)
(二)认为家齐而后国治,服务家庭间接的也是为社会服务。《申报》编辑周瘦鹃认为:“妇女们的出处,还须采用折衷办法,就是社会和国家有事时,便当挺身而出,为社会为国家直接服务,社会和国家没事时,那么不妨退守在家庭中,做伊们的贤妻良母……古人有言,治国必须齐家,家齐而后国治,这话实在是不错的。为家庭服务,其重要性正不在为社会为国家服务之下……妇女们离不了家庭,家庭中实在需要一位贤妻良母。”(注:周瘦鹃:《发刊辞》,《申报》副刊《妇女专刊》第1期,1936年1月11日。)1936年3月,上海市长吴铁城发表演说,认为妇女做贤妻良母能使民族复兴。他说:“我以为对于贤妻良母的解释,仅仅为家庭,这是太狭义了,要知道妇女解放的目的,为达到男女平权,要求民族的复兴。而民族复兴如何会成功呢?必要养成许多的贤妻良母,对象不仅是家庭,我们要广义的解释,譬如战国时的孟母教子,宋朝的岳母教子,并不仅限于家庭,要推广到整个民族的复兴,妇女本身的责任,就是贤妻良母,最好大家要模仿岳飞和孟子的母亲,来训导我们的小国民,从前的贤妻良母很少,现在我希望全国妇女,都要变成贤妻良母,那末国家能复兴,民族能生存。(注:《女青年会所昨行迁移典礼》,《申报》1936年3月8日。)1936年7月,有人明确提出妇女回到家庭去做现代贤妻良母。他说:“今天我们要喊出妇女回到家庭去,作一个现代‘贤妻良母’,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男女真正的平等。因回到家庭,与走入社会,是同样重大。能在家庭劳动服务,同样是等于为国家社会服务,能够把自身,自家,子女都健强起来,便可以把国家民族健强起来。”(注:张肇辉:《新生活运动与妇女解放——从贤妻良母说到劳动服务》,《新运月刊》第35期,1936年7月15日。)
(三)看不惯都市里浪漫摩登的女子,以为借贤妻良母的教育才能把女性的生活纳入正轨。1935年9月,署名“何子恒”的题为《中国女子教育问题之商榷》的文章指出:都市知识妇女生活“骄奢淫逸,靡丽纷华”,“除消费外,无所事事”。至于“家庭之如何管理,子女之如何教养”,则“往往毫不措意,悉以委之仆佣保姆之手”。作者指责这是“女子教育错误之结果”。他推崇日本的贤妻良母教育,认为“女子之将来,无论学问知识若何,结果不过生儿育女”,又“何必立极大之志愿,从事于某种专门科学之研究”?(注:何子恒:《中国女子教育问题之商榷》,上海《晨报》《星期评论》1935年9月8日。引自《从“一二·九”运动看女性的人生价值》,第224页。)一些地方当局重申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方针。1935年6月,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提出“今后女子教育方针,趋重贤妻良母,陶养安定家庭社会”(注:《鲁何教厅长谈贤妻良母为女教方针》,《申报》1935年6月6日。)。1936年4月,以“复古之声”闻名全国的广东省当局鉴于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禁令难以推行,认定“妇德之失修,实缘妇女们的缺乏贤妻良母教育”(注:兹《新妻母学校》,《妇女生活》第2卷第5期,1936年5月16日。),故实行提倡贤妻良母运动,指派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人赴日本考察贤妻良母教育。(注:《广州重视“贤妻良母”教育》,《申报》1936年4月22日;《提倡贤妻良母》,《女铎》第25卷第2期,1936年7月。)
总的来看,上述各种言论虽有不同的出发点,但有一个主张是一致的,即注重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希望每一位妇女都做贤妻良母。
不过,也有男性提出质疑。比如,1935年7月章锡琛在《妇女的分工》一文中批评:“大多数的人,虽然承认了男子的应该分工,而对于妇女,却仍然抱着古老的意见,以为她们只许专门去任游猎时代以来的一样的工作,——就是家庭的工作。虽然在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的妇女做着和男子一样各种不同的职业,但在他们看来,这是社会的变态,这样下去,是会得使民族衰颓或灭亡的。因为妇女的最重大的任务,是‘做母亲’,除了家庭的职务以外其他一切的职业,都和‘做母亲’的任务有妨碍。近来‘回到家庭去’的呼声,便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但是,所有的妇女,是不是全都适宜于养育儿童?……还是只要选择出最适宜的一部分去做就够?”(注:章锡琛:《妇女的分工》,《妇女生活》第1卷第1期,1935年7月1日。)
还有人呼吁不能单求女子做贤妻良母,男子也有必要做贤夫良父(注:蜀龙:《新贤良主义的基本概念》,《妇女共鸣》第4卷第12期,1935年11月20日。)。1936年2月,国民党员柳亚子撰文指出:“关于妇女问题,近来是分成两大营垒的了。一方面,说男性是人类,女性也是人类,所以男女应该不分性别,以人类的资格为全人类而努力。另一方面,却要叫妇女回到厨房里面去……而美其名曰贤母良妻论,或者是新贤母良妻论了。这二者中间,我是赞成前一个主张的。贤母良妻当然好听,谁会主张妇女应该做不贤良的母妻呢?不过,照同样的比例来讲,男子应该做贤父良夫……既然没有听见人家在提倡贤父良夫,那末提倡贤母良妻总也是多余的了。”(注:柳亚子:《关于妇女问题的我见》,《申报》副刊《妇女专刊》第1期,1936年1月11日。)1937年1月,郭沫若在《妇女生活》上发表《旋乾转坤论——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提出“我提倡贤夫良父,当然我也并不要求愚妻恶母,反而以人格为本位的真正的贤妻良母,我是极端地渴仰着的。妻而求其贤,母而求其良,也和夫而求其贤,父而求其良的一样,是应当的事体。”(注:郭沫若:《旋乾转坤论——由贤妻良母说到贤夫良父》,《妇女生活》第4卷第1期,1937年1月16日。)柳亚子、郭沫若等人的看法,在当时是较为理性和前瞻的。
三、女性的言论
女性的观点,很明显地可分为下列三种。
(一)反对贤妻良母论,主张服务社会比管理家庭重要,特别是在中华民族危机四伏的关头,妇女更应当参与救亡运动。1935年3月,有女性指出:“最近间,在封建旧礼教所造成之下的贤妻良母论,也给人提倡了……我们应该振作起精神来,扫除一切的封建臭味,反对贤妻良母的主张,我们要跑到社会去做生产事业,不要在家里做厨师和保姆,摆脱数千年来所压迫的铁锁。”(注:华:《谈谈贤妻良母》,《妇女月报》第1卷第1、2期合刊,1935年3月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理事罗琼(注:罗琼(1911-),江苏江阴人。1932年毕业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35年参加上海《妇女生活》杂志的编写工作,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理事。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调中共中央妇委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妇联常委、宣传部长、副主席。)认为“所谓贤妻良母,就是封建社会奴役妇女的美名”。她表示:“我们承认妇女应该为妻为母,但是我们觉得妇女还有更重要的‘天职’,这就是参加社会生产工作,进而促成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改革,假使背着妻母这块招牌,而用贤良的美名,想把妇女骗回家庭中去过她们的奴隶生活,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注:罗琼:《从“贤妻良母”到“贤夫良父”》,《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我们要想独立生存,为祖国服务,那么第一步就不得不找职业,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注:罗琼:《怎样走出家庭?走不出又怎样?》,《妇女生活》第4卷第7期,1937年4月16日。)《妇女生活》的特约撰稿者碧遥提出“设法使母性爱减少”。她说:“一向女性是家庭的附属物,她因经济的,环境的,事业的种种关系,将母性爱看得过分严重。人类固然不能违反育儿的本能,但最重要的是人类应该是社会的动物;人类对儿女的爱万不能超过他对社会的爱”。“男女要平等,不仅是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等要平等,而最重要的是工作也得平等。假使女性不努力于社会工作,那还不是寄生虫?还不是育儿的机器?我们走出家来原是争做自由平等的人”。(注:《娜拉座谈》,《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1936年9月,中共党员陈修良(注:陈修良(1907-1996),浙江宁波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秘书。1927年赴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主编,南京市委书记。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部长。)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署名“莫湮”的《中国妇女到哪里去》一文,指出:在中国民族危机四伏的时代,在人口上占着半数的妇女,更应当坚决地起来负荷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责任。“现在如果再主张妇女回到家庭去,不但主观上是忽视了妇女大众在救亡运动中伟大的作用,而且客观上也阻止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所以这是最不合于现实要求的一种主张”。(注:莫湮:《中国妇女到哪里去》,《东方杂志》第33卷第17号,1936年9月1日。)
(二)反对单做贤妻良母,主张服务社会与管理家庭并重。一些女性认为现代妇女负有对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真正有才学、肯进取的女子在家庭里也必是贤妻良母,决不因社会的职务而放弃子女的教养与家务的处理。
国民党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傅岩在《妇女的新生活》中指出:“妇女是家庭的主角,家务的处理,与儿童的教养,都是母性主要的任务,所以妇女在家庭内应当做一个贤妻良母。但妇女同时亦是社会一份子,对社会活动,妇女不仅有参加的权利,同时也是她们的义务。”她批评:“有些提倡贤妻良母主义,认为妇女要做贤妻良母,应当放弃家庭范围外的活动。这是无异说,社会事业应当让男子去活动,岂不是将妇女权利与义务,剥削了大部分,这是不正确的观念。”(注:傅岩:《妇女的新生活》,南京正中书局1935年版,第48-49页。)1936年2月,妇女专刊记者特地访问从事多年家政教育的黄寄马女士,黄女士对于妇女服务的看法是:“现代妇女,只是在家做主妇,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做有利于大众的社会事业,未免太狭隘,反之只为社会服务,而鄙弃了家政,也不是家庭的幸福。其实不应当把家庭服务和社会服务看得有显然的区别,这两方面,应该打成一片,因为社会服务,可说是间接替别人的家庭服务;而家庭服务,是直接为自己的家庭服务;所以我主张一个妇女要认定在家庭服务中,同时干社会服务的事业。”(注:寄萍:《邰霜秋夫人黄寄马女士谈家政教育》,《申报》副刊《妇女专刊》第4期,1936年2月8日。)1937年3月,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总干事王敏仪在《纪念“三八”节》中明确指出:“我们不反对贤妻良母的主义,同时我们并赞成提倡全国全世界的男子都成为贤夫良父。要知道贤妻良母不过是妇女一部分的责任,绝对不是妇女唯一的天职。我们所赞成的是以人格为本位的贤妻良母主义,决不是‘三从四德”重男轻女’的盲从主义。”针对人们常把一般只顾自身的享乐、置家庭于不顾的女子,作为“妇女应该回家去”的借口词,她强调:“其实自强不息的女子,决不是如此的,一个真正有才学的妇女,她们有克勤克俭的毅力,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吃得起苦,负得起责任,能够牺牲一切来谋人类的幸福,决不讲表面的享乐,和空言求平等的……现在一般负担社会事业的妇女们,那一个不是负着做事理家双重责任呢?况且忠于事业的妇女,常是组织快乐家庭的模范主妇。”(注:王敏仪:《纪念“三八”节》,《江西妇女》创刊号,1937年3月8日。)
(三)主张自主选择,爱做事的做事,爱回家的回家。由于社会上有种“留在家里是落后,走出家庭是解放”的观念,陈衡哲(注:陈衡哲(1890-1976),江苏武进人。1914年留学美国,先后入瓦沙学院、芝加哥大学研究历史、文学,1920获英文文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西洋史教授。)提出不同意见,她深有感触地说:“我自己对孩子的牺牲很大,这是没办法的事,生育无论如何女人是推不开,家庭里的事男人总是管不好,只要社会上的人养成一个不轻视管家的妇女的观念便好了,使不能作其余的事的妇女能毫不惭愧地管家,免得为了被轻视而硬要去参加自己所不能处理的事,结果反倒糟了。”(注:子冈:《陈衡哲女士访问记》,《女声》第3卷第2期,1934年10月31日。)1935年7月,她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的文章,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在现社会的情形之下,我们既不主张每一个女子都须走出家庭来做一点旁的事业,我们也不赞成‘不准有智识的女子走出家庭’的一类论调。因为假如每一个女子都走出了家庭,儿童们便须失掉他们的母亲;不准有智识的女子走出家庭,国家便须失掉天才女子的贡献。这两者都是一个民族的命脉,任何一样的损害都是担受不起的。”(注:陈衡哲:《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独立评论》第159号,1935年7月14日。)1936年4月,黄兴夫人徐宗汉在接受《申报》副刊《妇女专刊》记者访问时指出:妇女“在家做贤妻良母,这是份内事,毫无疑义的”,“妇女因生理上的关系,当然不能与男子相提并论,一般女子治理家政,已觉责任重大,遑论兼顾外务。但有一部分能力优厚的妇女,应各尽所能,各就所长,视其个性所好,尽力为社会服务,我相信获得的效果,必什倍于家庭”。(注:萍:《黄兴夫人对现代妇女的观感》,《申报》副刊《妇女专刊》第13期,1936年4月11日。)还有女性表示:“我们替社会服务的方式,间接或直接,不要拘泥在某一成见上,硬要这样行是对的,那样做是错的,做一个没有一点自主权的女人”,“我们要永久保护这神圣的自决权,不让任何人,任何势力,加以指挥,干涉,或是节制”。(注:陆顾文淑:《巩固我们的自决权》,《申报》副刊《妇女专刊》第14期,1936年4月18日。)
四、结语与反思
由上述言论可知,主张妇女回家的多为男性,而反对妇女回家的多为女性。两种立场,似乎各有道理,很难用对或错的标准去评判。其实,根本分歧是如何看待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贤妻良母”是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期待和要求,希望女性为家庭作出奉献与牺牲,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他们大都把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对立起来,认为女人要么留在家庭做贤妻良母,要么独身专为社会服务,二者难以两全。激进的知识女性也把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对立起来。不过与男性相反的是,她们认为“贤妻良母主义是锢禁妇女的工具”(注:罗琼:《怎样走出家庭?走不出又怎样?》,《妇女生活》第4卷第7期,1937年4月16日。),因而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主张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走到社会中去。
贤妻良母本身是个好名词。做妻子的、做母亲的,当然应该贤、当然应该良。但是由于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是“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女人的天地局限于家庭。在三从四德的教条下,贤妻良母这美好的名词,变成了束缚妇女的枷锁,以致“一般要在黑暗中争取光明的姊妹,见了这名词就有些害怕。原因是这美好的名词后面,就是‘服从’和‘奴役’的实质”(注:《真实的贤妻良母》,《妇女生活》第8卷第2期,1939年10月16日。)。妇女运动者主张妇女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服务,谋经济上的自主与自由,是有积极意义的。女子要具有独立精神,就应该和男子同样服务社会,才能与男子立在同等的地位。
当时都市里一些摩登女子,既不能跑进社会服务,又鄙夷“贤妻良母”的观念,对于家庭的事务,一概不管,而唯日夜沉醉于享乐的生活里。陈衡哲看不惯这种浪漫与放纵的自私女子,认为:“女子解放的真谛,在志愿的吃苦而不在浅薄的享乐,在给予而不在受取,在自我的上进而不在他人的优待。简单说来,即是在心理与人格方面,而不在形式方面。”教育家俞庆棠也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新时代女性,如仅骛于‘自由’与‘浪漫’,而忘其教育幼儿——即将来之国民——之任务,则非特影响于教育,且可影响于民族前途。”(注:封面语,《妇女月报》第2卷第5期,1936年6月10日。)
一些知识女性申言,由于性情、学识、环境因人而异,女性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管是跑入社会工作,还是留守家庭管理家务,“这两种职责的价值和意义是一样的”(注:志敏:《再论新贤妻良母》,1935年9月4日《中央日报》。),都值得敬重和赞美。冰心看重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与影响。她的母亲是一位纯粹的家庭妇女,但在冰心看来,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她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母亲那样的女人”。(注:《我的母亲》(1941年3月7日),冰心:《关于女人和男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著名的蚕丝专家费达生(注:费达生(1903-),江苏省吴江县人。1920年自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毕业后,入日本东京高等蚕丝专科学校,1923年毕业。曾在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任教员。自1938年9月起,任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乐山蚕丝实验区主任。1949后任中国蚕丝华东区公司总技师、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等。)直到1950年才结婚。1996年她接受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沈汉访问时,谈到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感悟:“应要照顾到社会,又要照顾到家庭。”“解放前像我这样没结婚的人很多,大家不想什么家庭了,做事起劲得很,连我的学生也做事起劲,不结婚。但解放后,觉得不对了,像我这样不结婚的,那下一代怎么办呢?不完整的。我一点也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也不知道家庭究竟应该怎么样”。(注:《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63页。)可见,女性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也是一种缺憾。
一些知识女性认为女子应承担对国家社会及家庭儿女的双重责任,使家庭与事业两全其美,内外兼顾。她们努力做到双重角色的和谐统一,既是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又是营造和谐家庭的贤妻良母。这是一种理想模式,但事实上却不容易办到。
当时除了极少数妇女到社会工作外,绝大多数的妇女还没有脱离家庭。客观的社会环境尚未具备妇女解放的条件,不可能为妇女走出家庭、服务社会提供健全保障和经济基础。家庭与社会的矛盾普遍存在,已婚职业女性在双重负荷下挣扎着。而一般社会人士对于家务和育儿还不承认是男女共有的责任,所以家庭对于职业妇女,不能不说是一种牵制与累赘。不少职业妇女,为了家事为了育儿而放弃工作,被困在狭小的家庭圈内。反之,一些女性为了事业而牺牲爱情、放弃婚姻。
女性革命者则强调,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环,在社会问题未曾解决之前,妇女问题决不能单独解决(注:君慧:《现阶段我国妇女运动的动向》,《妇女生活》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16日。)。中共党员陈修良在《中国妇女到哪里去》中深刻指出:女子对于社会与家庭服务并重的主张,“在中上产阶级的妇女,尚有实行的可能,但是贫困的妇女,家中既无佣仆,如果白天里劳动了一天,还要回家整理家务,是不大可能的。若是有了小孩子的,那末更谈不到离家出外工作了”。她认为,中国如果没有彻底的民族解放,则妇女问题的解决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一切先进的女性,一定会走到社会上,和男子们站在一起,去为民族独立而奋斗,去为她们本身的彻底解放而牺牲!(注:莫湮:《中国妇女到哪里去》,《东方杂志》第33卷第17号,1936年9月1日。)
1937年以后,随着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贤妻良母主义的说教,几乎已经完全销声匿迹”(注:罗琼:《怎样走出家庭?走不出又怎样?》,《妇女生活》第4卷第7期,1937年4月16日。)。经过这场讨论,更多的知识女性认识到:在国难严重、民族危急的时代,妇女的解放不能脱离整个的民族问题而单独解决,妇女解放运动必定要与民族解放运动合流,在民族解放运动成功之后,中国妇女才有解放的可能。同时,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党各派各方面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男女平等的法律保障下,广大家庭妇女走向社会参加生产劳动,集双重角色于一身,承担着双重责任。但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男性仍普遍地把家务劳动看作女性的天职,双重负担造成双重角色冲突。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整体就业形式严峻的情况下,又有男性提出“妇女回家”论,遭到大多数知识女性的反对。她们认为妇女回归家庭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应充分尊重个人选择的权利。而对于大多数知识女性来说,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她们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方式,宁愿承受双重角色的紧张压力,也不愿放弃社会角色,唯有这样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
女性双重角色的矛盾问题,绝不是“回到家庭去”的简单办法所能解决的。其解决希望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家庭是男女共同的栖息地,处理家务与教育孩子是男女双方共有的责任,男女宜建立平等合作意识,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担负家庭的责任。此外,女性要最终与男性取得平等的权利、地位,尚须格外努力,在社会活动中充分表现能力,赢得更广泛尊重与认同。
标签:东方杂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