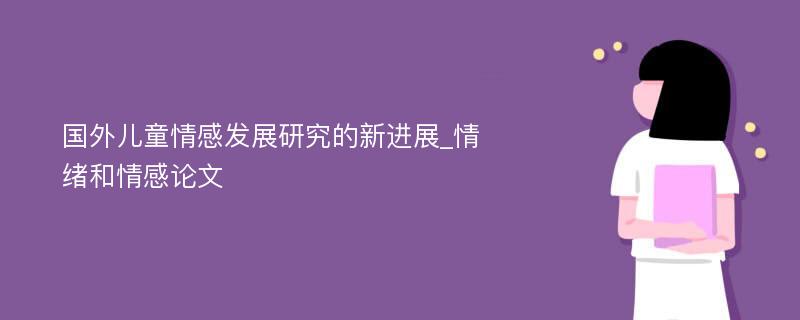
国外儿童情绪发展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情绪论文,国外论文,儿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6-0098-07
学前到学龄期间,儿童的情绪发展成就是惊人的,他们的许多情绪技能,例如控制消极情绪的爆发、表现出不同于真实感受的“表面情绪”或“情绪外壳(emotional front)”等,在5-12岁之间飞速增长[1]。早期关于情绪发展的研究多数将儿童看作是独立的个体,把他们的情绪发展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心灵内部的过程[2,3],关注个体的情绪控制和情绪的生理、言语表达,而很少有研究关注与情绪有关的人际交往过程、情绪交流、以及人际互动中的情绪动态。近期研究发现,外部的社会化过程例如他人对情绪的解释、对儿童情绪的积极或是消极反应能对儿童的情绪能力做出很好的预测[4],父母对孩子情绪的社会化措施对其情绪能力具有重要影响[5],因此近十几年来关于情绪发展的许多研究表现出一种从相互影响的、人际交往的角度研究情绪发展的趋向[2],或者说是强调情绪的社会化[4,5]。这种研究取向考虑到了人与生俱来的社会性以及产生情绪所离不开的社会情境,并且多采用观察研究、准自然实验设计,保障了实证研究的生态效度,突出体现了当前情绪发展研究的一种新动向。
在人际交往和协商中,个体必须采用大家都能理解的情绪表达策略,以达成共识。社会情境给个体提供了对事件、对与人关系、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及个体的主观体验(生理状态和情感状态)做出解释的“常模”,对其情绪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情绪常模”(emotionnorms),指的是一种类似规则的信念,它规定了人们在特定情境中交往时能接受的行为[2]。许多研究都说明,儿童在不同情境中获得各种团体,例如人类、家庭、同伴群体、小团体等中的情绪常模,并且随着年龄而发展变化。亲子交往、同伴交往是学前、学龄儿童情绪发展所必须面临的主要社会情境,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介绍一下当前国外情绪发展的研究状况。
一、亲子交往中的情绪发展
亲子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亲密的两极关系。父母的知识、社会权力都远远超过孩子,他们对儿童情绪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是孩子的依恋对象,还是认知和情绪“专家”。因此,父母对儿童一般具有两种作用:他们不仅是孩子情感需要的安慰者和支持者,还是其情绪发展的教育者和指导者。
在童年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孩子感到焦虑或悲伤的时候,父母一直都是孩子身边最主要的安慰者和支持者,他们帮助孩子在自身不能处理情绪困扰时进行情绪调节。父母对孩子的悲伤或挫折做出及时反应能够缓解他们当前的痛苦,并能从长远意义上帮助他们抑制消极情感,以控制可能引起他们沮丧的不良情境[6]。如果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忽略了他们的情绪体验,会促使儿童发展分心、转移注意的策略,最终限制儿童的相关情绪发展[7]。依恋方面的研究也表明,父母能否对孩子们发出的情绪信号做出即时反应对其情绪发展有很大影响,对母亲的安全依恋能促进学前儿童对消极情绪[8]、以及混合情绪[9]的理解;对父母具有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容易对同伴的意图做出敌意的归因[10]。
父母在学前期到学龄早期儿童的情绪发展中持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儿童长大,他们对父母支持的依赖逐渐减少,到青少年期其作用则迅速减弱。多数学龄早期男孩在听鬼怪故事感到害怕时,仍然需要父母的情感支持;多数小学儿童在研究者呈现的假想父母关注其情绪反应的故事中,仍然表现出真正的情绪表达如生气、焦虑、难过和痛苦,尤其是年幼一些的学龄儿童把母亲看作是愤怒表达的最佳对象,在自身缺乏调节技能时表达出愿意接受帮助的情绪[11,12]。从2年级开始,儿童对父母的这种单边的信任和情绪支持感开始有所改变,他们预期对他人的愤怒表达会得到父母的不赞同反应[12]。到青少年期,儿童对父母曾经有过的这种情感信任和依赖则完全改变了:8年级的青少年不愿意在父母面前显示他们的愤怒或难过情绪,并预期这样做会得到最消极的反应[13],8年级的女生认为在某些情境下应该掩饰情绪的表达,更愿意把同伴作为真正情绪表达的对象[11]。这既体现出青少年情感发展的日益成熟和独立,也反映出亲子关系在这一阶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适应。
作为“情绪专家”,父母教给孩子如何处理日常情绪事件。他们会告知孩子他们对情绪事件的评价,帮助孩子们针对情绪体验使用相应的情绪标签,使用情绪表达的文化或亚文化规则(这也是情绪的3种成分)。这主要是通过家庭中父母和儿童的“情感对话”(feeling talk)进行的[14],这种生活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功课”大大提升了儿童对各种情绪的理解力。研究发现,母亲在讨论家庭成员的情绪上花的时间越多,其3岁孩子的情感观点采择能力越好[14]、学前儿童的情绪理解能力越好[14,15]。如果18个月大的儿童听到关于感受方面的谈话比较多,那么该儿童2岁的时候就比那些听得比较少的儿童更爱谈论自己和他人的感受[16];在家庭对话中听到了较多关于感情话题的3岁儿童,到6岁半时能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情感,而且这一现象与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家庭中的谈话总量无关[17]。如果父母对情绪的教导和预警是误导性的,孩子在童年中期对情绪就具有扭曲的理解,例如倾向于认为引起其愤怒的同伴具有敌意的意图[18]。Dunn,Brown,& Maguire(1995)发现,早期的情绪理解与幼儿、1年级儿童道德认知水平有关[19]。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儿童在较多地谈论感情话题的家庭中长大,不仅有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绪和感受、发展社会交往技能,还可能导致学前或学龄儿童表现出良好的道德情绪[20]。
情感对话还为孩子提供了接触自身文化、亚文化(或家庭)的情绪表现规则(emotion display rule)的机会,例如亚洲文化中强调儿童应该尊敬年长成员、禁止对他们表现出愤怒或沮丧[21],西方某市区工薪阶层的母亲们教给孩子们“坚强”(toughness),以应付周边的恐吓事件[22]。这些宏观上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带有地域特色的教养风格给儿童的情绪发展打上了深刻的文化烙印。
总之,父母是认知、情绪上更成熟的成人,他们对孩子的情绪理解一方面可以做出比较全面的把握和导向,另一方面则又容易为自己的角色所局限。在某些情况下,儿童还有可能反过来成为父母的支持者。由于亲子之间客观存在的非对称关系,孩子们被要求遵守文化规定的关于情绪评价、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的规则,偏离常模的情绪表现例如愤怒爆发可能不能受到欣赏,并使得父母不能理解孩子的某些情绪反应。例如,父母担负着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充分保障的责任,这使得他们在孩子玩兴奋刺激、但可能比较危险的游戏时,不得不采取控制措施;同时他们又有着作为成人的特权,因而不可能完全告诉孩子们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些认知、情感相对成熟的孩子则有可能安慰遇到麻烦的父母,正如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懂事的孩子一样。这些都是从亲子交往的角度研究儿童情绪发展应该考虑的。
二、同伴交往中的情绪发展
相对于亲子关系而言,同伴关系是对称性的,双方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权力,因而同伴关系对儿童的情绪发展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一,同伴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随着其认知水平的同步提高,同伴更有可能理解对方的情绪发展,彼此扮演着协商者的角色,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情绪调节策略。例如,日常交往中他们从同样的社会认知水平和道德水平进行讨论和争论,面临同样的成长过渡期和生活事件,在学校和老师眼中都具有相同的角色,因而彼此之间能做到相互的支持和指导。其二,同伴之间可以形成群体、小团体或是友谊关系,从而抑制或加强其情绪体验。群体的形成使得儿童在伙伴们面前时避免表现出愤怒或是恐惧,在和伙伴们一起玩游戏时变得更加有趣、或者在看到某种怪物时加强彼此的恐惧情绪(如曾有所报道的集体性的癔病症)。作为一个群体,儿童和青少年形成了一种有着独特情绪规则的文化,他们对诸多的情绪事件有着类似的评价,构成了其情绪表现的同伴常模。
在和同伴交往、协商的过程中,儿童不断学会通过适当的认知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一项研究采用儿童愤怒调节策略问卷(SAR-C)考察了130个9-13岁柏林小学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2]。结果显示,年长儿童比年幼儿童更多地采用“沉默处理”,更多地转移注意力,远离让他们生气的同伴;在向同伴寻求社会支持上则不存在年龄差异。Underwood等(1999)同样发现[23],当受到不认识的同伴挑衅时,6年级儿童比2年级更容易做出沉默反应、显示中性的面部表情、以及耸肩。Murphy和Eisenberg(1996)发现[24],当被问到同伴引起他们愤怒怎么办时,越来越多的年长儿童表示他们将避免直接对峙,并且越来越懂得转移注意力会减轻他们的痛苦体验。10岁儿童几乎100%认为,认知回避是一种有效地减少他们的愤怒或难过情感的方式,这一比例比学前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都多。对四五岁的幼儿,他们还可能会通过担负更多的社交责任和表现出更积极的情绪来应付愤怒情境。在一项对学龄儿童的社会认知研究中[25],当主人公受到同伴伤害时,远离被认为是最好的策略;主人公受到同伴羞辱时,问题解决被选为最好的策略。远离和问题解决都不需要对同伴表现出消极情感,可以说是内隐的;而外显化、情绪爆发则被一致认为是最坏的策略。更进一步来看,小学低年级儿童大多数都已经知道,他们表现出来的情绪不必与他们自己感受到的一致,亦即表现出Saami(1988)称之为的“情绪外壳”(emotional front)。尽管这些“情绪外壳”使得孩子情绪表达的真实性少了,但却是积极的,多数情况下都意味着儿童能够控制主观情感的表达。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学前、学龄儿童对情绪的控制和调节能力逐渐增强,他们学会了减少愤怒的表达,以便和同伴的冲突观点进行协商或是重新形成新的观点,尤其是年长儿童更趋向于采用能达到目标而不破坏人际关系的方式来应付情绪冲突[26]。
同伴交往将无可避免地形成同伴群体,现代的同伴群体似乎倾向于抑制很多情况下的情绪表达。伙伴们拒绝不服从情绪表达规则的儿童:例如经常爆发愤怒、对其他儿童的失败洋洋得意会招致同伴拒绝[27],对他人成功的妒忌也与同伴拒绝有关[28]。这种同伴拒绝即便非常短暂,也将是一个很强的刺激,促使儿童服从同伴行为标准。因此,在同伴常模的压力下,对许多情境中的多数情绪表现出“酷”(cool)或者说是冷静的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社会压力要求男孩子保持坚强的外在形象,使得他们的某些情绪常模可能跟女孩子不一样。青春期男孩比女孩更加确信,如果同伴在场时表现出愤怒或难过,他们会被小看或嘲笑[13];学龄期男孩比女孩更多地报告说不对同伴或老师表现出愤怒[29]。在一项实验室观察中,10岁、12岁儿童面临挑衅时都能保持相当的镇静,年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中性面部表情和沉默反应、更少的消极手势,尤其是女孩[23]。这种同伴压力与儿童“情绪外壳”的形成不可谓无关。例如一个10岁男孩说道,“当你难过的时候,你应该面带微笑,与其他人呆在一起,并试着跟正常一样。”另一些场合,表现得过于泰然自若也不行,比如顺从的行为模式与6、8岁儿童中缺乏自信以及长期的伤害行为有关[30],因而在面临同伴挑衅时,采取保持冷静的策略并不总是凑效,还是应该表现出适当的自信。在众多同伴的眼光注视之下,儿童学会了自我表现和印象管理技巧,这对于公共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同伴群体的这种抑制作用可能与一定时期内父母还是儿童的主要交往对象、而同伴关系不及亲子关系亲密有关。Saami发现[11],学龄儿童只有在强度达到极端时才会把他们的焦虑、伤害告诉他们的同伴,或者是将那些外部可见的情况(例如流血了)告知同伴。小学儿童认为,如果他们在同伴面前表现出难过或是痛苦会得到比在父母面前时更多的消极反应。在愤怒情绪上也存在类似的情绪表现规则[31]。
总的来看,需要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儿童在各种具体情境下对各种不同情绪的同伴常模及其发展。可能是因为日常学习、生活实践的需要,研究者往往更关注同伴交往中的消极情绪及其调节,突出了同伴群体对情绪表达的抑制作用,而关于积极情绪及其常模的研究还不多见,同伴群体对情绪表达的促进作用还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在体验积极情绪时,是否也要表现得很“酷”呢?同伴世界中一些曾经受到许可的积极的情绪表达,随年龄增长可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许多情绪表达都可能会受到同伴群体的嘲笑,应注意防止同伴群体中形成抑制性的、乃至令人窒息的气氛。反过来,同伴群体是否会加强个体在某些情境下的情绪体验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比如一个儿童的恐惧感可能会传染给同伴,引发、并加强大家共同的恐惧感;一起玩游戏体会到的快乐情感应该会比一个人玩时要多。这些预期还有待进一步实验研究。
三、情绪发展研究前景展望
情绪发展是儿童社会性发展领域的重要内容,亲子交往、同伴交往是儿童情绪发展面临的主要社会情境,父母作为儿童情绪发展中的支持者和指导者,其影响作用随儿童年龄增长而有所变化;同伴作为平等交往的伙伴和彼此的协商者,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形成具有特定情绪规则的群体。尽管近十几年来国外关于情绪发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要勾勒出比较系统、全面的发展蓝图还比较困难。该领域可能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有:依恋问题是亲子交往中不可避开的话题,可以通过追踪研究考察早期依恋对后来亲子交往中的情感发展的影响;考察童年中期亲子“情感对话”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探查某些高级情绪,例如复杂情绪、混合情感、情绪外壳的发展。通过更加细致地探讨情绪表达的常模,可以确定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可以、甚至必须作出一定的情绪反应,例如父母之间的婚姻争端如何影响他们对孩子哭闹的情绪反应和教养方式?这是否会造成儿童的情绪问题?同伴打闹之后的情绪状态如何?如何达成相互的谅解?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助于设计临床干预手段,帮助儿童更好地为同伴群体成员所接受。同伴对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毋庸置疑,然而,他们对其同龄人的情绪理解是否比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理解更准确?这需要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进行验证;父母的情绪经验会教给学龄儿童如何和同伴进行情绪交流[32],但对青少年来说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他们之间的情绪行为会影响到随后他们与父母的情绪交流。因此进一步阐明亲子交往和同伴交往对儿童情绪发展的交互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综合情绪的各种成分、纳入发展变量的综合性的情绪发展理论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
收稿日期:2003-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