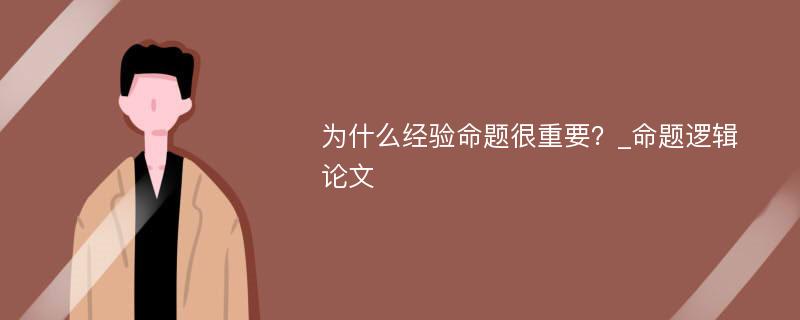
为何经验命题重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5 “语法”及其周边概念作为一个独立的论题本身没有争议,但如果涉及现实的经验世界的时候,“语法”这一概念所带有的自治性和任意性特点就显得不够用了。维特根斯坦正是在讨论外部世界怀疑论的时候逐渐放弃了对“语法”诸概念的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经验命题(empirical proposition)和逻辑命题(logic proposition)这样的概念。如果将外部世界怀疑论看作某种特殊的语言游戏①,那么,考虑到语言游戏中语法的自治性,我们将无法回应外部世界怀疑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无法处理语法任意性等概念所造成的语言游戏的封闭性和文化相对主义等疑难。 本文试图在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框架内,对“语法”、“逻辑命题”和“经验命题”等概念进行梳理。通过分析表明,维特根斯坦之前使用的语法概念和《论确定性》中的逻辑命题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逻辑命题可以由经验命题转化而来;而维特根斯坦晚年对经验命题的重视不仅有助于在客观上克服语法概念的缺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语法概念的自治性特征,从而使得语法/事实二分的哲学原则逐渐被淡化。 一、“语法”概念及其相对主义疑难 维特根斯坦对语法概念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与他对游戏规则的讨论联系起来。毕竟,不同的语言包含不同的语言游戏,而不同的语言游戏又涵盖不同的游戏规则。贝克和哈克从类似的角度谈到这一点,他们认为,“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法规则’……是《逻辑哲学论》中‘逻辑句法规则’的后裔。但语法的领域,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设想的,却比逻辑句法的范围更为广阔。它的规则涵盖意义解释的各种形式,不仅仅是形式的定义还包含实指定义,以及通过例子、改述、肢体语言的解释等等。”(cf.Baker & Hacker,p.45)贝克和哈克在此论及了哲学语法与逻辑句法之间的继承关系。根据他们的看法,所谓的语法大概就是语言游戏中的概念在使用过程中的表述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哲学语法研究”看作是“概念考察”的别名。(陈嘉映,2011年b,第67-68页)而事实则从这些概念中被表述出来,概念与事实的区别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所谓概念考察与事实考察之区分的基础,后来的许多哲学家也都从概念考察这个角度从事哲学研究。比较典型的如蒯因(Quine)和斯特劳森(Strawson)等人对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等概念的使用。(cf.Glock,2009,p.657) 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那么,这种不同究竟是如何体现出来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法的自治性就是这种不同的具体体现。“语法规则并不在真或正确与否的意义上回应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它们是‘自治的’。它们并不回应‘思维规律’,而是组成它们。它们并不是‘人类思维规律的表述’,而是决定那被唤作‘思想’或‘推理’的东西。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语法是自治的。”(Baker & Hacker,p.46)语法的自治性就是不同语言游戏表述现实方式的自治性。陈嘉映以度量单位为例对此专门做过论述:“度量单位的选择是任意的,语法规则在相同意义上是任意的。但这只是说:这种选择不依赖于所度量物体的长度;量出一个长度有对错,并不在同样的意义上,选择这一种度量单位是‘对’的而选择另一单位是‘错’的。这当然只是对‘长度单位’一词的语法所做的评注。”(陈嘉映,2011年a,第15页)我们可以设想,不同的语言游戏具有不同的度量单位。当不同语言游戏中的人们在谈到某个物体的长度时,他们往往从自己的度量单位出发进行谈论。这些地方性社会建制(settings)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从一个阿基米德点进行评判,而语言游戏中语法的自治性也主要体现在这个层面。 另外,陈嘉映还从实践活动的自治性谈到了语法规则的自治性:“我们的各种实践活动,也都含有自治的维度。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自治的思想,最好联系实践这个大题目来考察,而语言正是一种最典型的实践。如麦金泰尔所见,自治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一般实践概念。艺术、行医、政治,每一门实践都有它的外部目的,例如,行医是为了治病,但另一方面,每一门实践都或多或少有其自治性,无法完全通过外部目的来解说,疾病、健康等等概念都与医药的发展以及当前的医学建制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真切的理解。”(同上,第18页)换句话说,各种不同的实践活动都包含不同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我们谈论这些实践活动的形式条件;相应地,各种不同的实践活动逐渐会形成不同的语言游戏和语法规则,比如各种行话、专业术语等等。 可是,用实践活动来解说语言游戏的自治性会面临一定的困难。我们知道,一般人并不总是生活在某种单独的实践活动之中,一个人在成为医生的同时还可能是一个市长,一个父亲等等。各种实践活动尽管有其自治性,但在日常生活层面更有交汇的地方;并非每种实践活动都如棋类活动那般严格自治,即带有严格的规则封闭性。否则,我们无法理解维特根斯坦的那个例子:“如果想怀疑地球在我出生以前很久就已存在,我就不得不怀疑我所坚信的一切事情。”(Wittgenstein,1975,§234;中文参见维特根斯坦,2002年。下同)维特根斯坦所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地质学的例子,其中的道理在地质科学内部才能得到真切理解,但它仍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种情况说明,不同实践活动有着相对的自治性,但其基本道理却在日常经验层面相互交织。 语法自治性决定了语言游戏的自治性和封闭性特征。而在维特根斯坦晚年的写作中,语言游戏更多地作为文化的隐喻而出现,如此,研究者们很自然就会推论出维特根斯坦在文化上持有相对主义的观点。 二、从语法概念到逻辑命题的过渡 论者往往从语法命题与维特根斯坦早期所使用的逻辑概念进行对比研究。比如,格洛克(HansJohann Glock)就从二者对比的角度指出:“一种语言的语法大致就是其语法规则系统,即那些通过决定语词的有意义言说的方式定义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它)不同于其前辈逻辑句法,语法并非普遍性的——不同的语言包含不同的语法。”(Glock,1996,p.151)由此可以看出,哲学语法和逻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逻辑往往是从形式符号系统的角度谈到语言,各种语言都可以规约为一致的形式逻辑表达;而语法则着眼于某个单独的语言,即不同语言对现实的不同表述方式。 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仅有寥寥几处提到了“语法”,其中一处比较值得一提:“现在‘我知道,我不是仅仅在猜测,这里是我的手’难道不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语法命题吗?因此不是有时间的。”(Wittgenstein,1975,§57)他这里的讨论提示:摩尔以“我知道”开头所表达的诸多命题大致上都是某种语法命题。同时,维特根斯坦紧接着又针对这类命题发表评论道:“在这里‘我知道’是一种逻辑上的洞察。只是实在论不能被它证实。”(ibid,§59)维特根斯坦的上述两处论述显示,“语法”与“逻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正如格洛克所指出的:“维特根斯坦使用‘语法’这个语词来指涉包含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和哲学研究的工作或者这些规则的集合。终其(维特根斯坦)整个哲学生涯,他都在同样的这两种意义上持续使用‘逻辑’或者‘语言逻辑’这样的语词,来理解逻辑问题实际上就是语法问题,即关涉语词用法的规则。”(Glock,1996,p.150) 维特根斯坦总是强调,很多以“我知道”开头的命题都属于逻辑命题,其中就包含摩尔的那些陈述。比如,“当摩尔说他知道某些事情时,他实际上是在列举许多我们无须特别验证就可以肯定的经验命题。这些也就是我们在经验命题体系中完成特殊逻辑任务的命题。”(Wittgenstein,1975,§136)这些命题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出现怀疑一类的东西”。(ibid,§58)大致上,所有关于事物存在的陈述都可表达为以“我知道”开头的这种命题。维特根斯坦虽然是从反驳怀疑论的角度讨论这一点,但我们仍然可以推论说,事物的存在是语言游戏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这类命题描述了语言游戏的状况(cf.ibid,§56),并且它们决定了人们在语言游戏中能谈论些什么;其在语言游戏中的功能与上文分析的“语法”概念类似。 维特根斯坦之所以判定这些命题无意义就在于:当我们说出了这些命题的时候,其实也就仅仅相当于说出了某个事物的名字,比如胳臂。说“我知道我的胳臂存在”和说“我的胳臂”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后者对事物有本体论上的承诺。其实,这和当时康德评论存在不是谓词的道理是类似的。而从语言游戏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说出“我知道什么东西存在”仅仅相当于为某物命名,而命名仅仅是语言游戏的起点,即这种陈述还未进入语言游戏这个赋予语句意义的领域。②(cf.Wittgenstein,1999,§49;中文参见维特根斯坦,2005年。下同) 逻辑命题像语法一样决定了我们言说现实世界的形式和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反复提到的逻辑命题与他以往所讨论的语法概念在诸多用法上类似。但逻辑命题与语法概念不同的地方在于:逻辑命题可以由经验命题转化得来。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以“我知道”为开头的逻辑命题也可以被称为经验命题。(cf.Wittgenstein,1975,§136)在这个意义上,语法/逻辑和事实/经验二分的界限就被淡化了。 三、任何经验命题都能转化为逻辑命题 针对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命题与逻辑命题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曾评论道:经验命题,而非仅仅逻辑命题,是一切思想的基础。(ibid,§401)这说明,经验命题与逻辑命题在语言游戏中具有相通的地位。维特根斯坦曾以河流与河床对二者进行类比:“人们可以想象:某些具有经验命题形式的命题变得僵化并作为尚未僵化而是流动性的经验命题的渠道;而这种关系随着时间变化,因为流动性的命题变得僵化,而僵化的命题又变得具有流动性。”(Wittgenstein,1975,§96)不仅如此,维特根斯坦还从经验命题与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类似讨论: 但是这样人们是不是必须说,在逻辑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缺少明确性就是在规则与经验命题的界限上缺少明确性。 我是说:任何经验命题都能够转化为一个公设——而这也就成了一种规范的描述。(ibid,§319,§321) 很明显,我们的经验命题并非全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因为人们可以写下这样一个命题,把它从一个经验命题改变为一个描述规范。(ibid,§167) 维特根斯坦并未明确讨论逻辑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存在着哪些具体差异,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到底怎样才能将任何一个经验命题转化为一个逻辑命题或者描述的公设。不过,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对命题知识的体系性的讨论中理解此处的转化问题: 我们并不是通过学会规则才学会怎样作出经验判断的,别人教给我们的是判断以及该判断与其他判断之间的关联。一个由判断组成的整体对我们来说才显得言之成理。 当我们开始相信某件事情时,我们相信的并不是单独的一个命题,而是一个由命题组成的整个体系。 使我认为明显无误的并不是一些单独的公理,而是一个前提与结论相互支持的体系。(ibid,§140-142) 人们差不多可以说这些墙基是靠整个房子来支撑的。(ibid,§248) 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习得的各种经验命题构成了一个整体,命题与命题之间相互支撑构成了一个融贯的体系。而经验命题要转化为逻辑命题,则需要获得游戏规则的地位,即获得无条件的确定性(与摩尔“我知道”命题的确定性类似);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单独的经验命题被质疑的时候,此时,该命题就自动获得了整个命题体系所赋予的确定性。通过这种方式,经验命题与逻辑命题的转化得以完成③。 如此一来,逻辑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的界限就变得十分模糊。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合理推论说,逻辑命题谈论的是经验命题在语言游戏中的功能;而经验命题则谈论的是逻辑命题的构成。 可是,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为经验命题所给出的例子殊为多样,除了摩尔式的描述自然事实的经验命题,他还曾提到过那些依靠人们的承认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经验命题。 四、两种经验命题——一个推论 维特根斯坦曾谈到:知识与我们对之的承认(acknowledgement)态度相关。(Wittgenstein,1975,§378)有效性依赖于人们承认的知识,当然不受自然事实的约束而具有语法自治性。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类似的信念系统,这些信念系统内部的信念之间互相支持,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比如不同地方的文化、宗教和语言游戏等等。 从传统或习俗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来看,它们的确只是取决于我们对之的态度。比如,某人承认巫医的效果,但同时却在患了重病的时候去向现代医学求治。维特根斯坦就曾谈到过这一点:“如果某人说他不会承认任何反面证据的经验,那么这毕竟还是一种决定。违背这种决定行事,对他来说是可能的。”(ibid,§368)维特根斯坦此处的论断仅对各种特殊的地方知识(各种文化、宗教等)有效,而对那些描述自然事实的科学理论无效。比如,某人决定相信重力的作用,他如何才能违背重力作用形式呢?几乎无法设想这样的例子,不过,这人倒是可以逃避重力的作用,比如在外太空等等,但这种情况并不是违背重力规律。换句话说,承认这种态度(或者语法自治性)对于经验知识的有效性作用有限。 因而,我们有理由将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经验命题区分为两类:一类指的是那些传统上继承下来的相互支撑的信念体系,比如原始巫术、宗教信念等等;另一类指的是那些和事实证据相互支持的科学规律。 一方面,第一种经验命题体系之所以被称为经验命题,是因为我们可以按照它们所描述的世界观或者世界图景去经验这个世界。比如,基督教教徒往往会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又或者,中医说阴阳五行等概念,古代中国人就按照这种观点看待世界。人们根据这些经验命题去经验世界,它们与科学规律的正误判断标准有着重大不同:在宗教信念体系中,我们往往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回溯到宗教的经验命题中,符合这些命题的经验才能被称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有关世界的科学经验命题则与人们对之的承认并无多大关系,即使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不懂得重力学原理,他们的行事方式也不会与之违背,也就是说,科学经验命题在各种文化和传统社会中通用。 但现实往往更为复杂,即使那些古代的信念系统,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经验命题,它们所包含的科学经验命题的丰富程度与那时的人们对之发现的程度有关。我们可以简单举例说明,有个流行的故事桥段是这样开始的:“村后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里就包含上述两种不同的经验命题所提示出来的世界图景:一是人们对存在着一座山这个事实的陈述,二是人们对庙宇这种文化存在的描写。它们彼此交织共同坐落于我们的语言游戏之中,日常生活中说理的复杂性往往与这种情况有着紧密联系。 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我们将上述两种经验命题分别唤作:特殊经验命题(local empirical propositions)和普遍经验命题(general empirical propositions)④。但我们应该始终牢记:现实生活中它们往往互相纠缠。 既然任何经验命题都可以转化为逻辑命题,那么,逻辑命题则包含了此处分析的普遍经验命题,也涵盖了那些依靠承认而生效的特殊经验命题。因而,维特根斯坦所谓的逻辑命题既携带了语法概念的功能同时也兼具描述自然事实的特征。 单个语言游戏中的经验命题可以是特殊的也可能是普遍的,这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经验命题是否符合自然事实。并非普遍的经验命题和特殊的经验命题之间就无法兼容,比如“人都是有死的动物”这一符合自然事实的普遍经验命题就与各种原始宗教的世界观相兼容。但各种宗教对世界的描述却因其地方性而具有特殊性。毋宁说,特殊经验命题隐喻了维特根斯坦的语法概念;而普遍经验命题则显示了语言游戏受自然事实制约的面相。 五、从语言游戏的演变看经验命题的地位 如果维特根斯坦所讨论的经验命题系统是自成体系,不对自然事实负责,具有自治性和任意性的话,我们基本上无法处理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第609-612小节中所谈到的不同世界观(语言游戏)之间的争论问题(该处还涉及科学理论是否能作为一种语言游戏这样的复杂问题,此处不论)。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描述,或者参考世界历史,传教士(missionaries)和土著人(primitive)之间并不仅仅互相斥责对方为蠢货或异教徒就匆匆结束了故事;最终,传教士还是让土著人改了宗。 陈嘉映对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说理做出了精彩的评论:我们不能在符合意义上谈论语法的对错;我们谈论语法是否合宜。(参见陈嘉映,2011年a,第23页)这个评论对于我们理解单个的语言游戏中的语法有着重要意义,但却无法处理此处语言游戏演变的问题。是否合宜取决于谈论者的立场,巫术对于土著居民是合宜的;而科学理论对于现代人是合宜的。那么,像维特根斯坦反复强调的,只要土著坚持自己的巫术,在命题上添加自己的确定性,则被说服改宗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 换言之,当我们看到语法概念的自治性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了维特根斯坦所反复强调的,语言游戏受自然事实制约这一现实。“如果我们想象的事实不同于其实际情况,那么某些语言游戏就失去了一些重要性,而另外一些语言游戏则变得重要起来。”(Wittgenstein,1975,§63)维特根斯坦认为,“某些事件会让我处于一种不能继续使用旧的语言游戏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这种语言游戏就失去了确定性。……难道这不十分明显地表示一种语言游戏的可能性受某些事实的限制吗?”(ibid,§617) 语言游戏受自然事实制约这一现象表明:语言游戏中的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都受制于自然事实。自然事实在语言层面被表达为经验命题,因此,语言游戏中的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都受关乎自然事实的经验命题的制约。 维特根斯坦一方面强调,逻辑命题在语言游戏中起着规则性的作用,决定了语言游戏的运作;同时,他又强调,语言游戏受自然事实的制约。结合上述语言游戏演变的例子,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语言游戏受制于自然事实比起语言游戏中语法的自治性和任意性而言更为基础。或者说,自然事实对语言游戏的制约使得语法自治性不再重要,而语法和事实的区分相应地也就被淡化了。 论者如格洛克后来的研究则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中也没有放弃对语法和事实之间的区分。他认为,“存在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区分的坚持。(《论确定性》中——引者注)第51节就承认了经验命题和对‘概念(语言)情况的’逻辑描述之间存在着区别。进一步,在河流—河床的比喻中维特根斯坦明确拒绝将逻辑或语法与经验合二为一。”(Glock,2009,p.660) 格洛克列举了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定性》文本中对逻辑命题的描述,并以之为例论证维特根斯坦并未放弃语法和经验之间的区分。但格洛克并未注意到逻辑命题与语法命题之间的区别,以及经验命题和逻辑命题之间的紧密关联。 另外,里斯(Rush Rhees)和维特根斯坦的对话挑战了格洛克的上述观点: 在《论确定性》的相关评论中出现的新观点就是对那些在我们的言说和语言中“扮演逻辑角色的特定经验命题”的讨论。在1944年他与我在语法命题和经验命题之间的关系这个论题上讨论了数周。他当时正在思考二者的区分并不明晰这样的观点,并且他自己早先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错误的和具有误导性的。(这时蒯因还未从这个思路的角度发表过任何作品。)有一阵子,当这种讨论停滞的时候,我们就断断续续地讨论,他说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有必要回头批判甚至修改他早期在很多论题上的观点——“否则我会思路枯竭”。(Rhees,p.44) 我们从里斯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后来承认早先对语法/事实这样的区分有问题。若坚持语法的自治性,我们就无法对怀疑论问题进行有效回应;并且,语法的自治性和任意性无法解释语言游戏随着时间逐渐演变这一历史现象。 维特根斯坦晚年对经验命题的重视使得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推论:晚年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了语法概念的先天不足,并试图从经验和经验命题的角度重新看待语法概念。无论是特殊经验命题还是普遍经验命题,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被认为在语言游戏中扮演着逻辑命题的角色。其中,特殊经验命题隐喻了语法概念中的自治性特征;当这些特殊经验命题(比如宗教)作为解释世界的理论出现的时候(cf.Harré,pp.211-237),就会受到自然事实以及相应经验的评判。语言游戏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得以完成,相对主义的疑难也得到缓解。 注释: ①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认为外部世界怀疑论之类的问题没有意义,主要是因为它们与日常语言游戏和日常经验不兼容,我们无法以之行事,甚至无法想象一个外部世界不存在的情形。(参见李果,第68-74页) ②此段阐论是作者对维特根斯坦有关摩尔评论的合理推论。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如下:(1)一切描述语言游戏的东西都属于逻辑(cf.Wittgenstein,1975,§56);(2)如果“我知道等等”被认为是一个语法命题,当然“我”不可能是重要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出现怀疑一类的东西”,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个表达式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又可以推出,“我知道”也是没有意义的。而维特根斯坦在紧接着的第61小节指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对该词的一种使用。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出,摩尔所谓“我知道”所表达的内容只是作为我们各种语言游戏的前提性条件出现,它们保证了我们的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和持续性。换句话说,它们是我们开展语言游戏的规则所在;而规则赋予语言游戏以意义,且并不赋予其自身以意义。这是维特根斯坦上述讨论的要点所在。另外,在第424小节以及第587小节中,维特根斯坦认为,说“我知道”等于在强调知道的内容,即这种表达方式只有语气上的意义,并无实质意义。 ③很可能,维特根斯坦所谓的逻辑命题也能转化为经验命题。在《论确定性》第622小节对摩尔“我知道”类型句子的讨论,维特根斯坦提到,对于这些句子中的每一个句子来说,我都能够想象出使之成为我们语言游戏中一步的情境,而这样一来它也就完全失去了它在哲学上令人惊奇的成分。 ④事实上,从维特根斯坦的《论确定性》中析出这两种经验命题或者说理词是有道理的。他自己就曾在评论摩尔那些命题的时候说道:“有无数个我们认为是确定的普遍经验命题”。(cf.Wittgenstein,1975,§273)尽管若维特根斯坦继续思考下去也很可能不会使用这两个概念作为说理词,但他对经验的强调以及《论确定性》中语言游戏的说服问题(ibid,§609-612),都使得这种区分成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合理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