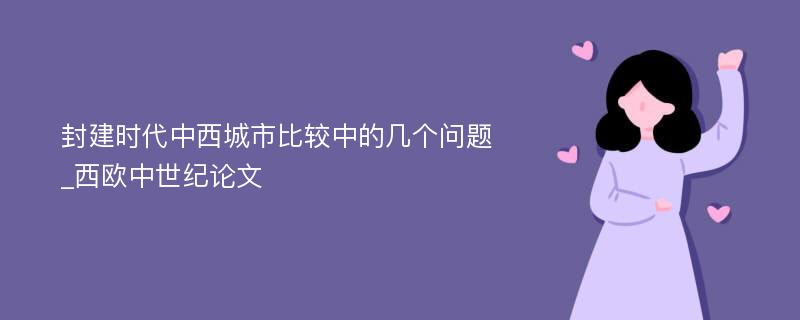
封建时代中西城市比较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西论文,封建论文,时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7)02-0031-07
早些年讨论中西封建社会延续长短,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时,史学界对封建时代城市有过一些研究和比较。本文认为,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及其作用,是西欧有别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显著特征之一,这一认识,可以通过对一些关键问题的比较来加深。
一、关于城市的产生问题
1.西欧中世纪城市是由工商业者的聚居自下而上兴起来的。
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极具特性的历史事件。与中国封建城市发展具有承继性和连续性不同,西欧城市是在经历了五六个世纪的断裂期后重新出现的。西欧中世纪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们大多是作为工商业中心出现的,都是工商业者的聚居地。因此,讨论城市的兴起,必须与其工商业发展相联系,学术界关于中世纪城市起源的几种主要观点,都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的。
我国史学界普遍流行“手工业起源论”。这种观点认为,公元11世纪前后,随着封建关系的最后确立,西欧式封建制度即庄园制、农奴制的最后形成,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农产品有了剩余,可以养活专门的手工业者;另一方面,手工业技术日趋复杂,农民们无法继续兼营,需要专门的手工业者从事。这样,专业手工业者的出现既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手工业者和农村居民交换产品,商品交换便因此发展起来,并促使作为交换中介的专门商人出现。工商业者聚居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便成长为城市。近些年,我国学者还从分析西欧农本经济的特点入手,阐述西欧手工业生产的特点[1],为丰富“手工业起源论”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西方史学界,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提出的“商业起源论”有较大影响。他认为,中世纪城市是作为商人围绕设防地点(城堡和堡垒)的聚居地而兴起来的。由于8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和堵塞商道,引起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衰落。到11世纪,随着商道畅通和商业恢复,最早的城市作为商业据点出现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意大利。在北欧,诺曼人的航海活动也刺激了佛兰德尔地区的商业发展,在那里出现了一系列商埠。随着国际贸易越来越向欧洲内地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作为商业据点,作为国际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就出现了。[2] 商业起源论后来虽然遭到了许多批评,但至今仍是西方学术界最经典的论述。
这两种观点各有侧重,留下了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是否也可以说,城市是中世纪西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产物。这一基本矛盾,就是西欧不断增长着的人口的物质生活需要与其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解决这一矛盾,除了从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外,还必须依靠发展工商业,利用外部物质产品来补充内部需求缺口。发展工商业的结果,是城市的兴起。在封建庄园制下,农奴家庭在原有份地上的生产难以维持不断增长着的人口的生活,便分离出剩余的劳动力。农奴兼营的庄园手工业不能满足领主的较高需要,这就为工商业专门化提供了市场需求;领主庄园可以输出多余农产品,又能为专门手工业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多余的农村劳动力转而专门从事工商业便成为可能。“商业和工业最初从没有土地的人们中间获得发展。”[3] (P41)从事工商业的人们聚居在一起,中世纪城市便因此自下而上地广泛兴起。[4] (P16—39)
这些观点都注意到了一大特点,即西欧城市是“兴起”的,是一种“自发”的社会运动的产物;工商业者自动聚居于一地,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手工业起源论”等着重从封建经济结构内部考察城市的兴起,认为城市兴起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市是因专门手工业者和商人聚居才形成的。“商业起源论”侧重外部因素即国际贸易的刺激,但也仍然强调城市因商人聚居才得以出现。至于聚居地点,都是工商业者根据条件和需要自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在西欧,一个地方能否成长为城市,关键要看该地发展工商业的条件和工商业者的意愿。至于封建主主动设立城市,提供种种优惠,那是为吸引工商业者以增加财政收入。中世纪城市街道、房舍的布局大多杂乱无序,也反映了各个聚落逐渐形成的自然过程。
2.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是由统治者“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
中国封建时代上溯于春秋战国之际,下延至清朝前期。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在这个版图广大的国家中,统一和分裂频仍,起义和战争不断,王朝更迭,外族入主,历史舞台中心的活动者以权力和政治作为行为的主轴。城市就是封建统治者为政治目的而“建立”的。
封建统治者是将城市作为统治中心或军事堡垒建立起来的。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和皇帝要维持对庞大版图每个角落的绝对统治,必须要有一套从上至下的严密统治体系,使国土上的臣民都能直接感知国家的存在,服从皇帝的权威。因此,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地方作为绝对政治权力中心的驻所,由此便有了都城的建立;另一方面,权力中心在各地的代表也须有自己的治所,于是便有了省城、府(郡、州)城、县城等地方层级城市的设立。中国封建城市多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建立”的政治城市。
作为政治需要的产物,城市的兴与废、盛或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格局的演变和统治者的意志。中国统治者在“政治战略上的特殊考虑,甚至几乎可以凭空建起有规划的城市”[5] (P123)。政治变化使得中国历史版图上常见这种现象:显赫一时的城市后来湮没无闻,不见经传的小城却能突然崛起。由于政治的不稳定性,统治者最初往往只用不经久的材料来建造城市,哪怕是都城,也不打算使它“万古长存”。[6] (P37—38)这表明,统治者认为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可能会有“临时性”,因而不愿下大力气建设。如东周时期城市遍及中原,但那些列国国都,却是常迁常毁常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将各国的内城外城,一概予以拆除。[6] (P42—47)隋朝也有类似做法。它在攻克南陈都城南京后,害怕南京仍为南方政权的象征,因而下令毁城,用犁头翻耕了城内土地,只另建一小城作行政之用。[5] (P135)即使到了封建晚期,也还有统治者任意建立或毁掉城市。元朝忽必烈统一全国后,下令“堕天下城郭”,对原有城市尽情破坏,并声称这是为了“示天下为公之义”。这一蠢行,实则是草原游牧民族尚不知城市的政治重要性。蒙古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了不妥,于是不仅保留了大多数现存城市,而且还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城市。其对大都、上都进行的大规模建设,几乎相当于建造了两座新城。[7] (P193—195)
一旦统治者重视城市,城市建设也就会体现其意志和要求。中国城市的形态和地域结构,都程度不一地经过了统治者的规划。城市的外缘形态即城墙和城墙所圈定的城市轮廓,城内的空间结构即街道布局和功能区域划分,统治者都使其赋予了政治意义。他们通过对城市规模、形态和布局的刻意追求与严格统一,借此来象征皇权的力量、中央政令的通达和国家的强盛。[8] (P249)在街区布局、建筑式样等方面,统治者还特别注意考虑其军事和政治职能的发挥。如城郭多呈四方形,大街多为网格状,这些都便于管理。城门上有城楼,便于瞭望敌情;城墙外有壕沟,名曰“护城河”,军事上起防御作用。统治者在城内的皇宫、官府,也特别考虑方便、安全等因素,并受风水、吉凶等观念支配。它们多占据要害部位或有利地形,既便于对全城的控制,也便于安全保卫和军事指挥。
概括地说,中国城市的产生有两条道路:一是统治者在选定地点建“城”之后,由于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需要而聚集了工商业者;二是统治者在确定行政中心地时,也可能选择已有一定数量工商业者聚落的地方。但无论是哪条道路,一个地方要成长为城市,统治者的意志和选择是第一位的,这和西欧城市兴起主要由工商业者自身力量的推动迥然相异。
二、关于“城市”的概念内涵
当我们说到封建时代的城市时,城市的概念内涵在中国和西欧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
1.西欧中世纪城市不但是一个人文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概念。当我们说“中世纪城市”时,语义中常常包含了“城市共同体”或“市民共同体”这一内涵。
西欧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是在市民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聚居在一起的工商业者,都有自己的个人要求。他们从庄园来到城市,为的是能有新的生活,而不是重入另一个领主的枷锁,因此他们希望得到人身的自由。他们来到城市,也体现一种求生存的愿望,因此他们要求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当这些个人要求汇聚在一起时,就形成了一种共同利益,变成了一种共同要求,这是结成共同体的基础。要维护共同利益,取得共同体的自治权应当是最好的保障之一。因此,城市从一出现就开始了争取自治权的斗争。
中世纪城市形成后,便拥有很多的自由,有市民个人的人身自由、经济活动自由;有城市整体处理本城经济、社会和法律事务的自由。城市还可自行配备治安人员,自行组织军队。获得了自治权的城市是这样,那些没有自治的城市,领主统治也只表现为对城市的一种较为松懈的控制。可以说,城市自由的实质,是城市共同体摆脱了对领主的依附地位。城市作为共同体还有集体行动的自由。不论自治与否,所有的中世纪城市都是一种社会共同体,也称为公社。“所有的中世纪城市从法律意义上来讲都是公社,它们都是具有自己权利的集团。”[3] (P43)城市内部是典型的公社制度,有按市民集体意志确立的管理机构,有经市民或代表选举产生的管理人员。城市共同体也是一种地缘共同体,市民一般无血缘关系可言,即使有也退居到次要地位。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是一纸契约,即大家共同遵守的城市章程。市民们共同享有各种权利,并得到城市保护。作为一种共同体,城市是中世纪西欧的一种基层社会单位,但它是代表本城及市民利益的,而不是更高级政治权力如国王、诸侯或主教的代表,不对他们负责。有的城市是高度独立的政治主体,其上很少有能驾驭它们的政治权力。
城市内部也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关系。居民大致可分为市民和非市民两大类。所谓非市民,主要指住在城里的各类封建人员包括国王、诸侯、领主、骑士、主教和教堂神父等,以及他们的家人、仆役。这些人不属于城市共同体,但他们既然住在城内,势必要对城市生活产生影响,不能对此完全忽略。市民即城市共同体成员。从法律意义上说,所有市民的身份是平等的,所有市民的人身和工商活动也是自由的。但由于进入城市有时间先后的差异,从事工作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因而市民也有地位上的不平等。城市贫民虽有人身自由,但在城市政治生活中基本没有地位。手工业者和店主是城市的中间阶层。富有的批发商、外贸商、高利贷者和房地产主,是城市的上层阶级。拥有政治权利的共同体成员,作为城市社会基础的市民,指的是手工业者和店主以上的人员。
城市是逃亡农奴向往的地方,想成为市民的人就是冲着自由和平等而来,因此,城市在本质上不应该有社会等级。事实上,没有哪个中世纪城市公开张扬等级制度,或在法律上规定社会等级。但由于城市诞生于等级的封建社会母体之中,又同外部等级社会有无法分割的联系,因此它“无论如何绕不开”封建母体中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影响。因此,中世纪城市虽不具有明确的等级制度特征,但等级意识、等级观念是存在着的。[9] (P481—508)这种等级观念与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贫富程度相结合,从而出现了城市中十分明确的等级分层。不过,这种以财富为基础的等级划分,是开放式的、动态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是可以改变的,人人都可通过致富而向社会中上层流动。
2.中国封建城市作为各级政治中心(以及衍生的经济中心、社会中心),吸引了众多人口来此聚居,因此城市概念除了人文地理意义外,也有“人口的集合体”这种社会性含义,但一般不具备“市民共同体”这个特有内涵。
中国城市无疑也是众多人口的聚居地,居民成分就籍贯而论,有移住和流入城市的农民和外地人口,也有土生土长的城市原籍居民。在各个时期的都城,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学、赶考和从业人员。从居民身份和职业构成看,大致包括各级官吏、地主、军人、知识界人士等社会中上层阶级;官府作坊工匠、个体手工业者、店铺老板、贩运商人等各类工商业者;宗教徒、迷信职业者、艺人、妓女、奴婢及各种依附者;无固定职业的下层市井居民和流民。城市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只不过人口更集中而已。但这些聚居的人口基本没有共同利益,很难发出共同声音,城市一般也不以共同体身份与外界交往。
就社会地位来说,中国城市居民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部分人员的截然划分,这和西欧不一样。统治阶级成员是官府即城市当局的服务对象,其内部亦有层次等级之分,官府对他们有一定的管理和监督权,目的在于督促其行为符合封建礼制,符合身份等级。这是为了维持统治阶级内部既定秩序的需要。任何私自犯禁的人,即使是官达显贵,在伦理上也被认为是违反礼制、僭越纲常而可能被官衙稽查。对城市的普通居民,官府则代表国家实行绝对统治,城市的管理者是国家的各级官府和官吏。因此在中国封建城市里,不存在西欧中世纪城市那样的市民自由、市民权利、市民自治之类概念。工商业者虽然也有利益、权利要求,但一般由个人直接向官府诉求。他们虽有一些共同利益,但由于官府压制而难以找到共同的表达方式,因此中国封建社会不可能也没有出现城市公社、市民共同体。城市居民同农村居民一样,只是皇帝的臣民、国家的子民而已,政治上处在官府的绝对管制之下。由于城市居民更集中,并与各级统治者共处一城,因而他们所受的人身限制可能比农村更严厉。城市各种治安管理制度实行时,普通居民无疑首当其冲。另一方面,官府不认为城市居民有何特权,因而居民的移进迁出,反倒没有制度上的障碍,非常时期除外。城市居住权的这种开放性,不利于市民结成共同体,却有利于统治者对市民的分化政策。
但国家对城内居民的管理和控制是极其严厉的。凡城内居民,都被按社会身份严格统治在官府划定的里坊内,分别士庶,不令杂居。当社会动荡时期大量流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造成困难时,官府便会整饬里坊,强化控制。随着城市发展,居民增多,统治者的管理措施也会有些变化。唐代以后,官府开始用“坊郭户”等名称来专指城市工商业者,单独列级定等,以与“乡村户”相区别。城内居民始终是封建官府控制下的在册“编户”。在这种严厉的管制之下,虽不排除市民因个人权益受侵害而有抗议举动,但很难见到他们为了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反对或反抗官府。马克思关于中国小农像一堆马铃薯,被国家统装在一个麻袋里的说法,同样适合于封建城市里的居民。处在一盘散沙状态的市民,既便于统治者的统治,也利于统治者实行分化。上层市民为获得更多利益或更高地位,常常还会主动投靠官府、巴结官吏。
三、关于行会等民众组织
1.在西欧中世纪,行会作为城市的基层组织,不但具有经济和社会功能,而且起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
中世纪西欧城市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按行业组织起来的行会。在英法等国,城市里最先出现的是所谓商人基尔特。一个城市通常只有一个商人基尔特,把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囊括了进来。有的城市里它和城市当局合二而一,有的城市里它是市政当局领导下的最高经济组织。[10] (第2—6章)虽然商人基尔特所拥有的监管权多在商业和经营方面,但它的政治和社会作用不可低估。如英国林城的商人基尔特就是城市的实际统治者,它被称为“大行会”,其长老可以自动变成城市的代理市长,城市官员必须出自这个“大行会”。[11] (P175—176)
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按行业分别组织的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不断涌现,行会便成为城市中的核心组织。行会早期的经济政策是保护性的,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保守性。行会的政治作用有诸多表现,诸如行会对城市的政治领导权。如市政机构负责人多来自行会人员,或行会信得过的人员;行会的种种规定,往往是市政当局制定政策的基石。势力大的行会还可从领主那里直接取得某些特权而凌驾于市政之上,或者不服从市政管辖。市政当局官员均由行会选举或推举,就连市政大厅,也因为是各行会代表开会场所而常被称为“行会厅”。行会还是城市中的基层行政组织,不但要对本行会成员负责,也要对市政机构负责。要执行市政下达的命令,完成市政交给的任务,包括缴纳税收,维持治安,管理街区等。在城市需要组成军队时,一个行会往往就是一个成编制的战斗单位。
行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有会徽、会旗,有对成员扶困济危的责任,成员间也有相互帮助的义务。会所作为行会的活动中心,对成员有强烈的吸引力。行会还调解成员之间的矛盾,化解冲突,同时也负有伸张正义、剪除邪恶的责任。城市举行庆典时,以行会为单位参加。演出神秘剧时,行会要出节目;街头游行时,以行会为单位组成方队,前面有会旗开路。参加庆典的开销由各个行会自行负责。
在行会政治时期,城市里的行业差别、市民们的贫富差距都还不是很大。经济平等决定了政治平等,因此行会时期的城市还是很有民主气氛的。然而,这种平等和民主在大多数城市里都只是短暂的。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即城市贵族手中,城市进入了寡头政治阶段。寡头们掌握了市政权力后,极力实施对行会的控制。普通市民反对城市贵族的斗争,习称为“行会革命”。斗争主要是行会发动的,参加者也多为行会成员。如14世纪佛兰德尔城市行会与城市贵族的斗争异常激烈,而且还有领主介入其中,矛盾错综交织,演变成一种三角斗争。行会反对寡头统治的成功例子是佛罗伦萨。在那里,城市政权由7个大行会把持,并有14个小行会协助。在伦敦,寡头政治几乎没有出现过。15世纪,伦敦的大小行会相继过渡为公会,城市政治权力由12家大号服公会控制。
2.唐代以前,中国城市中几乎没有民众组织。唐宋以后的行会基本上停留在松散的经济或社会社团层面,很难体现出政治作用。
在中国封建时代前期,由于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政治功能,因此城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主要掌控在官府、官吏和地主手中。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中心的职能日益突出,市民在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活跃。宋代以后,那种封闭管理式的里坊制度渐趋松弛,统治者对居民的控制有所减弱,市民有组织性的自主活动多了起来。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社团组织渐渐兴起。这些组织可分为工商业组织、文人结社与市民社团、民间秘密结社三大类。前两类是公开的、合法的。工商业组织最多、最重要,名称有行(同业者的组织)、市(同业商人的组织)、团(某些城市中的工商业者组织)、作(手工业者组织)、帮(雇工们的组织)、商帮(按地域或经营品种组成的商人集团)、会馆(在外地的同乡商人组织)、公所(以行业命名的组织)等,还有借用社、堂、公会等名称的组织。文人和市民的结社包括文人结社、艺人社团、市民互助性社团和宗教性社团等。第三类即民间秘密结社是不为官方所允许的,有各种江湖帮会、城市无赖结社、秘密宗教等,成员主要为下层民众。[12]
在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三类社团各有不同。各种秘密结社以另类方式直接介入社会和政治生活,甚至还危及封建统治,因而国家和官府坚决不允许其存在,必要时还进行严厉镇压。第二类社团停留在社会和文化生活层面,其活动大多有利于社会协调和稳定,实际上成了政治治理的一种辅助机制,因而能得到官府的容忍甚至鼓励。不过,这种社团也已暗含着民间的某种自主能力,或许会对统治体制形成潜在威胁。工商业组织也是合法存在的,因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会对政治生活秩序产生一定影响。它们中以会馆和行会最具代表性。
会馆是城市中外地人士的同乡组织。由于国家的高度统一,超越地区需要的国内市场体系比较稳固,从而使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性加大,商务人员的地理流动增多,因而各地城市中的会馆普遍出现,尤其是京城。如清代北京的商人会馆将近100所,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各地进京商帮手里,势力最为显赫的晋商,渗透到城市经济各部门。[13] (P227—229)从政治层面可以这样看会馆:其一,会馆的出现,本身表明国家统制下的城市工商业是向全国开放的,城市居民并不具有本城工商业经营的专有权。管理城市的当地官府,并不阻止外来商人进城,而是容许外地商人来本城从事工商业。其二,会馆不是直接的政治组织,但有互济互助的社会性功能,有保护同乡商人的政治性功能,因而实际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这一特性在本质上有助于城市乃至国家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其三,官府或官吏有时还通过会馆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会馆因此也有政治上的保护伞,形成一种互利关系。有些会馆还是由工商业者和封建官僚共同建立的,因而具有极强的封建依附性。其四,会馆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势力,但只有遇上某种政治气候,才有可能转化为反官府力量,威胁封建秩序。
中国城市行会的出现,大致开始于唐宋时期。明清行会已普遍存在。与西欧无大差异,行会产生最初也是为了保护本行业人员利益,传授生产技术,维持对本行业的垄断权等。中国行会产生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那就是为了抵制牙行的敲诈勒索。牙商本是掮客、经纪人,牙行多依仗官府势力,甚至就是官府设立的。充当牙人的多是恶霸流氓无赖之徒,越到后来越欺行霸市。工商业者苦不堪言,自行组织起行会与之斗争。与西欧不同,中国城市行会没有政治上的自治权,更没有成为城市中的基层行政单位。但它既然有社会协调和经济调节功能,其存在无疑也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封建晚期的所谓“市民运动”,有的就是行会出面组织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政治极度成熟的社会里,行会在政治方面潜在的积极性作用总是被抑制,而其保守性却越到晚期越明显,并且越来越傍上了封建官府,依靠封建政治力量来扑杀新生因素和对立因素。如当内部违规事件频繁发生时,行会便试图通过官府,用行政命令手段来“重申”前规,并把行规刻在石碑上。[13] (P240—242)又如,行东与帮工之间的劳资纠纷时有发生,行东们“东家帮”与雇工们“西家帮”之间的对立也颇为常见。这时,行会又成了行东勾结官府镇压工人的一种组织。所以,要把行会看成一种能对封建体系产生冲击力的社会力量,那是不恰当的。虽然西欧行会也有许多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封建因素,但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城市行会不但也有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统治势力所利用,单用“顽固守旧”不足以说明它的落后性。
上述问题,实际上都论及了城市在封建体系中的政治定位。可否这样说,西欧中世纪城市是在与封建阶级对立的态势中产生的,虽然它不可能与封建主完全脱离关系,甚至它还和国王建立联盟,但大部分自治城市独立性强,政治经济生活有很高的自主权。城市作为市民共同体的凝聚体,行会作为市民行业共同体的代表,将这种自主权发挥到了极大程度。在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还孕育了近代政治机制。[14] 因此,虽然我们不一定赞成中世纪西欧城市是“体制外权力中心”[15] 的说法,但把它们看成基本对封建体系具有离心力的独立政治单位,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因此它们也就最有可能成为冲击封建体系的社会力量。相反,中国封建城市无论其起源和发展,还是其建设和管理,都和统治者的意志相关,它们是封建政治体系中的主要堡垒。即使在晚期城市中形成的主要民众组织,也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演变为统治者的工具。这样,也就不要指望城市能具备率先挣脱封建网络的力量了。
标签:西欧中世纪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封建时代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世纪论文; 经济学论文; 手工业论文; 工商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