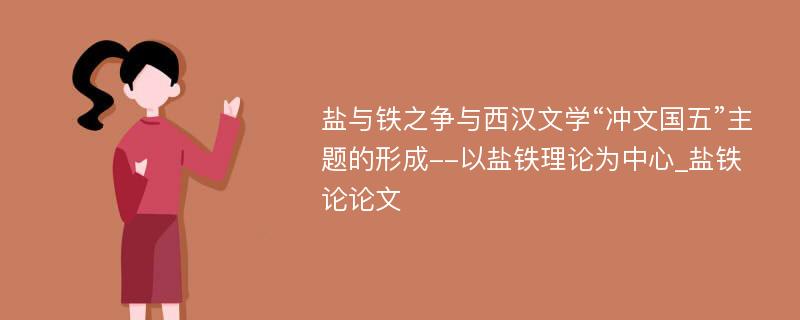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文论文,西汉论文,主题论文,中心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39-08
一、盐铁论争前西汉文学“过秦”主题的基本走向
梁启超在总论我国春秋以前学术的重史传统时曾指出:“吾中华……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1](P10)重经验、重先例的文化传统在西汉文学中得到充分继承发扬。借重前代历史以古证今,以古讽今。成为西汉政论散文乃至辞赋的重要特色。
自陆贾应汉高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汉书·陆贾传》)之命作《新语》肇“过秦”之端,贾谊著《过秦论》、贾山作《至言》振其波流,汉代文学就涌动着一股“过秦”的社会批判思潮。士人们纷纷借剖析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建构提供理论依据,形成了治国为政当施仁义的思想共识①,对汉初统治者革除秦朝暴政、推行休息养民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
武帝承文景之治,从元光二年(前133)于马邑诱伏单于、与匈奴绝和亲开始,师旅连出,尽管获得匈奴远遁漠北、通西域、平两越、开西南夷、消除边患的显赫成就,但也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的巨大代价。为筹集巨额军费与奢侈享乐费用,武帝时期实施了盐铁专卖、平准、均输、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并为维护这些经济政策的推行,任用酷吏,刑法苛繁,致使武帝在位后期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危机四伏。当此之时,士人们继踵陆贾、贾谊,继续借“过秦”以抨击时政。如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严安《上书言世务》借批判秦皇征匈奴导致天下畔秦,谏止武帝征伐匈奴、拓土开边;董仲舒《又言限民名田》借批评秦朝经济政策导致社会贫富悬殊、百姓赋税徭役过重,劝导武帝“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2](《食货志》,P1137);司马相如《哀二世赋》借指责秦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3](《司马相如列传》,P3055),讽谏武帝以秦为鉴,持身谨慎,信用忠臣,以稳固政权。但由于武帝统治下西汉国势空前强大,受时代感召,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作家多偏重润色鸿业;加以武帝晚年刑法苛严,尽管士人们对当时政治弊端有认识,但缺乏大胆激烈的批判。因此,“过秦”主题虽在这时期得到延续,但表现多委婉,居于末流。
然而,危机毕竟不能用颂声平复。其实汉武帝本人也意识到危机,意识到转变治国方略的必要性。《资治通鉴》载武帝对卫青语:“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4](P726)如果说司马光所记未见载于《史记》《汉书》,其真实性可能令人怀疑的话,那么,玉门市花海柴墩子南墩采集简牍中发现了记载武帝临终前诏太子的木觚书②,就无可置疑。木觚书云:“腃(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腃(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谞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侅(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腃(朕)言,众(终)身毋久(疚)。”(简1448)[5](P31)诏中告诫太子(即汉昭帝)以秦二世胡亥为诫,善待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聚士,反映了武帝临终前对过往所为的反省。这则木觚书与《资治通鉴》所记精神一致,足见武帝晚年已意识到在兴师征伐之后,当行修文偃武之政。他在征和四年(前89)轮台诏中还深陈既往之悔,由此不复出军,封车千秋为富民侯,以示休息养民。虽然武帝晚年的自省并不彻底,却给了朝野士人对其统治方略批判反思以有益启示。
后元二年(前87),武帝驾崩,年始八岁的昭帝即位。在社会矛盾尖锐、政治面临危机,辅政大臣霍光与桑弘羊等在对继续武帝战时政策还是执行武帝轮台诏精神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盐铁会议顺势召开。在反思历史问题、为建构新时期的为政思想出谋划策之际,盐铁会议上的士人们不仅仅承汉初“过秦”余绪,更多批判现实,深刻反思武帝政治得失,由此深化并拓展了陆贾、贾谊以来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
二、盐铁论争“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及其表现
据《汉书·昭帝纪》,昭帝始元五年(前82)六月令三辅、太常和各郡国举贤良、文学,始元六年(前81)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应劭注云:“武帝时,以国用不足,县官悉自卖盐铁,酤酒。昭帝务本抑末,不与天下争利,故罢之。”[2](P223)又《汉书·田千秋传》:“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颜师古注云:“议罢盐铁之官,令百姓皆得煮盐铸铁,因总论政治得失也。”[2](P2886)由这些记载与注释,可见盐铁会议是以经济问题为中心议题,总论武帝时的政治得失;会议发起初衷是了解民生疾苦,最终目标则是平稳渡过危机,稳定西汉政权。与会者有朝廷的“有司”,即《盐铁论》记载的丞相、御史及其属官;有全国各地荐举来的贤良、文学之士。根据《盐铁论·杂论》,盐铁会上“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6](P613),足见这次会议规模之大,参加者来源范围之广,会上士人们都能畅所欲言。正因盐铁会议实际是总论政治得失,故除讨论了经济这一中心问题外,还涉及了武帝时期的军事、刑法、人事、文化思想、社会风俗等各方面问题。会上,贤良、文学不仅借批判秦朝政治影射武帝政策之失,还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多欲扰民政治,更多是直接批评武帝时政,体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汉初至武帝时期文学的“过秦”主题由此获得了延续与深化,促使西汉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
参加盐铁会议的士人们在反思历史时,将“过秦”、“崇文”、“过武”结合在一起,既有历史的哲思,更有现实的审视。根据《盐铁论》的记载,当时朝野士人均继承了荀子“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7](《性恶篇》,P440)、陆贾“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8](《术事》,P37)的历史批判精神,强调批判历史,服务现实。如桑弘羊提出,“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盐铁论·论菑》)、“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盐铁论·诏圣》);文学也认为“言远必考之迩”(《盐铁论·论菑》)。在具体论辩中,他们也重视将“言古”、“道古”与“合之近”、“考之今”结合起来,既有“过秦”,也有“崇文”,还有“过武”,从而将西汉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过秦”方面,贤良、文学批判了秦朝的经济、军事、刑法失误。这在《盐铁论·非鞅篇》有集中表现。本篇中,文学针对御史大夫桑弘羊颂扬商鞅“内立法度,严刑罚”、“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使秦“卒并六国而成帝业”的功绩,剖析了自秦孝公任用商鞅以来,秦在刑法、经济、军事方面的政策失误,并尖锐指出:“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6](P96),不独否定商鞅,更是否定秦严刑峻法、横征赋敛、与民争利、穷兵黩武的暴政。此外,如文学在《复古》中揭露秦竭天下之财力出击胡、越乃是为满足“一夫之任”;在《园池》中抨击秦统治者“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在《褒贤》中批判秦尚刑法、崇武力,任用赵高、蒙恬,导致“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在《论诽》中揭示秦崇尚刑法霸道,任用小人,堵塞儒墨等贤士仕进之途与进谏之口,终招致灭亡之祸;在《诏圣》中批判秦二世暴政使“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指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贤良在《备胡》中认为秦亡是因“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这些都是借“过秦”反思武帝时政。其中对秦举天下之力击胡、越的批判尤多,体现了士人们对连年战争的厌倦与反对;而贤良、文学对秦刑法苛严、赋敛徭役过重、用人任刑法而弃儒墨等弊政的抨击,也表达了昭帝时期士人对推行仁政、任用贤臣的清明政治的急切呼唤。
在盐铁会议前,杜延年曾多次劝霍光“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汉书·杜延年传》)。其实,在当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天下疲弊的情况下,“修孝文时政”并非只是杜延年的个人提议,而是昭帝时期士人解决社会矛盾的集体构想。这在盐铁论争中有充分体现。为证明以宽政革除武帝弊政的合理性,文学、贤良除重视远颂周德之外,还注意“考之迩”,将文、景时期无为政治与武帝时期有为政治进行比较,形成了“崇文过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在《盐铁论·国疾》有较突出反映。本篇中,贤良针对桑弘羊提出的“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弥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的困惑,指出:
窃以所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赢,止则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大臣正而无欲,执政宽而不苛;故黎民宁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义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夏兰之属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杀,残吏萌起,扰乱良民。当此之时,百姓不保其首领,豪富莫必其族姓。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诛灭残贼,以杀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责,然居民肆然复安。然其祸累世不复,疮痍至今未息。[6](P334)。
在此,贤良描述了文景之治下本修民富、崇文修德、政宽臣贤、世风敦朴的社会图景,与武帝建元之后与民争利、任用酷吏、严刑妄杀以至“其祸累世不复,疮痍至今未息”的政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深刻揭示了世风敦朴还是败坏、国家富足还是贫敝,与统治者是修本富民还是严急征民、是政宽臣贤还是政苛吏酷有直接联系。另外,《盐铁论》里,如《非鞅》中,文学将文帝时无盐、铁专卖政策而民富,武帝时有之而百姓困乏进行对比,突出了盐铁专卖政策困乏百姓的弊端。《未通》中,文学还将伐胡、越前后的社会状况进行对比,颂扬了文、景时期轻徭薄赋、百姓富足的社会政治,否定了武帝征伐胡、越的军事措施。《结和》中,文学还将汉初与匈奴和亲时无胡、越之患,国富民安的社会景况。与武帝绝和亲后“退文任武,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发屯乘城,挽辇而赡之”的社会状况进行对比,批判了武帝绝和亲、兴师扰民、立朔方等郡的政策。贤良、文学对文帝时政的肯定,与他们“过秦”、“过武”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这些批判不乏偏颇,并且期待复归文帝时政,乃是在历史批判前提下、在重经验重教训的历史思维下得出的不乏天真的结论,但都体现了昭帝时期士人对如何调整统治方略以渡过社会政治危机的深沉思考。
在“考之今”的社会批判思想指导下,盐铁论争中的士人不只“过秦”、“崇文”,更致力于“过武”,全面反思武帝时政,为当时社会政治提供思想方略。《盐铁论》中《本议》《力耕》《通有》《错币》《禁耕》《园池》《轻重》《未通》《水旱》《取下》等篇都较集中反思了武帝的战时经济政策。如《本议》开篇即载文学语: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6](P1)
文学在此本着儒家崇本抑末、崇尚仁义的思想,否定了武帝时期实施的盐铁专卖、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导致百姓舍本逐末,直接造成了世风衰败,宜予革除;并针对桑弘羊以盐铁、酒榷、均输等政策是为助边费的解释,认为“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6](P2)。由此可见,当时士人已意识到合理的经济政策对社会稳定、军事活动、文化建设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对而言,由于自身经济状况的原因,贤良、文学更能感受到经济弊政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痛苦。如《本议》中文学就针对大夫“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的辩白,指出了均输、平准政策在具体实施的弊端:
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6](P4-5)
应该说,在当时主要以实物缴纳赋税情况下,均输政策正如桑弘羊所解释:“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盐铁路·本议》),主要是为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节省货运费用;平准亦如桑弘羊所说:“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盐铁路·本议》)是通过官府财力平抑物价的措施。在货币制度稳定的情况下,这两项经济调控措施无疑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官商一体、官商勾结、信息获取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里,其对普通百姓而言,只能再加一层盘剥。故文学对这项措施弊端的揭露,可谓鞭辟入里。又如《水旱》篇,贤良抨击盐铁专卖政策的弊端时云:
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6](P430)
官府统一盐、铁冶炼铸造,固可以在增加国库收入、助边费及其他开销的同时,集中国力优势提高盐、铁质量,平抑物价,但在官府凭借权力优势垄断市场、缺乏竞争机制情况下,也势必造成贤良所揭露的盐、铁价格与质量相悖、购买不便、硬性摊派、致使农民“木耕手耨,土耰淡食”,经济负担与更徭加重,极大损害农民经济利益与生产积极性的严重问题。《禁耕》中,文学还批评盐铁官营政策下,由官方铸造的铁器未能因地制宜,致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为保证盐铁生产、运输,官府还“发征无限”,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这些都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贤良、文学还揭露了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具体实施时,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利用权力“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盐铁论·刺权》),侵吞社会财富,导致当时社会苦乐不均、贫富悬殊:
夫高堂邃宇、广厦洞房者,不知专屋狭庐、上漏下湿者之也。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也。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窜头宅者之役也。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纨蹑韦、搏粱啮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之苦也。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檐步行者之劳也。匡床旃席、侍御满侧者,不知负辂挽船、登高绝流者之难也。衣轻暖、被美裘、处温室、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孙保之者,不知老母之顦顇、匹妇之悲恨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者之死也。[6](P462-463)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等级社会中在上位者取下无量造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社会贫富悬殊巨大,百姓不仅遭受直接经济剥削,而且还遭受劳力剥削,家室离散、生命朝不保夕的黑暗现实。这些批判均可谓实录,切中时弊,无可辩驳,以至当时的公卿听后都不能不为之愀然无语。
武帝时开始实施的盐铁专卖等经济政策所获收入,有相当部分是为支持频繁的对外战争与边备。因此,这时期的军事政策也成为盐铁论争中被诟病的焦点。这在《盐铁论》中《本议》《复古》《刺复》《轻重》《未通》《地广》《备胡》《击之》《诛秦》《结和》《西域》《和亲》《繇役》等篇均有体现。如《地广》载文学语:
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瑜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律;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6](P208-209)
在此,文学抨击了战争对百姓生命的摧残,以及武帝四处征伐、拓土开边耗费巨大,致使国库空虚、天下疲弊的过失。值得一提的是,文学此处批评可谓与司马迁《史记·平准书》“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3](P1421)的记载前后相承,由此可见,对武帝征伐扩张政策弊端的认识乃武、昭时期士人所共有。相对而言,昭帝时期士人对此批判更加具体而沉重。如《备胡》中,贤良剖析了匈奴所在地形与作战特点,认为征伐匈奴对国家有害无利,进而揭露了武帝征伐胡、越不只耗费财力,而且兵役繁重,给百姓带来了“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6](P446)的巨大痛苦。其中还征引《诗经·小雅·采薇》末章,借助经典,否定了无视人类生命价值的战争,极其有力而感人,以至于主张继续征伐的桑弘羊“默然不对”。
除抨击武帝时期的经济、军事政策失误外,盐铁会上,贤良、文学还对武帝时期的刑法制度给予了猛烈批判。如前引《国疾》贤良之论,就批判了武帝时期的张汤、杜周、夏兰、王温舒等酷吏妄杀扰民的罪行,表达了对酷吏政治的痛恨。此外,《论诽》《刑德》《周秦》《诏圣》等篇均从不同角度抨击了武帝时期的刑法制度。如《刑德》中文学指出:
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6](P566-567)
文学在此尖锐抨击了武帝时期律法繁多、量刑过重、用刑随意。这在《汉书·刑法志》的记载中亦可得到印证:“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3](P1101)两相对比,不难发现《汉书》这段记载对《盐铁论》有所继承。由此也可见文学批评切中武帝刑法之弊。《周秦》中,文学还指出武帝设“首匿相坐”之法,导致骨肉疏远、犯罪者多;《诏圣》中,文学还以御马为喻,批判严刑治民如拙夫御马,无益于治,并援引春秋梁国灭亡的历史教训说明“梁氏内溃,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棰,罢民不畏刑法”,揭示了在社会危机情况下施行严刑峻罚只能自招灭亡的道理。
盐铁会上,文学、贤良还对武帝时期的用人制度进行较多批判。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汲郑列传》),他独尊儒术,实质上是利用儒学强调君尊臣卑的等级思想维护皇权独尊,并利用儒术缘饰其多欲政治,这就势必造成其用人上向服务于其军事、经济、刑法等政策推行的人才倾斜,而将儒臣边沿化,变成其缘饰政治的工具。因此,武帝的用人问题也成了盐铁会上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如《刺复》中,御史以武帝任用公孙弘、褚泰、徐偃等儒者但“无益于治”、“流俗不改”为证,说明并非武帝不用贤,而是儒者非贤。针对御史观点,文学驳斥道: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劫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成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6](P132)
这段话深刻揭露了武帝用人是以服务其征发四夷军事策略为中心的。在这一用人思想指导下,尽管他任用公孙弘,但他更重用权谋之士、奋击之士、兴利之臣、酷吏之徒,甚至还卖官鬻爵。在文学看来,这样的用人制度直接导致了当时吏道杂、政治惨刻而少仁义的弊端。文学还抨击道:“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认为武帝任用酷吏乃贤愚倒置。贤良还在《除狭》中揭露:“今吏道杂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这些批评,与司马迁《史记·平准书》记载的“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这些情况,可以补充印证。而贤良、文学的批判则更集中、更深刻地剖析了武帝吏道杂的政治根源。
此外,盐铁会上还批判了当时的世风衰败问题。《盐铁论·散不足》中的贤良就通过大量古今对比,揭示了武帝统治下“士大夫务于权利,怠于礼义”,导致整个社会世风日下,形成了贪图享乐、追逐声色玩好与口服耳目之欲、越礼逾制、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并总论道:“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财用之蠹也。衣服靡丽,布帛之蠹也。狗马食人之食,五谷之蠹也。口腹从恣,鱼肉之蠹也。用费不节,府库之蠹也。漏积不禁,田野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堕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故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目修于五色,耳营于五音,体极轻薄,口极甘脆,功积于无用,财尽于不急,口腹不可为多。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6](P356)这就深刻指出了在当时社会享乐之风影响下,各种奢靡行为已造成了巨大浪费,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对国家政治有严重危害性。
在此需指出的是,贤良、文学的“过武”,批判的主要是汉武帝的战时政策,而对武帝晚年欲转换治国方略的思想则给予肯定。这体现在《地广》载文学语中:“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由此可见,盐铁论争中的在野士人对武帝政治并非简单批判否定,体现出了甄别扬弃的可贵批判精神。
由盐铁论争中贤良、文学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不难发现,他们的“过秦”、“崇文”实际是为“过武”服务的。然而,批判只是过程,最终目的在于全面揭示现实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为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建构提供谋略。正是在由“过秦”走向“崇文过武”的社会批判历程中,昭帝时期士人从本朝历史中找到了推崇和批判的目标,不仅体现出了敢于反思当世历史的勇气,而且也体现出了建构新时期统治方略的信心。
三、“崇文过武”批判主题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盐铁论争中形成的“崇文过武”的社会批判主题对此后的西汉文学影响深远,并远及东汉。这一主题对汉代政论散文的影响尤为显著。
首先体现在直接促成了《盐铁论》这部著作的产生。据桓宽在《杂论》中借客之口所作的追忆,当时与会的贤良、文学等在朝廷上“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6](P613-614)。可见桓宽对盐铁会议中的贤良、文学在朝堂上针砭时政、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极为倾慕,因而根据会议的议文及曾与会的同乡朱子伯的转述,编撰成《盐铁论》六十篇。班固还在《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中称桓宽著此书是“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由此可见,《盐铁论》还继承了盐铁论争借“崇文过武”考察历史经验教训以服务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
其次体现在深刻影响了汉代政论散文的批判内容与批判精神。盐铁会议后的政论散文作家在作品中,有的批判武帝经济政策,主张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如萧望之任御史大夫时就根据其属官徐宫所言指出:“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2](《食货志》,P1141)借武帝时增海租、垄断渔业经营遭到灾异警示,反对宣帝从耿寿昌之议增海租,与渔民争利。又如贡禹《上书言得失》:“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2](《贡禹传》,P3075),抨击了武帝为筹集军费横征口钱,导致贫民“生子辄杀”的人间惨剧。贡禹还上书批判武帝颁行五铢钱以来,“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商贾贩卖货物谋取暴利而不出租税,农民辛苦劳作却承担谷租、稿税,遭受盘剥,致使“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2](《贡禹传》,P3075),从而建议废除货币制度。这显然也受到了盐铁论争中文学抨击武帝时“币数变而民滋伪”、“上好货而下死利”(《盐铁论·错币》)的社会弊端的影响,反对武帝以来的铸币政策。
有的批判武帝奢侈浪费与对外战争之过。如宣帝即位第二年,下诏议武帝庙号、庙乐,遭到夏侯胜反对:“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2](《夏侯胜传》,P3156)尽管夏侯胜的建议没被接受,并因此下狱,但就宣帝执政崇尚修文偃武、使汉匈关系空前友好的历史看,盐铁论争以来士人们对武帝军事征伐的批判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一定程度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又翼奉《上疏请徙都洛阳》在颂美文帝节俭之后,抨击武帝奢侈,“国家之费当数代之用,非直费财,又乃费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胜数”,由此劝谏元帝在当时“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的情况下宜“怀怵惕而戒万分之一乎”[2](《翼奉传》,P3177)。夏侯胜、翼奉的这些议论,都延续了贤良、文学在盐铁论争中对武帝奢侈享乐、穷兵黩武的批判。而翼奉在“过武”讽今同时劝元帝“因天变而徙都”,则可谓开东汉迁都洛阳思想之先,值得重视。
有的批判武帝刑法过失。如宣帝神爵元年(前61),西羌反,张敞建议令罪人以差入谷赎罪以筹集军费,萧望之、李强作《对两府难入谷赎罪议》驳之:“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强吏民请夺假黄,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诛者过半,然后衰止。愚以为此使死罪赎之败也,故曰不便。”[2](《萧望之传》,P3278)这是借批判武帝入谷赎罪的战时刑法措施流弊,阻止可能发生的军事与刑法失误。
有的批判武帝用人制度,建议整顿吏治。如《汉书·贡禹传》载贡禹奏言,就先颂扬了文帝时期“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壻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获得“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的统治效果,然后批判武帝为追求嗜欲,“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从而任用酷吏镇压百姓,导致“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2](P3077)。这不独是批判武帝时政,更是切中元帝信用宦官、外戚,导致萧望之、刘向等儒臣受压制排挤的用人时弊。又如《后汉书·冯衍传》载冯衍《上疏自陈》借武帝时期董仲舒遭公孙弘嫉妒、李广被卫青排挤的史事,及其先祖冯参在哀帝时被害的遭遇,揭露了古代帝王专制下忠臣常“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9](《冯衍传》,P984)的黑暗政治现实,呼吁统治者珍惜人才。
政论散文之外,汉代辞赋也有表现“崇文过武”主题,这以扬雄、张衡赋为典型。扬雄《羽猎赋序》在表明其创作宗旨时,就批判了汉武帝广开上林苑,穿昆明池、大修宫室,“至羽猎田车戎马器械储俯禁御所营,尚泰奢丽夸诩”的奢侈行为,认为此“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2](《扬雄传》,P3541)。其《长杨赋》则盛赞了文帝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玳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雕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2](《扬雄传》,P3560)一批判一颂扬,形成了鲜明对比。结合《汉书·外戚传》对汉成帝宠妃赵倢妤所居昭阳舍的记载:“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2](P3989),足见扬雄赋“崇文过武”实为讽谏汉成帝沉迷田猎、奢侈浪费。张衡《西京赋》在铺陈西汉历史时批判了西汉帝王的奢侈荒淫,其中特别点出武帝时“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10](P40),营造建章宫。极尽豪华壮丽。赋中还批判了武帝迷信少君、栾大等方士之说企求升仙、同时又大修陵墓的荒唐:“想升龙于鼎湖,岂时俗之足慕?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10](P42)这些批判,也是有感于“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9](《张衡传》,P1897)的时政而发。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作家在反思历史时并非一味崇拜汉文帝、否定汉武帝,如同《盐铁论·地广》中文学肯定武帝轮台诏“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转换治国方略的精神一样,他们在面对新的历史形势时,也对文帝和武帝的功过给予甄别、评价。这以桓谭为代表。桓谭《新论·识通篇》在肯定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后,也批评了文帝“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的弱点[11](P42);对于武帝,他在批判其“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废陈皇后,致卫后忧死,太子死亡,迷信巫蛊,求不死方药,大起宫室,使“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等过失前,也肯定了武帝“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之功,认为其“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11](P42)。桓谭的评价客观公允,尤其指出了文帝逐贤臣、惑于女宠之过,乃发人所未发,不仅体现了他反思历史的独立批判精神,而且代表了东汉建立之初士人们对西汉兴亡历史教训的深沉思考。
总之,昭帝时期的盐铁论争在继承汉初至武帝时期“过秦”的社会批评精神同时,重视反思本朝历史,形成了“崇文过武”的文学批判主题,拓展并深化了汉初以来文学的社会批评主题,对此后的汉代政论散文与辞赋的创作均具有深远影响。本着重经验、重教训的历史反思传统,汉代作家把“过秦”、“崇文”、“过武”作为社会批判的一种重要手段,把矫正当世政治弊端作为其最终目的。也正因其最终目的在于矫正时弊,为现实政治谋出路,因此,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汉代作家往往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近世或当世弊政,体现出热心用世、救危扶倾的社会责任感。这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建设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具有深刻认识价值与启示意义。
注释:
①《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语:“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汉书·贾山传》载贾山《至言》:“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秦)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②此觚发掘报告公布后,学术界已考订为武帝诏书。可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论轮台诏》跋语,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页。
标签:盐铁论论文; 汉朝论文; 文学论文; 西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桑弘羊论文; 武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