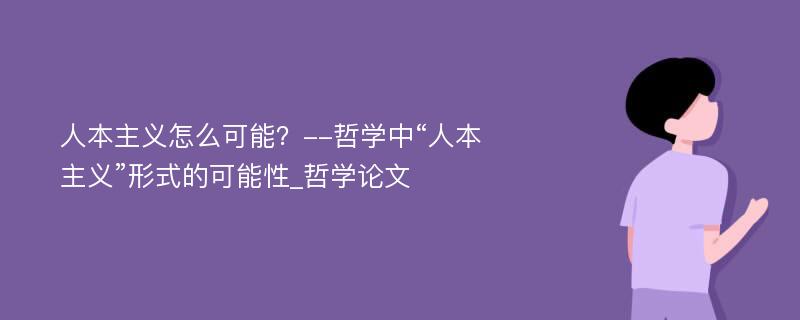
人学何以可能——哲学的“人学”形态之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形态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人学”的确是一个充满疑窦、歧义丛生的名词。因为“人”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有限的客体,只消我们从外部研究就可以了。人是要自己把握自己,并且,人又总是生发着新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我认为,“人学”还是能箾成立的,这里关键在于对“人学”作何理解。我的基本看法是:一个非哲学意义上的“人学”学科是不可能的,一个与“世界”观完全外在的哲学“人学”也是难以成立的,“人学”只能作为哲学发展的一个形态而存在,下面试述理由。
2.东方和西方的古代思想家们早就给人们提出了“认识自己”的任务,然而,直到今天,一个非哲学意义上的独立的“人学”仍未建立起来。经验科学如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等等无疑都是以“人”以及“人事”为研究对象的,但它们都无力对人作总体的把握。把这些学科“综合”为一门“人学”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那不过是“知识总汇”,“人”的“面目”仍然模糊不清。除非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并能转化为哲学(其实哲学单靠经验知识的“概括总结”是达不到的)。正是在哲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宇宙”和“人生”这两个主题的互相缠绕。哲学自古至今都不是单纯的“世界观”或单纯的“人学”,在哲学里面,“世界观”(或“宇宙学”)与“人学”(或“人类学”)总是相辅相成并且彼此渗透。这是中西哲学史所证明了的。
3.在古代和近代,有不少哲学家主张哲学主要应当关注、研究“人”而非“自然”。然而,尽管这些哲学家做了很大努力也很有贡献,却均未能建构出一个相对完备的“哲学人学”。如所周知,西方哲学的早期形态是自然本体论,后来则转向认识论。这是为什么?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如同马克思所说,人来到世上并没有携带镜子,他首先是从自然这个对象中“发现”自己的,而人自身在生理上属于自然,生活资料也取自于自然,所以早期哲学才以“自然”为本体,中国哲学也大致是这样。后来哲学家们意识到了本体论“背后”的认识论根据,社会也迫切需要提高认知能力更有效地改造外部世界,创造财富,这就导致了认识论问题在哲学中的突出。可以说,这时人们对“人”的理解主要是对人作为“认知主体”的理解。到了康德才明确提出从“知”、“情”、“意”这三个层面阐发人的主体性并解决“人是什么”这个最难也最有价值的问题,虽然康德解决得不理想,但他关于“人是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的思想却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因为它将哲学的世界观(或“宇宙学”)内在地导向了人学。后来,黑格尔实际上形成了关于“精神的”、“理性的”人的哲学。费尔巴哈则经由否定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性、神秘性提出了关于“感性的人”的“人本”哲学。诚然,随着马克思对于人的特有生存方式——实践——的揭示,哲学的人学转向才变得清晰起来,而与此同时,“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开始获得实践的从而也是社会历史的理解,马克思由此预言:关于人的科学和关于自然的科学将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
4.预言从提出到实现是需要时间的。本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以“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为中坚的人文主义潮流,科学主义也甚嚣尘上,人及其世界都变得更加支离破碎。有感于此,英国科学家和作家C·P·斯诺疾呼:“文学”和“科学”这“两种文化”都只能是片面的“子文化”,它们必须统一到“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和谐发展”的同一人类文化中来。[①]。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则试图从“文化”出发对人的各种创造和表现形式给予总体的把握,从而建构真正的哲学人学。他说:“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②]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和马克思是一致的,并应当承认是从文化的视界对“人”的整体把握的推进。
5.这里不妨再看看我们的传统哲学。不少学者曾指出,中国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按说,中国传统哲学早该形成关于“完整的人”学说了,其实不然。中国传统哲学看重的是以伦常关系为纽带的群体,这里并没有独立个体的地位。不错,它也讲个体的人,但所讲的是个体的心性修养,是个体在所从属的群体中的名分。这里有“君臣父子”,却没有“人”,充其量也只有一般的“人格”。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血缘宗法社会,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生产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个人缺少独立性,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也缺少深层的分化,所以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总是喜欢把“天”与“人”直接类比、契合,董仲舒不就讲什么“天”“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③]的话么。“人文”与“天文”在中国倒是未出现西方那样的分裂,但这决非充分发展后的整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学和“天”学内容也是如此,不可抬得过高。
6.基于上述简略的考察分析,笔者认为,哲学人学的确立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人的现实实践条件。人的活动要相当全面,人与周围世界形成多方面的、普遍的联系;人的职业和身份规定不是终生不变的,它可以由个人自主选择;二是理论条件,人的各种活动形式和各种关系都得到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理论,因而“人”在各个论域各个层面都被彰显、被观照,对“人”的全方位把握或各视界融合,业已成为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两个条件现在已基本具备,因此笔者认为建立哲学人学已具有现实可能性。换言之,哲学发展的“人学”转向已是顺理成章之事。但笔者要强调指出一点:人的“自然化”、“世界化”和自然、世界的“人化”总是在同时地进行着,因而,哲学人学既不可撇开人的世界这一人的非人格存在形式来把握人这一世界人格存在形式,亦不可能建构关于人的终极性理论模式。如何避免独断论并使理论具有开放性,是人学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注释:
[①]《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②]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③]《春秋繁露·阴阳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