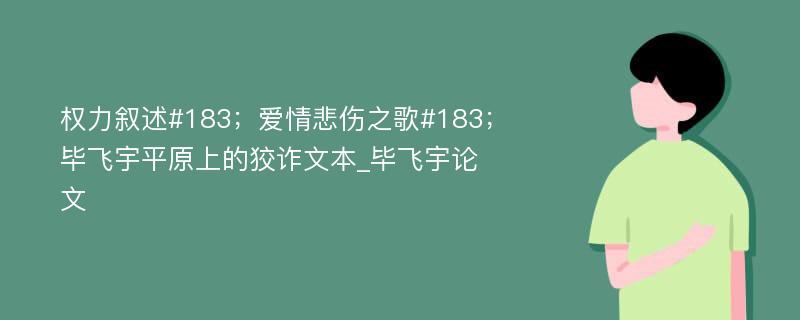
权力叙事#183;情爱悲歌#183;狡黠文本——论毕飞宇的《平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狡黠论文,悲歌论文,情爱论文,平原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7)07—01115—06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平原》,再次以王家庄为背景,为我们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乡村中国的生活画卷。故事虽然发生在王家庄,不过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王连方和玉米一家,而是端方和一群年轻人。小说摹写了乡村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他们的梦想与幻灭、奋斗与挣扎,在既广阔又逼仄的乡村中国的生活舞台上,成功地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阅读这部长篇,我们首先会为其细密的权力叙事而震撼,权力是怎样被建造,怎样被解构,怎样伤害他人,怎样扭曲自身……我们还会被其中五色杂呈的性爱描写所迷惑,从而深刻地认识到,在那个贫瘠的年代,人们原始狂野的性力因为得不到正常的发泄渠道是如何冲撞和毁坏着人性的门墙,从那一曲曲性爱悲歌之中体会到灵魂颤栗般的“疼痛”。同时,我们还会在它冷峻俏泼的小说语言中,感受到反讽的魅力和狡黠的智慧,小说大量的历史语境的戏仿和创造,使得作品在把捉70年代的历史总体性的同时,也拓展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语言向度。
一
和《玉米》一样,小说《平原》关于权力的叙事是最为生动具体、也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围绕着权力的获得、权力的展开和权力的释放,毕飞宇不断探讨着有关伤害的“疼痛”主题。应当说,与《玉米》相比,《平原》对于权力的叙述更具有了层次感和多元视野,也更自觉、更深刻地与历史、政治、文化、伦理、性别等因素交融为一。毫无疑问,毕飞宇在苏北平原构建的王家庄,将和阎连科的具有商落地域色彩的“笆篓世界”一样,因为成功地解析了历史语境下的微观权力网和权力生态,从而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一个独特的文学景观。
《平原》中的权力叙事,随着端方的成长史,实质上给我们展现了生存哲学和斗争哲学的全部奥义。在毕飞宇的叙事历险中,我总感觉存在着两个端方:一个可敬,一个可畏。一个是撑门立户、处变不惊的铁血男儿;一个是工于心计、深谙斗争哲学的铁腕人物。端方虽不是《平原》中最有权力的人,但无疑却是最有权谋的人物形象。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端方的形象站立起来了,但他也逐渐变异为一个施虐狂,一个既有可怕的破坏力量,又极度自卑和软弱的复杂形象。
如果对应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可以将端方的权力斗争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生存权力争夺史、爱情权力争夺史和发展权力争夺史,与此相应,我们分别看到了可敬的端方、复杂的端方和可怕的端方。在生存权力场域中争斗的端方是可爱和可敬的,围绕着家庭日常生活而展开的细密的权力叙事,把一个时常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在我们周围的端方生动地勾画出来。其实,《平原》的权力叙事,从端方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就已开始。端方用自己的一身蛮力气,想要证明自己在乡村中的存在和地位,但不熟农事的他却吃尽了苦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回乡青年,他开始为自己与土地无法脱离的关系而沮丧,诗意般的农村生活并没有给端方带来诗意的享受,而是沉重的压抑和生存的焦虑。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和文化背景下为我们展开了乡村生活的风俗画卷,但这幅画卷里没有和谐,却充满着对立和冲突,充满着苦涩和艰辛,充满着权谋和争斗。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主题,是很多乡土中国小说挥之不去的主题情结,小说家们会在此设置冲突,强化矛盾,会寄托他们对于乡村文明衰落的哀叹和对于城市文明吞噬自然和谐的愤怒。然而,毕飞宇另辟蹊径,他并没有急着去强化这种冲突以获得情节的飞速发展和主题的单性呈现,因为他要遵循人物的命运逻辑,他要看看端方在这样的命运之中,是怎样以他自己的方式来为生存权力挣扎和抗争,因为端方自有端方的办法。端方的办法是什么?那就是从羊变成狼,在素朴和自然的乡村生活中,这是潜在的惟一生存法则。你永远不要忽视乡村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可能其后都关联着一个家族的利益,在这个微观权力结构中,家庭往往是最为基本的一个权力单位,经由家庭,端方和整个乡村社群发生权力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小说为什么着重会在家庭这个层面展开端方对于生存权力的争夺,与继父的冲突、处理大棒子之死、处理网子被打的事件……从个人生存到家庭生存,凡此种种,都是端方对权力的抓取、表达和代言。因为紧紧围绕着农村家庭日常生活冲突展开叙写,《平原》对于端方的权力叙事才显得如此细密真实,而在这些琐屑的日常故事中,端方的沉着镇静、坚韧顽强;端方的处变不惊、心计之深;端方的恩威并施、心狠手辣……一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残酷的生存环境馈赠给他的品格,所以,当其继父王存粮不知不觉将家庭权威让渡到端方手中,当小说借王存粮之口说出“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感喟时,我们完全领略到了作者此时关于端方的权力叙述,是表达着对端方为生存而战斗的赞赏和敬佩之情。
对于权力的反思和批判的蕴涵,则更多表现在小说的中部和后半部分。围绕着端方和三丫的爱的权力的争取和维护,端方的性格也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他告三丫母亲孔素贞搞迷信活动,他威胁前来媒娶三丫的鞋匠房成富,在这些违反人情事理和诚厚心性的极端行为中,人性中的阴损和狠毒虽然借着爱的名义,但也足使我们不寒而栗。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抢救三丫的过程中,为了掩人耳目,端方要把假死当成真死来抢救,然而,假死和真死,最终却有了戏剧性的对转。这一充满矛盾、误解和冲突的情节使得端方的智谋、机巧和可怕的成熟得以生动地呈现。特别是当他明白了三丫的哥哥红旗误拿了汽水瓶是三丫真正的死因时,端方在极度悲痛中,仍然显示了其过人的自制能力,他把两个致命的吊瓶敲碎了丢在河里,从此,三丫的死就成了只有他和赤脚医生兴隆两个人知道的秘密。面对这段关于爱的权力的争斗史,我们很难作出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因为那是事实,那是伤痛本身,那也是偶然的命运。在以往的权力的争夺中,端方已经养成了极为敏锐的自我保护和衡度轻重的本能,所以面对三丫的死亡,端方选择了无声的哀痛,选择了敲碎真实,但这是怎样复杂的哀痛和“敲碎”,因为端方敲碎的不只是爱的幻影,他敲碎了人性的本真,敲碎了善和恶的界限,留下的是一地残酷的现实碎片。在这近乎张爱玲式的“惘惘的威胁”和“苍凉的悲哀”中,我们感受到了毕飞宇对生存哲学的深刻反思。
可以这样来形容《平原》的权力叙事,它像一部拥有诸多复调变奏的交响乐,但每一乐章都有一个主调,正如小说前部的生存主调和小说中部的爱情主调一样,小说后半部分的主调就是对斗争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是对于权力的反思和批判。随着端方在青年群团中权威的建立,他开始释放他的权力了。他的权力逐渐具有了恶魔般的力量,四处挥舞着伤害之剑,不再仅仅具有为着生存的正义感了。小说也由一个创世神话的叙写转入到毁世灾难的记录,端方身上的人性魅力开始演变为恶魔般的符咒,而这个转变的关键,是权力和权力语境的变异——他现在已是乡村民间微观权力结构中的统治者了。所以,当红粉出嫁时,端方就显露了他所拥有的权力的伤害性,他对姐姐红粉的刻意刁难,无形中放大了后母和继女之间的矛盾,让这个复杂家庭的所有成员在大庭广众之下陷入了伦理困境,使母亲无地自容,使红粉肝肠寸断,使王存粮痛彻心肺地啮齿怒叹:养儿如狼,不如养儿如羊!这个与前文对应的巧妙的反转,隐含着作为父亲的对权力崛起者的复杂情感。权力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原先为维护生存的正义摇身一变,成为了伤害的诡诈和狡猾。小说接下来的情节更显示了这一点。如,那段看电影时和高家庄的青年的群殴的描写,就完全展露了端方的智谋和铁腕的权威,端方的权力扩张在这个传奇性的战斗中达到了顶点。正像小说中所说的:某种意义上,这个晚上的电影是为端方一个人放的。端方善于战斗的形象,尤其是智勇双全的形象,在电影散场之后彻底建立起来了。在端方神闲气定的指挥下,王家庄的青年们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而端方则进入了一个领袖般的精神境地。此时,他没有忘记胜利后及时开总结会,总结战略,提醒和敲打不安定份子,体现了高超而可怕的斗争智慧:
端方说:“我在这里要提醒极个别的人,再这样下去,乱发号,乱施令,瞎激动,是要吃苦头的。这样的风气不能长,我们必须统一我们的思想。”[1]
在毕飞宇的笔下,这个农村生活场景中常见的打斗场面,被赋予了深刻的权力内涵。端方通过战斗和巧妙的运用战斗,把自己的权力地位推向顶点,甚至得到了神化,他不但要统治红旗等人的身体,更要统治他们的思想。上世纪70年代社会和文化精神生活中常见的斗争哲学,在小说戏仿的语境中具象化了。历史在这个节点上,一方面得到了艺术的还原,另一方面揭示了某种本质的真实。毫无疑问,《平原》这一独特的权力叙事,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内涵形象地加以了丰富和拓展。端方既深谙权力的获得之道,更精通权力的维护之法,那个特殊年代的斗争哲学和政治幻影,被作者巧妙地融入到端方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之中。难怪有评论家说:毕飞宇的小说就像以文学形式写成的历史论文。
我们不妨来看一段有关端方的心理活动:
红旗、大路等那一干手下倒常常过来,向他作一些汇报,当然还有请示。因为个别的谈话多了,端方意外地发现,他的手下并不团结,相互之间总要说一些坏话,打打小报告什么的。在这样的问题上端方一般都不发表意见,免得有所偏袒。他谁也不偏袒,这就是说,他谁都可以收拾,闲得无聊了,他就拎出一个来,收拾收拾,解解闷。还是蛮好玩的。内部的斗争与教育永远都是必须的,它是长期的,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更加残酷一点。端方就喜欢看着人们人心惶惶的样子,这里面有说不出的快乐……抽个空还是要把佩全拉出来一次,好生修理一顿。前些日子佩全表现可不好了。以为端方能当兵,迟早会离开王家庄的。他看到了希望,有了蠢蠢欲动的苗头,他的身上滋生了复辟的危险性。……这个问题要解决。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年不行大后年。要找点苦头给他吃吃,让他吃够了。[1]
这哪里是端方的心理活动,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内心独白!《平原》的权力叙事,因为端方的奋斗史而具有了历史的象征意韵,毕飞宇或许在以他的艺术直觉,为历史祛魅。因为,从这一乡村微观权力网的文学镜像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宏大历史的真实面影。无论多么复杂的权力网的构建和运行,其实都是源起于这种朴素的斗争哲学。所以,当我们看到端方以极为凶残的手段威逼红旗吃下了猪屎以掩其耳目,彻底从精神上把红旗等变为自己的奴隶的时候,辉煌的奋斗史背后附着上了另一番的血泪史,我们看到了欺压、瞒骗、斗争等各种语言花衫掩饰下的噬人血口。毕飞宇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污辱被损害者的身上。”[2](P86) 显然,毕飞宇对权力的反思和审视已经从压迫者拓展到被压迫者,从身体层面掘进到人性的精神层面,他不是诘问式的批判,而是含着眼泪的悲视。通过端方的权力构造史,作者把其在《玉米》系列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对权力的反思批判引入到历史和文化的深层。
二
如果用严格的爱情文学标准来看待《平原》,这可能是一部看起来不太“纯洁”的爱情文本。因为《平原》中有太多的关于性压抑、性变态、性伤害、性阴谋的描写。《平原》似乎要致力于从这一人性的基点,来展演20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普通百姓生活的幽微叙事。有趣的是,和《玉米》三部曲中对王连方等权力人物的性放纵描写不同,《平原》展现了更多的性压抑和因之而来的各种变形诉求,并把这些模样怪诞的“利比多”原形和人物的性格、命运交织在一起,在最深层的人性本质舞台上,演奏出一曲曲充满原始狂野性力的乡村悲歌。当然,在这曲悲歌之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就是吴蔓玲的性爱悲剧了。权力可以张扬性权力,同时也可能压抑性权力。我们将《平原》和《玉米》联系起来看,王家庄的新旧支书的不同命运在这一主题上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吊诡,“性”是“伤害”的武器,“性”也是“疼痛”的源泉,当然,这一次毕飞宇把“疼痛与伤害”的主题仍然交给了女性来承受。
就性格的层次性和心灵的丰富性来说,吴蔓玲这个人物形象,显然要比端方具备更为丰富的心理内涵,毕飞宇决心要在这个人物身上探究关于女性的所有复杂主题。通过吴蔓玲高处不胜寒的性别困境,作者细致地展开了对女性性别觉醒的过程探讨和前程追问。套用西蒙·波芙娃的女性谶语: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造成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吴蔓玲不是天生的吴支书和铁姑娘,而是被王家庄造就的。一个偶然的机缘,王家庄的王连方支书因为纵欲触及了军婚这个政治高压线(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对转,他的政治身份是其纵欲成功也是纵欲失败的关键符码),于是,作为下乡女知青的吴蔓玲获得了政治身份,成为了王家庄的新支书。而与此同时,她的女性性别特征和性别本能开始在这一刻被一种新的社会角色所压抑和扭曲。她近乎自虐似地劳动,她身先士卒,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一点也不摆领导架子。凡此种种,都是那个年代一个成功女性领袖和女性精英的社会镜像,她们有一个文学共名——“铁姑娘”。然而,毕飞宇显然不会在这个“文革”文学中并不鲜见的女英雄形象面前止步不前,他从女性生理和心理深层,展开了对这类人物的颠覆性描写,揭示了女性性别问题的自反性特征。
和玉米不同,吴蔓玲不需要用身体依附权势的方式来获取社会权力,她在王家庄是说一不二的人,她的一句话能够决定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支书是王家庄女性社会中最具有女性独立主体地位的人,她难道不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辉煌缩影吗?然而,遗憾的是,女性解放的命题,在吴蔓玲身上只完成了社会属性的那一半,而自然属性的另一半却被压抑和放逐了。作为一个女性,她也有对爱情和婚姻的自然人性的渴望,可她的渴望却被她的权力光环所笼罩,被时代的政治文化语境所压抑和掩盖。在王家庄,有哪一个年青人敢配女支书呢?她的政治空间是无比开阔的——“前程无量”;而她的私人生活空间却又是那么的逼仄和压抑——“高处不胜寒”。所以,她在参加闺中密友的婚礼时,在喝醉酒的情况下,终于表露出女性最柔弱的那一面,她甚至开始羡慕那些被婚姻牵着走的、在婚姻中迷失的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了。然而,她是支书,她是政治前途无比光明的人,她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在规约和惩罚着她的身体欲望。如果仅从外部特征来看,吴蔓玲显然具有当代文学中“铁姑娘”这一文学形象的所有特征。“铁姑娘”这一文学镜像,作为70年代文学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女性形象的最高审美范式,她们身上的女性性别特征已经降低为零,只是其政治身份的花边点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文化在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在一个单一的崇尚极权文化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当然是以男性为中心),女性的自然人性必然会被扭曲和遮蔽。作为“铁姑娘”的吴蔓玲并不是天生的,她也有女性的柔情和对爱情的向往,然而正是这些在政治上翻了身并与男子并辔齐行、在新中国“半边天”语境下拥有最大社会平等权力的女性,恰恰成为了女性迷失的牺牲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而荒谬的存在悖论,一个对政治文化的无情反讽。所以,当《平原》的结尾,患了狂犬症的吴蔓玲一口咬向端方的时候,她疯癫的行为正反射着政治文化对自然人性的移重压抑,她也只有在这疯癫的语境中实现着她真实人性的复归。在我看来,吴蔓玲最终这一口的咬啮因是那样深透而悲壮地“咬”到了人性的弱点和文明的软肋,而将成为当代小说中最为难忘的记忆之一。这或许是对“铁姑娘”这一文学范型的一个颠覆性的终结。
《平原》中写得比较光明的是端方和三丫的情爱故事。其实,在端方和三丫这两个当婚当嫁的农村青年男女之间,劳动之余发生些男女情爱故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乡野叙事主题了。所以,在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矫饰和伪装,也没有城市爱情故事的缠绵悱恻,没有太多的铺垫和前奏,他们甚至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在黄昏村边的大堤上,他们如飞蛾扑火,尽情地让身体开始了狂欢的旅程。这质朴、自然、清新的性爱描写,是当代小说中少有的自然乐章,和莫言《红高粱》中充满酒神精神的高粱地野合场景颇为相似,是充满阳刚之气的对自然人性的礼赞和讴歌。然而在短暂的欢会之后,三丫不得不以死来维护自己爱的权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早不允许包办婚姻的70年代,王家庄依然因循着成规和旧礼,小二黑和小芹50年代所受到的爱的磨难,在端方和三丫这里,已经演变为血与火的冲突。所以,当《平原》以一系列宿命般的巧合来完成端方和三丫的情爱悲剧,而不是借助新社会和党的政策来收获一个爱情喜剧的时候,它已经超越了《小二黑结婚》那样一个文本的稚嫩的宣教理念,具有了深邃的历史感和宿命意识。这可以说是对一个老故事的第一次反转。而三丫死后,端方努力回忆,却怎么也回想不起三丫的长相了,当端方在三丫只有身体而没有脸孔的梦魇中惊醒的时候,毕飞宇开始了对自然人性的更深层的追问思考。这里,已触及到一个更隐秘的哲学问题:身体与意识。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强调,身体的感性知觉是一切意识的前提。他提出让“身体—主体”的概念取代传统主体的概念,认为主体“它不是精神,不是灵魂,不是意识,不是思想,而是身体。这个身体—主体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3](P6) 然而,我们发现,许多传统的经典艺术在努力够着虚拟的天国理念和精神幻境的同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记忆。尴尬的是,此时的端方对三丫只有身体记忆,他怎么也想不起三丫的面孔和脸庞,这是对传统爱情故事的一个悖离,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完成了对自身的第二次反转。从它的背后,我们读到了性的压抑和性的诉求,读到了肉身和精神的巨大裂隙,读到了隔绝和遗忘的主题,感受到了存在的荒谬和存在的忧伤。端方解决不了这个高深的哲学问题,所以他到“马列主义者”顾先生那里去寻求答案,顾先生用唯物主义的宣喻,帮助端方做了“彻了底”的解脱,使得其后的行为更有了悲剧性控诉的意味。更为不幸的是,那个年代的总体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它的乐观的蒙昧,豪迈的冲动,悲壮的抗争,压抑和束缚等等,都可以在这个隐喻的镜像中找到其波光粼影。
还有,混世魔王这个人物作为小说中一个恶的语符,也以其独特的方式测量着人性的深度。他的存在和挣扎,同样折射着农村青年极为逼仄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他原本是想通过积极的劳动换取人民的信任,争取离开农村返回城市,然而当他的希望破灭时,他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以慵懒颓废的生活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命运不公的愤怒。从此,他变为乡村生活场景中的边缘人和局外人。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个荒诞的缩影。现在他可以当兵入伍了,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惟一出路。为了争夺王家庄这一宝贵的名额,他以极为阴损的方式来夺取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强奸了能决定他命运的吴支书。他深谙人性的弱点,所以他在公社广播站的扩音器前对吴支书的性侵犯,就具有了多重复杂的内涵。消解权威,颠覆政治,原来可以用这样赤裸而罪恶的方式;那个象征着无所不在的权威政治的广播,原来并不是无所畏惧的。广播和广播站,把持话语权力的麦克风,是舆论和政治威权的象征,是一个时代的形象隐喻,但真是成也由之,败也由之,王支书、吴支书们平日里通过它传达政令,显示威权;王支书、吴支书们也是在它面前显示了自己人性的弱点。所以从《玉米》到《平原》,我们看到了在“巨大”麦克风下的充满戏剧性的情节逆转。如果说在《玉米》中,这一幕是作为喜剧上演的话,在《平原》中,这一幕却具有了悲剧性的意味:混世魔王经由此堕入了性罪恶和性无能的深渊,而吴蔓玲却在失贞的痛苦中,不经意间体察到自身巨大的性缺憾,在愈加剧烈的充满悲剧色彩的身体觉醒和自我压抑的矛盾痛苦中,走向了最后的疯癫。毫无疑问,由混世魔王展开的性阴谋、性罪恶和性痛苦,是《平原》里这曲性爱悲歌中最为低沉芜杂的复调变奏。
此外,《平原》中关于老骆驼的性变态、房成富的性欲望、老鱼叉的性征服、“马列主义者”顾先生的性迷失……这些离奇古怪的性欲诉求,却恰恰揭示了那个贫瘠的年代人性的扭曲和迷失。《平原》没有为这些超离了人性门槛的行为去有意辩护,但的确,我们通过这些王家庄的边缘人物的边缘行为,听到的是人性招致扭曲的悲怨之声,触摸到的是人性碎裂之后尖锐寒冷的锋刃。
三
毕飞宇的小说语言向来是富有个性特征的。他不像某些先锋作家那样故意在叙述语言上显奇弄怪,他的小说叙事总是追求一种明白晓畅的阅读效果,然而在质朴的本色语言背后,却闪动着智慧的甚至有些狡黠的灵光。这一特征在《平原》狡黠智慧的反讽修辞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格非认为:反讽这一叙事方式对读者的引导,实际上是一种作者与读者的秘密交流和共谋。作家总是根据其自身的气质修养,对存在的体验以及不同的作品加以选择。“只有一种方式对叙事构成了损害,那就是作者未经改造的爱与恨在作品中公然露面。”[4](P35) 显然,格非在这里是不太赞赏那种直接“爱”或者直接“恨”的叙事的,他强调作者的创造意义。生活本来如此,作家何为?小说何为?为此,先锋作家们的叙事立场自然要寻求一个书写的策略性转向——转向语言本身。当代先锋小说的这一语言转向确实为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拓开了新的天地,在这个转向之中我们也发现,反讽是他们最为喜欢运用的“叙事圈套”之一。当然,我无意在此将毕飞宇定位于“先锋”,但在毕飞宇的《平原》中,确实能够读到与众不同的反讽叙事。
我们来看小说描写三丫死后端方深陷痛苦而顾先生为其开解的一段描述:
顾先生有些难过,说:“你还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眼泪。眼泪是很可耻。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会害怕,我们无所畏惧。”……端方还注意到顾先生说话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就是他从来不说我,而说我们。这样一来就不是顾先生在说话了,他只是一个代表。他代表了一个整体,有千人、万人、千万人,众志成城了,有了大合唱的气魄。这气魄就成了一个背景与底子,坚固了。端方仔细地望着顾先生,这刻儿顾先生坐得很正,面无表情。端方意外地发现,这个晚上的顾先生特别的硬,在月光的下面,他像一把椅子,是木头做的,是铁打的。顾先生的身上洋溢着一种刀枪不入的气质。端方相信,他自己在顾先生的眼里肯定也不是端方了,同样是一把椅子,是木头做的,是铁打的,面对面,放在了一起。是两把空椅子,里面坐着无所畏惧。
端方突然意识到,彻底的唯物主义真的好。好就好在彻底二字。都彻了底了。
这一大段的描写本为了解决端方的失爱之痛,然而由于创造性地将顾先生的哲理宣讲和端方的个人感受糅合起来,因而出现了含混复杂的反讽修辞效果。唯物主义哲学观是怎样将人物化,人类的情感是怎样被“彻了底”地抽空,在“马列主义”的化身顾先生的思维逻辑中得到了惊人的展现。换言之,上世纪中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就是如此改造着个体精神的独立性,如此删削着个人情感而将之纳入到抽象的社会主义的金光(精光)大道中的吗?可以说,这种源起于王朔的政治反讽修辞策略在《平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知道,王朔最主要的反讽修辞策略就是将革命的、崇高的政治“大”语汇挪用到个人琐屑的“小”生活之中,在“大”与“小”的强烈的对比中轰毁一切神圣和崇高的价值体系。因为其破坏的欲望是如此强烈,范围是如此广阔,嘲笑是那样的尖刻,因此招来“痞子文学”的讥评。而毕飞宇在《平原》中的价值消解立场的选择显然是具有历史本质主义的用意,他自觉地将个人命运和历史命运放在一起考量,因此他的反讽叙述祛除了王朔的痞子气息,而具有了一种新的历史理性高度。
从众多的语例段落中(恕不一一列举),我们还可以发现,毕飞宇的反讽策略是把普通人的生命感受和宏大的国家主义话语叙述杂糅并呈,从而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百姓经典生活场景之间出现了语义的变动和能指的滑行。在这里,反讽的语义重心并不再是对伟人事功和正典意义的消解,而是从凡人百姓的心理感受角度揭示那个统整众一、消泯个性的“时代病”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奴性是如此地深隐,又如此地自然,它已经被“钉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理解毕飞宇的反讽叙事,我们就能在更加具体地了解那个时代的同时,也会获得更加深刻的批评深度。朱大可对反讽修辞的功能有这样的体会:反讽(Irony)是对国家主义话语的解构和终结。它解放了被象征所压抑的他者,并把主体从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因之,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平原》中的反讽叙事解放了我们的批判力和自省力,它促使我们反思历史、反思自身、反思当下。
王小波在《文明与反讽》中说: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而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如果说文学应该有什么使命的话。显然,王小波认为反讽修辞能带来文学趣味,我们可能不会完全赞同王小波的趣味主义文学立场,因为趣味主义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油滑的泥潭,但我们决不喜欢枯燥干瘪、味同嚼蜡的文学叙事。可喜的是,《平原》的反讽叙事是祛除了油滑的,是反思性的反讽;而不是搞笑式的反讽,是具有新历史主义品格的智慧的反思文学,而不是搞笑的俗众文本。这一修辞策略和毕飞宇一向坚持的“疼痛”文学主题并不龃龉,因为在这对传统和历史的撕裂行为背后,有着作家对人类历史命运的严肃思考。在挖空心思追逐眼球的当下文坛,有许多所谓新锐作家都能轻松地“脱下裤子对着父辈撒野”,并以此作为他们的文化反抗姿态,来博取先锋的美名和美圆的青睐,而他们作品形式上的无比尖锐和语义上的无比轻飘,却又构成了对自身的反讽。此种文学态度是作为人类的精神史、心灵史的文学的“不能承受之轻”,是应当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的。
经由毕飞宇的系列作品,我们知道了苏北平原上有一个王家庄。据说,现在有些读者想去江苏兴化寻访这个生动的文学世界了。这让我们想起了美国作家福克纳在他的文学经典中创造的美国南部小镇约克那法郡,如今那里已是游人如织。而王家庄,地球上的王家庄,我们能作相同的期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