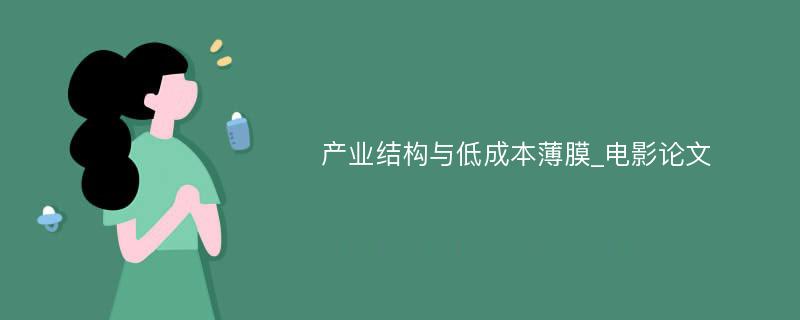
产业架构与中低成本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低成本论文,架构论文,产业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片”救市与产业的整体架构
最近华语电影界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出现了所谓的“大片”,这是一种泛亚洲或者说是泛华语圈的现象。这种制作已经跨越了中国内地的制作圈,开始跨整个华语圈,甚至介入了亚洲、美国以及西方世界的一些制作力量。这种大片实际上已经把中小成本电影挤压到了一个令人悲观的空间,而这一现象影响的不只是内地,对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影响也非常大。拿成龙的《神话》来说,这部影片在香港地区收入是1000万,而在内地就是1亿。以这个倍数来考量,制作者必然会把其制作重心转移到内地,就像台湾地区早年所经历的状况一样。过去每天都会有很多港星拼命到台湾来做宣传,不停上电视,不停抢票房。但是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没有票房了,大家说你们台湾没电影了?其实不是这样,台湾还有电影,只不过就是这种大片挤压了中小成本电影生存的空间,以致最终做坏了整个市场。
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台湾电影产业的低迷”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问我,我觉得其中原因有很多,而最严重的是台湾当局犯的错误——在对外贸易谈判中取消了对于台湾电影的保护措施,在1993年将台湾电影牺牲了,让好莱坞电影长驱直入,彻底打开了台湾电影市场的大门。在台湾有接近700块银幕,好莱坞一个电影进来就可以进100多个拷贝,那么就吃掉了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银幕。由此,台湾电影的空间就挤压得越来越小,跟这边的状况一样——一般低成本电影或者独立成本电影,包括香港电影要上院线就非常困难。然而,台湾当局有没有做事?也有。前段时间吕秀莲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要建立台湾的电影产业园区,要强力推动台湾电影,这对于我们是一件好事,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她能不能做完这个任期,但是有希望。只要当局强力推动并认为电影是重要的产业,这个产业就一定能做起来,台湾目前的市场状况就会有转变;另外台湾电影市场的困境还有社会原因,台湾有线电视的占有率为90%以上,几乎是世界第一或第二。每一个普通家庭都可以收到100多个电视频道,节目五花八门。其中,有五六个电影频道是全天候的电影放映,专业化程度很高,有专门放港片的,也有专门放好莱坞电影的,以前还有法国电影频道。你坐在家里面就像置身天堂一样,不用出门看电影,可是这样自然对本土电影产业是有伤害的。台湾有线电视的普及率高,加之电视中政论节目多,精彩的程度远超过连续剧、惊悚剧,连贾樟柯到台湾来时也说你们台湾政论节目太好看了,怪不得大家根本不爱看电影。总之,台湾社会替代性的娱乐方式很多,电影不是唯一。也因此,台湾电影市场的低迷也与社会整体情况有关系。
上个月台湾电影新闻局电影处找我们开了一个会,目的在如何拯救台湾电影产业。会上有人提出要学内地,做几个大成本制作,并且还规划了好几部,都是几亿新台币的投资,认为这样台湾电影就起来了。我当时就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一部大片能不能救中国电影产业呢?从《卧虎藏龙》、《十面埋伏》到《英雄》、《无极》乃至《夜宴》,无不采取了同样的大片模式,这些影片均获得了非常好的产业成绩,证明了“大片”的确有创造中国电影观众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潜在市场的存在,这对于西方世界是非常振奋的,我也非常高兴,但是它跟电影市场的关系是值得更多商榷的。就台湾而言,虽然台湾人口仅两千多万,而且集中在台北,但却是目前好莱坞电影的第13大市场,以前是第9大。这个潜在市场是客观存在的,也无需用“大片”去证明,但是你要靠一两部大片来救这个市场,这个我是怀疑的。
我认为电影产业的振兴,政府或企业界应该大量支持中间成本的电影。一个“金字塔”的产业结构,大片总是尖端、是很少数的;“金字塔”最底层的低成本电影不担心其回收,就像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所说的,DV解放了电影。因为DV便宜,普通人就可以用它来做影像,用一点钱就可以完成一部剧情片,不需要太多花费。产业结构中最尖端的以大片形态存在的电影,事实上都有机会找到投资,至于你的大片是用什么样的演员,有什么故事,针对什么市场,找什么样的资金,那基本上不是问题。所以做产业最困难的一定在“金字塔”中间层,而中间层的电影又是产业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值得大家花力气和成本去做的,因为它形成规模和生产节奏。
从产业角度,我认为目前大家都太注重导演了,都是从导演出发,认为这个成本是哪一种导演拍,拍大片还是拍小片。我们一直在探讨韩国电影成功的模式,把它当成一个奇迹,而这种奇迹的产生源于不从导演着手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的四个面去着手的思维方式。韩国电影固然有制作的层面,但是他更注重发行、营销、宣传,还有融资。这是超越导演个体和具体成本的,是韩国政府经过缜密思维后对于产业的整体规划。
韩国电影在振兴之初,远在华人电影的声誉之后。我当时接触了很多西方人,他们都说不看韩国电影,太沉重,都不喜欢。所以,韩国电影要革新。他们深知韩国电影产业内部的人已经不能够改变发展的现状,因此他们请非常多国外的、不管是韩裔或者不是韩裔的电影人到韩国来帮他们做故事、拍电影,吸引各个环节的专业人才。不仅如此,政府还在融资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给企业界提供一些减税的方案和应变的措施,把企业界的资金引进来,让他们看到投资文化事业是有保障、有回收的。其中电影营销的通道是重要的。现在内地大概还有90%的地区没有很好的影院,而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内地市场,这个影院的建构就不仅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是政府如何吸引外资、吸引企业界人士架构这个行业管道、把这个渠道做起来的问题,此外还包括将影片销往国外的渠道建设。
从产业发展来看,整体思维是重要的,而这种思维又需要通过严密的政治立法和政府介入得以体现,它不是目前的企业界所能负担的。如果没有对这些渠道的照顾,电影观众就无法被实体化。而其中,政府应该负担大部分的渠道建设成本。至于法律的运作,包括盗版的问题,我看大家也谈到了。盗版是大家创作时的地下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的进步与年轻导演的成长和盗版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可以通过盗版很快拉近和外面世界的距离,理解外面的节奏和口味。这些在社会已经运作成熟一点以后,应该给予合法化,将这些盗版商转为正式合法的DVD厂商。在台湾,很多电视台也都是由当年的非法电视台转变而来,而很多DVD厂商也都是当年卖盗版的厂商。从国外的情况来看,DVD的销售值已经改变了电影的形态,也许电影院将来会被淘汰,而真正一部电影的产值很多都是从DVD中来,因此,我认为这是公权力应该介入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低成本电影的制作与市场推广
回到“中低成本电影的市场拓展”这个问题,它跟大片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大片的规律是清楚的,大片就是你必须把你的市场思维放到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由此,国家的界限一定要小,文化的界限不一定要很清楚,你创作的语言大家都能懂,这就是你吸引观众的做法,也是大片的做法;可是对于中小成本影片,从整体生存模式来看,如果我们明确百分之几十从国外市场吸收,百分之几十从国内市场吸收,那么很大程度上我们就必须知道中小成本电影的观众群是谁,愿意看这部分影片的分众在哪里。
目前我们看到的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符合欧洲和世界观众的电影制作,例如台湾地区的侯孝贤、内地的贾樟柯,他们的影片营销是非常清楚的。他强调本土性,因为人家关心的不是你作品中世界性的语言,他关心的是你独特的电影语言、独特的本土状态,如贾樟柯这次拍《三峡好人》,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决策。三峡改造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力的事件。我看见很多拍这样的纪录片或者是以这样思维出发拍摄的剧情片,我觉得将来都会变成一个历史的佐证,这个就是非常好的立足点,他在本土题材的选择上会造成很多人的兴趣;而像台湾早期的新电影,这些新电影反映了我们几十年走的文化路,可是一到国外市场,他们看到的就是美学,是台湾这群电影人在这些影片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于是就有一些小众为这些电影大力鼓吹,从而创造了观众。实际上,小成本电影的回收与不回收,造成的伤害都不会太大,也不会有暴利出现;但是中层电影,因为成本比较高,所以他就需要更多思维和结构上的考量,必须强调他的本土性,必须强调他的某一些分众。
另一种就是针对本土市场的电影制作。如果一些中低成本的电影试图在本土市场找到自己的观众群,那么它跨文化的可能性就很低了。例如《疯狂的石头》,本地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很多人觉得很开心,抓到了内地现在大家都为钱发烧的现象,但将影片拿到香港和台湾地区市场,就不见得有效。我们在台湾放给学生看时,学生就认为都是抄盖·瑞奇的《三支枪管》(又名《两杆大烟枪》),分镜都一样。我说这个有关系吗?你不看看他抄的美学背后所表现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物活不活泼?他创造的角色是不是生动?学生看到的第一个是美学,社会现象他不关心,因为离他太遥远了。同样,这个电影在香港也是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社会思维不一样。当影片针对的是本土市场,它就一定会和本土观众趣味高度结合。我曾经监制过一部电影《蓝色大门》,我们针对的就是年轻的在校学生,结果学生会自发地把这个电影介绍给别人,甚至因为影片而影响了自己的人生选择,而这个电影拿到别的地方同样人家也不一定喜欢。我开始也认为这个电影应该有市场,但法国人不接受,人家跟我说你的电影太幼稚,没办法,你们这是淡淡的、青涩的、年轻的爱情,而法国年轻人早在谈“性”了。这是文化上的区别,也是市场的障碍。
另外,从营销上,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整体性思考的。我们发现很多人做电影,抱着影片去市场上营销,以为人家喜欢我的电影就会买我的电影,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片商的组织也跟我们编导一样,是一个专业化的状态,他们是要花非常高成本做公关、联系关系以及证明法律的透明度的。如果你自己卖片的话,成本更高,屏障更多,如语言、法律、谈判技巧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公权力之外,我们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产业界市场观念非常欠缺。比如我们帮一位导演营销一部作品,人家愿意出两万美金买,可导演认为我的电影值一百万不肯卖,这中间会产生很大差距。如果你总端持着不卖,过一个时期,就有另外30部电影出来,再过一段时间,你的电影就是老片子了。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差距非常大。可以说,中间层的电影很大部分都是针对国外市场制作的,但如果你对国外市场这么陌生,根本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市场。我曾经接触到一些比利时、荷兰的片商和发行商,他们说他们国家每年只能容纳一部中国片。而如果贾樟柯的电影和张艺谋的电影,购买价格都差不多,你觉得他会选谁?所以,我认为对这个市场概念理不理解,常常会耽误自己作品进入市场。还有一个就是法律观念的问题,而其中信誉是绝对重要的。版权不清楚,签了约不完成交片,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卖埠信誉。
而以上情况在台湾也是一样。台湾导演总是抱着电影不卖,认为他的电影20年后被人发现,可以赚很多钱。这个就是很尴尬的情况。电影产业要升级,大片是一种模式,小片也是一种模式:大片是遵循经济规律而产生的,小片是不影响经济规律的,而只有中间层的电影是最重要的。香港在这方面做得最为完整,从行业规律到行业法律、法规以及政府的一些公权力都已经铺设得比较完整。而台湾跟内地,我觉得在这方面应该说还是非常薄弱的。而从营销上看,韩国的整体营销思路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它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贩卖。我买一部电影,跟我到另外一家买十部电影,我的手续是同一个,签约是同一个,我一次可以买十部电影,我的片源也不担心,可是单个买,就要花十倍的力气。所以,很多买家需要找一个统销的状态,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贱卖。你卖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这些市场存在,你为了创造这个市场,你就宁愿牺牲一点钱,先培养人家看你的电影的口味。西方人这么讨厌韩国片,但突然觉得韩国片挺好看的,就是这个量做的。像韩国人在这方面就很注重,比如《我的野蛮女友》,大家觉得很好看,可是片商在拍摄的时候,他在测试这个市场的时候,是做了几十次根据观众意见来进行修正的。他放一次修改一下,我记得是做了20-30次,就是说他敢花这个成本不断地调整,最终和观众的口味完全结合。像这些做法都是韩国非常厉害的手法。以韩剧打开台湾市场来说,过去韩剧在台湾完全没有市场,大家都在看日剧。突然有一个电视台,因为日剧的价钱越来越高就找到韩剧,人家几乎是不要钱给你,然而等他的市场打开后,他的价钱就超过了日剧。目前盗版在内地也是同样的意义。美国没有施压打击内地的盗版,就是在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电影的喜爱程度,等你的市场依赖度建立起来的时候,就会要求打击盗版,价钱也上去了。
所以,我觉得营销是必须要用一点智慧的,不能抱着价钱空等人家的欣赏。韩国的做法很多,他们也学法国人,把法国所有电影集中在一起做宣传,那个宣传法国电影的机构叫Unifrance。内地每年都有法国电影节,那个就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努力将法国电影在海外的口味建立起来,宁愿白给你们看,宁愿找一些法国明星和导演来站台,就是让大家熟悉法国文化,这个也是国家整体营销的一些做法。
因此,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电影产业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刻不容缓,其中真的不仅仅是创造力问题。中国的创作人才很多,台湾也有很多年轻的导演嗷嗷待哺。我觉得创作人才、编导人才、技术人才,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你可以四处借用。在我来看这是最充足的部分,真正不充足的是硬体。你如果不花大力气把硬体和渠道做起来,整个产业就无法真正的升级。而一旦渠道建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就很有可能变成全世界唯一有机会对抗好莱坞的体系。由此,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将是很重要的发展时期,它将考验我们能不能转换,能不能在竞争中占有主动。目前好莱坞虎视眈眈,他已经看到这个潜在市场的存在。所以,人家也是所有的脚步都跨了进来,用各种形式进行将来可能的掠夺。话说得好听点是产业升级,共同结合,共同创造生机,但是在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生机都会被好莱坞拿走了,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