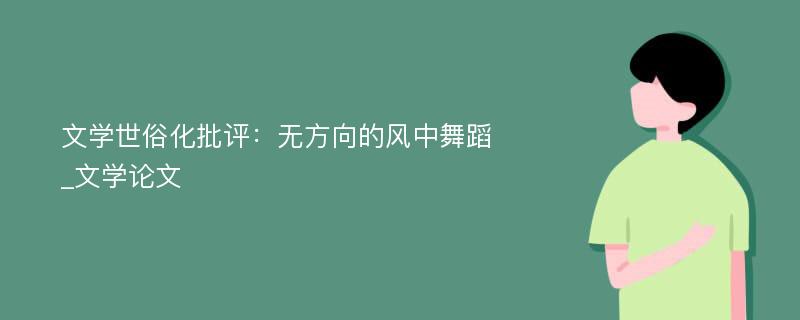
文学世俗化批判——在没有方向的风中跳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中论文,世俗论文,方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风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辞典里,北戴河不仅是一个宜人的风景区,它更与历史上,尤其是文革时期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连在一起。我所一向尊敬的几位师长在赞助商的支持下,选择这个“风水宝地”对整个社会文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且将其言论冠以“北戴河对话”的总题目,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这是继1995年文化论争以后的一场“肇事”,几位评论家、作家、出版家在北戴河建成一个“批评作坊”,生产出杂乱的言论,穿过国内几家有影响的报刊杂志,涌进文化界。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无谓的侵袭,但读这样的文章,仍然匪夷所思。
1.还能寻找到位置吗?
参加北戴河对话的几位理论家、诗人、作家都是新时期文学“贯穿性人物”,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做过贡献。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清理文革废墟,构建新时期文学过程中,作用不可低估。但是,昔日的“成就”却成为他们今天沉重的包袱,使他们在文学多元化以后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学的多元化,它在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的同时,也给人文知识分子带来角色的困惑,以上的几位当然也不能幸免,甚至是首当其冲。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充当文学的代言人角色,像刘心武还曾扮演过“文化英雄”,自认为“还是相当中心的”。[①]文学多元化使各“元”之间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也使各元之间形成张力,在对抗与融合中促进文学的发展。而几位批评家、作家长期处于主流文化的漩涡,习惯于对主流文化“唯马首是瞻”,文学多元化无疑使他们迷失了风向,显得手足无措。对于一直依赖于主流文化的批评家来说,主流文化的丧失,令他们感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刘心武等在“北戴河对话”中,表面谈了诸多问题,但每一个问题都没有实际内容,在“北戴河对话”里,他们仿佛成了失去剑的武士,只能打几下空拳而已。文学的多元化解构并吞没了他们的“文化英雄”的社会功能,将其抛向边缘,取而代之的是被大众传媒炒出的“文化明星”。对于曾经“还是相当中心的”人来说,角色的危机可能使他们比常人更加惶惑和痛苦。因此,他们想用“北戴河对话”这种商业化操作爆炒自己,欲通过当下极时髦的方式将“文化英雄”的角色转换成“文化明星”。但他们却忽略了对话的内容和质量,在拉杂的对话中不失时机地互相吹捧,什么“伤痕文学之父”、“桂冠诗人”、“我们几位是优化的结构”,[②]似乎要强迫读者吞下一只只苍蝇。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这么良好的自我感觉,也许是为了掩饰角色危机带来的心虚吧!他们已不能象以往那样从容地把握文学的现实,从而显得有几分无奈。
让几位批评家、作家更无奈的是他们的知识结构的陈旧过时。他们几位都可以说是中年批评家,大多属于“文革”前毕业的60年代大学生,所接受的理论教育是苏联模式,因此,他们较习惯使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这在文革后的文学的拨乱反正时期也许较适用,因为那时的文学大多属于政治层面的(况且此种方法当时还有些生气)。而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批评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尤其是西方各种理论思潮不断被应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之后,已经模式化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使包括几位在内的中老年评论家处于尴尬的地位。尽管他们想利用“北戴河对话”进行一次猛烈的冲击,欲重振“雄风”,赚回一点廉价的知名度,但毕竟底气不足,似乎是无济于事。
这也许就是宿命,包括几位在内的许多中老年评论家、作家很难再重放“光彩”,只能充当过渡性人物。“文化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靠商业化操作去扮演一个“文学明星”,好象没有任何意义,况且年龄上也不太合适。去年冯立三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论中年评论家》,[③]意在总结这个群体的优点,可惜写成了一封表扬信,毫无说服力。在这里,我不是否定这个群体,倘若其中有人能甘于寂寞,卧薪偿胆,以“十年磨一剑”之功,再对文学有所贡献是完全可能的。问题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为“名气”所累,又偏偏到了半老不老的年龄,深恐来不及磨出一剑,反倒产生了“十年太久,只争相夕”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利用世俗化浪潮繁殖并贩卖一些肤浅花哨的“思想”(也许只是想法而已),这完全可能事与愿违。
但像王元化等先生虽然历经蹉跌,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其思想锋芒,也没有随波逐流。他的名气不能说不大,官阶也曾很高,但都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文学的执著追求。在他的《思辨随笔》中,可以看到他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认真思索、辨析,充满真知酌见。像他这样的批评家仍然是我们文学界的中流砥柱。而对某些中老年评论家来说,倘若思维已成定势,又无更新知识的能力,那最好是保持沉默,这样至少能保住晚节,再用商业化操作去做表演,只能留下笑柄。
2.不是所有的迎合都能让人叫好
“北戴河对话”是几位评论家、作家表演性极强的活动。只不过这次表演受世俗化的影响,少了些庄严,而添了些调侃。插科打诨、耍嘴逗趣,文章的一些段落后面还特意标出“笑”、“大笑”的字样[⑤](这不禁让人想到《废都》中□□□),不知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嘲讽,还是受到那位京城侃爷调教后的“涂鸦”,但我敢说那绝对称不上幽默。幽默需要大智慧,更需要自由的心态,贪名图利,哗众取宠者不可能有自由的心态,也与幽默无缘。尽管据他们的文章记载整个对话笑声不断,但最多也只能算是群口相声,逗人一乐而已。
除了形式之外,对话的内容也极富表演性。表面看来,他们谈了当今人们关心的许多问题,如腐败、权力寻租、理性与启蒙、知识分子焦虑等,但大都是浅尝辄止,流于肤浅化。像对腐败问题他们提到了王宝森,也谈到了一些腐败现象,似乎想表现其勇气(当然是有分寸的,他们从来都是游刃有余的)。但产生腐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却无法从中找到答案,他们对腐败的认识倒不如一些街头民谣更深刻。当然,我并没有想让他们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知道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但几个从事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人为什么要热衷于这样的一个社会问题呢?而且要罗列一些随便在街头都可以听到的现象呢?这只能说明他们在表演,想迎合大众的心理,因为大众关心这个问题。
再如,所谓的“新华体”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这大概可以勉强归到文学的范畴。他们把“新华体”说成是“毛泽东体”,[⑥]似乎是惊世骇俗之举。其实从事文学的人都知道,“新华体”实质上是一种新闻体,新闻体限制人的想象能力,“使人的想象的思维变得枯竭”(波德莱尔语),它与其它形式的文学创作不同,限制了人的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至于它承载过什么内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把新闻体的局限归属于“新华体”,进而说成是“毛泽东体”,这显然是把一个文学的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借以表现自己的政治勇气,其用意也是为了迎合大众。因为当下关心政治的人显然要比关心文学的人多得多。
大众文化使大众变成消费主体,但不是所有对大众的迎合都能让他们叫好,因为大众文化同样需要思想的深刻性和精神的独立性。
3.有点学理性和良知
尽管在“北戴河对话”中,刘心武被吹捧为“是有能力跨创作、研究和批评的有实力的作家”,是“伤痕文学之父”,[⑤]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能力。
一个作家参与文学批评是极正常的现象,阿尔贝·蒂博代甚至把一些作家的文学批评归结为“大师的批评”,认为“往往表现出极高的悟性,迸射出天才的火花”。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批评的弊病是容易形成“作坊批评”,作坊者,小圈子也。“作坊倾向于变成小教堂,小教堂则又倾向于变成堡垒”。[⑥]纵观刘心武近年来的文学批评,我们看不到“悟性”和“天才的火花”,倒是看到了一个党同伐异的“作坊”,他对张承志的批评便是一例。
刘心武是写小说的,张承志也以此为业,按说刘心武评论张承志的小说也许还有发言权。可在“北戴河对话”中,刘心武却要追溯张承志的“心路历程”,似乎是要认定一下张承志这个作家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且不是对张承志的小说家身份,而是他的政治身份,我不知道是谁授给刘心武这样的权利。
如果从文学创作及其所表达的精神方面看,我感觉张承志的思想和精神更有魅力。因为读他的作品能够感到其思想的内在的逻辑性。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方的河》,到《黑骏马》和《心灵史》,我们都能感到张承志所追求的精神和信仰。就是文革初期,张承志主动要求下乡,也是无可非议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选择,而且类似这种的选择一直贯穿他以后的生命中。而刘心武等人用所谓的“原红旨主义”将其与文革和红卫兵联系起来,将一些历史性的错误赐给他一份“功劳”,那显然是对张承志的“抬举”,因为他不可能具有那样大的能量。就是今天他皈依宗教,也是他的个人选择,无限夸大其社会性,进而进行一些政治暗示,这不仅是杞人忧天之举,也暴露出“肇事者”的阴暗心理。
而我所不能理解的却是刘心武,在张承志文革期间下乡的时候,他在做一些什么?他在写小说。在那个“极左”的时代究竟能写一些什么样的小说,我虽然未曾拜读过,但也可想而知,可能会恨不得写出一部《金光大道》或《艳阳天》 之类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说,他可能有权评论张承志,但却没有资格。因为张承志作为一个“没有打过人的红卫兵”,同时也是那场灾难的承受者——知青,他走向人民虽然有时代的痕迹,也是他自我选择使然,他自觉地和人民承受了一场灾难。而刘心武的思想发展缺少内在逻辑性,或者说没有自己的精神立场。文革结束以后,他以《班主任》、《醒来吧,弟弟》等作品赢得了声誉,并极得意地称自己处于“很中心的位置”。其实仔细分析便可以看出,《班主任》等作品在艺术上是极为粗糙的,它之所以能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展示了文革留给人们的“伤痕”,更重要的是符合当时的政治的需要。他曾坦露“这些小说一经发表,很快得到官方的肯定,认同,动员文化机器加以宣传流布。”[⑦]由此可以看出,《班主任》是极好地诠释了当时的政治。由此便吹嘘自己“处于很中心的位置”可以说是一种“自恋”情结,因为是政治使他处于那样的位置,而不是小说文本,不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力量,更不是他的人格和精神魅力。而后,刘心武的思想不断变化,小说的主题也是随风向而动。大众需要启蒙,要张扬个性的时候,他写《我爱每一片绿叶》;人们关心足球,他写《五·一九长镜头》;王朔骂知识分子成为时髦的时候,他写《风过耳》;当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不满时,他近期又写了充满“批判色彩”的《风月楼》。他永远是随风而动,虽然每个时期他似乎都找到了风向,但贯穿起来观察,他便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一直在没有方向的风中跳舞。
他似乎也曾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曾写道:“我所有的小说都乏味,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下这些,在乏味纸堆里再增添些乏味。”[⑧]曾经被捧为很有“责任感”,关注“社会问题”的刘心武,怎么突然感到自己的小说乏味了呢?原因是他一直围着“问题”打转,使他掌握了察言观色的本领。他关注的“问题”既不是人类的真实处境,亦非人类精神在现实面前的种种困惑,因此,他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更无法产生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正如有论者所说的,刘心武小说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难忘的人物,看不到应有的痛苦和颤栗。作家在严酷的环境中缺乏精神深度和承担时代重压的能力。[⑨]这也正是一般作家与大师的区别。
实事求是地说,刘心武作为一个小说家已算勉强,而他的文学批评水平实在不敢让人恭维。这在近期一些杂志刊物的与张颐武的对话中,便一目了然。[⑩]若偏要说他懂得文学批评,那他只会两种方法:自我吹嘘和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前一种方法是“自恋情结”使然,而后一种方法则是一种文革遗风。在深层次的心理上说,留下文革病根的是刘心武,而不是张承志。在去年的文化论争中,青年评论家王彬彬说中国作家“聪明”,批评了王蒙等人的圆滑世故,因形而下的处世技巧发达,使形而上的情思受到阻断。这本是探讨作家创作心理的问题,却被刘心武说成是“极左势力以另一副面孔出现”,“破坏安定团结”。[①①]张承志皈依宗教,并决心“以笔为旗”同世俗化斗争,刘心武又联想到“沙林毒气”、“义和团”,认为是“产生极端主义的温床”,“很可怕”。就连张承志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歌颂人民,也被他认定为“人民情结”,因为他自己“当时还对党,甚至对当时党的领袖,寄予高昂的热情”。[①②]这居然成为他排斥张承志的理由。我不知道刘心武为什么总愿意把文化的或文学的问题扯到政治上去。如果我们借用刘心武的逻辑和批评方法,那么请问:作家难道只能歌颂党而不能歌颂人民吗?你凭什么把党和人民完全割裂开来?还有,你认为王彬彬“破坏安定团结”,张承志“很可怕”,很危险,似乎允许他们的存在,我们就将大难临头,难道你对我们党的力量表示怀疑吗?你是不是对我们党不够信任?我相信这种“文革”式的闷棍同样会使刘心武晕头转向。但这毕竟是一种无用也很无聊的事情。我不想和刘心武同样无聊。
文化论争和文学批评都需要有学理性,更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并不是在多元的幌子下,谁都可以胡说八道。也许还是孔夫子说得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所以我想奉劝刘心武:别瞎说,行不?
结语:世俗化的力量
当我的文章就要结束的时候,收音机里正播放一首歌,歌名叫《垃圾场》。歌手声嘶力竭地喊着: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我感到震惊:难道世俗化真的就具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吗?
但当我又想起“北戴河对话”,想起我向来所尊敬的,曾将文学作为信仰的几位师长的时候,我心里一时有些茫然了。
注释:
① ⑦参见《艺术广角》1996年第3期《知识分子:位置的再寻求》。
② ④ ⑤ ①②参见《钟山》1996年第1期《历史转型与知识分子定位》。
③《光明日报》1995年2月14日。
⑥《六说文学批评·前言》,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⑧ ⑨参见《中华读书报》1996年1月31日《刘心武围着问题打转》。
⑩参见近期《作家》、《通俗文学评论》、《艺术广角》、《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
①①参见《护林与“烧荒”》,《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3月。
标签:文学论文; 张承志论文; 刘心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班主任论文; 作家论文; 北戴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