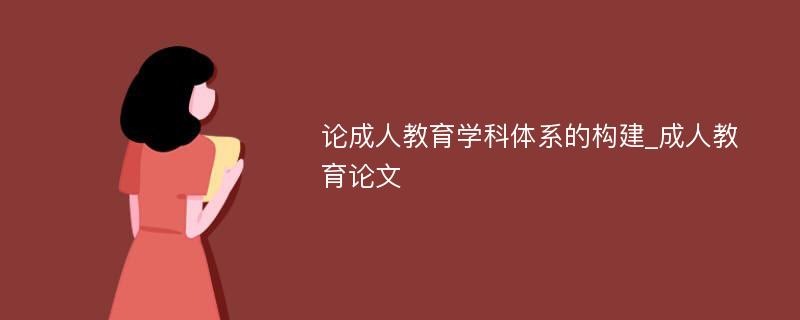
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人教育论文,体系建设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学科体系建设被迫切地提上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议程,这是成人教育走向成熟的需求,更是建设学习型社会发展目标的时代要求。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要想取得事半功倍的理想效果,必须采取有力而得当的推进策略,这又必须首先搞清楚完善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确定其总体建设目标,把握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推进方向。
一、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完善的标志
1992年,“成人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其代码为880·57。然而,学术界特别是教育界对成人教育学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能否成为一门完整学科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说明,成人教育学的学科地位还没有被学界普遍承认,成人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还远未成熟。
那么,判定一门学科能否独立的标准是什么?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成熟有什么标志?这是 推进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
我国学者就此做了不少研究。有学者认为,评判一门学科或分支学科是否成熟要看两个方面,理论方面要看其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实践方面要看其是否有代表人物、代表论著、学术组织、学术刊物等。(注:唐莹、瞿葆奎:《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3年第2期。)有学者提出,判定教育学科的独立性有三方面标准,一是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概念、范畴、原理,并且已经或正在形成学科结构体系;二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活动,有代表性著作,有学术团体,有学术传播活动;三是该学科的思想、方法已经在相应的教育实践中被应用、检验、且已发挥了特有的功能。(注:安文涛:《教育科学学引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也有学者将教育分支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Ⅰ期为酝酿期——研究对象尚未从纷繁的教育对象中清晰、明确地分离出来、尚未找到适合自己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正处于学科创建的舆论准备阶段和学科材料积累阶段;Ⅱ期为形成期——研究对象逐渐独立但仍具模糊性,基本概念、规范体系逐渐清晰但仍缺乏系统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研究方法尚具移植的简单性与机械性;Ⅲ期为相对成熟期——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和适合自己对象特征的科学方法体系,有公认的学科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或学科刊物、研究团体等等。(注:姜安丽:《教育交叉学科的结构与功能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国外学者对于学科以及判定学科独立性的标志等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更丰富。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显著提高,科学得到了系统而全面地发展,且从综合走向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科学分化已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门类学科,对“学科”的研究便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关注。许多科学大家如培根、达兰贝尔、圣西门、黑格尔、恩格斯等对学科及其分类、联系等都做了精深而卓有见地的研究。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 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这从辩证唯物的高度对学科的分类、联系作了科学判断,为学科及其体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到了现代,庞杂而形形色色的学科不断涌现,其产生来源、形成过程各不相同,很难用一个公认的标准来进行评判。比利时跨学科理论家阿玻斯特尔就指出:“学科这个词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含义。有时,学科是根据观察的方法来定义的(如摄谱学),有时是按照模型来定义的(如物理学),有时则是按照研究对象来定义的(如历史学)。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不同的例子。”(注:刘仲林:《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版。)(P34)
而对学科能否独立、是否成熟,论者们也有不同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德国波库大学教授黑克豪森认为,判定学科独立性与成熟度的标准应该有7项:1.学科的“材料域”,即根据常识可以理解的一组研究对象;2.学科的“题材”,即从材料域中划分出来的可观察现象的范围;3.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即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树,这是衡量学科的最重要标准;4.学科的独特方法;5.学科的“分析工具”;6.学科在实验领域中的应用;7.学科的“历史偶然性”。(注:刘仲林:《跨学科学导论》,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P34—38)德国布瓦索教授认为一门学科是三种成分的集合 :1.可观察或已形式化的客体;2.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具体现象;3.用来解释现象,并 预测现象作用方式的定律。(注:刘仲林:《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 版。)(P41—42)比利时根特大学教授阿玻斯特尔认为建立学科要具备五方面条件:1.一 群人;2.这些人进行一系列的活动(观测、实验、思考等);3.这些活动导致某些相互作 用,并在这些人内部、外部进行交流;4.通过教育、交流使这些人的知识不断更新;5.这种活动通过历史性的学习方法代代传递。同时,他认为一门学科决不仅仅是一系列论 题、文章或教科书,而是一系列行动、目的、组织和发展。(注:刘仲林:《跨学科学 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P52—53)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尽管具体表述不同,但它们对判定学科的独立性、成熟度却有大体一致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简明概括为:1.要有独特的研究对象;2.要有完善的学科架构;3.要有科学的学科体系;4.要有专门的研究方法;5.要有公认的代表人物;6.要有典范的代表论著;7.要有众多的科研团体;8.要有活跃的学术交流;9.要有成功的社会实践;10.它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用这些要求来衡量,我国成人教育学科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显然已经走过了“学科酝酿期”,处于“学科形成期”,虽然离“学科成熟期”还有相当距离,但毫无疑问应该被视为一门独立而完整的教育学分支学科。
二、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推进方向
仔细分析国内外学者判定学科独立性、成熟度的共通性要求,可以发现,这些要求中有些是必具的“基本标准”,有些是学科走向成熟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伴生标志”。前者如“独特的研究对象”、“完善的学科架构”、“科学的理论体系”、“专门的研究方法”、“典范的代表论著”、“成功的教育实践”等,是教育学科要成为独立学科必须达到的标准;后者如“公认的代表人物”、“众多的科研团体”、“活跃的学术交流”等则是教育学科走向成熟过程中自然而然会形成的标志,而“时代的必然要求”则是该学科得以立足、生存、发展的根本性前提。对那些“标志性要求”无须去刻意追求,一定要着意追求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而对成为独立学科必须达到的“标准性要求”,则应该通过有意识、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的努力,争取尽快基本达到并不断完善、提高。
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应该着重从以下方面把握好推进方向。
(一)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
成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报》1993年2月13日。),这都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再深究下去,成人教育的具体对象 是什么?成人教育的范畴有多大?成人教育的类型有多少?成人教育的覆盖面有多广?成人 教育的研究内容是什么等等,则见仁见智了。仅仅一个看似简单明了的“成人”概念, 到了成人教育学科研究中也变得复杂化了——有从生理年龄界定的,有以接受教育类型 划分的,有以从业状态不同判定的——遑论成人教育范畴、成人教育学涵盖等更复杂的 问题。
而且,成人教育又是与经济、社会、成人生存状态等紧密结合的教育类型,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的时期,成人教育的对象、范畴、使命、类型等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这就为成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定带来一定变数。
研究对象的明确是学科体系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根据我国成人教育实际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研究范畴,是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进一步完善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基本架构是学科研究对象、范畴等的具体化展示,是学科“有机体”各部分相互联接、相互支撑的立体化组合,是学科体系理论建树、实践拓进的方向性指导。学科体系基本架构的搭建、完善,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成人教育学“大厦”的规模、样式、稳固程度与成长、发展。
目前,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基本架构的搭建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定性问题。众说纷纭的观点从根本上看归为两大类:
一类观点认为,成人教育是对成年人的教育,它与非成人教育并没有本质性差异,一般教育理论、规律完全可以指导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学只是教育学科体系中按“教育对 象”区分出的一个小类(譬如毛祖桓划分的“教育科学的系统分类”便如此处理(注:毛 祖桓:《教育学科体系的结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再 构建自外于一般教育学科体系的成人教育学科架构没有什么必要。——普通教育理论工 作者多持这类观点。
另一类观点认为,成人教育是为成人提供的“非传统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活动”,“是与未成年人全日制学校教育相对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体系”,(注:叶忠海:《成人教育通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页。)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有着本质性差别,一般教育理论、规律不能机械地适用于成人教育。因此,成人教育学应该搭建自己的学科架构,建立完善的成人教育理论体系。——成人教育理论工作者多持此类观点。
按照前一类观点,成人教育学完全可以采用普通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不必构建自己的学科架构,成人教育学也便失去了学科独立性,非常容易被普通教育学科吞并、替代;按照后一类观点,成人教育学须从成人、成人教育的实际出发,从成人的生理、心理、社会存在、全面发展等角度,从成人教育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关系的角度,从成人教育自身的独特性质、体制、机制、运作方式、规律等角度来设计崭新的学科架构,逐层搭建创新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这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原创性工作,但唯其如此,成人教育学才可能真正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架构,使自身扎根于成人教育实践的沃土,在独特、稳固的学科体系架构支撑下成长、发展。
学科体系基本架构的搭建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它需要一个不断设计、调整的建构过程。只有搭建起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架构,成人教育学的不断发展、趋于成熟才具有正确的指南。
(三)进一步拓进理论研究
如果说学科架构是学科体系的“骨架”,那么,学科理论及其核心思想便是学科体系的“血肉”与“灵魂”。所以,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最重要部分在其理论研究的拓进。
德国学科理论家黑克豪森认为,衡量学科“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学科的“理论一体化水平”。(注:刘仲林:《跨学科学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P36)他所 谓的“理论一体化水平”,是指经验性学科(除数学那样的纯理论学科之外的学科)在理 论层面上重建研究对象的“真面目”,并在了解、解释、预测与研究对象相关联的现象 、事件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系统的成熟程度。也就是指学科理论与 学科实践的吻合程度,或曰学科理论的“科学度”、“合理度”。
近20余年,我国成人教育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可观的成绩,但从总体看,也还存在三种明显的偏向:
一是国外理论的盲目“移植”。发达国家现代成人教育发展历史较长,又高度重视其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成果。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时,凭借国外资料,引经据典搞出术语满篇的“理论成果”,读之艰涩乏味,思之与我国成人教育实际相去甚远。
二是普教理论的机械“翻版”。我国历来重视普通教育研究,普通教育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一些学者研究成人教育时自觉不自觉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观点、体系、方法甚至结论,搞出普教理论的“成教版”。
三是运作体会的感性归整。我国不少成人教育实务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又因为专门知 识基础的薄弱、科学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维的僵滞,而大多停留在实践运作体会感性归 整的层面,达不到应有的理性高度。
三种偏向导致了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脱节——理论不能有效地剖析、预测、指导成人教育实践,而实践中产生的新思考、新体会、新经验又得不到理性概括、提 高——呈现出理论的苍白与实践的盲目。
用黑克豪森的标准衡量,我国成人教育学的“理论一体化水平”还比较低,学科的成熟度还差得很远。所以,注重学科理论的拓进,注重理论研究对成人教育对象的关注、了解、解释、预测,着力提高“理论一体化水平”,是强化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关键。
(四)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学科理论研究的推进具有三方面重要价值:其一是科学的方法可以对对象进行准确的剖析、解释;其二是恰切的方法可以将研究对象转换为对研究课题极 有价值的数据、论据,来支撑理论的建立;其三是适宜的方法可以帮助理论设想在社会 实践中应用,并在应用过程中对理论进行检验。所以,方法创新对学科体系建设意义重 大。
学科研究的方法,应该分三个层面。最高层面是哲学研究方法层面,其次是众多学科普遍运用的一般方法层面,再次是某一学科专门使用的特殊方法层面。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其体系建设过程中应该全面运用三个层面的方法,并且特别重视本学科特殊研究方法的创新。
我国成人教育学在学科研究的方法运用、创新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在学科理论研究中,成人教育哲学的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甚至空缺的部分,用哲学方法研究成人教育学对象也不普遍,直到最近两年,哲学层面的研究、哲学方法的运用才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对于经验性学科常用的一般方法,譬如观察法、调查法、实证法、实验法、模型法、模拟法、比较法、历史分析法、数理统计法、双向反馈法、个案剖析法、系统研究法等,我国成人教育学科研究都有运用,但运用范围、频次,特别是专注程度(像国外一项成人教育实验搞三五年、七八年那样)、深入程度还很不理想;而迄今为止,我国成人教育学似乎还没有形成拿得出、叫得响、能站住脚的独特的专门研究方法。
而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最多用的方法是“坐而论道”。或一般归纳:“成教问题——因果剖析——对策建议”;或简单演绎:“一般理论(国外理论或普教理论)——成教现状——改革取向”。方法的单调、机械导致了理论成果的肤浅,严重制约着成人教育学的理论发展、学科建设。
方法是工具,“器利”方可“善其事”;方法是桥梁,“途通”才能“达彼岸”。我国成人教育学只有善用已有的研究方法,再努力创造出自身独特的研究手段,才可能具备学科的独立性,才能使学科体系建设拥有工具性依托。
(五)进一步催生代表论著
学科核心思想、学科基本理论对于学科体系而言,是“灵魂”,是“血肉”,是学科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核心思想、基本理论的载体主要是论著,而代表性论著又是学科思想、理论的典范性载体。于是,代表性论著的数量多寡、水准高下与影响大小,既成为衡量学科独立性的标准,又成为判定学科成熟度的标志。
国外成人教育学科的兴起、逐步发展、日趋成熟,就是以其代表性论著的产生为标志的。1816年,移居英国的美国人托马斯·波尔(Thomas Pole)出版《成人学校的起源及发展》,首次使用“成人教育”术语。1851年,英国人哈德逊(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前苏联麦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组织与技术》,提出创建成人学习学科。1926年,美国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义》,系统探讨了成人教育的目的、意义、特性。1928年,美国桑代克(E.L.Thorndike)发表《成人的学习》,对成人学习及其能力做了实证研究。1964年,由以北美专家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CPAE)编辑出版的《成人教育——一个正在形成的大学研究领域的概况 》(即著名的“黑皮书”),引导成人教育走向新兴独立学科。1969年,美国成人教育家 诺尔斯(M.Knowles)在威廉斯堡大会上正式提出“成人教育学”理论,次年,他的《现 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出版,书中构建了成人教育理论的 基本模型,初步建立了成人教育学的总体框架。1970年,法国成人教育家保罗·郎格朗 (Paul lengrand)《终身教育导论》出版,标志着成人教育理论研究走向成熟。
近20余年来,我国出版了超过500种成人教育研究专著(不含译著),不过,平心而论,能称得上“代表性论著”的比较少见。其中,王文林等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1988年出版)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成人教育专著;叶忠海主编的《成人教育学通论》(1997年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理论;黄尧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国家“九五”课题成果,2002年出版)则是一部贯通古今中外、颇具前瞻意识的原创性著作。
代表性论著的产生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基础,与论著者的理论修养、科研经历、研究态度、思维表达能力,与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代表性论著的产生与公认的代表性人物的产生又有着一体两面的必然因果关系,它从两个向量决定着学科的独立与成熟。所以,创造条件、多方催生代表性论著,应该是今后强化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
(六)进一步推进教育实践
成人教育学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经验性学科,一方面,它以成人教育为研究对象,离开了成人教育实践,其研究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科便难以发展、成熟;另一方面,教育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离开了这个总目标,成人教育学科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所以,成人教育学科还应该注重在推进成人教育实践过程中加强建设。
国外尤其是北美国家的成人教育学科研究非常强调与成人教育实践的结合。譬如,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为研究成人智力、学习力与年龄的关系,以14~50岁的人群为对象,进行了两年实验研究、其结论通过《成人的学习》发表后引起相当轰动,美国教育学杂志评价道:“桑代克在教育心理学及成人教育方面有最大的贡献。”再如,美国诺尔斯用20余年时间深入民间组织和30余家企业,推广、促进成人教育,才为其建立“成人教育学”基本模型和总体框架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和成人教育社会实践基本是“两张皮”,脱节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一些学者坐在书斋中,凭国内外资料演绎“成人教育学”,撰写论文、出版专著,却很少走出研究室、院校到社会去宣传、调查、推广、实验成人教育(这也是代表性论著难以产生的要因);另一方面,我国不少成人教育办学主体受经济利益驱动而“跟着感觉走”,追着“浪头”行,出现市场化、商业化办学倾向,办学思想的偏误导致漠视理论的指导,根本没有将成人教育视为一项学术性工作。
中国成人教育实践是中国成人教育学科成长的“土壤”,“沃土”才能结出“硕果”,所以,“改良土壤”的工作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至关重要。我国成人教育实践的优化最重要的是端正教育思想,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将促进成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发展作为最高目标。教育思想端正了,办学方向、办学体制、运作机制、教育教学等都会不断优化。而学科研究只有深入我国不断优化的成人教育实践,从我国成人教育实践中去抽象、去检验,才可能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
正确把握构建方向,只是强化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然而,目标不清、方向不明,便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明确推进方向,对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