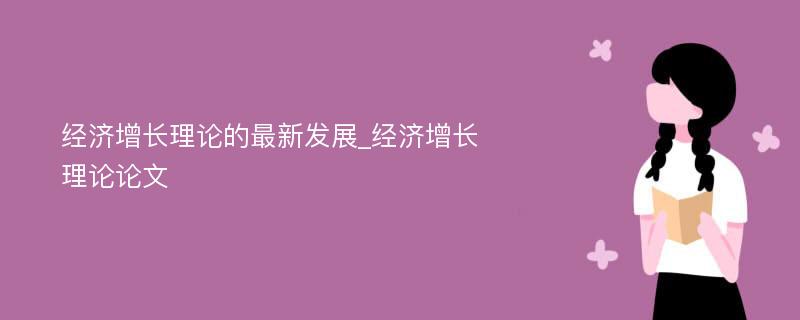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最新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并力图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又称R&D模型),将知识或技术创新在模型中内生化,从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大大发展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实践上对各国政府加强技术创新激励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然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规模效应这一不合事实的结论。因此,近期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就是围绕消除规模效应而进行的。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与简要评价,并阐述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意义。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 and 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一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能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己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标签:经济增长理论论文; 内生增长理论论文; 规模效应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成本分析论文; 模仿创新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