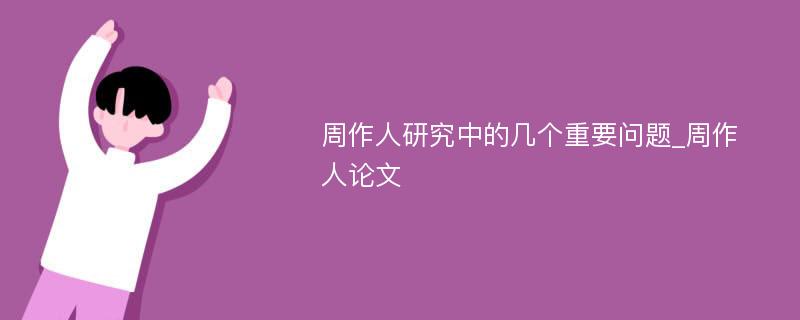
周作人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评论周作人的第一篇专门文章是赵景深发表于1923年1 月的《周作人的诗》(注:1923年1月《虹纹季刊》第1卷第1期。), 如果从这时算起,周作人研究走过了七十四年历史的风风雨雨。 这七十多年大致可分为1949年以前,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三个研究阶段。1949年以前为周作人研究的开始期,在有关的论文中,绝大多数是一般性的评论,真正达到学术研究层次的极少。三十年代后期,研究工作因为周作人的附逆而出现了转折。在八十年代,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地位受到重视,周作人研究逐步展开。八十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绩斐然,然而研究者于对象还或多或少地有点“隔”。步入九十年代后,他们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独特的艺术与精神世界中去;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始试图建立周作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广泛联系。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渐深入,有几个重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问题、对他后期散文的评价问题和研究他的价值标准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制约着周作人研究的格局和进展,并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思想研究产生或多或少的冲击。
三十年代是阶段斗争激烈和派别之争纷繁的时期,革命文学勃兴并取得了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周作人日趋系统化的世界观、文艺观及其影响对革命文学构成了挑战,因此,他是革命文学回避不开的存在,必须对他的存在做出反应。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论争。论争虽然带来了局限,使评论和研究渗入了过于直接的功利成分,但也刺激了周作人研究的开展,引导人们以更宏阔的视野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他。
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中,三十年代的几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早对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作出较为冷静、客观的评价。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注:1934年12月《青年界》第6卷第5期。)中说:“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该文最突出的特点是视周作人为思想家,并进行了论述。她写道:“我们如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十年以来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固然他的思想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如他的历史轮回观和文学轮回观——但大部分对于青年的利益是非常之大的。他与乃兄鲁迅在过去同称为‘思想界的权威’。因为他的革命性被他的隐逸性所遮掩,情形已比鲁迅冷落了。”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他的思想方面的表现:“(一)对国民劣根性的掊击”;“(二)驱除死鬼的精神,论其轮回观的历史观念”;“(三)健全的性道德的提倡。”此文收入了陶明志(即赵景深)编《周作人论》(注:北新书局1934年12月版,收入已发表过的文章四十三篇。),解放后海外有人说这本书除苏雪林的文章最有内容外,余悉是阿谀与谩骂的文章,得到过周作人的赞许。(注:致曹聚仁信,见《周曹通信集》第48页。苏雪林称周作人为思想家,后来沈从文曾表示过赞成(见《习作奉例》 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1940年9月《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确实, 《周作人先生研究》没有情绪化,较为客观、较为准确地论述了周作人的贡献。康嗣群在他的印象记《周作人先生》(注:1933年11月《现代》第4卷第1期。)里认为,“岂明先生不仅在现代散文上站着创始者的地位,同时,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和战士;他给现代中国青年指示了一条路,那便是已走过了的,并且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留下了他的杰作和名言。”胡白认为知堂对做人谈得系统、明晰,说:“我对于这一派思想家是感觉异常亲近的。”(注:胡白:《知堂论人》,1937年1月 7 日《益世报·语林》第1510号。)施蛰存写道:“鄙意以为周作人先生之文集,自当以《谈虎集》为代表。现在的人,听说话的本领甚为低劣,看看周先生最近的《苦竹什记》及《夜读抄》等书,总以为是周先生自己的身边琐事,于是一个正确思想的指导者被误解为悠闲自得之隐士。”(注:施蛰存:《一人一书——论鲁迅、知堂、蒋光慈、巴金、沈从文及废名的创作》,1937年1月1日《宇宙风》第32期。)
后来由于他的不光彩的行为,人们就讳谈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的贡献了。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在九十年代,这个问题又被显著地提了出来。
舒芜于1986年发表长文《周作人概观》(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5期。),点到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存在,此文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周作人概观”为题收入他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一书时, 作者作了补充:“他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功绩,正因为都具有文化思想上的意义,才高出于当时的一般的水平,也才能够成为我们不该拒绝的遗产。‘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家很多,文学家而同时还是思想家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周作人两个,尽管两人的思想不相同,各人的思想前后也有变化,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则是一样的。”
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属于周作人的一本叫《理性与人道——周作人文选》(注:1994年12月版。),这本书凸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存在。高瑞泉在《编选者序》里说:“这本集子选编的标准,自然不在它的文学的或审美的意义,而在于它的思想史价值。编者希望这些篇什能够反映一个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一个中国化的自由主义者周作人的精神探险历程和最重要的思想建树。”此文当然不是全面评价周作人的思想,但揭示出了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两个基本的特质:启蒙主义与中国化的自由主义。正像本书的书名作提示的那样,编者认为“理性与人道”是其思想面貌的主要特征,周作人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常常是点到为止,甚至借他人的著述约略道出,极少作严密的逻辑推理、详细的铺陈论证,高瑞泉对此还有着精彩的分析。
高瑞泉的序言初步揭示了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内涵。在此之前,钱理群曾说周作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注:《试论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1981年第4期。),舒芜在《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中, 刘绪源在《解读周作人》(注: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版。)中, 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中, 都提到周作人的思想家的身份。承认周作人为一个思想家与后面我要谈到的充分肯定他的后期散文一样对周作人研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必然会带来研究格局的调整。尤其是承认周是一个思想家意义更大,透过这个视角,我们就会看到和过去大不一样的周作人。苏雪林、康嗣群等人是从同时代人的切身感受来得出这个结论的,今天的研究者是从更宏观的背景来论述的,这说明周作人的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也认为周作人的思想家的地位是无疑的。我很赞成王富仁对鲁迅是否是一个思想家的辨析:“假若不把思想家仅仅按照西方的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学说的营造者,而理解为实际推动了一个民族并由这个民族及于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发展、丰富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的人,那么,鲁迅的思想家的地位就是不可忽视的。”(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三),《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3期。)” 我想这段话对周作人来说也是大致适合。具体一点说,他在现代思想史上最具特色的思想是他的人的发现以及与之密切相联的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对封建礼教的掊击,对国民“恶根性”的批判,还有对自由与宽容思想的提倡。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舒芜的《不要完全抛 在脑后》。(注:《读书》1994年第5期。)1993年, 《废都》现象和顾城的杀妻事件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舒芜借助知堂的妇女论思想,抨击了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把女人当作平等的人,而视她们为淫杀对象的封建道德观念。他们的抨击是有力的,这件事情也说明知堂妇女论仍然有着它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再一篇是日本学者尾崎文昭的文章《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注: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7 月版。)该文评介了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中周作人与陈独秀之间的论战。尾崎文昭指出在论战中“运动一方是一贯以政治问题来对待,周作人则一贯以思想问题来看待”。周作人继承和推进了作为“五四”精神的“西欧近代主义”,“他以此对或明或暗的封建思想之复活,给以了激烈的批判。终而至于批判了渗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阴影,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当时则近乎被人忽视。打那后相隔了五、六十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的今天,它才终于为人们所重新认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今天看来实在令人钦佩、警醒。周作人的思想是一笔我们需要继承的遗产,我们实在不该把它当作污水泼出去。承认周作人是思想家,我们又会面临着一批新的研究课题:他提出了哪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他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等等。这又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难题,必然会引起一些异议,因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一个失节者和一个思想家是难以调和的。问题既然鲜明地提出来了,可以以学术的态度进行讨论。
唐弢曾说:“周作人早期散文很漂亮,思想开明,要肯定,后期不行了,专门抄古书,不行就说他不行。”(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5期。)其实,周作人1928 年以后的后期散文颇多大胆的创制。他在解放后致友人的信中说,他自己一直喜爱后期的《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信息》等篇章。(注:1965年4月21日致鲍耀明,见《知堂晚年手札一百封》。) 这类作者自视甚高的文章与他前期的散文不同,抒情表意的线索更加内在化,更多的是抄录古今中外的书籍,只用极为简单的语句把材料联缀起来,但表达却是自己的意思。“趣味”与人情物理高度和融,读起来感到味道醇厚。由于其内容与时代热点问题的睽隔,加上文体的苦涩,这些文章遂不被人所深知,误读甚多,以致于有人戏称作者为“文抄公”。
不过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一些真心喜爱周氏后期散文的人,甚至崇拜者。堵述初的《周作人与陶渊明》(注:1936年4月《艺风》第4 卷第4期。)赞美道:“单说在他所谓‘闭门读书’时代所写读书记,已有人称为现代中国所有读书记的最好者。”曹聚仁在《夜读抄》(注:1934年12月20日《太白》第1卷第7期。)中说:“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合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言下之意,周氏的文章是越写越好,这与流行的看法相左。他写道:“《夜读抄》大部分是周先生谈他读过的书;周先生读书,没有半点冬烘气,懂得体会得,如故交相叙,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切切实实地说一番。……正如树荫底下闲谈,谈起故交消息,好好坏坏,夹杂批评一点,自觉亲切有味。”他在另一篇文章《“苦茶”——阿猫文话之二》(注:1935年11月18日《立报》。)中进一步寻找周作人取得成功的原因:“周作人先生读了别人的书,经历了别人的思想历程,又能把别人的思想历程排遣掉,组成自己的思想系统,所以那么明白事理,通达人情。”该文还引述了朱自清的评价:“朱自清先生说周作人先生的读书记最不可及,有其淹博的学识,就没有他那通达的见地,而胸中通达的,又缺少学识,两者难得像先生那样兼全的。”郭沫若也曾表示过对具体篇目的喜爱:“最近读到了周作人写的《谈文字狱》,所谈的是关于李卓吾的事,那文章我觉得写得极好。像那样的文章,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是‘俛首心服’的”(注:郭沫若:《借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1937年7月《中华公论》创刊号。)。
四十年代,胡兰成在读了《苦竹杂记》以后说:“读书如此之多,而不被书籍弄昏了头,处世如此平实而能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在这凡事急促,局限,而潦草的时代,他使人感觉余裕。可是对于那时代的遗老遗少,以其沉淀为安详,以其发霉为灵感之氤氲者,他所显示的却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注:《谈谈周作人》,1943年10月《人间》第1卷第4期。) 黄陇西的《读〈 药堂语录〉》(注:1943年4月《中国文艺》第7卷第4期。) 称赞这个文集披沙拣金,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看似平淡无奇,却也颇可发人深省。文载道是四十年代初期周作人散文的追随者,他在《读〈药味集〉》(注:收入《文抄》,新民印书馆1944年11月版。)中这样肯定周作人的抄书:“我们通常读知堂文章有意外的一笔收获,有几个古人古书,一经他的引用或称读,即觉栩栩然活跃纸上,这时如果再拿几部原著来读,仿佛就添了一重亲切感,一个轮廓。”
知堂后期散文解放前得到过少数几个人的喜爱,解放后一直倍受鄙视。在新时期,舒芜于《周作人概观》中率先对这些散文予以肯定:“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记之类,常常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中间寥寥数语的连缀点染,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在《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中, 他更明确地说:“事实上,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指1924年以后——引者),甚至包括了他附敌以后的部分作品,这是今天应该冷静承认的。”“到了晚年(主要指抗战爆发以后——引者),刊落浮华,枯淡瘦劲,而腴润自在其中,文境更高。”在《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注:《文艺研究》1988年第4期、第5期。)一文里,他把知堂以抄书见长的文章的文体称为“‘文抄公’的文体”。我于1990年发表《新时期周作人研究述评》(注:《文学评论》1990年第5 期。),也呼吁人们重视知堂后期散文。
在九十年代,知堂后期散文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研究。
几篇谈论知堂散文的书评、随笔值得特别注意。舒芜在为刘绪源著《解读周作人》所写的书评《真赏尚存 斯文未坠》(注:《读书》1995年第5期。)中表示,他高度评价周作人的抄书之作, 但最推重的还是周晚年的那些刊落浮华、枯淡瘦劲的也不大量抄书的本色文章,——他指的是《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中的文章及解放后写的少数篇什。金性尧(即文载道)看重知堂三十年代以后的散文,不过意见与舒芜有所不同:“知堂的文集,我个人最爱读的,还是中期写的《夜读抄》、《苦茶随笔》、《瓜豆集》、《苦竹杂记》等,后期的如《药堂语录》,便觉涩味过重,情趣稍逊。”(注:《知堂的两本书》,《读书》1992年第8期。)张中行在随笔《再读苦雨斋》(注:收入《负暄续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中对知堂的散文艺术也有精彩的阐明, 他指出,要说知堂散文的写法有什么特点,“这比谈《滕王阁序》之类的文章要难,因为那是浓,这是淡;那是有法,这是无法。还是先由印象说起……像是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怎么说方便就怎么说。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语),可是意思却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总的一句话,不像坐在书桌前写的,像个白发过来人,冬晚坐在热炕头说的,虽然还有余热,却没有一点火气。”他的作品“寓繁于简,寓浓于淡,寓严整于松散,寓有法于无法。”张中行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他针对的是知堂后期散文,但很显然他的描述更符合知堂后期散文的特点。
刘绪源的《解读周作人》是第一部以周作人的散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率先对知堂后期散文进行了研究。他给予周作人的抄书之作比他前期散文更高的评价,通过实际的考察向我们表明,那些看起来黑压压一片的抄书之作其实也是曲尽其妙的。他进而说:“周作人更多的是在别人的书中寻找自己,借别人的书说自己的话,所以抄书也成了他‘表现自我’的极好途径。他的文章大多是夹叙夹议的,有时候,所抄之书成了他文中‘叙’的内容,与他的‘议’天然融成了一体。”周作人追求简单、本色,但人们往往看重周较多地运用了技巧的文章,如早期锋芒较露的杂文,或那些色彩比较鲜亮的小品。何以如此?作者的分析是精辟的:“只因为它们更好评、更好看,更能让人一下子读出好处来。但事实上,知堂散文更精彩的部分,真正能代表他的最高艺术追求的,恰恰不是这一部分,而是那些更平淡朴素,一眼望去更找不到好处的本色文章。——一旦你改变了过去的看惯漂亮衣服的阅读目光,真正从这些没有外在魅力的本色文章中发现了人的魅力,那么,你就将获得更为深邃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散文艺术的天地里,你也会有‘一览众山小’的真切体验。”我在《知堂小品散文的文体研究》(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一文中, 描述了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文体发展史,并从语体、总体风格、趣味、语言、抄书诸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我把知堂抄书之作的文体称为“抄书体”,认为其代表着他文体创造的最高成就。文章列专节讨论了抄书与抄书体的关系,指出周的抄书方式的源头是中国传统的笔记。
肯定知堂后期散文意义重大。周作人早被称为“小品文之王”,不过以前人们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建立在视其前期的《故乡的野菜》、《乌篷船》等为代表作的基础上的。因此,给予周氏后期文章以更高的评价,必然会带来周作人研究格局的调整;鉴于周作人散文的杰出地位,这样也势必会对现代散文史的研究产生冲击,并且带来某些理论突破。文体的价值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周作人的后期散文与他的一段思想历程和人生道路密切相联,与新文学史上已形成深厚传统的散文趣味相悖,所以其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并不容易。
“周作人热”大约初兴于1985年前后,从那时到现在经久不衰,事实上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作家热。周作人的作品对世俗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然而却能在这个喜新厌旧已经成为风尚的时代里热起来,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不知假如生前寂寥、失意的周作人死后有知,会作何感想?
“周作人热”的持续,研究的推进,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对周作人和周作人研究最激烈的否定意见出自何满子的杂感《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注:1995年7月20日《文汇报》,8月4 日《文艺报》曾转载。)。文章对周作人先从人格到“文格”作了全盘否定:“要谈人,首先要定个性。周作人嘛,首先第一他是一个汉奸,必须郑重其事地说;这不仅是个政治定性,也是人格定性。如果‘风格即人’这命题不错的话,那么这个定性也是文格的定性,其他的这样那样都得靠边站。”进而这样评论周作人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周作人做汉奸,不是日寇占领北平后才一时突然堕落。早的不说,从1923年和鲁迅反目起,他当汉奸的道路已经铸定了,或脚步已经跨出。”周作人“从此便把鲁迅作为他要压倒、超过、反对的‘终极关怀’。一直到死,周作人心目中都把鲁迅当作头号敌人而加以损害。”他骂周作人夫妇为“一张床上睡的两个同样的货”,“狼狈为奸”的两个“枭獍”,“泼妇孽弟”,等等。对周作人研究也是一棍子打倒:“研究周作人如今十分时髦,论文连篇累牍,专著一本接一本,剖文风,抉文心,屎里觅道,臀上贴金,探幽寻微,妙不可言。或拈出‘苦涩’的妙谛,或颂为‘一览众山小’;或曰有此‘真赏’才是‘斯文未坠’。舔嘴咂舌,唾溢涎滴。”文章里还有很多类似的骂街式的话,有些观点如说周作人在兄弟失和之时已经踏出了当汉奸的脚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袁良骏也对“周作人热”甚为不满,发表《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注:1996年3月28日《光明日报》。)、《周作人余谈》(注:1996年5月 8日《北京日报》。)。两文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外,既没有新观点也没有新材料。然而,在一个广泛传播的新闻媒体上赫然写着前一篇文章那样的题目,只能煽动人们的感情,给本来就深受非学术因素干扰的周作人研究再添新的障碍。作者列举一些不正常现象,由于缺乏具体的分析,很容易导致不熟悉情况的人把帐算在周作人研究者的头上。作者的口气是新闻发言人式的,但文章中却有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说周作人从监狱中出来是“沾了乃兄鲁迅的光,人民政府让他‘保外就医’”,说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绍兴同乡”。
解志熙的《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注:《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 从一个角度对周作人研究提出批评。他认为,“近年来文化批评的一个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失去了应有的历史分寸感,以至于有意无意地用文化的尺度来淡化或代替历史的原则”,“犯了非历史而唯文化的错误”。“这在近年来的周作人研究中有突出的表现。”为此,他向舒芜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陈思和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董炳月的《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2年10月号。)发难。舒芜认为传统的中庸主义是周作人悲剧的基本原因,解文指出,“这其实是一种以文化宿命论形式出现的文化决定论”。他把这个具体的观点概括为“‘唯文化’批评”,进而质问:这种批评“又能比历史决定论和庸俗社会学好多少呢?”接着,他又对陈、董二人的文章进行挞伐。他说,从主观方面,他们刻意强调周作人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独立身分”及其附逆行径中的“‘文化因素’的独立性”。他们只是在“客观”、“科学”的名义下,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证明:“客观”的一切,从历史传统到社会现实,都似乎不可抗拒地决定了周作人除了当汉奸别无选择,因而一切责任都应由这“客观”负责。因此,他们都“有意夸大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刻意抬高文化的地位来代替历史的尺度,试图以文化来淡化社会现实和政治及道德等历史性因素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被视为完全消极以至于有害的东西),遂把文化批评推向了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极端。”解氏最后表明了他的民族至上的价值观。本文的一些观点是值得周作人研究者重视的,但作者的火气太盛,口气是审判式的,对别人观点的引用也有片面之嫌。
周作人研究的价值何在呢?徐中玉认为研究周作人主要应该研究他的汉奸问题,以惩前毖后。他说:“我认为除掉或非常淡化他晚年投敌这一段,又过分吹捧他早年什么什么成绩如何重要之类的做法,会给今天读者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认为周作人仍是一位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这已模糊了对一个学者、作家评价上至少应有的界限:爱国的还是民族危急关头变节投敌为虎为伥的。”(注:《我看周作人》,1995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我们同意“除掉或非常淡化”、 “过分吹捧”之类都是错误的,应该摒弃,“进步思想家”的头衔也可以扣发,可是为什么连周作人的文学大家的身份也不予承认呢?徐中玉的观点有一定的典型性,我又想到了曾镇南评周作人的话:“他留给后人的,主要是历史的鉴戒。正确评价这个人物,就必须抓住这个大关节,推源其失节的根由,以垂训后世。”(注:《略释周作人失节之“谜”》,1991年12月21日《文艺报》。)
简单地否定周作人反映了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儒家伦理道德往往把个人的道德节操看作衡量一个价值的绝对标准,像孟子就曾对杨朱、墨翟一骂了之。在文学批评上,往往出现“因人废文”或“因人重文”的现象。在西方,海德格尔在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时发表过亲纳粹主义的就职演说,且是一个激烈的反犹主义者,庞德于二战爆发时在罗马电台发表过数百次抨击美国的广播讲话。他们的政治行为都曾受到惩罚,然而这些似乎并不妨碍人们去理解海德格尔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欣赏庞德卓越的诗艺,也没有听说有谁怀疑他们的大哲学家、大诗人的身份;可是我们的不少人偏偏要把孩子和污水一起泼掉。
在本文讨论的三个问题中,评论周作人的价值标准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另外两个问题的研究就谈不上了。对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上地位和后期散文价值的肯定是理解周作人的两个重要角度,然而意义并不仅仅在此。周作人代表着与主流文化不同的世界观、文学价值观、思维方式,这为我们总结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周作人是一个敏感的历史人物,问题又是敏感的问题,话难免说重了或说轻了,这就格外需要宽容和理解。
收稿日期:1998—5—12
标签:周作人论文; 读书论文; 散文论文; 周作人的是非功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鲁迅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论文;
